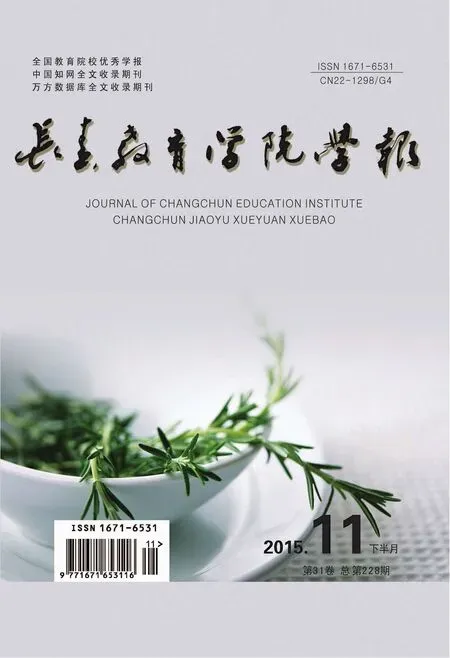浅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婚恋的矛盾性
——以鲁迅、郭沫若为例
叶雅风,邓利群
浅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婚恋的矛盾性
——以鲁迅、郭沫若为例
叶雅风,邓利群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鲁迅和郭沫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方面提倡婚恋自由,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践行传统婚姻模式。本文以鲁迅、郭沫若面对婚恋时的言行矛盾为切入点,在对深层原因的分析中,揭示五四时期婚恋自由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五四时期;婚恋;矛盾
婚恋自由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实践自己的婚恋自由理想,但是,婚恋自由从提倡到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当先进青年试图从家族、父母的手中获得婚恋的权利时,他们一方面受着新观念的影响,对配偶提出学识、爱情、革命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标准;另一方面面对传统婚姻又往往迟疑和犹豫,以致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矛盾。本文通过对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代表——鲁迅和郭沫若婚恋情况的解读,以折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婚恋自由的矛盾心路历程。
一、婚恋表现形式的复杂性
(一)面对包办婚姻
鲁迅与郭沫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是婚恋自由的倡导者。当他们不约而同面临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时,鲁迅选择了妥协,郭沫若选择了逃离。
1906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在母亲的催促下,回家与朱安成婚。结婚四日后,就以“不能荒废学业”为理由,与二弟回日本。在接受这段婚姻时,鲁迅是痛苦的,因为当时他已受到新文化的熏陶。以鲁迅对婚姻的认识,这桩婚姻无论从外在形式还是婚礼程式都是传统的。在反抗无效后,说朱安只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他无法拒绝;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朱安的痛苦,最终默默选择“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1]甚至在此后二十多年自我恪守贞节。
1912年,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完婚。新婚之夜,看到张琼华是个容貌平平的旧式女子,失望之余的郭沫若不与她同房,并在五日后逃离家乡。郭沫若在日本成立新家庭后,长兄郭开文曾问及对张琼华的解决方法,郭沫若回信说:“离掉张氏,我思想没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2]自此张琼华独处于封建婚约的牢笼中,做郭家一世的客。
婚恋自由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可是,鲁迅和郭沫若最终都接受了这段旧式包办婚姻。在举行完结婚仪式后,无论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还是“不新不旧的暧昧态度”,鲁迅与郭沫若均未解除包办婚姻,这与他们所提倡的婚恋自由观念是相矛盾的。当然,这也体现了在新旧婚姻冲突中的无奈,因为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吃人的社会舆论下,被休的女子无路可走。朱安和张琼华都是旧式女子,既没有自立的经济能力,也没有重嫁的胆量,离婚可能不是给她们带来自由,而是陷入更悲惨的深渊。
(二)面对爱情
当追求自由爱情成为知识阶层的普遍现象时,鲁迅和郭沫若也实践着恋爱自由的观念,找到了各自心中的理想爱情对象。那么,两人爱情的归宿是什么呢?鲁迅选择了与许广平“有实无名”的新式婚姻,郭沫若选择了先后与安娜、于立群的重婚。
1926年,鲁迅与许广平结合,结束了“陪着做一世牺牲”的承诺,也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禁欲和性压抑状态。在与许广平的恋情发展中,相对于许广平的主动、热情,鲁迅却表现出疑虑、胆怯和矛盾:“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3]他宣称反抗,却未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终其一生,鲁迅始终未解除与朱安的“旧式婚姻”,只给许广平一个有实无名的“新式婚姻”。换言之,朱安是鲁迅世俗、礼仪上的妻子,许广平虽是实际的妻子,但没有世俗的名分。
1916年,郭沫若遇到了面容姣好,并有日本贵族后裔身份的安娜,他得到了安娜的爱情,并结婚了。他们共同生活了21年,养育了5个孩子。对于在苦难中始终支持他创作的安娜,郭沫若应该视若珍宝,永远忠诚才对,但他没有,反而时时有“拈花惹草”。甚至在1937年,郭沫若抛妇别雏回国,与于立群一见如故,并在1939年再次结婚,将安娜和子女抛至九霄云外。
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4]五四时期婚恋自由观中的婚姻道德基础与恩格斯所说是类似的,人类婚姻的道德基础从旧式的义务到新式的爱情,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知识分子们呼吁爱情是婚姻的道德基础,要破除不自由、无爱情的传统婚姻。作为新式婚姻的道德基础——爱情是有排他性的,所以它促成了现代婚姻模式——一夫一妻制。鲁迅与许广平的“有实无名”的婚姻,郭沫若一次又一次的婚姻,也同样背离了他们所提倡的婚恋自由的思想,成了他们自己所反对的那种多妻者。
二、婚恋矛盾的深层原因
鲁迅和郭沫若身处中国社会新旧思想冲击的时期,他们在婚恋思想和行动上的矛盾,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早年经历以及不自觉承继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
(一)早年的生活环境
周家是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但到鲁迅父亲手里已经败落,后来甚至到破产的地步,少年的鲁迅常常出入当铺和药铺之间。作为家中长子,鲁迅有承担家庭门面的义务,家境富裕的朱家不管在门面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能对周家有所帮助。为了家族的利益,鲁迅在经历了抗拒→改造→逃避过程后,最终接受了与朱安的婚姻。
郭沫若出自商贾家庭,家境殷实,所以在幼年充满自由浪漫的幻想,不会去理解痛苦的人生。他走出家门后,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影响,成为无所羁绊、常动不息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以,郭沫若的三次婚姻无一不是其泛爱和随性的表现。
(二)对传统文化的承继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但不可否认他们自身潜藏着更多传统文化的因子。
1.其一,儒家传统文化的伦理核心是“仁”,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外化为 “孝”和“悌”,孝悌观念在鲁迅心中形成深厚的积淀,并形成无意识的自觉行为。接受朱安,一方面是不忍让母亲伤心,另一方面也考虑到自己长年在外,需要一个人替自己尽孝。将妻子的角色定位为替自己孝顺母亲,可见传统文化在鲁迅身上的强烈表现。这也是数千年伦理价值体系的致命缺陷:它在人们还没意识自己是“人”的时候,就先意识自己是父亲和儿子,妻子和丈夫……其二,儒家倡导道德人生,提倡人道,这些观念成为构建鲁迅人生观的主要因素。鲁迅同情弱者,他一生未同朱安解除婚姻。他也试图唤醒弱者,所以在抗拒这段婚姻的同时也提出要求朱安“放脚”“进学堂学习”。即使在与许广平相爱时,始终没有公开和许广平举行婚礼,甚至把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住在二楼,对外说许广平是他的助手。种种行为表明,在外在形式上,他始终恪守着旧文化、旧道德的要求。
鲁迅与朱安旧式婚姻的维持,得到了传统道德群体的许可,与许广平同居式的结合,又得到了新道德群体的认同。鲁迅的婚恋生活体现了新旧婚恋观念冲突下的荒诞。
2.郭沫若童年生活在巴蜀之地,除了受到儒家文化熏陶,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所以他的身上兼具儒道互补的处世哲学。在五四时期新思潮的冲击下,郭沫若作为爱国的有志青年,提出人的解放与自由,包括妇女的解放。但他满腔热情提倡妇女解放却又没弄清什么是真正的女性解放,所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郭沫若只是通过几首诗歌、几篇文章来口号式地提倡女性解放。正如他追求个性主义一样,他的个性主义中更多包含有个人主义特征。他从男性角度出发,把女性看成美的欣赏物。在第一次婚姻中,仅凭揭盖一瞥,便认定了张琼华的“黑猫”外貌而逃离了家庭,并认为这次婚姻是“隔着麻布口袋买猫子,交订要白的,拿回家去却是黑的”。[5]安娜美丽高雅,有学识且爱情至上,符合郭沫若心目中旧式婚姻的“佳人”形象,两人一见钟情。于立群性格独立,对革命充满激情,这让刚回国,身处如火如荼战争中的郭沫若“一见如故”。所以,郭沫若是矛盾的,他提出女性解放,却又一次次伤害妇女;他主张女性解放,却不愿在行动上为张琼华做些什么;他提倡女性平等,却让自己的家庭成为禁锢女性的枷锁(婚后的安娜再无少女时代的追求和理想)。郭沫若的呐喊是朦胧的、茫然的,轻视女性、泛爱和男权主义等封建遗风使他始终没有把女性放在婚恋自由和平等的地位。
由此可见,鲁迅和郭沫若都试图否定中国道德传统,自己却又摆脱不了道德传统的虚伪;他们批判传统劣根性,却又无法彻底根除自己身上的传统劣根性。
党员、团员的党性教育中,注重发挥学生的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重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综合能力培养,发挥学生党员、团员的骨干作用,使其成为其他学生学习、生活和服务社会的先进典范,进而激发他们相互学习、自发向上。
学生会是学生实行自我管理、服务和教育的重要组织。学校各级党团组织、系部应积极支持、指导学生会依法、依规行使职能和组织开展活动,充分发挥学生会这一群众性组织的优势,坚持学生会来自于学生、服务于学生的宗旨,使其成为学生开展自我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开展师生交流的重要桥梁。
社团是学生根据共同的兴趣、特长等自发结成的学生团体,是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政干部、任课教师等可根据自己的特长参与对社团的指导与服务,鼓励和引导学生自主开展社会调查、创业培训、义演义卖、才能展示等实践活动,激发其自信心和进取心。
班级是学生组织的最基本形式,也是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主要载体。辅导员、班主任应指导学生进行班级建设,通过组建优秀的班干部队伍,制定详尽可行的班规,定期召开主题班会,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等,激发每个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班级荣誉感,营造和谐、有序、积极、进取的班级氛围和凝聚力。
寝室是学生群体中关系最密切、互动最频繁、影响最深远、结构最牢固的组织。学工、保卫等职能部门和教学系部等应着力于服务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大力开展寝室制度建设和寝室文化建设,合力做好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工作。包括宿管员等在内的教育工作者都应参与到寝室制度建设和寝室文化建设中来,调动和激发学生参与寝室管理与服务的热情,引导他们在自觉规范言行、自觉服务同学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
[1]侯志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合力育人机制的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
[2]储德峰.高校“大思政”教育模式的特征及理念[J].中国高等教育,2012( 20).
[3]杨建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贺正
I209
:A
:167-6531(2015)22-0008-02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大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合力育人探究》(课题编号:2014B420)的中期研究成果
叶雅风/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福建福州350002);邓利群/通讯作者,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福建福州3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