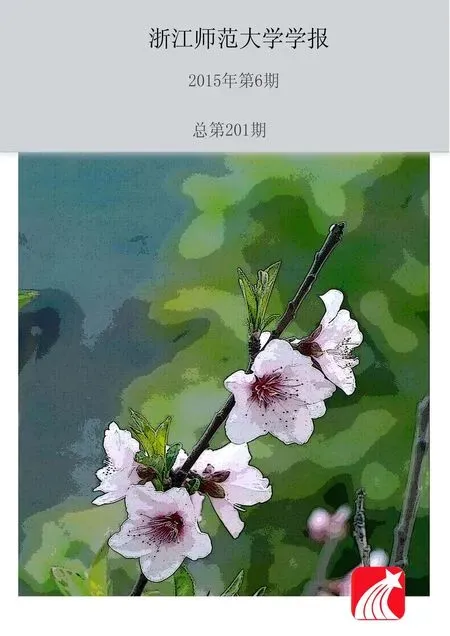关于生态翻译学理论建构的三点思考
张小丽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艺术系,浙江 杭州 311231)*
关于生态翻译学理论建构的三点思考
张小丽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艺术系,浙江 杭州 311231)*
摘要:生态翻译学自创立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原因有二:一是它受惠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是中国学者首创的翻译学理论;二是在全球生态浪潮下,它将翻译研究与生态学研究合二为一,可谓与时俱进。但生态翻译学在译学理论建构上仍然有三个突出问题值得思考:一是生态翻译学的术语缺少稳定的解释力,严谨性有待商榷;二是能否将进化论作为其哲学理据,同为哲学理据的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之重要性又如何体现;三是作为生态翻译学核心研究方法的相似类比推理是一种或然性推理,可靠性有待提升。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生态学;译学理论建设
公元前55年,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提出语篇意义要大于单词意义,提倡“演说家”式的翻译,即译者创造性质的意译或活译,这是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1]从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哲罗姆等古代翻译理论家到现代的纽马克、奈达、雅克布森、德里达,西方翻译理论家不胜枚举,翻译理论层出不穷。译学领域从最初的语文学研究范式到之后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再到翻译研究的解构主义和多元系统理论,西方翻译研究的风向标频繁转向。在理论建构方面,中国“拿来主义”的历史悠久,翻译理论方面也不例外,国际译坛很少听到中国译界学者的声音。所以,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所作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一文格外引人注目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全球生态浪潮的大背景下,胡氏翻译学的出现成为国内翻译理论研究新的“兴奋点”。生态学时代是一个众神喧哗、多元共存的时代,是一个理性与情性这对千年怨偶相互牵手的时代。[2]
2006年,胡教授在“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构建国际会议”上宣读“Understanding Eco-Translatology”(生态翻译学诠释)一文,将翻译适应选择论深化为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十五年来,生态翻译学研究呈现蓬勃的发展态势:以此为理论框架的博士硕士论文超过80篇,相关的应用研究已逾400篇,生态翻译学国际研讨会每年一次,已连续召开五届。第五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2015年6月在台湾长荣大学举行。胡庚申教授的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也在2013年问世,著作对生态翻译学作出了全景式描述,对其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进行了全方位论述,是展示生态翻译学研究成果的最重要著作。
翻译学本质上是多语种和跨学科的(by its nature it is multilingual and also interdisciplinary) 。[3]胡庚申教授创立的生态翻译学充分利用供体——生态学作为显学的优势,从生态学视角推进翻译研究的理论创新与深化。生态翻译学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明确的翻译原则和极强的翻译实践指导意义。它结合东方哲学的智慧,提倡生态整体论,直面中国翻译界缺乏理论创新的困境,用独特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原则和现象作出解释,显示出较强的理论张力与价值。胡庚申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独树一帜,百折不挠,其颇具创新性的译学理论使东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平等对话成为一种可能。但另一方面,自生态翻译学提出以来,译界一直争议不断:其中一些问题是由于该学说在初创期外界对其理解不透引起的,[4-5]而另一些反驳和争议则是由于该学说本身不完善导致的,[6-7]胡庚申教授也对部分质疑进行了回应。[8]随着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有必要在全球化视野下考察生态学与各学科的交互现状,可以发现生态学与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仍然困难重重。任何一种新的理论都有不完备甚至理论盲点,生态翻译学也不例外,其术语体系、复杂的哲学理据和相似类比的研究方法仍然值得商榷,有待完善。
一、生态翻译学之跨界的术语体系:重要性及不足
翻译理论体系必须具有一套严密科学的翻译理论话语,尤以术语为代表。中国译界的“求真说”“神韵说”“化境说”“神似说”等译学理论无不以神秘的、随感式的研究方式出现,且一直处在“零敲碎打”的阶段,缺乏对整个翻译系统的“宏大叙事”。其中,翻译术语体系的匮乏是中国翻译理论无法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生态翻译学通过概念移植和跨学科类比尝试性建立一整套翻译术语体系。这套术语体系融合了生态学术语的特点,创建了“选择性适应”“适应性选择”“生态移植”“多元共生”“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群落”“事后追惩”“生存”“生态”和“三维转换”等术语。这些术语新颖、独特、辨识度高。然而,在明晰性、准确性和专业性上仍然有待加强,在解释翻译过程和描述翻译现象时,术语使用不够严谨。以“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核心术语为例,它被定义为译者、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近几年,它又拓宽为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在内的、除译者以外的所有因素。[9]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对译文产生过程的解释是,第一阶段,适应——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或者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第二阶段,选择——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就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选择,[10]而选择结果的累积就产生了译文。在第一阶段中,胡庚申教授强调的是原语翻译生态环境的客观因素,是物化的一面——但如果这样理解,作为客观的、物化的“环境”又如何具有主动选择权,从而选择合适的译者呢?也许是认识到这一点的局限,胡教授随即将其转换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提法。但问题是,译者被翻译生态环境所选择≠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译者的地位从“被选择”的对象到“主动适应”的主观能动者之间存在天壤之别;译文产生的第二阶段是“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即是译者,即“译者选择译文”,既然“翻译生态环境”是与“译者”相对的概念,如何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选择,成为翻译生态环境的替代词呢?
生态环境这一术语来自生态学,它是影响人类生活、生产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总和,是相对独立于人类世界的术语概念,是一种客体化的概念(objectify)形式。离开了生态学这个语境,两者概念的嫁接就只能以隐喻为认知机制,缺乏生态学科专业的概念系统之下,是无法厘定“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生态翻译学中的术语系统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性和较强的辨识度,但其存在的概念边界含混、术语概念的任意替换以及原始定义与实际术语运用自相矛盾等问题,值得商榷。与“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术语类似的还有“共生互动”“生存”“生命”“生态”等概念,它们的定义过于笼统,缺少专业标记性和稳定的解释力。
当然,翻译跨学科研究的术语借用并非不可,翻译研究因从语言学、文学、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借用术语而获得丰富的术语,[11]但翻译跨学科研究主要借鉴的还是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与方法。不同学科的理论话语体系有其特定的生存和使用语境,离开了这个语境,这些术语的使用就要格外小心,否则会造成理论话语系统内部的抵牾。若借用某些术语,便要在新的翻译学语境下重新定义并将其纳入翻译学科理论话语的系统中,使其可以适存并利于本学科理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在这个吸纳过程中,要涉及不同程度的术语改造,使之能产生与翻译学语境融合的可能。新的术语必须接受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考验,移植的最终产物不能是“混合物”,而应是“化和物”。[12]
韩礼德认为,语言具有概念、人际和文本三大主要功能。就翻译领域而言,翻译理论话语在概念功能方面要能以简洁的语言清晰表述翻译研究的多层次内容,能对译者的真实经验世界和内心世界(心理特征与过程)进行关照;在人际功能方面,翻译理论话语要能解释主体间意义的跨语言理解与生成过程,特别是能描述作者、译者和读者等交际主体之间的跨文化人际关系;在文本功能方面,翻译理论话语应当以文本的衔接性、连贯性和信息性为特征,考虑交际者的可接受性,同时考虑其情境性和互文性特征。笔者认为,生态翻译学的术语建构基于隐喻和转意之上,因此其术语系统在描述作者、译者、读者等交际主体间关系的人际功能方面较强,但在概念功能方面欠清晰,部分跨学科术语缺少科学性,可接受性较弱。
二、生态翻译学之哲学理据:困惑及潜力
哲学理据是翻译理论得以支撑的根本,是译学理论在哲学层面的基石。生态翻译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前期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哲学理据一直是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2006年8月,胡庚申教授在“翻译全球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构建”(Translating Global Cultures: Towards Inter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国际会议上提出“Eco-translatology”一词,之后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生态翻译学解读》一文,正式将翻译适应选择论深化为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改称“生态翻译学”。
翻译学的建立离不开哲学的视野,翻译理论涉及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符号学、社会学众多供体学科的边缘性,胡庚申教授认为达尔文的传世之作《物种起源》可以认为是生态学的先驱著作,其能成为生态学思想的伟大倡导者就在于他认为生物进化的原因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适应性的演进。[13]为此,以生物进化论为重要理论启示来源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和后续发展的生态翻译学是“同源”的,是一种继承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14]不过,从翻译适应选择论到生态翻译学,其哲学理据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前期的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后期的理论基础则为自然选择学说和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那么,进化论是否可以完全作为前期翻译适应选择论和后期生态翻译学的哲学基础呢?答案值得商榷。
首先,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不同。进化论强调自然观基础上的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其最大意义就在于让“绝对的人类中心说”成为过去。它克服了人类中心观念的盲目性,为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奠定了科学基础。[15]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和灵魂,它产生的结果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以及新物种的形成;而翻译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译者、译作、原作及其相关的翻译过程和翻译元素,其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影响翻译的多种因素及成因,研究“怎么译”“为什么这样译”,他们或关注翻译行为本身,或研究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可以说,翻译行为更多关注翻译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生物进化论则更关注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新物种的形成。
其次,生态学所属的自然学科与翻译学所在的人文学科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存在巨大差异。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进行人文科学领域的移植,不得不提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没有非常确切的事实表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16]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确将类比和隐喻的方式运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它用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定律诠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隐喻的逻辑前提就是事物或现象之间存在相似关系,因此,如果将两者进行类比,势必假设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同质性”和“同构性”,但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非生物界可比,其文化、道德、伦理和社会组织方式与自然界存在太多差异。将进化论运用于翻译学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将其基本规律以隐喻的方式类比翻译研究中诸多因素的相互牵制作用是创新、无可厚非的,但实指则不太理智。两者之间理论移植的可能或者说跨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应该主要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发”(inspiration)或借鉴,而不是机械的理论借用或类推。
第三,胡庚申教授撰文指出,生态翻译学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系统探讨翻译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生态智慧是生态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和思想依归。[17]生态翻译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东方智慧,这种中国式的对翻译的观察源自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This Chinese way of observing translation spring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about the universal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his- or her-environment)。[18]参加第二届生态翻译学会议的Radegundis Stolze女士还专门写了报道——《生态翻译学在中国》(Eco-translatology in China),认为生态翻译学是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等中国传统哲理为特征,这些由儒家、道家和佛家所提倡的生态翻译学理念成为翻译研究生态学视角的基础。[19]欧洲翻译协会对生态翻译学给予关注,对它持乐观态度,认为可以提供很多东西(have much to offer)。与西方译界对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关注程度相比,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相对较弱,就连胡庚申教授对此也语焉不详、泛泛而谈(Hu himself adduces the main principles of the ecological thought in fairly broad strokes)。[20]相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中很少涉及东方哲学对生态翻译学的具体影响。此外,当代生态学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之间关系如何,在生态翻译学理论架构中扮演何种角色,都是生态翻译学研究所欠缺的。中国古代生态智慧是生态翻译学的一大亮点,但这个哲学基础更多流于表面,在整个理论架构中缺少实质性的体现。同时,即使是将进化论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同时作为哲学基础,其作用也并非平分秋色;孰轻孰重,地位如何,都需要研究者将其分清。生态翻译学是基于翻译适应选择学说的基础建构的,将进化论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下,必然出现后者的“贬低”与“边缘化”。笔者认为,找准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与翻译理论建构的共振点和切合点、挖掘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研究价值、凸显东方文化“异质性”,从而塑造中国译学理论的民族认同,是生态翻译学在哲理层面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根本问题。
三、生态翻译学之方法论:相似类比的困境
西方文化注重演绎思维,东方文化注重类比思维。中国古代先人很早就用相对完备的符号类比推理系统写成了《周易》,流传至今。类比推理能将任意的对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推论,因此它不但可使不同种类事物的知识相互移植,而且有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特殊功能。相似类比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其基础和前提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学与生态学进行类比的前提是翻译活动与自然界存在的互联关系,即翻译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这一关联序列。[21]狭义的翻译活动的确是语言的转换,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又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属性,人类是自然存在物,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诚然,这一关系链中翻译活动与自然界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翻译、语言和文化都是人类活动的属性或现象,人类和自然界则是客观实体,“翻译—语言—文化”与“人类—自然界”分属于不同范畴,将其进行关联合乎情理,但将其作为翻译学与生态学相似类比的基础和前提则欠妥。此外,从翻译与自然界存在关联并不能归纳推断出适用于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亦适合于翻译活动研究。
相似类比推理是指两个或两类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同或相似的,而且已知其中的一个或一类对象还具有其他属性,从而推出另一对象也具有同样的其他属性的推理。[22]相似类比是生态翻译学跨学科研究得以存在的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基础,其概念移植的方法也建立在这一理据之上。运用相似类比推理能让类比对象的抽象概念形象化和具体化,但相似类比推理只能给出或然性推理,并且这种推理的根据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进行类比的两类事物之间,除同一性外,还具有差异性。事物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无法保证其他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就生态翻译学而言,虽然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存在较多相似性,如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互相影响和关联,都会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都存在“适应”“选择”“竞争”等现象,但应该看到,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然界生态系统以食物为核心要素形成“食物链”,促使物质和能量在整个系统内流动,翻译生态系统中却缺乏这样的核心要素。此外,自然生态系统中最关键的要素——生产者,具有排他性和独一性,生产者不可能同时又是消费者和分解者。而在翻译生态系统中,生产者具有双重指向性(bidirectionality),既指译者,又指作者,[23]作者提供原作,是翻译链中的发起者,译者以原作为根据提供译作,既可以认为是生产者(就读者而言),又可以认为是初级消费者(就原作者而言)。这种双重身份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是不存在的。既然翻译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存在如此本质性的差异,在考察翻译生态系统时使用“汰弱留强”“共生共存”这类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核心理念就值得商榷了。
相似类比推理属于归纳推理的一种,哲学家休谟曾对其客观性提出根本性质疑,认为归纳推理以自然齐一律和普遍因果律为基础,而两者并不具有客观真理性,只不过是出于人们的习惯性心理联想罢了,这就是著名的“休谟问题”。无独有偶,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也指出,类比推理可以“刺激人们的想象力图景,但没有科学解释所具有的那种说明问题的力量”。[24]生态翻译学将从属于人文学科的翻译学与从属于自然学科的生态学作相似类比,毋庸置疑需要使用更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但类比推理的结论可靠程度低,在科学研究上不能仅仅依靠类比就建立科学定律,还必须用其他方法补充。提高生态学与翻译学可靠性程度的方法是尽可能多地搜集和列举所比较对象的相同属性和本质属性,提高翻译学与生态学已知属性之间的相关程度。如果仅仅根据表面现象进行类推,就会犯“机械类比”的错误。
四、小结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译界学问家多,思想家少;理论实践者多,自创体系者少;在新世纪,中国学者固然仍有必要“照着说”,但更要有勇气“自己说”,让国际译界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生态翻译学的创新是东方生态智慧运用于翻译研究的结果,也是人文性强的中国传统翻译论为科学性强的西方翻译论提供滋养和互动的结果。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东方哲学有更多的人性深度和人文厚度。我们需要在东方哲学中找寻自性圆融的灵感,给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以新思维,在人类未来文化新价值中寻找新的文化契机。[25]东方哲学以生态之气韵给翻译以灵性,为其提供了译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即在翻译研究时注重系统观和整体观的运用,这是它与西方翻译理论最大的区别。
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生态学的翻译研究途径,属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跨界研究,是一种理论创新,但在理论建构中要更加突出东方元素,尤其是东方的生态整体论,而不是片面盲从适应选择学说。东方的生态智慧给予翻译研究更多哲学层面的思考,而西方生态学说的适应选择论在生态翻译学中更多的是方法论的指导。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二字,其喻指大于实指,在仔细分析跨学科及学科交叉的性质、模式和特征后,研究者应做到合理有效的借鉴、整合及利用。生态翻译学的术语建构仍然困难重重,很多术语缺少专业性和稳定的解释力。生态翻译学无法解决翻译学的所有问题,它和其他学派一样只能解决翻译学某些方面的问题。从这三点来说,从事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学者们,仍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杨建华.西方译学理论辑要[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4.
[2]贺爱军.知识系统图谱下的译者地位考量[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4):49-52.
[3]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
[4]王宏.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考辨[J].上海翻译,2011(4):10-11.
[5]王育平,吴志杰.超越“自然选择”、促进“文化多元”——试与胡庚申教授商榷[J].外国语文,2009(4):135-138.
[6]陈水平.生态翻译学的悖论——兼与胡庚申教授商榷[J].中国翻译,2014(2):68-73.
[7]苗福光,王莉娜.建构、质疑与未来:生态翻译学之生态[J].上海翻译,2014(2):77-82.
[8]胡庚申.对生态翻译学几个问题“商榷”的回应与建议[J].中国翻译,2014(6):86-89.
[9]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10]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4):90-95.
[11]Shuttleworth M, 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vi.
[12]李运兴.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J].外国语,1999(1):55-61.
[13]王如松,周鸿.人与生态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77.
[1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2010(4):62-67.
[15]程倩春.论达尔文进化论的生态思想及其意义[J].学术交流,2011(11):5-8.
[16]侯波.斯宾塞社会进化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之考异[J].求索,2009(12):91-93.
[17]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异”与“新”[J],中国外语,2014(5):104-111.
[18]Dollerup C. “A New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Eco-translatology”[C]// In Hu, Gengshen(eds.). Journal of Eco-Translatolog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1, 16-17.
[19]Radegundis S. Eco-translatology in China[N/EB]. EST Newsletter,2011(39):13-14.http://issuu.com/est.newsletter/docs/est.newsletter_39_2011/22.
[20]Robinson D. “Eco-Translatology and the Mencian Four Shoots”[C]//Journal of Eco-Translatolog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2, 78-86.
[2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4.
[22]徐锦中.逻辑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180.
[23]刘国兵.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外语教学,2011(3):97-100.
[24]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1.
[25]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475.
(责任编辑傅新忠)
Three Reflec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Translatology
ZHANG Xiaoli
(TourismCollegeofZhejiang,Hangzhou311231,China)
Abstract:Eco-translatology has receiv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for two reasons: first, it was initiated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eco-wisdom in ancient China; second, it combines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ecology, thus keeping pace with the recent ecological trend of thought globally. However, there are three questions which call for further reflection, namely, the terms of eco-translatology are not scientific enough and lack of stable explanatory power; Whether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how important is ancient Chinese eco-wisdom? As the core research method, analogy is a kind of probability inference, and its reliabi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eco-translatology; ecology; theory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5)06-0073-06
基金项目: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青年重点课题“五四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研究——生态翻译学视角”(2014KYZD05)
作者简介:张小丽(1981-),女,浙江萧山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艺术系讲师,文学硕士。
收稿日期:2015-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