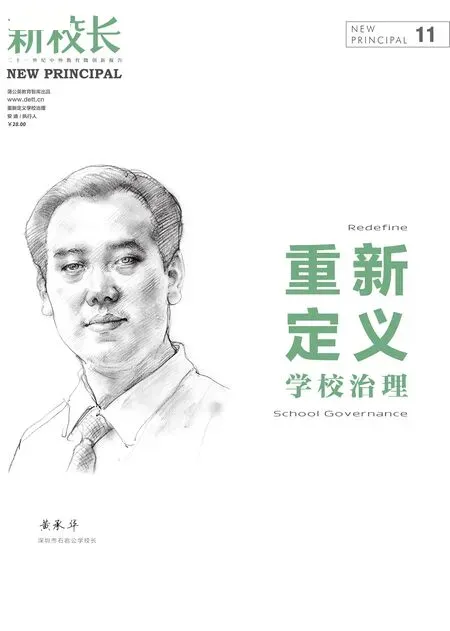观点:亮点与欠缺
文 / 熊丙奇

按照教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要求,到2015年全国全面形成“一校一章程”。岁末年初,北京十一学校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北京市十一学校章程》。这份由100多位教师代表以不记名方式高票通过的章程,在很多人看来似乎要“革”了校长的命——章程第六条规定,教代会每年8月底对校长进行信任投票,采取无记名投票,并当场公布投票结果。达不到60%的信任票,校长必须自行辞职;达到60%但连续3年未达80%时,校长也必须自行辞职。而第七条则规定,教代会代表20人及以上提议,可临时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提请对校长的弹劾或对有关政策方案修改的建议议程,经全体代表60%以上同意后,方可启动弹劾校长或修订政策方案的程序。
我国《教育法》规定,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有组织机构和章程。但长期以来,我国学校没有章程,这导致学校办学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政府部门可越权干预学校办学,而学校行政办学也有很大的随意性,教师和学生在学校治理中,缺乏知情、参与、表达、决策权利,教育法律法规的落实并不理想。
既然制订章程目的在于依法治教,让学校自主办学,实行现代治理,办出个性和特色,那么,在制订章程时,就必须解决当前存在于教育管理、学校办学中的行政化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学校在制订章程时,基本采取的是行政程序——由学校行政主导制订,再提交上级行政部门审批,然后发布。这种章程,从本质上说,只是行政规章,法律效力有限,很难成为学校依法治校的法律文本。
十一学校的章程,也有这方面的欠缺。舆论关注具体条款的“亮点”没有错,可以说,从“教师可以弹劾校长”角度看,这是迄今为止,包括已经颁布的大学章程在内,力度最大的学校章程。但必须指出的是,其制订的程序,也和其他学校颁布的章程一样。因此,这一章程所具的法律效力还很有限,基调还是学校内部的行政规定。
学校的章程,应该着重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举办者和办学的关系,对于公办学校来说,就是政府和学校办学者的关系。二是明确学校内部治理的结构,即明晰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社会机构的关系。如果前者的关系已经明确,那么,章程着重解决后者。
我国学校办学,上述两方面关系其实都没有明晰——在政府和学校之间,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要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在学校内部,缺乏现代治理结构。因此,这两方面问题都必须解决。这也就决定了学校章程不能由学校起草制订,提交上级行政部门审批。一方面,学校无法要求行政部门放权,即使章程明确了学校有哪些自主办学权,行政部门也审核、通过了章程,可行政部门不执行,谁来监督行政部门?另一方面,作为学校内部的规章,其他社会机构会遵守吗?具有法律效力的学校章程,应该得到全社会遵守,而不是学校的“家规”。
在发达国家,学校章程的制订,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立法机构讨论、审议,这适用于学校初创时期,立法审议,最主要的是解决政府(举办者)和学校的权责关系;另一种方式是,学校获得“特许”,自主办学,在自主办学权限范围内,制订学校运行的章程,亦称学校内部立法。
我国不少人认为,学校章程,就应该是学校内部立法,通过教代会审议,提交上级部门审批通过。但这忽视了两个基本现实。其一,我国学校并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学校内部立法缺乏前提和基础。其二,学校的教代会,也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并非全体教职工民主选举代表参加。
十一学校制订学校章程,应该说,在校内实行了民主决策,让教职工充分表达意见,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却无法回避学校并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这一根本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学校就难以成为自主办学的主体,依法治校就存在很大的隐患。
“一校一章程”,这是依法治教的关键。要把这一工作做好,在笔者看来,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国家层面,制订学校法,通过学校法,明晰政府、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然后在学校法框架之下,制订学校章程,这就理顺了政府授权、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早在2012年7月,教育部下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就提到要开展学校法的调研起草工作,依法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制度。并明确“以公办学校财政拨款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为重点,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保障教师和学生的民主管理权”。希望能加快学校法立法的进程。二是在没有出台学校法的情况下,将每所学校的章程,纳入地方立法程序,即学校的章程,在经过行政部门审批后,还要提交人大讨论、审议,以让学校章程真正成为学校依法治校的“最高宪章”。总之,要做到依法治教,必须按法律办事,要用法治思维来制订学校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