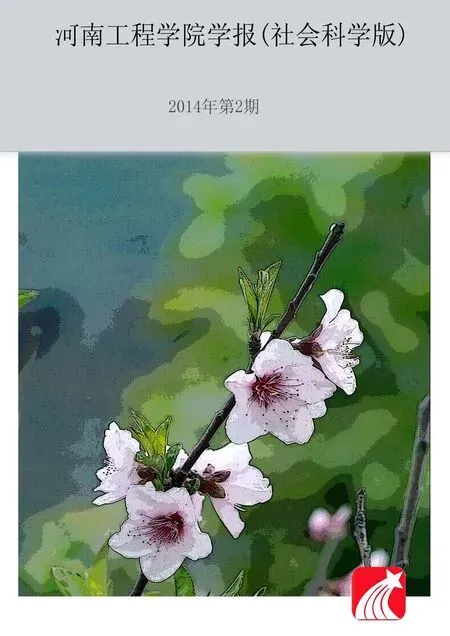论《管子》的道德修养思想
王 辉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道德修养是个体成就德性自我的中心环节,在中国古代通常与人性问题紧密相连。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仁义礼智根植于心,个体只要明心见性、存心知性,就可实现道德圆满,确证道德自我;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一切善行都反于人之本性,个体只有习行礼法,化性起伪,方可完成道德迁善,成就德性自我。《管子》则一改儒家人性善恶二分的致思路向,从人性之真出发,指出人性既包括静之心性又包括趋利避害之情性,个体只有在以心知道、自省其过、谨禁微邪的德性修养中以心性统御情性,才能达至个体德性生命的圆融,成就德性自我。
一、《管子》道德修养的理论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股由关注宗教之天转向现世之人的人文主义思潮,各派思想家开始试图从人性角度解释与解决社会问题,构建自己的道德体系。孟、荀虽然在人性论上表现为善恶的截然有别,但他们道德修养的价值旨归并没有太大差别,均是为了修身达仁。《管子》则与他们有着明显的不同:不仅在人性论上讲求辩证的人性之真,而且在道德修养的价值旨归上表现为修身达道。道在《管子》这里既是宇宙万物得以生成与持存的本原、本根,又代表着宇宙世界之生生不息的秩序,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这种秩序即指个体生命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统一。
《管子》认为,个体生命由形体与精神两部分组成,是天地“和合”的产物,“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1]945。这里的“和”,是指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协和、身与心的谐调。身心和调,个体生命就得以生成、持存;身心失调,个体生命就可能受损、死亡。也就是说,个体生命之所以得以生成与持存,在于人的精神与形体、身与心处于一种融洽、协调的状态或境界。然而,“凡人之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1]947。由于喜怒忧患的情性作祟,个体生命这种内在平衡有序极易被打破,从和谐走向混乱。
《管子》在《禁藏》篇中对人之情性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1]1012“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1]1015这里的“情”,实际上是指人之趋利避害之情性,它是人类经济生产行为的动力之源,可以激发人追逐物质利益的欲望,无论是贵者还是贱者,均要受其支配。商人不顾“千仞之山”而“倍道兼行,夜以继日”,渔人无视“海深万仞”而“就波逆流,乘危百里”,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利之所在”,而实质上是人之情性的自然表露,不可阻逆。然而,人欲富、欲贵、欲尊、欲显等情性显然是处于自发状态,如果不加任何约束,任其随意发展,整个社会就极有可能形成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局面,成为个体利益博弈的争斗场,从而危及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
可见,人之情性既是人的行动动力,具有肯定性的一面,又是人类之恶的发端,具有否定性的一面,故而不可对之简单地加以窒灭、去除,而要合理地加以顺导、规约。具体而言,人之情性作为客观事实存在,虽不可人为地完全否定之,但可以合理疏导与调控之,使之在合宜的限度内畅行,如此就可避免恶行的出现,实现个体生命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显然这种调控不能依靠趋利避害之情性自身的力量,因为它属于人生而具有的自然冲动,难以克服自身趋恶的可能性。所以,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即礼义的规约就显得极为重要:“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也。”[1]568不可否认,《管子》在此把道德归于智者贤人有其思想的局限性,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管子》没有把道德的起源归于性善论之良知、良能,也没有从宗教之天中引出道德,而是明确提出道德产生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这无疑是十分现实且深刻的。
不过道德规范作为普遍的当然之则总是超越并外在于个体,它只有能为个体自觉自愿接受并化为自律性行为,才能起到其应有的效用。而这一过程的完成自然离不开心的理性之思与内在的心性修养。《管子》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1]758心作为精神性存在,处于至高无上的君位;九窍等身体器官作为物质性存在,则处于相对低下的官位。前者实质上就是指发于心的心性,后者则是指动于身的情性。在此,心显然要高于身,身必然要从于心。心性如果能够“处其道”,处于合宜的位置或状态,情性就会“循理”,有序运行,达至身心和调,形神合一。把此推之于社会领域,个体如果都以心性统御情性,遵道而行,依理而动,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将降至最小乃至消除,尔虞我诈的混乱局面也就会消失,从而实现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
然而,如何使人之情性复归于静之心性呢?《管子》认为,学诗、习乐、守礼是重要的解决方法。诗可把人类之道传输到人的内心,消除怒气;乐可通过悠扬的乐调抚慰人的内心,去除忧愁;礼可提高人们的道德责任意识,去除骄奢淫逸。一旦人们学诗、习乐、守礼,就可在内保持尊敬之情,向外显出敬畏之貌,从而返回到静之心性。这种修养方法与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的道德修养之方有相通之处。
正是因为有了心性之调控功能的存在,《管子》认为,人之情性虽具有趋恶的可能性,但并不意味着其必然发展为恶,相反,这种趋恶可能性一旦得到有效引导,不但不会衍化为恶行,反而会成为激励个体行动与推动社会发展的合理动力。由此,《管子》在肯定人之情性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论证了个体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个体唯有不断地进行心性修养,以静之心性统御与调控趋利避害之情性,方可促使自我身心的合一、自我行动的合理,从而确证道德自我,实现社会和谐。
二、《管子》道德修养的实践路径
《管子》认为,因为人之情性具有趋恶的可能性,极易形成个体情欲冲动与社会整体和谐的矛盾,而化解的路径就是通过心之思虑功能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并激发个体的道德自觉,让个体主动以心性统御情性,去恶向善,复归于道德本体,从而把礼义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形式内化为自身的内在德性。那么,如何做才能完成自身德性的沉淀与涵养呢?
首先,以心知道。在《管子》看来,礼义道德规范之所以是必然的、合理的,就在于它们根源于终极之道。从此种意义上说,对礼义道德规范的遵从也就是对终极之道的体认,个体一旦能够以心知道,他的行为自然而然就会中规中矩,合乎规范。可是,个体经常受到情性冲动的干扰而打破心性的虚静状态,结果导致心为物欲所拘,难以对终极之道形成正确的认知,因而《管子》要求个体“洁其宫”,去除心中的好恶情感,摆脱外界物欲的烦扰,如此才能充分阐扬心之理性认知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求人们主动加强内心修养,在“虚”“一”“静”“因”四个字上下功夫。
“虚”就是“无藏”。“无藏”就是“无虑”“无求”。“虚者,无藏也。故曰:去知则奚率求矣,无藏则奚设矣。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反复虚矣。”[1]767可见,人心如能不受主观的先入之见影响,去除嗜欲、过欲以及不必要的情感的烦扰,排除一切巧饰、诈伪的干扰,就可以做到“无藏”,回复至与大道一致的本然之“虚”的状态;“一”是指专心一意,心无二致。《心术下》云:“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证。”[1]780这里的“远”就是指“道”,人只有专心一意,持之以恒,才能端正耳目,察知大道之征候。因此,《管子》多次问及“能专乎?能一乎?”[1]943其目的就是强调人们在认知大道的过程中要“一意搏心,耳目不淫”[1]943,自觉坚定自身的道德意志。“静”是指要保持心的安定宁静的状态。《管子》多次把“静”与“动”和“躁”对举,认为“动则失位,静乃自得”[1]758,“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1]950。人心之所以不能够认识、把握“道”,主要在于其通常为物所拘、为欲所困,处于急躁紊乱、烦躁不安的状态。如水浊不可照物一样,人心一旦躁动,自然就不可能对“道”有真切的认识和把握。所以,《管子》说:“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被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道乃可得。”[1]935人在美声淫音的干扰下是难以把握和安顿“道”的,唯有修心静音,心静气理,“道”才能为人心所认识和把握。“因”是指以物为法、循理而动。《心术上》云:“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1]764《管子》认为,如果个体都如君子不受个人好恶之困扰,不把主观臆想强加他物,恬淡无为,因循他物之本性而行,就可做到物至而应,缘理而动。与之相反,如果个体刚愎自用,依凭主观臆见而动,改变他物本性而行,就会出现错误,犯下罪过。
可见,《管子》之所以强调虚、一、静、因等心性修养,是因为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排除一切外在干扰而竭力以心知道,确证主体价值存在,成就德性自我。这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与自身情欲冲动抗争、克己自制、积累道德知识的过程。不仅需要个体专心致志、一心一意地坚持下去,而且需要经常反省自身,检验自身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
其次,自省其过。《管子》认为,人们由于受到自身趋利避害之情性的导引而皆欲贵欲佚,所以极有可能导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欲所惑、为物所拘,也极有可能出现偏离道德法则的不道德行为。这种情况不仅不肖者有之,而且贤者有之,甚至圣王也有之。“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1]598-599《管子》在此把圣王的德性在身比作“丹青在山”和“美珠在渊”,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要时刻担心自己的不善。假如自身有善,民众定会称颂其善;同样,假如自身不善,人们也定会指责其不善。当人们指责自身不善时,不要再去问自己身边的人,而应该虚心听从民众的指责而改正之。
由此观之,在面对错误的时候,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掩盖自身的错误,而是如何自省其过而改正之。人们唯有经常改正自身错误,避免谬误当身,才能去恶向善,日新其德。孟子在此问题上也有所见:“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3]子路、禹、大舜等人的品质不可谓不善,但是也有出现错误的时候,他们一旦听到别人的指责,不是寻找推脱之辞,而是虚心改正之,所以他们才得以成为圣人,为后人称颂。
再次,谨禁微邪。《周易》有言:“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4]可见,人们的善恶之分在于后天的积为,人们积小善为大善而成就善之德性,积小恶为大恶而成就恶之罪身,故而人们不要以善小而不为,以恶小而为之。对此,《管子》指出,人们虽没有先天的或善或恶的差别,但都有辨别礼义的知性能力,一旦能合理阐扬这种知性能力,就可遇微邪而戒除之,遇小礼而谨守之,遇小义而推行之,遇小廉而修治之,遇小耻而整饬之,从而达至“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1]11,形成道德自觉,涵养自身德性。也就是说,人们唯有从微不足道的细微处着手,在具体的日常习行中经常磨砺,不断进行道德积靡,方可把客观的道德法则化为内心的行动诫命,养成道德习惯,成就自身德性。
三、《管子》道德修养的理想人格
理想人格是人们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要求不断修养自身而达到的精神层次,也是个体进行道德修养所要实现的道德理想自我。它的设计既要基于个体的现实性、特殊性、个别性,又要兼顾个体实现自我内在超越的理想性、普遍性、一般性。根据人们对道的体认程度不同,《管子》把道德修养的理想人格划分为君子和圣人两个层次。
《管子》全书总共38次言及君子,其在《法法》篇云:“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1]298在《管子》看来,君子是指在位的上层阶级,他们理应志于行道且借此为生;小人是指劳动者等下层阶级,他们理应尽其力以求得生存。“君子食于道”表明在位者在道德问题上是先知先觉者,具有较为高尚的道德品质,并负有把道传之且行之于天下的使命;与之相对,“小人食于力”则表明劳动者虽在生产劳动层面是精通者,但在道德层面却远不如君子,唯有得到君子的启发和教化之后,才能理解道德的真言奥义,涵养自身德性。
因此,君子在《管子》眼中是既有地位又有德性的人,必然要在社会中担当比一般人重的社会职责与义务:“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1]584基于此,《管子》明确规定了君子的道德要求或道德人格:“君子恬愉无为,去智与故,言虚素也。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其应物也,若偶之,言时适也、若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物至则应,过则舍矣。舍矣者,言复所于虚也。”[1]776这就是说,人们在面临自我与他人冲突与矛盾之时,通常流向唯我独尊的自我中心主义,这就极有可能把自身的一己之见或个体私欲强加于他人而忽视他人原有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极有可能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乃至给自身带来伤害。因此,对于《管子》来说,君子唯有去除主观之见,因循他物之本性,做到以物为法、物至而应、缘理而动,才能促使他物得以充分发展,完成“君子使物,不为物使”[1]937的重大职责。
《管子》的以物为法的君子道德人格明显不同于儒家君子强调慎独的“为己之学”。在儒家看来,人们唯有不断地谨慎地加强自身心性修养,反省自身,改过自身,提升自身,避免受到外在的物欲或利益的干扰,才能超越自身物质性的存在而获得精神层面的自由,这是实现君子道德人格或成人的必由之路。这种思路固然可以激励人们修养自身的昂扬斗志,但也存有仅顾慎独自身而忽视他人存在的危险,而且儒家的君子一旦把自身较高的道德标准强加于普通人身上,就极有可能戕害他人的本性,从而使得道德修养成为名实不符、表里不一的虚幻之名,使得君子的理想人格变成一个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与之相对,《管子》的以物为法的君子人格就为避免这种错误作出有效努力,它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提出以物为法的因循之方,试图让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缓解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乃至与整个宇宙世界之间的紧张与矛盾,从而可以确保实现个体生命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
可是,君子毕竟不是道德上最为完善的人,在其上还有更为完善的圣人。在《管子》看来,圣人才是最高的理想人格,才是众人应当效仿的道德榜样与楷模。在《管子》看来,圣人具有如下优秀品质:
首先是“因物之性”。《宙合》篇有言:“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挡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1]235这就是说,前有所唱,后必有所和,而且和之不差,这就是天地的自然法则。弯曲物体的影子不会变直,丑恶声音的回声不会美好,所以圣人能通晓万物之本性,并据此以应物。并且,《心术上》篇也云:“强不能遍立,智不能尽谋。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殊形异执,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始。”[1]764强力不能遍立万物,巧智不能尽谋万事。万物皆有形,有形方有名,能够致使形名完全契合相当,才可成为圣人。所以圣人顺应万物之本性,通晓不言无为之事,才算懂得道的要领。事物虽然千变万化,但圣人仍旧可以与万物同理,所以才能够为天下始。由此可见,万物虽殊形异埶,万事虽千变万化,但圣人如能做到因物之性,以形而名,物至而应,就可实现无为而治。基于此,《管子》认为,圣人在社会治理之时运用心智好像混混沌沌博大圆通,若隐若现而不得其门,纷纷杂杂犹如乱丝,但又像有次序可以梳理。对于欲知的人就让他有知,欲利的人就让他有利,欲勇的人就让他有勇,欲贵的人就让他有贵,如此这般,人们就称颂圣人为有礼、恭敬、仁爱、聪敏。显然,圣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效就在于其能够因物之性,顺人之心,从而实现身闲而天下治。
其次是“因时而变”。“时”在《管子》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总共出现346次。《管子》认为,天、地、四时具有内在规律性,万物也因时而生长收藏,亦即“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1]1169。所以,圣人应该明知四时之变的内在规律性,做到“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1]218-219如果圣人不因四时颁布法令,就极有可能损害农业生产,给民众造成伤害乃至国毁人亡,故《管子》曰:“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1]837-838其实,《管子》之所以要求圣人要因时而变,是因为“道”虽为宇宙世界的终极本体,但其在表现形式上是即时的、多样的,唯有动态性的眼光或视野,才能体见遍流不息的本体之道,把握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性。因此,《管子》说:“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1]922圣人在治理民众之时既不要受到古时旧制的束缚,也不要拘囿于当今的奇名偏法,而是要以利民为本务,做到“与时变,与俗化”。直言之,圣人正是因为不拘泥于外在的形式,以动态的视角对待万物的发展,“不慕古,不留今”,所以其能够做到蓄道以待物,体见道之本质,使民众莫不心服体从,进而实现国家大治。
再次是“无私公正”。《心术下》篇云:“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1]778在《管子》看来,天下之所以出现混乱,主要是因为一己之私横行于社会政治生活中,故而圣人一定要像天无私覆、地无私载那样一视同仁地对待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公而无私。所以,《管子》要求圣人言行要以公义为重,符合公义就行,不可则止,“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1]1177。进而论之,为了能使包括圣人在内的所有人有一个较为客观统一的行为标准,《管子》力倡在社会中树立和推行明法。明法虽然形式上是由圣人制定,但是由于其以客观公正的道为本根,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即使是圣人本人也应该无条件地遵从之,亦即“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1]307。也就是说,圣人若依法而行,“不为一人枉其法”,那么社会公正就可得到维护,百姓也就备受其利,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圣人之治”[1]789。
孔子和《管子》虽然都极为推崇圣人,均认为圣人应该具有高尚的道德人格,但两者的致思方向还是存有差异的:孔子的着力点在“仁”,指出圣人只要能够终日无违于仁并将此种仁爱精神推及他人,就可实现天下大治;《管子》则更为注重“道”,认为圣人唯有蓄道以待物,时刻以“因物之性”“因时而变”“无私公正”等为行为尺度,方可“参于天地”,实现无为而治。两者之间更为本质的区别在于:孔子的圣人的仁爱精神由于对个体的心性修养要求极高,致使其圣人理想人格极有可能成为大多数人终生难以企及的“海市蜃楼”;《管子》的蓄道待物则由于充分考虑到人类社会的现实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不仅可以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均能顺其本性而行,实现自身价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和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紧张和矛盾,所以相对而言更具有可操作性,更能确保达到个体生命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
[参 考 文 献]
[1]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81.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82-83.
[4]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