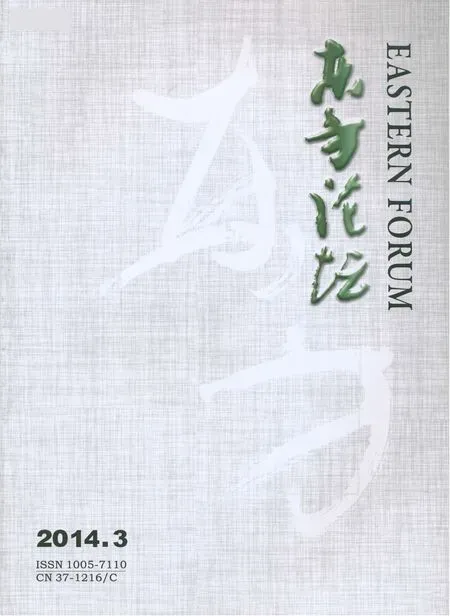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与庄子的性命之情
王 凯
论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与庄子的性命之情
王 凯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澄明”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词语。在心物一体的神秘境界里,获得显现的世间一切是被世界化、澄明了的事物,而不是没有灵性的生硬之物。世间万物是在心物一体之境域中舒展着,在这一境域中天与人、心与物聚集为统一的空间,海德格尔将这境域称之为澄明。庄子的“性命之情”与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有着共通之处。庄子之性命之情,指的是人素朴真纯的自然本性和原初天性,是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融通会合的诗意情境。
海德格尔;庄子;澄明;性情
对于世界的追问是人类所独有的追问,因为此追问相关于世界对于人类所具有的意义,是追问与人相关的、人生活于其中并能体验到的世界。但是,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亦即以论证性的表象思维去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不是人所能体验到的世界。思想的神圣使命就是要重新唤起“存在之思”,如果说胡塞尔关注的是“面向事情本身”,那么海德格尔关注的则是“思想的事情的规定”。
一、此在之“澄明”
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海德格尔说“‘澄明’源于动词‘照亮’(lichten)。形容词‘明亮的’(licht)与‘轻柔的’(leicht)是同一个词。照亮某物意味着:使某物轻柔,使某物敞开。”[1](P1252)
在德语语言史中,“澄明”(Lichtung)一词是对法文clairiere的直译,它是仿照更古老的词语“森林化”(Waldung)和“田野化”(Feldung)构成起来的。正像在林中开辟出一块空地那样,使森林的某处没有树木,这样形成的自由之域便是澄明。澄明是最后所归结的空间的敞开,澄明的亮光能照亮黑暗,使世间的一切呈现出来。因而“澄明之境”就是一种无蔽的状态,它与“现象”概念不同,现象是“就其自身显现其自身”,存在于与表象对立的状态中,它的“在”就表现为现象,表明为敞开出来的在场状态。因此,只有对存在本身发问,迄今一直被遮蔽着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处才会透入一丝光亮,才能够抵达存在的敞开状态,这里所说的敞开状态即展开那由存在的遗忘所掩盖的东西。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澄明即存在之光亮,在亮光里显露,这同时表现为世界的敞开,假若存在没有光亮,世界就会变得一片灰暗,存在的澄明就意味着世界的光亮。由于人与世界是共在的,所以世界的敞开即是在世界中的感性个体站出来的生存。剥离人,去掉世界,就无从谈世界的敞开。
海德格尔以诗意的语言把这一敞开领域称为轻柔的怀抱。他说,自然把万事万物吸收在它的敞开和澄明中轻柔地怀抱着。“这一包融天地主宰万物的无所不在的自然,与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的道非常相似。自然之道把澄明之光给予了万千事物,因而进入澄明之境的天地万物才能够作为天地万物本身存在,才能够显现为本身所是的东西。”[2](P204)这个自然之道不是一直存在的,它存在于一切现实存在之前,存在于被感知、被认识的对象性的事物之前。
海德格尔在诠释荷尔德林的诗句“在光明之上居住着纯洁的心灵之神”时,将喜悦者、明朗者、澄明都解释为澄明之境。澄明之境指的既是指人之性情的敞开,又指天地万物作为本身的不受干扰的一种状态。这时人的心灵是博大无私、宽容与开放的,是能包融下万事万物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在这一境域中开放着,即使是那幽冥的深渊也融入澄明之中,融会贯通,得到认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在这一片令人喜悦的澄明境域中,天地万物摆脱了束缚,丢掉了功用、性质的约束,融入物成其物的神圣之中。人消解了由欲望和成见组成的种种烦恼,沉浸于万物为一的极乐之中。
澄明之境是作为人之性情的敞开,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性情,就是人自然素朴的自然天性、原初本性。澄明之境与庄子的性命之情有着异曲同工的诠释。在海德格尔认看来,荷尔德林的诗就包含着这样的性情,因为只有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原初的言说才不会终止其生成,而是保持无限敞开的状态。人只有不把自然与人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只有走出有形有名之物的遮蔽,去体悟人在大地上的原初生存,重返人生存的本根,才能秉受人与万物之间交相呼应的语言,倾听到人与万物之间永无止息的往返交流。这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是一致的。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诗意地居住”才触及人本真的生存。在海德格尔心目中,荷尔德林的诗歌,带给人的不是一般诗论中那样的主观感受,而是对天地神人的本质存在的创建者的命名。只有诗人能达到澄明之境。此澄明也是愉悦,在其作用下,每一事物都自由徜徉着,澄明将每一事物都保持在宁静与完整之中。对诗人来说,“最高者”与“神圣”是同一个东西即澄明。通过愉悦的澄明,他照亮人的精神以使他们的本性得以对那些在其田野、城市、住宅中的本真者敞开。
发自本真心性的诗歌是在生活、劳动中自然产生出来的,是从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是与自然万物没有任何距离的原初境域。
其实,海德格尔不认为澄明是由别的事物引起的光明,而是由人的本性以及人的性情引起的。人只要存在,他就能够在事物中融入自己的心与自己的情,人的天命是人展开自身。澄明指人在世界中的生存,不是如同太阳般的光明,而是人把自己融入万物之中,也即“他是照亮着的”,即人作为在世界中存在本身是澄明着的,不是说由于其他的存在者,而是说他本身就是澄明,他自身就可以敞开一个世界。
这样境域的澄明,“既不是纯粹的光明,也不是纯粹的黑暗,类似于老子讲的‘袭明’”。[2](P206)“袭”字中有“藏”的意思,“袭明”,即含藏着的光明,意味着将智慧或锋芒藏起来,老子的“袭明”,也就是说人还未开启自己的聪明智慧,处在隐性的状态,人居留于世界中就好像把天下藏之于天下。
二、“性命”之情
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涉及到人的天性和人的性情问题。中国道家也历来关注和重视人的天性及其性情问题,尤其是庄子在此方面有详尽的论述。
《庄子》内篇中“情”字出现多次,虽然未出现“性”字,但常常以“生”或“德”替之。《德充符》谓:“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林希逸谓:“此生字只是性字。”在庄子看来,“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存在,所以《庄子》内篇有以“生”代替“性”之例。“物得以生谓之德”是《庄子》书中对德字的界定,物得以生即物得到以生,庄子继承老子“道生之,德畜之”的观念,认为“通于天地者德也”,德即性,即道。徐复观便有这样的观点∶“内篇的德字,实际便是性字。”[2]“情”的字义较“性”丰富,有“情实”“情欲”之义,还有一种便是与“性”同义,如“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事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天地》)。此处的“情”则作“性”字解。
庄子后学遵循了庄子的思路,外篇和杂篇中不断提及“性”“情”,并且开始提及性、情两者的关系,将两者连用,称为“情性”或“性情”。《马蹄》篇谓“性情不离,安用礼乐”,性是与生俱来的;《庚桑楚》“性者,生之质也”,所以人有生命即有性,情当出乎人的本性,与性是不应当分离的。与性不分离的情,便被称为“性命之情”,谓“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性命之情”即性情,指的是万事万物遵循“道”的衍化生成而自然呈现出来的天性。《缮性》篇谓:“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此处所谓的“性”也即万物禀自本源之“道”的天性。《庄子》中描写了许多动物的自然性状,如《马蹄》和《骈拇》中描写了马的种种自然习性:“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都是庄子对原始状态下的自然性情的赞赏,并指出此即马之真性。而等到伯乐之类的驯马人出现后,便对马进行各种残害其自然性情的人为活动,诸如“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致使马群死伤过半。此类因欲望而起的人为活动,因损害了马之天性,致使马丧失性命。“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岐;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只要是不失其性命之情的便是合于事物的本然状态,而不应该人为地加以分割或拼凑。由此可看出,庄子注重从万物自身呈现出来的自然天性,反对人类出于功利欲望目的来任意破坏万物这种禀自“道”的自然天性。道无所不在,真性情与道同生,它源于道,生于道,随于道,归根结底,性命之情即是道之情。
庄子反复申述,道、德、天地万物原本都是虚静的。同于道,性命之情最大的特点便是虚静,这种虚静的形态使它成为人与天地溶一沟通的最大快乐和自然适意,同时使它成为以心契入万物从而体悟万物本然运化的生存方式。《秋水》篇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白鱼悠哉悠哉地游着,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回答说∶“我在濠水的桥上,我就知道鱼的快乐。”庄子站在濠水桥上,心情愉快,因此他能够体悟到悠哉悠哉游着的鱼是快乐的。这时的庄子不是作为站在桥上的人去观察游在水中的鱼,而是处身于由自己的愉快情绪所展开的境域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万物之本也。”“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圣人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虚无活淡,乃合天德。”心能虚静,则如明镜高悬,不仅包容广大,而且上下内外皆与天地同流。“德至同于初,同则虚,虚乃大”,“无视无听,抱神以静,面上无乐,形将自正”,“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论证着同一个观点,虚静祛除了一切激动、颤栗和忧伤,它作为“道”的形态包含着最大最深最纯的乐,这就是性命之情。《天道》说:“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虚静的性命之情单纯无杂,空诸一切,无任何心智欲望的扰动,然而能使人心与寒暑春秋同其冷暖,与天地精神完全融合,取得纯粹自然性的和谐。正如《大宗师》说“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由此可知,庄子所言性命之情指称人素朴真纯的自然本性和生命之内秉道而有的原初天性,也指称人的本然生命与天地万物的生命本然混冥一体、融通会合的心意状态。在心物一体的神秘境域中获得显现的万事万物,不再是捆绑在周围环境上没有灵性的呆板之物,而是被世界化,澄明了的东西。这时候的自然万物是持续地在心物一体境域中展现着,生发着。在这一澄明的境域中天与人、心与物聚集为统一的空间。这一心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境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澄明。
海德格尔不把澄明看作由任何别的什么东西引起的光明,而是人的天性。人只要是人,他就能够把自己的心、自己的情伸展到事物中,人展开自身是人的天命。澄明指的不是如同太阳那样的纯粹的光亮,而是指人在世界中的生存,人把他的此在分离到万物之中去,也就是说他是照亮着的,即人作为在世界中存在本身是澄明的,不是说由于其他的存在者,而是说他本身就是澄明。这样境域的光明,既不是亮如朗日的彻底通透的光明,也不是完全的黑暗,老子称之为“袭明”,庄子的《人间世》中也有与老子相似的论述,“绝迹易,无行地难”,在分析辨别、昭昭察察、锱铢必较的世俗世界要隐藏自己的足迹,做事隐匿,还不是没有可能,但要想完全地无所作为,完全地不去行动,即不在世界中生存,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人间世》)观照空明的心境,空明的心境能够生出光明来,福善之事止于凝静之心。澄明之境在庄子是“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是“朝彻”,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物化之境。
庄子的“性命之情”即性情,是万物遵循“道”的衍化生成而自然呈现出来的天性。“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缮性》)这里的“性”也就是指“道”的天性,是万物之本源。《庄子》 赞美原始状态下的自然性情,他描写了许多动物的自然性状,正体现了这一点。庄子认为,不能把自然性情现成化,人为地分割、拼凑,而需要不失其性命之情,这才是合乎事物的自然状态,而也就是说,庄子看重的是自然自身表现出的天性,反对人类出于功利目的任意破坏万物这种继承于“道”的自然天性。
道无所不在,真性情与道同生,它源于道,生于道,随于道,归根结底,性命之性情即是道之性情。在庄子看来,道、德、天地万物原本都是虚静的,与道相合,性命之情也是虚静的,人只有在虚静的状态下才能融入万物从而体悟万物本然运化的生存方式。心能虚静,则如明镜高悬,不仅包容广大,而且上下内外皆与天地同流。“德至同于初,同则虚,虚乃大”,“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天道》)
虚静的性命之情单纯无杂,空诸一切,无任何心智欲望的扰动,然而能使人心与与天地精神完全融合,获得纯粹自然性的和谐。正如《大宗师》说:“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至于通达澄明之境的方式,庄子与海德格尔也是一致的。庄子的“忘知”,是去除关于天下、物我、生死等诸思虑,“忘知”即是“坐忘”。“坐忘”靠的是淡化、克制、忘掉来源于外界的干预和纷扰,从而呈现出心的虚静本性。虚才能容物,容道,才能达到游的境界。在“致虚静,守静笃”式的体道方式中,由心斋而达坐忘之境,坐忘之境亦即同于大道的澄明之境。
庄子强调,性命之情起自人顺应本然生命,安时处顺,摒绝欲望心知,以道通为一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因此,在性命之情中,整个世界除本然的生命之外,其余一切拘限、形役、物役,操心、思虑乃至逻辑因果,统统都被人的心灵超越,能企达这种精神境界的人,即是真人、圣人、至人和神人。圣人以本真之性参与万物的存在与运化。圣人并不认为外物自然是作为立于面前的独立于人心的东西,也不会琢磨如何以自己的心去迎合外物。圣人始终把他的心灵时时刻刻地敞开到万物的生存中去,它展开的每一瞬间都都充溢着物之自然,圣人的心性与物本身之间是零隔膜和距离。
所以说,庄子所言性命之情,乃是人素朴真纯的自然本性和生命之内秉道而有的原初天性,也指称人的本然生命与天地万物的生命混冥一体、融通会合的心意状态。此情境与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是一致的。海德格尔说万物虽然要靠光亮来引导自己,但“光可以涌入澄明之中并且在澄明中让光亮与黑暗游戏运作。但决不是光才创造了澄明。光倒是以澄明为前提的。然而。澄明敞开之境,不仅是对光亮和黑暗来说是自由的,而且对回声和余响,对声音以及声音的减弱也是自由的。澄明乃是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敞开之境。”[1](P1253)这就是说,光本身创造不出澄明之境,澄明之境是光的前提,也可以这样说,澄明之境存在先于作为永恒在场者。
世界是将人寓于其中、融于其中的。唯有这种方式,个体事物才能显示自身,进入澄明。世界上的事物形形色色,都属于一个敞开的存在者整体。这个最宽广的领域是一种“全面相互牵引”的领域,这里说说的“敞开”是指“没有阻碍”、“不设定界限”[3](P96,115)。用中国语言来形容便是“相通”与“畅通”,万物一体即相通无阻、畅通顺达。人对万物一体的领悟是相通的,就是万物的意义,也就是万事万物都被照亮着,敞开着。换句话说,天地万物得以敞开的必要条件是人的领悟。因而,人的这种领悟才可以称为“澄明之境”,万事万物在这里得以澄明、被照亮。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表述,用领悟替代直观,单纯在场的、自满自足的东西的优先地位被在场与不在场的结合替代,从而推翻了西方旧传统那种以直观、求知和认知作为进入“澄明之境”的形而上学的途径。
海德格尔的“此在”对存在的“领悟”或“此在”的内涵则大大超过道德意识的狭隘范围。“此在”是整个存在敞开的处所,决非道德意识可以囊括,海德格尔特别强调澄明之境乃是“对存在者整体的超越”,是“无”。包括人的思想在内的任何事物,都来自这个澄明之境,这是个不能改变的前提。它是“无”,却又是有;它超越了存在,却又无处不在。总之,海德格尔哲学以“无”为最高原则的,海德格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即可概括为“无之无化”(彭富春语)。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 中指出,Dasein(“此在”)之为Dasein,就在于它的Da,——在于它之为天地万物之展示处,所以此“Dasein”本身就是一种“澄明”(Lichtung,Clearing),一种“领悟”(Verstehen,Understanding)[4](P120)。
领悟什么?就是领悟“一切存在者之整体性”,亦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性”(Wettlichkeit,Worldhood)。如何去领悟?靠的是诗性感悟,诗性的想象,而不是对象性思维,因为澄明之境乃诗性之境。同样,我们要真正领悟老子和庄子,需要的也是诗意地想象。
三、澄明之真与性情之真
对于“真”,海德格尔与庄子有着类似的见解。在庄子的《渔父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郭庆藩在《庄子集释》解释道:“夫真者不伪,精者不杂,诚者不矫也。故矫情伪性者,不能动人也。”指出这里的“真”含有两层意思:第一指的是精,即不杂、纯粹与单一;第二指的是诚,也就是不矫、忠于与顺应。这表明,在庄子看来,“真”是一种顺应,是对事物的原初纯粹状态的顺承。他用“真”来描述人的喜怒哀乐等各种自然情感,一方面阐明了这些源于自然的性情,能充分体现出人的纯粹的原初状态;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只有顺应这些自然性情,不把人自我的欲求为出发点来任意割裂与伤害它们,最终才能显现它们纯粹的原初状态。
从这里可以看出,情感之真来源于内在的真诚,它不需要借助外在的任何形式,就能引起强大的心灵共鸣,真情便是指个体心灵的安其性命之情、任其性命之情。《天运》篇中所描写的“丑人效颦”,她之所以表现出“丑”的状态,原因就在于其矫揉造作,没有真正明白“颦之所以美”的“美”的根源来源内在情感的真诚。
“真”与道共同具有同一性。从“真者,所以受于天也”到“法天贵真”,获知天与真的涵义在此是一致的,此时天与道又是相通的。庄子所说的天,即是道。针对“是谓反其真”(《秋水》)一句,郭象注释为:“真在性分之内”;成玄英则直接把“反其真”理解为“复归真性”。“反其真”,正是复归本性的意思。
再看庄子书中其他单独使用的“真”,全部可以解释为本性,比如《齐物论》中的“无益损乎其真”、《山木》中的“见利而忘其真”等。“真”与“伪”对立的。庄子有感于社会上所见的各种各样的“伪”,才提出了“真”这个概念。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注曰:“人为为伪也。”“伪”指的就是人为的改变自然物的内在规定性。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乐,也都包含于庄子所指的伪之列。庄子人为,所有人为性的东西,都是扭曲了人的本性,都是多余的、有害的,庄子以“伪”“淫”“侈”来称呼它们。但是庄子提出“真”的概念,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庄子赞许本性,并且拒斥人为。在日常生活里,人的本性经常被名利等外在事物扭曲,人不能真切地呈现本真。但一旦人回归本性,用本真的性情来面对这个世界时,用庄子的话来形容,亦即得道之时。
在庄子看来,只有做到消除“人”,才有可能回归到“天”,才有可能回归到本真的状态,从而达到安其性命之情。这里的“人”和“天”都是特指的,天即自然,指的是事物原初的本真状态;“人”指的是人为,即人们出于各种欲望的妄作为来改变原本的自然性情;“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秋水》)
庄子提倡去除人为妄作,从而让事物复归其本真状态,以显现它们的真情。庄子的性命之情既描述了本真之心的运作,也表达了损聪明、弃智虑、返朴归真,重新获得的心物一体的愿望。惟有大彻大悟,才能使人的心境如同朝阳初启,澄明透彻,直到“见独”,在此超越中返归到了纯真的性命之情。
“真”在庄子那里和在海德格尔那里有着许多共通性。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类似于道家所说的“道”。刘若愚说:“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描述,几乎可以用来描述‘道’。”海德格尔说的“存在者”,实质便是天地万物。换句话说,海德格尔所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与庄子所描述的“真者,所以受于天也”,也就是真是万物本性的敞开与澄明,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的美,就是庄子所言的“天地之大美”。
海德格尔曾说过,我们是居住在世界,这世界值得依恋、值得逗留。居住世界,这句话意思是人是“居住”在世界之中,世界因为人的“此在”而敞开自身。他指出:存在者处于世界,即存在者能够领悟到自己处在它的“天命”之中,已经与那些它自己的世界之内向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捆绑在一起了。
人存在于世界中,注定了人必须先同世界上的万物打交道,并不是先对物进行认识与了解。人先于世界万物融和在一起,之后才认识世界万物,人早已经把自己融合于他所活动的世界万物之中。海德格尔把真理称为“林中空地”(Lichtung),照亮某物就是使某自由地敞开,所以说林中空地形象地显示了真理的开放性,“只有当有林中空地的话,才可能有自由作为让存在,因为林中空地即虚无,此虚无使存在者整体成为自由。在此范围内,存在者能够在敞开的敞开性中显现出来。”[5](P54)
“就真理的本质来说,那种在真理之本质中处于澄明与遮蔽之间的对抗,可以用遮蔽着的否定来称呼它。这是原始的争执的对立。就其本身而言,真理之本质即是原始争执,那个敞开的中心就是在这一原始争执中被争得的;而存在者站到这个敞开中心中去,或离开这个中心,把自身置回到自身中去。”[6](P41)常人存在的方式是非自立的与非本真的,因而此在的存在有两种样式,本真与非本真,非此即彼。
人必须站出来,才能真正地存在于世界上,从而到达一种本真的生存状态。所以,世界需打开自身,而且必是这世界本身站出来生存,即人类自身的存在,操心、思虑与奔忙,对自己的存在有所领悟、有所作为。海德格尔称诸神的逃遁,大地的毁灭,人类的大众化,平庸之辈的优越地位为“世界黑夜的时代”的特征,这些不过是遗忘了真正的存在之后的必然后果而已。
因而海德格尔存在论就是要表现出一种存在的澄明之境,也可以称之为“林中空地”。存在的澄明,本体的诗化,即让人出场,站出来生存,只有这样世界才明亮。“真”是具有极强包容性的,具有真性的人也是心胸极其包容和豁达的人,他们无意于建构某种约束性的体制,也不给人的生存和发展设立种种限制。他们追求的是人性的解放,从各种成见、束缚中解脱出来,还原获自己的本真之情。
道家的境域是独特的,心物一体、天人合一,道家描述心物关系,既没有从纯粹主体的精神境界,也不是从纯粹客体的物质世界,更不是从主体与客体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去展开,而是从人的心与情来谈人的本质、人的存在。道家认为,圣人的存在即把本真之性发挥到客观世界之中。圣人也是存在者,他们敞开恬淡素朴的心境,把自己抛向、指派并且关联到世界之内。
圣人的立于自身就是存在,是随顺、任凭万物按其本然之性,老子说∶“塞其兑,闭其门”(《第五十二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玄同之境指的是混沌、原初的境域,这原初的境域是很容易隐藏起来的。如果想要去掉这些遮蔽就必须切断通向外部世界的门户,即切断眼、耳、鼻、舌、身,摆脱对象性的认识模式。
道家理想中的圣人始终把彼此、内外统统消融为一体,因而往往会显得愚钝,圣人的坚守自身并不代表着与世隔绝,与此相反,而是全身心地、毫无阻隔地生存在世界中。道家的核心概念是道,道家在描述道时关注的重点不是道是什么,不是道的实在性和现成性,而是人们怎样才能够体道悟道,并指出什么是合于道的,什么是违背道的。
道家把道与人的生存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人总是处身于现实世界之中,人能够向世界敞开本真的一面,世界中的其它存在者也如其所是地显露出来。一旦人把各种意愿和情欲伸展到世界万物中,人的恬淡宁静的本性就会被遮蔽,于是人便开始远离人自身,物亦远离物自身。
道家反复强调无智无欲的心境,把灵府、心斋视为最高的精神境界。道家崇尚心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境域,这个境域中没有心与物的对立,没有主体与客体之分,是非现成的混沌的境域。同样,海德格尔想要说明的是世界与此在也不是两个现成存在着的东西的关系,他指出从根本上说此在存在于世界之中,此在的生存本身即打开了一个境域,也生发出一个世界。
海德格尔认为,假如把人与世界看作是两个现成的东西,就会导致人与世界的分裂。如果以对象性思维的主体客体对立为前提,那么就不可能让人与世界重新组合:
老庄的有心有情与无心无情的区别不在于人或者可以有情绪,或者可以无情绪,而是说人可以有不同的情绪,但不可以没有情绪。这里所说的有心有情是机巧之心与爱憎之情,无心无情并不是说把自己的心、自己的情独立于世界的万事万物之外,而是说不让好恶之心干扰的恬淡无欲之心。道家提倡过一种无知无欲、清静恬淡的生活,主张持守本真之性,顺应万物之自然,使心不受物欲的干扰。这种生存方式,是把素朴之心开敞通达于万物之本然。[2](P198)
不管是有情亦是无情,不管是本真亦是非本真,全部是心与物的相互牵涉,都是来自同一本源。这些原初的情绪,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着的。在这种原初的关联和交往中,人并不是独立于万事万物的现成的东西,物也非现成性的物。
道家强调人心的恬淡虚静,并非要否定人的情感,而是说人的各种情感,无论是喜是怒,都应像天地四季变化那样自然。正如庄子借惠施之口所说的:“人故无情乎?”(《德充符》)庄子眼中的无情指的是“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他并不否认人的正常的情感欲望,而是指出以人的本性顺应自然,不去纵情肆欲。庄子笔下的至人、真人、神人的共同特征就是与天地万物共同运化,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因此也没有常人那些因欲望和意愿引起的喜怒哀乐等情感。
人应该让自己归属于存在之道,按其本真之性去生存。自然之道,是心与物相遇照面的原初境域,既广泛地流行于天地万物中,也展开在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社会领域中。自然之道把澄明之光给予了万物,万物就有情有意;自然之道把澄明之光给予了人,人也就有了真情真性。
总之,海德格尔和庄子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在主体与客体的现成性关系之外,还有一个主体客体不分的更原初的情绪或性情领域,在这个领域,心与物交融相契,庄子的心物一体与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向我们显现的正是原始的生存论状态,回到这种状态也就是回到人的原初的、纯粹自然的状态,这也包括原始真性情的回归。
[1]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 那薇.道家与海德格尔相互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诗学文集[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2.
[4] John Sallis.Delimitations[M].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
[5] 彭富春.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6] 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潘文竹
Heidegger's Mirror of Aletheia and Zhuang Zi's Natural Disposition
WANG Kai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Aletheia" is an important term of Heidegger's philosophy. In a mysterious state where the mind and thing are united as one, everything that is manifested in the world is clarifi ed. In this state, heaven and man, mind and thing form a united space, which Heidegger called "aletheia". There is something common between this aletheia and Zhuang Zi's "natural disposition. This disposition refers to the human innocent nature. It is the poetic state where life and all things are integrated into one.
Heidegger; Zhuang Zi; aletheia; dispositiono
B089/B223.5
A
1005-7110(2014)03-0009-07
2014-03-26
王凯(1957-),男,吉林延吉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哲学、文学、美学研究;韦丽丽(1988-),女,山东淄博人,青岛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