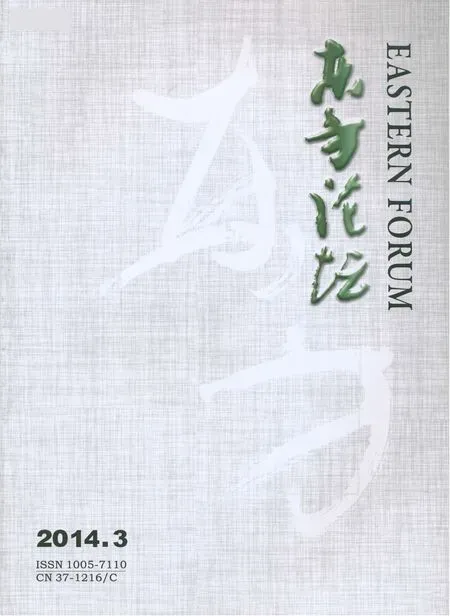基于语言生态平衡考量的新加坡华语升沉探微
蔡 明 宏
基于语言生态平衡考量的新加坡华语升沉探微
蔡 明 宏
(福建师范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新加坡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下多语言环境极具代表性的国家,在兼顾族群和睦和国家意识的权衡中,语言文化环境凸显出庞杂繁复与敏感。以新加坡华语升沉嬗变为基点,以语言生态学为崭新视角,对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背景下语言生态环境的失衡进行观照和思辨,洞彻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诉求和情感依附对语言选择的影响,提出任何语言的一枝独秀都不利于语言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健全,任何语言的衰退和泯灭也都会殃及其他语言的共存和发展,以期探寻多语言成长在整体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具有的客观价值。
新加坡;华语;语言生态;平衡考量
新加坡作为荟萃了东西方文明的国际化都市,语言文化背景相当复杂:新加坡人多由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组成,据2000年新加坡统计局人口普查的官方数据,构成其社会主体的各种族中,华族人(Chinese)占76.8%,马来族人(Malay)占13.9%,印度族人(Indian)占7.9%,其他种族主要为欧裔占1.4%。而新加坡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内部,大大小小的族群更约有 25个之多。[1]面对如此繁复敏感的语言文化现状,新加坡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族群和睦,在语言政策的制定上煞费苦心、如履薄冰。基于新加坡庞杂审慎的语言生态境况,以及对于语言环境的平衡适宜的迫切需要,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加以探究和考量新加坡华语的开沉嬗变,将有利于洞彻新加坡华语历史升沉的脉动与趋向,梳理和省思新加坡华语的历史流变,以期从崭新的维度对新加坡华语的发展进行观照和思辨。
一、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新加坡华语生存处境
语言生态学是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最初是由挪威语言学家Haugen在1972年提出并定义,他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了隐喻性的类比,从动态而非静态的角度,将语言放在生态文化的背景下进行微观和宏观的探析,提出“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2]的概念。此后,“语言生态 ”开始被语言研究者接受并广泛使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态语言学真正开始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迄今,生态语言学已主要用于二语习得、双语或多语现象等领域的研究中。语言生态理论特别强调特定语言所处的环境,既包括族群、文化、地理等因素在内的内外环境的优化与和谐,注重语言的相依相存、互融互惠的生存状态。任何一种语言的一枝独秀都不利于语言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健全,任何一种语言的衰退和泯灭也都会殃及其他语言的共存和发展。
然后,纵观新加坡的建国之史,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迄今,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在独立前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英语在新加坡社会的独领风骚及其带来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已可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英语在法律或政治等上层领域的主导地位都处于不可撼摇之势。在多语言多文化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顾虑重重,因为选择本国内的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作为主要语言,势必引起他族的不满,华族作为人数最为庞大的族群,选择华语作为“族际共同语”,将会造成部分人质责有引发“第三中国”的风险,且华语包纳太多方言,潮汕话、广东话、闽南话、客家话、海南话杂糅于新加坡华族社会中,在语言共通性方面有着天生的缺陷。从平衡性和普及性考虑,以及新加坡出于走向世界金贸中心的国际地位和中立态度出发,英语成了必然的选择。
放眼全球,英语的语言霸权地位其实并非新加坡一国独专。作为全球的强势语言,英语在各国的流通和强力渗透给其他语言带来的生存威胁已经引起了不少语言专家的警惕和关注。不少语言学家明确指出,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语言生态环境的失衡不仅对灭亡的语言和幸存的语言是一种灾难,而且会导致文化生态的失衡,文化生态的失衡将会阻碍甚至终止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3]在新加坡英语一枝独秀的语言现状下,华语的生存举步维艰。自1984年新加坡单语学校彻底结束历史使命始,长期以来英语在教育领域的“淹没式”覆盖不仅大幅减少了华语教学的课时数,也使得英语成为了新加坡中小学绝大部分科目的教学用语。新加坡政府的“双语”教育施行导致的却是语言的单极化发展。很多新加坡华人的华语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生活用语阶段,读写能力有限,政治、文化、科技等较深领域等无法涉及。据新加坡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5岁至14岁的华人在家里讲华语或方言的百分比,从1990年的76.15%跌至2000年的63.19%。[4]“英语被视为是打进专业和高收入阶级的最佳、甚至是唯一语言。华语只有在对象是老年人或者中下层阶级的时候才派上用场。人们只有在乘搭的士或者到小贩中心买东西的时候才会用到华语。”[5]另据资料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加坡华文报纸的销售量便开始下滑,而同期英文报纸读者不断上升。华文报纸的阅读者年龄偏大,年轻读者大都为中国新移民或来访学者。新加坡年轻一代华人不喜欢华文,不看华文书报,对本族文化没有兴趣。“事实上,许多会华语的新加坡人几乎是华文文盲。”[6]当英语“正在缓慢但坚定地向社会交往、家庭用语和个人生活场域渗透”[7]的同时,华语的生存空间正在逐步萎靡。
二、语码夹杂现象凸显出新加坡华语生态环境的改变
在双语制或多语制的国家,经常会出现所谓的“双语人才”或“多语人才”,那么语言兼用现象也必然会发生。在华语方面,新加坡华裔尽管有着同文同种的血脉源流,但“新加坡式华语”(Singlish)的大行其道却让人足以见微知著。
新加坡华语在词汇量方面显得较为贫乏,形容词、量词等往往呈单一性,有人笑言,一条鱼也可称为“美”,所有牲畜,无论猪、马、牛皆可称为“只”,乃至人也可称为“好大只”。在英语作为新加坡社会行政、媒体用语,以及教学媒介语的巨大压力下,“新加坡式华语”中语码混用和语码转换更是成为了语言兼用的两个突出表现。对此,不少专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郭熙在《新加坡中学生华语词语使用情况调查》中发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很多传统的家庭称谓已经被笼统英化的“安娣”(untie)、“安哥”(uncle)所取代,华语中细致生动的动词和形容词往往被简化、回避,时间词语和日常用词甚至直接取自英语。郭熙不无焦虑地指出“动词是语言结构的核心部分,这么大比例的动词在中学生中不再使用,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新加坡华语前景的忧虑。”[8]周清海在《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中也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对新加坡华语的变异进行了考量[9],仅以被字句为例,“水果被吃了”、“马路被修了”等句子的高频率使用都可看出新加坡华语受外来语的影响。
值得警醒的是,周清海也提出一点,语言的趋异可以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也可能是自觉的、主动的行为。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如果不自觉的语码夹杂、语言兼用现象,逐步发展到自觉自主的语言转用方向,那么即意味着该语言的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因为语言使用者对于语码的选择往往出于该语言的社会威望、交际频繁度、政策的导向性等因素,一旦这些外在因素不断地壮大、渗透,使得强势语言夹裹着强势文化对其他语言产生冲击,以平衡和谐为指要的语言生态环境必然逐步恶化,这种恶化以语码的变异、夹杂、借用、替用、转换为外在显像,以潜移默化地改变语言使用者的心理依附和诉求为内化标识。
“一个民族的人如果整体上放弃自己的母语,而转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势必造成这个民族语言的消亡。”[10]当一位新加坡华裔青年习惯于在餐厅中说出“安替,请给我一粒apple。”时,“会不会”汉语已经不是考量的重点,“愿不愿意”用汉语倒成了值得深究的课题。
三、语言情感忠诚度对新加坡华语维持造成的掣肘
为了避免语言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的语言消亡,有专家提出应力争“语言维持”。而语言维持的条件包括:1、争取成为官方语言存在的可能性,以寻求扩大华语生存的空间;2、强化语言使用者的忠诚度,以获得华语情感方面的依附;3、从政策层面完善语言规划,从上而下创造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10]纵观这三个条件,期许华语成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的可行性渺茫,而政策层面的语言规划新加坡政府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和完善,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务实的新加坡政府了看见了华语增值的潜力。然而,功利主义的驱动与情感忠诚度的推动是语言发展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内在力量,促使语言环境的净化和优化的根本力量、深度力量更应该来自语言使用者内化、深化的情感诉求,这种语言态度,即语言使用的忠诚度,将左右着该语言的最终走向。“人的语言态度也直接影响着一种语言的发展趋向。在语言接触中,使用某种语言的人的语言态度可以决定这种语言的兴衰。因为人的语言态度制约着人对语言的取舍,如是否坚持语言忠诚,是否发生语言转用等等。如果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全部坚持语言忠诚,那么这种语言一定时期内是不会濒危的。如果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放弃语言忠诚,而大多发生语言转用,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呈现濒危状态。”[11]
长期以来,新加坡政府奉行多语政策(Multilingual policy)和双语教育体制(Bilingual education),旨在从培养公民国家意识、兼顾各民族情感、融入国际金融社会等方面取得平衡。然而曾有学者针对华语的声誉状态进行了考察,发现并没有出现双语社会中令人期待的语言互补现象。“恰恰相反的是,在任何场合下受到鼓励的都只有英语。华语呈现出越来越‘荒芜化’、‘边缘化’的趋势。”[7]华语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和声誉领域的低迷状态更加淡化了新加坡人对华语的情感依赖,“现在的新加坡华人对华语采取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一是受政府的引导,二是英语有利于个人前途的发展,三是缺乏感情。”[12]
据陈玉清和黄明对新加坡华人语言习惯和态度的调查数据显示,[11]在语言的情感态度上,“最喜欢说”和“最容易学”的选项中,新加坡各民族都认为英语最容易学,印度族的比例甚至高达92.31%,其次就是华族学生,占57.42%,华族学生对于华语的喜欢度仅为为38.9%,比英语还要低10%。而在实用态度方面,认为英语最有用的华族学生占67.67%,认为华语最有用的华族学生仅有13.7%。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华语最有用的其他族学生人数比例居然还高出华族学生10个百分点。
新加坡华族学生对华语情感的疏离和忠诚度的缺失,不仅会带来华语发展趋向的衰落性预期,也会带来语言生态环境失衡的忧虑。200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显示,5岁至14岁的华族孩童在家里常使用英语的比率由1999年的23.3 %提高到2000年的35.8 %,1年内激增12.5个百分点。其速度是惊人的。而5岁至14岁的华人在家里讲华语或方言的百分比,从1990年的76.5 %跌至2000年的63.9 %,跌了12.6 %。“其衰退程度同样是惊人的。孙辈一代越来越差了。”“事实上,如果连这一代华文水平最优者都不使用华语,那么下一代必然失去华语的习得环境。”[13]情感忠诚度的缺失从内肇始于新加坡华人民族情感认同、社会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向外直接影响了新加坡人对于华语价值的评价和认定,从而互为表里地同构了新加坡华语的生存处境:华语低声誉的生存现状和受限的发展前景,与华语使用者的负向情感选择互为掣肘,使得华语在新加坡社会的维持显得胶着和促狭。
四、结语
与自然生态环境一样,语言系统自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有着同构的关系特征,语言的繁衍与发展不仅需要有生存的环境,更加需要有平衡和谐的生态环境。在新加坡这个竭力维持语言平衡、维护种族和谐的国度里,“英语+母语”的双语教育政策尽管兼顾了新加坡统一的国家意识和各种族的民族情感依附,但英国曾统治新加坡近140年,英语在新加坡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独权地位和强势发展已是既定事实。纵观全球,英语的强势凸显不仅在新加坡一国,其在全球范围内对语言环境公平性和稳定性的破坏已备受语言专家关注,有学者担心到本世纪末全球75%- 90%的其他地方语言,特别是本土语言将被英语逐渐取代而消亡。无怪乎有国外学者称英语为“杀手语言(killer language)”[14]。随着新加坡语言生态环境的逐步失衡,华语在新加坡生存状态步入边缘,华语语码变异、夹杂、转换等日趋彰显,华语使用者的语言感情忠诚度逐渐嬗变减弱,华语在新加坡的生态环境在浮浮沉沉中走向低迷,这是值得警醒和审视的。因为多样性的语言正是健全的语言生态最显著的特征,它使得多元的民族文化得以绵延长续,是文化生态延续的必须和保障。一旦某种语言的衰退与灭亡,将会打破语言的生态平衡,甚至殃及其他语言的发展。语言也是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生态平衡和自然生态平衡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语言的衰变和失衡同样是世界生态危机的构成部件。因而,为了维护全球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不少学者都将语言生态平衡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也正因为语言生态环境与其所创造的文化环境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态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2000年起更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专门成立跨部门语言及语言多样性特别小组,以倡导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坚持文化多元和族群包容。[14]
新加坡作为一个在全球化进程下多语言环境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国家,如何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权衡中维持语言生态平衡,值得引起关注和探究。而以新加坡华语升沉嬗变为基点,从全球语言生态的角度,探寻语言成长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将更具有普世价值。
[1] 王天舒.新加坡的多语政策与双语教育[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1).
[2] 程潇菊.生态语言学初探[J].安徽文学,2011,(11).
[3] 崔桂华,齐洪英.生态语言学∶语言系统的生态学视角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58(2).
[4] 徐峰.新加坡华语地位的变迁与华文教育所面临的挑战[J].中文自学指导,2008,(6).
[5] 周聿峨.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机遇和困惑[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1,(1).
[6] 陆建义.一份厚重的华文报纸 ——新加坡 《联合早报 》印象[J].今传媒,2008,(11).
[7 赵守辉,王一敏.语言规划视域下新加坡华语教育的五大关系[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3).
[8] 郭熙.新加坡中学生华语词语使用情况调查[J].华文教学与研究[J].2010,(4).
[9] 周清海.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J].中国语文,2006,291(6).
[10] 冯广艺.论语言接触对语言生态的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2(5).
[11] 陈玉清,黄明.新加坡双语教育与华人语言习惯和态度的变迁[J].集美大学学报,2012,13(2).
[12] 刘丽宁.80年代初至今新加坡华语使用状况分析及展望[J].东南亚研究,2002,(3).
[13] 胡光明,黄昆章.新加坡华语生存环境及前景展望[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2).
[14] 覃薇.英语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生态与语言多样性的维护[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25,(7).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Language-based Ecological Balance Considerations
CAI Ming-hong
(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China )
In Singapore -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language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highlights the complication and sensitivity of its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wh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thnic harmony and national awareness. Based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Singapore, the author studies the languag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context of many ethnic groups, cultures and langu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ecology, perceiving the infl uence of language users' psychological appeals and emotional attachments on language choices. It concludes that different language are mutually dependent and coexist.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ecology; balance consideration
H0-09
A
1005-7110(2014)03-0102-04
2013-10-26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以来东南亚地区华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研究 ”(项目编号:12YJA740047)阶段性成果。
蔡明宏(1978-),女,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华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