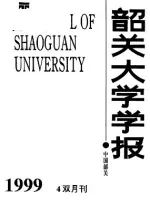日本佛教本土化进程探略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珠海519090)
一般认为,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实际上佛教自从传入日本,便开始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接受外来文化,并不断使外来文化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日本对于佛教的接受及其日后对佛教的发扬,或者说日本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也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甚至有学者认为“日本佛教由于始终受到其现实社会政治需要和传统宗教(神道)的深刻制约,已经造成变质”[1]。纵观日本佛教的历史不难发现,日本佛教在日本社会历史环境的漫长流传和发展中,确实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深深打上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烙印。
一、日本对佛教的最初接受——“镇护国家”思想的确立
关于日本佛教的历史,一般认为最早是在公元6世纪中叶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的。《日本书纪》描述了佛教传入日本的最初一幕:公元552年钦明天皇传播早期儒学之时,接受了百济送来的“释迦佛金铜像”[2],还接受了同时带来的经论等,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日本。
佛教进入日本伊始,便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苏我氏和物部氏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关于崇佛与抑佛的斗争,就是佛教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被利用于政治斗争的表现,这场斗争最终以崇佛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佛教在日本传播的初期仍然受到来自贵族阶层乃至庶民阶层的抵制,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日本当时已经基本确立神道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佛教思想冲突;其次,佛教所宣扬的人生哲学,尤其是消极厌世和出世的态度,与当时日本民族的思维水平和生活趣味相去甚远;再次,佛教宣扬出家人“六亲不认”,脱离社会政治与家庭责任,而这对于一向注重血缘氏族的日本也是极大的冲击[3]。
直到“镇护国家”的思想被确立起来,并成为佛教的主要使命,才使得佛教在日本找到了一条适合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圣德太子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摄政期间,日本发布了名垂史册的“三宝兴隆诏”(三宝者,佛法僧也,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又再次强调了佛法普渡一切众生,使用于万国。这样实际上就是以政府法令的形式肯定了日本民族对于佛教的接受,实现了佛教与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最初融合。
圣德太子之后,历经奈良、平安、藤原几个时代,佛教在日本得以继续传播与发展,但一直延续着镇护国家的思想,日本佛教的各宗各派也始终是以镇护国家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具有天生弱势岛民意识的民族来说,强调爱国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可以算作日本民族文化精神中最重要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对于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得日本佛教具有了强烈的“国家宗教”的色彩。
二、日本佛教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发扬
从奈良时期到平安末期,佛教对日本民族而言仍然处于一个不断吸收和引进的时期,但是日本文化对于佛教的吸收和引进是有所选择的,甚至于不惜对其进行筛选和曲解,以便其能更加适应日本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需要,这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在日本佛教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日本佛教的独特性。
(一)“神佛融合、神佛同体”的日本佛教
早在佛教传入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了原始神道的宗教信仰,虽然已经初步具备宗教理论的雏形,但事实上原始神道仍然保持着大量原始宗教的特点,也就是说,带着原始宗教信仰的那种强烈的现实性和功利性的特点。譬如人们祭神,为的就是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农耕丰收和生活圆满而已。较之于深奥难懂的佛教,日本人对于神道自然要容易接受得多,那些抽象的佛教思想,深奥的佛教教义,玄妙的佛教经典,对于抽象思维能力贫弱的日本人来说,与其说难以理解、难以驾驭,倒不如说一开始就缺乏去理解、去驾驭的信心和思想准备[4]。因此,佛教要想在日本这个国家落地生根,必须要迎合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找到更易于为日本人所接受的方式。
在原始神道信仰的强烈影响下,日本佛教最终走上了一条与原始神道相靠拢相融合的道路,“神佛融合”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特征。神道实用主义的精神和现实功利的色彩也逐渐附丽于佛教,从而使日本佛教蒙上了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神前读经、僧侣兼任神官的现象,开始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固有的八幡大神也最终变成了八幡大菩萨。玄妙深奥、难以悟得的“佛”最终与随处可见、亲近随和的“神”融为了一体,其实正是日本佛教对其传统文化的一种妥协。
(二)与祖先崇拜融为一体的“葬式”佛教
祖先崇拜也是日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信仰。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古代的葬礼是根据神道的仪式进行的。镰仓时代之前,在庶民之间普遍使用风葬,尸体一般都被放置于野外。然而随着佛教在庶民之间的推广,火葬也开始渐渐被庶民所接受。除了在葬式方面获得了全面胜利之外,佛教在葬仪方面也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由于佛教的传入,使得日本民族固有的祖先崇拜信仰在葬式、祭祀、供养等方式上也更加趋于固定化和完备化了。正因如此,日本佛教也被普遍认为是“葬式”佛教,日本人将生前的幸福寄托于神社,而死后的安宁则托付给了寺庙。“葬式佛教”既反映了祖先崇拜这一民族传统文化对日本佛教的深刻影响,也证明了佛教在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普及,是日本佛教对其传统文化的又一次妥协。
(三)宗教艺术高度发达的“造形佛教”
与中国佛教相比,日本佛教在佛教教义和思想体系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少有建树,但在佛教艺术的成就上却比中国佛教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学者指出:“日本人具有一种把语言(文字)性的、抽象的东西用某种形状表现出来,以便用自己的眼来看的倾向。”[4]就是这样一种倾向,反映到日本佛教上,便导致了日本佛教在抽象理论上并不发达,而一味注重伽蓝、佛像等营造的所谓“造形佛教”的出现。日本佛教史上出现的艺术珍品真可谓不胜枚举,其中有7世纪初完成的内有金铜释迦佛像的飞鸟寺,包括金堂、五重塔、中门、回廊在内的、金堂内置释迦三尊像的法隆寺,还有广为人知的东大寺、唐招提寺等,不仅如此,在佛像、佛具的制作方面以及佛教的绘画,寺院建筑的雕刻等方面全都不乏上乘之作,难怪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佛教在日本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产生了许多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
一方面,是建筑、绘画、雕刻等表现了日本的佛教思想,另一方面,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佛教吸收了民族文化中的许多艺术元素,或者说日本佛教通过与其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从而更加符合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和接受习惯,最终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有特色的日本佛教。
三、日本佛教对传统文化的妥协——具有日本民族文化特征的日本佛教的最终形成
镰仓时代之后,日本佛教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佛教对于日本民族而言,已经不是外来异己文化,而是已经发展成了具有深厚日本文化特征和传统文化精神的日本佛教。其民族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特有的“祖师崇拜”情结
日本民族基本上是由同一祖先下的同一氏族组成,以皇室为中心,极其注重血缘关系。或者说日本传统文化的中枢就是皇室中心主义,这也是日本其他一切文化精神的源泉[5]。佛教自从传入日本之后,即受制于日本人特有的“天皇崇拜”与“祖师崇拜”的情结,也形成了日本佛教特有的“祖师崇拜”情结。如今在日本寺庙中随处可见的各宗各派的祖师殿,其规模甚至超过供奉释迦牟尼的大佛殿,每一个祖师殿中都供奉着各宗各派的开山祖师,而对于这些开山祖师的崇拜,其强烈程度甚至超越了对于释迦牟尼的崇拜。换句话说,日本民众在信奉佛教的同时,也使得民族意识通过祖师崇拜得以强化,从而使民族意识、祖师崇拜和佛教信仰融为一体,构成日本佛教的一大特征。
(二)传统的“自然主义”的倾向
日本民族文化一向尊崇人类的自然天性,日本佛教的又一大特征就是在充分满足人的欲望和感情这一意义上形成的“自然主义”倾向。日本佛教从尊崇自然人性的角度出发,将各种“清规戒律”予以废弃,即以自然人性排斥佛教所谓的“禁欲主义”,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也造成了日本佛教理论教义不够发达,却一味注重佛教建筑、绘画、雕刻等外在艺术形式的结果,并且由此诞生了一大批灿烂辉煌的佛教艺术文化遗产。
(三)鲜明的“入世精神”
事实上印度和中国的佛教都不乏积极的入世精神,中国佛教在一千多年的发展中也一直推崇自利利人、自觉觉人、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理念,然而将佛教的“入世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并推向极致的在世界范围内恐怕都非日本佛教莫属。这主要是由于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早有原始神道根深蒂固,随着佛教进入日本,并取代原始神道成为日本社会的主要宗教信仰,原始神道的独立地位丧失,但经过与佛教的斗争、协调,原始神道与佛教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6]。而原始神道所带有的强烈的现实功利性也附丽于佛教,从而使日本佛教蒙上了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实用主义的日本佛教在千余年来始终积极介入世俗事务,力图救世救心,无论是平安时代护国思想的发展,还是后来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发了日本佛教戒律上的变革,使得僧侣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并延续至今。日本佛教每一步的发展和变革,都伴随着日本佛教“入世”程度的不断加深,最终使得日本佛教附上了一层鲜明的“入世”色彩。
四、结语
日本的佛教是在吸收中国佛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最终成为具有日本民族文化特征的日本佛教。在这一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地吸收日本的传统文化,当与本土的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时,也大多呈现出“外来”的佛教向本土的传统文化妥协的倾向,这在其他民族的佛教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1]吴金霞,卜庆霞.日本佛教变质略论[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3(5):91-92.
[2]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7-76.
[3]楼晓洁.日本佛教发展之研究[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1):22-23.
[4]韦立新.试论佛教在日本化过程中的文化现象[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3):84-85.
[5]李向平.佛教信仰与日本文化精神[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60-63.
[6]郭青生.中日佛教入世精神的比较研究[J].浙江学刊,1998(4):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