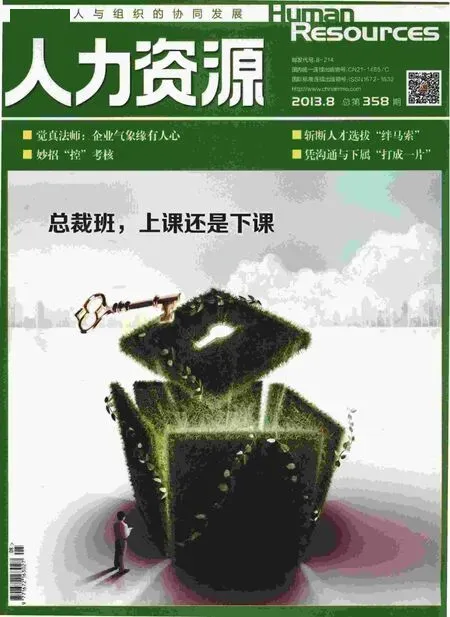造就“新市民”员工:主人翁精神是关键
张华强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城镇户口的逐渐放开,农民工的概念已经慢慢淡出职场,取而代之的则是“新市民”的称谓。如果说城市化主要体现在人的素质城镇化,需要“新市民”在精神层面更多地融入城市,那么,对于大多数“新市民”来说,则需要具体地体现为融入企业,在职业化中树立主人翁精神,分享企业的精神和物质成果。这其实就是将昔日“土地的主人”所蕴含的主人翁精神,通过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一次再发动。
“新市民”与企业的不解之缘
“新市民”的概念肇始于2006年,它的出现避免了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称之为“农民工”而产生的歧视倾向。然而,这个转换了的名词背后仍包含着政策需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诉求。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问题在于,如今,“新市民”的结构出现了新变化,这就是拆迁户新市民的异军突起。如果将农村进城务工的“新市民”称为外来新市民,那么,他们与拆迁户新市民的并存,也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所谓拆迁户新市民,原本是农民,多属城镇郊区的农民。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他们的土地被征,又属于“失地农民”,只不过随着郊区被规划为开发区,地价高起,他们获得了至少在目前来说还算数目可观的补偿款。没了地的农民进入企业“打工”后,具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他们不是外来务工者,而是本地人。在不少情况下,企业是为了利用当地的人脉资源、平衡各方面关系而聘用他们。第二,他们原有宅基地上的住房面积比较大,按照“拆多少补多少”的原则,一般可分到四套左右的单元房,因此有比较丰厚的拆迁补偿款和稳定的租金收入。因此,打工不再是他们解决家庭开支的唯一来源,而更像是第二职业。第三,企业效益不错的时候,他们乐见其成,但是当企业发不出工资时,他们随时可能拔脚离开。
随着拆迁户新市民的日益增多,新市民的队伍内部出现差异。与那些“农二代”进城务工人员相比,拆迁户新市民具有明显的优越感。他们的主流当然是好的,有较好的心态,有自尊和保持自尊的经济基础。比如武汉火车站站前广场有一位80后女环卫工,她开着15万元的轿车上班,家有四套房产,但是她仍然十分敬业。在同期被聘用的环卫工都先后辞职的情况下,她不离不弃,身兼环卫班长和质检员两个职务。但是也应当看到,这部分新市民也会因为拥有一
定的身家而产生“贵族化”倾向:对工作环境比较挑剔,更看重对业余生活的享受,随时可以驾着私家车离开公司。他们并不特别把基层管理人员看在眼里,对参加集体活动不够热心。如果基层管理人员是外来人,对他们这些本地人往往不敢大胆管理,而他们也不会轻易地“言听计从”。
这样一来,拆迁户新市民的“贵族化”倾向,往往会对企业管理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一些单一的激励措施很容易在他们那里“失效”。比如设在一个大型安置项目附近的西安某混凝土搅拌站,12名罐车司机中有6名属于本地人,搅拌站所在地就是他们村原来的农田。司机的工资由基本工资与出车提成构成,后者主要是为了鼓励司机多出车,即每出一趟车提成10元左右。但是这6名本地司机都拿到过数目可观的拆迁补偿金,都有闲置房可出租,都开着轿车上班,即使多出车,每月也只不过多拿一千多块钱,所以他们出车并不积极,只满足于拿基本工资,让自己有份职业有份收入保障即可。这对他们个人来说是“合理”的,但对企业来说则“苦不堪言”——不仅显得管理松散,而且不能提高效率。进一步说,企业如果只对外来新市民进行严格管理就有失公允。
重振“主人翁精神”
企业应该清晰地意识到,既然拆迁户新市民与外来新市民在经济条件上存在如此大的差距,那么,对二者主人翁精神的重振也应“因人而宜”,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说在拆迁户新市民身上多少有着“被城市化”的成分,那些有土地却“手无寸金”的农二代进城,更像是到城市“追梦”。重振后者主人翁精神,重点在于帮其扫除物资和精神上的设限障碍;而对于拆迁户新市民,重点则应当是怎样帮助他们从“失地富翁”回归到“企业员工”的正常生活轨道上来。比如,帮助他们放下本地人的身段,不要因为企业离不开本地人脉资源的支持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促使他们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企业的各项变革措施和一视同仁的管理。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提升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而不仅仅是有利则合、无利则散。
从积极乐观的方面看,拆迁户新市民与外来新市民的待遇基本相同,可以和谐相处。作为“失地富翁”,拆迁户新市民能够在底层岗位上选择一份工作,说明他们不想坐吃山空。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从土地主人的惯性中走出来,学会或者适应做企业的员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有责任帮助他们尽快结束在土地和城市之间的彷徨,以企业主人翁精神的重振完成新市民的城市化。
重振新市民企业主人翁精神的基础是职业化,然而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职业化,需要企业为其提供精神载体。在上文某混凝土搅拌站的例子中,拆迁户新市民能够胜任罐车司机的工作,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职业技能。而且,他们在获得土地补偿款之后,也不会吝于在获得一技之长方面进行投资。此外,既然他们大多数是在家门口就业,曾经是脚下这片热土的主人,那么,以企业生产的形式再度找回主人翁的感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问题在于,其经济上的富足有可能导致职业道德和职业心态的缺失,而这恰恰需要企业积极跟进,及时为他们补上这至关重要的一课,以帮助他们实现从自由人到职场人的角色转变。
现代企业的经营活动与传统农业生产有所不同,拆迁户新市民由农民转化为企业员工,其主人翁意义主要体现为包括对团对协作精神的弘扬、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等。
重振主人翁精神,首先应当是企业与拆迁户新市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拆迁户新市民在经济条件上与城市居民已经没有区别,企业应将他们纳入常态管理。而拆迁户新市民也应该意识到,他们需要改变的不是曾经的农民身份,而是生活方式、从业方式以及思想观念。
其次,拆迁户新市民与外来新市民可以相互认同。前者可以对后者亟需增加收入的愿望表示理解,
但也不能把自己当做职场上的“替补队员”,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二者都可以成为企业的骨干力量。
再次,拆迁户新市民应当对企业的制度、规定实现认同。团队协作需要制度约束,既然是企业的主人,无论是拆迁户新市民,还是外来新市民,谁也不能例外。
通过“分享”提升角色意识
重振新市民的主人翁精神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体现个性特色,又不可能按照统一的模式生搬硬套。可以肯定的是,它绝不是对员工尽职尽责的单方面要求,而是需要通过让大家分享企业的现实回报体现出来。比如,让新市民拥有企业一定的股份,分享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喜悦,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等等。在沃尔玛,公司员工被称为“伙伴”,国内不少企业将员工称为“家人”,称谓上的变化意在传达企业将员工作为主人的积极讯息。
重视对拆迁户新市民进行精神上的鼓励,校正他们“小富即安”的心态。拆迁户新市民一般人到中年,文化程度不高。因拆迁获得的可观补偿金是他们过去未曾想到的。他们的父辈因拆迁可以获得基本的养老保障,而下一代的安置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因而,他们对现状比较知足,这种“满足”表现在工作上,就表现为缺乏工作动力。这其实是对企业激励机制的一种考验。不少企业对员工的激励往往侧重于那些肯加班的外来新市民,其实,拆迁户新市民同样需要精神上的鼓励,企业在评选先进的时候千万不能把他们边缘化。毕竟各有各的精彩,应当对他们的精彩予以及时表彰,否则长此以往,企业很难对他们产生凝聚力。
克服实用主义的用人观,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拆迁户新市民物资生活条件比较稳定,对脚下的这片热土有特殊的感情,完全可以成为企业发展的骨干力量。但是,企业在使用他们时往往标准不高。这样的工作思路难免让一些本来有热情想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新市民员工冷了心,久而久之,更像是企业的客卿。在上述武汉火车站环卫工的例子中,最初招聘的七十多人中,许多人因嫌待遇较低,不到一周就离职,最终只剩下15人。而那位开私家车上班的80后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在于企业对她的重用,让其承担起管理十多位员工的职责。由此可见,企业在用人时应改变这种“短视”的用人观,有必要按照正常的工作标准要求拆迁户新市民,充分调动和激活他们的主动性,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也是企业的主人。这样,即使是帮助企业平衡当地的利益冲突,他们也会从被动应对变为主动维护。
在具体工作中进行合理搭配,使之与外来新市民形成优势互补。应当承认,拆迁户新市民相对于外来新市民而言比较难管。个别的还会在受到处罚后对基层管理者恶语相加。但是,人力资源管理者应该清楚,只要将他们的优势发挥出来,就可以顺利将他们的“强势”态度转化为企业主人翁的满足感。这里所说的合理搭配,指的是根据拆迁户新市民与外来新市民的不同特点,在内部分工方面进行优化组合,以各自的个性特色体现主人翁精神。仍以上述的西安某一搅拌站为例,如果每辆罐车要安排两名司机倒班,该搅拌站就有意识地在每辆车上安排拆迁户新市民与外来新市民各一名,因为拆迁户新市民喜欢正常上下班,而外来新市民则希望多加班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样,当需要加班的时候,二者就不会因为争夺利益而发生争执,反而顺畅和谐,各尽职责,从而保证了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当然,在类似的分工合作中,一定要让拆迁户新市民与外来新市民一样,都有出彩的满足感。
一个具有发展眼光的企业,必然深谙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之道,懂得发掘不同“族群”的内在需求。对于“新市民”群体来说,企业通过重振其职场主人翁精神,才能同时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