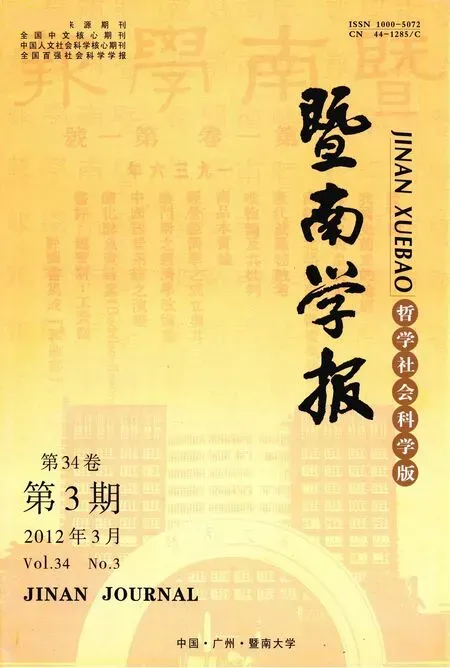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
单韵鸣
(华南理工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
单韵鸣
(华南理工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通过问卷调查、模拟情景调查和语料库搜索等手段,调查分析了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结果显示广州人最常用“VCO+佢”的形式;“VCO”式常用度排行第二,说明在不用“佢”的情况下,VO语序的“VCO”式仍是表示处置义的优选句式;“‘将’字句+佢”排第三;“将”字句排最后,是广州人说得最少的形式。结果反映出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依然是方言特征明显的形式占优,未有出现向普通话真正靠拢的趋势。语料库搜索到的语料还证明不管是“‘将’字句+佢”还是“将”字句都常见于谈论时政类话题的话语当中。
广州话;处置句;变异;调查;语料库
语言变异(language variation),笼统来说指的是某个语言项目在实际使用着的话语中的状况[1]48,更确切地说是语言结构系统中某些内容的实现形式不唯一的现象[2]3。广义的语言变异包括语言历时的变化,即通常所说的“语言变化”,狭义的语言变异则只针对使用语言项目时的共时差异,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语言差异。本文所论述的变异主要是指狭义的语言变异。根据语言变异的定义,语法变异是指具体某个语法项目的变异。这个项目可以是某个语法范畴(如时、体、态、性)、语义—语法范畴(如程度范畴、否定)、词类(如形容词、副词、动词)、具有相同句法分布的词形成的组合或结构(如such…、“副+名”、“有VP”)以及某项语法规则等等[3]。句式是表达特定语义的一种句法规则,句式的变异顺理成章也属于语法变异的一种。
一、关于广州话的处置句
(一)普通话和广州话的处置句
普通话中体现处置义常用“把”字句,广州话中句法结构跟普通话“把”字句相当的是“将”字句。李炜[4]细致地比较了普通话的“把”字句和广州话的“将”字句,指出广州话中只有在实施者主动地、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对某个特定的人或物以某种动作行为方式进行处理或施加影响,使之产生某种结果、发生某种变化的情况下才使用“将”字句。同时,他认为“把”字句在普通话里是常用句式,“将”字句在广州话里则是“极不常用的”。广州话里几乎没有只能用“将”字句而不能用其他句式的情况,在可供选择的若干句式中,正常情况下“将”字句“很少被选择”。李炜举了一些例子说明SVO型的句式才是广州话的常用句式:
(1)抹干净张台。(把桌子擦干净。)
(2)我唔记得晒呢件事。(我把这事忘光了。)
(3)佢放本书喺嗰度。(他把这本书放在那儿。)
(4)掟个波去水度。(把球扔到水那里。)
(5)拉佢落嚟。(把他拉下来。)
李炜还调查了不同文化层次的广州人使用“将”字句或用SVO语序的表达方式来表示处置义的情况。他发现,大多数的广州人认为使用“将”字句总给人以“文气”或“书面味”的感觉;“将”字句常用度的高低可能与言者的文化层次有正比关系。由此他推断,广州话“将”字句常用度的提高是受到普通话影响的结果,以后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普及、提高,“将”字句的范围可能会扩大,常用度也会不断提高。李炜的研究反映出以下三点:(1)广州话表示处置义时存在句式的变异,且变异的句式有明显的语序差别,“将”字句的语序跟普通话一致,而SVO型的处置句则体现广州方言特色。(2)变异与使用者的文化水平相关。(3)变异可能反映出广州话向普通话靠拢的状况和程度。
广州话向普通话靠拢的状况和程度如何是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广州话的处置句存在句式的变异,且变异的句式有明显的语序差别,那么研究广州话处置句的变异正是观察广州话向普通话靠拢的状况和程度的一个切入点。
(二)广州话典型狭义的处置句
广州话的处置句除了用“将”字句,还有三种表达方式,一种是VO语序的VCO式(有独立补语时为VOC式),一种是在VCO句式的宾语后再用“佢”(它/他)来复指被处置的对象,还有一种是在“将”字句加上代词“佢”(它/他)来复指“将”的宾语——被处置的对象。以普通话一个常见的表示典型处置义的句子“把门关上”为例,广州话就有4个说法:
(6)闩好道门佢。
(7)闩好道门。
(8)将道门闩好佢。
(9)将道门闩好。
麦耘[5]曾对复指受事者的“佢”有过较细致的研究。他指出不是所有处置句的受事成分都能用“佢”来复指,下面的情况就不能用“佢”:
(一)“将”字句带“成(或“为”)”字补语的情况:将个故事拍成电影。(把故事拍成电影。)
(二)VO后有独立的补语:搬晒啲凳上嚟(把凳子全部搬上来。)
(三)在双宾语中:将本书畀我/畀本书我(把书给我。)
(四)VO中的受事宾语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人称,用“佢”会造成矛盾或重复。
(五)有些处置义不很明显的“将”字句也不能用“佢”:将个仔闹咗一餐。(把儿子骂了一顿)。
可见,带复指受事成分“佢”的处置句是广州话处置句里面使用范围最窄的,用VCO句式表示处置义以及单纯的“将”字句,它们的使用范围都比带“佢”的处置句广。不过,VCO“VCO+佢”、“将”字句、“‘将’字句+佢”四个表达句式之间会有交集,带“佢”的处置句一定能用VCO或“将”字句来替换表达,而且处置义非常明显,相反,部分VCO句式和“将”字句的处置义就不一定很明显,如“做完啲功课喇(作业做完了)”和“将个仔闹咗一餐(把儿子骂了一顿)”。因此,可以认为,带复指受事成分“佢”的处置句是广州话处置句里面最典型狭义的一种为了能更准确地定义变项和变式,让调查更具操作性,本文立足于带复指受事成分“佢”的处置句式,研究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
二、研究方法
(一)变项和变式的确定
“变项(variable)是变异具体表现形式的集合……一个‘变项’总是由一组特定‘变式’(variant)组成。”[6]由于句法系统的无定性(non-finite),讲话人在表达某个意义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语法形式供选用,句法形式的选择还很容易受到语用和语义因素的制约。对语法变项的确立目前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2]112。在众多的标准当中,我们比较赞同语义对等的标准,就是在表达同一语义时不同的形式即可确定为不同的变式。不过人们说出来的形式有可能千差万别,如果不排除语用因素和词汇因素,就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变式,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尽量摒除语用因素对“形式”的干扰,并且要对众多的“形式”进行归纳,然后才能确定有限个变式来进行研究。
基于这一原则,我们把“典型狭义的处置句”看作一个变项,VCO、“VCO+佢”、“将”字句、“‘将’字句+佢”等四个能互相替换的说法视为变项的四个变式。可能有人会问,用了“佢”的处置句,处置义会不会有所加强而形成变式之间语义的不对等?凭我们的语感,只要“佢”没有被重读,处置义没有特别加强的意味。如果“佢”重读了,当然处置的意味就强了。同理,即便是没有“佢”的另外两句,只要重读末尾的音节,同样有加强处置义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认为句子有“佢”没“佢”意思或语气就会差别很大。这四种说法形式各有特点,在体现方言特征上各有侧重,变式1是“VCO+佢”,这个变式方言特色最强,既用VO语序,又用复指受事成分的代词“佢”;变式2是“VCO”,该变式的语序区别于普通话,也反映一定的方言特色;变式3是“‘将’字句末尾+佢”①麦耘(2003)提到有时“将”句中的“佢”不在句尾,如“将眼螺丝拧到佢实一实(把那枚螺丝拧得紧紧的)”,不过这种情况不多,而且有句法限制,就是要“当表示结果的成分……以其他形式形成独立补语时”,“佢”才放到动词与补语之间。因此,我们暂不考虑这种情况,而选较常见的“佢”字在末尾的形式作为变式3。,句式结构与普通话的“把”字句相近,末尾用复指受事宾语的代词“佢”,仍保留一些方言的特色;变式4是“将”字句,句式结构跟普通话完全相同。
(二)调查方法
我们将结合使用三个方法来进行调查:一是问卷调查法,根据设定的变量抽取一定数量的广州人对变式的常用度进行调查分析;二是模拟情景调查,选取数个广州人,让他们在多个模拟情景中说出自己的话语;三是对广州电台节目的语料进行搜索调查。
1.调查问卷的设计
我们只调查一个用例,考察人们习惯上要表达“把门关上”的语义时使用四个变式的频率是否存在差异。尽管只调查一个例子,但该用例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又具有典型的处置义,而且我们将要调查具有一定数量规模的广州本地人,在一定数量保证下的调查结果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我们要求每个被访者按平时的说话习惯判断“闩好道门佢”、“闩好道门”、“将道门闩好佢”、“将道门闩好”这四个说法(即四个变式)的常用度,选“3”表示“经常说”,选“2”表示“也说,但不是经常”,选“1”表示“极少说甚至不说”。四个变式可以选相同的常用度。如果四个变式都不符合他的说话习惯(即没有一个选“3”的),要写出符合他说话习惯的句子。
2.变量的设定和抽样方法
我们调查的整体对象只限于广州出生,最好是在荔湾、越秀(包括旧东山区)、海珠这几个传统老区长大的,母语是广州话的本地人,这样调查结果会比较有代表性。
我们假设变项不同变式的常用度跟被访者的年龄和文化水平有关,即被访者的年龄和文化水平是自变量,变式的常用度是因变量。就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只关注成年人的语言状况。对于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划分标准,目前世界各国、国际组织和我国都尚无明确统一的界定。参照过往的一些调查研究[3][7][8][9],我们界定20-35岁为青年,36-55岁为中年,56岁及以上为老年。
文化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分层的作用。我们把文化水平分为两段,20-45岁的人群接受过本科或以上教育的属于“本上”段,本科以下(大专、高中、职中、初中等)的属于“本下”段①把本科与大专分开,是考虑到两个现实的情况:一是上本科接触到的同学更大机会来自五湖四海,而读大专接触到的同学更多的来自本地或本省,从语言接触的程度来看,上本科的人会比上大专的人深;另一方面虽然本科和大专同属高等教育,而实际上接受这两种不同学历教育的人毕业后,职业的层次有差别,从而形成不同社会地位和社交圈子。语言接触的程度、社会地位、社交圈子等都会对他们的语言产生影响,所以调查时我们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历史原因,46岁及以上接受过专科或以上教育的就可认为属于“本上”段了,专科以下就属于“本下”段。利用滚雪球的方法,共回收有效答卷238份,为了均衡各年龄小段(以5年为一段)的人数,我们抽取青年、中年各60名,分“本上”和“本下”各30名,共得4组,每组30人;老年共30名,分“本上”和“本下”各15名,得两组,每组15人。虽然后两组人数少了,但用于比较性研究②在统计分析的过程中,分年龄三段、文化水平两段,形成6个比较组,从这点来看,我们的研究也属于比较性研究。,15人也在可接受人数的范围[10]125。这样我们总共从238份答卷中选取了150份样本作为最终统计分析样本。
性别我们不作为特别关注的社会因素来抽样,在选取的150个样本中,男的共71人,占总样本数量的47.3%,女的79人,占总样本数量的52.7%,两者人数大致均衡。我们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男女之间在判分上的差异。结果显示,男女在判断变式的常用度上面没有显著差异,t=-.031,df=148,p=0.975。
3.模拟情景调查
我们设计了10个需要使用处置句的模拟情景③我们要求被访者在模拟情景中说出自己或者别人要如何处理的话。10个情景用文字可描述为:①有一张凳子摆在路中间,挡住了去路,需要移开。②地上的东西非常杂乱,需要收拾。③发现饭锅里有毛毛虫,需要剔开。④房间里的窗帘都落下来了,房间里很暗,窗帘需要拉开。⑤垃圾桶里的垃圾已经很满了,需要倒掉。⑥饭菜已经凉了,需要加热。⑦饭菜只剩下一点,不要浪费,最好吃完。⑧衣服很脏,需要认真洗干净。⑨同事留下手尾活,要让他自己收拾。⑩桌子有根螺丝松了,要扭紧。,在150个样本当中选取6人,编号从1号到6号,他们分别属于老年本科上、老年本科下、中年本科上、中年本科下、青年本科上和青年本科下6个不同群体。我们让每个被访者分别置身于10个模拟情景中,让他们在自然的状态中说出他们的话语,继而得到共60个输出话语可供统计分析。
4.语料库的制作
我们选取了由广州电台制作的各类清谈和访谈节目,共21小时,作为语料库的语料来源。这些节目内容多样,语言输出者的年龄跨度也比较大,言语全部是未经处理过的原生态话语,能较真实地反映出现代广州话的语言面貌。21小时电台节目的转写工作完成以后,共获得近30万字的广州话话语文本材料,用以检验或补充调查结果。
三、调查结果
(一)问卷调查结果
我们对四种变式的常用度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四种变式的常用度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F(3,,447)=16.16,p=0.000。使用Bonferroni多重比较法对四种变式两两之间差异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变式1和变式2之间差异显著,均值差为0.35,p<0.01变式1和变式3之间差异极为显著,均值差为0.47,p=0.000。变式1和变式4之间差异极为显著,均值差为0.64,p=0.000。变式2和变式3之间差异不显著,均值差为0.13,p=1.00变式2和变式4之间差异显著,均值差为0.29 p<0.01。变式3和变式4之间差异不显著,均值差为0.17,p=0.34。四种变式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变式1、变式2、变式3、变式4。变式1与其余句式之间差异显著;变式2和变式3之间差异不显著,和变式4之间差异显著;变式3和变式4之间差异不显著。
我们再使用两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的群体使用四种不同变式的情况。对于变式1,数据显示,年龄和文化水平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F1(2,144)=2.00,p1=0.14。年龄对变式1的常用度影响显著,F1(2 144)=4.14,p1<0.05。文化水平对变式1的常用度影响不显著,F1(1,144)=0.56,p1=0.46。使用Scheffe检验法对年龄的主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变式1常用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年、青年、老年。排序后相邻的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只有头尾两个群体之间差异显著。
我们再使用两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的群体使用四种不同变式的情况。对于变式1,数据显示,年龄和文化水平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F1(2,144)=2.00,p1=0.14。年龄对变式1的使用频率影响显著,F1(2,144),p1<0.05。文化水平对变式1的使用频率影响不显著,F1(1,144)=0.56,p1=0.46。使用Scheffe检验法对年龄的主效应进行检验,发现青年讲变式1的频率低于中年人,但差异不显著,均值差为-0.15,p=0.57。青年将变式1的频率高于老年人,差异不显著,均值差为0.35,p=0.14。中年将变式1的频率高于老年人,差异显著,均值差为0.50,p<0.05。概括起来,变式1使用频率有高到低依次为:中年、青年、老年。排序后相邻的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只有头尾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显著。
再看其他变式的情况。使用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变式2、变式3和变式4,年龄和文化水平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年龄的主效应也不显著,文化水平的主效应同样不显著。换句话说,变式2、变式3和变式4的常用度在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水平的群体之中都没有显著差异。
(二)模拟情景调查结果
我们共得到60个输出话语,整理分类后得到下表1。

表1
(三)电台节目语料库的搜索结果
不含“佢”的处置句在表达上没有特殊的词汇标记,难以在单纯的文字数据库中检索出变式2的例句,其余3种变式的情况则都能用“佢”和“将”来检索,并筛选确认出来。经过搜索和确认,变式1只找到一例:
(10)炒香啲黄豆佢。(把黄豆炒香。)《招积叹世界》
变式3找到9例,其中6例出现在连通观众讨论时政话题的《由理话事》节目中,其余3例零散散布在三个节目中,如:
(11)即係你就将啲痛苦根源斩咗佢啦嘛。(就是你就把那些痛苦根源斩断了嘛。)《拉阔车厢》
(12)其实将佢嘅通菜就灼咗佢嗻(其实把通菜烫熟而已。)《招积叹世界》
(13)亚运会即将召开,噉我哋呢就将个城市扮靓佢,噉当然亦都係情理之中嘅事情。(亚运会即将召开,那我们把城市打扮漂亮,那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由理话事》
(14)要搞干净你个车尾箱其实好简单嘅啫,……将个尾箱垫呢抽佢出嚟,用软刷啊同埋啲清洁剂卒翻靓佢。(要搞干净你的车尾箱其实很简单,把尾箱垫子抽出来,用软刷和清洁剂把它擦干净。)《车生活》
变式4找到8例,其中3例也出自讨论时政话题的《由理话事》节目中,余下5例也是散布在其他节目当中,如:
(15)将一张相呢,斩开。(把一张照片呢,砍开。)《游车河》
(16)我决定呢,暂且将呢个念头放低。(我决定呢,暂且把这个念头放下。)《电影世界》
(17)你将啲丝瓜呢,洗干净,刨皮,切丁。(你把这丝瓜呢,洗干净,削皮,切丁。)《招积叹世界》
(18)我漫画入边咪话就将我以前细个呢个烂gag5画落去。(我漫画里面不就说了,把我以前小时候这个烂笑话画了进去。)《时尚东西》
(19)你将以前应该做嗰啲做翻好就得喇。(你把以前应该做的那些重新做好就行了。)《由理话事》
四、分析和讨论
四种变式的常用度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在共时层面,广州话典型狭义的处置句存在极其明显的变异。四种变式的常用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变式1、变式2、变式3、变式4。变式1的常用度与其他句式之间差异显著,变式2和变式4的常用度差异显著,但与变式3的常用度差异不显著。由此得出:(1)变式1的常用度在四种变式中独占鳌头,“VCO+佢”的表达形式是广州人的最爱;(2)变式2和变式4都不含“佢”,变式2的常用度显著高于变式4,说明不用“佢”时,在VO语序和将字句之间,人们仍倾向多用VO语序。这与李炜的观察一致,时隔近二十年,不用“佢”时,广州话典型狭义的处置句依然是VO语序强势;(3)变式2虽然比变式3的常用度高,但差异不显著,意味着“佢”在“将”字句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没有“佢”的“将”字句完全不具备优势,一旦“将”字句后有了“佢”,句式的方言特征加强,在常用度上就能拉近与变式2的差距。
以上发现获得模拟情景调查结果的支持。在60个输出话语里面,4个变式的出现数量从多到少的排序与问卷调查结果完全相同。变式1共有25句,占总量的41.7%,稳稳占据第一的位置。变式2共有19句,占总量的31.7%,变式4只有3句,占总量的5%,两者数量的悬殊证明VO语序的处置句远比“将”字句常用。变式3出现了7次,占总量的11.6%,出现频率比变式4高,与变式2的差距确实要少一些。
至于语料库的搜索结果,只要留意句子的节目出处就会发现,不管带不带“佢”,“将”字句出现最多是在《由理话事》节目中。该节目讨论时政热点,讨论时政话题或许会对人们潜意识选择的句式造成一定的影响。余霭芹[11]就“比”字句曾调查数十名讲粤语的被访者,“比”字句被认为是“斯文”的说法,而李炜就“将”字句的调查,被访者也认为“将”字句给人“文气”的感觉。两个句式给人感觉一致,说明“比”字句和“将”字句应该常在同一个语域内被使用。潘小洛[12]调查过粤语“比”字句出现的语域,发现“比”字句常用于新闻广播中,按此推理,“将”字句也应常用于新闻类节目中那么人们在讨论时政话题时潜意识倾向选择“将”字句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只比较《由理话事》节目中变式3和变式4的数量,变式3的数量是变式4的数量的2倍(6句:3句),也能说明即便是用“将”字句,带“佢”的“将”字句还是比不带“佢”的“将”字句常见,结果与问卷调查和模拟情景调查结果一致。撇开《由理话事》这个时政类节目,其他节目三个变式的语料数量都不多,而且都是零散散布于各个节目当中的,单从那么少的数量很难判断出实质性的差别来,因此关于四种变式常用度差异的结论主要立足于前面两个调查的结果。
问卷和模拟情景的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就典型狭义处置句这个语法项目来看,广州话仍然坚持方言特色,并未有向普通话真正靠拢的趋势。
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四种变式常用度的群体差异只体现在变式1上,主要是年龄段的差异,中年人使用变式1最多,青年和老年渐次之。其余三个变式的常用度均在不同年龄或不同文化水平的群体中没有显著差异。由于我们只在6种群体中选取了一个人作模拟情景调查,语料库得到的语料也不十分充分,各个变式常用度的群体差异有待日后再做检验。
五、结 语
我们使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模拟情景调查和语料库搜索等手段,调查分析了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结果显示广州人最常用“VCO+佢”的形式;“VCO”式常用度排行第二,说明在不用“佢”的情况下,VO语序的“VCO”式仍是表示处置义的优选句式;“‘将’字句+佢”比“将”字句常用,排第三;“将”字句排最后,是广州人说得最少的形式。结果反映出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依然是方言特征明显的形式占优,未有出现向普通话真正靠拢的趋势。语料库搜索到的语料还证明不管是“‘将’字句+佢”还是“将”字句都常见于谈论时政类话题的话语当中。
[1]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2]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3]曾炜.变异视角下的语法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4]李炜.“将”字句与“把”字句[C]∥郑定欧主编.广州话研究与教学.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5]麦耘.广州话以“佢”复指受事者的句式[C]∥詹伯慧主编.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彭小川,陈启萍.广州话类同义副词历时演变的特点与机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8]伍巍,陈卫强.一百年来广州话反复问句演变过程初探[J].语言研究,2008,(3).
[6]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004.
[9]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广州市团校.广州青年发展状况报告[A].广州日报,2011.1.10.
[10]张延国,郝树壮.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1]余霭芹.Syntactic change in progress,Part I: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in Hong Kong Cantonese[C]∥余霭芹,远藤光晓共编.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东京:内山书店,1997.
[12]潘小洛.广州话的比较句式[C]∥单周尧,陆镜光主编.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
The Variations of Typical and Narrowdefined Disposal Construction in Cantonese
SHAN Yun-m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China,510640
Through questionnaires,investigation in simulation scenario and a thorough search in corpus,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variations of typical and narrow-defined disposal of construction in Cantonese.It shows that the variant of“VCO+佢”is most commonly used by Cantonese people;the variant of VCO comes to the second which implicates that without using“佢”,the variant in VO word order is still the optimal choice;the variant of“Jiang's construction+佢”is at the third place;the variant of Jiang's construction is the last choice that Cantonese people choose to speak.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as to this disposal variable,the Cantonese construction is still characterized by the dialectic features,resisting the influence from Mandarin.The texts from the corpus also prove that“Jiang's construction+佢”and Jiang's construction are both commonly applied when people talk about political topics.
Cantonese;Disposal Sentence;Variation;Investigation;Corpus
H07
A
1000-5072(2012)03-0118-06
2011-10-18
单韵鸣(1978—),女,广东广州人,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粤方言语法与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项目《粤方言语法变异研究》(批准号:GD10YZW06);广东省教育厅“育苗工程”项目《广州话语法变异研究》(批准号:WYM10055)。
*文章得到导师郭熙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表谢意。文中谬误由本人负责。
[责任编辑 范俊军 责任校对 王 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