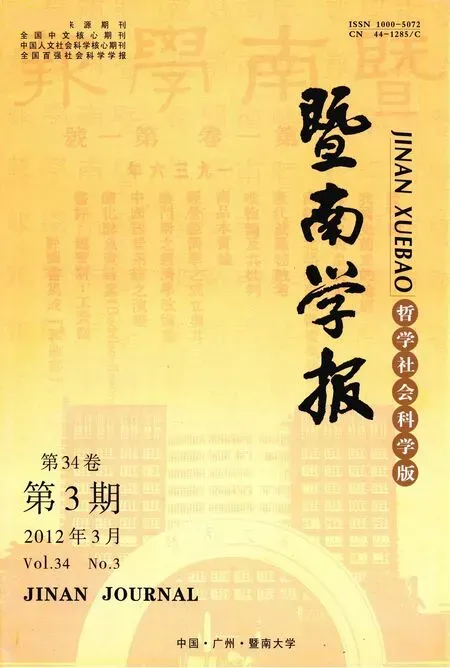南京政府时期英法两国对华租界政策调整的差异性——以1932~1933年上海法租界私立学校争取补助费运动为中心
陆华东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南京政府时期英法两国对华租界政策调整的差异性
——以1932~1933年上海法租界私立学校争取补助费运动为中心
陆华东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英、法两国在华租界在应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与渐趋强大的威权政治的双重挑战时,均采取了相应政策调整,但调整的步调并不趋于一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即英租界的调整政策有较强的主动性与灵活性,而法租界的调整政策则显得被动与滞后。这种现象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一是两国在华租界面临的外交压力不同;二是英、法租界内的华人参政水平的悬殊;三是两国在华租界的政治运作的文化理念及权力结构的差异。
租界;法租界;私立学校
近代英、法两国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建立了诸多租界,长期以来,由于受各自国家的文化传统及政治理念差异性的影响,以及相伴生的租界内华人参政力量不同的现实因素的制约,两国在华的各租界在施政理念及权力运作方面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但造成了它们在政治运作风格上的悬殊性,还深深地影响了它们在应对来自中国民众、官方的历次挑战时的政策选择。对于近代中国租界史的研究,学术界已有相当的成果问世,但在研究旨趣上,同质性取向较强,而差异性的关注则明显不够。①关于上海两大租界的差异性:(法)梅朋傅立德所著的《上海法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出版)、白吉尔(法)所著王菊∥赵念国译的《上海史:走向现代化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出版)两书中曾有精彩阐述,国内的租界史研究中也对英、法租界的不同点也有所分析。但相比较而言,对于这种差异性及其引发的中外政治冲突的模式不同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基于此,本文以1932~1933年发生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场私立学校要求法租界当局给予经费补助的请愿运动为个案研究,通过对这场运动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力图管窥运动背后所内含的丰富的历史脉象,以揭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英、法两国在华租界对华政策的差异性及深刻缘由。不足之处,请方家见谅。
一、“援公共租界之条例”——运动兴起之缘由
近代上海私立学校是整个城市教育体系中的主干,这在南京政府时期表现尤为突出。以1931年为例,是年全市共有各类公私立学校829,其中私立学校585所,所占比例达70.5%[1]35,而这些私立学校又多兴办于两大租界,还是以1931年为例,该年447所初等私立学校中的226所、114所私立中等学校中的64所分布在租界之内[1]37。长期以来,租界内的华人私立学校为上海城市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它们又多处于自生自灭、缺乏援助的困难境地,其主要原因就是租界当局推行了“厚西薄华”的教育歧视政策,不承担相应的发展公共教育的政府职能,从而使租界内的华人教育事业异常落后。以1927年以前的公共租界为例,一方面租界当局所办学校规模极小,仅接办了华童学校4所,入学儿童比例尚不足学龄华童的1%,学生只好入租界内外的私立学校就学,另一方面,教育政策上实行“中外有别”政策,4所华童学校所占比例仅占全部教育经费的1/3,而界内的数百所华人私立学校除享受所办学校校舍可免征部分房捐的政策外,其他没有任何补助,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租界内华人教育发展。教育政策不公平及工部局不承担教育责任,不但受到了华人的指责,连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是租界政策的一个严重的缺陷,如费唐在其著名报告书里就认为“关于指责租界内华人教育向无相当设备之确有根据。”[2]19
1927年以后,在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压力下,英国当局为确保其在中国特别是上海的租界的生存,逐渐改变了租界政策,主张“在保持外人的优越地位的同时实行中外合作。”[3]252表现在租界教育改革方面就是逐渐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能,工部局当局从1927年开始一方面新创办了一所中学,7所小学,4所青工夜校,承担了部分办学责任,另一方面决定以“为公共租界内居民之子弟及直接或间接纳税者之儿童设备相当之教育机关,而不问就学者之国籍。但非谓设置是项机关之责任,由本局或应归本局单独担当,本局对于各国侨民团体、会馆、慈善或宗教机关或有相当资格之个人所设学校,一致欢迎。”[4]477为指导方针,加大对各类私立学校的扶持力度,决定“自1932年起,凡私立学校,其管理设备及教学设备等认为满意,而有发展之可能者,一律予以补助。”[5]181补助的标准是将学务预算单独划出,作为工部局的专款,用以补助界内的中外私学及中西儿童学校,1932年的学务预算额为银1923520两[6]344。补助的形式“一是豁免中外人士所办学校校舍应纳房捐之一部分,籍资补助。二是直接补助。”[5]181尽管受“一.二八”事变的影响,该项补助没有完全落实,但该年的工部局补助私校的金额仍达115384元,依旧可观。
更为重要的是,工部局当局还在私立学校的管理上与上海市教育局达成了“合作”共识即公共租界当局承认中国政府对界内的私立学校拥有管理主权,认为“公共租界内之华人私立学校,应尽量使之与华界各校办法一致,此乃工部局之期望。界内非工部局设立之华童学校全由华人管理,除因租界特殊情形外,绝未受任何限制。依照中国法律,其管理权实在上海市教育局。”[7]在补助经费的标准上,基本达到了大学院提出的“租界当局应从华人方面收入的市政经费中提出至少20%经费举办华人教育”[8]的比例标准。在补助的操作程序上,也以上海市教育局的主导意见为主,即“已在上海市教育局立案或正在立案的学校,其申请工部局经费补助,须向上海市教育局呈递申请书,未立案的学校向工部局直接申请”[9]472。通过这种形式的合作,在补助标准与程序方面,华界与公共租界当局均达成了默契,既有利于上海市教育局对公共租界内私立学校的管理,也有利于公共租界内私立学校的自身发展,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成功的租界教育的管理政策。
而与公共租界内的私立学校的有利政策形成极大反差的则是法租界的各私立学校直至1932年依然没有享受法国公董局方面的同等待遇。近代上海的法租界尽管在经济实力方面较公共租界为弱,但它环境幽雅,宜居性强,人口也很密集,至1932年界内“人口达4795751人,其中华人占478755人”[10],学龄儿童数为125700[11]84。但界内的华人教育则尤其落后由于法租界当局长期实行“华洋有别”的教育歧视政策,直至1932年界内仅有设立于1886年的中法公学及新设立的华童小学两所,这对于界内的庞大的学龄儿童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在教育经费的支出上,1932年全年的教育预算费为218200两,而其中西童学校占去130000两,两所华童学校仅占88200两。”[11]85至于界内数十所私立中小学校除部分享受减免房地捐的优惠政策外,(注:1932年对华人私立学校免捐补助仅为8277两,而对局办各类学校的现金补助达20701两[12])没有任何现金补助。在1932年公共租界的私立学校首次被纳入工部局的教育经费预算的范围政策的鼓舞下,法租界各私立学校开始进行了要求“援公共租界之条例”的诉求运动。
二、运动的过程及各方态度
(一)运动的准备阶段
该运动的发起人为法租界私立华东女子中学的创办者马家振。为争取法租界私立学校获取公董局经费补助的要求,在他的倡导与组织下,法租界私立学校争取补助费的运动逐渐展开。
首先是成立了运动的领导机构——法租界私立学校联合会。为能使行动有组织地进行,马家振于1932年11月2日向各学校发出邀请函,号召各学校于5日在该校开会并采取一致行动。邀请函的内容是“本市法租界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教育欠发展,急不容缓,界内学校,虽达数十,然多私立。往往以经费支绌,无法扩充。切念法租界当局向我华人每所收之税,为数至巨,而对我华人之教育事业之负担,我教育界同仁,似宜急起直追,要求公董局,按照公共租界之办法,将每年税收之一部分,补助私立学校,并创设华人学校,以期教育发达。并定于11月5日下午1时,在鄙校专议办法,届时务请贵校派员出席,共商进行。”[13]邀请函发出后,得到社会各界及法租界内各私立学校的响应,“本市教育行政当局及市党部、市教育会,均表示同情,并将予以有力的赞助。至各私校响应者,已达30余校。”[14]11月5日各私立学校派代表在华东女子中学进行集会,第二日由马家振等牵头组织了运动领导机构——法租界私校联合会,该会以“联络感情,促进教育,发展私立学校”[11]108为宗旨,“入会中学11所,入会小学38所,还组成了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15]
其次,积极寻求外界支持。私校联合会成立当天,首先派代表赴市教育会寻求支持,市教育会也表明了支持的立场。11月6日,市教育会的常务理事黄造雄在接见该会代表时说:“私立学校受经费之限制,不能发展校务,确实事实。法租界华人每年纳税数甚巨,租界当局对于华人应尽协助之义务。公共租界私立学校之得补助,是为华董力争之结果,如法租界方面之华董亦能为华人教育事业而力争,亦当有同等之结果,本会站在发展华人教育事业之立场上当然予以协助云。”[16]受市教育会的联合华董为成功关键的启示,私校联合会于11月9日拜访了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程竹荪,程氏回答说:“依余观察,如学校方面坚决实行,并援公共租界之条例,一方面要求华董以纳税人之权利事务相较,一致主张力争,则亦不难办到。”[17]在得到纳税华人会的明确支持后,私校联合会又转各法租界华董,寻求支持。11月19日,准备赴华董杜月笙、朱炎之等寓所请愿,“适两君外出未悟,拟准备下星期一下午二时,继续请愿。”[18]3日后即11月22日,他们再去拜会以上两位华董,结果见杜月笙未果,朱炎之华董予以了接见,并回答说:“本人对贵会此种活动,深表同情,今日各代表要求补助私校,本人当与各华董商洽后,一致力争云。”[19]同日他们还拜访了另一重要华董魏廷荣,魏氏也答称:“本人对于贵会此举,深表同情,决尽华董之义务,向法当局力争。”[20]通过对以上各相关团体的拜会游说,法租界私立学校争取补助费运动得到了租界内外各华人团体的支援,为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有力基础。
再次,是通过媒体扩大影响。11月16日下午6时私校联合会在大西洋欧荣社举行记者招待会,20多位记者参加。马家振代表私校联合会向媒体阐述了该会的宗旨及运动的目标他说:“本会组织之最大目的,为发展界内华人教育事业。按法租界人口,约有48万之多,其中华人约占46万余人,学龄儿童有13万之多,西童仅占2000余人,其人口比例如此。又据法租界1932年预算,全年税收约690万两,为数之巨,诚实可观,而教育经费仅占21万8千两,在此仅有之教育经费中,用于西童公学约13万两,中法学堂者约6万两,其纯粹华人教育经费,仅为本年创设之华童公学2万两,分配不公,莫过于是。再以公共租界之统计,全年收入1500余万两,中以100余万两为华人教育,两相比较,相去甚远。况公共租界之教育事业,尚未为我人满意。故本会誓必为华人教育事业而向法公董局力争,要求以全年收入20%为华人教育经费,优先补助界内私立学校。”[11]117明确提出要求法公董局采取公共租界的做法,一方面以全年总收入的约20%为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发展华人教育特别是补助华人私立学校。对于私校联合会的主张,在场的各位媒体记者均表示赞同并承诺予以必要的支持,《申报》记者马崇敬说:“贵会努力此事,足见热心教育,甚为敬佩,报界同仁自当作舆论之赞助,并祝贵会成功。”[11]112《晨报》记者陶百川也说:“贵会此次要求补助,是为市民争应得之权利,不应向法租界当局作乞怜之态度,应唤起全法租界市民共同进行,并请政府交涉。”[11]112此外,《时事新报》等其他报纸记者也纷纷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并表示愿意为该运动的进一步的开展提供舆论支持。
(二)运动的请愿阶段
在该阶段,法租界私校联合会正式向法公董局、市政府、市教育局、法租界华董及纳税华人会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请愿活动,表达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决心,各方也相继表达了各自立场。
11月28日,由私校联合会组织,各校各出一名代表组成请愿团拟于上午9时赴法公董局请愿,但出发前法公董局政治部召见马家振等,“告以要求补助费事,可以从长商量,请愿代表万务勿过多,免生事端。”[11]87于是决定由各执监委员前往请愿,但即将出发时,市教育局突然派人通知要求“关于请愿之事暂缓进行,并召集全体执监委员前往市教育局。”[11]112各位执监委员随即来到市教育局,由该局科长周斐成接见,他转达了市教育局及市政府的立场,即“本局对于贵会要求法公董局补助私立学校事,极表同情,自当予以援助,惟本局认为请愿一事目前暂可缓行,法租界曾为此事赴市府与吴市长(注:即吴铁城)一度磋商,吴市长曾派市府耿秘书来局,嘱为劝阻贵会请愿之举,并与昨日又接吴市长来函,向法公董局接洽进行,至迟一星期内可将结果报告各位,谅能使各位满意,今日请愿,尚希暂作罢论。”[11]87由于市教育局与市政府的主动介入,使私校联合会直接向法公董局申诉的努力归于流产,反映了市府及教育局方面鉴于此事涉及外方而采取的审慎立场,从此,这一请愿基本被限于中国政府的范围之内。
12月3日,私校联合会给市政府首次呈文,申明“本会此次要求法公董局补助经费运动,前往请愿,原为不得已之举,本会自可静候解决。惟本会更有欲钧府力争者,即法租界对界内西人及华人之教育事业,应求平衡发展,应使华童与西童获得平等之待遇为原则。”[21]请求市府介入此事,并给予大力支持。
为扩大运动的影响,联合会还决定自12月5日起,每周一、周四上午10时至11时,由全体执监委员轮流在四马路中西大药房播音台用国语、英语、法语演讲。不料12月1日英租界警务处派人往中西大药房通知禁止演讲,引起私校联合会的不满。他们认为“是项活动,纯为宣传发展租界教育事业,既不违反租界治安,又不违反租界禁令,给予禁止,无理之极。”[22]因而决定除呈市政府向英租界提出抗议外,将召集全体会议,共商对策。
12月4日,在征得全体执监委员同意后决定次日将进行两项请愿,一是首先为英租界禁止广播演讲一事赴市政府“晋遏吴市长,以泻公愤,而保障租界华人自由。”[23]同时准备赴教育局询问一周前教育局承诺的会同市政府向法租界接洽一事的结果。5日上午他们首先来到市教育局,“适教育局正在举行纪念周,各委员候至11时纪念周毕,由该局周斐成接见,向各委员报告接洽结果。经过云:关于贵会要求法公董局要求向法公董局自1933年补助界内私立学校事,上周经本局与市政府商定:由市府派耿秘书往公董局与法领事接洽。前日,耿秘书来巨,据云:业已与法领事接洽妥当。依法领事意见,待华董于法公董局1933年预算会议中正式提出后,予以接受云。现贵会应与法公董局中担任教育委员之张啸林、朱炎之两华董接洽,并俟约定时间后,本局当派员前往。”[24]各位委员认为市教育局的答复较令人满意,遂返回,由于时间关系原定的赴市政府的请愿改为第二天进行。
12月6日,他们来到市政府继续请愿,“嗣以市长尚未到府,由市政府耿秘书接见,当由各代表陈述要求法公董局补助私校之主旨及此次英租界禁止该会播音演讲认为处置不当,请求抗议等事。耿秘书当即答复各代表数点:(1)、关于要求公董局要求补助事,数天之前已与法领事磋商。法领事当即允许华董在预算会议中提出。故现在此事重心在华董能在会议中提出。今日诸君既来接洽,本人当于明日往赴张啸林、朱炎之。(2)、关于播音演讲事,当于近日与公共租界接洽,请准许举行。但播音演讲,应俟适当时间举行,目前并不需要。”[25]各代表对于市府的答复也认为颇为满意,旋即返回。
12月7日,私校联合会又趁热打铁,加快运动步伐,他们“派代表三人,会同市教育局第二科科长周斐成与法租界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之朱炎之商谈,朱氏已允与各华董接洽后,共同在会议中提出。”[26]至此,经过近一月的奔波,补助一事似乎成功在望,加之寒假临近,联合会开始停止请愿,静候佳音。
(三)运动的不了了之
经过私校联合会及市政府、市教育局的努力,法租界当局承诺只要各华董在1933年的预算会议上正式提出私校补助案后即加以解决,而以朱炎之为代表的华董也表示予以配合,至此该运动似乎已经成功在望,但后来的结果并非如此。
1933年1月14,法租界婉言拒绝了私校联合会要求集体补助的要求。法公董局于该日正式发表报告,明确其对界内私立学校申请补助费的原则,公告如下:“本公董局近据法租界私立学校联合会函,为补助费前来。查本局对于公共教育素所重视,而训育问题,尤为法租界当局重视,故本局不惟曾拨巨资创立各华童学校且在租界内各华人教育机关之经费,本局亦或以津贴或免捐之形式,协巨资在案。本局对各私校单独前来请求补助者,自当特予秉公。特此公告。”[27]此公告实际上婉言拒绝了私校联合会所提出的以法租界年收入的20%作为教育经费补助私校的集体补助要求。第2天,法公董局表示“对界内私校联合会请求补助事,表示困难”[28]1月19日,法租界正式公布了该年的财政预算,该预算本着“对开支方面,力言撙节之必要,一切糜费,纵数目甚小,亦必切实删除。”[28]为原则,规定教育预算总数为295969.73两[29](上年为218000两[30]),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从而基本宣告此次运动没有取得成功。
三、运动失败原因之分析
法租界当局选择了不接纳华人诉求的政策,这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决定的:
(一)两国租界面临的外交形势不同
公共租界在30年代之所以要进行华人教育改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当时面临着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压力。英国一直被近代中国人视为侵略者的代表,在“五卅”以后表现尤为突出,因为“五卅”中“枪杀学生者,为英人手下的巡捕,发令开枪的,亦为英人。加以公共租界内的势力,英人占一大部分。于是我们的敌人将此事的责任完全诿诸英国;我们的友人亦极愿英国担负如此责任,后来又加以沙面、万县两案,更使恶意的宣传又添若干材料。”[31]所以,中国大革命兴起以后,国共两党实行了‘单独对英’政策,对在华的英国势力发动了猛烈的冲击,汉口与九江的英国租界相继被中国收回在面临巨大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压力下,英国方面为确保其在上海这个最大租界的利益,开始采取了“对华新政策”,主张“准备在任何时候以宽大精神与能代表中国人民发言能以中国人民之民义从事订约而又能履行其所定之约之任何人开谈判,以期调整条约,使适合新情形,并对于中国人民发展其国家独立之正当的要求,予以一种宽大的满足。”[32]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政策调整方面,工部局1931年邀请南非独立大法官费唐来上海考察租界制度,费唐于1932年发表了著名的4大卷近百万字的《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在报告书里,他主张在继续保留在华租界制度的同时,要求公共租界当局进行必要改革,以满足华人需要,这个建议为工部局当局采纳。自此以后,上海公共租界在领事裁判权谈判、工厂检查法实施、关税自主权谈判、华人参政、教育管理权等问题上均与中国政府保持了较大程度的合作,其中关于补助界内的华人私立学校就是英国所谓“对华新政策”的一项内容,系一种对华人的让步政策。
而与之相反的是,在华法租界没有面临如此大的压力,即“1925年以后,国共两党实行“单独对英”政策,也未在北伐革命的高潮中发动对法租界的冲击。”[33]249由于外交压力的相对缓和,因而与英租界对华政策的积极调整相比较,法国在华租界在对华政策调整方面显得比较消极与被动。
(二)英、法在华租界的华人参政力量的不同
法租界之所以能拒绝界内的私立学校的要求,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法租界的华人参政的实力明显低于公共租界。在公共租界,作为公共租界最高的行政机构的工部局的权力结构有独立与民主的倾向,一方面它受英国政府、英国在华公使及驻沪总领事的影响都不大,甚至可以被视为一个自治政权,即“由于领事团和公使团对当地的行政事务只是加以监督,故而当时的人们称公共租界为实行‘侨民自治’制度的租界。”[33]161公共租界的政治民主性较强的特点,为界内的华人参政提供了有效保障,在界内的纳税华人会成立以后,华人参政的实力更是大为增强,如1928年由纳税华人会选举的3名华董首次代表华人参加工部局,1930年华董数又增加至5名。华董比例的提高使华人在公共租界的政治生活的话语权有所提高,以1932年为例,是年工部局有14名董事组成(内华人5名、日人2名、西人7名)[34]438,权力的多元制衡的特征明显。另外在工部局的各委员会之中,华人也都有很大比例。公共租界内的华人参政力量的强大,是英租界的政策调整的强大的内部动力。表现在教育改革方面,由于工部局长期实行的对华人教育“不闻不问”政策引起了华人的强烈不满,在1927年以后,界内各华人参政力量开始与中国的党政、民众相配合,积极推动工部局的政策调整,使公共租界教育改革终于成为现实。除私立学校开始被纳入工部局的财政预算外,陈鹤琴还于1928年担任华人教育处处长,开始了长达10年的租界华人教育建设。同时在工部局学务委员会里还有华人教育分委员会,由刘湛恩、欧元怀、袁履登等为代表的知名华人组成,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公共租界内的华人教育有了长足发展。
而与此不同的是,法租界内的华人参政实质意义不大,“法租界的华人参政问题,基本上是作为公共租界华人参政的附属物出现的,在规模与意义上都远逊于后者。”[35]83其主要原因是“法国驻沪领事是法租界内所有重要事务的最终决策者,法领事在法租界的权力则较英领事在公共租界为大,相应地,公董局在法租界内的权力则较工部局在公共租界的权力大,因此法租界的华人参政问题就没有公共租界突出。”[35]83尽管法租界的纳税华人会自1927年成立以后也选举5名华董参加了公董局董事会,但在其间并没有多大发言权,表现一是在董事会中比例不大,以1932年为例,董事会由18人组成,其中法人13名,华人5名[34]463,比例较公共租界为低;二是由于法国驻沪总领事兼任公董局总办,他不但有权随时解散董事会,而且对董事实行的委任制,董事的自主权很小;三是董事会尽管由选举人会议选举,但选举人会议对董事会无监督权,决定公董局大小事务的均为总领事。可见,“法国专管租界的行政特点是行政机构没有独立地位,只是领事的附属机构是一种领事“独裁”的体制。”[36]76法籍董事如此,华人董事更是缺乏真正的权力。在这次运动中,法租界诸位华人曾被寄予厚望,法方也曾承诺只要华董在1933年预算会议中提出即予考虑,至于他们是否提出,我们缺乏资料核实,但我们设想他们即使提出会有效果吗?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该年的预算委员会名单,该委员会共有9人组成,其中华董中只有教育委员朱炎之与财政委员陆伯鸿参加,其他7人均为法人[37],在华董比例如此之小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有预期的结果。
(三)两国租界的政治运作的文化理念及权力结构的差异
此次运动的不成功也与法租界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传统的差异,英、法租界在执政理念上有较大不同,即“公共租界是典型的英国精神,这个最早实现自由共和的国家,相信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遵守公共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而法租界则信奉古典共和主义的‘公益至上与公民义务’的美德。”[38]79文化理念的不同使两个租界在其政治制度上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即“公共租界的商人寡头和法租界雅各宾派的官僚主义之间,前者关心他们企业的繁荣,后者经常显示他们的价值观并注重宣布他们的重大原则并时而付诸实施。”[39]130换而言之,公共租界更注重自由、民主,而法租界则更注重官僚集权与整体性原则。
1932年11月28日,就是正当法租界私校联合会正在进行请愿的过程中,法公董局曾开会讨论了《公共教育案》,在会上法董莱昂(Lion)(注:系法公董局卫生委员会委员)就法租界私校请愿一事发表了以下意见:
“查本局创办华童小学之成绩。幸有良善结果。孰料值此法公董局为中国民众设一全沪最完美学校之时。乃闻有界内若干私立学校校长。掀起一种报纸上宣传活动。指责本会董事会不为中国教育尽力。籍以要求补助各校之经费。本董事对此不胜诧异。此次发生报纸上宣传活动及组织私立中小学联合会。但尚无任何学校前来请求补助费。致使本局无从考虑此项问题。查补助校费问题。殊非可由报纸上宣传运动而解决之问题,如此问题应予考虑时,自应先由本局切实查各校,方能明了各该校之如何管理,有何成绩,有否需要补助等。如径行笼统决定。予以津贴经费。则殊违反逻辑与善政,盖此种事件,应各就其各个之价值。而加以分别考察为宜也……本人核得本董事会固常思尽在本巨财政上之可能,为华人教育界专心努力也,今有此事,能不痛心。如以公正眼光视之则法公董局所为华人教育创设之事业,较之邻界行政机关,至少相等也。有一点不宜遗忘者公共教育之组织实为中央政府应负之责任,就通当而论,并非市政府应负之责任,本董事会对于lion先生之感想,认为绝对正确。爰对于法租界内中国各私立学校校长所早之宣传运动表示悲痛”[40]。
那么为何法国不愿意效仿公共租界补助私立学校的政策呢?其主要原因就是法租界不愿意改变集权主义的体制,众所周知,法租界的权力为总领事控制,“法领事成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而由于法国领事又须接受本国政府和驻华公使的训示和制约这又是一种法国政府通过领事来控制租界的体制。”[36]76这种体制假如在华人的私立教育政策上发生改变,在财政预算上将丧失自主性,在行政体制上也将受到华人的掣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租界拒绝的不单纯是教育经费的支出问题,而是一种政治传统的保留问题。
结 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西方在华租界的政策调整的重要时期,在中国日益高涨的的民族主义与国民党政权的革命外交的双重要求下,西方列强从1927年以后在租界政策方面开始作出了必要的调整。但这种调整的步伐与力度并不趋于一致,由于受各自国家文化差异及政治传统的影响,英、法两国的在华租界在应对这种挑战时采取的政策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同时由于外交压力形势的不同、内部华人参政力量的差异及各自政治运作特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英、法两国在华租界在南京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调整的力度与态度也存在明显的不同。这在1932~1933年法租界私立学校申请补助费运动中得到了有力的验证,即英国公共租界由于面临强大的外交压力、内部华人参政力量的有力及传统政治传统的支撑,其在南京政府时期的租界政策调整方面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与灵活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由于法租界的集权政治、华人参政力量的薄弱及外交压力的较轻,其在对华政策的调整上则显得消极与固守,它不但婉言拒绝了私立学校的集体要求补助的要求,还力图维护其对租界内的私立学校管理权。英、法在华租界的这种政策上的差异性,不但体现了近代中国租界问题的复杂性,还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与中外关系。
[1]上海教育统计民20年度,(民国)上海市教育局编.
[2]费君提交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报告书第二卷摘要译文[M].(出版地与时间均不详,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3]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4]193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M].
[5]陈鹤琴:一年来之租界教育,1933年上海之教育[M].上海:上海新闻社编,1934.
[6]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M].
[7]工部局公布私立学校补助办法上海:申报1932 12 7
[8]大学院公报[M](1928年第3期),台湾文海出版社,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6辑.
[9]施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0]法租界公董局公报[N].上海档案馆档案,档号:U38-1-2838
[11]马家振:一年来法租界私立中小学联合会,见1933年之上海教育[M].上海新闻社编,1934(3)
[12]法租界公董局公报[J].上海档案馆档案,档号:U38-1-2842,第61号.
[13]上海法租界私校讨论补助上海.申报(N)1932-11-2
[14]上海法租界私校继续讨论补助上海.申报(N)1932-11-5
[15]法租界私校讨论申请补助上海.申报(N)1932-11-6
[16]法租界私校要求补助之积极上海.申报[N]1932-11 12
[17]法租界私校联合会昨向华董请愿未果上海.申报[N]1932-11-19
[18]法租界私校联合会拜会朱炎之华董上海.申报[N]1932-11-22
[19]朱炎之华董答复:并与其他华董共同力争上海:申报[N]1932-11-22
[20]法租界私校联合会执委会议上海:申报[N]1932-11-22
[21]法租界私校联合会积极进行补助运动上海:申报[N]1932-12-3
[22]英租界当局禁播音演讲上海:申报[N]1932-12-4
[23]法租界私校联合会开紧急执监会议上海:申报[N]1932-12-5
[24]法租界私校联合会要求补助渐趋实现上海:申报[N]1932-12-6
[25]法租界私校联合会昨派代表晋遏吴市长上海:申报[N]1932-12-7
[26]法租界私校联合会要求补助暂告段落上海:申报[N]1932-12-8
[27]法租界公董局公报,上海图书馆馆藏,编号:J-0174.
[28]一年来教育界日记,1933年上海之教育[M].上海新闻社编,1934.
[29]法租界本年预算案上海:申报[N]1933-1-19
[30]法租界公董局公报[N].上海档案馆档案,档号:U38-1-2842-61号.
[31]丁恩(Richard Dane)英国人眼中的中国问题[J].东方杂志,24卷第13号.
[32]张伯伦的对外外交演说,东方杂志[J].25卷第2号1928年1月19日出版.
[33]费成康著:中国租界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34]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5卷附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5]卢汉超: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述论,见唐振常、沈恒春主编的上海史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36]李育民著: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37]法租界公董局华文公报[N].上海档案馆档案,档号:U38-1-2841-58号.
[38]孙倩:上海近代公共管理制度与空间建设[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39]白吉尔(法)著,王菊∥赵念国译:上海史:走向现代化之路[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40]法租界公董局公报[N].上海档案馆档案,档号:U38-1-2842-73号.
The differences of British and French concession adjustting policy toward China in Nanjing Government period——as 1932~1933 French Concession in Shanghai private schools apply for Subsidies centric study
LU Hua-d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China
IN Nanjing Government.Period,the concessions of England and France in China confront rising nationalism of China and becoming stronger with the authoritarian politics,so they were forced to take some appropriate poliay adjustments,but the pace of adjustment is ninconisteut,there was clear difference:the British concession of adjustment policies have great initiative and flexibility,while the French Concession with a strong adjustment policies and passive lag.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are the following:First,China's“single on the British”foreign policy make Britain confrontd more diplomatic pressure than the French;Second,there were different Chinese power politics in the British and the French Concession;Third,thery were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concession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hilosophy and opera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Concession Private schools in French Concession Concession policy
K258
A
1000-5072(2012)03-0130-08
2011-9-22
陆华东(1972—),男,安徽定远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危机中的繁荣:1929~1933上海市民社会生活研究》(批准号:09YJA770040);上海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的民间文化生态》(A.15-A 011-09-001)。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吴奕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