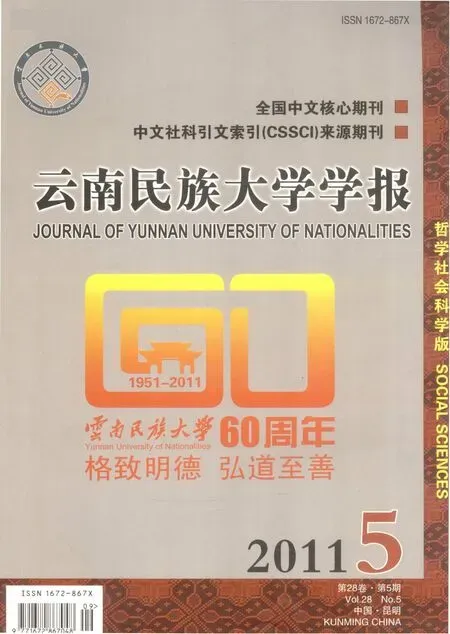李绂《秋山论文》中的叙事论:比较叙事学研究
谭君强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清代学者李绂 (穆堂)在《秋山论文》(1703年)中所提出的叙事论,在中外叙事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结合叙事作品研究所提出顺叙、倒叙、分叙、类叙、追叙、暗叙、借叙、补叙、特叙等9类叙事方式,较为完整而全面地概括了叙事作品中的话语叙说方式,早于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约270年在其《叙事话语》 (Narrative Discourse)这一现代叙事学研究中对叙述顺序、叙述节奏等所作的全面分析,其理论论说方式也具有科学的意义。对李绂叙事论的研究,将对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国古代文论论说方式、中外文论的交流与对话、比较叙事学研究等具有诸多启示意义。
一
在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各类作品中就存在着优秀的叙事传统,这一传统在诸如《左传》、《史记》这样的叙事作品中一直流传下来,绵延不绝,不断发展。这些作品对于叙事的处理既富于原创性,又表现出中国叙事作品独有的特色。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很早也就留下了涉及对叙事作品理论的探讨,留下了不少益人心智的论述,即使其中一些不过是片言只语,仍然十分富于启示意义。在这些叙事理论中,清代学者李绂在《秋山论文》中的论述是十分引人瞩目的。
李绂 (1673-1750年),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以进士入翰林,任内阁学士,官至广西巡抚、直隶总督、户部左侍郎,清代著名政治家、理学家和诗文家。著有《穆堂类稿》五十卷, 《别稿》五十卷,《陆子学谱》二十卷,《朱子晚年学谱》八卷和《阳明学录》等。梁启超认为他是“陆王派之最后一人”,“结江右王学之局”[1](P48);钱穆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专章对他进行了论述,誉之为“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2](P312)。
李绂著述丰富,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学界关注较多的是他在理学、方志学等方面的著述,尤其是前者,而在其他方面,如他在中国古代叙事理论史上的成就则尚未引起人们注意。实际上,他在这方面是可以大书一笔的。李绂在中国古代叙事理论史上的成就,其《秋山论文》是一个重要的代表。《秋山论文》出自其《别稿》卷四十四。据作者所说:“《秋山论文》者,余癸未春主秋山书院,杂书代答问,以应诸生之请业请益者也。时余年二十有九。”[3](P3998)这是作者在主持书院讲习中,应门生弟子请教之需所撰,其时应在1703年前后。
《秋山论文》四十则,前二十九则论古文,后十一则论时文。每则均不长,但不乏精到之论。如谈道、文之关系:“文所言载道,而能文者常不允于道,知道者多不善于文。”在论及“为文须有学问,学不博不可轻为文”时说到:“如治经者欲立一解,必尽见古人之说,而后可以折其中。治史者欲论一事,必洞彻其事之本末,而后可定其得失。”他以自己读书、研究的经历为例,说自己在
20岁以前尝作《经史外论》一书,但当时所见之经史书籍未备,所见寥寥无几。后来购得《通志堂经解》等数10种书,阅读之后,“试覆观少作,则所论者多昔人所已发,或前人言之而后人又已驳正之者。然后知阅书不备,不可以为文也”[4]。这不仅是对学术研究极有启发的经验之谈,同时也表明了作者对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他还明确提出“文章字句须有成处……不可勉强抄袭,降为剽贼,亦即《曲礼》所谓‘毋儳言,毋剿說’也。”[4](P3999-4000)谆谆告诫学子不要剽窃,不要窃取别人的言论为己说。论文四十则中最长的一则为对叙事的论述,兹照录如下:
文章惟敘事最難,非具史法者不能窮其奧窔也。有順敘,有倒敘,有分敘,有類敘,有追敘,有暗敘,有借敘,有補敘,有特敘。順序最易拖闒,必言簡而意盡乃佳。蘇子瞻《方山子傳》,則倒敘之法也。分敘者,本合也,而故析其理。類敘者,本分也,而巧相聯屬。追敘者,事已過而覆數于後。暗敘者,事未至而逆揭于前。《左傳》“箕之役”,敘狼瞫取戈斬囚事,追敘之法也。蹇叔哭送師曰“晉人禦師必于殽”云云,暗敘之法也。敘中所闕,重綴于後為補敘。不用正面,旁逕出之為借敘。《史記》“鉅鹿之戰”,敘事已畢,忽添出諸侯從壁上觀一段,此補敘而兼借敘也。特敘者,意有所重,特表而出之,如昌黎作《子厚墓誌》,獨抽出“以柳易播”一段是也。而又有夾敘夾議者。如《史記》 “伯夷”、“屈原”等傳是也。大約敘事之文,《左》、《國》為之祖,《莊》、《列》分其流,子長會其宗,退之大其傳,至荊公而盡其變。學者誠盡心于數子之書,庶乎其有所從人也夫。[4]
李绂上述对叙事理论的概括言简意赅,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任何文学理论、包括叙事理论在内都是在对大量文学作品进行总结、概括、提炼、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对普鲁斯特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进行细致研究之后,完成了他在现代叙事学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话语》一书。李绂的上述论述不足400字,却仍然是在他在对大量的中国经、史、子、集各类作品阅读、研究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精要之论。他在谈到自己以往阅读的情况时说:“小时看书,日可二十本,字版细密者,犹不下十本;今来馆务分心,余力无几,或一二本而止。七阅月中,看《三国志》、 《晋书》、 《南北史》及李白、子美、义山、飞卿、子瞻、放翁诗各二遍;《尔雅》、《孝经》、《仪礼》、《论》、《孟》诸注疏,《史记》、《前后汉》、《隋唐书》、《五代史》各一遍;《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诸书及《宋》、《辽》、《金》、《元》史不及一遍。”[2](P285-286)李绂的论述,条分缕析,论从文出,虽然只提及不多的几部叙事作品以作为例证,但这些例证无疑都是作者从所阅读的大量作品中提炼出来的,论与文密切结合,富于说服力。
在《秋山论文》上述引文接下来的一则论述中,李绂探讨了“论事之文”与“说理之文”,所谓“論事之文以說理出之,則根柢深厚而無小非大矣;說理之文以論事出之,則精神刻露而無微不著矣”[4](P4005)。由此可知,作者是将文分为“叙事之文”、“论事之文”与“说理之文”来进行探讨的。李绂在对“叙事之文”学术史的简要概括中指出:《左传》、《国语》为叙事文之宗祖,至《庄子》、《列子》而出现了叙事文的各种流变,子长(司马迁)的《史记》融会贯通,退之 (韩愈)的叙事文进一步光大其传统,至荊公 (王安石)则已历尽其变。寥寥数语,即将自公元前约5世纪的《左传》至11世纪王安石 (1021-1086年)前后1600年来的叙事文的发展变化作了很好的总结与概括。
在李绂的上述学术史概述中,所提到的叙事文既有历史著作,也有文学著作,以及蕴含哲学的著作,他将这些著作均列在“叙事之文”中,这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与哲学著作往往相涉相通的情况是一致的。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为中国现存最早一部阐释史学理论的名著,其中许多部分如《言语》、《浮词》、《叙事》、《模拟》等都涉及文学。如论《叙事》一节曰:“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记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赞论而自见者”。刘知几论述的此类情况,文史皆然。
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现代叙事学研究中,其研究对象“叙事文本” (narrative text)主要是以对诸如小说类的叙事虚构作品 (narrative fiction)为主要对象的。但是,由分析叙事虚构作品所总结、概括而形成的叙事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可用于对历史文本的分析和研究,反之亦然。在当代史学界,有学者认为历史著作具有与虚构作品相类似的虚构性。海登·怀特提到:“最近的话语理论消除了实在话语与虚构话语之间的区分。”[5](P1-22)法国学者保尔·利科认为: “严格地讲,应当把研究叙述结构的科学称为叙事学,而不去考虑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的区别。然而,按照当今对叙事学一词的用法,它集中研究的是虚构叙事,但不排除间或涉足历史编撰学领域。”[6](P4)
就中国古代所形成的大量文、史、哲兼备的作品来说,一如美籍学者王靖宇所言,如果我们给叙事作品下一个最宽泛的定义:即由故事和故事讲述者所构成的文学,那么“中国古代文学无疑包含各种各样的叙事形式。不仅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著作等形式明显属于叙事作品,许多汉代以前的哲学著作——例如《孟子》——也可被当作关于某个哲学家的所做、所说、所想的‘故事’来读。”[7](P21)李绂通过对文史兼备的叙事之文进行的叙事理论概括,既可在一定程度上看作为史学叙事的理论概括,更应视为文学叙事理论的概括。
二
李绂将叙事文的叙事之法归结为9种,分别是:顺叙、倒叙、分叙、类叙、追叙、暗叙、借叙、补叙、特叙。从叙事理论的角度看,其涉及的主要是叙事事件、叙事文本与叙事时间的关系问题。现代叙事学在对事件、文本与叙事时间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时,通常要区分所谓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叙事文本中叙述时间 (话语时间或文本时间)的顺序不可能与被叙述时间 (故事时间)的顺序完全平行,其中必然存在“前”与“后”之间的错置关系。这种相互错置或倒置的现象可以归之于两种时间性质的不同:话语时间是线性的,而故事时间则是多维的。[8](P62)也就是说,实际发生的“事”与形之为“文”的文本,二者在时间顺序上不可能完全一致。热奈特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时间倒错”(anachrony),即“两个时间顺序之间一切不协调的形式”[9](P17)。在李绂的论述中,他显然已意识到这种“事”与“文”之间不平行的关系。如在谈及“追叙”与“暗叙”时就明确说到:“追敘者,事已過而覆數于後。暗敘者,事未至而逆揭于前。”这里的前后错置,即“事”与“文”之间的不相平行,也即热奈特所谓“时间倒错”。
李绂对叙事之法所作的归纳之细密,分类之完整,在中外叙事理论史上,实属罕见。在现代叙事学研究中,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所进行的研究,其中对叙事时间与叙述方式的分析被视为是到当时为止对叙事作品所归纳的最为细密、涵盖面最广的叙事时间理论。我们可以以此为对照与比较,看看先于热奈特约270年的中国学者李绂在《秋山论文》中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探讨。
热奈特《叙事话语》一书约有2/3的篇幅涉及对叙事时间的探讨。他分别从顺序 (order)、时距 (duration)和频率 (frequency)三个方面对叙事作品中的时间关系进行了研究。“顺序”所探讨的,实际上就是“时序”问题。热奈特强调了时间的双重性,“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是不一致的,以这两种不同的时间作为依据和对照,他区分了叙事文本中两种最基本的时序状态,即倒叙 (analepses)和预叙 (prolepses)。倒叙指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叙;预叙则指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其他一切有所变换的形式均在此基础上产生,如预叙性倒叙、倒叙性预叙,以及所谓无时性结构等。[9](P12-52)
李绂首先提到的叙述方式是“顺叙”。从与其他叙述方式比较来看,可知他所谓顺叙,是指叙事文中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所进行的叙述。顺叙作为一种基本的叙述方式,在中外古今的叙事作品中大量存在。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就“大体上采纳了符合时间顺序的布局”[9](P24),这种叙述方式的长处是事件按序展开,清晰易辨,但同时也有其不足。在李绂看来: “順敘最易拖闒,必言簡而意盡乃佳。”这应是切中要害之论。因此,叙事作品必须以其他叙事方式交替出现,以克服这种虽然清晰、却缺少变化的叙述。
倒叙与预叙,在李绂《秋山论文》的论述中,被概括为两种最基本的形式,只不过李绂对预叙以“暗叙”之名命之。首先,我们来看看“倒叙”。李绂是在与“顺叙”作为参照的情况下探讨倒叙的,并以具体的叙事作品作为说明:“蘇子瞻《方山子傳》,則倒敘之法也。”《方山子傳》文不长,全录如下: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裏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10](P513-515)
苏轼此文全以叙其故人方山子之行状为宗,其中所包括的议论也自事而出。开篇从其“少时”直至“晚乃遁于光、黄间”,以及方山子古怪名字的来历,均属顺叙。倒叙始于与方山子之相遇,知为故友,并点出其名与字,再回顾“方山子少时”与其交往的情形,叙方山子本系勋阀富家之后,却弃而不取,“独来穷山中”。从时间的顺序来说,是在其讲述事件之时,插入方山子之往事。按热奈特所言:“时间倒错可以在过去与‘现在’的时刻,即故事 (其中叙事中断为之让位)的时刻隔开一段距离,我们把这段时间间隔称为时间倒错的跨度。时间倒错本身也可以涵盖一段或长或短的故事时距,我们将称之为它的幅度。”[9](P24)《方山子传》中倒叙的时间跨度明显可见:“独念方山子少时……。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10]在这里,时间的跨度 (reach)不止十年。 “幅度” (extent),又名“广度”,在《方山子传》中同样包含在内,如“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以及在叙说方山子射鹊一发中的之一节,其中均包含着故事事件所经历时间在内。
热奈特在时间倒错中区分了所谓第一叙事与第二叙事:“任何时间倒错与它插入其中、嫁接其上的叙事相比均构成一个时间上的第二叙事,在某种叙述结构中从属于第一叙事。……与一个时间倒错相比,整个上下文可以被视为第一叙事。”[9](P25)在《方山子传》中,当叙事人的讲述中断而让位于错时、插入倒叙时,它在时间上就构成为第二叙事。在时间上区分的第一叙事与第二叙事均可成为叙事文中的重要部分。《方山子传》中作为倒叙的第二叙事,叙说了方山子一箭中鹊、并与叙事人“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紧接着,叙说了叙事人此时所面对的方山子,依然“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自开端至此,撇开其中倒叙的部分,在时间上所形成的即为前后相连接的第一叙事,而插入其中的倒叙部分,也就是第二叙事。第一叙事不仅对方山子作了概述,叙说了与其相遇的情况,而且在时间上形成为叙事框架。作为倒叙的第二叙事则主要以对射鹊一事的叙述,展现出方山子的精悍与豪气,使人对其性格有更好的了解。以苏轼所作《方山子傳》作为倒叙之例,以例证理,清晰明了。
从叙事时间来说,李绂所探讨的可以归之为倒叙的,尚有追叙和补叙。先看“追叙”。 “倒叙”与“追叙”,在现代叙事学中,几乎被视为同一概念,而李绂则将二者加以区分,显现出其对叙事时间的思考细密而周全。李绂对“追叙”之法未有定义,而是以具体的叙事作品为例说明之:“《左傳》 ‘箕之役’,敘狼瞫取戈斬囚事,追敘之法也。”这在《左传·文公二年》有如下叙说: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戰于殽也,晉梁弘禦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11](P343)开篇一段即叙秦为报殽之役之败绩,再次举兵伐晋,但又以失败告终。以“顺叙”出之,扼要地对战事作了叙说。从“战于殽也”,则回顾殽之役中所发生的事件:(当年)在殽地作战时,晋国的梁弘驾御战车,莱驹担任车右。战事第二天,晋襄公让莱驹用戈斩掉绑着的秦国俘虏,俘虏大声喊叫,莱驹戈掉地上,狼瞫取戈斩了俘虏,赶上了晋襄公的战车,于是让狼瞫取代莱驹为车右。而在此后所叙的箕之役中,先轸将狼瞫免职,让续简伯担任车右,狼瞫十分愤怒。遂有其友提出一起发难造反,而狼瞫以道义为上不为。晋军到彭衙后,狼瞫率军飞驰冲入秦军,战死在那里。而晋师追从他,大败秦军。
从事件所发生的先后顺序、即故事时间来说,上述殽之役自然是发生在开篇所叙的箕之役及此后所叙的发生在该战役中的彭衙一战之前。它们是对开篇部分概述箕之役之后对它的进一步补充与细化,这一补充与细化和在追叙中出现的狼瞫取戈斩囚事连接起来,叙说了狼瞫此后的情况。这里结合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在叙述时间上回旋往复,不仅在开头的概述中对战事的大致情况作了明确的叙说,也通过对狼瞫的叙述突出了晋军之勇,并将狼瞫这一人物活生生地表现出来。
李绂将敘狼瞫取戈斩囚事这段十分富于艺术性、在时间上前后回旋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归之为“追叙”,是非常合理的,它可以成为叙事文描述的重要部分,以艺术的方式突出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如果将李绂所提出的“倒叙”与“追叙”作某些区分的话,大致可以看出:倒叙所强调的更多的是一种整体的叙说,以及人物、事件、背景等的整体性关联;而追叙则是以对某一突出的人物、事件等的描述,来凸显其对整体性事件发展的意义,以点与面相结合的方式,使对人物、事件的叙说有声有色,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一般说来,在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中,对叙事时间的运用是有所不同的。保尔·利科说到:“提及如荷马的《奥德修记》那样从中间开始写,继而回顾往事以便解释当前局面的严格义务,就可以把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区分得一清二楚,后者被假定必须顺时间之河而下,把人物不间断地从生写到死,用叙述填满一切时间空隙。”[6](P4)而李绂从《左传》所归结的“追叙”、 “倒叙”之法,不仅可见出中国古代以历史叙事为主的叙事作品同时也兼备文学叙事的艺术方式,由此形成中国古代史传作品与诸如西方的历史叙事不同的特色,同时,也可见李绂在归纳中国叙事作品的叙述方式时的独特眼光。
除此而外,李绂还提出“补叙”,将其定义为“敘中所闕,重綴于後為補敘”,并以《史记·项羽本纪》“钜鹿之战”中诸侯从壁上观一节加以说明。钜鹿之战,发生于秦二世三年 (公元前207年)十二月,它是秦末楚将项羽率军与秦军主力章邯部在钜鹿地区 (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的一场决战。秦将章邯在取得定陶之战胜利后,“渡河擊趙,大破之”,赵王被迫退守钜鹿,“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栗。陳馀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统率楚军主力北上救赵,伺机歼灭秦军主力。宋义率军抵达安阳 (今山东曹县东)后,一连驻扎了46天,拥兵不出。项羽力劝无效,在晨朝上将军宋义时,即其帐中斩其头,相与共立项羽为假上将军,并“使恒楚報命於懷王”,接恒楚所报后,怀王使項羽為上将军,最后:
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盧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12](P307)在对钜鹿之役叙说完毕后,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又以“當是時”为转折,将发生在已叙说完毕的战事中所曾发生的事件,加以补充叙述。这些当时发生的事件并未按其发生的时间在叙事文中呈现,而属于原先“敘中所闕”部分,在其后加以“补叙”。这样的补叙,自然也属于追叙。热奈特所谈到的一类叙述方式与李绂所提出的“补叙”极为吻合,这就是所谓“补充倒叙” (completing analepses)或“附注”(returns):“补充倒叙或‘附注’,包括事后填补叙事以前留下的空白的回顾段……这些先前的空白可以是纯粹的省略,即时间连续中的断层。”[9](P26-27)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叙说了诸侯摄于秦军之威,虽围绕钜鹿城扎下十多座营垒,但无一人出战,皆作“壁上观”,即仅仅凭营垒眺望而已。而在项羽破釜沉舟,攻破钜鹿,获得胜利之后,诸侯将则又表现出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作“壁上观”正是“事后填补叙事以前留下的空白的回顾段”。
李绂对“借叙”的定义为:“不用正面,旁逕出之為借敘”,并认为上述“钜鹿之战”中诸侯从壁上观,“此補敘而兼借敘也”。这里可以让我们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对借叙的定义,可知是不直接从正面叙说,而以侧面叙说的方式来表现;另外,所提出的各种叙事方式是可以交叉而兼而有之的。除这里补叙而兼借叙外,其他的一些叙述方式也可以有类似的情况,如前述《左传·文公二年》中作为“追叙”的狼瞫取戈斩囚事,也可看作为“特叙”。
与“倒叙”相对应的是“预叙”,即李绂所称的“暗叙”:“暗敘者,事未至而逆揭于前。”他以《左传·秦晋殽之战》为例加以说明:“蹇叔哭送師曰‘晉人禦師必于殽’云云,暗敘之法也。”[4](P4005)“秦晋殽之战”所叙的是晋文公死后,秦穆公举兵袭郑,晋、秦两国战于殽的经过。蹇叔力谏勿袭郑,而秦穆公不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紧接着即蹇叔哭师一节: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 “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秦師遂東。[11](P325-326)
秦师最后以大败于殽而告终,晋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在这场战役之前,秦穆公曾访诸蹇叔,询问蹇叔的意见。蹇叔以“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力劝穆公打消兴兵之意,但穆公不从,依然决定起兵。这样,在对将要发生的战事进行分析之后,蹇叔在战争尚未开始之前,已意识到其可能的结果。因而,在秦师即将出发之时,哭着为参加这场战役的儿子送行,并预示了这场战争最后的结局。不论是从李绂所谓“事未至而逆揭于前”,还是热奈特“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的定义来说,蹇叔哭师都是一段明显的预叙。一般说来,预叙往往“可以表明一种命定的意识:没什么可以做的,我们只能观察朝最终结果的行进,期待着以后会看出凶多吉少的征兆。”[13]在李绂以蹇叔哭师为例所归纳的“暗叙”中,在一定程度上就有某种宿命论与命定的意味,但除此而外,它尚包含着对客观形势以及对立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对可能的结局作出的判断。蹇叔在指出“勞師以襲遠,……無乃不可乎”之外,尚提出“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这应该说是一种具有一定科学意义的分析和判断。
《秋山论文》中所探讨的“特叙”,应属于叙述节奏的问题。李绂对“特叙”的定义是“特敘者,意有所重,特表而出之”,并同样以一例证对特叙作说明: “如昌黎作《子厚墓誌》,獨抽出‘以柳易播’一段是也。”韩愈《子厚墓誌》开篇自柳子厚先祖七世祖、曾伯祖和其父的行迹起叙,再叙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在概要地叙说了其博学俊杰,崭然见头角,直至名声大振之后,接下来: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禦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氾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14](P327-328)
柳子厚到柳州之后,在偏远之地作出了种种政绩,因而,被再次“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之后,即特别叙说了子厚“以柳易播”一事:
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裏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在《子厚墓誌》中,“以柳易播”的叙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且,又以事为据,发出了“士穷乃见节义”的大段慨叹。从故事时间来说,“以柳易播”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并不长。柳子厚被召回京师再次被遣做刺史时,刘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去播州。子厚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而无憾,最后使刘禹锡得以改任连州刺史。显然,这一事件从发生到延续其时间十分有限。而此后讲述人所发出的慨叹,则是离开故事进程缘事而出,从时间来说,并未有故事时间延续其中。《子厚墓誌》全文不足千字,而“以柳易播”连同为之而发的慨叹大约有220余字,占全篇篇幅超过1/5。
这一“特叙”,“特”在何处呢?特在以大量的篇幅重笔叙说,故事所延续的时间与文本时间(这里应转换为文本篇幅)二者不成比例。热奈特《叙事话语》对“时距”的探讨,与上面所讨论的“特叙”可以说有所关联。热奈特区分了小说速度的4种基本形式,他将之称为4个叙述运动,分别是省略 (ellipsis)、停顿 (pause)、场景 (scene)、概要 (summary)。[9](P53-61)所谓省略就是相应于一定量的故事时间跨度的叙事文本篇幅为零;停顿指的是在叙事文本中其中故事时间显然不移动的情况下出现的所有叙述部分;场景传统地成为戏剧性情节的集中点,其中故事时间的跨度和文本时间的跨度大体上是相当的;概要是指叙事文本中把一段特定的故事时间压缩为表现其主要特征的较短的话语。李绂的“特叙”就其“意有所重,特表而出之”而言,已经包含着对那些具有重要意义、需要特别加以叙述的部分,详加叙说的意味。而这样的详加叙说,不仅在叙述话语的叙说方式、用语等方面要细加选择,在叙述的篇幅、即文本的长度上也不可避免地会随之延伸。这些“意有所重”的部分,对于所叙说的人物、事件而言,不见得是在故事中那些延续时间很长的部分;相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言语、行动,一些富于意义的细节,往往可以将人物的特征很好地勾画出来,将事件的意蕴很好地展现出来。上述“以柳易播”一段就是如此。热奈特所论及的“场景”大体即为此类叙述。
就叙述节奏来说,李绂在《秋山论文》中已经意识到文本篇幅与故事事件在叙述中的节奏关系。他在谈到“顺叙”时,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文本篇幅、即长度与所叙事件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要避免由于顺叙而出现的拖泥带水,导致文本长度的过度延续,而必须言简意赅,意尽即可。从顺叙的言简意赅,到特叙的重其意,“特表而出之”,其间有繁有简,作者强调叙事作品的叙述节奏,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叙事学所探讨的叙述节奏问题,正是从这一意义入手的。
除此而外,李绂提出的叙述方式还有“分叙”与“类叙”,其定义分别为: “分敘者,本合也,而故析其理。類敘者,本分也,而巧相聯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叙事作品中叙事的连贯性与条理性,以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在分别叙说时不忘其整体的一贯性,在分类叙说时其间的关联不容忽视。
李绂在《秋山论文》中,还谈及了叙事作品中的“夹叙夹议”: “又有夾敘夾議者。如《史記》“伯夷”、“屈原”等傳是也”。中国自古以来的史传与叙事作品传统中,这种缘人缘事而发的讲述人的议论并不罕见。李绂所提到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屈原列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怀王听信上官大夫的谗言,“怒而疏屈平”,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讲述人缘事慨然而叹: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15](P2482)
这种慨叹,即李绂所谓“夹叙夹议”,从叙事学的意义来说,指的就是叙述者干预,讲述人的指点品评。它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叙述者对于围绕其所讲述的事件、人物等所表达的看法、见解与评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叙述者干预又往往被称之为叙述者评论。这种干预无可避免地表达了评论主体特定的立场与看法。[16](P207-208)在许多情况下,叙述者的干预往往与作者的观念意识与价值判断有更多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叙述者干预或评论又被视为“作者闯入”(an author's intrusion)[17](P14),甚至被直接称之为“小说中作者的声音”[18](P188)。前面《子厚墓誌》中讲述人针对“以柳易播”一事所作的是这样一种干预,《屈原贾生列传》中针对屈原遭谗而作《离骚》所“议”,同样如此。它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所叙人物的理解,同时,也增强了所叙事件的意义,并扩大了从单一事件所引发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判断,使对这一事件和人物的叙述超越了纯粹事件与人物本身的意义。李绂对中国传统的叙事作品中“夹叙夹议”的关注,自然是注意到了这类叙说方式所具有的意义。
在热奈特在对叙述时间的探讨中,还包括所谓“频率”问题。所谓频率即叙述频率,也就是叙事和故事间的频率关系,主要是一种重复关系。故事中的“相同事件”或“同一事件”可以在叙事文本中出现一次,也可以出现多次。事件发生的次数与它在叙事文本中被描述或提及的次数之间的不平衡就出现了叙述的频率问题。对所谓“频率”问题的探讨,在李绂的《秋山论文》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原因无他,在中国传统的叙事文中,简洁自一开始就几乎是首要的要求之一。刘知幾《史通·叙事》明确说道:“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李绂《秋山论文》中,“必言簡而意盡乃佳”。在中国传统的叙事作品中,也极少出现类似于现代西方叙事作品中所出现的重复,这样,对涉及叙事作品重复的“频率”问题的探讨,没有进入李绂的视野,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
李绂《秋山论文》所阐述的叙事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透过其《秋山论文》对相关理论的探讨,以及其理论本身的意义,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示。
第一,李绂的叙事论,尤其是对叙事时间与叙事方式的探讨,系统而周密,在中外叙事理论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叙事方式对于叙事作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叙事方式又与人类所面对的最基本的时间要素相关联,因而它一直是叙事理论中一个十分引人关注的问题。李绂结合中国古代叙事作品对顺叙、倒叙、分叙、类叙、追叙、暗叙、借叙、补叙、特叙等9种不同叙事方式所作的探讨,在其理论的严整性与系统性上,除元代学者陈绎曾进行过简要的探讨而外①元代陈绎曾在其《汉赋谱》中论及“叙事”时提出了正叙、总叙、间叙、引叙、铺叙、略叙、列叙、直叙、婉叙、意叙、平叙等11种叙事方式,并对每种叙事方式作了简要的说明,显然有其意义,但未以具体的叙事作品作为每一叙事方式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说明。陈绎曾的论述自有其意义,当另文予以阐述。,在此前的中外叙事理论史上几乎前所未有。他的探讨既涉及到时间倒错的问题,也涉及到叙事节奏的问题,这都是现代叙事理论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问题。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研究被认为是涉及到叙事时间问题所作的最完备的研究,而李绂早热奈特270年前就提出如此系统的叙事时间理论,其理论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9种叙事方式,其中一些作为现代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不断为叙事学界所讨论。而他所提出的分叙与类叙,作为对应的一对概念,在现代叙事学理论上,尚未引起叙事学者的充分关注。而这一对概念,无论对叙事作品的创作也好,还是分析与研究叙事作品的连贯性、完整性与条理性也好,都不无意义,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二,李绂在探讨叙事理论时,其理论论说方式值得格外注意。在不少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论说方式既不系统,又不注重定义,显得含混不清。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认为,中西文学思想传统的差异性是多方面的。他说:“寻求定义始终是西方文学思想的一个最深层、最持久的工程”,可是“这种追寻在中国文学思想中的缺席 (以及在中国思想史其他领域中的缺席)就显得颇为惊人。”[19](P3)这样的说法,显得过于绝对和武断。在中国文学思想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确实存在着源自于论者对概念、术语的各自理解而出现的某种百花齐放的局面,导致对同一概念、术语的种种解释,以及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的不同运用,从而造成某种含混的状况。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文论中不可一以概之,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其实,此类情况在西方文论也存在。刘若愚在谈到“在中文的批评著作中,同一个词,即使由同一作者所用,也经常表示不同的概念;而不同的词,可能事实上表示同一概念”时就提到,“这当然不是中文所独有的现象:且想想看英文中像style和form这些字”[20](P7),就是一个证明。而在传统的中国文学思想和文论中,同样也存在着追求定义的精确性的理论阐述,追求以特定的理论对作品进行分析的传统,以及由作品而概括与进行理论阐释的合理追求。李绂《秋山论文》中对9种不同的叙述方式的界定,尽管其中包含着一些相互交叉与重合的部分,但他对概念与术语精确性与完整性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从整体上来说,他在结合叙事作品对一些重要概念与术语作定义时,显得准确而严整,并注意到了各种不同叙事方式之间内在的关联。这样的论说方式,具有某种科学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应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
第三,通过李绂《秋山论文》对叙事论的论述,可为人们思考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或现代转换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中外文论界、尤其是西方文论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西方自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古典文艺理论由于注重其系统性与分析性,在西方文艺理论领域主宰了长达二千年之久,至今在分析现代文艺作品时仍然适用。而中国古代文论则不然,无法直接运用以对现代文艺作品进行分析,因此,需要有现代转换或转型,以适应现代文艺理论发展与创作实践的需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总体上说来是一个合理的问题。毕竟,一如蔡锺翔所说:“近百年来中国文化 (不仅是文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裂,今天要把这条断裂的线索再连接起来是有很大的难度的,而这种现象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却没有发生。”[21]但是,对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具体分析。中国古代文论并非必定得经过现代转换方可运用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作品分析的实践中。应该说,丰富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些部分,一如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所开创的《诗学》理论可以为现代批评与理论所运用一样,也可为现代中国、甚至现代世界文论与文学批评所运用。李绂在《秋山论文》中所提出的叙事理论就是如此。
第四,如何挖掘中国丰富的文艺理论资源,以建设具有中国意义的文艺理论,并与世界文论相融合,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源自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理论,各有差别,不足为奇。同时,人类毕竟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而,不同文化的文学理论也会有许多共同与一致之处。这就为刘若愚所提出的“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20](P3)提供了基础。在这类比较研究中,将中外文论进行比较研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而就叙事理论来说,与探讨诸如李绂《秋山论文》叙事理论相关的比较叙事学研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挖掘中国自身丰富的叙事理论资源,“使以中国自身作为立足点的基础上开展的比较叙事学研究日益丰富,范围更为广泛,以使叙事学研究真正形成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学科”[22],形成与世界其他文化中的叙事理论的沟通、对话与交流,从而构筑真正的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理论”,这理应是中国学者积极从事的研究工作。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李绂.刻秋山论文序说[A].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李绂.秋山论文[A].王水照编.历代文话 (第四册)[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5][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6][法]保尔·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二[M].王文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7][美]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法]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A].黄晓敏译.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9][法]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0]苏轼.方山子傳[A].吳楚材,吳調侯選.古文觀止 (下册)[C].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李梦生.十三经注译·左传译注(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2]司马迁.史記(第一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4]韩愈.柳子厚墓誌銘[A].朱东润.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第一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5]司马迁.史記(第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7]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Revised Edi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
[18][美]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9[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0][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杜国清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1]蔡锺翔.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J].文学评论,1997,(5).
[22]谭君强.比较叙事学: “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J].江西社会科学,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