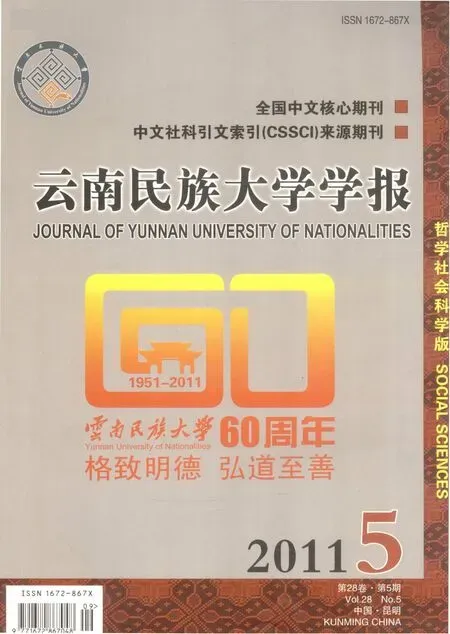《文心雕龙》集校、集注集释十则
张国庆
(云南大学中文系,云南 昆明 650091)
2008年,我与辽宁大学涂光社教授合作,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批准立项,开始做《文心雕龙》集校、集注集释的工作。现选取《原道》《练字》2篇集校、集注集释中较有学术性或较有笔者看法的十则文字,都为一篇发表,以向学界同仁、相关专家请益。
一、《原道》篇集校、集注集释选
集校一: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杨明照《校注》①为节省篇幅,本文于《文心雕龙》的各种校注本,均略去“文心雕龙”4字。[1]:“黄叔琳校云:‘一本实上有人字,心下有生字。’…… 《礼记·礼运》‘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为舍人此文所本。疑原作‘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气’正作‘气’,‘人’其残也;‘生’字非羡文。)下文‘心生而言立’,即紧承‘天地’句。 《征圣》篇赞‘秀气成采’,亦以‘秀气’连文。《春秋演孔图》:‘秀气为人。’(《后汉书·朗顗传》注《太平御览》三百六十引) 《文选》王融《曲水诗序》:‘冠五行之秀气。’陆德明《经典释文序》:‘人禀二气之淳和,含五行之秀气。’并其旁证。”○王叔岷《缀补》[2]:“黄叔琳云:‘一本实上有人字,心下有生字。’案‘人实天地之心生’。文不成义,一本非也。‘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并承上文人言之。则实上不必赘人字,盖涉上文‘惟人参之’而衍;《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即此文‘天地之心’所本,则心下不当有生字,盖涉下文‘心生而言立’而衍。”
按:杨明照《校注》、王利器《校证》[3]征引十数种版本皆有“人”“生”二字。杨明照认为:二语本于《礼记·礼运》,疑原当作“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因为“秀气”一词不仅为《礼运》原有,也为《文心雕龙》中它篇文章以及多种古文所用,而诸本中的“人”字正是“气”字的残文。然而,“实天地之心生”,却遭到学者们普遍的责难,除上引《缀补》外,如李曰刚《斠诠》[4]引潘重规语曰:“‘人者天地之心’,本于《礼运》,从无谓‘人为天地之心生’者,且‘心生’一词,前所无本,义亦牵强,实不宜辄改。”而李氏本人亦认为潘说“议甚的当”。不过,李氏同时又提出了一个特别的看法,即认为《文心》二句原本于《礼运》,当作“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对于由此形成的二句参差不偶,李氏解说道:“若夫辞不相俪,古人属文,原非字字等称,彦和《丽辞》篇不云乎:‘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况摘用礼经成文,语组天然,庸何伤乎?”综观各种版本和诸家说法,《文心》二句本于《礼运》,本无可疑,但“心生”二字,确属不词,更难与“秀气”成偶。李氏将“秀气”与“心”字相对成文,其关于“辞不相俪”的解释,亦比较勉强。固然“古人属文,原非字字等称”,甚至《文心》属文亦非都是骈俪,但试观一部《文心》,在明为骈偶的上下句中出现如此突兀不调“辞不相俪”的文字,这种情况恐怕是少之又少乃至于根本就未曾有过的!一般而言,将《礼运》 “五行之秀气”和“天地之心”改造成对仗的偶句,最简便易行的办法有二:一是在“心”后加一字组成适当的双音节词以与“秀气”相对。但我们看到,现在的“心生”并不属于能与“秀气”相对的适当词语,各种版本中又没出现“心”与它字组成的其它双音节词,可见,此路目前不通。二是将“秀气”减去一字而成为一单音节词以与“心”相对。我们看到,将“秀气”缩为“秀”或以“秀”字意指“秀气”,在古代汉语中实在是毫无障碍的。所以,这里有两个推断:第一、 《文心》二句,本即如黄本,诸本之“人”“生”为衍文(具体如何致衍,学者们曾有种种推断,不赘)。第二、如果真像杨明照等所认为,“人”乃是“气”的残文,那么,“心”字后面当有并非“生”字的另一字,可是现存的版本不能提供这样的字,所以,在刘勰原文难以确知的情况下,“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仍是最合理的校勘结果、最漂亮的校勘文字。
集注集释一:惟人参之。
詹瑛《义证》[5]:“《荀子·王制》:‘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杨倞注:‘参,与之相参,共成化育也。’《礼记·孔子闲居》:‘三王之德,参于天地。’郑注:‘参天地者,其德与天地为三也。’《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朱注:‘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汉书·扬雄传》上:‘参天地而独立兮。’注云:‘参之言三也。’‘之’,指天地。”罗宗强《手记》[6]:“彦和谓天地有文,人参之,人亦有文,故《赞》谓:‘天文斯观,民胥以效。’这‘天文斯观,民胥以效’,乃是彦和论天文、人文之基本观点,人文乃仿效天文而来,是则论述天地有文采之后,论人亦有文,仿效的意义自亦不言而在其中。这样,‘惟人参之’就存在着另一种解释,即:人仿效天地。参,参拟、模仿、效法。”
按:“惟人参之”,“参”(音cān)当为“参入”义,人因参入天地而得与天地并立为三,并称“三才”,故感觉上“参”似又因此而附带具有“三”义。在《原道》的语境里,人之所以得与天地配而为三,是因为人独得天地之灵气,为天地间天性灵智之最著者,是万物的精华,天地的心灵,因此,人在其原初、根本的存在意义上 (从时间上说,即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已得与天地并立为三了。说“参”为“参拟”,则“人”较“天地”已自先落下一层矣,又怎能与天地并称“三才”呢?就“文”来看,天地自然有文,万品自然有文,动植自然有文,人既为“万品”之一,更为“万品”之灵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当然也自然有文,人又何须参拟仿效天地而方始有文呢?再看《原道》“赞”语里所说的“天文斯观,民胥以效”。此语是说圣人观察天文创造了以符号、文字等为载体的经典载籍,百姓们都加以仿效,这里讨论的是以符号、文字等为载体的“文”“文章”的发端及其推广演进。圣人对天文的参拟仿效,是在人已成其为“人”很久很久(人间都已经出现了“圣人”)之后才展开的 (在刘勰笔下,对天文的参拟仿效始于“玄圣”伏羲),这样的参拟仿效显然只具有历史的存在意义而并不具有原初、根本的存在意义,事实上后世人们对天地的参拟仿效也随时在发生,但所有这些参拟仿效都已不再具有使人从根本上得以与天地并称“三才”的功能和意义了。因为远在此前,人已因其天聚灵秀而早与天地并立为三了。
集注集释二: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
李曰刚《斠诠》: “人文:人类之文化也。……太极,指生成天地之宇宙本体。此处可解作混沌初开之‘太古’。《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韩注:‘夫有必始于无,故太极生两仪也。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疏:‘太极,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太初太一也。’…… 《札记》: ‘据韩义,则所谓形气未分以前为太极。……非陈抟半明半昧之太极图。’”周振甫《注释》[7]:“人文:《情采》中作‘情文’,指五性。五性发而为文章。元:始。肇:开端。太极: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太极生天地,天地的灵秀之气蕴育成人的五性,就是人文。这是从理论上说明人文也与天地并生。其实人文是人类产生以后才有,不可能始于太极。幽赞神明:幽是隐而难见,故深;赞是助成,使微的着明,故明;神明是变化不测的道。指圣人通过《易》来说明神明之道。”牟世金、陆侃如《译注》[8]:“《易》象:《易经》的卦象。”张少康《新探》[9]: “一般认为这里的‘太极’即是《易传》中所说的‘太极生两仪’之‘太极’。 ‘太极’生天地,人是‘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所以‘太极’是‘人文之元’。其实,这里的‘太极’是指的‘易象’,即八卦。因为‘太极→天地→人→文’这个道理在《原道》第一段中已经讲清楚了,第二段说的是最早的‘人文’之产生和发展。这四句话中,‘肇自太极’和‘易象惟先’的含义是一样的,它是骈文常见的‘互文见义’的表达形式。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人文的起源,始自八卦,它乃是神明意志的体现”。
按:关于“太极”,笔者基本同意张少康的意见,并曾有不尽相同的具体分析,见笔者《儒、道美学与文化》。且扼要说明笔者的看法。这里的“太极”似不宜看作即是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标示宇宙本体的范畴“太极”,为什么呢?首先,“人文”源自宇宙本体的道理,前文已讲得很清楚了,这里要是再回头讲一遍,说“人文”乃产生于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则不免累赘。其次,再讲一遍,不仅重复,且反倒自生歧义。《原道》开篇所谈的“道”,是与老子的“道”密切相关的。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的“道”与《周易》的“太极”、一般所说的“元气”,都是表达宇宙本体的概念,具体含义却并不相同。老子的“道”,究竟是非物质性的还是也具有某种物质性,久有争议,不易判定,但它不是物质性的元气,则较可肯定。如果《原道》这里的“太极”按传统哲学范畴“太极”理解指的是“元气”的话,那么前面刚说过“人文”产生于非“元气”的“道”,这里又马上说“人文”产生于“元气”,岂非自生歧义?所以,“太极”若作“元气”解,则文意既重复又歧离。熟悉《老》《易》且文章高妙的刘勰,大约是不会如此使用“太极”一词的。再次,其实从“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开始,刘勰已经转入了对与人的自觉创造密切相关的,见于符号、文字或载籍的“文”、 “人文”的讨论了。这样的“文”、“人文”,当然不会始于混沌的“太极”或遥远的太古,在刘勰看来,它们确切是始于“玄圣”所“创”的“典”(《周易》)的。所以,这里的“太极”,即指的是《周易》 (从下文“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看,这里的“太极”和下句的“《易》象”,不仅指《易》象,而且指整部《周易》。当然, 《易》象仍是其中产生最早的部份,也最符合“人文之元”的身份)。 “太极”作《易》象、 《周易》解,则“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意为:见于载籍的或说以符号、文字记载的“人文”的开端,始于《易》象、《周易》。
顺便申言,《原道》中与“人”相关的“文”大约有两个层次。“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文”,是伴随人及其语言的产生即来,是与“动植皆文”一样的自然成文,无待乎由人的自觉创造而来的符号、文字、载籍的出现和运用。“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及以下所论的“文”和文化、文学现象,则大多正是与由人的自觉创造而来的符号、文字、载籍的运用密切相关的。分清这两个层次,对于正确理解《原道》中的“文”、“人文”是很重要的。
二、《练字》篇集校、集注集释选
集校一:文象列而结绳移。
刘永济《校释》[10]: “按各本皆如此,疑当作‘爻象’。《易·繋辞》下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此言圣人因八卦爻象可治民事,故以易结绳。下句始及造文字之事,疑‘文’乃‘爻’字之形误。”詹瑛《义证》:“按全文均与爻象无关,且‘爻’字亦于板本无据,不当改。‘文象’,文字形象,即最初之象形文字。”
按:《校释》之说,不为无据,亦有一些注家从之。然《义证》所据以反驳之二点理由,亦甚有力。此外,陈拱《本义》[11]指出:《校释》所引《易·繋辞》(上)之另一段话(“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云云),乃许慎《说文解字·叙》首引之,《校释》依许氏以为说,但“唯此实误。许叙虽以此为始,盖以卦象与文字有关也。然彦和实不必如此。故不得以彼例此也。”《本义》又指出:“《易·繋辞》(上):‘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此言以文字记载代结绳之治也。”彦和“文象列而结绳移之说”即“本此”。综《义证》、《本义》之说,字仍当作“文”。
集校二: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
范文澜《注》[12]:“据《艺文志》及《说文序》,张敞正读在孝宣时,扬雄纂训在孝平时,此云‘宣成二帝’,疑‘成’是‘平’之误。”张立斋《考异》[13]:“汉自孝宣至孝平,颇重小学,张敞扬雄诸作皆在此时。历宣、元、成、平诸帝,作辍不一。 《汉志》所载,未必为全。而本文所指,概言其略,故曰宣成。杨注疑‘成’为‘平’之误,胶柱之见也,非是。”
按:明言“二帝”而不言“诸帝”,且“二帝”又与张敞“正读”、扬雄“纂训”二事呼应,时与事切,显然说的是具体的时代与事件。《考异》说本文是在“概言” “宣、元、成、平诸帝” “作辍”之“略”,似乏确据。故范、杨疑“成”为“平”之误,应是。陈拱《本义》亦认为范《注》 “是也”,而评《考异》作者在之前的《注订》中的类似上述《考异》的说法道:“此实在随便瞎扯。若略翻《汉书》,将不如是矣!”
集校三:鸿笔之徒。
王利器《校证》:“‘鸿’原作‘鸣’,梅据朱改作‘鸿’,黄注本改。”陈拱《本义》:“《纪评》:‘鸣字不误。’按作鸣固通,然不及鸿义饱满也。原疑作鸿,或因形似而讹也。”张立斋《考异》:“鸣鸠之善鸣者也,鸣笔言文之善者也。假笔墨以出之故曰鸣笔。韩退之曾本之为文,是征鸣字之用较鸿为长,朱改非是。”
按:“鸿笔”,大手笔。“鸣笔”,善以笔鸣。二者皆意义显豁,容易理解。但“鸣笔”尚值得推敲。《考异》云“韩退之曾本之为文”者,应指韩愈《送孟东野序》之本“鸣”以为文,但此文并未用到“鸣笔”。在光盘版《四库全书》的韩愈文中乃至整个集部之中搜检“鸣笔”,都无其踪影。这表明“鸣笔”在古代是否成词,是有疑问的,至少古人极少使用它。而在《文心雕龙》中,除《练字》篇外,又曾两度使用“鸿笔”:《封禅》云:“鸿笔蟠采”;《熔裁》云:“草创鸿笔”。可见彦和所习用者,乃是“鸿笔”。作“鸿笔”是。
集注集释一: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
牟世金、陆侃如《译注》:“玮字:奇异的字。制异:制造奇异。共晓难:指扬雄、司马相如等都通晓难字。”周振甫《注释》:“非独制异:京苑等赋,不但因古今制度不同,就是文字,要共同理解也很困难,指浅学所不能晓。”李曰刚《斠诠》:“言不独制作奇异,而词字训义古奥,非浅学之士所易共晓也。”祖保泉《解说》[14]:“制异:字的体制异常,即异体字。共晓:世人知晓。按:相如、扬雄,都是当时的古文字学家,他们的赋作,显示了他们识古文奇字的本领,但也确为后世读者设置了一些障碍,以致造成‘共晓难也’。”
按:“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一句,歧解甚多。“制”,有解“制造”、“制作”的,有解“制度”、“字的体制”的;“难”,有解“难字”的,有解“难易”之“难”的。种种歧解,难以在此详析其得失。
合《译注》与王礼卿《通解》[15]之说,似可得其确解。《译注》注解已引出,译文曰:“因此西汉时期擅长文字学的作家,大都好用奇文异字。这并非他们特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当时的作家都通晓难字。”《通解》云:“斯非其时故炫奇博,实由通小学者,并晓古义,后世以为难者,当时学人皆视为易。”总之,言扬雄、司马相如等人多用奇异文字,并非故炫奇博实因后人引以为“难”的那些文字,他们都能通晓而皆视为易罢了。
集注集释二: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
牟世金、陆侃如《译注》:“暨:及,到。复文隐训:复杂的文字,深刻的意义。‘复’ ‘隐’连用,二字义近,本书多用以表示丰富深刻的意思。如《原道》: ‘符采复隐,精义坚深。’ 《总术》: ‘奥者复隐,诡者亦典。’臧否:好坏,善恶。这里用作偏义复词,指否,即错误的理解。”范文澜《注》:“‘复文’,谓如有长字斗字而重作马头人之长,人持十之斗。‘隐训’,谓诡僻之训,如‘屈中为虫’,‘苛之字止句也’之类。‘大’疑是‘亦’字之误,谓后汉之文,有深于小学者,有疏于小学者,臧否各半也。’”斯波六郎[16]:“案‘复文隐训’要为难解之文字。所谓‘复’,所谓‘隐’,分用‘复隐’之语。如区别‘复文’与‘隐训’,则前者谓字形复杂难懂者之意,后者则字形简单,而使其意义难懂者之意。范氏解‘复文’为异体文字,解‘隐训’为诡僻之字义,其说难从。其举‘马头人之长’以下之四例于《说文解字叙》,据俗字任何方面而言,皆是标示无稽之字义说例,与此之‘复文隐训’无关。‘臧否大半’,后汉人之文字用法,其大半皆用为非难之意。”王礼卿《通解》:“复文疑若后世之俗字、简字,失形音义结构之理,致文字紊乱繁杂之象。隐训疑若王荆公《字说》,缺渊源之训诂,为穿凿破碎之解。”吴林伯《义疏》[17]:“‘复文’句,犹云‘复隐文训’,谓文字之音训不明也。臧否,……评议也。……后汉学者言文字音训,可评议者居太半,则其作文用字之失当必矣。”
按:《译注》之解不妥。 《文心》多处“复隐”连文,确有“丰富深刻”之意,但此处“复隐”若指“复杂的文字,深刻的意义”,则显然与上下文字不协。因这里正说后汉“小学转疏”,有贬意,是很不可能忽又言其意义深刻的。
试对其余诸解,作一综合性的总括。“复文”,由种种原因 (异体字、“俗字、简字,失形音义结构之理”等等)导致文字“紊乱繁杂之象”、“字形复杂难懂”。 “隐训”,由种种原因(“诡僻之训”、“缺渊源之训诂,为穿凿破碎之解”等等)导致“文字之音训不明”、“意义难懂”。“臧否大半”,《义疏》“后汉学者言文字音训,可评议者居太半,则其作文用字之失当必矣”之说似更能得其意思。如此,则正足见后汉之小学“转疏”矣。
以上说解,有其理据,有其所得,然犹似未能透彻地揭示出彦和的真实意旨。笔者在参考众说的基础上,尝试再提出一个不尽相同的解释。
要解释清楚本句的意思,需要联系上句乃至前面多句进行分析,因为本句议论原是承上而发的。“复文”,指上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中的“玮字”而言,即奇文异字。这些在后人看来“复”杂“难”懂的奇文异字,在前汉却是为“贯练《雅》《颉》”的扬雄、司马相如等众多“鸿笔之徒”所“共晓”、所“莫不洞晓”的。到了后汉,由于“小学转疏”,这些玮字的义训渐渐少为人们了解、“隐”(隐伏、隐沦、隐晦)而不明了,换言之,也就是“复文”渐“隐”其“训”了。由于后汉“复文隐训”,先前“鸿笔之徒”们“莫不洞晓”的玮字,也才真正地由易转“难”了。(顺便说,本篇下文“岂直才悬,抑亦字隐”的“隐”,同样是指前汉玮字的义训已渐渐变得隐晦不明,遂令玮字深奥难懂了。)
至于“臧否大半”的“大”,则当如范《注》说作“亦”,“臧否亦半”乃“谓后汉之文,有深于小学者,有疏于小学者,臧否各半也。”陈拱《本义》认为,“臧否大半”的“大”,“或各字之误”。二说义近。
集注集释三:“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
牟世金、陆侃如《译注》:“潜移:暗暗改变。淫:过分。列:通‘烈’。说‘过多的雨’、‘猛烈的风’,所以‘义当’。乖:违,不合。”
按:注家对彦和此处所述有疑问和不同理解,当予辨别。
陈拱《本义》认为“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二句“颇可疑,应误”,分析说:“上句‘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意谓别移为列、淮变为淫,乃后起之‘文变’,已失原义。而此反言淫、列义当,淮、别理乖,前后文意殊相扞格,细审之可知。故此二句似应作: ‘淮别义当而不奇,淫列理乖而新异’。”王礼卿《通解》则云:“举《尚书大传》别风淮雨,证以《帝王世纪》,知其为列风淫雨之讹变,彼固义当而不奇,斯则理乖而新异。此明讹变之特例,义虽不可训解,风致则嫣新可取,文人爱奇,……斯则足成练字之失也。”周振甫《注释》又曰: “列风淫雨是对的,别风淮雨是传抄致误。”
上述诸解呈现出两个问题,下面分别讨论。
第一个问题,在实际上和在刘勰看来,是“别风淮雨”演变为“列风淫雨”呢,还是“列风淫雨”演变为“别风淮雨”?按《注释》的说法,实际上是“列风淫雨”演变为“别风淮雨”;按《通解》的说法,刘勰是指出了“列风淫雨”演变为“别风淮雨”的。但就二语的出现时间看,说“别风淮雨”的《尚书大传》的作者是西汉人,说“列风淫雨”的《帝王世纪》的作者是西晋人,先出的“别风淮雨”不可能是很晚才出现的“列风淫雨”的“讹变”或“传抄致误”,情况只可能是相反。就本篇的叙述看,“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显然是指发生了从“别”到“列”、从“淮”到“淫”的潜移变化,这就表明,在刘勰看来,确切是从“别风淮雨”演变为“列风淫雨”的。
第二个问题,本篇此处是否如《本义》所言“前后文意殊相扞格”,是否“淫列”二句当改作“淮别义当而不奇,淫列理乖而新异”?《本义》认为,“淮别”变作“淫列”,是一种“已失原义”的“文变”,因此就不应当再说“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了。这样的理解,确与本篇的表述有关。本篇上文刚指出传写中的“文变”会导致原先字义的改变,这里就指出“淫列”是“淮别”的“文变”,照理,接下去就应当批评这一“文变”了。可是,接下去却肯定了作为“文变”的“淫列”而批评了原先的文字“淮别”。这难道不是“前后文意殊相扞格”吗?依照对“文变”的否定,不是应该将二句改为“淮别义当而不奇,淫列理乖而新异”才逻辑顺当吗?所以,《本义》之说是有根据有道理的。不过,问题似乎不这么简单。就辞语的实际情况看,“列风淫雨”的确是“义当而不奇”的,而“别风淮雨”也的确是“理乖而新异”的。那末,是不是刘勰谈“文变”的时候举例失当了呢?一方面,似乎可以这样说,但另一方面,大约也还可以作另外的理解。“淮别”固然早出,但也许由于其辞过于僻异不易理解,故并不为世所通用。 “淫列”虽然晚出,但由于其辞义当无奇通俗易懂而为世所共享。久而久之, “列风淫雨”成了这一语词的标准表述,而“别风淮雨”渐为世所淡忘。此后,有人忽觉“淮别”“风致嫣新可取”而偶用之,也确实取得了用古旧而得“新异”的效果,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淮别”实在又是标准表述“淫列”的一种“文变”了。很可能,本篇举“淮别”、“淫列”为例来谈“文变”,并批评由文人“爱奇”、求“新异”而导致的“文变”,而造成《通解》所说的“练字之失”,主要就是在这后一种变化(“淫列”再变为“淮别”)的意义上讲的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本篇的相关交代、叙说、理路是没有根本性错误的,只有不够清楚、完备的不足。而上述注家解说上的歧异,便是由这种不足所直接导致。
集注集释四:篆隶相熔,《苍》《雅》品训。
周振甫《注释》:“相熔:指文字形体的熔入变化,如篆字据大籀省减,隶书据篆字省减。”《苍》《雅》品训:周振甫《注释》:“品训:品评训释,指字义的解释。”詹瑛《义证》: “‘品’,品量。《斠诠》:‘谓《苍颉》品字形,《尔雅》训字义,前文所谓“《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是也。’”牟世金、陆侃如《译注》:“品训:多种解释。品:众多。”陈拱《本义》:“品,类也。品训,谓以类相为训也。”吴林伯《义疏》:“《苍》《雅》,《苍颉篇》与《尔雅》。上文以此二书‘异体’,盖《尔雅》为训诂渊源,《苍颉篇》为奇文苑囿。但为与上句‘篆隶’对偶,二者并提,实复词偏义,‘品训’者,只《尔雅》云。”
按:这里提出一个与上述诸家注解不尽相同的解释。《苍》《雅》并不是“复词偏义”,“品训”也并不是“只《尔雅》云”。《苍颉》《尔雅》都是本篇非常重要的讨论对象,前文曾予专门的重点的论述,在做全篇总结的时候,同时言及二者,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须的。“《苍》《雅》品训”皆实指,一字一义,其中“品”就“《苍》”言,“训”就“《雅》”言。品是品列,指《苍颉》篇“苑囿奇文”,列示众多的文字;训是训释,指《尔雅》“渊源诂训”,解释文字的字义。“《苍》《雅》品训”,换言之即是“《苍》品《雅》训”。
[1]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王叔岷.文心雕龙缀补[A].慕庐论学集 (二)[C].北京:中华书局,2007.
[3]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M].台北: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2.
[5]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罗宗强.文心雕龙手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8]牟世金,陆侃如.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1.
[9]张少康.文心雕龙新探[M].济南:齐鲁书社,1987.
[10]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陈拱.文心雕龙本义[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
[1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3]张立斋.文心雕龙考异[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14]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15]王礼卿.文心雕龙通解[M].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16]詹瑛.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7]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School of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Abstract:Since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there have been quite a few annotations on Wenxindiaolong(a greatwork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However,there are some misinterpretations or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se annotations.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gives a correction of ten annotations on Wenxindiao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