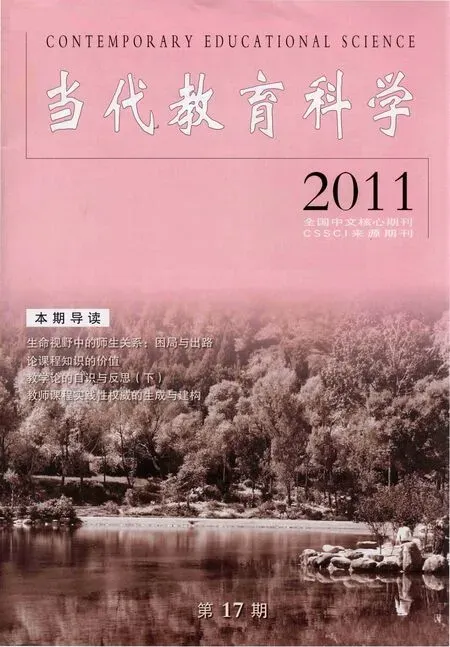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生成与建构
● 邓 浩 高丽丹
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生成与建构
● 邓 浩 高丽丹
教师的课程实践性权威是本文提出的一个尝试性概念,它有别于课程的学术性权威与行政性权威。课程实践是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生成的源泉,课程批判意识体现着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意识的本体觉醒,课程行动研究是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重塑的现实力量,教学实践智慧是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塑造的内在动力,而自主性理论的形成标志着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正式确立。
课程实践性权威;课程行动研究;课程批判意识;自主性理论
课程实践性权威是本文提出的一个尝试性概念,用于表述课程权威的一种具体形式。根据课程参与主体职能的不同,我们将课程权威划分为三种形式:课程学术性权威、课程行政性权威与课程实践性权威。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当提到“课程权威”时,我们更多的是倾向于专家所具有的学术性权威,其次为教育行政人员的行政性权威,而往往忽略教师的实践性权威。作为课程实施主体的教师往往能够建立起以“他者”为中心的课程权威意识,而对以“自我”为中心的课程权威意识却漠然处之、浑然不知或无所适从。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教师的角色及教师教学观等多方面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中担当课程研发的生力军,在课堂教学中扮演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强调课程的创生与生成,强调“教师即研究者”、“教师即课程”。这些观点无不在表明同一个命题,即:教师个体、教师群体对课程的重要意义。相对于这样的倡导,我们在现实中所能找寻到的痕迹却是教师对课程影响的无力感,因此,我们在此提出重建教师的课程实践性权威,目的就在于要帮助教师意识到“我”的存在,“我”对课程的影响力,“我”对课程阐释的权威。这种以“我”为中心而建立起的课程权威意识标志着以“他者”为中心的课程权威意识的消解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课程权威意识的重建。
一、教师的课程实践性权威
所谓权威,从哲学意义上讲,是指在实践中形成的最有威望、最有支配作用的力量,亦或指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当权威这一概念延伸至课程领域,并与课程结盟——课程权威——而出现时,我们往往把目光聚焦于课程专家、学者等具有学术性权威的群体指向,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权威的第二层含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而对于产生权威的根本领域却极少关注。权威在课程领域表现出专业化的态势,此时的权威既不是指传统赋予的世俗性权威,也不是社会赋予的制度性权威以及由人格魅力而产生的个体性权威,而是专指一种专业性权威——学术性权威。课程的学术性权威在课程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恭敬与尊崇。但是,毕竟每一种权威发挥作用的区域是有限的,当它高高在上的指导教学实践时,由于过分的学术化而使其失去了本源的支持,在学术领域中,它的声名与威望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实践领域,它只不过是获得了“摆设”的权威,而实质的权威效应并没有发挥的余地,因此,实践领域亟需自己的权威“领袖”,由实践而生、为实践服务,这样生成的课程权威,我们便称之为“课程实践性权威”,它的主体不是课程专家,也不是课程学者,而是长期坚守于教学一线的广大教师。
二、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虚化与异化
校本课程开发和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都应该是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建构、生成、发生影响的重要领域。一方面,教师通过参与学校的集体决策从而确定本地资源所能支持的课程内容,通过决策决议结果的执行与实施来塑造自己的课程权威;另一方面,教师根据具体的学生和问题的不同作出一定情境下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方法的创生与生成,实现生本教学的目标,获得学生的信任与支持,从而建立课堂中的课程权威。但是,由于外在因素(例如社会性因素的规约或者制度性因素的牵制等)的干扰以及内在因素(教师个体的专业能力、教学技能、个人认识等)的困扰,教师对自我的权威意识认识不足,导致了实践领域中教师权威的虚化与异化。
(一)校本课程开发中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虚化
校本课程将教师纳入到开发体系中来,以教师开发为主导,其目的就在于激活学校教师参与课程设计的积极性,强化教师作为课程研究者的角色,从本校实际出发,为学生提供具有本校文化特色、更贴近学生生活的课程。然而,现实的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与课程权力紧密相连的,它否定教师的课程设计权利、课程开发权利,将教师的课程实践性权威丢掷于一边,而是利用行政性权威将校本课程的开发纳入学校文化体系。在作为科层组织的学校决策体系中,教师往往是权力关系中的弱者。许多教师本人也认为,在那些不够民主的学校文化中,课程的决策权只是集中在少数当权者手中,其他教师只是执行已有的决定而非参与决策,由是,教师对课程的意义、对课程的真知灼见、因课程而积累的实践经验等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中被隐匿或忽略不计了,教师的课程实践性权威的塑造也就无从谈起,没有课程实践,何来实践权威呢?
(二)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异化
校本课程的开发虽然排斥了教师的课程实践能力与经验,但课堂教学却为教师课程权威发挥提供了重要场所。教师一旦关上教室的门,他(她)就成为了唯一的教学决策者,学生感知到的课程最终形态大多来自于教师的课程决策。长期以来,受到“师道尊严”教化的学人慢慢的适应了社会所赋予教师的“世俗性权威”,受到“尊师重教”思想的提倡与普及,人们也慢慢的接受了制度所赋予教师的“制度性权威”。在这种传统、制度加之闻道在先的优势,使得教师渐渐成为不容置疑的课堂权威。但是,反思此种形态的课程权威,我们不仅要追问:难道这种控制性课堂教学实践或者去批判性的教学实践就是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真实状态吗?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一种非理性权威的泛滥。真正的课程实践性权威源于对学生个体的真切关怀,能够充分发挥自我的主体性,引领学生过一种自由、舒畅的教学生活,而不是控制。由此看来,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教师课程权威虽存在,但却已异化,失去了其本有的权威功能。
三、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生成与建构
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生成与建构,既不是源于对权力的追求与服从,也不是源于对生活的控制与操纵,而是源于自我教学生活的自主性与发展性。教师应从课程实践出发,不断增强对课程的批判意识,采取行动研究的方法,凭借个体的实践智慧生成属于自我的自主性理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在课程实践中的权威。
(一)课程实践是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生成的源泉
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生成源于何者?课程实践还是课程理论?亦或者是教师本身所接受的课程知识、课程培训或者课程指导?显然,是课程实践。对教师而言,课程实践比其他一切课程相关物都要更为根本。课程实践是教师教育生活的真实反映,是教师知能发展的原始状态,是教师教育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直接对象。而课程理论、课程知识只不过是对课程实践进行抽象、加工后的产物。因此,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树立并不在于教师掌握了多少课程理论,也不在于教师是否懂得更多的课程理论,而是在于教师在课程实践中是否能够与课程教学情境达成暂时的一致,能否在课程实践的过程中创造或创生新的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样式。这当然不是否定课程理论存在的意义,而是在于,唯有当教师的课程实践达到较高层次,进入反思性或者批判性实践的阶段时,他(她)才会亟需课程理论的引导。而一般意义上的课程理论只是对教师课程实践中一个个课程场景进行浓缩、截取、重组、拼贴,使之具有某种人造理论结构而已。理论对教师总体而言可算作是精神食粮,而实践却是教师向理论层次不断攀登的阶梯。
(二)课程批判意识体现着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意识的本体觉醒
当我们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我们周围的一切时,我们也就获得了对这个世界的主动权,并会因此种行为而使得我们更加强大。批判,理性的批判,不仅仅表明我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我们拥有了思想本身。唯有有思想的人才能更好的发展,因此,批判意识的培养对于每一个人的发展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始于一致性要求的现代性教学理论追求客观、普适的教育教学范式,在其规约下教师对课程鲜有批判和见解。[1]为此,我们需要培育教师的课程批判意识,提升其课程批判意识力。通过教师对其既有“预成论”教学思想的检视与批判,以适应变革时代的变革要求。教师在日常的课程教学生活中,在应对复杂多变的教育教学实践时,对实践现象和对专家学者所生产的理论的去蔽与反思,并在判断反思的基础上生成自己的理性认识与基于这种生成的理性认识而尝试进行课程教学的变革实践。进而言之,教师的课程批判意识,一方面是教师在种种教育教学变革理论面前,不再把自己盲目地定位于理论的忠实执行者,而是依据自己教学实际的情况和自己的理性分析,对理论进行辨别与筛选,进而作出改进的意识。另一方面是指教师对自己既有的、长期养成的教学惯习,譬如知识人的教学目的论和教学价值观、讲授认识论取向的方法论及其指导下的教学行为等予以批判反思的意识。[2]教师课程批判意识的培育与提升,为教师对现代性教学理论和其“预成论”教学思想进行批判与解构提供了条件,也为其自身课程理念的提升与升华以及其在课程领域中的话语权的权重增加了砝码,这种本体性的觉醒在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意识建设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批判,便唯有迎合;没有批判意识,便唯有唯诺是从,因此,教师的课程批判意识的觉醒是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意识建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课程行动研究是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重塑的现实力量
课程行动研究在欧美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对我国的课程研究者来说还并非谙熟于心,对于广大的一线教师来说更是如此。这对于长期以来在我国集权式的课程体制运作下习惯于被动服从和执行国家课程规定的教师来说,对于以往课程的设计和实施强调统一性而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课程体系强调划一和封闭、忽视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动参与而造成教师缺乏专业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而言,课程行动研究及其模式无疑为我国的课程创新及教师的课程实践提供了全新的理念。课程行动研究是指实施课程的教师基于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具体的课程问题,将问题发展成研究计划或研究主题,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对课程问题所进行的系统研究。[3]课程行动研究主要基于教师即研究者这一精神理念和特征,是课程理论与实际教学情境不断对话的辩证循环过程,已成为学者及教育工作者从事课程研究的主要方向。近年来许多肯定课程行动研究价值的学者认为教师不但可以成为课程理论家和研究者,而且应担当起推动课程发展的大任。作为研究者的教师,应把课堂当作课程改革的实验室,把课程评价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走向研究模式。课堂是教学实际发生之处,教师始终是自然情境中的参与观察者,他们会对其工作情境与问题产生专业知觉进而透过系统的探究过程予以理解、解释乃至改进教育的价值。
(四)教学实践智慧是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塑造的内在动力
教师的教学实践智慧是学科专业知识、教育教学知识和技能充分整合、内化、升华的结果。教学实践智慧的获得既不是单纯理论的学习或实践观摩就能获得的,也不是单凭教师的聪明才智、或者教育机智所能容括的,而必须借助于教师自身的实践性反思与反思性实践两种方式,方能获得教学实践智慧。实践性反思采取“情境取向”的反思路径——大部分的实践问题都是情境性的,开放、变动不居是它的主要特点,主体既无法事先准确的确知具体情形,也很难在行动时充分观察、从容分析思考,这就决定了“事后诊断”的必要性,即通过反思实践从而加以提升;而反思性实践采取“理性取向”的反思路径——在实践开始之前,教师会根据普遍性规律、原则和对实践情境的一般了解,制定大体的行动纲领,在实践进行的过程中,又可以随时、灵活的调整行走路线,由此可见,这种预设性的反思方式彰显了教师实践行为的策略性。通过这种基于实践的反思,教师才能够真正沟通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也才能自觉地涵养自身的教学实践智慧。
(五)自主性理论的形成是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确立的重要标志
教师作为课程实践的主导者,对课程方案的实施、课程理念的建构、课程整体的规划发展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难以忘怀的心路历程。他们从实践中所凝练而出的带有个人特色的课程理论,即教师个人理论,是教师对课程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精神向往、理想追求和观念体系,是课程的生命力之所在。是一种集实践智慧、课程批判意识为一体的课程理论体系,并且这种课程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课程实践为基础,并为课程实践服务。教师所形成的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有着天然的关联性,它不像学术性课程理论,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显得晦涩与懵懂,之间的断层感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有效的指导课程实践,它对教师课程实践的影响是直接的、有效的和深远的。当然,教师自主性理论的建构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她)要从自己的大量的、繁琐的课程实践活动中总结经验,提升经验、升华经验,而经验的表征只是教师自主性理论建设的第一步,接下来,为使这种经验具有普适性,它必须获得理论研究的外衣,唯有如此,才具有了推广的意义,也才能形成具有个体认识特色的课程体系。教师在将课程实践经验理论化的过程中,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教师课程思想的建构主要是建基于模仿方式,将学者、专家的学术性思想的逻辑文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运用到自己的理论建设中来,随着其对课程实践研究的加深,他(她)将逐步摆脱这些支配性话语的束缚,能够运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去表征课程实践,这便进入了自主性理论建设的初级阶段。而独创性的课程思想的产生是以上两个阶段不断累积的结果,教师开始以实践中的问题为原点,通过理性的思考与批判性的反思,建构出自己独立的整体理论方式和思考空间,这也标志着教师自主性理论的形成。自主性理论的形成对教师专业发展、专业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其参与课程决策,获得更多的课程权利提供了有效条件,当然,也就为教师课程实践性权威的确立提供了保障。
[1][2]孟凡丽等.课程改革中教师的教学哲学及其重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11).
[3]焦炜等.课程行动研究模式探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0,(8).
邓 浩/河南财经大学成功学院,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 高丽丹/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
(责任编辑:孙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