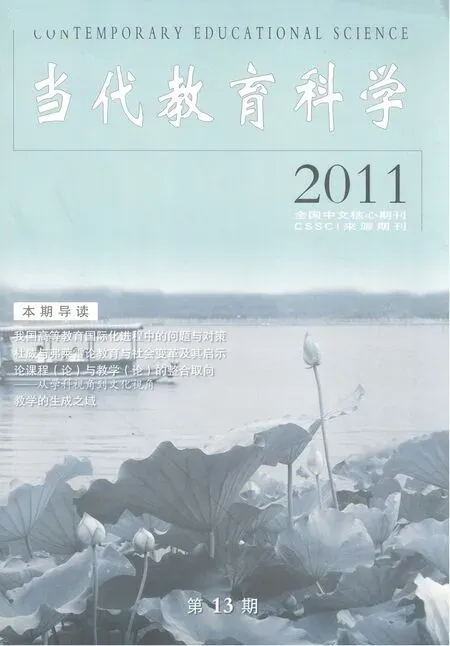论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之关系
● 伊 鑫
论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之关系
● 伊 鑫
同权论认为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同属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制度保障说则将大学自治视为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制度保障说准确界定了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对我国大学法治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同权论;制度保障论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两个关系密切而又容易混淆的概念。一项对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析认为,如果被法律或公共观点支持,学术自由可以在大学自治缺失的情况下存在。但是又有情况显示有些外部干预会或明或暗地侵蚀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有助于维护学术自由的精神和保护这种自由免于外部的攻击。[1]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都是建立在“传播和创造高深学问”这一大学内在逻辑的基础上的,但二者之间具有何种内在关系却一直存在争论,二者同权论和制度保障论就是两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本文试图在分析上述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澄清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之间的关系。
一、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渊源
“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2],大学争取自治是从建校时开始的,在中世纪产生之初,大学就产生了自治的诉求。大学具有国际性,其成员来自世界,主张普遍教学的自由,它的领域是基督教世界,而且冲破了城市的范围。大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与教会、王室甚至是普通市民进行斗争的过程,斗争的手段是罢课和迁校,斗争的结果是大学有了自己的特权。
而学术自由概念的产生则要晚的多,作为大学探索真理的原则学术自由首先被德国大学接受,其思想奠基者是洪堡、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等人,认为大学必须将研究提升到与知识传授同等重要的地位,而要开展学术研究就需要确立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这一思想逐渐形成经典大学的基本理念并被欧美大学普遍认同。学术自由在最初仅仅限于学校内部,是学校自身的行为,却无法防止来自外部力量的侵害,因此需要国家法律的认可和保障。到了20世纪初期,则上升为宪法基本权利,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开始明确保障学术自由。因此,从历史上看,大学自治的理念和制度先于学术自由而产生。
二、二者同权论
二者同权论把学术自由视为大学的基本权利,大学是学术自由的组织体,大学自治是一种团体性的学术自由,是学术自由的合理延伸和当然结果。确实,随着学术自由权内涵的发展,权利主体已经实现了从学者向普通公民、从个体向组织转化的过程,许多国家将学术自由的主体扩展到了包括大学在内的机构,把学术自由视为大学的基本权利自在情理之中。同时,这种观点立足于自由主义的精神,为大学自治提供一种自然法上的正当性,使学校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能够形成一种对峙而又互动的良性格局[3],更易于直接明确的论证大学自治的合法性依据。不过,把大学自治权直接等同于宪法学术自由权,存在许多不足:
首先,掩盖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之间的内在关系。大学自治以实现学术自由为旨归,具有手段性价值,与学术自由权的实现之间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并非等同关系。相反,如果一所大学自治的主体是学校的行政系统,反而可能会带来对学术自由的伤害。事实上,学术自由并不必然产生于大学自治,大学自治也不必然以学术自由为最终目的。大学自治不包含学者个人的学术自由等权力诉求的意义,而是指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为避免外界干扰而提出的属于大学整体需要的自我决策、自我管理的权力诉求。大学自治有可能损害学者个体的学术自由。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知识分子进入学院化的大学校园后,大学里烦琐的规定成为最麻烦的学术障碍,……大大限制了学者们的独立人格和学术自由。[4]因此,当大学自治行为损害到了教师和学生的学术自由时,应该受到限制,大学自治作为手段并不是无限的。大学自治要受到国家合法性的监督,使得大学自治在保护学术自由、学习自由以及大学成员其他宪法性权利前提下展开。
其次,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二者的内容并非完全等同。一般认为,学术自由的内容包括学术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以及研究成果的传授、交流与发表自由等三个方面。而大学自治则是指大学必须由自己的机关独自负责并且不受国家之指示以完成事务之意,亦即大学之管理、运营系委诸于大学内部之自主性决定。[5]大学自治内容上则要丰富的多,从实体和程序角度来看,大学自治分为实质性自治和程序性自治;从自治权的分立和运行来看,又可以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监督权;从具体内容来看,大学的自治权包括人事的自治、学生选择的自治、教育课程决定的自治、研究计划决定的自治、财源分配的自治等。
再次,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二者的主体不完全相同。学术自由权的主体一般适用于全体国民,但大学自治的主体却有很大差异。德国大学自治权的主体主要是教授,形成了教授治校的大学自治模式;而美国则形成了董事会领导下的大学自治模式。我国教育法规定办学自主权的主体是大学,而高等教育法中主体是大学和校长,而没有作为大学重要构成人员的教师和学生,特别忽视了学生的权利,但在大陆法系许多地区,学生一直处于大学构成主体的地位。可见,在学校这一集体之内,仍然存在着自治权主体的差别,而这一差别可能使之对学术自由的保障功能也会有所不同。
三、制度保障论
制度性保障理论最初由德国威玛宪法时期学者施密特将其体系化,意指在宪法规范之下,某些具有特定范畴、任务及目的的制度应为国家宪法所承认,受到宪法的特别保护,立法者不能通过立法而将其废弃。制度性保障的功能在于避免某些先存性法律制度免受立法者废弃,这是一种消极的制度性保障。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内涵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制度性保障的目的在于保障特定的法律制度,而非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制度性保障是以一定法律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其所保障的乃是一种被形构、组织乃至被界分的具体法律制度。制度有别于自由权利本身,制度对于个人自由的保护与强化则具有补充的功能,因此制度性保障的结果可形成对某些自由权利的连接性、补充性的保障。其二,制度性保障的客体是既存的法律制度,是现行宪法制定之前即已存在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制度文明建设的结晶,运行多年,且有组织、结构上的表征,并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法律保障,其核心部分必须予以尊重。其三,制度性保障的前提是相关法律制度必须有宪法连接点。传统的法律制度只有被宪法纳入时才能获得制度性保障。“经由宪法法律的规范,特定制度可以获得特殊的保护。此种规范的目的在于使立法者无法以单纯法律的方式废除此等制度。”[6]其四,制度性保障的内容是立法者不能对已经纳入宪法范畴的法律制度的典型特征加以侵害。立法者在对某一法律制度进行改革时,必须尊重现存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如需废弃该法律制度,则必须启动修宪程序。当然,宪法对该类制度的保障并非保障这些制度的现状,而是保障这些制度的本质内容,国家可根据立法对这些制度的周边部分进行界定和变更,但不可侵害其核心部分。
依据制度性保障理论,大学自治在作为传统制度受到宪法保护的同时,又成为宪法基本权利,从而得到宪法的双重保护:在消极层面,防御立法者创设法律侵害大学依据学术本质需要而应享有的自治制度的核心部分;在积极层面,则可以要求立法者积极创设法律对大学自治进行确认,并通过具体的制度去实现和保护大学自治。基于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理论,德国传统的大学自治制度与作为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建立了紧密的连结。按照积极性制度保障理论,一方面要求立法机关创设的法律不得侵害大学依学术本质需要而应享有的自治权利,另一方面则要求立法机关积极创设法律对大学自治进行确认,并通过具体的制度去实现和保护大学自治。
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制度性保障,大学自治不仅是对大学构成人员学术自由的保护,而且是对大学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学术自由的保障。学术自由为基本权之一,其权利主体除从事学术研究之个人外,还包括大学本身。倘使只有从事研究个人享有学术自由基本权,而大学并不拥有此项权利,则国家对于大学干预,例如限制大学图书馆收藏图书种类,仅能当其直接影响个人研究活动时,个人才可以主张学术自由的保护,而大学本身并不能直接、立即地援用基本权防御功能,不啻为国家提供一个间接、但是极为有效干预学术研究自由的途径,显然悖离宪法保障学术自由精神。而且由于现代学术研究工作早已非研究者凭借自己毅力和天分所能完成,而往往必须透过研究机构各种设备与人力的支持始得进行,大学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学术研究工作得以开展实现的必要场域,国家除了应消极地不干预研究者个人学术研究活动外,更应创设制度以协助保障学术自由之实现,而大学自治,正是为达成此一目标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性保障功能。
四、对我国大学法治建设的启示意义
制度保障说在德国的大学自治的法理理论中目前处于通说的地位,也得到了联邦宪法法院的认可,对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宪法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日本,二战前,大学自治制度被视为一种惯行,在战后则被视为与学术自由的宪法规定具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而受宪法的保障。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相关的法律文件中更是明确认定了制度保障说,如在380号解释理由书中明确指出,“讲学自由之规定,以保障学术自由为目的,学术自由之保障,应自大学组织及其它建制方面,加以确保,亦即为制度性之保障。为保障大学之学术自由,应承认大学自治之制度,对于研究、教学及学习等活动,担保其不受不当之干涉,使大学享有组织经营之自治权能,个人享有学术自由。”[7]在大法官林永谋、杨慧英的协同意见书中也指出,“大学自治既系源自学术自由之本质,则‘宪法’第十一条关于讲学自由之规定,在实际问题上,当系指大学讲学之自由,故就此意义言,大学自治可谓系对于学术自由之制度性保障,从而其侵害大学自治者,即为侵害‘宪法’第十一条讲学之自由;且此一制度性保障并不变更大学教师基本人权保障之意义,要属当然。‘大学法’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大学应受学术自由之保障,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享有自治权。’即系上开宪法对讲学自由即学术自由以及由此衍生之大学自治所为保障之积极的法律性宣示。”[8]
当然,对制度保障说也有不同声音。在日本,制度性保障受到严厉批判之处在于,制度性保障过分强调制度的核心内涵,反而对于不是核心内涵的制度会倾向于让法律任意更改,弱化了所想要保障的制度或基本权,另外制度性保障的概念过于模糊,有人为操作的空间。在我国台湾,有学者指出大法官引入制度性保障并没有充分的理论基础,而是面对现实的结果,因为在台湾公立大学并没有独立法人地位,无法从法人基本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只好改用制度性保障这种说理方式。[9]制度保障说并非是对等同论的修正和发展,事实上二者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制度保障说是德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应急的功利目的,不过,制度保障说相比于等同论正确界定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之间的手段和目的关系,对于学术自由的保护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是制度保障说虽遭非议但却没有被代替的主要原因。
我国虽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学术自由权,但在建构具体的权利保护制度方面却存在很多不足,使得学术自由权有沦为纸面权利的危险。特别是对大学学术自由的保护方面,没有建立一种制度性保障措施来实现学术自由,甚至没有提到大学自治,只在高等教育法中规定了办学自主权,自主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高等教育事业性质认识的一种延续,是政府在有限的范围内让渡给高等院校的一部分教育行政管理权,甚至只是国家默认的一种恩赐。所以,在人们的意识中,它是下放的而非大学应有的权利。[10]更为致命的是,这种自主权并不是出于对学术自由的保障,而是为了维护学校秩序的管理权,正是办学自主权与学术自由的这种疏离,使得自主权反而可能伤害学术自由权。比如在邹柳娟诉教育部一案中,法院认为华中科技大学未评聘邹柳娟为教授属该校行使自主权的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1]因此,在我国大学法治的建设过程中,应当借鉴制度保障说,将办学自主权视为教师和学生学术自由的保障手段,并以此为基础来配置学校权力,并将学术自由的实现作为判断办学自主权的正当性的依据。
[1]Altbach,Philip G.etc.(ed.)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n Society.Prometheus Books,1994:57,70.
[2]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郑继伟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0.
[3]湛中乐等.论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J].教育管理研究.2005,(3).
[4]邓光平.如何识读现代大学组织特性:罗伯特·伯恩鲍姆的大学组织结构观[J].复旦教育论坛,2005,(2).
[5][8]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第380号解释大法官林永谋 杨慧英协同意见书[EB/OL].法源法律网.http://fyjud.lawbank.com.tw.
[6]李建良.“制度性保障理论”探源——寻索卡尔史密特学说的大义与微言[G].吴庚大法官荣退论文集:公法学与政治理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222.
[7]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M].台北:蔚理法律出版社,1989:53.
[9]李建良.论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宪法保障[J].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8卷第1期:280-281.
[10]熊庆年.对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再认识[J].复旦教育论坛.2004,(2).
[11]评教授是高校的自主权不是具体行政行为[EB/OL].北大法意.http://www.lawyee.net.
伊 鑫/山东政法学院人事处师资职称科科长,法学理论硕士,讲师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