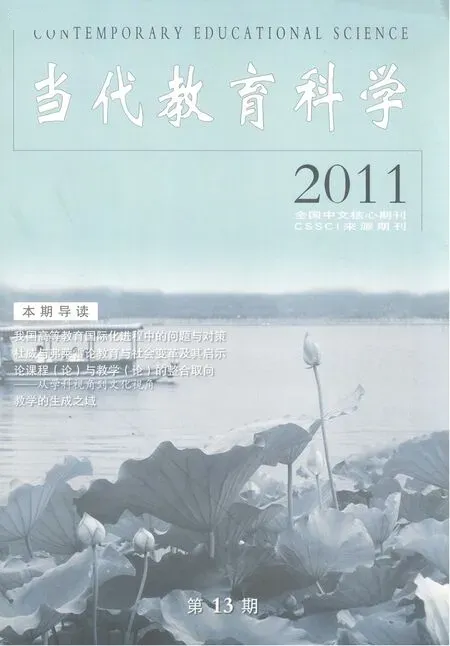教学的生成之域*
● 张雪冬
教学的生成之域*
● 张雪冬
生成的窄化会使教学走向僵化,乱生成、伪生成也会使教学走向虚化。生成之域从窄化走向延拓:是生命生成、认知生成、关系和意义生成及创造;生成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连续性与突变性的统一;生成与预设是“包络”、“调谐”关系。
生成之域;窄化;延拓;重构;关系
教学具有预设性与生成性。没有非生成的教学,也没有非预设的教学。但迄今为止,教育理论界对预设与生成的认知仅停留在含义解析、不同点介绍等方面,且诸多观点带有复制的痕迹。生成的窄化使人们难以摆脱二元对立、线性因果的思维模式来思考生成及生成与预设的深层关系,与预设的视域融合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生成的窄化会使教学走向僵化;乱生成、伪生成也会使教学走向虚化。求解生成之域,重构教学生成,建立二者应然关系,不仅有理论价值亦有实践意义。
一、教学的生成之域窄化
仅把预设之外的精彩或教师的机智处理看作生成是对教学生成之域的窄化。“预设过度必然导致对生成的忽视,挤占生成的时间和空间;生成过多也必然影响预设目标的实现以及教学计划的落实。从实践层面上,不少有价值的生成是对预设的背离、反叛、否定,还有一些则是随机偶发的神来之笔,生成和预设无论从内容、性质还是从时间、空间讲都具有反向性。[1]生成是指“在教学活动中会涌现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和问题,教师不能机械地按原计划确定的一种思路进行教学,而是应凭借自身的素质,根据学生学习的情况,把教学中人的、物的、精神的诸多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生成表现在课前,指的是教师的“空白”意识,教学活动留下拓展、发挥的时空;生成表现在课堂上,指的是师生教学活动离开或超越了原有的思路和教案;表现在结果上,指的是学生获得了非预期的发展。”[3]我们把生成的“幽灵”禁放在教学的一个角落,但又恐惧它扩占其盘踞的空间构成对预设的威胁,于是在墙角处再放置一个隔板,惶恐地盯着角落里这个不可驾驭的怪物,生怕它出来打乱整个教学的秩序。把任何对象或实体作为封闭的来理解会导致一种分类的、分析的、还原的世界观,单线式的因果性。这样一种世界观在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物理学中作出了卓越成就,但是在今天,随着认识的深入和向复杂性迈进,它到处发生搁浅。简单化的思想只想控制与主宰现实,瓦解现实的复杂性。这种简单化看问题的方式“或者是分开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或者是把多样性的东西统一化。”[4]
二、教学的生成之域延拓
教学是生成性的活动。生成性是活动的基本特征。最早使用“活动”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灵魂不是脱离有机体的实质,而是有机体的具有不同形式或水平的活动;过去人们只注意感觉——映象,这是不够的,还应研究人的感觉——活动。[5]胡塞尔认为,即使是简单的“看”,也是一个从事看的人的活动,所看到的东西涉及“动觉”,即主体有目的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联系的各种期待。马克思认为,“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生成自我的过程。人不仅在劳动中创造自己的他在,而且在劳动中改变、完善着自身。”“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6]生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又是一个突变的状态,这个突变的状态以结果的形式出现。现实中,人们可能更多地关注生成的突变——结果,而很少关注生成的渐变过程。
(一)教学是生命生成的活动
教师和学生都是生命的个体,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没有生命的生成,生命就不存在了。教学中,师生共历生命历程,体验生命的快乐与意义,注重生命的自我超越,师生个体生命在教学过程中得到了生成。
(二)教学是认知生成的活动
教学内容不可能完全是镜像式地反映在学生大脑中,它必定要与个体自身经验、经历相结合,生成新的知识。“知识的生成过程除了必然、逻辑、理性的因素,还充满着许多偶然的因素和非理性的力量。”[7]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提出的生物的主体和自组织的概念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生物的最小行动都以“自我运算”为前提,通过这个运算,个体自我中心地根据它自己来处理所有的对象和材料。主体就是这样一个进行运算的存在。进而指出“至于我们人类,具有意识、语言和文化,我们就是运算、认识的个体——主体,能够做出决定,进行选择、制定政策、享有自由、进行发明创造。”[8]赫尔巴特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就是通过经验获得材料,再通过心智活动从经验中产生观念,并不断地依靠旧的观念来同化新的观念形成观念团的“统觉”过程。这个“统觉”的过程就是生成的过程。美国心理学家威特罗克认为,学习的过程是个体不断生成意义的过程,生成是理解不可缺少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是掌握客观知识,而是生成自己的意义、理解和假设。生成不完全等于“语义加工”,也不限于将信息纳入图式中,而是对信息进行自己的建构。正因为生成是建构关系的过程,所以才带来真正的理解。[9]
(三)教学是师生交往生成关系和意义的活动
互动是交往的形式,生成是活动的特征。在互动中,教师与学生通过倾听和对话,不但生成相互尊重、理解、信任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而且还在于使置身于其中的每一个人,把经过交往活动生成的知识、经验、精神模式、人生体验等作为共享的生存资源,使每一个人不断完善自身、超越自我。然而,现实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往往带有先入为主的专制的影子,教学中充斥着假倾听、虚对话和伪生成。
(四)教学是创造性的活动
生成的核心是创造。“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味强调‘教学即知识传授’,必然敲响‘教师时代’的丧钟;反之,当教师带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充满激情地投入创造活动的时候,才可真正的宣布‘教师时代’的来临”。[10]现实教学中,教学的创造性还远未达到,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使之生成,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兰德曼说:“人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有创造性。创造性决不局限于少数人的少数活动;它作为一种必然性植根于人本身存在结构中。”[11]幼儿就有创造性的萌芽,这表现在幼儿的好奇心和创造性想象上。然而,我们的教育没有很好的培育它,甚至把它连根拔起了。我国的学生在校考试成绩不比美国学生差,但毕业后除少数人外,多数人的创新能力明显不如美国学生,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往往是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创新教育。没有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是教育的一种失职。
三、教学的生成之重构
(一)生成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生成既不是本质既定的、无创造的“流”,也不是天马行空、无任何确定性的、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变”,而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统一。“我们努力要走的是一条窄道,它介于皆导致异化的两个概念之间:一个是确定性的定律所支配的世界,它没有给新奇留有位置;另一个则是由掷骰子的上帝所支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荒诞的、非因果的、无法理喻的。”[12]就课程知识的选择过程而言,选择知识、整理知识的过程也是一种知识的生成过程。选择什么样的知识,除了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知识间的内在逻辑外,还必须考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同样的知识场域,政治立场、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和技术水平等不同,选择的知识不同。这些先验的知识最终以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但是,这种确定性并不排斥师生对它的理解和生成建构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和创造性。否则,只关注生成的确定性,遗忘了生成的不确定性,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生成虽可以掌控,但也没有了新奇和创造。这样的生成就会变成“生米变熟饭”,此种生成观只能陷入机械主义。同样,只关注生成的不确定性,遗忘了生成的确定性,“在一个没有确定性的世界,生成虽消除了限制,但也没有了历史、保证和方向。这样的生成虽然是一条永不止息的河流,但却是人无法把握的 ‘克拉底鲁之河’。此种生成观除了陷入相对主义之外,并无它途。”[13]此外,生成没有一定的确定性导向,生成也将走向乱生成。教学中,我们既要赞赏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哈姆雷特,又不要陷入塞翁失马是“公马”还是“母马”的纷争之中。
(二)生成是连续性与突变性的统一
就生成的连续性而言,生成表现为过程;就生成的突变性而言,生成表现为结果。连续性是生成的“线”, 这些“线”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保持一定的秩序和方向;突变性是生成的“节点”,这些“节点”不是连续地在空间中穿行,而是出现在空间里一系列个别的位置之上,连续地占据一定的时间,使生成具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成就是由“线”和“节点”织成的“网”,是连续性与突变性的统一。只关注生成的连续性,遗忘了生成的突变性,在一个连续性的世界,生成虽可以连绵不绝,生生不息,但也没有了源头。这样的生成只会变成无源之水,此种生成观只能陷入虚无主义;只关注生成的突变性,遗忘了生成的连续性,在一个突变性的世界,生成虽给人以惊喜,但也使人容易产生浮躁之意。此种生成观只能陷入机会主义。教学中,师生既要共同经历生命历程,也要追寻生命的价值与真谛,形成一定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学习既要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和持之以恒,也要树立远大理想、善于反馈和总结;探究既要寻找一定的方法、经历实际过程,也要生成一定的知识和形成一定的技能、追问事实的真相;师生既要对话和交流,也要达成一定的共识;教师既要重视学生的积极参与,也要反思学生是否获得了真正的收获。
四、教学的生成与预设之关系
预设把握生成的方向,生成使预设成为现实,是宏观的预设,微观的生成。
(一)二者为“包络”关系
生成是教学的一种常态。无论是在连续性的过程中,还是在突变性的结果中,生成无时无处不在。由于预设的开放性,它在把握生成的方向性时,并没有为生成指明了唯一的方向,而是预设多个有意义的方向;由于预设的非线性和动态性,教师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预设策略,能坦然面对偶发事件,灵活运用和处理,并使之朝向预设的方向生成。因此,二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二者都具有多元性。预设是对各种生成的“包络”。
(二)二者为“调谐”关系
理想的教学,生成应朝着预设的各个指向,但实际情况,生成有时会偏离预设的方向。如果生成要走向无价值,要及时调节生成的进程,使其趋向原来的方向,防止出现乱生成和伪生成;如果生成有价值,但偏离了预设的方向,教师要及时调节原来的预设,确定生成的方向,接纳教学信息,动态地修正原先设计的教学方案,及时地调整原先计划的教学环节和步骤,灵活地选择原先预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防止出现僵死的教条。通过“调谐”使二者达到“相同频率”,产生教学的“共振”。我们“远非尝试一种僵硬的统一,我们保证能够在系统的开放性和哥德尔式的缺口、经验的不肯定性和理念的不可判定性、物理的/热力学的开放性和认识的理论的开放性之间,实行一种柔性的但是不可缺少的综合。”[14]
[1]王鉴,张晓洁.试论预设性教学的内涵与特点[J].课程·教材·教法,2008,(2).
[2]李祎.生成性教学研究述评[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4).
[3]余文森.论教学中的预设与生成[J].课程·教材·教法,2007,(5).
[4][14]【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M].陈一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9.45.
[5]车文博.心理学原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20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7]潘洪建,当代知识观及其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J].教育研究,2004,(6).
[8]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1.
[9]Wittrock,M.C.Learning as a generative process[J].Educational Psychologist,1974,(11).
[10]张华.研究性教学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5.
[11][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张天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02.
[12][比]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M].湛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150.
[13]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本研究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经费资助。
张雪冬/齐鲁师范学院物理系教师,硕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责任编辑:孙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