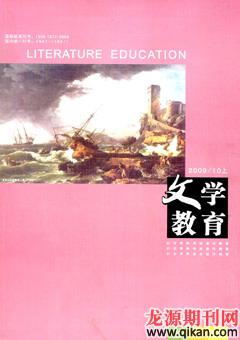论悖论中的陌生化
高晓焘
俄国形式主义是20世纪初在俄国文坛上盛行的一个文学流派,“形式主义”是它的反对者加诸其上的诬蔑性称呼。“‘形式主义这个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怍为20世纪初的第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俄国形式主义是在对传统文学观的反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不满传统的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等文学批评模式,把焦点主要投注在文学自身的语言与结构方面。在形式主义者看来,文学是一种自我指涉的人类活动,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只能依据文学内在的自身标准加以说明。“因为每一种艺术之所以有它的确定的性格,是由于它所用的是某一种确定的外在的材料,以及这种特殊材料所决定的使它得到充分实现的表现方式。”所以形式主义者坚信,艺术的形式可以由艺术自身的规律解释清楚。
在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众多观点中,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为了说明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阅读了大量的托尔斯泰作品,并在其中找到不了不少例证:在《量布人》这篇小说中,以马为叙述者,用马的眼光来看私有制和人类社会。《战争与和平》在描写战争的画面时,出其不意地将笔墨转到细节的描绘上,从而改变了平常的比例,打破了读者日常的观察定势,创作出独特的动态……那么,为什么需要陌生化呢?什克洛夫斯基在其《作为艺术的手法》里说:“如果我们对感觉的一般规律作一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动作一旦成为习惯性的就变得带有自动化了,这样,我们所有熟悉的动作都进入了无意识的、自动的领域。如果有谁回忆起他第一次手握钢笔或第一次讲外语时的感觉,并把这种感觉同他经上千次重复后所体验的感觉作比较,他便会赞同我们的意见。”
一、第一个悖论,陌生化审美效果的来源
什克洛夫斯基曾这样阐释艺术的目的:“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叫子细品昧,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隐蔽的前提:陌生化必须以习见事物和惯性体验为前提。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使石头成其为石头”,也就是强调接受者在面对任何艺术的时候,头脑都不可能是一片空白,而是既有以往艺术的印象与痕迹,又有个人的接受习惯与审美趣味,这些都在潜意识中影响着接受者的审美取舍。如霍克斯所说:“‘陌生化的程序预先要有一批‘我们熟悉的和似乎是有内容的材料的存在。如果一切文学作品在任何时候都从事于陌生化过程,那么就缺乏为我们所习知的标准或‘对照物,陌生化过程的任何特性也就因此被剥夺了。”
也就是说,陌生化在取消语言及文本经验的“前在性”的同时,一个内在的、但又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悖论呈现了出来:陌生化与“前在性”处于矛盾的共存。一方面,接受者在对文本进行感知时,脑海中不会是一片空白,而是存在着一个理解对象的“前在性”。由于“前在性”的存在,接受者对文本的感受和理解才成为可能,“前在性”是理解的前提,对经陌生化处理过的文本的感知也不能脱离“前在性”的预设。另一方面,任何陌生化的处理又都是对“前在性”的宣战和施暴,陌生化的内在本质在于消除和解构“前在性”,在于取消和打破语言及文本经验的先设。
海德格尔提出的“前见”、“先见”、“先有”等概念,认为对文本进行任何解释之前都必然有这种先人之见。伽达默尔在借鉴海德格尔的基础上提出“前理解”概念,用以表征接受者在进行理解时具有的先于当下理解的知识结构和人生经验。接受者感知结构中的前理解在接受美学那里,则体现于姚斯的“期待视野”概念中。姚斯认为接受者对文本的接受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以历史经验所积累起来的期待视野为接受的前提。无论是“前理解”,抑或是“期待视野”,都是指接受者在与文本对话时所存在的先有的思维与知识结构——为接受者所特有的前在性,它是接受者与文本展开对话的前提与基础。“前理解”否认阐释始于一个没有任何前见的纯洁状态,无论接受者自觉与否,“前在性”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与文本的对话只能由此开始,它规定了接受者的立足点以及他由此所能遭遇的一切。
陌生化以“前在性”为潜在前提,但又力求消解这种“前在性”。在这种悖论性的共存中,前在与此在的相互冲突引发出一种张力,陌生化也正是凭这种紧张关系而使接受者最大限度地体验到一种张力美,从而使审美成为可能。
二、第二个悖论,陌生化陷入消解
二十世纪中后期,世界各主要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背景下,生产中心开始向消费中心转移,物质消费向符号消费转移,原本以实用性为主的领域大量审美化,消费逻辑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感性经验,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1988年4月费瑟斯通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讲演时明确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概念,他最主要的理论依据来自于法国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认为日常生活与审美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日常生活进入审美的领域。
时至今日,美已淡化了它的形而上学的意味。它从高高的艺术殿堂走出,从传统的理论思辨和纯文艺领域急剧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形式之中。经典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也不仅仅被供奉在博物馆或珍藏于私人宅邸,它们被疯狂地复制、翻版,和各色商品一样地进入市场,被摆放在各种面向大众的书店、商场、旅馆或饭店,只要人们愿意,随时都可以买回家或肆意欣赏,具有崇高艺术规则的、有灵气的艺术,以及自命不凡的教养,都被折价转让了。
由此,所有的一切,只要通过陌生化,都可以披着“美”的外衣而受到人们礼赞。生活起居、时尚享受,乃至生活中的丑或恶,统统都汇到一个平面上,经过陌生化,抹去其棱角,成为了无处不在的“审美体验”。正如后现代理论家凯尔纳、贝斯特所阐述的那样:“美学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以至于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当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为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景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又如韦尔施所说:“普遍化的审美被体验为烦恼甚至是恐惧,审美的冷漠既而变成一种直觉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对普遍
存在的美的逃避倾向。”也就是说,经过陌生化后,什么都是美的,同样就不存在美了,持续不断的追求刺激将会导致个体审美的麻木不仁,审美化由此进入了麻痹化,难再有审美的愉悦体验。
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的市场化生产者为了能够刺激起大众的购买欲望,在包装和媚俗上下足功夫,内在的涵义则退居其次。而此时作为手段的陌生化,却抛弃了艺术那种高尚、精英的特征,仅仅是把艺术当成一种商品类型。使得“美不再是艺术‘蛋糕上的酥皮,美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在女士婀娜的线条中,就在楼盘销售的广告间,就在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中。”
此时的陌生化实际上也陷人了一个自我消解当中:一方面,在消费社会中,艺术成为商品,陌生化必然成为形式化创作的必要手段,尽其所能,把一切可以进入市场的东西改造成美的,引起消费者的惊奇并最终成功诱使其购买;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大背景下,经由陌生化改造成的美,剥去了艺术深层次的内涵。结果并不是和接受者(也可称为消费者)拉开距离,延长审美感受,相反是要融入接受者当中,尽可能地得到接受者的认可。就这样,陌生化,陷入了自己的陷阱,自己和自己的目的相背离。
三、结语
陌生化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其创新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是一切艺术创作必要遵循的原则。凭借对“前在性”和自动化的突波和颠覆,使人们从迟钝麻木中惊醒过来,重新调整心理定势,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去感受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同时陌生化的基础也在于此,它虽然强调审美接受中接受者与对象之间的张力美,但过于突破接受者的前在限定,会使接受者难于理解或不能接受,而过于遵循前在的传统,也不能引发接受者的审美注意和达到陌生化的目的。所以,陌生化无论怎样新奇,都要既在意料之外,叉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只有在悖论中,才会产生最大的审美效果。
进入消费社会后,艺术原本那些神秘、崇高和诗意的品质在高度市场化的世界里荡然无存,所有的一切都进入了艺术,传统的主体与艺术、生活与艺术的界线被打破,主体与艺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无原则地刻意模仿以及艺术与现实的相互指涉,其结果是艺术直接以现实的名义出场,艺术本身就是生活。艺术褪去其深刻的内涵,与日常生活距离消褪,被现代化的机械流线性地创造、复制。陌生化,作为一种创作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着帮凶的角色,它把高尚变成平庸,剥去艺术神圣的外衣,把艺术的美一展无疑地暴露在接受者面前,目的只有一个:消费。这也使得陌生化产生了与其自身相悖的结果:为了刺激购买欲望必须拉开与消费者的距离,使消费者感到惊奇,结果却是消解了艺术与消费者的距离。在抹去了横亘在创作者与接受者(也可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许久的屏障的同时,陌生化丧失了其特性,自己消解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