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天信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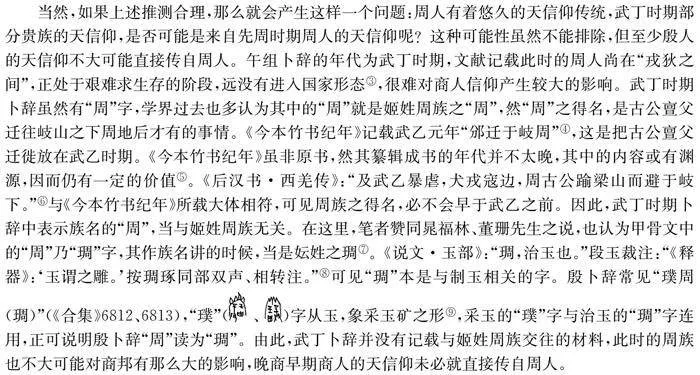
[摘 要]商人宗教观念中是否只有帝信仰,而没有天信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涉及中国天命宗教思想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天信仰是周人特色,商人仅有帝信仰。不过,非王的午组卜辞中有祭天现象,也有“天戊”等以“天”美称祖先神的情况,说明午组卜辞主人存在天信仰。到了商末,黄组卜辞中的“天邑商”并非“大邑商”,而是天建商邦的意思,是商王在此时也有天信仰的证据。大量帝乙帝辛之前的王卜辞中只有帝信仰材料,没有天信仰材料,暗示此时商王尚没有形成天信仰。因此,商人的天信仰,有一个从部分贵族的信仰,最终在商末转化为商王室信仰的变化过程。另外,汉代文献中的武乙射天故事,应该是由宋康王射天故事转变而来的,并不能成为否定商人天信仰的证据。
[关键词]殷商;天邑商;天道观;天命;武乙射天
[中图分类号]K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5)02000512
在商周宗教观念研究中,商人是否有天信仰,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学者是郭沫若先生,他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指出,商代天信仰有早晚的区分,殷末之前不存在天信仰,殷末才产生天信仰,周人的天信仰延续于殷末人而有极大的进步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青铜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332页。。文章发表之后,学术界对商人是否有天信仰争议较大,大体有肯定商人天信仰和否定商人天信仰两种不同的认识,且这两种认识都与郭老的观点有所不同。
就肯定的一方面来说,傅斯年先生在《性命古训辩正》中认为商代“自当有‘天’之一观念,以为一切上神先王之综合名”傅斯年:《性命古训辩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13页。。罗新慧先生曾提出,“殷周天命论存在关联,周人天命论中理性精神的出现,实是由商人铺垫而来……殷人的天命论特别是殷商晚期的天命思想,实是周人天命观念发展的基础”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4~18页。,也暗含商人存在天信仰的观点。陈来先生认为,“甲骨卜辞即使未发现‘天’字或未发现以‘天’为上帝的用法,至少在逻辑上,并不能终极地证明商人没有‘天’的观念或以‘天’为至上神的观念”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7页。。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也多认为商代有天信仰,且这一天信仰贯通整个商代,而没有如郭沫若先生那样将天信仰视为殷末人的思想,冯友兰、任继愈、金景芳、徐复观、葛兆光等先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4~45页。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金景芳:《金景芳先秦思想史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4~65页。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8页。徐先生也认为,周初的天和天命信仰,都属于殷文化系统,这点与郭沫若先生基本一致。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皆是如此。
不过,这肯定的一面,面临着一个较大的难题,就是殷墟甲骨文(尤其是早期甲骨文)中缺乏天信仰的材料,这一点郭沫若先生已经讲得较为明白。下文还会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此处不复赘言。
就否定的一方面来说,胡厚宣先生指出,“惟终殷之世,未见天称……称帝为天,盖自周武王时之‘大丰簋’言‘天亡尤王’始”胡厚宣:《殷代之天神崇拜》,《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陈梦家先生认为,“西周时代开始有了‘天’的观念,代替了殷人的上帝”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62页。。顾立雅先生也有同样的认识,只是认为“天”作为周部落神,早在先周时期就已存在顾立雅:《释天》,《燕京学报》1935年第18期,第59~71页。。这几人的观点,虽然有与郭老观点相同之处,但都否定天信仰是由商末殷人发明的。当代学者中,李绍连、常玉芝、晁福林、王震中等先生李绍连:《殷的“上帝”与周的“天”》,《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第9~15页;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第99~112页;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4~10页。都有专文讨论商周天命观,也都基本持天信仰为周人所创立的观点。最近,晁福林先生明确指出,甲骨文中虽有“天”字,却与神灵之天无关,商人的神灵之天是由“帝”来表示的晁福林:《说商代的“天”和“帝”》,《史学集刊》2016年3期,第130~146页。。
这否定的一面,也面临一个较大的难题。周初以天命建构自己代商合理性的时候,周人不仅对自己宣扬天命,也对殷遗民宣扬天命。在《尚书·多士》、《多方》与《逸周书·商誓》诸篇中,周公面对殷遗民,多次宣称商王自成汤受天命到纣王时因暴虐失去天命,天命才转移到了周,此即“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尚书正义》卷一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87页。。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若商人只有帝信仰,没有天信仰,不知天命,周人何以能够用天命来号召殷遗民呢此问题,何炳棣先生早已指出,参见何炳棣:《“天”与“天命”探源》,《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2页。?周人所宣称的天命观,一定是当时周人和殷遗民所共有的思想观念,否则周公的讲话就成了空中楼阁,产生不了什么实际意义。
对于上述观点及其所面临之难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目前的材料可证商人天信仰有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动过程。只有这样解释,才能在史料和逻辑之间进行调和。下面笔者将根据武丁时期的午组卜辞与殷末的黄组卜辞,详细讨论商人天信仰的变动过程。
一 午组卜辞中的天信仰
在非王的午组卜辞(或称乙种子卜辞)中,有直接祭祀“天”的材料,如:
天御量。十一月。《合集》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至1982年版。本文简称《合集》。22093
叀丘豕于天。《合集》22454
叀御牛于天。《屯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本文简称《屯南》。2241
丁酉卜:御于祖戊牛,祼于天。《村中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简称《村中南》。453
“天御量”,是指向“天”御祭于量。“叀丘豕于天”,是用“丘豕”祭祀于“天”的意思。“叀御牛于天”是御祭“牛”于“天”。“祼于天”,“”字虽不识,但整体句意较为明确,是用祼礼祭祀“天”的意思。
对于上述卜辞中的“天”,董莲池先生指出,卜辞是把“天”作为祭祀对象并将“天”奉为至上神对待的,“天”为商王室之外的民间信仰至上神董莲池:《非王卜辞中的“天”字研究——兼论商代民间尊天为至上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中国文字研究》第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上述卜辞中的“天”是祖先神“天某”的简称,并举出了“大示”可以简称为“大”的证据王蕴智:《商代甲金文中“天”字构形及用法小考》,臧克和主编:《中国文字研究》第3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喻遂生先生也有此类看法,参见喻遂生:《甲金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93页。。甲骨文中的“大示”确实偶见简称为“大”的例子(如《屯南》1115),但以“大”为名的祖先神“大某”,基本没有简称“大”的现象,因为这会导致祭祀对象不够明晰的问题。是以,用“大示”为例,否定午组卜辞存在祭祀“天”的现象,证据是不足的。而且,上述《合集》22093可以与《乙》4944缀合,缀合后为一版较为完整的卜甲刻辞蒋玉斌:《乙种子卜辞(午组卜辞)新缀十四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2期,第9~13页。,其中的“天”根本不存在是“天某”之省称的可能性,否则当会有相应完整的“天某”对贞卜辞。因此,董莲池先生将上述午组祭“天”卜辞视为商人天信仰的证据,是可信的。
除了董先生,朱凤瀚先生也早有将午组卜辞被祭祀之“天”视为受祭的上天的意思,并强调:
就现所见商代文字资料看,说天并未成为商王室宗教崇拜对象,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但在殷墟卜辞中还是可以见到“天”这一概念,并可以知道“天”已在商人的词语中具有值得尊敬、景仰的含义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第204页。。
也认为天是商代民间或部分贵族的信仰。
午组卜辞中除了直接祭祀天的材料,还有祭祀祖先神“天某”的材料,也是商人天信仰的反映。
天戊五牢。《合集》22054
己亥卜,?兺歲乇天庚子用盧豕。《合集》22077
惠豭,禦量于天庚,允田。《合集》22097
乙巳,于天癸。《合集》22094+22441
对于上述“天戊”“天庚”“天癸”中的“天”,学术界多将其读为“大”,认为是“大戊”“大庚”“大癸”的通假。不过,朱凤瀚先生在上文中同时指出,“天戊”“天庚”“天癸”等可与西周金文中的“天君”“天尹”相对比,其中的“天”是美称,而不是通假为“大”。将“天君”“天尹”视为“美称”,实际上反映出“天君”“天尹”与“天”的密切关系。古人有天降下民,天为下民设立君、师的观念,见于下列文献:
(天)乃畴方,设正,降民,监德;廼自作配,向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豳公盨,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567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简称《铭图》。。
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10页。。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注疏》卷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818页。。
古者天之始生民……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6页。。
古天氐降下民,作寺后王、君公,正之以四辅:祝、宗、史、师,乃有司正、典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九)》,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154页。。
在这种观念下,人间的统治者往往被冠以“天”的修饰语,表示他们为上天所派遣以治理人间事务的合法性和崇高性谢乃和先生指出,两周金文与《尚书》中存在诸多冠以“天”字的神性名号,参见氏著:《天帝与君王之间:商周天命授受的对象及其演变》,《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5期,第93~94页。。比如,《尚书·吕刑》称“四方司政典狱”为“天牧”《尚书正义》卷一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9页。,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再如,清华简《四告》周公称皋陶为“鲁天尹皋繇”“受命天丁辟子司慎皋繇”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十)》,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110页。,“皋繇”之称“鲁天尹”“受命天丁”,表示皋繇是上天派来的官尹。西周金文称召公为“皇天尹”(《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本文简称《集成》。27582761)、称虢仲为“天尹”(《集成》41844187),无疑也是“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观念的具体呈现。由此可知,“天”可以用来修饰人名或形容人物,表此人与上天的密切关系,此时的“天”无法通假为“大”。从两周文献来看,“天”“大”的区分较为明显,其通假之例不见于以“天”为修饰词的名词性短语。比如,除了“天尹”“天君”“天牧”,两周文献中有“天子”“天王”“天巫”等表示某种身份的例子,也有“天室”“天位”等表示特定场所的例子,这些“天”皆为“上天”意思,均无法通假为“大”。也就是说,作为专有名词,“天某”没有通假为“大某”的现象。
在上述天信仰之下,部分先王被冠以“天”的称号。比如,成汤日名大乙,《荀子·成相》《世本》《史记·殷本纪》等有“天乙”,宋公?冘3簠称(《集成》4589、4590)“有殷天乙唐孙宋公?冘3”,清华简《四告》谓之“其先王天乙”。关于大乙之称“天乙”,学术界多认为是因为“天”与“大”相通的缘故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7~428页。。不过,“天乙”之名的普遍存在表明其业已是一个专有名词,用偶然的通假说来解释专有名词并不合适。因而,笔者认为“天乙”的名号,强调的是成汤为上天所降或由上天所派遣的意思,犹如皋陶之称“天丁辟子”,显示出对成汤的尊崇之义。也就是说,“大乙”和“天乙”虽然都可以表示成汤,但二者内涵可能略有差异,“大乙”是“大示”中日名为“乙”的先王,“天乙”则是来自上天的日名为“乙”的先王。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自然可以将午组卜辞中的“天戊”“天庚”“天癸”三名理解为如“天乙”一样的称号。尤其是考虑到午组卜辞本来就有直接祭祀天的材料,将“天戊”等三名视为午组卜辞对“天戊”三位祖先(很可能是商先王)的敬称、美称,就更为合适。
通过对午组卜辞的分析可知,商代子姓贵族确实有信仰天的实证材料,朱凤瀚、董莲池等学者所提出的商代部分贵族有天信仰的观点是可信的。这里不使用董先生“民间信仰”之说,是因为目前的材料仅能看到“天”是部分贵族所拥有的信仰。
二 “天邑商”内涵分析
不过,天信仰是否仅见于部分非王的贵族,而在王卜辞中毫无踪迹?似乎也不是这样的,至少殷末王卜辞中已有相关线索。
王卜辞中有“天邑商”一词,也有“大邑商”一词,它们分别见于下列卜辞:
1.辛卯…方于…余其戋…[受]余祐。不翦…天邑商。亡害…
《合集》36535【黄组】
2.甲午卜,贞:在天邑商皿宫衣,兹夕亡忧,宁。
乙丑卜,贞:在天邑商公宫衣,兹夕亡忧,宁。在九月。
《缀集》256蔡哲茂:《甲骨缀合集》,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413页。【黄组】
3.壬戌卜,贞:在天邑商公宫衣,兹夕忧,宁。
辛卯卜,贞:在天邑商公宫衣,兹夕亡忧,宁。
辛酉卜,贞:在天邑商公宫衣,兹夕亡忧,宁。
□卯卜,贞:在[天]邑商公宫[衣],[兹]夕亡忧,宁。
《英藏》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文简称《英藏》。2529+《合集》36541【黄组】
4.癸巳卜,贞:在黄林…天邑商公宫,衣…
壬午卜,贞:在天邑商皿宫,衣,兹夕亡忧,宁。
《合补》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甲骨文合集补编》,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本文简称《合补》。11248【黄组】
5.…贞:巫九,作余酒朕…戋人方。上下于示受余祐…于大邑商,亡害在忧。
《合集》36507【黄组】
6.丁卯王卜,贞:巫九,余其比多田于多伯,正盂方伯炎。惠衣,翌日步,亡尤。自上下于示余受有祐,不翦,忧。告于兹大邑商,亡害在忧。[王占曰]:“引吉。”在十月。遘大丁翌。《合集》36511【黄组】
7.甲午王卜,贞:作余酒朕酉,余步,比侯喜,征人方。上下、示受余有祐。不翦,忧。告于大邑商,[亡害]在忧。王占曰:“吉。”在九月。遘上甲,唯十祀。《合集》364821【黄组】
8.己酉王卜,贞:余征三封[方],惠令邑,弗悔,不亡□□,在大邑商。王占曰:“大吉。”在九月。遘上甲□五牛。
惠令。《合集》36530【黄组】
另外,“天邑商”“大邑商”还见于西周早期文献,如《尚书·多士》:“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尚书正义》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8页。何尊(《集成》6014):“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这说明,“天邑商”“大邑商”名号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仅商人这样自称,周人也承认了这一名号。
对于上述材料中“天邑商”与“大邑商”的关系,学术争议较大。一种观点认为,“天邑商”就是“大邑商”。这一观点最早见于罗振玉先生,他认为《尚书·多士》中的“天邑商”是“大邑商”之讹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3页。。于省吾先生则认为卜辞中的“大邑商”“天邑商”互见,“天邑商”非“大邑商”之讹,而是“天”与“大”相通的结果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5页。。郭沫若先生也持此观点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青铜时代》,第321页。。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天邑商”与“大邑商”非指一地,内涵有异。董作宾先生就明确指出,“大邑商”在商丘,“天邑商”为商王驻跸处行宫之名董作宾:《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二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年版,第600页。。陈梦家先生则认为“天邑商”指朝歌,“大邑商”指沁阳田猎区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57页。。既然二者不是一地,自然也就谈不上“天”与“大”通假的问题。
就上举《尚书·多士》与何尊而言,周人认为“天邑商”“大邑商”皆指商邦,与文献中的“大邦殷”相同。在甲骨文中,“天邑商”与“大邑商”出现的语境虽然各有偏重,但皆用于地名,暗示“天邑商”“大邑商”所指相同。因此,说“天邑商”就是“大邑商”,大致不会有错。
“天邑商”“大邑商”都可指商邦,为何商邦要用“天邑商”“大邑商”两个词汇表达呢?学术界虽然多用“天”“大”相通来解释这一问题,但“天”“大”相通是有前提的。在王卜辞中,“天”的主要用法有二:一,《说文》“天,颠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因此“天”可用为“颠”,《合集》20975“弗疾朕天(颠)”就是此例;二,《庄子·德充符》“独成其天”,《释文》“崔本作‘大’”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27页。,因此“天”可用为“大”,《合集》32834“尸方天(大)其”即为此确例。后一种“天”“大”相通的情况仅此一例,王卜辞不见明确的“大+日名”“大示”等通假为“天+日名”“天示”的例子。这说明王卜辞中的“天”“大”相通,乃为特例。《甲骨文字诂林》对此已略有提及于省吾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13页。。但是,在王卜辞中,“天邑商”是普遍存在的,其出现的次数与“大邑商”基本相当,“天邑商”明显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这就与王卜辞中“天”与“大”相通的特例原则相悖。因此,从“天邑商”出现的频率来说,用通假为“大”来解释其中的“天”,似有将特例普遍化的嫌疑。
既然不能用“天”“大”相通来解释“天邑商”,那么,我们只能从其他角度认识“天邑商”。《尚书·多士》“天邑商”一句,孔颖达疏:“郑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肃云:言商今为我之天邑。”《尚书正义》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8页。郑玄、王肃是将“天邑”等同于“天之邑”,“天邑商”有商邦为天所建之义。上引罗振玉先生之说认为郑玄之说不足为据,实则郑玄、王肃之说是有根据的。《墨子·法仪》:“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⑧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第29、219页。《非攻》:“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⑧墨子认为,天下万邦皆是“天之邑”;天下万民皆是“天之臣”。《墨子》虽然是东周文献,然此观点却有可与之对应的早期文献。上举清华简《厚父》:“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时下民,共帝之子,咸天之臣。”明确指出“下民”由天所降,“万邦”由天所设,其中“咸天之臣”与《墨子》“皆天之臣”一致,反映出二者的思想关联性。既然下民可称“帝之子”“天之臣”,那么同样由天所作的“邦”,自然可以称为“天邑”,这与《墨子》“天之邑”之说又一脉相承。学界一般认为《厚父》是西周时期的文献,其“天设万邦”的观念,可与《诗经·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毛诗正义》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19页。、豳公盨“(天)乃畴方”等西周文献相互印证,证明西周时期的人们认为邦国为上天所建。另外,《逸周书·度邑》中有周武王“定天保,依天室”章宁疏证,晁福林审定:《〈逸周书〉疏证》,西安:三秦出版社2023年版,第292页。之愿,其中的“保”可训为小城(“保”即“堡”字),“天保”就是“天”之“堡”的意思,也属于“天邑”范畴。由此说来,《墨子》“天之邑”之说适用于西周时期。郑玄、王肃之注取此“天邑”之义,渊源有自,可以信从。
仅就《尚书·多士》所称“天邑商”而言,周人应该也是从天命角度对其加以理解的。《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尚书正义》卷一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50页。这里的“大国殷”“大邦殷”与“天邑商”“大邑商”等同,皆指商邦。周人认为,“大国殷”本为“皇天上帝”的“元子”,直到商纣王时,这一“元子”身份才被终结。既然商邦本是天帝“元子”,那么“元子”被称为“天邑商”,自然强调的是其承受天命、由天所设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逸周书·度邑》讲商的早期历史时提到“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章宁疏证,晁福林审定:《〈逸周书〉疏证》,第290页。,意思是上天建立殷邦时,聚集了三百六十夫的“天民”,由他们建立殷邦。商邦之民可称“天民”,则商邦之邑自然可称为“天邑”。这都可以证明郑玄、王肃之注是可信的。
就商族而言,也有证据证明商人及其遗民视商邦为天所建立之邦。《诗经·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③ 《毛诗正义》卷二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0、1343页。这是商的后裔追溯商人起源的诗歌,商遗民认为商邦由上帝所生。不过,《商颂》时期的殷遗民并不区分帝和天,所以《长发》中同时出现“帝”和“天”,并称殷王为“天子”。因此“帝立子生商”也是上天建立商邦的意思。《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③也是说商邦由上天所降。这两首诗歌,皆能证明殷遗民认为商邦为上天所建之邦。这一思想自然不可能是殷遗民在周代才形成的思想,而应该是渊源有自。这一渊源目前只能追溯到商末的“天邑商”卜辞。
《尚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尚书正义》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56~357页。商人迁徙其邦、建设“新邑”,是在“天命”指引下进行的,与“天设万邦”“天之邑”等观念一致。学界多认为《盘庚》为商代文献,文中的天信仰为后世所改。假使此观点可信,那文中的观念若非盘庚时期的天信仰,也可能是盘庚以后商人的天信仰。值得注意的是,“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的“新邑”是盘庚所迁之都,参考《古本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二’之误)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当指以殷墟为核心的“天邑商”。也就是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是上天命令我商人永远住在新邑“天邑商”的意思。从《盘庚》文本来说,作为“新邑”的“天邑商”乃由“天”所“命”,与“天邑商”的字面意思完全相符。这一文本上的关联暗示《盘庚》篇中天信仰的时代可能是商末(“天邑商”卜辞所在时期),而不必晚至周代。
上举《厚父》“天设万邦”之说,乃厚父所追溯的“古”时发生之事,意味着“天设万邦”观念的产生还远在西周之前。“天邑商”仅见甲骨黄组卜辞,黄组卜辞的年代在殷末,距离周初不远,自然属于《厚父》所说的“古”时。因此,将黄组卜辞中的“天邑商”也理解为天所建之邑的意思,是有文献基础的。“天邑商”虽与“大邑商”所指相同,但二者来源仍略有差异:“天邑商”强调的是商邦为上天所设、受“天命”,“大邑商”则强调商邦为大邦、大邑刘家和先生曾谓:“当殷还是大邦或天邑的时候,它不仅在量上为大,而且在质上为‘天’,即‘天命’所在之邑或邦。”(氏著:《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愚庵论史:刘家和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也认为“天邑商”中的“天”是上天或天命之义。。可见,“天邑商”与“大邑商”有着不同的名号渊源。
与天邑商、大邑商之关系类似的一组词汇是天命、大命。在西周文献中,“天命”与“大命”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当“大命”的发布者为天、帝的时候,“大命”在本质上指的就是“天命”。比如,《尚书·康诰》的“天乃大命文王”B11 《尚书正义》卷一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1、436页。、《尚书·君奭》的“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⑨ 《尚书正义》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7、469页。、大盂鼎(《集成》2837)的“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其中的“大命”都是“天命”。不过,并非所有“大命”都可以理解为“天命”,“大命”还可以表示天子之命。比如,《尚书·多士》的“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⑨、《尚书·多方》的“我惟大降尔命,尔罔不知……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尚书正义》卷一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85~488页。,这里的“大降命”就是“大命”,指的都是天子之命,而非上天之命。《尚书·酒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B11这里的“大命”专指周天子所传达的关于戒酒之命,也是文后“乃穆考文王”针对“无彝酒”而发表的讲话,“大命”乃周王之命。就“大命”与“天命”内涵的差异而言,二者无疑是有不同来源的:“天命”指上天之命,“大命”指宏大之命。既然“大命”与“天命”来源不同,我们自然不能用“天”“大”相通而将“天命”读为“大命”。天邑商、大邑商之关系,正可由天命、大命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佐证。
三 商人的天信仰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知,商人的宗教观念中确实存在天信仰,且不仅存在于非王的子姓贵族之中,也存在于商王室之中。不过,这里仍需要解释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商人有天信仰,何以王卜辞中不见其他天信仰线索,更不见祭祀天的材料?这一问题涉及到商代天信仰的演变。
午组卜辞的年代为武丁时期黄天树:《午组卜辞研究》,《黄天树古文字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此时的王卜辞有大量与“帝”有关的内容,我们在此时的王卜辞中只能看到“帝”的命令,而看不到“天”发号施令。由于卜辞是贞卜祭祀的产物,若此时商王室存在天信仰,不大可能不反映在卜辞之中。这一现象说明,武丁时期的商王室确实可能不存在天信仰,天信仰仅是部分贵族的观念。
黄组卜辞是王卜辞中年代最晚的一类,其主体部分是帝乙、帝辛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殷末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289页;徐明波、彭裕商:《殷墟黄组卜辞断代研究》,《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3~15页。。此一时期,相距午组卜辞的年代已经相当久远。在这一较长的时间段中,商王室很可能逐渐吸收了商的部分贵族的信仰,或吸收了商末其他族群的信仰,而将天信仰融合到王室信仰体系中,进而产生了“天邑商”的称谓。关于殷末的天信仰,《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一句是学界常常征引的史料,此篇还记载商大臣祖伊称商王为“天子”,又谓“天既讫我殷命”“天弃我”“不虞天性”“天曷不降威”等《尚书正义》卷一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74~375页。,却不见“帝”字。其中的“天”不大可能都是“帝”之讹。这不仅可以证明殷末商人信仰天神,而且还能证明这一信仰也存在于商王室。
当然,殷末的黄组卜辞中除了“天邑商”外,也不见其他天信仰材料,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则,黄组卜辞有自己的祭祀特征,其中不仅不见天信仰,甚至也罕见帝信仰。黄组卜辞中的“帝”多为表示先王的“文武帝”,而非表示上帝之“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期待黄组卜辞中会出现直接与“天”有关的其他线索,这是黄组卜辞不同于早期卜辞(尤其是宾组卜辞)的地方。因此,黄组卜辞中不出现“天邑商”之外的天信仰材料,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本文一开始提及周初周人对殷遗民宣讲天命转移的合理性,其背景自然是周人业已知道了殷人有此信仰。那么,周人是否仅是在灭商后才知道殷人有天信仰的呢?就目前的材料来看,周人很可能在先周时期已经知道商人有天信仰,这一点可以从周原甲骨中的祭祀卜辞材料来探寻。周原甲骨中有四条较为重要的祭祀材料:
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祭成唐,禦二女。其彝血三、豕三。甶有正。(H11∶1)
……[在]文武……王其帝……天□典周方伯□□甶正,亡左……王受有祐。(H11∶82)
贞:王其?桙1祐大甲,周方伯□甶正,不左。王受有祐。(H11∶84)
彝文武丁必,贞:王翌日乙酉,其爯中……[文]武丁豐……卯……左王……(H11∶112)
这四条先周时期卜辞中既出现了“王”,也出现了“周方伯”,且有文武帝乙、成唐、大甲、文武丁等殷先王名号,因此学界对卜辞的族属多有争议,或认为是周人卜辞,或认为是商人卜辞曹玮:《周原甲骨文》“前言”,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本文所引用周原甲骨卜辞,也出自此书。。笔者认为,无论是周人卜辞,还是商人卜辞,其中被祭祀的对象都是商人神灵,且为先周时期的周人所熟知,则是无疑的。从这一原则出发,H11∶82中作为被祭祀对象的“天”周原甲骨文中的“天”往往是被祭祀对象,如H11∶96“□告于天,甶亡咎”,因此H11∶82卜辞虽然残破,但其中的“天”是天神,则是学界的共识。,只能被理解为商人之“天”,最多这一“天”也为周人所共享。这一方面提供了“天”在殷末已经成为商人信仰神的一个重要线索,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殷末周人业已知道了商人的这一信仰。
总之,商人天信仰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最初是部分贵族的信仰,殷末则发展为商王室的信仰。当然,如果天信仰最初仅是商的部分贵族的信仰,而非商人主流的信仰,那么这一信仰不大可能是商族原初的信仰,而更可能是商族在发展过程中由部分贵族所吸收的外族信仰。众所周知,商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依靠武力征服周边的部族、国家,进而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武丁时期甲骨文中商与周边邦国、部族的战争十分频繁,就是这一进取势头的真实写照。即使到了商末,商人依旧持续向东部地区扩张,帝辛就发动了大规模征伐夷方的战争。在这种长期的军事扩张过程中,商族与其他族群必然有各种层面的文化交流,也必然有相互的影响,这其中自然不排除宗教信仰方面的影响。伊藤道治先生指出,甲骨文中不少自然神本来有其信奉的部族集团,随着这些部族被商人征服,其自然神也会被纳入到商人的信仰体系中,成为被商人祭祀的对象伊藤道治著,江蓝生译:《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49页。。这种因为族群融合而导致神灵信仰体系融合的现象在早期中国极为常见,而且并不局限于自然神,较为明显的例子还有皋陶原本来自东夷族,却被纳入华夏族的信仰体系之中王震中:《夷夏互化融合说》,《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51页。。午组卜辞中的天信仰,不排除就是此时或之前殷人部分贵族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受到了某些信奉天的族群的影响而接受了他们的部分信仰,进而有了信仰天、祭祀天的行为。只是这一信仰在此时尚没有达到影响王室、成为主流信仰的程度。
当然,如果上述推测合理,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周人有着悠久的天信仰传统,武丁时期部分贵族的天信仰,是否可能是来自先周时期周人的天信仰呢?这种可能性虽然不能排除,但至少殷人的天信仰不大可能直接传自周人。午组卜辞的年代为武丁时期,文献记载此时的周人尚在“戎狄之间”,正处于艰难求生存的阶段,远没有进入国家形态周自古公亶父时始称“王”,如古公亶父父子之太王、王季名号,暗示周进入国家始于古公亶父时。《逸周书·世俘》谓武王克商后:“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章宁疏证,晁福林审定:《〈逸周书〉疏证》,第258页)《尚书·无逸》:“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尚书正义》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2页)皆将古公亶父视为周族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很难对商人信仰产生较大的影响。武丁时期卜辞虽然有“周”字,学界过去也多认为其中的“周”就是姬姓周族之“周”,然“周”之得名,是古公亶父迁往岐山之下周地后才有的事情。《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元年“邠迁于岐周”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这是把古公亶父迁徙放在武乙时期。《今本竹书纪年》虽非原书,然其纂辑成书的年代并不太晚,其中的内容或有渊源,因而仍有一定的价值张富祥:《今本〈竹书纪年〉纂辑考》,《文史哲》2007年第2期,第22~46页。。《后汉书·西羌传》:“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70页。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载大体相符,可见周族之得名,必不会早于武乙之前。因此,武丁时期卜辞中表示族名的“周”,当与姬姓周族无关。在这里,笔者赞同晁福林、董珊先生之说,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周”乃“琱”字,其作族名讲的时候,当是妘姓之琱晁福林:《从甲骨卜辞看姬周族的国号及其相关诸问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2~219页;董珊:《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7期,第48~63页。。《说文·玉部》:“琱,治玉也。”段玉裁注:“《释器》:‘玉谓之雕。’按琱琢同部双声、相转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15页。可见“琱”本是与制玉相关的字。殷卜辞常见“璞周(琱)”(《合集》6812、6813),“璞”( 、 )字从玉,象采玉矿之形唐兰:《殷虚文字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0~74页;林沄:《究竟是“翦伐”还是“擈伐”》,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编:《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5~118页。,采玉的“璞”字与治玉的“琱”字连用,正可说明殷卜辞“周”读为“琱”。由此,武丁卜辞并没有记载与姬姓周族交往的材料,此时的周族也不大可能对商邦有那么大的影响,晚商早期商人的天信仰未必就直接传自周人。
午组卜辞中的天信仰虽然不大可能直接来自周人,但此天信仰又与周初周人的天信仰关系密切,这也是不能不注意的地方。王卜辞中极为罕见祭祀“帝”的情形,然午组卜辞中的“天”是作为被祭祀对象出现的,这可能是不同身份人群祭祀习惯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天、帝信仰最初有差异导致的。有趣的是,周人也有直接祭祀“天”的材料。《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克商后:“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绥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章宁疏证,晁福林审定:《〈逸周书〉疏证》,第269~270页。这是周武王用牛祭祀天的明证,时在周初。上举《屯南》2241贞卜用进贡的牛御祭于天,正与《世俘》用牛祭祀天的记载一致。
周人祭天之礼又称郊祭,所谓“郊祀后稷以配天”,周初《尚书·召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逸周书·作洛》“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皆其谓也张鹤泉:《周代郊天之祭初探》,《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第8~15页。。周初德方鼎(《集成》2661):“唯三月,王才成周,珷祼自。”“”,旧释多认为是镐京之镐,但唐兰先生认为是蒿字,在铭文中假借为郊字,表示郊祭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李学勤先生也有此观点李学勤:《释“郊”》,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36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10页。。“祼自郊”暗示周人曾在郊举行过祼礼。由于郊祭乃祭天之礼,故祼礼的对象应该是“天”。同样是周初的何尊(《集成》6014)有铭:“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爯武王礼祼自天。”直接证明周初可以祼祭上天。上举《村中南》453“祼(侑?)于天”,又证明祼祭天乃午组卜辞天信仰旧俗,此为周初周人祭天礼中又一处与午组卜辞天信仰相近的例子。
产生这种相似性的原因目前尚不甚清楚,可能是因为商人(主要是商的部分贵族)天信仰对周人天信仰施加影响而产生的,但也可能是因为晚商时期存在一个由多个部族、国家所接受的大体相似的天信仰体系。后一种可能性暗示天信仰早在晚商时期,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信仰体系。目前限于材料不足,我们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四 武乙射天故事的形成
上述午组卜辞祭天材料及黄组卜辞“天邑商”材料,皆可证明商人存在天信仰。不过,汉代文献有武乙射天的传说,学者常据此否定商代存在天信仰。因此,本文需要详细辨析这一传说的形成过程。武乙射天故事详见于《史记·殷本纪》: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司马迁:《史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4页。。
《殷本纪》记载的武乙之事,主要有三件:其一,制作偶人,称之为天神,与之搏斗而胜之;其二,制作盛血的革囊(用皮革做的袋子),用箭射囊,称之为“射天”;其三,在河渭之间狩猎,被雷震死。这三件事情中,前两件皆为武乙无道、侮辱天神的罪证,第三件事则是天对武乙的惩罚。《史记·封禅书》对武乙事迹的总结为“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司马迁:《史记》卷二八,第1633页。,即是依据上述三事。《汉书·郊祀志》:“后五世,帝乙嫚神而震死。后三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班固:《汉书》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93页。这里的“帝乙”,明显是“武乙”之误。王充《论衡·感类篇》:“纣父帝乙,射天殴地,游泾、渭之间,雷电击而杀之。”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935页。这更是把武乙和纣父帝乙搞混淆了,把本属于武乙的事情安到了帝乙的身上。
在汉代,武乙慢神射天是一个较为流行的故事。不少学者认为武乙射天为真实存在的史实,并将其放在殷周革命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此故事的历史寓意杨光熙:《殷武乙、宋康王“射天”解》,《古籍研究》2002年第4期,第10~12页;李小光:《商代人神关系论略》,《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2~117页;樊荣:《试析殷商武乙“射天”的涵义》,《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96~98页;陈立柱:《“敬天”与“射天”:上古夏、夷族群融合之殇》,《史学月刊》2020年第4期,第5~21页。。比如,王晖先生认为盛血革囊是取象周人所祭祀的黄帝的神主形象,武乙射天正好反映了商周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对立王晖:《周代天神形象与黄帝部落图腾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38~42页。。晁福林先生也是从厌胜的角度来理解武乙射天内涵的晁福林:《作册般鼋与商代厌胜》,《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第48~54页。。这种将武乙射天与商周族群冲突相关联的观点,在历史背景与文本线索两个层面,都很难得到支持。
在历史背景层面,武乙时期的商人与周人有着较为友好的关系。《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又谓:“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⑥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第25、26页。《后汉书·西羌传》:“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范晔:《后汉书》卷八七,第2870页。季历伐西落鬼戎之事,或即周人伐鬼方之事。《易·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周易正义》卷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1页。徐中舒先生谓:“此虽不著何人伐鬼方,但下文云‘有赏于大国’,大国则指殷人言……此谓周伐鬼方而殷人赏之。”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二重证据与文明探源:徐中舒先秦史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96页。其说可从。《诗经·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毛诗正义》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090~1091页。嫁给季历的太任来自“殷商”,当是殷商属臣之女。季历不仅朝见武乙,为商人讨伐鬼方,又迎娶了来自“殷商”的太任,足见此时殷周关系之友好。直到文丁初年,殷、周关系也依旧良好,《古本竹书纪年》谓文丁四年“周王季命为殷牧师”⑥。在这一友好关系下,很难产生武乙通过“射天”的形式意图消灭周人的史实。有学者试图将“武乙射天”与清华简《程窹》“攻于商神”相类比,认为两者都是上古时期的厌胜巫术李凯:《说清华简〈程窹〉“攻于商神”》,《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68~171页。。然而,周人“攻于商神”是为了代商而为天下共主,是为了打败商邦,但武乙时期的商人却是需要周邦的,武乙不可能做出以毁灭周人神灵为目的的“射天”行为。因此,从历史背景来看,“武乙射天”之事不可信。
在文本层面,文献中除了“武乙射天”外,还有宋康王射天、桀纣射天,“武乙射天”并非年代最早的“射天”故事。在这三组射天故事里,最早产生的是宋康王射天,相关史料有:
宋王筑为蘖帝,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胄从下,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以加矣。”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33页。
(宋康王)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曰威服天下鬼神刘向:《战国策》卷三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7页。。
今宋王射天笞埊(地),铸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弹其鼻,此天下之无道不义刘向:《战国策》卷三〇,第1114页。。
上述三个文献记载宋康王在慢神方面同样有射天的恶行,其目的是“威服天下鬼神”。这一射天事迹还被记载于《史记·宋微子世家》《新书》等西汉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战国策·燕二》除了记载宋康王“射天笞地”,还有“铸诸侯之象”而辱之的事迹。同书记载秦王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即为“铸诸侯之象”之说明。可见,宋康王除了射天,还制作过辱人的“木人”。在射天与制作木人两个方面,宋康王故事与武乙故事非常相似,不免令人怀疑二者的关系。崔适怀疑二者“疑是一事,传者误分为二事”崔适:《史记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页。。丁山先生甚至认为,武乙射天之事本之宋康王射天,而宋康王射天则是由其射秦王木人演绎而成的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2页。。从年代上看,宋康王射天故事发生在战国末年,记载此故事的《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也是战国末年的文献,故事发生时间与记载故事的年代接近;从地域上看,宋康王射天故事在战国末年已经较为流行,因此才能在大体相同的时间段内,被著录于上述《吕氏春秋》《战国策·宋卫》、《战国策·燕二》等不同地域和不同来源的文献之中。这两方面的事实说明,这一故事不大可能是战国末年的人们凭空编造的,而是有着一定的事实依据,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何以这一故事在宋康王去世不久就能在当时广泛流传。因此,本文认同丁山先生的观点,也认为《吕氏春秋》等书所载宋康王射天故事,是一系列射天故事的祖本。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武乙射天之事更加原初,另外两个版本的产生是其文本移置和派生的结果顾颉刚:《宋王偃的绍述先德》,《古史辨》第2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殷湛:《试论“射天”记载及其意识图景》,《运城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46~51页。。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除了《史记》之外,我们不能从更早的文献中发现任何武乙射天的线索。《今本竹书纪年》仅记载武乙“畋于河、渭,暴雷震死”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第72页。,不见射天之事,其他战国文献也没有相关记载。如果武乙真的有“射天”的暴行,信仰天神的周人又怎么可能忘记武乙这一罪证,而不拿出来作为伐商的重要根据?相反,我们看周初的文献,周人认为“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尚书正义》卷一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9页。、“(成汤)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尚书正义》卷一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86页。、“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尚书正义》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7页。,高度赞扬了包括武乙在内的殷先王的功绩和德行,其中根本看不出“武乙射天”的任何迹象。因此,从文本线索来看,认为武乙射天之事更加原初的观点,找不到汉代之前的文献依据。
这里需要对桀纣射天故事作一简单分析,以进一步说明武乙射天故事的不可信。桀纣射天的故事见《史记·龟策列传》:
桀纣为暴强也,固以为常。桀为瓦室,纣为象郎……杀人六畜,以韦为囊。囊盛其血,与人县而射之,与天帝争强司马迁:《史记》卷六八,第3930页。。
同书又谓“桀纣之时,与天争功,拥遏鬼神,使不得通”,正可与“与天帝争强”对读。晚期文献中的天、帝常区分不明显,天、帝、天帝具有同一性。由“与天帝争强”一句来看,《史记》所谓“射天”并非仅是与“天”争胜,其中的“天”也包含了“帝”。上举《吕氏春秋》“宋王筑为蘖帝”“今王胜天”等句,一为“帝”,一为“天”,也反映出战国秦汉时期的人们,认为“射天”等同于“射帝”。若认为殷人及殷遗民的“射天”有厌胜周人天信仰的内涵,那么《史记》“与天帝争强”、《吕氏春秋》“宋王筑为蘖帝”,岂非是殷人及殷遗民厌胜自己的帝信仰?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桀纣射天,与天争功,当演变自周初以降的殷末不敬鬼神的观念。《逸周书·商誓》的“今在商纣,昏忧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章宁疏证,晁福林审定:《〈逸周书〉疏证》,第278页。、《尚书·微子》的“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尚书正义》卷一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76页。、《尚书·牧誓》的“昬弃厥肆祀弗荅”《尚书正义》卷一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89页。,证明周人在伐商过程中,认为纣王的不敬上帝鬼神是其罪证之一,并据此建立伐商的合理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一观念依旧存在,如清华简《系年》的“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36页。。这一不敬上帝鬼神的观念,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诟天侮鬼”,如《墨子》所载“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第30页。。到这一步,“诟天侮鬼”也只是模糊的指责,尚没有落在实处,人们难免疑惑这一指责所对应的事实。到了战国末年,由于宋康王射天故事的流行,“诟天”就有了非常好的参考系,“射天”自然很容易被拿来作为“诟天”的具体证据。可见,桀纣射天故事,有一个从不敬上帝鬼神,到“诟天侮鬼”,再到“射天”的演变过程。
桀纣射天尚且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又怎么能确定武乙射天就是晚商的史实?这又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武乙射天的不可信。总之,武乙射天故事与桀纣射天故事皆为战国末到西汉时期比附而成的事迹,它们自然就不可以被拿来作为否定商人天信仰的依据。
综上所述,天信仰是早期中国宗教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它可能并非周人所独创,而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为商周二族所共享的信仰。只是这一天信仰,在商代有一个从部分贵族的信仰,逐渐发展为商王室信仰的过程。在商末的帝乙帝辛时期,卜辞中的“天邑商”就是商王业已接受天信仰的直接证据。“天邑商”虽然与“大邑商”所指相同,然其来源非为“大邑商”之通假,而是强调商邦为天所建立的内涵。
从西周文献来看,天信仰还有更为悠久的渊源。周初诸诰在追溯周之前历史时,往往强调最初接受“天命”的邦国为夏邦,夏人不能保有“天命”,“天命”才转移到了商人那里。上引清华简《厚父》为夏遗民文献,也多次提到了夏人的天命。西周中期豳公盨有铭:“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更是把“天命”与大禹平水土之事联系起来。由这些材料可知,至少西周时期的人们认为,“天命”的宗教观念在夏代就已经存在了,且以禹平水土为起点。如果这一认识不仅仅是西周时期人们的臆测,而是有真实的历史依据,那么,天信仰的历史自然就要远早于商代。由此,天信仰发展到晚商时期,其为较多族群所信仰而演变为相对普遍的“一统”信仰,就是一件能够讲得通的事情了。
Research on the Heavenly Belief of the Shang People
Wang Qi
Abstract:In the religious beliefs of the Shang people,whether there is only a belief in god and no belief in heaven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question.It concerns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heaven in the subsequent thousands of years.The academic community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the belief in heaven i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Zhou people,while the Shang people only believes in god.However,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worshiping the heaven in the Wu group divination,as well as situations in which Tianwu (天戊) and other deities refer to “heaven” as ancestral gods,indicating that the owner of the Wu group divination has a belief in heaven.By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the term “Tian-yi-shang”(天邑商)in the Huang group divination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Da-yi-shang”(大邑商),but rather as the meaning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ng dynasty is preordained by heaven,which is evidence that the king of Shang also has a belief in heaven at this time.A large number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efore Di Yi(帝乙) and Di Xin(帝辛)only contain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belief in god,without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belief in heaven,implying that the king of Shang has not yet formed a belief in heaven at this time.Therefore,the belief in heaven among the Shang people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belief of some nobles to the belief of the royal family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In addition,the story of Wu Yi(武乙)shooting the heaven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Han dynasty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the story of Song Kangwang(宋康王)shooting the heaven,and cannot be used as evidence to deny the Shang people’s belief in heaven.
Keywords:Shang Dynasty;Tian-yi-shang;Concept of Destiny;Mandate of Heaven;Wu Yi Shooting the Heaven
【责任编校 徐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