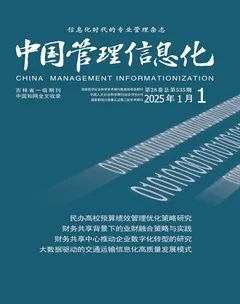融情于理:非正式制度在城市老旧社区环境治理中何以可为
[摘 要]城市老旧社区充斥着大量复杂的问题与矛盾,其治理常出现正式制度失能难为,而非正式制度因柔性为群众所接纳的现象。本文以北京大兴G社区拉家常议事会为例,探究非正式制度在城市老旧社区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正式制度通过对关键群体的情感动员赢得初步支持、通过积极回应民情诉求从而将不支持的民众转化为支持力量、通过利益与责任等社区共同体意识感化联结更多民众成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庞大力量,从而实现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社区治理;老旧社区;拉家常议事会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25.01.053
[中图分类号]D630;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25)01-0186-04
1" " "问题的提出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层单元和微观场域,亦是环境问题的聚合末梢。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社区尤其是老旧社区在升级改造中面临着复杂的环境整治难题。作为公共产品,社区环境的供给和维护离不开每一位居民的参与,其治理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民众生活质量。具有官方权威性与实施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和经由民俗习惯与情感基础等形成的非正式制度都是我国在环境治理中推进某项政策落地并要求民众配合支持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实践中,时常出现刚性的正式制度在社区环境治理场景下作用式微,而非正式制度却能有效动员居民并柔性可为的现象。本研究以作为全国基层治理典型模式的北京市大兴区G社区拉家常议事会为例,探究非正式制度在城市老旧社区环境治理中何以可为的作用机制,创新从“情”“理”融合角度分析如何更好地将柔性的非正式制度用于社区治理的经验启示。
2" " "文献综述
作为制度的基本构成,非正式制度是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核心议题,具有丰富的概念内涵。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延伸阐释或修正,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准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1],通过塑造和约束参与者行为来构建社会互动的规则。在行政管理领域,非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官员在日常工作中所表现出的那些未经官方认可甚至与正式制度相悖,但体现为稳定的、广为接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2],例如基层政府间的“变通”和“共谋”等现象。与正式制度不同的是,非正式制度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约束机制,而非具有强制力的外在约束机制。
非正式制度和行为弥漫于政府过程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时段[3]。当下,基层治理涉及不少民生痛点、难点、堵点,传统刚性或强制性的“行政主导型”的执行方式在不少事件前不再适用,而逐渐强调运用内含“非正式制度”的共识性或引导性的政府模式,即政府披上以“情”和“义”制造“自愿”等更为隐蔽柔性的“策略动员型”外衣达成治理目标[4],如通过广泛宣传和行政参与,在各个主体间形成具体明确的合法行为的规范共识[5]。具体到社区环境治理领域,如在社区垃圾分类实践中,党建引领这一整合型的正式制度可通过开放纳入非正式的习俗、文化、情感等非正式制度[6],利用民情社会关系等形成社区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合力。
纵观学界对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主要从非正式制度的本质特征、与正式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及在乡村社会等基层治理中的运用三个方面展开。但关于在基层治理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及其与正式制度间的张力等研究尚且较少,本文将对在特定情境下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正式制度失能难为但非正式制度却可为这一张力现象进行解释,探究非正式制度在基层治理中可为的作用机制,并从非正式制度“情”之柔性与正式制度“理”之刚性融合的角度探究两者的良性耦合关系。
3" " "北京大兴G社区环境治理:困境、对策与成效
北京市大兴区G社区属于老旧小区,有31栋居民楼、158个单元门、180位楼门长。近些年来,因对小区进行升级改造,受建筑施工影响,社区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现象严重,既破坏了社区环境,又影响了居民出行,但社区并无相应的制度条例对该行为做出约束或明确规定,也无法在短期内强制要求各居民停止家装升级业务或禁止建筑施工团队进入社区。源头制止困难,则只能考虑治理,但是仅凭社区居委会及网格长的力量又不足以对社区环境进行有效整改,且如果仅对现有建筑垃圾进行处理而不纠正居民行为,本质上对解决社区环境脏乱差的困境于事无补,因此,G社区环境整改一度面临窘境。
作为北京大兴拉家常议事会机制的试点社区,G社区党支部书记小陈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方面迅速召集居委会工作人员、物业公司人员和部分楼栋居民商议此事,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各抒己见。同时,积极与社区居委会成员、楼门长们访邻问友、串门聊天,主动征集居民关于社区环境整治的意见建议。经过充分调研与意见征集,社区居民们一致表达了对社区环境现状的不满,并希望能整顿提升。
调研了居民意见后,如何动员起社区居民加入,共同推动生活环境整治成为社区的一道考题。社区支部书记小陈构想了组建“环境监督队”的计划,通过和楼长们拉家常的形式,小陈询问了楼长们的意见,并得到了众热心楼长的支持。紧接着,小陈和楼长们通过拉家常的形式,走进所在楼栋居民家里谈心聊天,推介社区“环境监督队”及环境整治的重要性,凭借着在社区的良好人际关系、居民的充分信任和丰富的情感资源,赢得了一些群众的热心支持。不久,一支由楼长和热心群众组成的“环境监督队”迅速成立,并积极投身社区环境治理中。
“环境监督队”成员们每日不间断地排班值守,拆旧家具、清小广告、垃圾分类、运输投放、入户宣传……这一暖心举措赢得了更多居民的支持响应,渐渐地,队伍越发壮大,社区环境变得焕然一新。大家纷纷表示“居委会、楼长们有不少是关系好的邻居好友,他们加班加点地为社区服务,咱们也不能冷眼旁观。”
G社区凭借“拉家常议事会”倾听民声民意,借助社会关系与民情资源组建并壮大环境监督队,以民情民心交往互助这类非正式制度资源,赢得了居民对社区环境治理的广泛支持,突破了刚性的社区制度条例治理失能的约束,解决了社区正式制度无法解决的难题。
4" " "社区环境治理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分析
4.1" "动员:关键群体下的情感动员
“关键群体”是集体行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群体代替绝大多数群体,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着承担行动初始成本、动员其他群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关键性作用。城市社区治理动员需要广泛主体参与,但由于社区居民间的原子化倾向,不少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持冷漠疏离态度,参与的意愿程度和积极性不高。因此,需借助关键群体的力量,以“关键群体”作为媒介,动员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此即“媒介式参与”。关键群体往往以退休赋闲在家、热情积极、人员关系好且在社区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的人士为主,他们在社区居民间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可以聚合社区利益,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推动社区集体行动。案例中G社区通过党建引领,发挥社区支部书记的示范带头和主体作用,动员了楼栋长等关键群体。楼栋长是所在楼栋居民推选而上的受居民信赖的群体,他们可凭借自身拥有的丰富社会关系资源动员其他居民,且极大降低了社区居委会动员社区居民工作的难度。通过下沉社区居民家中以“拉家常”的形式,打好“感情牌”,楼栋长等关键群体对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意义展开动员,以此赢得了居民的支持。
4.2" "转化:诉求回应下的力量转化
在关键群体支持的基础上,社区环境治理仍然需要动员广大居民的参与支持。只有将群众诉求置于首位,回应并满足群众诉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真正将解决民生问题落到实处,让民众切实感受到“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才能将更多的主体转化为社区建设的力量,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的重要目标。当下城市基层治理中,社区应主动回应并满足居民的合理诉求与需求,让居民感受到社区在为居民的更好生活谋幸福,从而愿意主动投身社区建设。案例中G社区面临着居民对小区建筑垃圾影响美观与出行的不满,以及对清理建筑垃圾、改善生活环境的合理诉求。一方面是居民诉求的满足,一方面是对人手不足难题的突破,社区陷入了居民诉求难以回应、居民力量难以动员的双重困境。但G社区敢于突破既有思路,通过楼栋长上门安抚民众情绪并作出了会尽快成立环境监督队、积极整改社区环境的承诺,既回应了民众诉求,巧妙化解了居民们对社区环境治理不作为的抱怨不满,展示了在民生领域积极作为的良好风貌,又在诉求回应后努力争取一批可加入环境监督队的群体,并将其顺利转化成了支持力量,壮大了社区环境整治的支持队伍。
4.3" "联结:价值导向下的主体联结
社区是一种理想和价值意义兼具的生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打造需要信任、合作、利益和责任等的共同配合。利益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行动、建设社区共同体的前提,更是建设成功后居民利益得以保障的渠道。责任是居民在社区治理中付出行动的价值基础,良好的责任意识可有效推动社区治理的集体行动。在社区环境整治共同建设环节,需要借助利益观增强共同体的事实性与现实性、借助责任感来强化治理共同体的责任意识,主动推动居民为社区建设做出实际贡献。在本案例中,在关键群体的情感动员以及居民诉求回应所致部分主体力量转化之后,G社区又借助社区广大居民个人利益等的满足以及社区共同目标实现后给居民带来的实际利益壮大了参与力量。G社区环境监督队成立后,楼门长和热心居民加入其中并每日值班轮值,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社区居民共同体利益的满足做出了一定的实质性改善,证明了居民力量的壮大可以为社区带来整体性的利益增加,并且未来更为现实、广大的利益目标需要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共同加入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在“拉家常”议事会下,随着热心居民队伍的壮大,凭借着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居民内心的责任意识也被邻里亲友关系的唤起所激发,并同熟人一同加入社区环境治理队伍,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下,社区环境治理的联结效应越来越明显。
5" " "结论与启示
目前,城市老旧社区环境治理中充斥着大量复杂交织的疑难杂症,若仅靠社区居委会的正式组织力量或正式制度的刚性力量存在失能难为现象。不可否认,非正式制度因其价值理性、工具柔性,以及内生的社会关系纽带、内含的民情民意、内化的柔性策略动员可为基层治理巧妙化用,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邻里困难帮扶、社会秩序良性运转等具有良好的制约和调节作用,是基于刚性治理框架下的策略调适,是化解现实矛盾、推动有为治理的优势之道。为此,要积极促成非正式制度之“情”与正式组织制度之“理”相融合,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结合本案例启发,本文认为可从如下方面推动“情理结合”,促进老旧社区环境治理。
5.1" "融情:发挥非正式制度的柔性优势
民情与社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将情感作为治理工具,通过积极培育情感资源引导情感价值回归,是对复杂基层治理现实的弹性回应和调适补充,能在正式制度难以企及之处建构邻里互动秩序,可作为正式制度的配套机制和补充力量存在。如若社区居委会利用制度对居民做出刚性约束要求,反而会适得其反。老旧社区是个熟人社会,利用熟人间的亲邻好友等社会关系动员关键群体,再借助关键群体的人际关系、情感牵绊等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动员社区居民往往能取得不错的效果。G社区的拉家常议事会便是个良好的秩序建构、关系维持、柔性动员的非正式平台,在老旧社区环境整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5.2" "互构:促进制度与民情的有效耦合
非正式制度入场基层社区治理时,务必会与“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发生互动。当组织中个人的偏好与正式制度的总体目标一致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才能兼容。因此,为达到社区治理效果,必须引导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形成良性互动耦合。一方面,社区居民的情感诉求及利益目标是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正式制度的代理人(社区两委等)须有效关注民情、尊重民意、回应民声,构建良好的邻里秩序,积极培育社区内生资本与平台,如本案例中的“拉家常议事会”和“环境监督队”等,引导非正式制度参与治理,并尝试逐渐将其向正式制度转化。当然,正式制度不应过分干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生长。另一方面,正式制度在引导和控制非正式制度的过程中,其过度的刚性与强制性也会被非正式制度的柔性与经常性所消解,为此,正式制度也应主动汲取非正式制度的经验并进行适治化的自我变革,努力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有效耦合的良好治理局面。
主要参考文献
[1]LAUTH H J.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democracy[J].Democr atization,2000,17(4):21-50.
[2]崔晶.基层治理中政策的搁置与模糊执行分析:一个非正式制度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20(1):83-91.
[3]周雪光.论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J].清华社会科学,2019(1):7-42.
[4]余丽娟,李俊龙.非正式治理者何以可为:政策动员中的非正式制度运作透视——以S省J社区拆迁动员环节为例[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4(1):62-71.
[5]何哲.从硬治理到软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一个趋势[J].行政管理改革,2019(12):16-23.
[6]侯利文.社区治理的民情基础: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为例[J].求索,2023(4):129-136.
[收稿日期]2024-06-18
[作者简介]吴湘玲(1967— ),湖北通城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区治理、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