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小径分岔的花园》与《罪与罚》的犯罪母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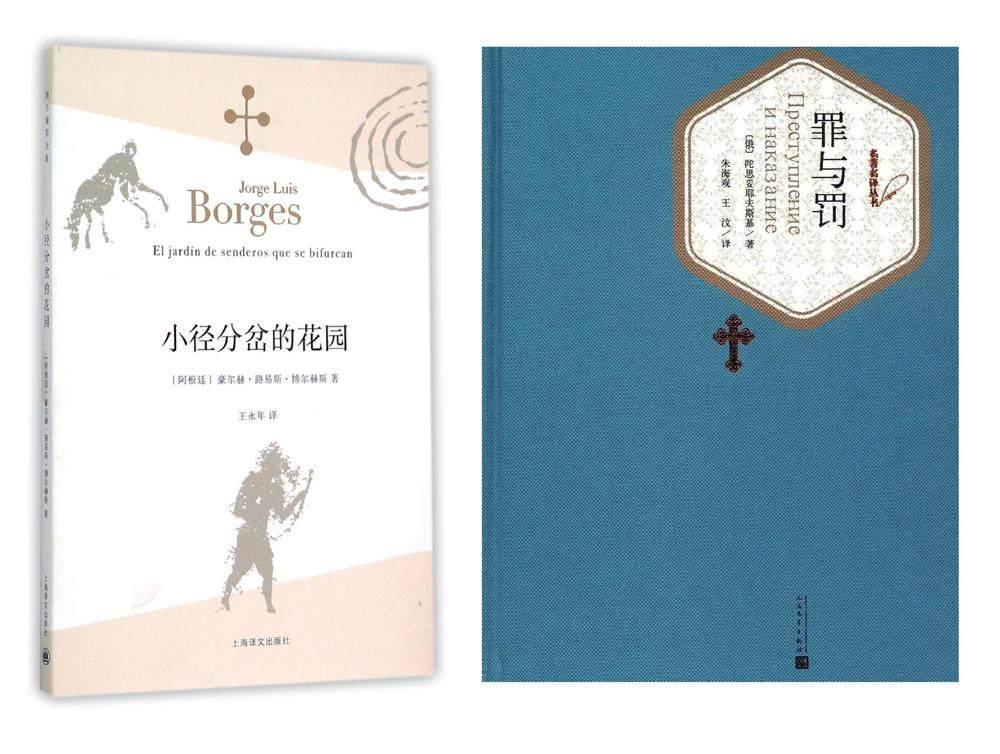
摘 要:“母题”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的核心研究范畴之一,母题研究对分析文学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有重要作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代表作《罪与罚》在表现犯罪母题时出现了很多共同特点,主要表现在犯罪动机、情节偶合性和犯罪者特殊的罪罚观等方面。这些特点将它们与其它表现犯罪母题的文学作品区别开来,丰富了文学的犯罪母题。
关键词:小径分岔的花园;罪与罚;比较文学主题学;犯罪母题
主题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研究门类之一,“主题”与“母题”则当属主题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世界文学发展到今日,出现了如“爱情”“死亡”“命运”“战争”等许多的母题,对人的精神世界和外在物质世界都有涉及。文学作品中,母题的存在与主题的阐发往往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客观叙事,会在不同国家的作家笔下以各种形态反复出现,为文学作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都讲述了主人公的一次犯罪事件。从实证性影响角度来看,两部作品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但当我们从中抽取出犯罪母题,思考两部小说建构该母题时所呈现出的诸多共同点,就可以发现它们与其它讲述犯罪事件的小说有极大不同。
一、母题与犯罪母题
母题研究是比较文学主题学中的重要研究范畴之一,中外学者对“母题”作过不同的解释。维谢洛夫斯基认为:“它是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最小意义单元”[1]254;托马舍夫斯基认为,母题“是指‘叙事句的最小基本单位”;民俗學家史蒂斯·汤普森认为,母题是故事中最小的、能在传统中持续的元素;乐黛云认为,母题是反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人类基本行为、精神现象和人关于世界的概念……在这里,我们主要采用杨乃乔在《比较文学概论》中综合了中外学者的观点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母题”兼具维谢洛夫斯基和托马舍夫斯基二人定义里的特点,既是“最小意义单元”,也是“叙事句的最小基本单位”。另外他指出:“只有当这些最小的意义单元与主题构成了直接而密切的关联之时,它们才能被称为母题。”[1]254也就是说,作家将多个母题“进行组合、重构,使之具体化”[1]255,最后提升成具有作家主观倾向性的主题。
关于母题的特性,王立曾在《主题学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实践》一文中,通过区分“母题”与“主题”,提出了以下四点:“母题是具象性的”;“母题较多地展现出中性、客观性”;“母题数目有限”;“进行跨民族、跨文化比较时,母题的着眼点偏重在‘同,而主题的着眼点偏重在‘异”[2]。根据这些特点,可以发现《小径分岔的花园》和《罪与罚》两部小说中都能抽取出“犯罪”这一母题。
事实上,犯罪母题在世界文学史中并不少见,从麦克白谋杀邓肯王、克劳狄斯杀兄夺位到沟口烧毁金阁……犯罪母题无疑都是这些故事的关键组成部分。作家们热衷于描写犯罪,因为它最考验人性,也最能反映人性,像一个放大镜,将人性里的善和恶放大给读者(或观众)看。犯罪行为会把一个普通人扔进极端境遇中,让他违背人世的道德、法律和自己的良心,不仅要面临与外在世界的矛盾,也无法逃避内在矛盾,即良心的谴责。之所以要把《小径分岔的花园》和《罪与罚》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此两部小说在犯罪母题的呈现方式上有很多共同点,具体表现为犯罪动机的相似、犯罪者身份及处境的相似、犯罪行为招致的惩罚方式相似等。同时,它们的这些共同点又明显区别于一般包含犯罪母题的文学作品,有其独特性。首先,《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余准和《罪与罚》里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动机都较为复杂,并非单纯地与被害者有仇怨,或为图谋对方财物;其次,二人都属于知识分子,一个是青岛大学的教师,一个是大学生,但都因各种原因身处困境;最后,他们并非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的坏人,反而是有善良、勇敢的一面的普通人,犯罪后的自我谴责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道德和法律的惩罚。研究这两部作品中的犯罪母题,有助于我们对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塑造以及西方文学中说不尽的“罪与罚”的话题进行再思考。
二、犯罪母题与犯罪动机
犯罪母题在不同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不同,但单就犯罪动机来说,本质往往离不开私欲。比如有艾米丽小姐为得不到的爱情杀人藏尸,有麦克白夫妇为篡位谋杀国王,也有美狄亚为了报复背信弃义的丈夫杀害亲子……一般来讲,在含有犯罪母题的故事中,人物的犯罪动机都是较为明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被害人的财物、地位,或者是为了自我满足、爱情和复仇——总而言之,都是为了一己之私。而这个结论在《小径分岔的花园》和《罪与罚》的犯罪故事中却并不适用,余准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动机与以上这些常见的动机没有直接联系,被害者艾伯特和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姐妹也并非和他们互为仇敌,甚至可以说是无辜受害,这正是两个犯罪事件的特殊之处。事实上,他们二人的犯罪动机与期待实现自我价值和反抗意识有关。
(一)犯罪者自我价值的实现
前文已提到,余准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具有相似的身份和处境。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开篇就明确地告诉了读者主人公余准的身份,他是“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也在第一章借拉斯科尔尼科夫之口介绍了主人公的大学生身份。毫无疑问,两个人物都是知识分子,但一个漂泊异乡,沦为德国军方的间谍;一个贫困潦倒靠典当东西度日,“已经有两天几乎什么东西也没吃了”。他们在社会生存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却做不到浑噩度日,越是处于困境,越是有证明自我价值、获得认同感和存在感的需要。
余准犯罪行为的浅层动机是通过杀死一个叫“艾伯特”的人向德军传递消息。但在“证词”当中,他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我不是为德国干的。我才不关心一个使我堕落成为间谍的野蛮的国家呢。……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3]72-73作为一个中国人,余准即使为德国人卖命,但始终保有自己的骄傲。他一面憎恨这个“野蛮的国家”,一面又期望能在对方面前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和自己的种族是有价值的。这种心理看似矛盾,实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时无可奈何的悲哀。余准已经被迫失去了在祖国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对他而言,唯有间谍工作的成功,才有可能博取西方人对他和他的民族的尊重,这也是他当下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实际上余准的这种想法是天真可笑的,间谍的身份使他注定无法成为战争中的英雄,没有人会感激一个外国间谍的牺牲。一句“证言记录缺了前两页”就是在暗示读者,关于他的痕迹最终只能淹没在无数卷宗之中。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始于他关于“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的哲学思考。他认为世界上的人应分为“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两类。“平凡的人”只是“繁殖同类的材料”,他们顺从、安于现状;“不平凡的人”则是有才能有禀赋的人,他们不会遵从规则,而是有权支配、处理“平凡的人”,可以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肆意犯法。拉斯科尔尼科夫将自己归为“不平凡的人”当中,认为自己会是拿破仑一样能够改变社会的人物。在谋杀老太婆的想法萌芽之时,他恰好在酒馆里听到了一个大学生和军官之间的谈话,他们的想法与拉斯科尔尼科夫不谋而合。那个大学生说:“我真想把那个该诅咒的老太婆杀死,把她的钱财抢走,……这样做,我不会感到于心有愧。”[4]74“杀了她,拿走她的钱,然后藉助于那些钱,献身于全人类的工作,和公共的事业。……难道做出成万件好事来还抵不过一宗小小的罪行吗?”[4]75这场看似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偶然听到的对话,其实正是他心理活动的现实映射。根据他所谓的“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哲学,此时需要一个“不平凡的人”杀掉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用老太婆“一个人的死换来一百人的生存”。也就是说,拉斯科尔尼科夫杀死老太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给社会除害,用她的死来造福千千万万个穷苦人。
“读者和学者们都很难将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另外一些肮脏低下的‘犯罪者相提并论,作家总是有意将拉斯科尔尼科夫描述成一个‘高尚的犯罪者形象,其根本原因在于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其一己之欲。”[5]23他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犯罪行为是正义的,实施犯罪行为的自己是救世英雄,他可以通过“正义的”犯罪来实现自我价值。这一思想对于穷困潦倒的、在社会上来回游荡、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年轻大学生来说,无疑极具诱惑性——他无力改变现状,因此急需一个可以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途径。
尽管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生活时时刻刻被贫穷的阴影笼罩着,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靠母亲和妹妹供养、日日为房租和三餐忧虑,但他的犯罪动机却和金钱毫不相干。“贫困是始终伴随着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他的家庭的,如果犯罪仅仅是为了改变窘困的家庭状况,那么犯罪行为或许早就已经发生。”[5]23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赃物的处理上看出来。他原本打算将东西扔进河里,经过一番考虑,把它们埋在了无人的角落,在这之后就算身无分文也没有取用过。这个细节足以将拉斯科尔尼科夫与其他表现犯罪母题的文学人物形象区别开来。
(二)犯罪母题背后的反抗意识
虽然《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个只有寥寥十几页篇幅的短篇小说,但博尔赫斯在设计犯罪事件的时候,却将主人公余准的形象塑造得极为丰满。如果说余准最初的犯罪动机是为了在西方人面前证明自我价值,那么随着他和艾伯特的交谈逐渐深入,这个动机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质变——杀死艾伯特是他对自己被定义、被书写的命运的反抗,也是中国人对中国故事被外国人所定义、书写的反抗。
余准在见到艾伯特之前从未想到,这个可以帮他传递消息的谋杀目标的名字会是一个研究自己曾祖彭冣的汉学家。艾伯特的花园让他熟悉万分,房间里有从未付印的《永乐大典》的佚卷,有青铜凤凰、红瓷花瓶等许多带有中国符号的东西。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艾伯特看似谦逊、实则以一个权威的姿态在余准的面前侃侃而谈,甚至拿出了彭冣的书信给他看。反观作为彭冣子孙的余准,他曾两次试图插话以证明自己对祖先有所了解,却每次都以尴尬收场,表现出他对祖先遗物的极大无知。在一个英国人面前,中国人余准感受到了无力和屈辱:他不仅没有能力解读自己祖先的思想,身为青年知识分子,他甚至堕落成异国间谍,没法将“中国故事”续写下去;偌大的中国虽然人才济济,但因深陷民族危机,汉学竟要倚仗外国人钻研。余准身不由己地被外国人支配,自我价值等待他人定义,现在连祖先的“中国故事”也要由外国人执笔书写。虽然艾伯特是一个对余准来说“并不低于歌德”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也是他在異国遇到的唯一一个真正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但同时艾伯特带给余准的无力感和屈辱感也足以激起他的反抗。杀了艾伯特就等于断绝彭冣的“中国故事”被外国人继续定义和书写的可能,也能让余准走上绞刑台,摆脱被定义和支配的悲哀命运。因此,这场有预谋的犯罪背后,是一个犯罪者最后的挣扎与反抗。
同样地,在《罪与罚》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也是他反抗意识的体现。“他的‘不平凡的人理念本质是对传统宗教精神的反叛”[6]153,是对法律体制和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观的反抗,也是“人的意志对忍让精神的反叛”[6]153。他自己本身就生活在社会底层,亲眼所见丽扎维达、玛尔美拉朵夫和索尼娅等人的悲剧,因而感受到社会对善良的穷人的极大恶意。既然所谓的神和社会规则不站在他们这边,反而让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伪君子卢仁等货色春风得意,那他唯有主动打破它才能改变现状——而犯罪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总之,余准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正是反抗意识的体现。虽然他们想要反抗的东西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犯罪之前都处于一个被压迫或被支配的境地。犯罪行为是他们用来改变处境的方式,而非谋求一己私利的工具。
三、犯罪母题和偶合情节
比起以破解犯罪案件为核心情节的侦探小说,博尔赫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处理犯罪母题时都不约而同地加入了许多偶合。有学者曾将一般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凶杀题材的小说进行对比,并指出了大量偶合性因素在陀氏小说中存在的合理性:“侦探小说讲求逻辑推理,看似出乎意外,想起来却又在意料之中。因此,侦探小说坚决排除意外或巧合,犯罪和破案方法都务求合乎科学,言之成理。……与之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犯罪就附着上了明显的神秘与偶合因素。毕竟犯罪事实本身并不是作家的终极追求,它服务于作家思想传达和人物心理刻画。”[7]这一结论其实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也同样适用,这两部小说里的犯罪事件都离不开偶合。
首先,艾伯特恰好是一个汉学家,汉学博大精深,他偏偏又是一个研究余准的曾祖彭冣的汉学家;其次,余准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千千万万,偏偏只有他是彭冣的后代。假如将他们放在现实世界里,二人相遇的概率几乎为零。在作家有意地设计下,这一对熟悉的陌生人在小说的世界里“偶然”相遇,起因不过是一个间谍为了向军方通报城市的名字而杀掉一个同名的人。博尔赫斯设计的最巧妙的偶合就在这里——如果余准不来杀艾伯特,他们大概永远不会相遇,既然相遇,艾伯特必然要死在余准枪下。
《罪与罚》里的偶合情节显然更多,大大小小的偶然几乎贯穿了小说始终,在此仅仅举两个发生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犯罪过程中的例子。一次是在他取用斧头作为犯罪工具时。按照拉斯科尔尼科夫原本的计划,是到女房东家的女佣人娜斯达霞日常工作的厨房里拿斧头,因为娜斯达霞在黄昏时常常不在家。但这一天她却出乎意料地没有出门,让拉斯科尔尼科夫“大吃一惊”,“遭到致命的一击”。然而他很快意外撞见了一个绝佳机会——扫院人的小屋敞着门,里面竟有一把斧头。连拉斯科尔尼科夫自己都感叹这一偶然:“理智没帮上忙,也自有魔鬼来帮忙!”[4]82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波折就像是有意要折磨他的神经一般。另一次偶合情节很快再次出现。当拉斯科尔尼科夫走到老太婆的房子前时,“正巧这当口,有一辆装满干草的大货车刚刚在他前边驶进大门,他跟在后面穿过门道,那辆车始终遮挡着他。”[4]83就这样,一个笨拙的杀人凶手竟然顺利躲过了所有可能看到他走进院子里的目光。作家本人都承认这是极大的偶然,“好像有谁故意安排好了似的”[4]83。命运好像一直在眷顾这个犯罪手法青涩的凶手,就连他次日处理赃物的时候都是这样。这个时而清醒时而神经质的年轻人,竟然最后选了个他完全陌生的、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的院子,并且直到他走出院子,都没人发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精神状态极为不稳定,很多行动甚至是轻率的,更谈不上谨慎。正是有作家设计的一系列偶合相助,他才能完成自己漏洞百出的犯罪计划,并且还让警方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凶手。
虽然偶合性情节颇多,但毕竟作品里的“犯罪”母题是用来服务主题表达的,作家无意将犯罪事件写得如侦探小说一般悬念迭生,许多看似不可思议的偶然事件不过是为了达成“人物成功实施了犯罪”这个最终目的。
四、犯罪母题与罪罚观
提到“犯罪”母题,我们就不能忽略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罪罚观和“惩罚”。分析犯罪者经受的惩罚方式,是解读“罪与罚”这一说不尽的文学话题的重要一环。《小径分岔的花园》和《罪与罚》对罪罚问题的处理大致采用了相同的模式,即“良心的谴责大于法律的惩罚”。
余准在“证词”的最后,将这场完全符合他计划的谋杀称作“糟糕的胜利”,道出了他最真实的感受——“无限悔恨和厌倦”[3]83。那他究竟在悔恨和厌倦什么呢?是因沦为德军间谍吗?可是沦为间谍并非一朝一夕,且他在到艾伯特家之前,还抱着向德国人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的想法。难道不杀艾伯特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吗?显然也不是。追捕他的理查德·马登上尉已经胜利在望,抓住这个德军间谍只是时间问题,在落入敌手之前完成任务,已经是余准最好的结局。那么,余准的悔恨和厌倦只能源于他和艾伯特在最后一小时里的谈话。
在前文已经提到,余准最后向艾伯特开枪的动机里,暗含了中国人对“中国故事”被外国人定义和书写的反抗。事实上,余准对艾伯特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面因艾伯特这个英国人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研究汉学带来的优渥生活,而作为彭冣后人的他却朝不保夕而不满,因艾伯特的话给他带来的无力感和屈辱感而愤恨;一面又认为艾伯特是一个谦逊的、不低于歌德的人,被他言谈中流露出的智慧和学养所折服,“感谢并且钦佩”他“重新创造了彭冣的花园”。余准既感谢艾伯特,又怨恨他。余准明白,艾伯特大概是首屈一指的对彭冣的思想研究得如此透彻的汉学家,也是重建他曾祖迷宫的恩人,他的死将阻断彭冣的思想被发现、被了解的可能。正因为余准杀害的是一个他所感谢且钦佩的人,一个发现并解读了彭冣的迷宫的人,才会有“无限悔恨和厌倦”。悔恨与厌倦正是他的良心对犯罪行为的谴责,也是最可怕的惩罚。
《罪与罚》是一部对“罚”的强调大于“罪”的小说,作家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双重心理的呈现,也正是作品最为人称道的地方之一。犯罪之后,他时而是那个邪恶的杀人凶手,时而还是善良勇敢的年轻大学生。“高尚与败坏、正直与邪恶、本我与自我之间的力量冲撞交替反复,组织起了这期间他几乎所有的心理活动。杀人之前的他渴望的是摆脱生活的困境和痛苦,可这却令自己跌入到了一个更大的苦难深渊无法自拔”[5]29。最后,他终于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走上了自首之路。
拉斯科尔尼科夫和余准一样,都是立体丰满的人物,并非单一化的恶人形象。他们的所思所想和实施犯罪时表现的怯懦、恐惧、纠结等心理,让他们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不失善良之心的普通人,因而必然要经受良心的拷问和折磨。相较之下,法律规则对他们的判决则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余准在犯罪之前显然很清楚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判决,杀人犯和间谍的身份足以让他死在英国。但让自己和被害者艾伯特的名字一起登报正是他的最终目的,死亡也是唯一能帮他摆脱间谍命运的方式。法律与其说是惩罚了他,不如说是成全了他。拉斯科尔尼科夫经历了漫长艰苦的内心挣扎,还曾多次面对狡猾多疑的侦探的心理攻击,和他斗智斗勇。在索尼娅帮助他获得精神的新生后,自首反而可以帮助他摆脱痛苦,对他而言是真正的解脱。
五、结语
“犯罪”是西方乃至世界文学中的重要母题,它将人性放在极端特殊的境遇中,使人性折射出本来的面貌。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试图用犯罪的情节,展现主人公性格的不同侧面,表达对人之存在的终极意义的思考。同时,作家对“犯罪”母题的书写又为两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身上蒙上了一层悲剧的阴影:余准从沦落为间谍开始就彻底失去了掌握自我命运的权力,艾伯特为揭开彭冣奇书之谜倾注一生心血,“虽然了解了‘谜底,但是他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冥冥之中,似乎书的作者就不愿意让人知道‘谜底,艾伯特正是触碰了这种禁忌,命运才给他死亡的惩罚”[8];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哲学,成为这部“多声部”小说中最重要的声部之一,最后却在外界压力和自我怀疑中宣告破产,不得不向自己曾经激烈反抗的东西寻求庇护。
两部小说在表现“犯罪”这一情节时,主要人物形象得到突显和丰富,两个实施犯罪的主人公完全不同于绝大部分文学作品中用以表现“犯罪”母题的人物。相反,作为走投无路的平凡人和知识分子,他们的犯罪动机及所思所想都能激发读者的同情与怜悯,成为“犯罪”母题书写中的特殊存在。
参考文献:
[1]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王立.主题学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实践[J].学术交流,2013(1):162-168.
[3]博尔赫斯.虚构集[M].王永年,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
[4]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汝龙,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
[5]刘文青.《罪与罚》中的犯罪叙事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5.
[6]袁强.谋杀母题中的反叛意识——《罪与罚》与《白夜行》的平行分析[J].名作欣赏,2017(27):152-153.
[7]杜庆波.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犯罪问题[D].广州:暨南大学,2003.
[8]劉婕.论博尔赫斯侦探小说的叙事特色[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4):154-155.
作者简介:扈雨涵,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