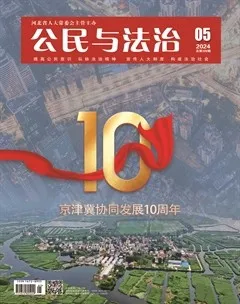由范进中举后的“疯”谈开去
易水寒
凡读过吴敬梓《儒林外史》的人,大抵都知道范进中举后疯了。范进因何而疯,原因多多。
比如说,范进从20岁开始科考,一直考到54岁才考中,可以说他大半生的好年华都献给了科考,这一期间所遭受的挫折,所付出的心血实在是太多了。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所以一旦中举,喜极而悲,疯了!再比如,明清两代,考举人虽然没有金榜题名的进士那么难考,但也确非易事。以清王朝为例,史料记载,其每年的举人招考名额仅500~600人,这五六百人的名额如果分配到全国的县,岂不少得可怜!还有史料显示,大清王朝的268年,总共才招了15万名举人,我们可以算一下,如果把这15万举人的名额平均分到每一年,也只有少得可怜的560人左右。举人的名额少,录取的难度就大,范进在如此少的名额下脱颖而出,他当然会高兴得发狂发疯。
范进除了难考而考中进而发狂发疯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举带给他的特权。据史料记载,明清之际,举人除可以直接任命副县级官员外,还享有如下特权:一,名下可以有田地200亩,且田地的收成免除赋税;二,举人及其直系亲属免除一切徭役;三,进官府不用下跪。如此等等。别的不说,只第一条,就能保证举人的全家衣食无忧。
一个人享有特權,意味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已今非昔比。众所周知,范进中举前,只是一位在乡村的破庙里教书的先生,寒酸得很。他因为经常吃不饱,曾经“抱着个老母鸡到集上去卖换钱买米”。最使范进难忘的是科考没路费时的一次借钱。俗话说:上山打虎易,开门求人难。当范进鼓足勇气到本村一屠户那里,刚开口,屠户就吐了他一脸口水。此时的范进受如此的羞辱,也只得赔个笑脸走人。不但本村稍富有的人看不起他,连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也看不起他,认为把女儿嫁给他吃了大亏,他甚至用长得“尖嘴猴腮”这种带有污辱性的话挖苦他。
而中举之后呢?人都好像变了似的,不但本县的大土豪亲自登门拜见,称兄道弟,而且还送了银两。就连那位“往脸上吐口水”的屠户也到家里套近乎。至于带着礼物纷纷到家拜见的街坊邻居就更多了。
之前,范进是没有机会会见知县的,中举后,恰逢母亲去世,范进在家守丧,因生活来源问题他去会见了知县。知县看到范举人来了,特别设宴款待了他。此时的范进自以为今非昔比,席间竟然也挑挑拣拣起来,说什么守丧期间不能用银碗银筷。知县听到后也不说什幺,直接命人换成了竹制的。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的老丈人胡屠户,在他中举前后判若两人,从前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现在见了居然也点头哈腰起来。
我们说,人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人格尊严。人的一生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往往不是曾经的挨饿受冻,而是人格曾经受到的羞辱和伤害。范进曾经不止一次地挨老丈人的骂,也曾不止一次地挨包括“往脸上吐口水”那样的羞辱,这一切都成了过往。范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眼看着从“人下人”变成了“人上人”,如此的反差,他焉能不发狂发疯。正如有评论说:如果你处在范进的位置,“叫你你也疯”。
科举,始于隋朝,相对于此前的门阀世袭,无疑是一大进步。科举的开启,为士人(读书人)晋升开辟了一条通道。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自隋至清,一千余年的科举也造就且强化了“官本位”的思想。当官发财,当官享有特权的思想至今仍深入人心。比如说,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那就是商人很难成为纯粹的商人。商人也渴望谋取官位。因为他们明白,在中国,要想发财保财,不可没有权力的庇护。
一位先贤说过:耕田之利不过十倍,珠宝之利不过百倍,而权力投资则可获利千倍万倍。
由以上来说,范进的疯是可以理解的。
由以上来说,要解决人们对权力的痴迷,进而杜绝权力腐败的问题,我们必须对不合理的选用人制度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