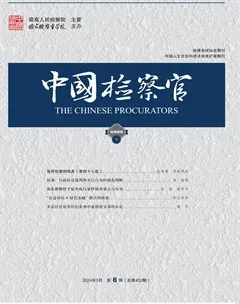以竞买相要挟索要财物的行为定性
冉巨火 张敏
一、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19日,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自规局”)挂牌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底价为1.18亿元。宗地用于承建市政府保障性住房(限价商品房,所建住房需以低于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20%的价格对外出售)项目,系先开工后补办手续项目,已由B公司先期投资3.8亿元进行建设,并完成了工程总量的80%。挂牌期限内,B公司与A公司先后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参加竞买并分别提交了报价为1.182亿元、1.184亿元的竞买报价单。B公司董事长乙得知A公司也参与竞买后,害怕宗地被A公司竞得,B公司前期投入收不回来,遂托中间人找到A公司董事长甲,央求A公司退出宗地挂牌出让。甲称,“A公司前期已经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未来一定会积极参与竞买,直到拿下宗地为止。鉴于该地块开发后利润巨大,要么甲给乙5000万,B公司退出挂牌出让;要么乙给甲5000万,A公司退出挂牌出让。”乙无奈之下托中间人与甲反复说和。甲告知乙,“如欲A公司退出竞买,除非B公司送给甲个人2200万元。”2021年1月18日,在乙的指示下,B公司财务通过B公司公户按照甲的要求将2200万元打入甲个人银行卡中。此后,在现场竞买阶段A公司仅象征性地举牌一次,加价100万元,B公司最终以1.186亿元的价格将宗地竞得。
二、分歧意见
关于本案的定性,存在如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B公司此前已经在该宗地上投入了3.8亿元,并完成了工程总量的80%。B公司之所以会拿出2200万元给甲,目的在于止损。如果B公司不给甲这2200万元,B公司就无法拿到宗地,前期投入的3.8亿元就无法收回。甲以参与宗地竞买、抬高宗地价格相要挟,让B公司产生了恐惧心理,并基于此种恐惧心理向甲交付了财物,故甲成立敲诈勒索罪,作为本案受害人的B公司无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在土地挂牌出让过程中与乙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利益,情节严重,故甲、乙成立串通投标罪的共同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甲作为A公司董事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B公司数额巨大的财物后,让A公司退出宗地挂牌出让,为B公司谋取利益,成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乙作为B公司的董事长,为了让A公司退出宗地挂牌出让,实现B公司利益最大化,指使B公司财务通过B公司公户给予A公司董事长甲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故B公司成立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系单位犯罪;根据刑法第163条第3款的规定,乙作为B公司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三、评析意见
我们赞同第三种意见,甲的行为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B公司的行为应认定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一)甲的行为不成立敲诈勒索罪
所谓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威胁(恐吓),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一般认为,敲诈勒索罪中的“要挟”必须是以恶害相通告,足以让对方产生恐惧心理的行为,因此,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不得认定为敲诈勒索罪。[1]本案中,甲的行为不成立敲诈勒索罪。
1.客观方面甲没有实施要挟行为。依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2条第4款,“本规定所称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出让人发布挂牌公告,按公告规定的期限将拟出让宗地的交易条件在指定的土地交易场所挂牌公布,接受竞买人的报价申请并更新挂牌价格,根据挂牌期限截止时的出价结果或者现场竞价结果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行为。”其具体操作模式为:挂牌期限届满,挂牌主持人现场宣布最高报价及其报价者,并询问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挂牌出让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挂牌主持人连续三次报出最高挂牌价格,没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是否成交:(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报价的,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但报价低于底价者除外;(3)在挂牌期限内无应价者或者竞买人的报价均低于底價或者均不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不成交。
不难看出,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目的在于追求土地出让价格的最大化,鼓励参与挂牌者竞价,遵循价高者得的原则。因此,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过程中,如参与挂牌出让者联合串通,压低宗地的出让价格,会违反这一原则,损害国家的利益。正因为如此,《规定》第25条规定,如宗地竞买者采取行贿或者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宗地,竞得的结果无效;不仅如此,造成损失的,还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据此,甲任职的A公司在报名参加宗地挂牌出让后,按照竞价规则竞买不仅是A公司的权利,也是A公司的义务。只有A、B两个公司都积极参与竞买,才能实现宗地出让价格的最大化,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失。由是观之,作为公司董事长的甲主张未来A公司会积极参与宗地竞价的行为具有正当性,没有超出权利行使的范围,符合挂牌出让的目的。既然参加挂牌出让后,积极竞买宗地是A公司的权利,当然不存在以此要挟B公司,索要财物的问题,据此认定A公司董事长甲成立敲诈勒索罪是存在问题的。
2.B公司并非本案的受害人。法谚有云,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依照刑法第64条的规定,本案如认定甲的行为成立敲诈勒索罪,则意味着B公司是本案中的受害人,未来应将这2200万元返还给B公司。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本案真正的受害人是国家而非B公司。非常明显,如果甲不是收受2200万元后让A公司退出竞买,而是指令A公司按照竞价规则积极与B公司展开竞买,则宗地最终的出让价格将远远高于B公司的摘牌价。正是因为甲、乙二人之间的联合串通行为,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国家才是本案中真正的受害人。
以乙给甲2200万元目的在于止损进而认定B公司为本案受害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B公司前期确实在宗地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这并不意味着宗地未来必须由其竞得;否则,挂牌出让就成了形式,国家的利益就得不到维护。事实上,关于宗地未来如由他人竞得,B公司前期投入资金的解决办法问题,该市自规局在挂牌公告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该宗地为保障性住房用地,根据年度进度考核要求,项目已经部分先期建设。地上建筑物由土地竞得者与开发建设方协商解决。”这样的规定意味着,如果B公司最终未能竞得该宗地,由未来的土地竞得者与B公司协商解决即可。以“止损”为名,主张宗地未来应由B公司竞得,进而认定B公司是本案中受害人的理由并不能成立。
(二)甲、乙二人的行为不成立串通投标罪
依照《招标投标法》第53条之规定,在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投标的,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串通投标的,不仅其中标结果无效,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的,司法机关还必须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与之相照应,刑法第223条规定了串通投标罪。
问题在于,前述《规定》第2条明确规定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出让方式有三种:“挂牌” “招标”与“拍卖”,并分别给出了各自的定义。既然《规定》将国有建设用地三种出让方式在同一法律文件中并列规定,这就说明三者之间存在明显不同,挂牌出让不能等同于招标、拍卖出让。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再将土地挂牌出让解释为招标出让,进而将甲、乙二人的行为认定为串通投标罪,就明显超出了“招标”一语的字面含义,有类推入罪之嫌。
对此,《刑事审判参考》第1136号案例“张建军、刘祥伟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也明确指出,“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挂牌竞买显然不能等同于招投标。”[2]
(三)甲成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B公司成立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1. 甲成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成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首先,甲系A公司董事长,符合本罪的主体要件。
其次,甲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了乙数额较大以上的财物,符合本罪的客观要件。本案中,甲虽然作出过提议,要么甲给乙5000万,B公司退出挂牌出让;要么乙给甲5000万,A公司退出挂牌出让。其真实想法是想在从乙处索要财物后,利用董事长的职务便利,让A公司退出宗地挂牌出让;事实上,甲也从乙处索走了2200万元,让A公司在现场竞买阶段退出了宗地挂牌出让。其行为具备了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符合本罪的客观方面。
最后,甲为B公司谋取了利益。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1款第(三)项的规定,本案中的甲作为A公司的董事长,系利用职权影响交易的个人,在收受贿赂后让A公司退出竞买,从而借机为B公司获取了竞争优势,符合刑法第163条中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
综上所述,甲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163条的相关规定,成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2.B公司成立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164条第1款规定,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成立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根据《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行贿人在招投标或者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过程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以财物,进而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本案中,乙作为B公司的董事长,在国有建设用地挂牌出让活动中,为了让A公司退出竞买,谋取B公司的竞争优势,指使B公司给予A公司董事长以数额较大的财物,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B公司的行为系单位犯罪,符合刑法第164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犯罪构成,成立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同时,根据刑法第164条第3款的规定,作为直接责任人员的乙需对B公司的这一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必须指出的是: B公司不成立单位行贿罪。根据刑法第393条的规定,单位行贿罪的对象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本案中的乙虽然是在为B公司这一主体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因接受贿赂的甲并非国家工作人员,故B公司不成立单位行贿罪。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 [710063]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专职委员、一级检察官 [056200]
[1]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333页。
[2] 《张建军、刘祥伟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过程中串通竞买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二、三、四、五庭主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6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頁。
——以106份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
——兼论《刑法修正案九》行贿罪新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