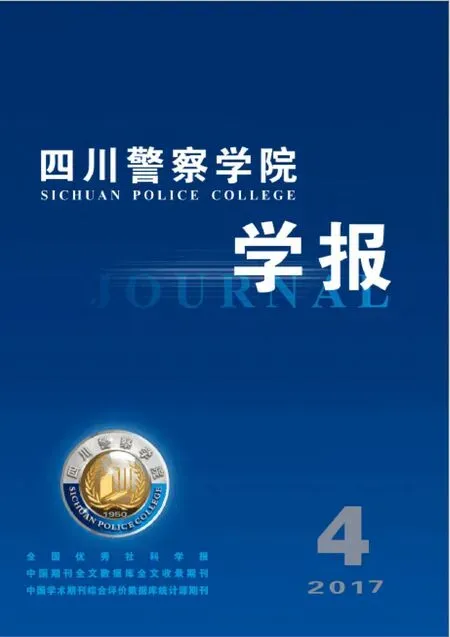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对行贿罪认定的影响
徐永伟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对行贿罪认定的影响
徐永伟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意在严密腐败犯罪刑事法网,但该罪的认定却不无与行贿罪相混淆的可能,将应认定为行贿罪的行为认定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会导致对行贿人的放纵,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也有可能沦为行贿罪的兜底罪名。因此,需要剖析两罪混淆的衍生机理,寻求避免混淆发生的解决方案,从而确保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在腐败犯罪惩处上的正面效用。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行贿罪;兜底罪名 ;特别自首
一、问题的提出
《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不可否认,该罪名的增设承载着明确的惩腐肃恶之旨趣。一方面,在影响力交易犯罪中,《刑法修正案(七)》只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却未将其对合的“行贿”行为纳入犯罪圈,而这也一直被学界视为该类犯罪刑法规制的漏洞所诟病,而此次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无疑实现了行贿受贿的双向构罪,堵塞了影响力交易犯罪的规范漏洞。自此,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形成了完整的闭合关系,严密了影响力交易犯罪的刑事法网;另一方面,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也是当前积极治理主义反腐理念的一种体现。行贿是受贿得以生存和蔓延的土壤,有效打击行贿行为,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1]。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业已入罪的情况下,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无疑可以肩负起从源头遏制影响力交易犯罪发生的使命。
在当前正风反腐的持续高压态势下,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带有积极的正面导向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应该认识到,新罪的增设可能会冲击既有的犯罪认定体系,所以在罪与罪的区分与认定上应尤为慎重。事实上,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增设后,在贿赂犯罪的某些特殊情形中,极易与行贿罪发生混淆,最终可能就会导致原本应认定为行贿罪的行为被认定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关注的乃是“核心权力的周边行为”,与行贿罪直接针对的“权、利交易”在属性上有着根本不同,两者在危害程度上也有显著不同,这一点在刑法分则对两罪法定刑的规定上也有所体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行贿罪的混淆是不被允许的,否则,就会导致对行贿人的放纵,从而背离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严惩腐败犯罪的设立初衷。对此,应及时剖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行贿罪相混淆的衍生机理,并藉此寻求应对措施,以使两罪“各安其位、并行不悖”的完成严惩腐败犯罪之使命。
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行贿罪混淆的衍生
(一)混淆衍生的外在基础:交付财物于第三人的外观表现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行为外在的呈现为请托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将财物交予第三人。按照正常的逻辑,事出必有其因,“既然请托人出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将财物交予第三人,就意味着该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具有某种密切关系,请托人也必然认识到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否则,也不会向第三者提供财物”[2]但对于该种行为的评价却不仅仅只有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一种。客观上讲,请托人出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将财物交予第三人的客观行为,伴随两种可能的主观态度推导:其一是请托人希望通过交付财物的方式收买第三人的影响力,继而通过第三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而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其二是请托人希望通过交付财物给第三人的方式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在此,第三人起到的作用其实是代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其实际上就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了一种共同受贿关系。在第一种情形下,请托人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而在第二种情形下,请托人则构成行贿罪。
对于请托人主观上的态度,难以实在的表现,只能通过既存的客观事实加以推定。根据构成要件理论,客观构成要素对于主观构成要素具有规制作用,即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内容须受制于客观要素[3]。因此,究竟以何种方式加以评价,就需要通过客观事实加以推导证明。在客观事实稀少乃至稀有的状况之下,面对外在呈现上相似的两种罪,混淆的发生也就不无可能。
(二)混淆衍生的内在机理:犯罪认定的迷惑与障碍
面对请托人将财物交于第三人的外在呈现,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混淆在两罪的认定的迷惑与障碍中放大,而对其混淆的内在机理,我们可以在以下两个维度内把握。
1.犯罪链条的一致性。首先,是犯罪链条特征的一致性。交付财物于第三人的外在呈现下,无论是影响力交易犯罪的过程还是请托人通过第三人行贿的过程,其犯罪链条的特征都表现的较为一致:同时涉及三方主体,即在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外,还存在第三人;接受财物方均为第三人;在“行贿”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均不与财物发生直接联系。
其次,是第三人的包容性。在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中,请托人交予财物的第三人即有影响力的人,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而在请托人通过第三人行贿的情形中,第三人作为代为受贿方,指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在这里,关系密切的人可以视作共同利益关系人的上位概念,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共同利益关系的人,“那些被特定关系人概念排除在外、仅仅有情感往来却无明显共同利益关系的其他人,就有可能属于‘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4]易言之,有影响力的人完全可以将特定关系人包容在内,特定关系人也完全可以被评价为有影响力的人。这种第三人的包容性特征就使得两罪的外在呈现上可以同时框定在同一主体外延之上。
两罪犯罪链条上的一致性与迷惑性是相伴而生的,正因为犯罪链条上的一致性才会导致两罪在认定上的迷惑性,这也为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混淆提供了客观的现实条件。
2.行贿罪认定的双重障碍。对于请托人而言,完成交付财物的行为既已宣告“行贿”行为的完成,但这种行为指向的主观意图却并非单一,既可能是在行贿国家工作人员的意图之下还可能是在行贿有影响力的人意图之下,两种主观意图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通过单纯的“行贿”行为并不能对两者加以明示,就需要有相关客观证据予以证明请托人到底是何“居心”。
事实上,只要有客观证据证明请托人有出于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向第三人交付财物的行为即可证明行为人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这是一个简单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认定逻辑。而要认定请托人构成行贿罪,除了要证明请托人有出于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向第三人交付财物的行为外,还需要请托人明知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通谋。请托人正是认识到这个通谋的存在,才会选择通过第三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而从证明的角度看,要证明行贿人认识到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通谋,则首先必须证明这种通谋的存在。
因此,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相比,此种情况下行贿罪的认定更为复杂,其成立还必须具备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通谋及请托人认识到这种通谋的存在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的证明实际就形成了认定行贿罪所必须经历的双重障碍。首先,要证明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通谋。但实际上,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与第三人(即特定关系人)关系的紧密型、经济的关联性、活动的隐蔽性[5],使得通谋的存在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心照不宣”,对通谋的证明自然困难重重。如果不能证明通谋的存在,客观上也就不具备请托人通过第三人行贿的可能,请托人的行为自然无法认定为行贿罪。于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第三人之间的这种通谋就成为行贿罪认定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其次,就是要证明请托人能够认识到这种通谋的存在,如果无法证明请托人认识到有这种通谋的存在,其交付财物的行为也就不应被评价为通过该第三人行贿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自然也难以认定为行贿罪。在此,证明请托人能够认识到这种通谋的存在就构成认定请托人成立行贿罪的第二重障碍
与行贿罪的认定需要历经这双重障碍不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认定却并不需要经过如此复杂的过程。换言之,相对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行贿罪的认定对证据具有更为强烈的依赖性。如此以来,面对相似外观的交付财物于第三人的行为,在既存的事实无法推导或者难以推导出请托人具有行贿的意图时,在请托人交付财物的两种主观推导中,司法机关就不可避免的就走向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某种程度上,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使司法机关有了可以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原本应当认定为行贿罪的行为就有可能被“降格”评价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三、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行贿罪相混淆的忧虑
(一)犯罪认定阶梯结构的形成
通过以上分析,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衍生出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混淆。一定条件下,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某种程度上就形成了一种犯罪认定上的阶梯状结构,在条件满足、有足够证据的时候认定为行贿罪,在条件不满足或者证据不足的状况下,请托人该种行为可能就会被认定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此时,尽管也外在的呈现了对请托人的刑事制裁,但对请托人行为的认定却已经偏离了事实的轨道,恐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也不符合现代法治的价值追求。
(二)行贿罪的专属“兜底罪名”的风险
按照以上的分析逻辑,更为恐惧的是,长此以往,在功利主义的推动下,该种类型案件的认定可能发展成某种“惰性”直至“惯性”,类似情形中,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很可能就会沦为行贿罪专属的“兜底罪名”。如果抛开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和行贿罪在属性和法益损害程度上均有很大不同这个事实,而认为认定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依然可以实现对行为人的处罚,而且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认定更加简便、快捷,则必然丧失竭尽全面搜集证据以认定行贿罪的动力。如此“饮鸩止渴”之举,一定情形下就会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走上成为为行贿罪“兜底罪名”的道路,最终,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于腐败案件的查处的积极效果会大打折扣,而弊端则会逐步放大。此时,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存在就会面临一种功能评价上的“亦正亦邪”的窘境,就如同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所遭受的争议,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功能评价上,就有“反腐的锐利武器”的肯定评价与“贪官污吏免死金牌”的否定批判之截然之分[6],同理,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也可能面临“严密刑事法网”与“放纵行贿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效果的争议。
(三)新的寻租空间的滋生
如果依照这种思路深入推演,在外观呈现相似又容易混淆的罪名面前,案件查处的方向就带有某种自主性与随机性,质言之,这样的混淆可能会滋生新的寻租的空间,又容易带来司法上新的腐败。而且,请托人无论是实施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的行为还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行为,其事实上都具有一种利用财物进行寻租的“前科”,某种程度上,在存在继续可以寻租的空间面前,请托人再次寻租的可能性相对就会高一些,同理,司法上面临腐蚀风险的可能也会相应的增加。
四、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行贿罪相混淆的求解
对以上可能存在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行贿罪的混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求解。
(一)理念之上的求解
1.公正司法理念的贯穿。在坚定不移的反腐败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公正是腐败的克星,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应对和解决腐败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正司法”[7]这反映到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中,就要求我们必须秉承公正司法的理念,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正确的对请托人的行为定罪,在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不能牺牲司法的公正,不能将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相混淆。同时,在处理类似“请托人交付财物于第三人”案件时,应进行两罪存在混淆可能性的评估、预警机制,要有意识的预防对有影响力的行贿罪有可能被当作行贿罪“兜底罪名”而使用的危险。
2.严惩行贿的刑事政策转向。长期以来,国家对贿赂犯罪整体上采取的是“重受贿、轻行贿”的惩治思路,有的办案机关甚至采取查出行贿服务于打击受贿的策略[8]。某种程度上,在腐败犯罪中,行贿罪的认定是可有可无的。既然行贿罪的认定与否无关紧要,对办案机关而言,那在类似案件中将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相混淆似乎也就“无关痛痒”了。因此,要防止出现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混淆,首先就要对“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政策予以调整。可喜的是,严惩行贿的刑事政策转向已经开始,例如很多资料证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正在调整惩治腐败犯罪的策略,从过去的“重受贿轻行贿”、“打击行贿服务于查处受贿”等政策,转变为当下的“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政策[9]。
在严惩行贿的刑事政策转向中,不仅仅包括提高行贿罪的办案率,还要实现对行贿罪的准确认定。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作为行贿罪的“兜底罪名”使用虽然也能实现对请托人的刑事制裁,但毕竟刑法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规定的法定刑要显著低于行贿罪,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放纵了请托人,降低了其行贿的成本。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经济人”的行贿人往往以行贿的经济成本核算作为其行为导向,加强对行贿行为的刑事惩治,提高行贿的犯罪成本,可以从整体上预防贿赂的发生[10]。因此,办案机关应该特别注意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行贿罪可能发生的混淆,防止请托人假借对影响力的人行贿之名行行贿罪之实,这与当前严惩行贿的刑事政策是不谋而合的,也是严惩行贿犯罪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
3.对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法益的厘清。笔者认为,对可能存在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行贿罪的混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将影响力交易犯罪的法益与贿赂犯罪的法益相混淆。认可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侵犯的属于同一或相似法益,实际上为两罪的混淆提供了法益上的“伪装”。即便是从避免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混淆出发,也应当将两罪的法益予以切实的厘清。
由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规定在“贪污贿赂犯罪”一章中,相当观点就认为应将影响力交易犯罪的法益置于贿赂犯罪法益之下进行理解。例如,就有观点认为,“由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属于贿赂罪,而贿赂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11],因此,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侵犯的法益也应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即使有观点考虑到影响力交易犯罪与贿赂犯罪的不同,依然也是在贿赂犯罪法益之下的“修补”,例如,“影响力交易犯罪保护法益是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公正性的信赖[12]。在笔者看来,贿赂的本质在于,它是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有关的,作为不正当报酬的利益,作为贿赂,其所影响的对象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13]。但在影响力交易犯罪中,贿赂的自始至终都不会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发生对价。质言之,影响力交易犯罪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贿赂犯罪,而是诱发、帮助贿赂犯罪的犯罪行为,是贿赂犯罪的外围犯罪[14]。既然如此,影响力交易犯罪的法益就不应在贿赂犯罪的法益中寻求。事实上,笔者更倾向认为影响力交易犯罪的法益是一种不同于贿赂犯罪法益的独立法益的概念。影响力交易犯罪作为贿赂犯罪的上游犯罪,应当认为其体现的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正当行使的威胁,并不具体体现为对职权本身的侵害,因此,其法益的重要性要低于国家工作人员职权的正当性,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而也低于贿赂犯罪本身[15]。
虽然影响交易犯罪的法益与贿赂犯罪的法益相互联系,但两者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不能表现对同一或类似法益的侵犯。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与行贿罪属于属性不同的两种犯罪,两罪可能产生的混淆是不容忽视也是不容允许的。不可否认,将行贿罪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法益的厘清有助于办案机关对两罪的准确把握,以预防两罪可能发生的混淆。
(二)具体操作上的求解
1.攻守同盟的瓦解。在请托人通过第三人行贿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形中,正因为获取证据与破案存在的难度,因此,司法机关应该更加积极的运用行贿罪的特别从宽制度,激励请托人配合司法机关指控受贿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在特别从宽的“诱惑”以及行贿行为证据的不断挖掘的压力下,“攻守同盟”不无被撕裂、瓦解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就避免了请托人的行贿行为被认定为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可能。同时,笔者认为,对“攻守同盟”的撕裂与瓦解适宜双向进行,单边型的特别自首某种程度也上有偏袒行贿人之嫌,“应增加受贿人的特别自首制度,人为制造出受贿者与行贿者的内在紧张关系,行贿人与受贿人共同面临着‘谁先说,谁先从宽’的选择”[16]这样,既可以免于受到放纵行贿人的质疑,也能提高瓦解“攻守同盟”的几率。当然,现行刑法并未有这样的规定,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建言,笔者认为可以增设双边的特别自首制度,以破解“攻守同盟”的难题。
概而言之,在特别从宽对“攻守同盟”的撕裂与瓦解中,不仅可以提高诉讼的效率,也有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避免可能发生的行贿罪与对有影响了的人行贿罪的混淆。
2.第三人的“堡垒”突破。与普通的行贿、受贿单向联系不同,在请托人通过第三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行为中,存在三方主体,这也就意味着在行贿方与受贿方“攻守同盟”的堡垒中多了一个突破口。相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言,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通谋,并实际参与了受贿过程的“设计”,最为知晓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勾当”;而相对于请托人而言,第三人作为收受财物一方,与请托人有实际的接触,对请托人的意图、目的有较为直观的了解与认知。因此,司法机关可以选定第三人作为“堡垒”的突破口。
首先,在一个三方主体中,任何一方的信息的传出都可能造成其他双方的猜疑与紧张,不可否认,第三人的存在实际就成为一般“攻守同盟”中所不具有的不特定因素,实际上,司法机关对特定关系人的突破过程本身足以造成请托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双方的紧张。
其次,在请托人通过第三人行贿国家工作人员情形中,虽然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相通谋,但就犯罪意志而言,其通常不是贿赂犯罪主要的推动者,所以,相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的突破是较为容易的。在此,刑法虽然没有专门针对受贿(其构成共同受贿)的特别从宽制度,但在刑法总则中依然有自首与坦白的规定,在特定关系人未到案的情形下,司法机关可以动员特定关系人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共同受贿罪行的,就可以认定为自首而获得刑法上“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优待;对于已经到案的特定关系人,司法机关可以向特定关系人表明政策,虽然其未主动到案,但只要如实供述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共同受贿罪行的,就构成坦白从而获得刑法上“可以从轻处罚”的对待,如果有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情形,还可以减轻处罚。通过自首、立功的激励作用,也能实现一定程度上特定关系人的“堡垒”突破。无疑,这些都有利于最大程度上挖掘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减少行贿罪与对有影响了的人行贿罪相混淆的可能。
五、结语
腐败是依附于国家政权的寄生虫,是社会的毒瘤,历来为民众所深恶痛绝[17]。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体现出了对腐败犯罪的事前预防,在反腐持续深入的今天,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事实上,对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也会导致某些特殊情形下其与行贿罪的混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这种混淆某种程度上就会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沦为行贿罪的“兜底罪名”。既然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增设目的在于严密腐败犯罪刑事法网,更加严厉的打击腐败犯罪,就应当避免可能造成与行贿罪的混淆,以防止对行贿人的放纵。
提出问题无非是为了解决问题或者避免问题的产生,然而知易行却难,目前来看,由于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是刑法新增设的罪名,尚未有成熟的操作经验来避免两罪可能发生的混淆,这也有待司法机关在以后实践中加以探索和完善。当前,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在处理涉及到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案件时应特别注意,要更加细致认真、最大可能的获取证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定犯罪,从而避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成为行贿罪的“避风港”抑或是“兜底罪名”。
[1]赵秉志.刑法修正案(九)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339.
[2]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207.
[3]劳东燕.揭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面纱—兼论持有与推定的适用规则[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6):53.
[4]于志刚.“关系人”受贿的定罪规制体系之思考[J].人民检察,2009,(7):6.
[6]赵秉志,彭新林.我国当前惩治高官腐败犯罪的法理思考[J].东方法学,2012,(2):94.
[7]苏明月.制度不足与“兜底条款--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理冲突、现实选择与司法应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9):55-56.
[8]吴建雄.司法反腐的法治功能与实现路径[J].人民周刊,2016,(4):53.
[9]何荣功.“行贿与受贿并重处罚”的法治逻辑悖论[J].法学,2015,(10):154.
[10]苗有水.为什么提倡“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N].人民法院报,2015-05-08(6).
[11]魏昌东.《刑法修正案(九)》贿赂犯罪立法修正评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2):29.
[12]张明楷.刑法学(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226.
[13]周光权.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84.
[14]黎 宏.刑法学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526-527.
[15]汪维才.论影响力交易罪的基本构造与转化适用[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683.
[16]袁 彬,徐永伟: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罪刑均衡性问题[C].中国刑法改革与适用研究:全国刑法学术文集(2016年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1545.
[17]魏昌东.《刑法修正案(九)》贿赂犯罪立法修正评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2):29.
[18]赵秉志.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J].当代法学,2013,(3):49.
The Influence of Adding Crime of Offering Bribes to the Influential Person on Conviction of Bribery
XU Yong-wei
The purpose of adding crime of offering bribes to the influential person is to improve anti-corruption law,but there is also the possibility of confusing it with bribery,which results in indulgence to briber and being the miscellaneous charges to bribery.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confusing the two types of crimes and to find ways to avoid confusion,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crime of offering bribes to the influential person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punishment of corruption.
crime of offering bribes to the influential person;crime of offering bribes;the miscellaneous charges;special confession
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12(2017)04-0134-07
(责任编辑:吴良培)
2017-05-03
徐永伟,(1992- ),男,山东诸城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2015级刑法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
——以106份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