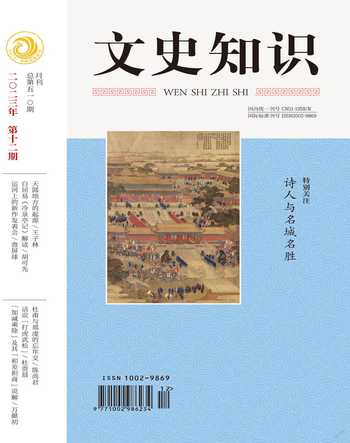话说“打虎武松”
笔者二十馀年间作《论武大郎之死》(《古典小说与传统文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论武大郎之生》(《文史知识》2023年第7期),又续作《漫说“迎儿”》(《文史知识》2023年第8期),乃油然想到说过武大这对可怜的父女,又岂能不说“打虎武松”那“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水浒传》第二十三回)?也不该对那位开窗就使武氏一家解体覆亡的“祸水”潘金莲置之不顾,然后竟也可以就此说“瞧这一家子”了!
另外,尽管其满门“苦主”,但《水浒传》中写唯一有兄弟、夫妻、父女之伦堪称“家庭”的“武大郎一家”,其实是后世“家庭”题材小说流派的“引子”之作。所以武大一家,必说武大、迎儿父女,也必说武大一家聚散存亡的关键—武松、潘金莲。于是又话说“打虎武松”,从“打虎”说起。
一 “武松,天人也”“断曰第一人”
《水浒传》写一百零八好汉,在掺杂各种令人莫名其妙理由的排名中,武松虽仅在“三十六天罡”中列第十四,但论其全人,明清评点家虽有明代怀林和尚《批评水浒传述语》和无名氏《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以李逵“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247—254页),但毕竟金圣叹评改大刀阔斧,铁嘴钢牙,后来居上,影响更大。
金圣叹评《水浒传》以九品论人,虽然也以“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读第五才子书法》,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247—254页),可谓推崇备至。但那只是“看他意思”,金圣叹自己的意思却是“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又曰:
然则《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然而此一百六人也者,固独人人未若武松之绝伦超群。然则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吳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曰第一人,不亦宜乎?
乃至同篇之中三复言之曰:
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
以上金圣叹赞武松似真有知人之明,但武松何以为“天人”“天神”“第一人”的道理,金氏却自言“不知何故”,也就是说他的崇尚武松只是跟着读书的感觉走,从而所说都是“有些”“亦甚”等似云里雾里的话,即使比连“不知何故”感觉也没有者要好,但与其所“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读第五才子书法》)者比,仍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乃所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而已。
“看门道”,就是要找到“打虎武松”使金圣叹惊为“天人”“天神”“第一人”之故。首在溯其根本,从《水浒传》写“武松打虎”的文化积淀其起点与原型说起。
二 “武松打虎”的原型
文学创作难,文学批评亦难。创作难,难在师造化而自主造化;批评难,难在就作者之造化以言造化。则前者可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处,后者唯须察言观色、亦步亦趋。故有“行百里者半九十”,亦有“过犹不及”,从而一世之中,大作家少,大批评家则少之又少。即使自《水浒传》问世流行数百年,“武松打虎”脍炙人口,口评无数,论文无数,于其有无本事、原型之争,仍众说纷纭,无可奈何之下而唯盛赞其描写之好。故明末清初大才子金圣叹评改《水浒传》,虽眼明手快、妙语连珠,也主要是在文笔鉴赏中打转,《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谈“打虎一篇”也不过如此:
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说矣。乃其尤妙者,则又如读庙门榜文后,欲待转身回来一段;风过虎来时,叫声“阿呀”,翻下青石来一段;大虫第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时,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寻思要拖死虎下去,原来使尽气力,手脚都苏软了,正提不动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黑了,惟恐再跳一只出来,且挣扎下冈子去一段;下冈子走不到半路,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叫声“阿呀,今番罢了”一段。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遂与后来沂岭杀虎一篇,更无一笔相犯也。
此评虽亦堪称精彩,但嫌浮光掠影,是如“望屠门而大嚼”的“看热闹”,而非“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看门道”。从而其所赞武松距“天人”“天神”“第一人”,岂止“五十步望百步”之遥!
按自上古宇宙洪荒,“丛林”世界,人兽对立,虎食人虽为常态,但有猛人不得已遭遇“打虎”并且打死老虎的壮举。《诗经·郑风·大叔于田》和《诗经·小雅·小旻》中都有“暴虎”即空手打虎之说,“武松打虎”就是这类“暴虎”现象的反映。其人与事之真假固难考实,但从书中“有一篇古风”,说及卞庄、李存孝等“打虎”,可见“武松打虎”也绝非神话,而是作者创作的“有意味的形式”(〔英〕克莱夫·贝尔著、周金环等译《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4页)。应该结合元明之前传统中“虎文化”可能的内涵上溯其源流,例如《礼记·檀弓下》和萧绎《金楼子》中载孔子与虎有关的两次著名的对谈,其各与“武松打虎”貌似神通,反证了“打虎武松”的真正原型,应该是基于历史上“暴虎”英雄,乃孔子期待中真能“打虎”救世以“替天行道”的理想人物,从而堪称“天人”等。
三 “武松打虎”与“替天行道”
具体说,按《礼记·檀弓下》载: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这个著名的故事赋予“虎(害)”以政治的性质,其“苛政猛于虎”的教训,千古而下至于今,也能发聋振聩,堪称古代读书求道者为民请命、为社会除恶政、为世界开太平的最强发声。孔子把“苛政”比于“虎”而感到更加无可奈何的经典意义,很自然地赋予了“虎”为人之大害而“苛政(更)猛于虎”的社会政治认知。向着这个方向思考必然就是要求“小子”们“打虎”救一方之民,更要扫除“(猛于虎的)苛政”以救天下之民。而这正是“打虎武松”的天赋秉性与人生追求。
《水浒传》写“打虎武松”性格志向与上引孔子“小子识之”云云精神的契合点有二:
一是“武松打虎”于寻兄路上,解除景阳冈一方虎害,造福一方,同时成就了“打虎武松”行侠仗义英雄性格的一面。
二是“梁山好汉”最具时代抗争精神的“替天行道”,最经典的表达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书中直接引用或化用这一表达的至少有十四次之多,而最典型者关乎武松。如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末曰:
直教: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
第三十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中写武松在筵席上把酒“开话道”:
“快活林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营造的屋宇等项买卖,被这蒋门神倚势豪强,公然夺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饭。”……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
武松这种“杀尽不平”和“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的心声,客观上不正是对孔子训教“小子识之”的响应吗?古代以孔子為“至圣先师”,“则天”行事,“武松打虎”,“杀尽不平”,除害救民,一身而集《水浒传》“替天行道”的精神岂不正可以推为“天人”“天神”“第一人”?这才是《水浒传》写“打虎武松”的真妙处。上举金圣叹“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云云,好处只是说得“热闹”而已。
四 “武松打虎”与“上士”人格
《水浒传》全书写三次四人“打虎”(另为李逵、解氏兄弟等)各有不同:解氏兄弟用叉,李逵用刀,唯“武松打虎”是赤手空拳。又“打虎”之法,解氏兄弟用猎人之常技,李逵用刀插虎之肛门,而只有“武松打虎”赤手空拳从虎头下手:
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疙瘩地揪住……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似躺着一个锦布袋。
与此相关,笔者曾有《试论中国古代小说“雅”观“通俗”的读法—以〈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为例》一文(杜贵晨《古典小说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244—255页)引南朝梁萧绎《金楼子》载:
孔子游舍于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与战,揽尾得之,内于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又见《殷芸小说》卷二《周六国前汉人》)
以此与上引“武松打虎”描写相对照,拙文认为以孔子杀虎之论与“李逵杀四虎”之相对照,则知《水浒传》写李逵杀四虎用刀从肛门刺入,绝非“上上”人物;而写“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打死老虎,才是孔子眼中真正的“上士”!
由此可见,文学描写“细节决定成败”:“魔鬼在细节里”,“神灵也在细节里”,一旦从孔子儒学之教明白能“打虎”的均非常人,但“打虎”有“持虎头”“持虎耳”和“捉虎尾”之别,这个“武松打虎”描写包含了以“打虎武松”为孔子心目中“上士”的寓意,就豁然开朗,而可“断曰第一人”。
总而言之,学习传统文化,读诗文须明典故,读通俗小说也要明典故,以治经研史的态度咀嚼品味其熔经铸史的内涵,即所谓“‘雅观‘通俗”,才可以读出作品之真义与作者之深心。以上从“武松打虎”看“打虎武松”,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