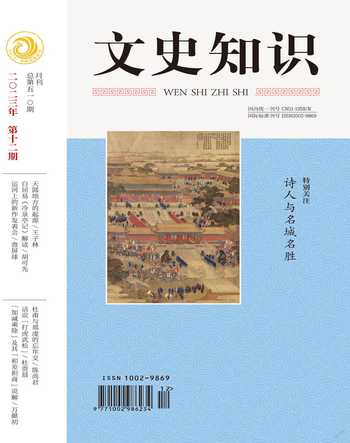陈寅恪与戴望舒的一段交集
龙成松
在现代学术史上,陈寅恪以擅长多种中外古族语文著称,其本人也收藏了数量可观的西方中古语言学论著,并且时常在研究中征引以助诗文、佛典、历史文献考证,往往发人所未发。如在《白香山新乐府笺证》(《元白诗笺证稿》之一)中,他考订白居易《阴山道》中“纥逻敦肥水泉好”一句,引W.Radloff《突厥方言字典》第二册第132页,疑“纥逻”为突厥语Kara之译音,是玄黑或青色之意。又引Radloff同书第三册第1440页,以“敦”为Tunā之对音,为草地之意。合言之,“纥逻敦”或为“青草”之意。其说精审,并且他还辅以了其他旁证,可以定论。但陈寅恪之外,戴望舒有《释“纥逻”、“掉罨子”、“脱稍儿”》一文,其中亦引W.Adlofe《突厥方言辞典》,证“纥逻”为突厥文Khara之对译,意为青色或黑色;“敦”为Tuna之对译,意为草或草原;“纥逻敦肥水泉好”即“青草肥,水泉好”之意。二人之说完全一致。
陈、戴二人,一为史学大家,一为诗坛才子,交集原本极少。刘克敌先生曾撰《道不同亦可为谋—陈寅恪与新文学作家交往漫谈》一文(《中华读书报》2018年7月25日第15版),提及陈寅恪与戴望舒的交往,钩沉发隐,别开生面,但未注意到二人在上面这个“冷门”学术问题上的关系。最早留意此事者似为杨焄先生,他在《诗人转业:戴望舒的古典文学研究》(原刊《澎湃新闻》2016年11月1日,收入《却顾所来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一文中,很有感慨地说:“两人几乎在同时有着同样的判断,参考的工具书竟然也是同一本,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可惜今人所撰白诗注本均径引陈氏之说,并未留意到戴氏的意见。”然二人之说孰先孰后,是否有熏习、传承关系,颇值得一辨。
陈、戴二人所引Radloff(戴本误作Adlofe),今译拉德洛夫(1837—1918),德裔俄国人,是十九、二十世纪之间最伟大的突厥语学者,其《突厥方言字典》(又译《实验突厥方言辞典》《突厥方言词典试编》),是一部囊括突厥语、德语、俄语的巨著,于一八九三年、一八九九年、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一年分四卷在圣彼得堡出版。陈寅恪游学德国期间,即于拉德洛夫曾经学习的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中载,一九二三年赵元任到德国,曾见证陈寅恪等人大买各种书籍之事,称其为“书呆子们”,并有“陈寅恪和傅斯年是宁国府门前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之说法。陈寅恪手中拉德洛夫的书,或即这一时期购入(参唐均《陈寅恪先生的外文庋藏》,《读书》2004年第8期)。陈氏一九三五年撰写的《武曌与佛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册)一文中也曾引突厥语Kara、Kachi、Kara黑暗之意,以此解释《北史·于阗国传》中“达利水”之“达利”。虽然未注明引用拉德洛夫书,但应该不差,可见《阴山道》中“纥逻”为Kara有先见之萌。
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一九五〇年初冬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刊行,后來又经助教黄萱协助修改交由文学古籍刊行社重版。但其书的写作动机、创作过程事实上可以上推到四十年代初。一九四〇年陈寅恪在昆明西南联大为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就有“白居易研究”课。一九四四年,在成都已完成书中“附论”《长恨歌笺证》《琵琶行笺证》等九篇,但未及《新乐府》诸篇。一九四六年陈氏有《来英治目疾无效将返国写刻近撰元白诗笺证》诗,其中说“归写香山新乐府”,证明当时《新乐府》部分尚未完成。一九四七年先生仍在修改在成都所撰《元白诗笺证稿》诸篇。据此可知其《新乐府》诸篇的笺证工作,或许就完成于这一时期。
另外一个旁证是,《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录陈寅恪自述,一九四七年冬因为天寒无经费取暖,曾将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其中“突厥文字典”或包括拉德洛夫的《突厥方言字典》。高山杉先生复原的北大东语系所购陈寅恪藏书残目,有拉德洛夫著作、论文九种,包括《蒙古出土古代突厥语碑铭》《北方突厥语语音学》《古突厥语译〈十方平安经〉》《突厥语部族民间文学样本》等(参《北京大学东语系所购陈寅恪藏书残目》,《中国文化》2020年第2期),其中并未包括此书。另外,陈寅恪去世后,其弟子蒋天枢整理他的一批外文书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计320馀种,640馀册(参刘经富、冯丽平《从陈寅恪外文藏书书目看其学贯中西》,《文史知识》2019年第6期),其中也未见《突厥方言字典》一书,陈氏所藏下落不明。
无论如何,陈寅恪《阴山道》诗笺证中引用了拉德洛夫书的第二、三册,且有具体页码,说明当时书尚在身边。综合来看,这一部分内容应该完成于一九四七年。当然,其想法的萌芽、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可能早在三十年代,即与陈寅恪专注西北史地之学尤其是突厥学的时间相当。
戴望舒《释“纥逻”、“掉罨子”、“脱稍儿”》一文创作的具体时间不详,收入吴晓铃根据戴望舒遗稿整理的《小说戏曲论集》中,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同编中还收录了《释“盆吊”》《释“掤扒”》等文,都是考释古典诗文、戏文、小说中方言、俗语的作品,应该大致创作于同一时期。戴望舒早年就关注小说戏曲问题,三十年代他旅欧期间就积极寻访和收集海外通俗文学汉籍,并且还校点过《豆棚闲话》《石点头》等明清小说。但他撰写相关研究文章似乎是从四十年代开始。其契机应该是一九四一年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俗文学》周刊之际。在《俗文学》第一期“编者致语”中,戴望舒阐释了办刊的宗旨:(一)本刊每周出版一次,以中国前代戏曲小说为研究主要对象,承静安先生遗志,继鲁迅先生馀业,意在整理文学遗产,阐明民族形式。(二)本刊登载诸家对于戏曲小说研究最近之心得,以及重要文献,陈说泛论,概不列入,除函约诸专家执笔外,并欢迎各界投稿。可见戴望舒对于古典戏曲小说的持续热情。
据关家铮《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总目》著录,该刊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首发,每周六出版一次,至同年十二月六日停刊,共出版了四十三期。其供稿者包括当时古典文学、语言学研究大家如孙楷第、赵景深、叶德均、浦江清、罗常培、谭正璧、冯沅君、吴晓铃等。其中吴晓铃的文章最多,计十六篇。戴望舒本人也在上面发表文章六篇,其中四篇收录在《小说戏曲论集》中,两篇未收入。但这些文章中并不包括《释“纥逻”、“掉罨子”、“脱稍儿”》一文,也没有见到考释俗语、方言词汇的论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沦陷,次年春戴望舒入狱,出狱后继续为一些报刊当编辑和作者。自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他在《大众周报》开设“广东俗语图解”专栏,前后创作短文有八十一篇。这些文章虽然其中也没有《释“纥逻”、“掉罨子”、“脱稍儿”》一文,但可以看到戴望舒兴趣和写作方法的转移。此后一直到一九五〇年去世之前,戴望舒還陆续有研究古典小说、戏剧的作品。
巧合的是,四十年代初陈寅恪也在香港,并与戴望舒有交集。一九四〇年夏,陈寅恪拟经香港赴英,因欧洲战事搁置,遂留香港大学为客座教授。次年,除两次返回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外,一直在港。一九四二年五月始经广州返回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陈寅恪在港时,关注到了戴望舒主编的《俗文学》周刊。《陈寅恪书信集》中收录陈氏《致戴望舒》一通:
敬启者,顷读
贵刊第二十九期吴晓铃先生《〈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论据精确,钦服至极。鄙意《青楼集序》中所谓“商颜黄公之裔孙”其实即指夏氏而言。盖商山四皓中有夏黄公一人,夏伯和自可目之为“商颜黄公之裔孙”也。叶郋园、吴晓玲二先生俱精于曲学,夙所景仰,并与寅恪有一日之雅,以读郋序,偶有所得,辨所不必辨,特陈妄谬之见,质正
高贵,兼以求教于世之读
贵刊者。顺颂
望舒先生 撰祺
弟陈寅恪拜启(一九四一年)十月廿五
文后还附了一段简短的辨析文字。该信函刊载于当年《俗文学》第四十一期,作“陈寅恪先生来函:谈《青楼集》作者的姓名”。这也是比较罕见的戴望舒和陈寅恪直接交往的证据。一九四三年以后,陈、戴二人未有同时、同域的机会,亦未见文字之交。
回过头来看戴说与陈说的关系,很难确定孰先孰后,也很难确定是二人意见互有冥合,还是二人经过交流后互相借鉴。无论如何,二人在民族语文研究方面的贡献都是不容抹杀的。陈自不必说,戴的功劳则仍有申说的必要。《小说戏曲论集》中所收录的戴氏考释俗语、方言短文,显示了戴氏作为文学家对于语言的敏感,尤其是小处着眼的方法。一字、一词之句读、校勘、补遗,虽然琐碎,但不失真见。另外,古方言、俗语尤其是元曲中蒙古语的考释,戴氏虽非专门研究者,但能注意各种对音资料,或采纳辞典及他人之说,实属难能可贵,且富有远见卓识。除前述《释“纥逻”、“掉罨子”、“脱稍儿”》文中引用《突厥方言辞典》的例子外,又如《跋〈元曲金钱记〉》中引用吉川幸次郎的《广东语之发音》;《释“葫芦提”、“酩子里”》引用蒙古语“Tein bolai”;《谈元曲的蒙古方言》一文关注了吉川幸次郎在编的《元曲辞典》及《读元曲选记》中元曲语言,并引用《华夷译语》解释关汉卿元杂剧中的蒙古语词汇。方贵龄在其《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一书中,多次提及戴望舒对于元曲中蒙古语考释的功劳。可以说,戴氏在古民族语研究中已颇有一些特色,并与陈寅恪“审音勘同”之法冥然契合。作为现代文学史、史学史上不同方向的两位大家,同时注意到了一个细微的对音问题,这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中外学术“预流”的微观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