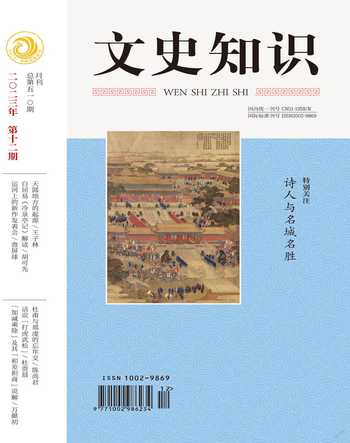运河上的新作发表会
查屏球
文学经典往往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作家天才创造力与艺术追求的自觉性固然是决定性因素,而这种创造力与自觉性得以展现,还与具体的创作活动相关。研究者通过文献考古,尽可能还原作家创作活动细节,建构作家创作时特定的思维场域,探究激发作家创作力爆发的具体因素,可对作品的经典性有更深认识。刘禹锡、白居易在扬州有过一场诗会,刘发表了近作《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并留下“扬州初逢”酬唱诗,事成佳话,诗为经典,自唐以来就为诸多诗话或诗选载录,今人亦有研究(参刘怀荣《刘禹锡、白居易“扬州唱和”及其文学史意义》,《中国诗歌研究》第2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然而,从实际交通线路看,刘禹锡由和州到洛阳,扬州不是必经之路,他可直接北上,经寿州达汝、颍入洛阳,全程约一千五百里,用时约一个月。如刘禹锡作有《和州送钱侍御自宣州幕拜官便于华州觐省》,所送者为钱徽之子钱可复,其由宣州到华州,在当涂县(属宣州)过江,再经和州直接北上。若走扬州,则需先沿江东行再过江北上,多出近三百里。如此舍近求远,应别有他因。以下即通过解析此事,对相关的作品作进一步的笺解。
一 选走热线官道,高调复出
宝历二年(826),苏州刺史白居易五十五岁,二月末坠马受伤,卧床一月,五月末又以眼病及肺伤再请假百日,九月初假满离职,沿京杭运河过瓜洲渡到达扬州。同时,与他同龄的刘禹锡在八月也结束了和州刺史任职,十月与白居易相会于扬州,再共同沿运河北上。二人旅程一样,但感受却大有不同。白居易从元和十年(815)外贬至江州司马到忠州刺史,再到杭、苏州刺史,先后在州郡任职十多年,其中杭、苏两任都是出于自愿,结束苏州任职也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对白而言,只因年老体衰而结束外放生涯;对于刘禹锡来说,却是一次关乎后半生命运的大转折,意义非凡。
刘禹锡自永贞元年(805)随八司马外谪至朗州司马之后,长期遭受政治迫害,《旧唐书·宪宗纪》:“(八月)壬午,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唐宪宗还说:“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旧唐书·刘禹锡传》)元和一朝,他在政治上已被判了死刑。朗州司马十年,连州刺史五年,至穆宗即位才有转变,先量移夔州再到和州,外谪二十二年。至和州时,元和宿敌已少,安在身上的政治紧箍咒渐有松动,他与政坛中心交往才明显增多,如汴州的令狐楚、润州的李德裕、越州的元稹,都是宰相级人物,他到和州后与他们频繁进行诗歌交往。如:
与令狐楚:《客有话汴州新政书事寄令狐相公》《和令狐相公郡斋对紫薇花》《令狐相公见示河中杨少尹赠答兼命继声》《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镇改月偶书所怀二十二韵》。
与李德裕:《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示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山喜径松成阴怅然怀古偶题临江亭并浙东元相公所和》《和浙西李大夫伊川卜居》。
与元稹:《遥和韩睦州元相公二君子》《和浙西李大夫示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山喜径松成阴怅然怀古偶题临江亭并浙东元相公所和》。
北上归京,更表明刘禹锡已恢复到谪前待遇了。其舍近求远,就是要借助官道官驿之便,增加与沿途州官交流的机会。其在扬州有《谢寺双桧》,在楚州有《楚州开元寺北院枸杞临井繁茂可观群贤赋诗因以继和》《罢郡归洛途次山阳留辞郭中丞使君》《韩信庙》《岁杪将发楚州呈乐天》,在汴州作《令狐相公俯赠篇章斐然仰谢》,一路写诗,频频出席州官诗会。由李翱《来南录》(《全唐文》卷六三八)所述看,从淮阴到洛阳,一千八百里,常规行程三十天左右。这是主要官道,也是一条信息散布热线,沿途的活动,为他的复归做了广告,等到汴州时已为众人关注了。刘禹锡为人旷达乐观,好强不服输,被贬十年,归京后仍讥讽权贵:“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结果招致再贬。这一次,他选择走官道,沿途发表新作,就是以一种高调方式向世人宣布自己的回归。如在楚州,他作《韩信庙》言:“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一吐二十多年被压抑的痛苦,比起前一首“玄都观”诗情感更强烈,人未至京,后一首“玄都观”诗中“前度刘郎今又来”情绪已开始流露了。
元和再贬之后,刘禹锡的政治热情已经下降,专力于诗,并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取法楚地民歌改造竹枝词,一是以学识为基础加强咏史怀古诗的学人色彩与思考深度。前者尚有张王元白乐府与之同质,而后者则是他的独创,无人比肩,兴致更浓。为重返诗坛中心,他已做了较长时间的准备。由夔州转和州,刘禹锡境遇略有改善,诗兴渐高,不断向诗坛推出新作,并集中写了一批咏史怀古诗。如:《西塞山怀古》《经檀道济故垒》《金陵五题》《金陵怀古》等。到扬州后,他向白居易展示的就是《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他想以这类别具一格的新作来宣示自己的复归(参拙文《刘禹锡咏史诗在大和初的影响—兼论中晚唐诗歌学人气渐显之趋向》,《晋阳学刊》2015年第4期)。因此,刘、白扬州之会,也是刘禹锡有意选择的新作发表会,是他重返诗坛中心的“首秀”之举。
二 东行游历,修改《金陵五题》
由《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二诗写作过程看,刘禹锡为这次新作发表做了精心准备。此前多认为《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都作于长庆四年(824)秋即初来和州时,实误。《西塞山怀古》有言“故壘萧萧芦荻秋”,明言作于秋季,而《金陵五题》则不同时,其序及诗曰:
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欻然有得。它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余四韵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尔。
《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台城》:“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生公讲堂》:“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江令宅》:“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池台竹榭三亩馀,至今人道江家宅。”(《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390—397页。文中所引刘禹锡诗文皆出于此书,不另注)
诗序言写诗时尚未到过金陵。其来和州是长庆四年秋,而诗中所叙是春天景象,如“朱雀桥边野草花”“结绮临春事最奢”等,皆写春色。其《金陵怀古》所叙季节也与之相同: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诗言“新草绿”,更明确表明时在春季。虽然,他在和州经历了宝历元年与二年的春天,和州与金陵仅隔江相望,但是,依照唐朝法律,作为和州刺史,他是不可以离开和州境而进入到润州的。《唐律疏义》卷九专列“刺史县令私出界”处罚规定:
诸刺史、县令、折冲、果毅,私自出界者,杖一百。疏义曰:“州县有境界,折冲府有地团,不因公事私自出境界者杖一百。注云:“经宿乃坐”,既不云经日,即非百刻之限,但是经宿,即合此坐。
因此,写春景的《金陵五题》《金陵怀古》应是他在和州时的悬想之辞。序言“它日”是指在扬州与白居易相会之时,时在宝历二年初冬。诗与序写作时间不同,序是在诗之后补写的,诗应作于宝历元年或二年之春,而非宝历二年的秋天。
细究文本还可见出,诗虽是想象之辞,然而所写之情景,如“夜深还过女墙来”“一方明月可中庭”,似乎写出了身临其“景”的感觉;《金陵怀古》诗中所列四个地名与《金陵五题》所言五地不重复:一石头城二乌衣巷三台城四生公讲堂五江令宅六冶城七征虏亭八蔡洲九幕府山,多处都在秦淮河边,基本上是围绕金陵城绕场一周。这种空间感与秩序性表明他可能到过现场。
由刘禹锡存诗看,这种“亲临感”是他在事后加工的结果。宝历二年秋,他结束和州刺史职任之后,在北上途中,专程游访了江宁,留有二诗记其事:
《罢和州游建康》:秋水清无力,寒山暮多思。官闲不计程,遍上南朝寺。
《台城怀古》: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宫墙隐嶙围野泽,鹳鶂夜鸣秋色深。
诗中明言“秋水”“秋色”,其到江宁尚在秋季。刘禹锡约于八月底九月初离开和州,约在十月中旬。从和州到扬州,三百里,正常行程不超过六天,实际上是走了近一个多月,其诗言“官闲不计程,遍上南朝寺”。遍游江宁,仅留下一首《台城怀古》,显然,其凭吊怀古之诗兴,已在《金陵五题》《金陵怀古》中抒发殆尽了,无须再写。《金陵五题》《金陵怀古》中的实景感与空间感,可能就是刘禹锡在经过实地考察后获得的,并据此对前作有了加工与修改。序言未到过金陵,只是记录了写作初稿时的状况。实际上,《金陵五题》从构思到修改再到完善,经历了二年。为修改旧作,刘禹锡花了近一个多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对实景的真切感受,如“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从总体上看,秦淮河流经石头城的西南,言“淮水东边”似误,但若身处石头城中,可感觉到月升东南,照在秦淮河上,故可言“淮水东边旧时月”,不到实地,很难做出这种想象,且其景象极具秋意,应是注入了这一次漫游时的感受。所以,在会面中,刘发表的是旧诗,也是新加工的近作。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也是在这次发表的,这是二年前的作品。宋时彭叔夏将本诗集本与《唐宋类诗》所录传本对校,发现异文颇多,见以下括号内的标注: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漠(“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荒苑至今生茂草”),山形(“古城”)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而今四海归皇化”),故垒(“两岸”)萧萧芦荻秋。(《文苑英华》卷三〇八)
异文表明《西塞山怀古》也经过后期修改,其经西塞山是在长庆四年秋,“生茂草”可能是原初的想象之辞,在扬州发表的仍是初稿,事后又有所改动。
《西塞山怀古》与《金陵五题》一为七律,一为七绝,诗体不同,在艺术思维上却是一脉相承的,《西塞山怀古》成功之处,就是善于以细节如“王濬楼船”“铁锁沉江”“一片降幡”等,将人带入具体的时空情景中,又以具体的场景沟通古今,如“山形依旧枕寒流”“故垒萧萧芦荻秋”,让人在特定的氛围中感受历史的运势。《金陵五题》对此更有发挥,不是以历史题材作为某一观点的论据,也不是像引用典故一样,只取用历史与结论之间固定的关系,不站在道德制高点作是非对错的判断,而是引人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思考,感叹人在历史的运势面前的无奈与伤感,诗人是咏史而不是写作史论。这种艺术意境表达了一代学人对整个时代的感受,拉开了晚唐感伤诗风的序幕。自此之后,这种意调与抒情模式在晚唐诗中屡屡出现。由刘禹锡这段时间对这类诗的集中书写与反复修改看,他对这种探索是非常自觉的,北归途中专访金陵,就是为修改旧作而做实地考察。
三 脱禁之后的直面交流
刘白二人出发时间不同,能在扬州会面,不是出于偶然,事先应有约定,这是他们后半世相伴相交的开始,也是他们在宝历年间情感交流的结果,“扬州初逢”的酬唱是他们情感交流、诗艺切磋的大会集。诗曰:
白居易《醉贈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筯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706—1707页。本文所引白氏诗文均出于此,不另注)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二诗都非常成功,在后世也有极强的接受效应。《旧唐书·刘禹锡传》记: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則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史家所据是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文中所引诗句表明扬州诗会在刘白酬唱活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这类社交化礼仪化写作活动中,两人却能脱略格式化的语言与章法,突出了久别重逢后的沧桑感,有很强的感染力。由具体创作环境看,这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
其一,和州、苏州近二年唱和,刘、白二人已由相识到相知,由一般读者上升为知心诗友。刘、白少年时代即有交往(见下文注),诗歌交往可能始于元和五年,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言:“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已准确地总结出白诗力求自然的风格。其时元、白两人既以新乐府及《长恨歌》大得声名,又以酬唱诗而成为流行明星。由于忌惮永贞党人的恶名,元和一朝刘、白交往并不多。长庆三年春,白居易把《杭州春望》分寄元稹、刘禹锡,刘禹锡作《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诗有柳色春藏苏小家之句因而戏酬兼寄浙东元相公》回应,说:“莫道骚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已被边缘化的刘禹锡,只能随众说出一些社交化的赞辞。长庆末,随着政治禁忌的解除,两人关系渐密,尤其是白居易到苏州任刺史后,唱和频繁,双方写作心态、表达方式、交往方式都有所变化。起初,刘禹锡多主动和白诗,如长庆四年底或宝历元年春,白居易由杭州返洛阳途中作有《真娘墓》《看常州柘枝赠贾使君》,刘禹锡在和州就和了这两首诗,后刘禹锡又作《和乐天鹦鹉》。宝历元年夏白居易到苏州后,白居易主动倡发增多,如宝历元年新春,刘禹锡作《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送给在洛阳的白居易,半年后,白居易至苏州后才作和诗《答刘和州禹锡》,后又作《白舍人见酬拙诗因以寄谢》回应;刘禹锡酬之以《白舍人曹长寄新诗有游宴之盛因以戏酬》,白居易马上以《酬刘和州戏赠》回应;白作《别苏州》,刘作《白太守行》,白居易随后应之以《答刘禹锡白太守行》。之前,对刘禹锡这样的边缘者,白居易多持有居高临下的同情心态。如白居易宝历元年秋《答刘和州禹锡》:“换印虽频命未通,历阳湖上又秋风。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我亦思归田舍下,君应厌卧郡斋中。好相收拾为闲伴,年齿官班约略同。”既同情刘才高运舛,又认为自己是其“闲伴”,以“年齿官班约略同”来拉近与对方的距离,其实年齿相同,官班大不相同。唐代州的等级分成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级,苏州为雄州,和州仅为上州,二者之间差三级。之后白诗中敬意渐增,谦辞更多。“不似刘郎无景行”,“敢有文章替左司”。“上愧刘君辞”,并为自己能与刘“同做千里伴”而兴奋。解除了政治禁忌,情感交流进入到无拘无束的诗家境界,扬州诗会中所写的“添酒饮”“击盘歌”“长精神”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其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都参与了几次集体性创作活动,有过同台竞技经历。如:刘禹锡有《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镇改月偶书所怀二十二韵》,白居易有《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二十二韵(同用淹字)》;刘有《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觱篥歌依本韵》,白有《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和浙西李大夫)》;刘有《楚州开元寺北院枸杞临井繁茂可观群贤赋诗因以继和》,白有《和郭使君题枸杞》,这是三次规模较大的诗会,虽各有风格,但在总体上白诗礼仪化社交化模式更明显,刘更重整饰雅致。其中李德裕发起的“听小童觱篥歌”,不仅有刘、白,还有元稹、张祜多人参加。关于音乐形象,二人有如下描写:
刘禹锡:长江凝练树无风,浏栗一声霄汉中。涵胡画角怨边草,萧瑟清蝉吟野丛。冲融顿挫心使指,雄吼如风转如水。思妇多情珠泪垂,仙禽欲舞双翅起。郡人寂听衣满霜,江城月斜楼影长。才惊指下繁韵息,已见树杪明星光。
白居易:山头江底何悄悄,猿声不喘鱼龙听。翕然声作疑管裂,诎然声尽疑刀截。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急声圆转促不断,轹轹辚辚似珠贯。缓声展引长有条,有条直直如笔描。下声乍坠石沉重,高声忽举云飘萧。
白居易在十年前已有《琵琶行》成功经验,写音乐形象应是他的长项。他以周边之静衬托乐声之引人,以有形之象叙写乐之旋律、节奏、音调之变化,但基本不出《琵琶行》路数,其中“急声圆转促不断,轹轹辚辚似珠贯”,与《琵琶行》中的“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意象多有重复之嫌,且全诗用语也较随意;刘诗以有声形象江涛、军号、蝉吟来比拟音响,以“心使”“转风”夸饰技法,以妇泪、禽舞渲染艺术效果,似更有创意。白居易可能就是缘此认识到刘的诗才过人之处,扬州诗会上,又以第一读者身份欣赏了刘的《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新作,对刘之创造力愈生敬意,其“国手”之论是有感而发的。
其三,扬州之会是他们交流最密之时。两人都在九月离任,都有意把归程安排得很宽松。如刘禹锡《罢和州游建康》言:“官闲不计程,遍上南朝寺。”白居易《自问行何迟》也说:“何必冒风水,促促赴程归。”他们都想在这一行程中享受“无官一身轻”的愉快,除了沿途观光交往,还结伴共游。刘约在九月上旬就离开和州开始建康之游,可能于十月中旬到达扬州;白在十月初才离开苏州(白居易《华严经社石记》)。在十月下旬在扬子津与刘会面,又一同游扬州半月,白居易《与梦得同登栖灵塔》言:“半月悠悠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又花了二十天由扬州到达楚州。白居易《自问行何迟》言:“前月发京口,今辰次淮涯。二旬四百里,自问行何迟?……逢山辄倚棹,遇寺多题诗。酒醒夜深后,睡足日高时。”约在十二月上旬到达楚州,又停留到月底才再北返。刘禹锡《岁杪将发楚州呈乐天》(楚泽雪初霁,楚城春欲归。清淮变寒色,远树含清晖。原野已多思,风霜潜减威。与君同旅雁,北向刷毛衣。)、白居易《除日答梦得同发楚州》(共作千里伴,俱为一郡回。岁阴中路尽,乡思先春来。山雪晚犹在,淮冰晴欲开。归欤吟可作,休恋主人杯。)都记下他们将于宝历二年除夕出发。从楚州到洛阳,行程一千四百里,用时约需一个月,故到达洛阳时,已是阳春二月了。如白居易《初到洛下闲游》言:“趁伴入朝应老丑,寻春放醉尚粗豪。”《罢郡归洛阳闲居》言:“花间数盏酒,月下一张琴。”所叙初到洛阳的景象,已有春花开放了。因此,这次北归旅程中,两人同处了三个多月,这是他们有意设计出来的诗会交流。在这一活动中,白居易更真切地认识了刘禹锡的人格与诗格,消除了元和以来污名化的印象,并对刘之蹉跎有了更多的不平之气与同情之意。
依据上述,可对二诗作出更具体的解析:(1)诗题问题:由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题看,白应先有一诗,题为“扬州初逢席上赠刘二十八使君”,其集中《席上答微之》《裴令公席上赠别梦得》《春夜宴席上戏赠裴淄州》等与之近似,现传诗题《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应是后来改动过的,或者是在事后换了一首新诗。扬州酬唱之作只是初稿,今所见之定稿是出于事后的修改[初逢,是指久别初逢,而非平生第一次见。刘、白二人可能相识于青少年时期。白居易有《初见刘二十八郎中有感》:“欲话毗陵君反袂,欲言夏口我沾衣。谁知临老相逢日,悲叹声多语笑稀。”作于大和五年(831)刘禹锡赴苏州任途中与白在洛阳相见之时。其中毗陵、夏口似指家丧之事。他们少年时都曾随父居于埇桥。刘禹锡《子刘子自传》:“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遂及大乱,举族东迁,以违患难。因为东诸侯所用,后为浙西从仕,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埇桥。其后罢归浙右,至扬州遇疾不讳。”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公讳季庚……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公与本州刺史李洧潜谋以徐州及埇口城归国……又除检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别驾。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终于襄阳官舍。”夏口属襄阳(山南道),故毗陵、夏口或指刘、白父亲亡故之事,两地或为二人奔丧之所。题中“初见”也是指久别初见],从初稿到定稿经历了三个月。(2)写作时间问题:从前注家都系这两诗与扬州诗会诗于宝历二年,但从刘禹锡贬谪时贞元元年(785)到扬州相会的宝历二年,仅有二十二年,诗中却言“二十三年折太多”“二十三年弃置身”。此前注家解释是诗家记忆有误,或为调合平仄有意变“二”为“三”,实有牵强之处。误记,不可能两人同时发生;“三”字在二诗中都处在可平可仄的位置,无须勉强调合。由上文列述的行止看,他们回到洛阳已是次年二月了,二诗最后定稿的时间就是大和元年二月,这则与“二十三”相合了,也与诗中所叙“万木春”之景相合。(3)白诗中“长寂寞”“独蹉跎”直接内容应是为刘禹锡回洛后未得新职而感伤。刘禹锡贞元九年进士,永贞元年为员外郎(从六品),沦落了二十三年,尚无新职(迟至六月或八月才授为主客郎中,从五品。)白居易与刘同岁,进士及第比刘晚七年,二月回到洛阳三月就授新职,由苏州刺史升为秘书监(从三品),由绯转紫。与白比较,刘的悲剧命运尤显悲惨,白之不平与嫉愤之中还含有愧疚与同情,刘在理解到对方用心后,也无奈地自认“沉舟”“病树”。(4)刘诗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叙就是他们在运河上所见到的实景,三个月里,他们一直沿着运河北上西进,既可见到沉舟,也可见到千帆竞发景象。到洛阳时,已是初春时节,也会见到万木争春的风光。诗家之妙就在于以当前之景中发现自我,如感叹“尽是刘郎去后栽”一样,既讽刺了新贵,又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
结语
这场发生在运河上的诗会,当时就在长安诗坛产生了反响,到了五代时何光远(900—959?)还编出了有关这一场诗会的故事,其《鉴诫录》卷七《四公会》言:
长庆中,元微之、刘梦得、韦楚客同会白乐天之居,论南朝兴废之事。乐天曰:“古者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今群公毕集,不可徒然,请各赋《金陵怀古》一篇,韵则任意择用。”时梦得方在郎署,元公已在翰林。刘骋其俊才,略无逊让,满斟一巨杯,请为首唱。饮讫不劳思忖,一笔而成。白公览诗曰:“四人探骊,吾子先获其珠,所馀鳞甲何用。”三公于是罢唱,但取刘诗吟味竟日,沉醉而散。刘诗曰:“王濬楼船下益州……”(《知不足斋从书》第二十二集《重雕足本〈鉴诫录〉十卷》,后蜀何光远撰,嘉庆八年覆天籁阁藏宋本)
《唐故处士韦君墓志铭》(《长安家族葬地出土墓志辑纂》,商务印书馆,2018,484页。引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载,韦楚客二十八卒于元和九年,而刘禹锡这首诗,是在长庆四年出任和州刺史经过西塞山时写的;“四公会”故事时间是在长庆中,在韦楚客卒后;所叙诗题是《金陵怀古》,诗句却是《西塞山怀古》,也见出虚构不实之处。不过,这一传闻也反映了一个事实:《西塞山怀古》与《金陵五题》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接受效应,推以实情,这种发表效应首先在扬州发生。刘禹锡咏史怀古诗一经发表,不僅惊艳了诗坛领袖白居易,也征服了整个诗坛,时人竞相仿效,元和以来的诗风走向也有所改变,在元轻白俗中增入了学人气与厚重感。三百年后,这些新型因素在宋诗中渐成主流,学人之诗大成气候。刘诗地位不断升高,如洪迈《绝唱不可和》言:
刘梦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乐天以为后之诗人无复措词。坡公仿之曰:“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语惊世,如追和陶诗,真与之齐驱,独此二者,比之韦、刘为不侔,岂非绝唱寡和,理自应尔邪!(《容斋随笔》卷一四,中华书局,2005,184—185页)
苏轼、洪迈等正是从刘诗中感受到与宋人学人化诗学理念契合的魅力,才以为刘诗是不可复制的诗家绝唱。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白扬州诗会,在古典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细理《金陵五题》及刘、白扬州酬唱诗创作过程,可发现名作产生含有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两个方面。深邃的学识、细节的掌握,对历史衰势的无奈与伤感,这是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创新点;对己受冤的悲愤,对人遭辱的同情,分别是刘白相会时的情绪,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判断出来的必然因素。诗起于悬想成于实地考察,二十多年后重逢并能同行百日,修改初赠之作,这些又是产生《金陵五题》与刘白扬州酬唱诗的特殊因素,尤其是白居易作为第一读者长时间近距离感受刘诗之魅力,更是激发白居易诗情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没有预设的偶然因素,多被作品正文过滤了。古典研究就是要从残简断片中找出这两方面的因素,尽可能拼合历史真相,才能推进读者不断地接近文本世界,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体验诗情的厚度,展开古今对话,发现那些能标志一代诗风走向经典的内在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