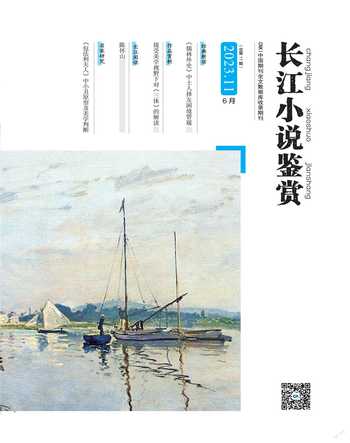恐惧与逃避
[摘 要] 《索拉里斯星》是一个关于恐惧的故事,作者莱姆将主角凯尔文的自我转置为一种实体景观,并通过描写其自我秩序与世界认知在面对这一实体景观时被彻底打碎的过程,着力探讨人类的“自我之惧”。段义孚认为,人拥有“他性”这一根本特点,而这一特点导致孤独感与分离感的产生,使得人趋向于在群体与社会文化活动中逃避自我。在索拉里斯星上,只有四位互不沟通的男性科学家和由他们的自我转置而来的“客人”,这种设定让主角在面对自我的深渊与宇宙的冷漠时无处可逃。最后,主角凯尔文达成了与“自我”和宇宙的和解,转向信服一种“有缺陷”的上帝。本文通过论述《索拉里斯星》中的恐惧景观与逃避主义,探究在一种宇宙性的荒诞背景下,“自我”如何成为一种恐惧的景观以及逃避路径。
[关键词] 宇宙性荒诞 恐惧景观 自我 他者 逃避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41-05
一、宇宙性的荒诞
段义孚提出了一种观点:相较于自然的残酷来说,冷漠更加可怕。“生命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存在。从根本上讲,无机界——不仅包括外太空或冷或热的物质,还包括地球上坚硬的岩石——对人类的计划、健康以及生命毫不关心。”[1]这种宇宙对人类的漠不关心,即是一种荒诞。“荒诞”的概念由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提出。所谓荒诞,就是世界的非理性同人们执意弄明白的渴望之间的冲突,是人的呼唤与世界毫无理性的沉默之间的对峙。《索拉里斯星》中,这种荒诞被扩展到了更广阔的星系,呈现出一种“宇宙性的荒诞”:不仅是无机界对于人类的呼唤毫不回应,地外文明对于人类的探索也置若罔闻。这种宇宙性的荒诞使人类与外星文明“神圣的接触”成了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展现出莱姆对科学根基的思考。
“拟人化”是人类试图对抗宇宙之冷漠的方式。段义孚指出:“自然的冷漠使人类难以忍受,以至于人类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征服大自然……(人们把)飓风看作是追击人类的恶棍,而且还将此视为一场追逐着人类的游戏。即使是国家气象局也接受了这种拟人化的模式,气象学家将热带风暴叫作卡米尔、雨果、弗兰或是安德鲁,现代人对此已司空见惯,一点儿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1]《索拉里斯星》中,科學家们也试图将索拉里斯海洋拟人化。但是,这种“拟人化”反而加剧了人类与自然间的对立,使得宇宙性荒诞更为深刻地浮现出来。莱姆认为:“在《索拉里斯星》中,我试图提出一个问题,即在太空中遇到一种既非人类也非人形的存在形式。……我想切断所有导致外星生物‘人化的线索,比如,索拉里亚海洋。因此,与它的接触不能遵循人类之间的模式——尽管这种接触确实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发生。”①因为这种对于科学和人类认识局限性的反思,莱姆的小说被贴上“元科学小说”的标签。
在《索拉里斯星》中,索拉里斯海洋是十分具有隐喻性的。索拉里斯海洋的存在是一个不可言说、无法解释的“切实存在之物”,其存在的方式与主角科学家们对其存在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科学家们无法与索拉里斯海洋进行任何层面上的沟通,只能用一种拟人化的手法形容与描述海洋的行为。各种观点浩如烟海,无一不指向一个事实:这些“科学研究”都建立在一种高度主观、高度个人化的基础上,没有一个能刺破索拉里斯海洋展现出的表象,进入其真实的存在领域,而是将认识论以强迫的方式凌驾于一个不可认知的事物之上。索拉里斯学是莱姆的另一个隐喻,即人类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其“拟人化”的探究目的并非为了尊重,而是为了同化。但沉默是无法同化的,人类无法通过演说自我来通向他者。从这种角度来看,宇宙的荒诞性是无法克服的。
将他者纳入自己的话语秩序也是人类克服宇宙之荒诞的努力。由于推测索拉里斯海洋可能会对高能射线做出反应,科学家们对索拉里斯海洋进行了一种X射线实验,用能量很高的X射线对海洋进行照射,而这种X射线因为具有致命性已经被联合国公约禁止使用。然而,面对科学家们的尝试,索拉里斯海洋保持沉默。科学家们的射线实验可以视为一种沟通的尝试,他们试图以一种“科学的语言”唤起索拉里斯海洋的回应。《逃避主义》中,段义孚提示人们应当注意语言对人类逃避宇宙冷漠的重要作用:“因为语言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如果没有语言,很难想象人类是如何改造世界、如何掩饰和如何逃避的。”[1]语言是人与人建立联系的纽带,每一个集体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从而将自己与其他集体区分开来。这种内部的凝聚力给予人类一种基于封闭世界的统一感与归属感,而不被了解的他者则被排除在外。基于此,人类科学家为索拉里斯星创造的“科学话语”则是人类试图将索拉里斯海洋纳入认知集体的尝试。
然而,索拉里斯海洋始终保持沉默。这“语言-沉默”的对比似乎暗示了科学家与作为他者的索拉里斯海洋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然而,此处索拉里斯海洋的沉默却具有一种兼含反叛性与本真性的深层结构。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指出:“(话语)加强权力, 又损害权力, 揭示权力, 又削弱和阻碍权力。同样, 沉默与隐秘庇护了权力, 确立了它的禁忌。”[2]在人类的语言秩序中,索拉里斯海洋的角色似乎是一位沉默的他者,处于失语和失权的地位。表面上看,人类科学家建构、操纵话语,以“科学”定义、压迫索拉里斯海洋,占据了话语权上的绝对优势。但是,莱姆指出,似乎沉默的海洋在这一组权力关系中才是位于主导地位的那一个。人类试图以语言使索拉里斯海洋“在场”的努力失败了,话语并没有使索拉里斯海洋显现其自身,而是如同攫住一团胶状物,索拉里斯海洋从语言的缝隙中滑走了,语言显示出其力不从心。索拉里斯海洋的沉默反而显示出了一种本真性的特征。在主角凯尔文做的一个梦中,他和索拉里斯海洋似乎终于实现了第一次接触。他们在出神的沉默中互相发现、互相创造了对方。在凯尔文对定义和描述的放弃之中,语言终于从主宰、操纵的地位上退下,让位于沉默,解构了言说-沉默、压迫-被压迫的二元对立,取消了争夺上位权的权力场域。沉默在此时成了一种新的语言符号,而在这种“沟通”之中,同化的尝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然的赤裸相对、本真的呈现。在这种意义上,人类与索拉里斯星才真正地实现了“接触”,宇宙性的荒诞也在这种“互相发现、互相创造”中真正消泯。
二、自我之惧
《索拉里斯星》中,“客人”哈丽具有独特的本体论位置:她没有属于自己的身份。索拉里斯星提取了凯尔文最为创痛的记忆,即他前妻的自杀,并将这段记忆创造为貌似凯尔文前妻的实体“生命”。她不属于人类的一员,因为任何足以杀死人类的手段都杀不死她,并且她血液中蛋白质和细胞是直接由难以稳定的中微子构成的;但她也不属于海洋,因为她的外貌、行事风格都与人类无异。她是一种没有目的的“介质”,是人类与索拉里斯海洋沟通的桥梁。
哈丽暗示了一种具有流动性与不可知性的自我,这种暗示动摇了现实本身。从索拉里斯海洋为凯尔文送来“客人”的那一刻起,凯尔文和世界的关系便被彻底改变了。这一时刻可被定义为“界线消失”:一般来说,主观感受是由肉体决定的,“自我即肉体”的概念在哈丽的存在面前彻底幻灭。被创造出来的“哈丽”没有任何真哈丽的记忆,只记得凯尔文一人。虽然独立于凯尔文,但本质仍是凯尔文记忆的一部分,从属于凯尔文的自我。因而,凯尔文可以用一种“他者”视角来观察自己的“自我”,这一“自我”绝对地独立于他的思想与意识的范畴。这也导致这一“自我”的存在方式是悖缪的,同时兼具内在性与不可抵达性。哈丽的存在提示凯尔文,自己的存在并非对其自身完全的占有。哈丽所代表的记忆存在凯尔文内心封闭的黑暗与暧昧之中,而当索拉里斯海洋将哈丽转置为一个“他者”呈现在凯尔文面前时,这种无意识就具体地暴露在了凯尔文面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表明:人似乎不全是自我的主人,潜意识与无意识是意识无法完全掌控的。当哈丽出现在凯尔文面前时,则如同已醒之姿态面对自己混乱的“白日梦”和自己无法掌控的潜意识。这种“无法掌控感”引起了凯尔文的主体性焦虑。而人类面对索拉里斯海洋的无力感具体化为凯尔文面对哈丽的无力感,科学因果链的断裂引起了关于个体能动性范畴的焦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索拉里斯星》中的恐惧已经超越了认识论的问题,成了一种本体论问题,代表着一种“内部/外部”的深刻混乱。
更可怕的是,哈丽不能离开凯尔文的身边,必须时时刻刻依附着他存在。凯尔文曾多次尝试杀掉哈丽。凯尔文对哈丽的恐惧和难以克制的暴力冲动,本质是对自我的逃避冲动。在面对哈丽时,自我认知和身份危机赤裸地显示出来。在孤独的索拉里斯星上,凯尔文无法“在群体中隐藏自我、忘记焦虑、默默无闻,……产生安全感”,只能趋向另一种方式:“无须在群体中丧失自我,只要能把自己包裹在权力和威望的华饰之中,也能获得安全感。”[1]为了获得对自我的掌控感,在与自我的较量中处于上风,凯尔文进行了许多暴力尝试,究其原因,是哈丽这一特殊他者对凯尔文对于自我绝对掌控地位、主导与控制权的颠覆。凯尔文对于哈丽的单向凝视也证实了这一权力关系。小說的叙述以凯尔文的第一视角展开,这一“非此即彼”的身份框架则注定了全景视野的必然失落。凯尔文没有探知哈丽的欲望,并且放弃了与她进行任何精神上沟通的尝试。在小说中,这是因为凯尔文将自己与前妻哈丽关系的溃败归因于“过度的诚实”。但从根本上来说,凯尔文对哈丽沟通的方式代表了一种轻蔑:凯尔文认为哈丽作为自我的一部分,自己能够完全看透她的主观思想,将哈丽看作自己的“感知域”对象。但事实是,在肉体上,凯尔文无法将哈丽等同于自己;在思想上,他将哈丽所代表的“无意识的自我”等同于自己的尝试也失败了。在小说后半段,哈丽试图褪下凯尔文在自己身上的烙印,建立自己的自主性,进而建构起一个全新的自我。在与凯尔文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哈丽发现了自我存在的荒诞性。在哈丽自我研究的过程中,她的主体性也在不断生长。她偷听凯尔文与其他科学家讨论“客人”的录音,观察自己是否需要睡眠,直至一个节点:哈丽试图喝液氧自杀。自杀,一般被认为是人类哲学中唯一重要的问题,因为其显现了人类终极自我决定的可能。自杀产生于个体对于自身存在荒诞性的体察,造成了其与世界连接纽带的断裂。“这种人与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谬感。无须多加解释,人们就会理解到:在所有健在而又已经想过要自杀的人身上,都存在着这种荒谬对虚无的渴望直接联系起来的关系。”[3]当矛盾的生存状况被觉察时,人便会试图以自杀来摆脱荒诞,抵达虚无的彼岸。哈丽不断质询自己存在的方式,并要求让自己不复存在,这无一不证明了此时的哈丽已经有了独立的主体意识。哈丽的自杀举动突破了笛卡尔式“我思故我在”的二元对立,肯定了身体的主体性。
哈丽依附于凯尔文的阶段,正对应着人类科学家试图以科学的方式定义索拉里斯海洋,都象征着“镜像阶段”,如拉康曾指出,婴儿在镜像阶段形成的“伪自我”来源于一种映射,是一种虚无的存在。镜子中的事物在不断地影响着婴儿,使婴儿逐渐对镜中的自己形成一种迷恋。在探索索拉里斯星时,科学家们认为自己没有征服其他种族的打算,只想向他们传授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自诩“神圣接触的骑士”,想要寻找的却并非外星文明,而是人。他们不需要任何其他世界,需要的只是一面镜子。而当哈丽放弃与凯尔文实现统一、凯尔文放弃掌控哈丽、人类科学家放弃定义索拉里斯星时,真正的自我才开始生长,索拉里斯星上的人类才能真正走出自我之惧,通往一种更深刻的真实。
三、更深刻的真实
索拉里斯海洋及其创造的“客人”深刻地解构了人类科学家与世界的关系,并在解构之后寻求建构一种新的、更深刻的真实,创造一种新的和解。凯尔文同化哈丽的失败昭示了人类对于主体性丧失的深刻恐惧。在与一个无法同化为自己的他者和难以掌控的自我的相处过程中,凯尔文逐渐发现了自我完满而同一的意识的无力。此时,发现一种新的主体意识便显得极为重要。笛卡尔认为,人可以通过内心的感知来清晰地认识自己,也就是说,人的意识是透明的,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自己。但是,梅洛-庞蒂则认为,人对自己的认识并不是完全的,因为人的身体和意识都是模糊不清的,而且人类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和行动中。因此,人只能通过与外界的互动来了解自己,而这种了解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梅洛-庞蒂指出,笛卡尔的错误在于认为自我是一个确定的对象,而实际上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总是处于不完全的状态。因此,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也是值得商榷的。莱姆以哈丽与凯尔文之间的关系变化向读者展示了这一转变:起初,凯尔文认为自我的意识是透明的,是可以被彻底认知的;但是,当他自我中被刻意压抑的部分以实体的方式呈现在他眼前时,他才终于发现,自己对自我的理解永远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人类永远无法成为上帝,自我也并非一个确定的对象,而是始终处于不连续的变化和模糊的动荡之中;最终,哈丽选择用湮灭器使自己永远消失,而在这之后,凯尔文终于开始明白:“一个人,不管表面上看上去如何,他的目标并不是他自己设定的,而是他所出生的时代强加于他的。他可能会顺从它,也可能会奋起反抗,但他顺从或反抗的对象来自外界。如果要完全自由自在地寻求他自己的目标,他就必须是独自一人,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是在其他人中间长大,他就不会成为一个人……”[4]在再一次失去自己的“爱人”,同时不断地与自己未明的自我的搏斗之中,他平静地走出了自我之惧,放弃了成为自己自我的“上帝”,而坦然地接受其模糊与断裂,以敞开的姿态拥抱自我。
科学家对海洋的同化及其失败,则表明了人对于无法同化他者的本能恐惧,提示了敌对的自我-他者关系的注定失败,以及寻求建立一种新的自我-他者关系的必要性。在以敞开而非征服的姿态与索拉里斯海洋接触之后,海洋“教导”了凯尔文通往他者更为真实的道路:在凯尔文的梦中,他感受到自己像由一只手创造而成。在开始时,他没有任何感官体验,但随着某种东西的触摸,他的嘴唇和脸颊逐渐从虚无中浮现,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随着触摸的扩散,他最终被“召唤”到了世界上。在被创造的同时,他自己也在创造着海洋。他看到了一张脸,这张脸既陌生又熟悉。他试图和这张脸对视,但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没有方向。他在这种沉默的状态中,和对方互相发现、互相创造着。这暗示了一种与他者之间关系的重新建构。梅洛-庞蒂认为,人们虽然通过意向性投射(即将自己的意图与谋划投射到他人身上)来感知他人的存在,但这种意向性并非来源于一种纯粹的精神,而是源自自身的存在。因此,身体是人与外部世界相连的媒介,通过身体与世界互动,人类才能了解世界和其他人。身体的知觉直接感知他人的存在和他们的意图,不需要通过意识来进行翻译或解释。在这种前反思的状态中,人与他人建立了一种主体间的交流系统,建立了更为深刻的联系。至此,凯尔文走出了唯我论和他者的敌对关系,建构了一种高于自我-他者的交互主体性,即敌对与互相斗争并非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本质,而互相发现、互相创造才是。
段义孚的《逃避主义》指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独特的,但从根本上讲,“与众不同”与“唯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这会导致分离、无意义与孤独,因而,人试图在人类的群体中逃避自我。但当群体消失时,人还能去何处逃避?又应当如何解决在人群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对立?《索拉里斯星》给出了其对更深刻的逃避路径的思索。凯尔文将与索拉里斯海洋的交互主体性视为一种“有缺陷的上帝”,认为索拉里斯海洋既不拯救什么,也不服务于什么,只是存在着。索拉里斯海洋的存在是先验的、绝对的和自明的,而他的个体自我则是在与索拉里斯海洋不断的接触之中被不断创造出来的。他人不是地狱,人类也不是“神圣接触的骑士”,人与他人的关系本质是有内在联系的,这种先验的相互作用高于任何对立。
注释
① 该句原文为:“Indeed, in ‘Solaris I attempted to present the problem of an encounter in Space with a form of being that is neither human nor humanoid . Science fiction almost always assumed the aliens we meet play some kind of game with us the rules of which we sooner or later may understand ...... However I wanted to cut all threads leading to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Creature, i.e. the Solarian Ocean ,so that the contact could not follow the human ,interpersonal pattern - although it did take place in some strange manner.”引用自:http://english.lem.pl/arround-lem/ adaptations/soderbergh/147-the-solaris-station.
參考文献
[1] 段义孚.逃避主义[M].周尚意,张春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2] 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 加缪.西西弗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4] 莱姆.索拉里斯星[M].靖振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田村童,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