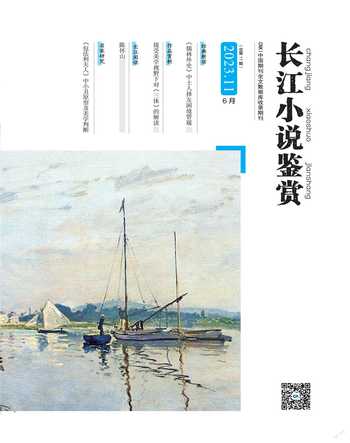晚清小说中的西方女豪杰形象
[摘 要] 晚清知识分子为应对民族危机,呼吁女性担负救国责任,在小说创作中引入了西方女豪杰形象,以此启蒙中国女性,号召她们效仿西方女豪杰,积极参与家国事务。中国知识分子在引入西方女豪杰形象的同时,都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晚清小说《东欧女豪杰》《黄绣球》中的西方女豪杰被塑造成了中国化的美女、神圣化的启蒙者,她们在这两部小说中的政治立场也受到了作者改良立场的影响,西方女豪杰形象在中国的重新建构反映了晚清男性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这两部小说中的西方女豪杰形象塑造具有符号化、套路化、国族化的特点。晚清小说的女豪杰形象塑造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然对中国女豪杰的生成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觉醒,构筑起了晚清甚至民国时期关于新女性的期待与想象。
[关键词] 晚清小说 西学东渐 女豪杰 形象建构 国族话语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80-05
一、西方女豪杰的引入背景
因国家动荡,内外交困,晚清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机,提出了各种救国主张。其中,女性问题得到了晚清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知识分子将女性问题同国族问题连接在一起,丁初我就曾提出“欲造国,先造家;欲生国民,先生女子”的观点[1]。金一也在《女子世界》发刊词里提出:“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2]与此同时,西方女权思想被译介到中国,如马军武就将斯宾塞和弥勒的女权理论译介到中国,他们“男女同权”的观点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舆论反响。由此,晚清知识分子在中国女性身上寄予了新的想象与期待,希望女性能够成为富有智识、关注国族命运、与男性同担国民责任的“女国民”。困守于闺阁绣楼中的传统女性则在此语境之下被视为坐食者、分利者,不符合晚清知识分子的新女性想象,被其排斥到舆论场边缘。此时,苏菲亚、罗兰夫人、若安、批茶等西方女豪杰就作为中国传统女性的对立面和这种新女性想象的具象呈现,被晚清知识分子引入中国,这些西方女豪杰的相关传记、弹词、诗歌直接促进了其女性形象在中国的传播,其中尤以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影响最大。晚清知识分子希望以西方女豪杰作为女性模范,建构、塑造、规训中国女性,使其成为统摄在国族话语之下的“女国民”。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也将这些西方女豪杰形象直接或间接地放置在其寄托了“群治”理想的新小说中,以期扩大西方女豪杰在中国的影响力,号召中国女性走出闺阁,进入社会,参与到救国运动中。苏菲亚、罗兰夫人这两位在当时中国颇具影响力的西方女豪杰就直接作为小说人物分别出现在《东欧女豪杰》《黄绣球》这两部晚清小说中。
二、西方女豪杰在晚清小说中的形象建构
1.中国化的美女
《东欧女豪杰》和《黄绣球》这两部晚清小说分别對苏菲亚和罗兰夫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外貌描写,苏菲亚和罗兰夫人在这两部小说中被塑造成带有浓厚中国色彩的美女。《东欧女豪杰》中,苏菲亚一出场,作者便着意强调其美貌:
青春十六,正长得不丰不瘦,不短不长,红颜夺花,素手欺玉,腰纤纤而若折,眼炯炯而多情,举止则凤舞鸾翔,谈笑则兰芬蕙馥。[3]
作者在这里显然运用了古典小说描写美女的传统笔法对苏菲亚的外貌进行刻画,苏菲亚的外貌在作者笔下并没有显露出明显的异域风情,其外貌的塑造始终没有脱离中国旧式文人的审美范式。
在小说《黄绣球》中,来自西方的罗兰夫人更是直接一身中国古代美人的装扮:
牌坊顶上站着一位女子,身上穿的衣服像戏上扮的杨贵妃,一派古装,却纯是雪白雪白的,裙子拖得甚长,脸也不像本地人,且又不像如今世上的人。[4]
《黄绣球》的作者在此处将罗兰夫人同杨贵妃联系起来,使罗兰夫人以一身中国化的装束亮相读者面前。气质、神韵的古典化、东方化以及装束的中国化、本土化都极大削减了苏菲亚和罗兰夫人的异域性,促使读者按照传统中国美人的外在形象来想象、建构这两位西方女豪杰。这种外在形象的建构策略不是一种简单的书写惯性,其背后所蕴含的心理机制尤为复杂。
当时,在舆论场极力贬抑中国传统女性身体阴柔特质的晚清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他们主张健美的女性审美标准,但在当时一些男性启蒙者的实际创作中,对于女性的外貌书写又不乏“腰纤纤而若折”之语,陷落在古典文学叙写传统美人的陈旧话语格套里。这一方面显露出晚清新小说作者在女性书写上的话语匮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清的男性启蒙者在女性审美标准方面的主张与具体创作实践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不丰不瘦”与“腰纤纤而若折”这两处矛盾之语本身就已经将晚清男性启蒙者隐藏于背后的纠结与反复展露出来。梁启超在议论女性之美时,就将“刚健”与“婀娜”这看似矛盾的两重标准并举,认为“最妙者是刚健之中处处含婀娜”[5]。 晚清男性启蒙者一方面期待刚健的女性身体的出现,一方面又留恋于旧式文人偏好女性柔美身体的审美意趣,这种处于新旧交织之际的内在心理矛盾恰好体现在作者对西方女豪杰的外貌书写中。这表明即使作为启蒙者的作者对西方女豪杰多有推崇,但这些女豪杰依旧被其不自觉放置在了被观看、被凝视的客体位置。不能否认的是,西方女豪杰外表的中国化可以减少读者对于她们形象的陌生感,而对她们的美女化描写则增添了这些西方女豪杰的传奇性,使其事迹更具浪漫色彩。这种方式使读者更容易想象、认同西方女豪杰,从而促进了西方女豪杰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接受,鲁迅就认为苏菲亚的美貌对其影响力的扩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6]而这种美女豪杰的叙事策略是否会使小说的读者仅仅迷恋于西方女豪杰的美丽风韵,是否会在读者接受过程中对女豪杰的革命精神与救世情怀造成新的遮蔽,这是值得进一步省思的。
2.神圣化的启蒙者
《东欧女豪杰》中的苏菲亚和《黄绣球》中的罗兰夫人都在小说中承担着启蒙者的角色,致力于使被启蒙者摆脱蒙昧的状态。苏菲亚在《东欧女豪杰》中通过演说,对俄国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向乌拉山的矿工灌输人人平等的理念;鼓励平民大众联合起来,组织新政府,造就人人平等的新世界。显然在小说中,苏菲亚自觉承担了启蒙大众的任务,主动向大众输出先进的价值理念和她认为行之有效的斗争手段。在小说《黄绣球》中,罗兰夫人入梦黄绣球,在其梦中先质疑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定位,向黄绣球传递“男女同权”的观念,进而促进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后她又授《英雄传》和地理书籍于黄绣球,赋予其解放自我、改良社会的思想支撑和知识武器。罗兰夫人成为黄绣球走出闺阁、进入公共领域的引路人,是促使其获得主体性的启蒙者。
同时,苏菲亚和罗兰夫人在这两部小说中的启蒙者形象又被作者神圣化。苏菲亚出生时有“白鹤舞庭,幽香满室”[3]的异象,直接使其形象被蒙上一层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罗兰夫人的出场、退场与启蒙过程同样被神化,罗兰夫人于黄绣球梦境中以一袭白衣出场,又在其梦境中倏忽消失于云端,黄绣球在梦中“忽见那女子拖着一条白裙,远远的像在云端里去了,须臾连牌坊都不见”[4]。这段退场描写明显借鉴了志怪小说中神仙退场的叙事手法,使罗兰夫人的形象如梦似幻。而罗兰夫人梦中授书的启蒙过程设置同样受到了志怪小说中神授天书情节的影响,梦醒之后黄绣球“把那梦中女子所讲的书开了思路,得着头绪,真如经过神佛点化似的,豁然贯通”[4]。这段描写直接点明这种神圣化、速成化的启蒙其实更近似于古代戏剧、小说中的“神仙点化”。这些借鉴于志怪小说中的叙事策略都诱引着读者以女神的形象来想象、建构这两位女豪杰。从被启蒙者的接受心理维度来看,苏菲亚和罗兰夫人的启蒙者形象与佛教中的观音菩萨形象重合,苏菲亚被工人视为渡化他们的菩萨:
苏姑娘回去了,我们正大家议论,都说苏姑娘是个救苦救难的菩萨,特来普度我们的,我们人人家里都崇拜他才是的话。[3]
黄绣球则猜测罗兰夫人为点化她的观音:
心中又想道难道是:“只难道是白衣观音吗?我向来也不曾相信菩萨,奉个观音斋,怎么他回来点化我?不去管他,我取了几本书快点回去吧。”[4]
将西方女豪杰的启蒙者形象神圣化实际上是对西方女豪杰形象的赋魅。一方面,这可能是作者希望借助神仙形象在普罗大众中的深远影响力和强大感召力,来增强苏菲亚和罗兰夫人形象的权威性、她们所秉持的启蒙观点的说服力及其在读者心中的可信度,以此促进小说启蒙思想的传播,达到开启民智的“群治”效果;另一方面,将西方女豪杰置换成神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偏狭和对古典文学资源的依赖,他们可能由于现实经验的缺乏和文化差异,难以把握准确塑造女性启蒙者形象的方式,于是只能从古典文学的形象谱系中来寻找对应物,并以此建构女豪杰形象,而作者对于启蒙者启迪民众的认识和理解也没有脱离“神仙救世”的传统逻辑。作者将启蒙的叙事嵌套在“神仙救世”的旧有模式里,使承担启蒙者角色的西方女豪杰需要借助神仙的外壳来传播启蒙思想,這可能既是作者在面对启蒙的现实困境时所做出的权宜之计,也是启蒙者借用宗教信仰建构新话语权威的有意之举。从而以救亡图存为最终目标的晚清启蒙运动与反宗教神权的西方启蒙运动的本质差异亦由此处得以被窥见。与此同时,当启蒙者在小说中作为一种超验性存在指引被启蒙对象时,启蒙者的启蒙实践就在作者的建构下走向了理想化,而与之相对的是启蒙理想落实在现实境遇中的艰难性。在虚构文学中被简化甚至被神化的启蒙过程与现实实践中的启蒙困境相互映照,这两者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张力。
3.服务于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
《东欧女豪杰》中的苏菲亚和《黄绣球》中的罗兰夫人虽然在小说中都是争取男女平等、追求自由独立、具有崇高理想和救世精神的女豪杰,但这两部小说对她们二人政治主张与政治立场的书写出现了明显的分野。
苏菲亚在俄国历史上以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著名,她所在的虚无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认为应该废除一切国家和政府,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虚无党常以暗杀手段对抗政府,因此该党在一段时间曾被中国的革命党人大力推崇。而《东欧女豪杰》中的苏菲亚却被作者塑造成一个与历史形象截然不同的温和改良派人物,苏菲亚否定了激进者直接没收贵族土地的主张,提倡进行政权的和平过渡,认为普罗大众应组建新的“大公局”,联合购买贵族土地,以温和平稳的手段实现土地的人民共有。苏菲亚在小说中的政治倾向与其事实上所持的政治理念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裂隙,作者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使得苏菲亚的政治主张在小说中被改换,苏菲亚在小说中被改写为“一位遵奉国家主义的改革者”[7]。
在法国历史上,罗兰夫人是革命党温和派吉伦特派的一员,并非属于革命党中另一支更为激进的派系——雅各宾派。吉伦特派虽主张共和,要求废除君主制,但反对处决国王与暴力革命,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称吉伦特派“平和义热”[8]。即便如此,当时同样持改良主张的梁启超在《罗兰夫人传》的撰写中仍然流露出对罗兰夫人的复杂态度,他一方面赞颂了罗兰夫人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也对罗兰夫人“放出革命之猛兽”[9]的行为颇有微词。与梁启超的态度相呼应的是小说《黄绣球》中的虚构人物对罗兰夫人的评价。《黄绣球》中,虽然罗兰夫人所授的“宗旨学问”被黄绣球的丈夫黄理通大加肯定,但其所做之事仍旧被黄理通认定为“激烈”,黄理通直言黄绣球“不必处那罗兰夫人的处境,不必学那夫人的激烈”[4],这直接显示了《黄绣球》作者温和改良的政治取向。而后罗兰夫人所启蒙的中国女性黄绣球在黄村所采取的兴办新式教育、以弹词教化大众等温和改良措施正印证了作者颐琐的政治立场。
《东欧女豪杰》对苏菲亚政治主张的改写和《黄绣球》对于罗兰夫人政治立场的判定,都表明了两部小说作者作为温和改良派的政治立场,展露了这两部小说创作的政治意图——宣扬改良主义,为其召唤更多的追随者。苏菲亚和罗兰夫人在晚清小说中的形象建构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作者的政治理念,从属于作者现代性的家国想象。这些西方女豪杰形象在中国有严重国族危机的背景下被引入中国,其文学形象最终亦无可避免地受到政治话语和国族话语的统摄。同时,晚清小说中西方女豪杰政治形象的重新建构也揭露了当时改良与革命两种政治力量激烈交锋的一隅。
三、晚清小说中西方女豪杰形象塑造的特点
1.符号化、概念化
苏菲亚和罗兰夫人在《东欧女豪杰》和《黄绣球》这两部小说中更像是凝结了丰富意韵的符号人物[10],成为表达作者改良政治主张、彰显其救世爱国情怀的工具。她们二人在小说里被设置为昭示女子独立的女性模范,是指引普罗大众的先知性人物,高扬爱国精神、承担救国责任的国民典范。她们同样是改良政治话语、启蒙神话的载体,是知识分子为表达现代性国族想象而建构起的借鉴对象。苏菲亚在《东欧女豪杰》中被塑造成出身不凡、外表姝丽、救世为民的完美女性典范;罗兰夫人在《黄绣球》中本身就是一个功能性人物,仅作为启蒙黄绣球的引路人存在。两位西方女豪杰在小说中性格模糊,缺少层次变化,内心情感缺失,形象扁平,缺乏人物的内在张力和个性呈现,其人物书写缺乏细节真实,完全服务于情节发展和作者的政治意图。这一方面是晚清政治小說常见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晚清新小说作者关于新女性想象的匮乏。除此之外,西方女豪杰形象引入中国的政治目的也一定程度上催发了符号化、概念化的女豪杰形象的产生,但符号化、概念化的西方女豪杰形象是否能够产生梁启超所期望新小说发挥的“熏”“浸”“刺”“提”四力?是否能够达到号召、感化普罗大众的原始目的?是否能够使读者将西方女豪杰形象上集合的概念内化到现实实践中?这是有待商榷的。
2.模式化、套路化
苏菲亚和罗兰夫人在两部小说中的形象塑造都流于模式化、套路化。两本小说的作者主要依靠对这两人的行动书写来呈现二者的女豪杰形象。苏菲亚和罗兰夫人在小说中都没有出现复杂的人物行动。苏菲亚仅仅出现了离家求学、成立盟会、大会演说、下狱被捕、等待被救这五个主要行动,其中,离家求学、成立盟会、大会演说、下狱被捕都是晚清小说中豪杰人物同质化的经典行动范式。这种同质化的行动范式既可以说是对多个女豪杰事迹的机械借鉴与模仿,也可以说是作者政治理念的套路化呈现:离家求学是为了说明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大会演说是豪杰精神与启蒙主张的现实实践;下狱被捕则是舍身为国情怀的显像呈现。罗兰夫人作为《黄绣球》中的功能性人物,其行动相比《东欧女豪杰》中的苏菲亚更为简单化,入梦授书这一行动模式则直接套用了志怪小说的程式化情节设置。苏菲亚和罗兰夫人女豪杰形象的模式化、套路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二人在小说中行动的模式化、套路化所造成的。西方女豪杰的套路化演绎一方面是由作者女豪杰想象的单一化所导致,另一方面亦是人物形象概念化的后果显现,人物行动都屈从于一定的政治框架,为展现政治观念服务,而这些政治观念都有与之对应的固化的人物行动模板。值得一提的是,行动的模式化造成了二人行动的简单化,小说中呈现出二人改进社会、启蒙他人的方式较为单一,大会演说成为《东欧女豪杰》中的苏菲亚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践行政治主张的主要途径;罗兰夫人在《黄绣球》只凭借入梦授书这一个简单动作便完成启蒙者的角色任务,这都展现出作者对于女性启蒙者形象塑造的陌生,女性启蒙大众的叙事在这两本小说中只能以简单化、套路化的模式呈现出来。
3.国族化
苏菲亚和罗兰夫人在小说中的形象塑造很明显由国族话语主导,统摄于国族叙事话语之下。《东欧女豪杰》的作者重点表现苏菲亚的国民责任感,苏菲亚在公共领域的演说带有强烈的国民意识,她组建新政府、和平实现土地共有的号召显然是其以国民身份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国族想象,小说开头的引子所提出的女性事业最终直接指向了救国济民的国民重任。在小说《黄绣球》中,罗兰夫人向黄绣球展开“雌雄之辩”、传递男女平等观念的最终目的是赋予女性“国民”的身份,让黄绣球这样的闺阁女性与男子一样同担救亡济世的责任,罗兰夫人对男女平权的倡导以国家主义为依归,促使女性主动进入国族叙事的话语之中。小说《黄绣球》的这样一处描写颇耐人寻味:当黄绣球向罗兰夫人寻求改良黄村的建议时,罗兰夫人则直接对黄绣球言道:“这是你黄姓村上的事,自然你姓黄的人关心切己,与我白家无涉,你黄家果然做得出点儿事,岂不叫我白家减色?”[4]这里表明,对于作者来说,罗兰夫人的国族身份仍旧盖过其性别身份,相互之间的国族竞存压力在此时越过性别困境所引起的同性相惜。小说中由这些女豪杰引出的女权话语明显具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
四、结语
虽然晚清小说中的西方女豪杰形象具有某种局限性;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女豪杰形象对于呼唤女性的主体意识、肯定女性的主体价值、促进女性挣脱旧的思想藩篱和激发女性爱国热情具有正向影响,小说中的西方女豪杰形象为当时的中国女性提供了某种可供借鉴与学习的范本,具有明显的典范作用。这些西方女豪杰形象不仅催生出了华明卿、黄绣球、贞娘等中国女豪杰形象,同时也推动了现实中中国女豪杰的出现,以秋瑾为代表的晚清革命女性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女豪杰形象的感召,她们作为西方女豪杰的精神追随者,突破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走出闺阁,积极参与到救国运动中。从西方到中国,从虚构小说到历史现实,这些女豪杰形象共同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觉醒与抗争,共同构筑起了晚清甚至民国时期关于新女性的期待与想象。
参考文献
[1]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J].女子世界,1904(4).
[2] 金一.社说:《女子世界》发刊词[J] . 女子世界,1904(1).
[3] 岭南羽衣女士,震旦女士自由花,轩辕正裔,等.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瓜分惨祸预言记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4] 颐琐.黄绣球[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5]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下)[M].夏晓虹,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6] 鲁迅.鲁迅全集 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7] 张新璐.罗普《东欧女豪杰》的女性设计与政治想象[J].妇女研究论丛,2017(3).
[8] 康有为.康南海政史文选[M].沈茂骏,编.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9]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上)[M].夏晓虹,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
[10]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龚雪莲,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