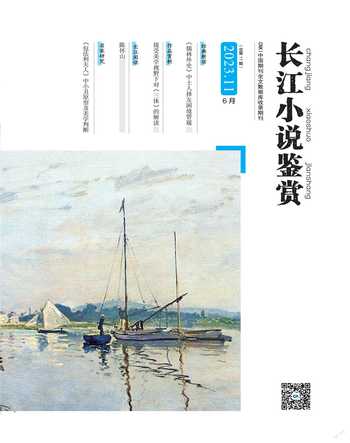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母性崇拜
[摘 要] 作家严歌苓善于书写女性,更擅长挖掘女性的母性特质。在《扶桑》《白蛇》《老师好美》中,严歌苓塑造了三位极具母性气质的女性,采用了他者崇拜的方式来彰显三位女性的母性美。虽然三本小说的内容不同,但母性崇拜的建构体系与情感表达有相似性。
[关键词] 母性崇拜 严歌苓 雌性书写 审美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72-04
严歌苓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有写头,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1]。在严歌苓的小说作品中,女性以主体的身份出现,她们在不同的情感关系中来回穿梭,体现出独特的魅力。“母性书写”是严歌苓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主线,从《雌性的草地》开始,严歌苓着力挖掘母性中的宽恕、包容的特征。在严歌苓2014年出版的小说《老师好美》中,其笔下的母性特质再次得到延伸与变化,她将母性与女性的时代困境相结合,打破母性中的神圣美,体现女性多样的身份内涵。严歌苓笔下的母性概念丰富多样,不同的主人公身上有不同的母性特征:“既拥有母性性质,又不局限于母亲身份;既具有母爱式的付出,又不拘泥于母亲和子女的相处模式;既有东方文化中女性形象的奉献,又融合了西方宗教文化中的救赎。”[2]
“在父系制的中国社会中,女性一方面被排挤在政治伦理制度‘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又在民族的家园意识和人伦情感的‘中心居于‘隐形权威的地位。这‘隐性中心地位得以恒久保持的标志,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母性崇拜文化。”[3]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她经常采用他者对年长女性的爱慕与崇拜来挖掘母性更为深刻的内涵,这种母性崇拜的结构在无形中展示出一种美感,并且在他者崇拜的过程中,人物双方都获得了情感与身心的救赎,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实现了自我的突破。《扶桑》《白蛇》《老师好美》三部作品都采用了母性崇拜的方式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挖掘人物内涵。虽然它们的创作时间、作品背景和人物形象截然不同,但严歌苓在表达这种“崇拜感”时,运用了类似的塑造手法,让人物形象在相异的故事背景下展现出相似的美感。
一、主人公“母亲”身份的缺失
《扶桑》中十二岁的克里斯第一眼见到扶桑时,便对她一见钟情,他沦陷于扶桑的身体与灵魂。年仅十二岁的克里斯为何会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中国妓女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扶桑背后的神秘东方文明以及身上所散发的原始母性是关键线索。小说开篇便将扶桑与其他女性区别开来,她缠裹的小脚、短宽的脸型、神秘的微笑都带着传统的东方情调,散发出别样的风韵。这种特色让克里斯好奇与沉醉,激发出年轻男性对于成熟美丽女性的向往与憧憬。
克里斯来自传统的军人家庭,小说中有关克里斯母亲的描写不多,仅说克里斯的母亲在生完克里斯后不久便去世了。在这样一个压抑严肃又缺乏母爱的家庭中成长,克里斯对于母亲情感的需求在此爆发,所以他才会在见到扶桑的第一眼便被她身上的东方母性气质所吸引。这种从未体验过的温情与接纳,让克里斯毫不犹豫地倾慕于扶桑,疯狂依赖与迷恋她,让她在自己的生命中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
《白蛇》中,徐群珊无数次地对孙丽坤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迷你。”十一二岁的徐群珊看过六遍孙丽坤主演的《白蛇》,她在日记本上写下对孙丽坤难以控制的迷恋。两人第一次对话时,风光的孙丽坤带徐群珊进场看自己的舞剧表演。这次对话充满了“母性关怀”气息。“你刚才乖,没有喊”“我不是男娃娃”,孙丽坤将徐群姗当小孩看待,但徐群珊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情感,她不希望孙丽坤仅将自己当作孩子。作者对于徐群珊童年经历的种种描写,无不透露出年少的她对孙丽坤的无限依恋与爱慕。
徐群珊的父亲徐东森是研究国防科技的科学家,母亲和父亲一起工作,都不在徐群珊身边,并且母亲总说徐群珊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母爱的缺失使得徐群珊迷恋孙丽坤身上成熟的母性魅力,并且由于舞蹈演员身份的加持,使这种魅力更为放大。
《老师好美》中,邵天一和刘畅两位男生对班主任丁佳心产生了疯狂的迷恋与渴望。他们因为无法获得母爱,所以将对于母亲的渴望转移到其他女性身上。刘畅的母亲是位强势的女企业家,将给儿子最好的物质生活看作是自己母爱的表现。“她的爱是六十英寸彩电,是德国进口的床具……”而邵天一的母亲则完全相反,与现代社会脱节的她不知道如何向儿子表达爱,所以以生疏与别扭的表达方式隔绝了母子关系。
十八岁的男生们在母亲那里没有得到安全感与依赖感,善解人意的丁老师缓解了他们的焦虑、痛苦、迷茫与忧伤。丁佳心相比扶桑和孙丽坤,更明显地担负起了“母亲”的责任,她毫无保留甚至错误地给予了刘畅和邵天一想要的关爱,并且也在他们炽热且丧失理智的热爱中迷失了部分的自己。
“恋母情结又称‘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从其 ‘力比多理论和人格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的第三阶段,儿童身上发展出一种情欲综合感,这种心理驱使儿童去爱异性父母而讨厌同性父母。”[4]克里斯、徐群珊、刘畅、邵天一都是少年时在母爱缺失的情况下遇到了可以满足这部分情感的女性,他们将近乎丧失理性的情感奉献出来,形成对她们的“母性崇拜”。
二、被崇拜者的形象特质
扶桑、孙丽坤和丁佳心是小说中接受母性崇拜的主体,严歌苓对于她们的形象刻画有相异之处,但总体都趋向于彰显其母性的气质,这种气质在她们的一舉一动中不断显露,由此激发出主人公的母性崇拜。
1.包容、宽恕的原始美
严歌苓将包容、宽恕的精神气质融于对扶桑的身体书写中,她的身体如流沙,缓缓地融入世间的苦难,她从不挣扎也不反抗,以坦然的姿态面对一切。当她以此般态度接纳与包容世间的万物时,就和她的名字扶桑一样,像大树根植于大地,“树属于生命与生长的层面,这一层面最直接地接触大地。比这一层面更古老的只有神圣的石头和山峦,它们与水一起,都是大地母神的化身,是她的组成部分”[5]。大地母神便是母性的象征,扶桑如同一个容器,包容、接纳了克里斯,让他既惊讶于母性所蕴含的苦痛与宽恕,又让他沦陷于这种自我毁灭的感情。
2.柔软、流动的梦幻美
孙丽坤是著名的舞蹈演员,她有完美的身材比例,对于身体的精准控制使其有如同白蛇般的妩媚。时间的流逝使她的魅惑中有了成熟的风韵。十一岁的徐群珊遇见二十八岁的孙丽坤,一个女孩倾倒于一个美丽的女舞蹈家。徐群珊甚至都不了解孫丽坤,但是在舞台上闪闪发亮的白蛇使徐群珊这样一个小女孩甚至想要改变舞剧内容,去拯救她心爱的人。
无论走到何处,她都随身携带白蛇的剧照,被批斗、被打压的孙丽坤没有了自尊,模样大变,徐群珊也可以一眼认出她,并且在徐群珊的心中,孙丽坤一直都是光彩夺目的样子。徐群珊爱的是孙丽坤的全部,这种感受不会随着青春的散去、身材的走样而消失。哪怕所有人都认为孙丽坤风姿不再,已经变成了一个俗气的妇人,徐群珊依然可以坦然地说出:“你还是那个样子,没变。”
3.纠结、不安的禁忌美
相比扶桑和孙丽坤,丁佳心的形象更为普通和具体:“头发简单地夹在脑后,垂荡下几缕,看上去是早晨睡过了头,随手收拾了一把。”邵天一和刘畅在高考的巨大压力下,心中压抑的情感无处释放,并且母亲的缺席让他们没有情感依靠。善解人意的班主任丁佳心懂得如何取得学生的信任,让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释放自己的情绪,隐形的“母亲”形象便塑造完成了。
在邵天一和刘畅的眼里,丁老师的美是真实可触摸的,她身上的香气、随风飘起的发丝,都可以使两人激动。这种细微的观察总是以两人偷看的方式展开,并通过丰富的内心想象不断深入,这是一种只有少年才可以体会到的母性温情。伦理道德的禁忌让这段牵动三个人关系的感情变得复杂起来,丁佳心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身份发生了错位,她的每一次放纵都将邵天一和刘畅拉进更深的深渊,但她的这份情感中又带有母性的纠结,担心因为自己的冷漠而导致男孩们内心崩溃。丁佳心的形象打破了传统的包容、宽恕、谅解的地母形象,展示了女性个体的丰富性。
三、母性崇拜带来的双向救赎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母性崇拜不但给崇拜者带来了心理上的慰藉,也将被崇拜者从黑暗中救赎出来。崇拜者得到了情感弥补,被崇拜者在强烈的情感面前感受到了人性的真诚,形成双向救赎的关系。
《扶桑》中的救赎关系在多重情节中缓缓展开。首先是克里斯第一次遇见扶桑,神秘的扶桑打开了克里斯情感的新世界,那一刻十二岁的克里斯产生了要将扶桑从这个如地狱般的世界中拯救出去的想法。“她明白自己从没忘记过那个十二岁的男童。”这是他们互相救赎关系的开始,扶桑被少年的真挚打动了,她无法用对待其他嫖客的懒散态度来对待克里斯,扶桑看出了他眼里的真诚与执着,克里斯也可以排除万难,坚定地走向她。扶桑的生命在克里斯的衬托下拥有了未曾有过的价值,宽恕、包容、和谐的东方气质彻底打动了克里斯,扶桑从不以受难者的姿态接受苦难,所以克里斯更加想将扶桑拉出苦海。他不顾家庭的反对、他人的谩骂,下定决心要拯救扶桑。而扶桑也渐渐接纳了少年汹涌的爱,有时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某些时刻她是多么需要克里斯。
扶桑推着年少的克里斯一步步走向成熟。半年后两人再次相见,扶桑看着烂醉如泥的克里斯出现在自己面前时流泪了,少年的热忱自十二岁开始就从未减弱。母性的本能让扶桑忍不住去保护克里斯,她也在克里斯的真心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唐人街的暴动使克里斯认为自己伤害了扶桑,并持续处于愧疚的状态。直到再次相见时,扶桑头发间掉落的纽扣让一切都真相大白,扶桑一如既往的宽恕与包容保护着克里斯,这一次,克里斯真正得到了救赎。
克里斯对扶桑的救赎是隐性的,甚至连克里斯自己都无法察觉。大勇放扶桑自由,扶桑将自己交给克里斯,所以她坦然地等待和克里斯的相遇。当她看到长大的克里斯,内心的母性再一次涌起。“扶桑像个年轻的母亲那样看着眨眼间长成男子汉的儿子,脸腾起血色。”之后的每一次相遇,克里斯都没有辜负扶桑,如同十二岁一样,他对她有着满腔的真诚与爱意。在异国他乡受尽屈辱的扶桑不奢望可以真正被爱一次,她性格中的忍耐、宽容、接纳让她与世无争,可是克里斯的出现让她的生命拥有了价值,将她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严歌苓最终并没有安排两人在一起,但这段关系改变了他们,让他们此后都被这段感情救赎与温暖着。结尾两人再次相遇,年迈、蹒跚的背影是这段救赎关系的见证,是无尽崇拜背后所带来的情感价值。
《白蛇》中的救赎从十二岁的徐群珊开始,穿着黑色宽大灯笼裤、印度红毛衫的孙丽坤打开了徐群珊的情感世界,两人只是短短说过几句话,但徐群珊却一直记得这件事。这份年少的迷恋一直陪伴着她,在潜移默化间成为一种力量,让徐群珊可以在世俗的诧异眼光中做自己。别人迷恋的是孙丽坤完美的肉体,只有徐群珊恋着的是孙丽坤身上的母性温情。
“她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如同眼看一尊佛像在面前崩塌那样,眼睛里充满坍塌的虔诚。小女孩是孙丽坤最后忘却的。”这是孙丽坤仅有的关于年少徐群珊的记忆。所有人都以打量的眼神审视着孙丽坤,唯独徐群珊的眼神里带着热忱与崇拜。徐群珊对于孙丽坤的救赎开始于孙丽坤最艰难的日子。遭受批判的孙丽坤没有了舞台上的光鲜亮丽,也失去了自尊和廉耻。这种混沌恍惚的状态随着徐群珊的到来才停止,在她的面前,孙丽坤依然想要展现自己的魅力,恢复作为舞蹈家的完美身材。徐群珊满怀崇拜性质的迷恋将惨遭放逐的孙丽坤救了回来。
孙丽坤与徐群珊之间的救赎带有不能明说的秘密色彩,超越性别禁锢。母性崇拜衍生出来的爱意更多样与复杂,她们注定无法在一起,无法拥有光明的未来。
《老师好美》中丁佳心与邵天一、刘畅之间的救赎关系更直接。邵天一是性格敏感又略带忧愁的男生,成绩优异的同时也备受学业压力的折磨,丁佳心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母亲般的关怀。为了解决邵天一的失眠问题,安抚邵天一的情绪,丁佳心选择退让与成全。所以邵天一只有在心爱的丁老师这里,才可以拥有完整的睡眠,只有丁老师能真正了解全部的自己。丁佳心的存在对于邵天一来说是救命稻草,丁佳心流露出的母性气质,拯救了邵天一。
刘畅是富家公子,从小缺乏家庭关爱使他性格中有成熟与理性的一面。丁佳心将刘畅从事事都讲求结果的环境中释放出来,在丁老师這里,刘畅收获了一丝温情和尊重。在得到了丁老师的爱后,刘畅对于生命的感知更真切了,丁佳心的出现,使刘畅完成了从男孩走向男人的蜕变。
丁佳心无法轻易地从两段年轻且炙热的感情中脱身,因为她也从中获得了精神慰藉。为了使丁佳心不受前夫的骚扰,刘畅在楼下守了丁佳心一夜。丁佳心总是期盼刘畅不要长大,一直保持男孩的模样,保持这种热忱且纯洁的爱恋。“你是在怎样的孤独中爱我,爱我们之间这种不伦不类的感情,爱到绝望和凶残的地步。”在伦理道德中挣扎的丁佳心被真诚的“少年爱”所打动。严歌苓让死去的邵天一在丁佳心面对危机时再一次活过来,以风的形态警醒丁佳心。从生到死,两个男孩都将自己最炽热的情感给了丁佳心。
四、结语
严歌苓的《扶桑》《白蛇》《老师好美》三部小说对母性崇拜的建构具有相似的体系,崇拜的起因都是因为主人公成长过程中母亲角色的缺失,产生了对于母爱的渴望。扶桑、孙丽坤、丁佳心三位女性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格,但是她们身上共同具有的母性使主人公产生了崇拜,并且在崇拜的过程中,双方皆从中获得了救赎,或是情感上的,或是个性上的,又或是价值体系建构上的。
“以强劲的生命力、宽厚的仁爱与包容以及隐藏在柔顺外表下的坚定的人生理念为显著特征的母性看似平凡卑微,却蕴藏着无与伦比的力量。这力量不仅能够支撑女人自己度过难以想象的世俗困难,更是能够帮助她们在与男人的较量中实现和谐与完满。”[6]《扶桑》《白蛇》《老师好美》的母性书写变化,是严歌苓笔下的女性越来越有主体性的表现,她们在包容他人的同时也可以直面内心的真实情感,这样的女性形象虽然渐渐脱离神圣性,但也愈加拥有真实性。
参考文献
[1] 展迎迎.严歌苓: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N].钱江晚报,2014-05-28.
[2] 李静.论严歌苓作品中的母性情怀[J].职大学报,2018(2).
[3] 仪平策.母性崇拜与审美文化—中国美学溯源研究述略[J].中国文化研究,1996(2).
[4] 韦柳娜.论《扶桑》中的恋母情结及其矛盾性[J].名作欣赏,2019(36).
[5] 缪丽芳.雌性·母性——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情结分析[J].华文文学,2006(6).
[6] 董娜.严歌苓小说中“母性·雌性”观的建构及特征[J].潍坊学院学报,2021(3).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徐婧纯,华侨大学文学院本科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