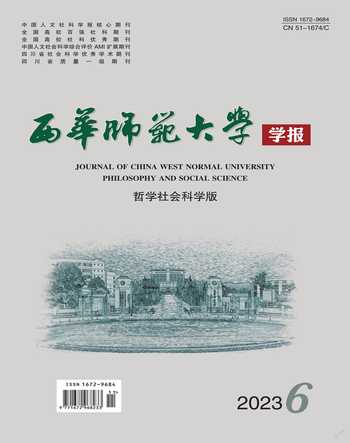脱贫地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机制
摘 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在激发贫困群体主体性、整合社会资源和多维度介入贫困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当前我国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在“十四五”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的路径主要是加强低收入人口帮扶、增强脱贫群体内生动力和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基于政府和社会协同发展的治理视角,为扩大社会组织参与和提升其专业能力需从政策支持、平台搭建、组织建设、技术赋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
关键词:社会组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政社协同
中图分类号:F323;D42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9684(2023)06-0032-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也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稳定完善帮扶政策。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乡村社会面临着相对贫困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等问题,这决定了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与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具有多元化主体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大格局[1]。因此,在接续过去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经验基础上,亟需结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背景下脱贫地区的工作重点,深入认识社会组织参与的路径,探讨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的体制机制。
一、文献回顾
实践表明,社会组织参与不仅是国际反贫困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也是我国扶贫开发与乡村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2],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广泛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从早期的弥补扶贫资金不足、提高扶贫效率和营造社会向善的氛围[3]到在完善瞄准机制、落实扶贫到户方面进行组织与制度创新,增强开展项目的自主性、创造性和选择性,尝试新的扶贫理念[4],对政府的扶贫工作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在新时代进入脱贫攻坚阶段以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丰富和发展了广泛参与、合力攻坚的社会动员体系,形成了社会大扶贫格局[5]。为此不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国办发〔2014〕58号)等政策文件,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的原则、主体和机制,也通过区域协作、定点帮扶和专项行动等举措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到村到户精准扶贫。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扶贫和农村发展领域的社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具有背景多元的特点,既有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与政府联系密切的全国性公益组织,也有四川海惠这类具有国际背景但已经本土化的地方性公益组织,还有企业、社会人士发起的基金会、行业协会商会、社会服务机构等,这些组织基于对乡村贫困和发展的认识,明确了重点关注的服务人群、开展项目的工作手法和策略,并积累了组织管理和运行、项目实施的经验,也形成了一批致力于农村发展的人才队伍。民政部的数据显示,自脱贫攻坚以来全国社会组织共实施扶贫项目超过9万个,投入各类资金1 245亿元[6],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方式助力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最终胜利。
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离不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早在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2月21日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一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不仅意味着关注对象、发展单元和方式的转变,也意味着更加注重区域发展,以及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协同[7]。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十四五”时期在脱贫地区设立五年过渡期,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不仅旨在避免大规模返贫和实现对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更要提升乡村社会自我发展能力。
在两者有效衔接的背景下,党和政府关于乡村振兴工作的意见和“十四五”民政事业规划都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参与的作用。在已有研究中,一方面集中探讨相对贫困的测度与治理,减贫形势总体变化及政策干预方向。目前脱贫地区和人口不仅面临着自然灾害、疾病和环境等多重社会风险,也面临着诸多次生灾害带来的威胁和挑战,这使得他们极易致贫或返貧。这种脱贫的不稳定性不仅表现在收入上,也体现在健康、教育、养老等多个维度,更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减贫动力的变化迫切需要开展缩小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异的常规性制度建设[8],以及治理逻辑向常态化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心下移和梯度推进方式转化[9]。因此,社会组织参与的重点是既需要考虑与相对贫困治理目标下的社会救助制度[10]相衔接,也要与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相融合。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已有宏观的学理讨论、微观的案例阐释[11]5-15,尤其是从结构和主体的角度指出社会力量在结构逻辑上可以从村民和村社主体性两个方向发力,在行动逻辑上则以社区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组织化两种手段分别参与社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培育,导向“新内源性发展”[12];有的研究从组织和过程的视角探讨社会组织在面对介入乡村振兴过程中环境的不确定性时,采取嵌入国家政策话语、地方行政体系、目标社区的优先次序和渐进策略等加以应对[13]。也有研究从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角度,基于社会组织参与的障碍因素与现实困境分析,强调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构建“对称性互惠”关系,形成协同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14]。总之,这些研究为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的制度建构带来启示,但缺乏在总结过去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经验基础上,从中观层面探讨脱贫地区社会组织参与路径和体制机制的完善。
二、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角色回顾
在精准扶贫战略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背景下,大量社会组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参与进来,创新性地回答“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精准识别贫困群体和激发其主体性,整合企业和动员公众捐赠等社会资源,并从不同维度介入贫困治理,使得社会组织的参与不仅实现了由点到面,也协同政府和企业等多方参与,改变了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助推了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扶持谁:社会组织激发贫困群体主体性
落实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是精准识别动态变化中的贫困对象,精准判断脱贫的多样性需求,以及精准填补帮扶中的最后一公里断层[15]203。社会组织扶贫项目强调对于贫困社区和农户的瞄准机制,一般将资源下沉到贫困对象所在的社区,并采用综合区域发展、参与式发展、小额信贷、社会性别等理念和手法,从权利角度去理解和对待贫困问题,强调激发扶贫对象的主体性并进行赋权,不断创新社会保护机制。如四川海惠以“礼品传递”的模式,通过“牲畜捐赠+项目培训”的方式传递信息、传授生产技能,并提升受助对象的自主发展能力[16]396-400。相比政府自上而下的体制内动员,社会组织扶贫项目往往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之形成资源的补充和手段的协同,也能在实现发展的同时增强扶贫对象的获得感。
(二)谁来扶:社会组织链接和整合社会资源
社会组织参与链接和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着通过第三次分配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一是扶贫领域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各界捐赠的重点方向,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2020年我国共接受境内外慈善捐赠2 253.13亿元,其中扶贫领域的捐赠达385.58亿元,仅次于卫生健康领域[17]。二是社会组织积极与企业合作,链接企业资源,推动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瞄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建档立卡户贫困人口,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携手推出“顶梁柱计划”,通过精准救助使其恢复劳动能力、实现脱贫;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则将慕课与电商扶贫结合,开发了“MOOC+贫困地区电商能力建设课程及相关服务体系——3+2+6”课程体系。这些具有示范性的品牌项目既探索了不同的参与模式,也不断拓展了参与的空间,有着独特的价值。三是改革开放以来,诸多境外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我国的乡村发展和反贫困工作,如香港乐施会等从境外筹集资源,培养了一批能与国际扶贫和管理理念接轨的人才,以参与式发展手法、社会性别视角的工作理念推动社区的综合发展和政策调整趋于更为利贫、利弱的方向,促进减贫工作的瞄准性和精准度[18],同时也影响了致力于农村发展的本土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工作方式。
(三)怎么扶:社会组织多维度介入贫困治理
乡村社会的贫困既有生理、心理、教育和家庭等层面的内在原因,诸如疾病、残疾、动机不足、文化水平太低等能力缺失,也有自然环境、社会等层面的外在原因,如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宏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利条件[19]。因此,贫困问题的解决始终与“发展”紧密相关,既涉及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与经济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有关。具体而言,扶贫与诸多公益慈善领域紧密关联,扶贫的对象涉及留守儿童、女性、空巢老人和残障人士等特定人群;实施的项目涵盖产业发展、社区教育、生态环保、灾后重建、农村养老、医疗救助、卫生与健康、性别平等和文化重建等诸多领域。如中国扶贫基金会、郭氏基金会、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福建永泰县乡村复兴基金会等主要以产业扶贫为切入口,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社赋能等助推乡村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这些组织及其实施的项目既针对乡村发展的基础条件和特殊困难群体,提出具体目标和问题解决方式,也强调从整体上注重乡村社会的发展。
总之,在政府和社会协同视角下的贫困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的不同环节针对不同的人群及其贫困程度,根据需求在不同阶段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项目,不仅发挥其深入基层社会、提供直接服务的优势,也充分体现跨界合作、链接资源的特点,因此它有助于弥补政府组织资源的不足,增强实效性,提高协同性,落实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社会组织一方面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尤其是避免深度贫困地区返贫,另一方面又要推动乡村振兴,并实现两者之间政策的衔接,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有了更广阔的作为空间。
三、有效衔接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的路径分析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阻滞脱贫人口返贫和应对相对贫困挑战是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重大任务,方向是通过经济、社会、观念和能力的发展,实现对相对贫困的发展型治理[20]。而从脱贫地区县域发展来看,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人才流动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瓶颈和难点[21]。2022年2月15日民政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的《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强调,通过专项行动、对接平台和项目库建设等举措,积极创造有利条件,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在总结过去参与脱贫攻坚经验的基础上,围绕乡村振兴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参与和实施各类公益项目,服务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和回应农村发展的现实需求。在社会组织过去参与脱贫攻坚重点地区开展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易地扶贫搬迁、贫困群体关爱保障等行动的基础上,《通知》强调:要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发展壮大脱贫产业,以及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因此,总体上聚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避免大规模返贫和实现对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增强乡村自我发展能力是社会组织参与的关键工作内容。
(一)加强低收入人口帮扶,巩固脱贫成果
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兜底保障是防止贫困人口返贫、低收入人口致贫的重要工作。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據,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认定低保边缘人口431万人、支出型困难人口433万人,连同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易致贫返贫人口等低收入人口共计5 800多万人[22]。目前民政部已开发建设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各地民政部门也相继出台了认定和动态监测工作的办法或实施方案。总体上这类人群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有着较高的返贫风险。2022年10月20日,民政部、中央农办、财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等社会救助范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切实兜住兜准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借助全国低收入人口数据库和监测平台,各地主管部门可以进行常态化监测和预警,并进一步拓展管理与服务功能,打通精准救助和帮扶的最后一公里。其中,各部门可以动员和支持社会组织开展救助帮扶服务,为监测预警、精准帮扶提供数据支撑。如村(社区)组织两委、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乡镇社会工作站工作人员、社区网格员等在日常工作中开展入户探视和上报数据。2021年5月,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发布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工作指南》区分了基本生活救助、综合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服务类救助和慈善类救助等5类,其中服务类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低收入人口提供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尤其要对失能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提供必要的访视和照料服务,并逐步扩大到老人、妇女和儿童等三大留守群体及其家庭。因此社会组织既可以发挥贴近服务对象的优势,如经常性的入户走访,有利于数据填报和共享,也可以发挥专业服务的特长,在帮扶中精准识别风险、挖掘需求,跟进和实施服务方案。
此外,相对贫困的治理需要超越单一收入维度的贫困概念,这涉及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贫困,以及小农面对权力、资本、市场的脆弱性和风险应对能力。因此,推动脱贫地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才是最终阻断低收入人口贫困代际传递的破解之策。目前脱贫地区的文化帮扶在领导体制、责任边界、投入渠道、考评机制等方面存在欠缺[23],教育帮扶在资源配置、技能培训、就业信息等方面存在短板[24],这无疑会为脱贫稳定性带来较大挑战。扶贫要“扶志”,乡村振兴更要实现“志智双扶”,社会组织可以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益性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尊重主体性,增强脱贫群体内生动力
在国内外的减贫实践中,扶贫对象的参与是核心,以参与式发展为代表的扶贫理念强调贫困群体共同学习和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力[25]84。如世界宣明会永胜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基本生活环境,而且通过数年的参与过程,很多社区已经开始自觉和主动地参与到项目中,因得到赋权而开始进行自我管理,形成了参与式发展的永胜模式[26]194。在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中,政策本身及其具体实施过程也包含着很多贫困群体参与的元素[27]。社会组织除了通过募集资金、发放物资等给予贫困人口直接帮扶外,还基于参与式发展理念在方式上从个体帮扶转向地区发展,注重培养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并以社区为本采用综合发展模式确保农民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
因此,在社会组织的参与过程中,首先要整合人力和资源,使其介入乡村发展,这也有助于动员当地民众主动参与到项目的实施中。尤其是针对相对贫困问题,重视扶贫对象的参与,调动受助对象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自己寻找贫困原因和解决方式,参与到乡村发展过程中来,从而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参与作为外部力量往往自身有其使命、理念、价值观和工作手法,但是挖掘乡村社会原有的经济、组织、文化、人才资源同等重要,如村落中生产、教育、养老互助等传统慈善形式,以及返乡新农人或新乡贤等人力资源。最终通过组织培育等方式,将由外向内的资源输入与农民内在的需求偏好相对接,提升农户自我组织、服务和管理水平,激发村民自我发展意识。作为外部干预者的社会组织通常在完成项目后就逐步撤出,因此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在于通过村民广泛参与和合作互助,助推乡村社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三)以合作组织建设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已有研究表明,中西部地区农村仍以发展农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产业有着较强的可行性[28]。在国际减贫实践中,社会组织参与减贫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是利用或结合市场机制开发道德市场、穷人资本和发展社会企业等[29]。在我国,社会组织通过小额贷款、农民合作社建设和地方特色资源开发等介入农村产业发展。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等组织已获得了成功探索的经验。面对“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难题,社会组织的项目实施一方面需要考虑该产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形成基于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并根据需求对产品进行定价;另一方面可以引导村组织申请各类政府扶贫资金的资助,撬动政府资源,或是组织社区骨干外出采访考察,借鉴优秀项目和学习企业经营文化等方式不断提升合作经济主体的自身能力。因为从产业发展价值链来看,不仅需要在前端解决农户生产启动、成本投入和运营技术等问题,也要在中途引进技术人员、组织各类培训考察以提高农户生产技术,更要在后端建立合作社,通过打造品牌、资源链接和统一销售来进行全产业链的优化。
因此,社会组织能通过互助组和合作社这类组织的建设,对村民互助合作意识进行培育和赋能。一是通过构建农产品价值链、改进生产技术,以及合作社的建设和集体经济的运作,提升村民的生产和经营能力,改善项目受益农户的生计,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农户的组织化和农民的增收。二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引导并促进农户进行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实践,合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帮助村民实现种养殖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的发展,改进社区卫生管理和社区环境。三是借助社区公共基金,助力道路、广场等基础设施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村容村貌的同时,在村落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事务中扩大村民参与,注重社区凝聚力的营造和整个社区的综合发展,进而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最终推动乡村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总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可以发挥社会力量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尤其是在项目工作方法上强调整合性、参与式和创新性,以及在资源筹集与使用、项目设计与管理、实施与监测评估等环节的系统性,能够最大化发挥社会公益资源的效用,提升项目实施地的福利水平。当然,这也意味着需要推动更多的社会组织扎根乡村,需要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当地社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实践表明,社会组织作为外部力量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部门的配合和村民的参与,这往往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要素。地方政府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合作伙伴,尤其是在项目设计之初,项目方案要求更好地与政府发展规划相衔接,并争取政策和资源支持;实施过程中加强与政府、企业和村庄之间的协同,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样才能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的体制机制。
四、政社协同视角下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的机制
在各级党委领导和政府推动下的乡村振兴工作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的协同合作,拓展社会组织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将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相结合,真正实现以农民农业农村为主体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尤其在有效衔接背景下,社会组织可以持续深耕当地,发挥其稳定性和公益性的优势,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西方NGO的发展是政府和市场失灵的产物,但是我国的社会组织有着独特的“政社二元性”特征,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是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定位,也是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0]。尽管如此,在宏观政策层面,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顶层设计尚未完成,以致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具有非常大的不稳定性,表现为政策的含混性及组织管理体制的弱整合性[31]58;在中观层面,相对于我国乡村社会的人口规模来说,在贫困地区开展乡村发展工作的组织数量及其专业能力有限,难以回应当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需求;在微观层面,目前普遍存在組织规模小、资金来源不稳定、专业人才稀缺、内部治理残缺等问题[32]69-78,比如由于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等因素乡村工作人才难以扎根,这些仍然是制约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要回应乡村振兴的复杂需求和行动目标,扩大乡村振兴领域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应着力从宏观的制度环境、中观的人才队伍,以及微观的组织建设等方面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的体制机制。
(一)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民政部和国家乡村振兴局的《通知》明确指出,在中央设立的5年过渡期内民政部门要从工作机制、发展规划、政策举措、服务对象、考核机制等方面保持支持、激励、规范社会组织参与帮扶的政策总体稳定。因此,各地省级民政和乡村振兴部门出台的实施意见或方案强调:要整合各类政策工具,从注册登记、孵化培育和支持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是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行业协会脱钩,以及促进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等背景下,推动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等业务主管单位主动作为、积极审批,基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改革,探索乡村振兴领域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二是目前大部分社会组织以项目运作为主,扮演着直接服务的角色。因此各级政府可以加大孵化培育力度,引导发展服务支持型、资金支持型、智力支持型、自律联盟型社会组织[32]419,尤其是那些发挥行业价值引领作用,需要承担资源筹集、能力建设等“基础设施”角色的社会组织,如乡村振兴领域的基金会、志愿者组织,以及在当地获得支持的其他社会组织。三是充分运用和创新政策工具。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慈善组织认定、税收捐赠优惠、设立专项基金和慈善信托等举措实现政府资源适当向社会组织倾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举措创新政府资金的使用机制。2022年3月28日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各地可以创新资金使用方式,如以奖代补、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在此基础上,各级乡村振兴部门可以出台政府购买乡村振兴领域服务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对利用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做出具体安排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撬动更多社会资源,激发社会组织参与活力,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搭建平台:汇聚专业人才和资源
当前全国正在推进的乡镇社工站点可以成为各类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2021年4月10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健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制度体系,力争‘十四五末实现乡镇(街道)都有社工站,村(社区)都有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的建设目标”。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截至2023年1月17日,全国已建成乡镇(街道)社工站2.9万余个,7万名社会工作者驻站开展服务,8个省份实现了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16个省份覆盖率已超过80%,全国覆盖率达到78%[33]。乡镇社工站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任务。社会工作参与的优势在于社会工作者聚焦于建立和强化社会支持网络,链接与整合资源,同时促进贫困群体观念的改变,增强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4]。因此,站点建设有助于汇聚专业人才队伍、社会组织、慈善资源,实现从传统的“公益下乡”“项目进村”到“驻守村居”“扎根社区”的转变,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构建政府主导制度建设、社会组织践行以人为本的专业实践与促进增能取向的职业发展的协同关系,以及互为主体的政社关系和服务关系[35]。因此,在实践层面社工站建设不仅有助于社会组织与当地政府、村庄与村民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也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持续投入,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动力。
(三)组织建设:推动多元发展和协同
在乡村振兴领域,社会组织的多元化發展、协同和创新有助于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需要引导和推动行业支持型、资源筹集型和项目运作型组织的均衡发展。乡村振兴可以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教育、社会心态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切入,对于村庄发展来说,这些方面紧密相连、互相影响。因此动员和参与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不仅需要关注自我发展能力弱的特殊困难群体,如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也应该覆盖乡村教育、文化发展、公共卫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实施补缺型和发展型两大类项目。为此,社会组织参与既需要与各级政府的民生保障、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和社会事业相衔接,也需要构建有效的网络,增强组织间协同行动的能力,进而扩大社会组织参与的影响力。如四川省成都市组建的乡村振兴公益联盟,旨在推动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高校、研究机构、农村合作组织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交流、资源共享、人才共建,助推该区域的乡村振兴工作。概而言之,在推进社会组织多元发展和提升其专业能力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间的网络和平台建设。
(四)技术赋能:创新乡村公益的生态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应用,不仅改变了公益慈善行动主体的构成及其互动方式,也改变了公益慈善系统的基础设施,从而改变了其实施方式[36]217,为社会组织创新参与形式带来多元化的选择。一是资源动员层面,随着网络支付与公益众筹的出现,基于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新浪微公益等网络平台,互联网筹款呈现出方便快捷、简单透明等特点,已经逐步演变为公众筹款的主流渠道之一;二是公众参与层面,基于社交网络组建和运营的志愿者社群可以实现快速集结、沟通和响应,增强社会联结,便于更广泛的社会动员;三是商业与公益互促互融,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规模价值突显,创新了公益项目实施的方式,如阿里巴巴、京东、美团等企业,通过培训和扶持小微电商、带动贫困人口就业、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等方式介入乡村产业发展。最后,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扶贫项目供需对接的精准度,如2022年5月12日安徽省民政厅和乡村振兴局印发的《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提到:探索将区块链技术与精准帮扶数据相结合,借助“区块链+”助推精准帮扶优化升级,在供需对接方面发挥科技支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创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赋能公益组织和乡村人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组织协同创新提供支撑。
五、结语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脱贫地区农民逐步从过去摆脱贫困的需求转向增加就业和收入、完善的公共服务、繁荣的乡村文化、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秩序等多元需求。按照中央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社会组织参与包括如下五个维度:一是乡村产业,实现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增强集体经济实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和增加收益;二是乡村人才,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社会“空心化”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增加乡村工作对人才的吸引力,为乡村建设和发展奠定人力基础;三是乡村文化,让乡土文化重新焕发活力,为乡村振兴奠定文化基础;四是乡村生态,既要做好人居环境整治,也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使优美的生态环境产生社会经济效益;五是乡村组织,一些地区基层组织弱化,难以真正有效推动乡村振兴与治理转型,因此需要健全党委领导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构建和完善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增强治理效能。总之,在政府和社会协同治理视角下,在脱贫地区的乡村振兴过程中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有着广阔的参与空间,可以持续发挥其直接服务和链接资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助力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
[责任编辑:张思军]
参考文献:
[1] 黄承伟.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前沿问题[J].行政管理改革,2021(8):22-31.
[2] 王名.NGO及其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5-80.
[3] 郑功成.中国的贫困问题与NGO扶贫的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2(7):9-13.
[4] 洪大用.中国民间组织扶贫工作的初步研究[J].江海学刊,2002(2):100-105.
[5] 黄承伟,杨进福.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史经验[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39-48.
[6] 赵宇新.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我国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历史轨迹[N].中国社会报,2021-06-29(1).
[7] 黄承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演进逻辑[J].农业经济问题,2022(6):4-11.
[8] 徐进,李小云.论脱贫的稳定性与减贫动力变化的若干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33-42.
[9] 李博,苏武峥.欠发达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治理逻辑与政策优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71-79.
[10]关信平.相对贫困治理中社会救助的制度定位与改革思路[J].社会保障评论,2021(1):105-114.
[11]董强.公益乡村:公益力量对接乡村振兴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12]李怀瑞,邓国胜.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发展路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1(5):15-22.
[13]郑观蕾,蓝煜昕.渐进式嵌入:不确定性视角下社会组织介入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J].公共管理学报,2021(1):126-136.
[14]邱玉婷.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治理相对贫困的行动策略[J].广西社会科学,2021(4):11-16.
[15]李小云.貧困的终结[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16]邢宇宙.乡村振兴战略下社会组织助力脱贫攻坚的实践探索——以四川海惠恩平生态农业扶贫项目为例[R]//黄晓勇,徐明,郭磊,吴丽丽.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17]中国慈善联合会.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R].2021.
[18]刘源.精准扶贫视野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国减贫——以乐施会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99-108.
[19]关信平.论现阶段我国贫困的复杂性及反贫困行动的长期性[J].社会科学辑刊,2018(1):15-22.
[20]王思斌.全面小康社会初期的相对贫困及其发展型治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5-13.
[21]冯丹萌,万君.脱贫地区提升县域发展能力的初步思考[J].城市发展研究,2022(5):37-43.
[22]李昌禹.低收入人口数据库已建成[N].人民日报,2022-01-27(7).
[23]胡守勇.脱贫地区文化帮扶体系的构建路径[J],行政管理改革,2022(9):44-52.
[24]邹培,雷明.教育帮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72-84.
[25]范大娜·德赛,罗伯特·B,波特.发展研究指南(上册)[M].杨先明,刘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6]陈思堂.参与式发展与扶贫:云南永胜县的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7]许汉泽,李小云.“行政治理扶贫”与反贫困的中国方案——回应吴新叶教授[J].探索与争鸣,2019(3):58-66.
[28]张吉岗,吴嘉莘,杨红娟.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脱贫地区产业兴旺实现路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8):153-162.
[29]苟天来,唐丽霞,王军强.国外在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经验和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4):204-211.
[30]柳拯.以制度建设为核心 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N].中国社会报,2020-01-06(2).
[31]黃晓春,张东苏.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组织:政策选择与发展路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2]马庆钰,廖鸿.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3]许娓,徐蕴.全国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已建成乡镇(街道)社工站2.9万个[N].中国社会报,2023-01-18(1).
[34]王思斌.社会工作要参与相对贫困治理[J].中国社会工作,2020(28):45.
[35]张和清,廖其能,李炯标.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以广东社工“双百”为例[J].社会建设,2021(2):3-34.
[36]康晓光,冯利.中国慈善透视[M].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20.
Approaches and Mechanis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Poverty Relief Areas
XING Yu-zhou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24,China)
Abstract:In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social organizations,as social forces,play an important complementary role in stimulating the subjectivity of poor groups,integrating social resources and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governance in multiple dimensions.At present,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In the context of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during the “Fourteenth Five Year Plan” period,the path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s mainly to strengthen the assistance to low-income people,enhanc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groups and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and society coordination,in order to exp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enhance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from policy support,platform building,organization building,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other aspects.
Key words:social organization;poverty allevi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government and social coord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