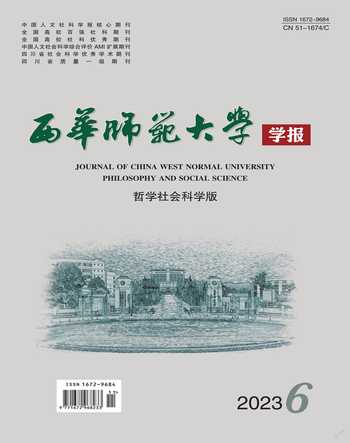新修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司法解释施行引发的司法实践转向及应对
王东 霍敏霞



摘 要:最高人民法院新修订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以虚假陈述行为主体侵权责任为规范对象,侧重于拓宽投资者的救济渠道,体现了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司法规制的实践转向。以229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类案件的判决书为研究样本,分析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类案件基本态势,可以发现其在司法规制转向方面的主要特点。在分析该司法解释对未来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诉讼影响的基础上,站在投资者维权策略的角度提出相应对策:注重维权主体证据能力的提升,引入第三方专业技术协助调查取证,精准认定中介机构及独立董事的勤勉尽责义务,准确认定虚假陈述的适格被告,完善登记结算机构、监管机构、交易所的信息获取制度。
关键词: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司法实践;投资者;诉讼策略
中图分类号:D922.28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9684(2023)06-0048-11
当前,中国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趋势持续从严,虚假陈述的违法成本不断提高,实践中呈现出虚假陈述相关纠纷诉讼激增、热点案件频现的态势。诸如中国首例特别代表人诉讼“康美药业案”①、中国首例实质取消中介机构前置程序“中安科案”②、中国首例人数不确定的普通代表人诉讼“飞乐音响案”③等,引发了资本市场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中国证券市场司法实践水平也在不断努力提升,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1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本文以下简称《虚假陈述新规》)便是适应证券市场深化改革实践的司法回应。旧有的司法解释(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2003年虚假陈述案件规定》)对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问题存在留白,新规则顺应了资本市场交易的多样性和网络时代的信息陈述行为。《虚假陈述新规》“充实和完善了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市场制度供给,畅通了投资者的权利救济渠道,夯实了市场参与各方归位尽责的规范基础,健全了中国特色资本市场法律体系,为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1]。《虚假陈述新规》对于不断涌现的虚假陈述行为所造成的投资者利益受损的司法保障等相关未尽问题做出了应对,同时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达到证券法对“投资者保护”的功能价值以及投资者维权机制的司法规制效果。
一、《虚假陈述新规》引发司法规制的实践转向
《虚假陈述新规》发布后必然引发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规制的实践变化,这充分展现了立法理念上的革新,决定了司法实践的转向。在中国民商事法律关系纠纷解决机制中,相比仲裁、和解和调解而言,诉讼是最权威的方式。诉讼的中心环节是审判,而判决书是审判的最终表现形式,发挥着确权分责、定纷止争的终局作用。虽然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裁判者(法官或合议庭)通过对每一个具体案件中的事实与法律关系的分析及法律适用的裁量而最终做出的判决书中蕴含着司法规制的方向,因此对于某一类型案件的一定数量判决书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法院总体上对类案的司法判定逻辑。面对日益“大众化”的金融活动,法院必须打破“严格主义”的束缚,从“压制性司法”走向“回应性司法”④,“通过创造性的司法活动扩展金融创新的制度空间”[2]。
基于此,为了预测分析《虚假陈述新规》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类案的诉讼将带来何种转向,对诉讼结果将发生何种影响,本文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基本原理,选取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北大法意等数据库中所收录的裁判文书作为分析样本,对2018—2022年上市公司单次或连续的虚假陈述行为所引发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进行了检索。截止2022年5月22日,通过数据检索与整理,最终得到41 489份已經公开的关于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裁判文书(数据仅从裁判文书统计所得,不排除部分案件尚未审结或者暂未公开):其中11 598份文书案件结果类型为判决,25 610份为裁定,4 281份为调解。本文主要对11 598份判决类案件的内容进行分析。为了提高对案件样本分析的准确性,本文对数据检索结果进行了处理,将组列为一个样本对象,对当前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进行统计和分析。分组的主要方法是以同一个上市公司作为被告为主要参数,对其单次或连续的虚假陈述行为所引起的同一类型(案由)的案件划分为一个案件组,最后共得到229组案件。
本文对《虚假陈述新规》中填补旧有法律规定漏洞和新增细化民事责任的两方面内容进行新旧规定的比较分析,研究目标有二:一是在于描述性统计,以此了解中国法院对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司法规制的倾向和特征;二是探究在《虚假陈述新规》背景下,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司法规制的变化,以及由投资者诉讼所引发的利益保护的变化。
如表1所示,从整体情况来看,近年来虚假陈述纠纷案件数量呈现倒V型变化趋势,在2019年出现一个爆发式增长后开始下降。其内在原因可能与2019年上海金融法院在全国首创证券类虚假陈述纠纷示范判决机制有直接联系——法院可以通过示范判决所确立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标准,引导其相关平行案件以调解或者简化审理的方式迅速结案⑤。而到了2020年和2021年,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纠纷类案件数量则有所回落,分析其原因,应该是2020年修订的《证券法》通过实体性规范的修改及特殊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引入,从而加大了对证券虚假陈述的规制力度,导致较多虚假陈述违法行为被证券监管部门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予以规制,从而减少了进入诉讼阶段的案件。从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规制渠道来看,司法规制层面的治理作用路径包含“事前威慑”和“事后监督”,并与行政处罚形成互补的治理效应[3]。这是虚假陈述类案件在《2003年虚假陈述案件规定》指引下的一个基本分布态势,那么在《虚假陈述新规》颁布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司法实践将会有哪些变化呢?
(一)取消前置程序将降低投资者起诉的门槛
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在受理虚假陈述纠纷过程中均以刑事判决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作为立案标准,即以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诉讼主张是否具有刑事判决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作为案件是否受理的前置程序。如表2所示,从已有案件来看,以证监会或其地方监管局的行政处罚为前置程序的案件占96.1%;以证监会或其他地方监督局行政监督为前置程序的案件占1.3%;以生效刑事判决为前置程序的案件占1.7%;以财政部等其他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为前置程序的案件占0.9%。《2003年虚假陈述案件规定》设置前置程序的本意是减轻作为原告的中小投资者的举证责任、统一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司法裁判标准等方面起到规范作用。但从司法实践的实际效果来看,前置程序的刚性要求也会带来对中小投资者的诉权保障不足、利益实现程序链条过长等问题[4]。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虚假陈述诉讼前置程序的法理基础和现实功能争议不断,而在实践中,一方面并非有刑事或处罚文书的虚假陈述均被投资者提起民事诉讼;另一方面法院并不完全认同警示函、通报批评等行政处理措施可作为前置程序的基本要求⑥。
《虚假陈述新规》的首要亮点是取消了虚假陈述纠纷案件中的前置程序更求,具体表现为投资者在初步掌握上市公司可能存在虚假陈述行为的情况下,即可以提起诉讼,而不必受到前置程序的限制⑦。其最大的现实意义有两点:一是使诉讼更加便利,切实保障了广大投资者合法维权的诉讼权利,真正落实了司法为民的理念,并解决了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立案难”的痛点;二是放松对于虚假陈述案件的受理限制使得投资者有机会在特别代表人诉讼以外,通过个体诉讼或者普通代表人进行维权,这其实也就是对2020年3月1日实施的新《证券法》中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司法回应,也是新规修订的亮点之一。
(二)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重大性”要件采用更加客观化的标准
虚假陈述的“重大性”要件是指可能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才有可能构成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如表3所示,案例内容分析显示,依照旧有规定,“证监会已有处罚认定”与“重要合同、重大担保或关联交易”两类事项,在已判决案件中是“重大性”要件认定的重要标准。其中,“虚增利润”“虚构营业收入”“虚构购销业务、虚增业务收入与成本”等上市公司在经营行为方面的虚假陈述行为,占直接被认定为违反《证券法》规定的信息真实披露要求的情形的比例达到了28%。由此可见,关于公司经营行为的陈述一旦不实,更容易被认为构成虚假陈述具有“重大性”的事项。典型案件为大唐电信案⑧,该公司因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虚增利润3 718万元,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未披露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被立案调查,最终被法院判决认定为其所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的情况;又如华锐风电案⑨,涉案公司因在2011年年度报告中虚构营业收入、虚增利润27亿元,最终被认定为信息披露违法;再如中基实业案⑩,涉案公司因连续多年虚构购销业务、虚增业务收入与成本、虚增或虚减利润导致2006年至2011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及重大遗漏的情形,并最终受到处罚。以上案件因涉案公司直接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违法行为的认定,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也直接采纳了行政管理部门的认定事实,即符合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标准。但其他关于“重大性”标准认定的事项比较多元化,主要根据具体案件中对于原告利益是否造成重大损害进行区分,导致实践中不同法院的认定标准不一而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为保证司法认定标准统一且明确,《虚假陈述新规》对于“重大性”的标准进行了一个符合中国实践和国际经验的修改,即第十条将“重大性标准”表述为:(1)虚假陈述的内容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事件;(2)虚假陳述的内容属于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披露的重大事件或者重要事项;(3)虚假陈述的实施、揭露或者更正导致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产生明显的变化。相比旧有规定而言,对于“重大性”这一主观性较强的认定标准,《虚假陈述新规》采用了更加客观化的判断方法,通过量化的指标对于虚假陈述的内容进行检验。若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虚假陈述并未导致相关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明显变化的,则应认定其内容不具有“重大性”[5]。并且结合上文所述,在取消前置程序的情况下,交易量以及交易价格将成为“重大性”判断的关键点,故采用“理性投资人”和“价格敏感”的认定标准。大多数情况下,“价格敏感标准”可以发挥作用,但在其失灵的情况下,“理性投资人标准”将起到补位作用。
(三)将虚假陈述与不正当披露信息行为进行区分
由于旧有规定中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认定标准较为模糊,司法实践中,判决书中并未明确对于虚假陈述的具体类型进行区分,常常出现将“隐瞒财务困境”及“延迟披露重大信息”等信息不正当披露行为也认定为虚假陈述行为。如表4所示,在本次检索的判决内容中,依据《证券法》规定而认定的虚假陈述行为的判决比例只占15%;以“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虚假记载行为”而认定的虚假陈述行为的判决比例占39%。除未区分具体类型的情况以外,“虚假记载行为”中数量居多的是“虚构收入”“虚增利润”“虚减成本”,以及“年报数据不真实”。以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重大遗漏行为”认定的虚假陈述案件占比29%,即对可能影响投资者投资判断的应披露信息未进行披露。以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不正当披露行为”认定的虚假陈述案件占比15%,此类行为除了未说明具体内容的情况外,“隐瞒财务困境”是不正当披露案件占比最多的(占54%),其次是“未就关联交易信息进行正当披露”(占24%),部分案件将“延迟披露重大信息”也作为不正当披露行为(占7%)。以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误导性陈述行为”认定的虚假陈述案件仅占5%。除在判决书中未说明具体行为的以外,误导性陈述主要为“专利权状态披露不实”(占“误导性陈述”案件的46%),其次是“披露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内容存在误导”(占17%)。
从以上案件分析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较多判决并没有将虚假信息陈述行为与信息披露不当行为进行严格区分,导致相关责任主体在抗辩时产生困扰。基于此,《虚假陈述新规》对虚假陈述行为进行了更加简洁明确的分类,不再将“不正当披露信息”行为认定为虚假陈述行为,故虚假陈述行为包括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然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证券法》第85条中,虚假陈述行为还包括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针对此项行为的认定,从《虚假陈述新规》的视域下分析,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方式等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因此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虚假陈述行为。
(四)明确连带责任中的“过错”认定标准
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在连带责任被告主体中,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占比92.5%,“董监高”占比9.6%,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起人占比8.7%,保荐人、证券承销商占比6.3%,提供专业服务中介机构占比2.8%,其他作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自然人占比2.3%,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占比1.3%(不排除部分被告主体出现重合情况)。从以上责任主体来看,主要是公司、发起人、股东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于虚假陈述民事案件承担连带责任,而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件非常少,其内在原因是对中介机构是否具有过错的责任认定较为困难。
然而,《虚假陈述新规》并没有拘泥于《证券法》第八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三条关于“连带责任”的结果规则,而是抓住了承担连带责任的逻辑前提——“过错推定”,即通过第十三条的规定确立了“故意明知”和“严重过失”的过错认定標准(也是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这就表示中介机构在共谋、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放任)和重大过失情形下将构成过错,且中介机构必须充分举证证明其并不存在过错行为才可免于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虚假陈述新规》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还分别就承销保荐、证券服务和会计师的免责划定了无过错的标准,由此建立起了“过错认定原则”+“免责事项具体化”的“统+分”认定模式,这就为中介机构充分预期执业行为的后果确立起了较为明确的红线。总体而言,“审验机构只对与其审验行为有因果关系的损害、与委托人一起向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审验机构之间连带责任的范围划分,应当根据各个审验机构的过错程度以及原因力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6]。
(五)细化独立董事责任的认定
《虚假陈述新规》对独立董事是否存在“过错”有了较为细致的阐述。第十四条其实是对第十三条“故意”与“严重过失”这两种“过错”类型的进一步细化,是对第十三条第二款“严重过失”的进一步释义。但《虚假陈述新规》并未对“一般过失”进行规定。因此,独立董事对属于“一般过失”的虚假陈述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就要求包括独董在内的全体董事不仅不能触碰“故意”这个明线,也要知道“严重过失”在日常董事工作中可能的表现形式。《虚假陈述新规》第十五条中提到“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照证券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以书面方式发表附具体理由的意见并依法披露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但在审议、审核信息披露文件时投赞成票的除外”。因此,《虚假陈述新规》明确注明了“签字即担责”的原则[7],不能说一方面反对议案,另一方面就签字赞成。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将与对公司经营管理事务享有决策权和执行影响力相伴随的勤勉义务作为责任人员划分的潜在“身份门槛”,再根据相关责任人的职责、职务、所起作用进行责任大小的考量。
(六)将“诱空型”虚假陈述正式纳入司法规制
案例分析中的数据显示,投资者因诱多型虚假陈述而买入证券的占96.5%;因诱空型虚假陈述而卖出证券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的案件仅占3.1%;案件中先后出现了诱多型、诱空型两种虚假陈述行为的占0.4%。《2003年虚假陈述案件规定》只规定了“诱多型”虚假陈述的侵权责任,没有规定“诱空型”虚假陈述的侵权责任,理由在于此类行为在实务中较为罕见[8]148。
《虚假陈述新规》将诱空型虚假陈述纳入调整范围,全面重构了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规范。诱空型虚假陈述是与诱多型虚假陈述截然相反的一种行为,常见的类型有未及时披露收购事项,如勤上光电案B11,因涉案公司未披露其于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发生的直接或间接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事项构成的关联交易,并且未按照规定及时发布临时报告被处以行政处罚;未及时披露重大交易,如彩虹精化案B12,因涉案公司未及时披露可能给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合同事项,未及时披露合同主体变更商谈事宜,被认定为存在隐瞒重大利多信息的诱空型虚假陈述行为而被处以行政处罚;未披露投资协议保底条款,诸如国民技术案B13。《虚假陈述新规》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了诱空型虚假陈述的交易因果关系是在实施日后、揭露日之前卖出的相关股票,因此此种情况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实施日前即持有股票、并在实施日后揭露日前卖出股票,另一种是实施日后揭露日前买入股票、又在该时段内卖出股票。第二十八条则根据基准日前是否买回相应股票,区分了这两种情况下的损失计算方式。《2003年虚假陈述案件规定》对于投资者主张的利益损失采用“事后视角”来计算,即以投资者是在虚假陈述被揭示日还是基准日卖出证券来分别计算,但是其存在“不符合证券市场的实际运作、诱发虚假陈述行为人的道德风险以及投资者获得赔偿过多或过少等”问题[9]。《虚假陈述新规》参照通行的“事前视角”来计算损失B14,即由于虚假陈述行为,投资者在股票交易时多支付的价款,即为投资者的损失。此外还引入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作为投资者损失计算的基准价格。由上,对于投资者证券交易损失如何计算,《虚假陈述新规》第二十七、二十八条区分了诱多型虚假陈述与诱空型虚假陈述的损失计算方法。该损失计算方法借鉴了金融领域采用较多的“事件分析法”来“事前”地计算,具有统一性强、较为公允、主观因素少以及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等优点。
二、《虚假陈述新规》对未来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司法实践产生的影响
对投资者诉讼请求的最终裁判结果进行抽样调查与分析,发现有31.4%的判决支持了全部诉讼请求;有31.4%的判决支持了部分诉讼请求;有37.1%的判决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大部分案件驳回理由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其它驳回理由还包括“损失由系统风险所致”“不具有重大性”“未能提交交易明细导致实际损失无法计算”“法院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核定发现投资者不存在损失”“上市公司已将赔偿款提存无需诉讼解决”等。案例判决结果的数据显示,针对投资者要求上述公司因虚假陈述而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在依照旧有规定做出的裁判结果中,上述三种情况分布均衡,并无明显差别。而《虚假陈述新规》在颁布生效后,将不可避免地对法院的司法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有必要从《虚假陈述新规》的新规范内容出发,分析未来的虚假陈述案件司法实践受到影响的具体环节。
(一)前置程序取消后对原告举证责任审查的影响
为方便投资者行使诉讼权,《虚假陈述新规》取消了之前所要求的前置程序。然而它的意义更多体现在民事诉讼的程序性保障方面,而对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民事案件的司法裁判来说,诉讼请求的支持仍旧依赖于原告对其主张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10]。
在原有的前置程序下,被告虚假陈述的违法事实可以通过刑事判决书、行政处罚书上的证据予以认定,这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对虚假陈述案件进行内容分析可以发现,96.1%的已有判决显示虚假陈述的上市公司在被起诉前已经受到证监会或其地方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取消前置程序后,原告(投资者)除了需要提供能够证明被告实施虚假陈述行为的相关文件、自认材料之外,还需要提供关于上市公司责任、相关责任人、损失计算等的文件材料,这将导致投资者维权成本的增加,并由此引发了举证难的后续问题。这些资料中,由国家有关权力机关作出的公文书证,诸如行政处罚决定文件、刑事判决书、交易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给予的纪律处分或自律管理措施等资料,并非是能轻易获得的证据材料,这就需要借助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申请法院调查取证[11]435-436。
由上分析可知,《虚假陈述新规》中虽然取消了原告(投资者)起诉时的前置程序,但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仍秉承“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有前置程序的案件可以简化原告对于被告侵权行为的举证义务,而对于取消前置程序的案件,法院虽然有依法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所等有关部门或机构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的职责,但这并不能增强投资者(原告)的举证能力,证据不足的起诉还是会被驳回。
(二)法院面临认定构成虚假陈述行为之“重大性要件”的新难点
基于“重大性”认定标准,如果一个虚假陈述行为属于《虚假陈述新规》规定的法定重大事件,但其未对市场产生明显影响,则该虚假陈述行为仍不具有重大性[12]。考虑到这种法定信息披露事项是建立在“欺诈市场理论”的前提下[13],因此,如果这些信息披露后市场价格或者交易量没有明显的变化,那说明原先法律在预设状态下对于市场保护的前提并不成立,这些公布出来的虚假信息没有影响市场,虚假信息披露行为人也就无需向投资者担责。
根据已有判决书样本数据分析,将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可能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即“重大性”要件)作为案件审理焦点的判决占样本的76%。由此也可以推测,《虚假陈述新规》对虚假陈述“重大性”的认定标准的改变,将成为上市公司可免责项的抗辩理由,即便上市公司被行政处罚,它仍旧具有免责的可能性,也不一定要对投资者承担责任,这将对法院如何切实维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提出了新挑战。
由于《虚假陈述新规》对“重大性要件”的认定采用更加客观化的判断方法,法院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将通过一些量化的指标对于虚假陈述行为的内容进行审查。因此,法院在对证券交易价格以及交易量的变动进行判断时,必将进行相关计算。此外,如何通过原告和被告的举证来审查判断虚假陈述责任主体是否构成虚假陈述行为,如何确定该行为是否具有重大性及交易因果关系,如何认定过错和损失,以及如何应用“理性投资人标准”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行“合理性”判断,这些都将成为未来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诉讼中法院审理的难点。
(三)法院将面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类型的审查难题
首先,《虚假陈述新规》在标题与首部就明确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侵权类”的民事责任[14],其基本意涵是将上市公司虚假陈述造成投资者利益受损界定为一种侵权,意味着其违约行为可能不带来违约责任。这就有可能使得投资者直接起诉证券交易场所违反证券交易服务义务行为的单纯违约之诉被排除在外。其次,在《虚假陈述新规》中,虚假陈述适用民事责任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存在“虚假陈述”这个行为并以此作为原因要件。根据已有判决书样本数据分析,判决书中对于“虚假陈述”的认定虽不完全统一,但基本按照“行为(原因)要件+重大性(程度/结果要件)”规则进行。由此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将面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类型的审查难题,即对责任的认定要设置“虚假陈述”与“侵权行为”的双归责要件模式,这必将导致法院对投资者的权利和利益受损事实的审查负担加重。最后,《虚假陈述新规》下,有股权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行为的股东往往成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这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履行股权转让信息披露义务过程中的不实陈述、误导陈述、延迟陈述构成虚假陈述,这就决定了基于这些虚假陈述所进行的股权交易,会产生传统民事交易行为中的违约之诉与证券交易中的侵权之诉的竞合,這也需要法院慎重审查其中的法律关系性质。
因此,法院需要重点审查投资者权利侵害的法律性质,深刻辨析致投资者权益受损的行为究竟属于何种违法类型。如果只是单纯的违约,法院判决的法律适用则不能援引《虚假陈述新规》之规定。但是法院查明投资者确实是基于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而开展交易行为的,并导致投资者的相关利益受到损害,则法院判决时可依照《虚假陈述新规》的责任认定规则,要求作出虚假陈述行为的涉案上市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四)中介机构责任认定需扩大法院对责任主体的审查范围
根据已有判决书样本数据分析,保荐人、证券承销商以及其他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最终承担连带责任的在总案件中占比9.1%,案件相对较少,原因是责任认定较为困难。对于投资者而言,惯用的诉讼策略是只要有能力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都应该作为被告,所以证券服务机构作为中介机构经常被起诉。但对于法院而言需要注意的是,《虚假陈述新规》为中介机构的免责设置了较多的抗辩事由,其基本逻辑在于中介机构的服务或者辅助行为是否构成在帮助信息披露义务人准备、整理、发布信息过程中的“合理信赖”[15]。合理信赖是基于一个行业的共识,从业者具有同等常识或者理性人的判断标准[16]。比如第十七条规定了承销保荐等机构如果“经过审慎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核,有合理理由排除了职业怀疑并形成合理信赖”,法院则应当认定其无过错。第十八条规定如果证券服务机构有证据证明其被认定构成的虚假陈述的基础工作或专业意见是经过审慎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核,并排除了职业怀疑、形成合理信赖的,也可以认定其无过错,给予相应免责。这种“理性人”判断标准不是以后来发生的虚假陈述结果为判断导向,而是以普通第三人在遭遇相同的情势时是否会采取同样的判断为参考。
因此,法院对于中介机构免责抗辩事由的审查重点在于其是否具有审慎性行为。法院需要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制定的规章与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行业的职业规范的要求,去查明中介机构的相关行为是否已经尽了审慎尽职调查,如果无法查明则该免责抗辩事由不成立。特别是如果承销保荐机构作为共同被告时,其作为中介机构是否通过正常的途径发询证函可以作为法院查明的重要方面。由此,在《虚假陈述新规》下,判断以上免责抗辩事由是否成立的标准已经较为明确,这使得法院在诉讼过程中,需要投入的判断成本增加。
(五)法院在适用“避风港”原则审查独立董事责任时需要坚持全面原则
根据已有判决书样本数据分析,“董监高”等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书占总案件的比例为9.6%,案件也相对较少,其内在原因依旧是责任认定较为困难。在“董监高”等高级管理人员的归责要件上,《证券法》用了比较严格的“过错推定”原则,即需要其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做到了尽职守则,而原告则不需要举证。《虚假陈述新规》设计“避风港原则”的本意是实现正向激励,而“过错推定”带来的举证责任会促使高管特别是独立董事在履职(比如参与讨论、参加会议或者表决时)的过程中充分“留痕”,以证明其充分履行了作为高管的注意义务。“避风港”原则并不是盲目地给予独立董事免责事项,它的逻辑基础仍然是要求高管“勤勉、尽职”[17]。因此,法院在适用“避风港”原则审查高管责任时,需要坚持全面原则,“对董事虚假陈述的过错认定,不应止步于法定的过错推定,也不应对董事的反证举证设定过高标准,应确立以司法审理为中心、对各种事实和证据予以综合判断的裁判思路和方法”[18]。
三、《虚假陈述新规》下法院维护投资者正当权益的应对策略
由于相对于上市公司,投资者在专业知识、信息获取、风险承受等方面存在天然弱势,容易错过利用诉讼救济自己合法权益的时机。因此,在《虚假陈述新规》发布后,法院要充分适应新变化来切实维护投资者的正当权益,需要考虑优化规制虚假陈述行为的司法策略。
(一)法院应首先注重向投资者释明,强化其举证能力
前置程序的取消对投资者维权过程中的举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案件受理阶段,法院就应首先向投资者释明,强化其举证能力。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是指能够初步证明其基本主张的证据,而非充分的保障案件事实能被完全认定的证据。无论是专业投资者还是普通投资者,都特别需要收集能证明虚假陈述行为与交易决定之间具有“交易因果关系”的材料,更需要高度重视能够证明依据《虚假陈述新规》第三十一条确立的虚假陈述损害与投资者损失之间具有“损失因果关系”的材料。法院审查“损失因果关系”目的是明确被告人赔偿责任的量化问题,其实质是对投资者任意主张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制。法院在判定系统风险时,“只需要求股价显著变动的定量要素,不宜强求以具体、明显的风险事件发生为定性要素,也不能以全有全无来理解系统风险的存在”[20]。因此法院需要向投资者释明,其既要提供证据证明虚假陈述造成投资差额损失,也要提供证据证明投资差额损失的佣金和印花税等次生损失,也要证明该损失是非系统风险损失。以上较高的举证责任一方面需要投资者提高自身对虚假陈述侵害行为的认知,一方面也需要法院及时固定全部事实证据,并明确各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与关联性,以及证明力的强弱。法院在运用证据进行投资者权益损害认定时,应当重点查明证据能否证明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而不能简单适用“推定信赖”原则。
(二)法院应当支持投资者申请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计算损失和固定证据
如上所述,《虚假陈述新规》对于证据的准确度要求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应当支持和同意投资者引入第三方的申请,通过其专业技术提供量化的证据以证明损失的存在以及明确具体的数额,这也体现了对证券市场专业性的尊重。因为“欺诈市场理论虽明确了虚假陈述通过扭曲市场价格影响投资者行为,但未能回答其在何时如何作用于市场价格。而有效市场假说则弥补了这一不足,指出新信息首次公开时,价格即会迅速调整至充分反映该信息的水平”[21]。在证券虚假陈述司法实践中,上海金融法院曾采用“多因子量化模型”的计算方法,通过“收益率曲线同步对比法”等,克服了无法将虚假陈述因素与其他股价变动因素予以有效联系或分离的弊端,精确地核算了投资者因虚假陈述行为导致的投資损失金额,符合虚假陈述案件中损失计算方法的立法本意和实践需求[22]。此外,《虚假陈述新规》对于独立董事责任、过错责任、重大性认定标准,以及保荐人、中介机构的连带责任进行了重新界定,且虚假陈述类诉讼本身具有行业壁垒高的特点,使得法院更加难以判断其是否构成了虚假陈述行为。因此,为了切实维护投资者的正当权益,法院可以充分贯彻司法的能动精神,充分利用律师调查证、书证、法院调查令,以及专业证券法律服务机构的协助,最大程度上减轻投资者的举证负担。
(三)法院应当衡量适用“勤勉尽责免责”与“责任区分认定”原则来认定中介机构及独立董事的责任
《虚假陈述新规》中关于中介机构及独立董事在虚假诉讼案件中勤勉尽责免责以及进行责任主体区分的规定,体现了《新规》并非仅仅考虑“投资者保护”的实践转向,而是更加注重虚假陈述纠纷解决效率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利益均衡”,这其实是充分发挥了司法保障对资本市场调节的有效性。
法院在具體案例审判时,如果将“勤勉尽责免责”与“责任区分认定”进行严格适用,即利益保护向投资者倾斜,虽然有利于保护投资者,但“矫枉过正”将会造成中介机构与独立董事等公司经营管理核心主体严格受限,危及市场整体利益,最终反噬损害投资者权益。法院在具体案例审判时,如果将“勤勉尽责免责”与“责任区分认定”进行宽泛适用,即利益保护向中介机构或者“董监高”等主体倾斜,那么资本市场的虚假陈述行为将很难得到有效规制,投资者就会对于证券市场望而却步。因此,法院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判定中介机构和独立董事能否作为虚假诉讼的被告或承担何种责任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1)是否直接策划/实施/参与了虚假陈述行为;(2)是否尽到了勤勉注意义务;(3)身份角色、知情程度、主观态度、职责相关性、专业知识背景;(4)是否能证明自己无过错。法院在对以上方面进行审查时,需要对相应事实和法律关系进行精准分析,避免错误裁判导致证券市场产生“寒蝉效应”。
(四)法院准确认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适格主体
虚假陈述的适格被告并不仅仅局限于上市公司,在案件有胜诉可能但是涉案上市公司缺乏赔付能力时,其经济实力雄厚的共同被告或许会成为责任主体,诸如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证券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
在《虚假陈述新规》的司法实践转向趋势下,法院需要更加注重责任主体的区分:1.保荐人作为承销商、财务顾问的角色下,其有义务对公众出具文件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2.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在职业领域负有特别注意义务,在非专业领域仅仅负有一般注意义务;3.董监高分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其他全职董监高和兼职董事,其责任依次递减;4.独立董事的责任标准类同于兼职董事。基于以上四项标准,法院需要重点审查虚假陈述事项是否与董监高、独立董事、甚至中介机构的职务及履职行为存在关联性以及关联程度,该事项是否超出其分管的领域之外,当事人是否履行了忠实勤勉义务。因此需要对诉讼主体是否提交了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会议等相关会议资料,甚至公司年度报告以及一些实质性发言记录文本进行审慎核查,精准区分责任主体,既不能为了维护投资者正当权益而扩大责任主体范围,更不能错误地缩小责任主体范围而无法切实保障投资者正当利益。
(五)法院可发出司法建议以保障投资者在结算机构、监管机构、交易所的信息获取权
投资者除了要提供自己掌握的有关虚假陈述的相关材料,还需要其他文件资料予以佐证,诸如因虚假陈述而引起交易的凭证、投资损失,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虚假陈述的相关证据。这些资料无疑需要从登记结算机构、监管机构、交易所等相关信息场所获取,但由于上述机构属于与虚假诉讼案件无关的第三人,并不当然地具备举证的必要义务。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这部分证据的获取无疑十分艰难,投资者个人难以做到,常常需要法院以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在这种投资者取证受阻的情势下,法院可依法发出司法建议以保障投资者在登记结算机构、监管机构、交易所的信息获取权,明确告知相关机构对于所掌握的相关涉案文件资料有义务进行提供,并明确可以具体公开、调取的上市公司文件资料,强化投资者获取证据的能力,推动诉讼的顺畅进行。
四、结语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中,民事责任的司法认定需要交织适用证券法、公司法和侵权责任法,其间必然要面对证券法的特别责任规范与侵权责任法一般责任规范的选择适用问题,更涉及如何科学运用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责任规范对证券法的特别规范加以必要修正与补充的问题。一方面,本次《虚假陈述新规》的发布,体现了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司法规制的实践转向,是中国证券市场现代化治理转向本土化建构的标志,同时其具体规制手段又借鉴了投资者保护的国际经验。相信随着《虚假陈述新规》的实施,通过对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实践中显现的特点进行一些富有针对性的规则设计,将会与其他制度一道构建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正当利益保护的全方位保障体系。另一方面,《虚假陈述新规》的具体适用依然面临着司法实践的检验,法院如何准确把握相关主体在虚假陈述责任关系中的法律属性、合理解决现有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在立法方面可能存在的冲突,以约束上市公司信息发布的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信赖利益”,在证券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双重语境下,仍然需要进一步展开实践与理论互哺的研究。
[责任编辑:张思军]
注释:
① 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民初2171民事判决书。广州中院一审判决责令康美药业因年报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证券投资者24.59亿元、原董事长、总经理马兴田及5名直接责任人、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直接责任人承担全部连带责任,13名相关责任人按过错程度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
② 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21)沪74民初4850号民事判决书。上海金融法院一审判决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因在重大资产重组中的虚假陈述行为赔偿投资者损失、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2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1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③ 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初2402号民事判决书,上海金融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虚增财务报表利润赔偿投资者支付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和利息损失等赔偿款共计1.23亿元,并以人均3 000元为标准、按本案315名原告计算律师费945 000元。
④ 法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宗旨,即力求能够说明法是怎样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据此将社会上存在的法律分为三种类型:“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本文借用这个概念意在说明司法应当秉持对金融创新的回应。具体可见塞尔兹尼克、诺内特《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性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⑤ 2019年1月,上海金融法院全国首创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即在处理群体性证券纠纷中,选定示范案件先行审理、先行判决,通过发挥示范案件的引领作用,妥善化解其他平行案件。截至2021年12月,上海金融法院通过示范判决机制共妥善化解10 683件群体性证券纠纷,平行案件平均审理时长缩短至17.71天。
⑥ 如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6227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534号民事裁定书。
⑦ 《规定》第二条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明确:首先,原告提起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诉讼,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交相应证据,人民法院就应当予以受理;其次,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后,不得仅以虚假陈述未经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由裁定不予受理。不过,为了防范没有事实根据的滥诉行为,《规定》第二条要求原告提起诉讼时,必须提交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虚假陈述的相关证据,以及原告因虚假陈述进行交易的凭证及投资损失等相关证据。
⑧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大唐电信、周寰等20名责任人员)》(证监罚字〔2008〕28号)。
⑨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韩俊良、陶刚等15名责任人员)》(证监罚字〔2015〕66号)。
⑩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刘一、文勇等8名责任人)》(证监罚字〔2014〕68号)。
B11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1038号民事判决书,广州高院终审判决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属于诱空型虚假陈述,与投资者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B12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商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系诱空型虚假陈述,投资者损失与彩虹精化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B13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1786号民事判决书,广州高院终审认为国民技术公司延迟公布利好消息的行为,属于诱空型虚假陈述,不属于《证券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应予赔偿的虚假陈述行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非受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影响;国民技术公司股价的下跌主要归结于失联事件而非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故投资者的损失与国民技术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起诉要求国民技术公司赔偿投资损失,不应支持。
B14 该观点认为投资者在买入证券时多支付的金额即为其投资差额,具体的计算方法是用买入股票的平均价格减去股票的真实价格乘以买入的股票数量。参见Causation and Fraud on the Market,NEW YORK LAW JOURNAL,September 14,2004,p.4。
参考文献:
[1] 汤欣,李卓卓.新修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司法解释评析[J].法律适用,2022(3):61-72.
[2] 王奕,李安安.法院如何发展金融法——以金融创新的司法审查为中心展开[J].证券法苑,2019(3):831-848.
[3] 徐星美,许荣,张俊岩.法律保护是行政监管的有效补充吗?——基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政处罚的实证检验[J]证券市场导报,2020(2):28-36.
[4] 丁宇翔.证券虚假陈述前置程序取消的辐散效应及其处理[J]财经法学,2021(5):3-46.
[5] 陈洁.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的新发展理念及其规范实现[J].法律适用,2022(4):48-60.
[6] 陈洁.证券虚假陈述中审验机构连带责任的厘清與修正[J]中国法学,2021(6):201-221.
[7] 邢会强.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政处罚内部责任人认定逻辑之改进[J]中国法学,2022(1):244-261.
[8] 李国光,贾纬.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评释[M].法律出版社,2003.
[9] 樊健.论证券虚假陈述投资者损失计算的“事前观点”[J].清华法学,2017(3):153-164.
[10]丁宇翔.证券虚假陈述前置程序取消的辐散效应及其处理[J].财经法学,2021(5):31-46.
[1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理解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12]樊健.证券虚假陈述重大性要件的再厘清:基于司法实践的批判性思考[J].深圳社会科学,2021(4):105-116.
[13]樊健.欺诈市场理论在公司债券虚假陈述纠纷中的适用[J].财经法学.2020(2):3-19.
[14]刑会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中的勤勉尽责标准与抗辩[J].清华法学,2021(5):69-85.
[15]薛智胜,李峰.我国债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问题的“求同存异”之道[J].金融市场研究,2022(4):28-37.
[16]徐彩云,薛智胜.原因力理论视角下的证券中介机构虚假陈述内部责任分担机制探讨[J].齐鲁金融法律评论,2021(1):110-126.
[17]馮果,王怡丞.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中责任人员类型划分的制度逻辑[J].法学论坛,2020(21):36-45.
[18]赵旭东.论虚假陈述董事责任的过错认定——兼《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若干规定》评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2):3-19.
[19]杨荣宽.连带与比例:证券虚假陈述视域下会计师事务所的“看门”责任[J].中国总会计师,2021(10):27.
[20]缪因知.精算抑或斟酌: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中的系统风险因素适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91-102.
[21]徐文鸣,莫丹.证券虚假陈述投资者损失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基于有效市场假说[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6):87-99.
[22]肖凯,张文婷,阮申正.构建多因子量化计算模型精准认定证券虚假陈述投资者损失——许某某等诉普天公司案评析[J].证券法苑,2021(2):313-327.
The Judicial Practice Diversion and Countermeasures Caus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ly Revised Securities Market False Statement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Judgments of 229 Groups of Misrepresentation Cases of Listed Companies
WANG Dong,HUO Min-xia
(Law School,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Urumqi 830012,China)
Abstract:The ne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trial of false statements in the securities market takes the tort liability of the false statements subject as the normative object,and focuses on broadening the investors relief channels,which reflects the practical diversion in the judicial regulation of false statements by listed companies.Taking the judgments of 229 groups false statements cases of listed companies as research samples,to analyze the basic situation of false statements case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t present,we can find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judicial regulation diversion.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i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false statements litigation of the future listed companies,w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estors rights protection strategy such as focusing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vidence ability of rights protection subjects,introducing the third-party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to assist in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the diligence and due obligations of intermediaries and agencies,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eligible defendants for false statements,and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ystems for registration and settlement institutions,regulatory agencies and exchanges.
Key words:listed company;false statements;judicial practice;investor;litigation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