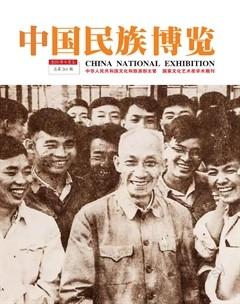基于民族审美文化视角分析《尘埃落定》中的审美特色
【摘 要】《尘埃落定》作为一部集浪漫、写实为一体的长篇历史小说,应用了独特的写作技巧和叙述方式让读者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细细揣摩这部作品,发现因为受到作者本身民族的影响,彰显出浓厚的藏族风情,不管是作品独特的叙述方式,还是作品的语言以及内在主旨,随处可见藏族简单朴素的生存哲学与独特的审美。《尘埃落定》不仅仅是作者阿莱在小说叙述方式与技巧方面的一次勇敢尝试与创新,同时也是展现民族美的代表作。本文便基于民族审美文化的视角对该作品的审美特色展开了分析。
【关键词】《尘埃落定》;民族审美文化;审美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17—014—03
《尘埃落定》这部小说中,阿来选取了“傻子”这一独特的视觉,对土司制度不断消亡的过程进行了描述,斩获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同时深受学术界的好评。《尘埃落定》之所以会取得满意的成绩,除了作者自身娴熟的写作技巧与独特的思维与审美方式外,民族文化也对其创作观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阿来其自身拥有开阔的民族文化观,然而其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又能摆脱本民族文化的束缚,能够游刃有余地在汉族与藏族两种文化灵活切换,从而把握审美的制高点,应用更全面、更广阔的文化视觉对多民族文化进行审视。
一、《尘埃落定》简介
(一)《尘埃落定》写作背景分析
《尘埃落定》的作者是阿来,其出生于四川的马尔康市,其从小在藏族地区生活,虽然从民族构成分析,其生活的地方属于藏区边缘,但是在边缘上又跟汉族聚居地接近,跟汉地接壤。阿来便出生于藏族与汉族文化的过渡地带,从小接受双重文化、语言、价值、习俗等洗礼。其最初是创作诗歌,然后逐步过渡至小说,最后再回归至真实中。其很多作品均流露出对藏族文化的深深热爱以及对藏族未来发展的关心。但是由于其在交接与过渡位置地区,以至于在文化、社会习俗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均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流动性,生活在这一特殊位置上的人民逐渐陷入了迷茫,进而引起其出现身份焦虑问题。正是在价值观念、文化身份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各类矛盾中,为了展现生活在文化过渡地区上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与不断融合的过程,阿来创作了《尘埃落定》这部小说,将新旧文化交替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作为写作背景,借此来表达自身的焦虑与忧虑情感[1]。
(二)《尘埃落定》的主要內容
《尘埃落定》这部小说中主要讲述的一个地位显赫的藏族老麦其土司,于酒后跟一名汉族的太太生下了一个傻儿子,众人都觉得这个傻儿子跟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是其却拥有超时代的预感与言行,常常做出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举措,在其他土司大量栽种的时候建议种植小麦,因为供过于求,无人问津,致使整个阿坝地区陷入了残废与饥荒的境地。为了生存,很多饥民投奔到麦其的领导下,以至于麦其家族的人口不断增多,领地不断扩大,而傻子也迎娶了当地美貌的妻子塔娜,并且在他的建议下开设了第一个边贸集市,由此其在麦其土司官寨中被族民当成英雄来对待,与此同时也遭受到大少爷的嫉妒与打击,由此拉开了一场围绕继承权家庭内部争夺之战。而故事以军队在对敌对残部进行围剿中麦其家的官寨坍塌为结局,麦其家在纷争与仇杀中灭亡,世界恢复平静,一切都尘埃落定[2]。
二、《尘埃落定》中的审美特色
(一)《尘埃落定》的叙述选角审美特色
在《尘埃落定》这部小说中,作者采取将第一人称结合第三人称的全新叙述视觉进行表示,从而带给读者“狂欢化”的审美效果。在《尘埃落定》中,阿来赋予了傻子少爷意识形态狂欢的象征,作为给予其预言家的身份,能够预见土司的灭亡时间、最终结局以及他人的命运,并由此引发老土司困惑儿子是不是傻,而正是因为傻子被公认为非正常的人,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以非常人的眼光与观念对世界进行解读,这些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狂欢化的理论。作者借助集戏谑与荒唐为一体的傻子视觉展开了叙述,这种写手手法打破了本身纯正但又严肃的情感,更淋漓尽致的刻画出了现实面前内心的压抑之情,同时还打破了现实与历史的束缚,真实与幻想的边界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的限制,最大程度拓展了表达的空间领域。作者便是通过傻子这一选角来展现自身无法直接言明的精神和情感,寄托了其对新世界进行重新审视的意图,实现了自身话语语言说与意义表达,同时也赋予了作品独特的民族审美。其原因是,傻子这一狂欢化的精神其本质跟藏族人民质朴、原始的人性以及生生不息、渴望自由的美学精神不谋而合,体现了任何规则都是不能束缚藏族人民的自由的,这样的写作方式更贴近审美,将文学作品的价值更好地展现出来[3]。
(二)《尘埃落定》的叙述逻辑颠覆审美特色
一般情形下,叙事型文学创作,不管其属于何种类型,均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律,但是一个完全悖谬的、不遵循规范、打破传统逻辑思维的作品摆在读者面前,使读者阅读完毕后便会不由自主地形成陌生化与荒诞的感受,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叙事逻辑写作技巧,但是其依然达到将真实的生活本质揭露出来的目的,具有陌生化的审美效应便于不同的读者对作品进行不同的解析,从而彰显出独特的艺术美。在《尘埃落定》中,作者便打破了传统规律,以独特的视觉,在尽可能增强小说真实感与可信度前提下,实现了真实感与可信度的颠覆,由此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面对逻辑与非逻辑形成迷惘,从而达到陌生化的阅读效果,打破读者以为传统叙述的美感。作者用诗歌文本取代了原本的叙事文本,借助诗歌拥有的超逻辑张力,将原本不可能是事实的事物变成真实存在的。正是因为叙事方面逻辑性矛盾,选取一个似傻非撒的任务视觉进行描写,目的是带给读者逻辑困惑。在文本叙事中,外人眼中的“我”是一个傻子,但是“我”又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不是傻子,如此便构成了超逻辑的“我”,又如:《尘埃落定》中一方面将“我”作为第一人称对故事进行自述,但是结尾却如下写道:“我躺在床上,被复仇者杀死了……血也慢慢变了颜色。”这句话从逻辑上分析存在矛盾,达到颠覆阅读理解逻辑的目的。作者之所以对叙事进行颠覆,是为了给读者引导一种不合情理、充满悖论的审美境界,在该境界中悲喜交加,进而促使读者身处在茫茫灰暗中去探寻生命的本色,因此采用荒诞的描写事实是为了对人们强烈的理想欲求进行反衬,相比于传统的叙事,充分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作业的创作新理念,彰显出不同民族独特审美[4]。
(三)《尘埃落定》诗歌与小说语言结合审美特色
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同时应用了象征性、韵律性、抒情性等多种表现手法,从而赋予了整个小说又如抒情诗一般的意境与韵律,从而加强了说话的声音层面与绘画层面,从而让读者不由自主地在内心形成视觉与听觉形象,直观地呈现出心理画面。例如:“起雾了。吹风了……就在这一瞬间,一切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这句话中,让读者感觉到这样的景色好似可以采取唱着歌的方式进行讲述,如此一来赋予了小说语言浓厚的诗性美特征,更重要的是还增强了小说自身的感染性与可读性。并且在叙事的间隙中,阿来采取了大量诗情的描写,例如:“风吹暖了河水……那就是冬天来到了。”阅读这部作品,发现诗意化的叙事场景随处可见,例如:第五章对时间、皮鞭的描写,第九章对城堡的刻画等等。作者应用灵性且跳跃的语言,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犹如在阅读诗歌一般,使原本的白描叙述方式中又具备诗歌的活跃与韵律,同时通过使用小说语言,而又解决了诗歌表现力有限的问题,小说语言和诗歌语言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在《尘埃落定》中通过实现小说语言同音乐语言的有机结合,从而打造出一种自然的音趣,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表达自身情感变化过程。让读者产生难以言传的感受。因此,不论是基于再现还是表现的视觉,小说语言与诗歌语言有机结合,共同为读者带来了和谐的美感。而有学者对《尘埃落定》进行评论时指出:作者拥有民族的诗化眼光。在该作品中,作者的艺术构造最明显的体现便是对其本族文化与历史创造性吸收与借鉴,兼容并蓄异域文学营养。对藏族母语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行文风格上的且诗且文”,在该小说中作者将小说语言和藏族的流传下来的诗化语言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形成开放性语境,打破了传统确定化的语境,提升了语言的表现力。因此,正是在藏族质朴和浪漫的生存风格的影响下,在诗性的历史人文精神的引导下,促使阿来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民族文学作品[5]。
(四)《尘埃落定》语言的音乐审美特色
文学语言的音乐学指的是有机组合语言的“声韵因素”,从而使其适应想要表达的情感与节奏,文学语言的音乐性跟民族语言的语言特征以及读者的审美愉悦存在紧密关系,而其是将情感节奏表现的需求作为基础的。在《尘埃落定》中作者应用了大量的叠词,从而增强了句子的灵动乐感。例如:“叮咣! 叮咣! 叮叮咣咣!”“嚓嚓,嚓嚓,嚓嚓嚓嚓。”通过重复的“叮咣”与“嚓嚓”对声音进行形象地模仿,充分体现了音乐的鲜明特征。又如“她嘤嘤的哭声叫人疑心已经到了夏天,像一群群蜜蜂在花间盘旋”这句话中,“嘤嘤”二字直接传达了声音的柔细婉转,好似蜜蜂在花间采蜜一般,同时让读者感受到了音乐的延续,同时还提升了作品舒缓又不失活泼、平稳的音乐美感。
(五)《尘埃落定》中的民间艺术审美特色
民间艺术激发了民族审美的形成,其包含了大量的民族審美心理结构以及类型众多的生命美学资源。在《尘埃落定》中,便是通过融入生命的活性精神元素,充分彰显了生命的美好,即便这对生命现象认识的方式不理性,但是依然增强生命感受强度的作用。对藏族而言,他们渴望征服恐惧、征服自然,他们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便是智慧和勇敢,这同时也是对生命的一次重大挑战。这些民间文化可以引导藏族人民在探寻自身生命价值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精神的自由和快乐,同时也凸显了藏族人民对大自然征服的企图,将命运把控在自己手中的强烈自我意识。在《尘埃落定》中,阿来通过对读者刻画这些活动,让读者感受到藏族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同时还能深刻体会藏族数千年来顽强不倒和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表达了作者对藏族原始生命之美爱爱与赞美[6]。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尘埃落定》不单单是一部族别小说,其之所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其题材的独特性以及异域风情,更重要的彰显了藏族民族的独特审美。作者阿莱将其自身对其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以及民族文化的深厚沉淀,结合民间文学素材和创作技巧,将故事的艺术性、传奇性、通俗性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为读者塑造出特定各异、具有鲜明特征的人物形象,描绘了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让傻子的命运牵动读者的心,应用复杂的人性描写引发读者深思,让读者感受到《尘埃落定》独特的民族审美。
参考文献:
[1]竺弋昱.文明与荒芜:浅析《尘埃落定》中的独特审美[J].大众文艺,2022(17).
[2]王相容,余迟宏.论《尘埃落定》的生态审美意识[J].青年时代,2015(1).
[3]张彩霞.论《尘埃落定》傻子叙事的审美价值[J].青年时代,2020(18).
[4]杨玉梅,来春刚.论傻子形象的审美价值——读阿来的《尘埃落定》[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
[5]吕佳.论《尘埃落定》叙事视角的审美意义[J].名作欣赏,2011(2).
[6]田晓箐.多民族文化交融中的阿来创作——以《尘埃落定》为例[J].榆林学院学报,2017(5).
作者简介:黄昱铭(199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202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