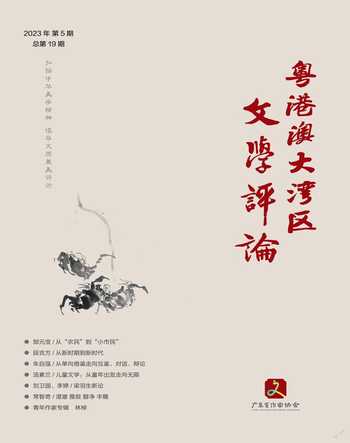亟需重新以鲁迅为本源
摘要:21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在中国化进程中增添了生机,可也还处在危机状态。如何重新辨识中国儿童文学自身并再出发?归根结底首先需要依靠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化的现代本源。而鲁迅,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驱者,因其“儿童文学”中的“中国叙事”“中国经验”与“整体性视野”而理应居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本源地带的经典中心。在此意义上,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在中国化进程中,若想走得高远,亟需承续20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界对鲁迅的接受传统,且重新以鲁迅为本源。
关键词: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化;鲁迅;本源
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人的境遇一样在中国化进程中增添了几番生机,可也还处在危机状态。特别是近年来,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愈加处于纷繁变化的生态环境当中,应该怎么办?如何“坚守儿童文学的本质与初心,思考儿童文学与民族未来的关系,与世界人类文明的关系”1?这些问题关涉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本要义,亦关涉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国化的观念内涵,需要中国儿童文学界做出思考与回应。
我以为,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国化进
程归根结底首先应该回返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本源,在现代本源处辨识自身、再出发。而鲁迅,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驱者,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本源地带,以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翻译、评论等多种样式而为“后来者”树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典范,理应居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现代本源地带的中心位置。在此意义上,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在中国化进程中,若想走得高远,亟需承续20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界对鲁迅的接受传统,且重新以鲁迅为本源。
那么,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要以哪个鲁迅为本源呢?鲁迅有其本体,但鲁迅本体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鲁迅映像,每一个鲁迅映像又有多个鲁迅面向。在百年中国鲁迅接受史中,鲁迅形象是当下的鲁迅与过去的鲁迅在未来的向度上被不断对话的产物,如果改变了当下的语境,与鲁迅对话的框架以及鲁迅形象自然也会在鲁迅本体的基点之上发生变化。正因如此,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界与中国当代文學界一道将重返“五四”时期的鲁迅作为重返“五四”传统的着力点,那么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界亦因21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由“五四”时期的“被现代”进入到中国化进程的“新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了对鲁迅形象的接受。对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界而言,鲁迅并非只是在演讲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表明“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1的“文学革命主将”2鲁迅、也并非只是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3的呐喊之声的现代启蒙思想家鲁迅,甚至并非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界所认同的启蒙思想家鲁迅,而是与21世纪中国一道同行并再生的构建“中国叙事”、面对“中国经验”、讲述“中国儿童故事”并塑造中国少年形象的鲁迅。同样是基于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所相遇的时代语境的变化,中国儿童文学界对鲁迅作品的接受视点也应有所变化,即鲁迅作品并非只是思想家或文学家或小说家或文体家的某个特定身份下的某个鲁迅作品的某个现代文体,而应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的“鲁迅文学”整体,即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应该视“鲁迅文学”整体为现代本源,而不仅仅视鲁迅“儿童文学”为现代本源。在此,“鲁迅文学”的概念在精神意蕴上部分参考汪晖的阐释观点:“所谓反抗绝望,也就是对绝望的否定,但这否定并不直接表述为希望,而是在困顿的处境中保存希望。”4,但在本文更理解为鲁迅通过多种现代文体来反抗绝望的方式,以此来保存希望,同时通过汲取西方现代主义叙事的方式来确立中国现代叙事源头,包括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叙事源头。
具体说,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国化进程亟需以鲁迅为本源,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亟需重新以鲁迅所确立的“中国叙事”起点为叙事本源。
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工作重心固然在于讲述中国儿童“故事”,但如何讲好中国儿童“故事”,才是讲述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工作难点,因此,不仅亟需承续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对鲁迅儿童观和启蒙思想的承继,而且亟需以鲁迅所开创的“中国叙事”作为叙事本源。本文中的“中国叙事”中的关键词是“中国”和“叙事”,其中,“叙事”既指叙事学层面上的中国与世界相通的传统叙事,即“叙事被视为因果相接的一串事件”5,也指叙事学层面上的中国与世界相通的现代叙事,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叙事。这意味着“中国叙事”这一概念的重心不是“叙事”,而是“中国”,即“中国叙事”是指用中国语言、中国风景、中国场景、中国手法、中国美感等中国要素进行“叙事”。鲁迅的“儿童文学”不仅具备了“中国叙事”的中国要素,而且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叙事”的本源。鲁迅的“儿童文学”不仅具有“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而且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中叙述“中国经验”的本源。
尽管严格说来鲁迅并不是专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家,鲁迅的“儿童文学”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但鲁迅因率先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驱者,其如下儿童文学实绩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本源:以“文体家”1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2讲述了少年儿童的海边拾贝壳、玩游戏、划船、看戏、吃罗汉豆、听阿长讲《山海经》、与父亲一同自制小木枪等无拘无束的快乐故事,以及背书、疾病、死亡等伤痛性记忆,既保有古典意境、也带有现代意味,展现了汉语言艺术的独特美感;以《孔乙己》(1919)《故乡》(1921)《社戏》(1922)等短篇小说中的少年与成人相交织的视角、诗化的叙事结构、民间英雄化的中国少年形象塑造,创造了中国少年小说的典范样式;以《五猖会》(1926)《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1926)《阿长与〈山海经〉》(1926)等散文、《自言自语》(1919)等散文诗、《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未有天才之前》(1924)《上海的儿童》(1933)《上海的少女》(1933)等杂文、望·蔼覃《小约翰》的译介、爱罗先珂的童话评论一并确立了中国现代儿童观,特别是确立了儿童散文、儿童散文诗、童话、儿童文学批评等多文类的文学性探索,建构了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性的多样性。其中,鲁迅特别重视汉语言的原初的古典美感——简洁、节制、留白、诗美,又新生了汉语言的现代意蕴——多义、繁复、深刻、深邃,一面通过富有温情的汉语言来讲述少年儿童的纯真情感,使得鲁迅所讲述的少年儿童故事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一面又在汉语言中内置思想的幽冷色调,使得汉语言具有丰富的现代思想意蕴。在运用汉语言叙事儿童成长的过程中,鲁迅还特别注重汉语言的白描艺术,进而通过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白描手法进行细部描写,既还原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又充分调动起读者的想象力,使人物、场景、风景等更显具象化,同时也使人物、场景、风景等更具隐喻化。3
其二,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亟需重新以鲁迅所叙述的“中国经验”为书写本源。
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主要工作难点固然在于如何叙述中国儿童“故事”,但“叙述就是回顾已经发生的一串真实事件或者虚构出来的事件。”4而鲁迅对于中国经验之一种即中国童年经验的叙述是真实的虚构,反过来也可以说,是虚构的真实。因此,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不仅亟需承续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对鲁迅的乡土中国儿童生活题材的承继,而且亟需以鲁迅所书写的“中国经验”为书写本源。本文中的“中国经验”受启发于这样的概念界定:通常指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所取得的符合中国社会国情的独特的发展经验,但还是从历史性的角度去溯源,鲁迅叙述的“中国经验”被理解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历程“中国经验”的一种——近现代中国儿童的成长经验。而且,如果说“中国经验”不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鲁迅所叙述的中国经验,亦是指“建设”,也包括“批判”。此外,“中国经验”与鲁迅所叙述的“中国经验”是独特的,但也是开放的;是自信的,但也是自省的;是首先符合中国社会、中国人的发展需求的,但也符合世界的多样性发展的。
鲁迅的“儿童文学”与鲁迅文学一道植根于“中国经验”的深处,因为“鲁迅从不离开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另外追求什么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表现手法的新奇诡异。”5而且,鲁迅的“儿童文学”所叙述的“中国经验”,不似一些时下儿童文学作家目光“横扫”的所谓“中国经验”,而是用鲁迅的目光所“凝视”的“中国经验”。鲁迅在选材上的严格确如鲁迅的自述:“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1特别是鲁迅的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像近现代乡土中国儿童生活一样纯真、素朴、温馨,但也同时与大人们一道承受着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贫穷、艰辛和困苦,读来让人感知到经久难忘的感动的力量和感伤的况味儿。例如:《故乡》《社戏》中少年“我”与小伙伴一同逮鸟、捕鱼、管西瓜、掘蚯蚓、划船、看社戏、吃罗汉豆有天下兒童的欢乐,可同时也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大人们过着“非常难”2的日子,一道与大人们遵守着不“犯上”3的行为、心理和观念。《故乡》《社戏》虽不是鲁迅“儿童文学”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但却足以从儿童视角传递出鲁迅的“儿童文学”对“中国经验”的忠实叙述。尤其是,鲁迅“儿童文学”在叙述“中国经验”时,并非将纯净的儿童视角贯穿于叙述“中国经验”的始终,而是配置以成人视角来透视“中国经验”。这样,鲁迅的“儿童文学”在叙述“中国经验”时,不只是叙述中国儿童的纯真、朴素、快乐的儿童生活,还会叙述儿童的生活问题,或者说叙述儿童的心理创伤。散文《五猖会》中儿童被父亲训导时的背书生活,杂文《我要骗人》中的小女孩被成人欺骗的募捐生活,散文《琐记》和《父亲的病》中儿童“我”被衍太太怂恿的流言生活,《上海少女》《上海儿童》中的现代儿童的早熟生活与跋扈生活……。鲁迅的“儿童文学”也正因为深入、复杂、多面地叙述了“中国经验”,才使得鲁迅的“儿童文学”中的“中国经验既具有“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也具有“世界经验”的普遍性,由此才成为了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国经验”的书写本源。
其三,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亟需重新以鲁迅所提供的“儿童文学”的整体性视野来作为视域本源。
五年前,我就曾经主要以鲁迅的“儿童文学”为暗中本源性写作资源作出这样的思考:“新世纪若想在新世纪背景上确立身份和定位,当务之急的工作便是在整体性视野下将儿童文学创作视为一个与思想文化世界、文学史(包括中国儿童文学史)世界、现实世界、未来世界相一体的世界。”4五年后的今日,我更加确信这一观点: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若想走得高远,亟需重新以鲁迅的“儿童文学”的整体性视野为视域本源。
如果从视域来说,鲁迅的“儿童文学”通常由三重视域构成:少年叙述者的视域、成人叙述者的视域、隐含作者的视域。因此,鲁迅的“儿童文学”的内容通常首先是由少年叙述者视域下所叙述的少年儿童的故事“近景”所构成;然后由成人视角下所叙述的中国社会历史“远景”所构成;再次由隐含作者鲁迅所体察的现代人类世界中的人性“光影”所构成。从这三重视域的构成来看,儿童文学除了将儿童文学作品的主体内容放置在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中进行叙述,作为“人”的意义上的“儿童”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中国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非但不能缺少,反而以特别隐喻的方式实存。鲁迅的《故乡》就是这三重视域所构成的少年儿童与成人、少年儿童与中国社会历史、中国的少年儿童与世界少年儿童、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关系的整体性叙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鲁迅的“儿童文学”之所以能够以非典型的儿童文学创作确立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原典性儿童文学作品,就是因为隐含作者鲁迅在他的“儿童文学”中内含了作为思想家型文学家的鲁迅对儿童与成人、现实与历史、过去与未来、中国儿童与国外儿童、中国与世界的整体性的体察、发现和预见。而一位作家是否有意识、有能力对他所表现的儿童世界持有整体性视域,影响乃至决定了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是否具有经典质地。以鲁迅的“儿童文学”为本源,足以发现,鲁迅的“儿童文学”的经典性特质不在于它隔离儿童世界与儿童之外的多重世界的整体性联系,而在于它以某种特别的方式与儿童之外的多重世界保持着整体性关系。不仅如此,因隐含作者鲁迅的整体性视野而使得鲁迅的“儿童文学作品”与“鲁迅文学”具有了共通的特质:“立人”为旨归的启蒙思想,悲悯情怀,不卑不亢的文化自信力,批判与建设同构的文化立场,文学性的至高标准,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相融合的创作方法,沉郁、感伤与孤独的况味儿、历史感与现实感相统一的历史叙事观念、自觉的现实关怀意识、带有凝视感的细节描写、讲究的语言语词和句子等。
需要指出的是,认为重新以鲁迅的整体性视野为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视域本源,并不是要将鲁迅的整体性视野中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等要素强行附加于少年儿童的形象塑造中,只是防控少年儿童被抽空。正如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所言:“强调‘整体性视野并不是说把成人的思考方式强加于儿童,让儿童文学走向‘成人化。始终以儿童的眼睛看世界,是儿童文学作品最牢靠的立足点。强调‘整体性视野的目的,意在引发儿童文学创作者的思考:如何处理儿童文学与时代重大命题间的关系?”1鲁迅的整体性视野不可模仿,也模仿不来。但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能否自觉地将鲁迅的“儿童文学”中的整体性视野作为一种视域本源,其质地还是很不一样的。
总之,无论发生了什么与将要发生什么,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只应、也只能以首先回返本源的方式来应对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万变。而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本源的意义上,中国儿童文学先驱者鲁迅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翻译、评论皆树立了典范,可谓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本源性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在此意义上,21世纪儿童文学亟需首先重新以鲁迅为本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规划项目“鲁迅与百年儿童文学观念史的中国化进程研究”(19BZW1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曹文轩:《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致辞》,见《为推动新时代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文学报》,2023年7月15日。
1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2 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史》,新蕾出版社2019年版,第84页。
3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页。
4 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
5 [美]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1 “文体家”鲁迅最早的发现者是黎锦明。1926年,黎锦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一文中指出鲁迅是一位“文体家”,鲁迅深以为然,有空谷足音之感。本文更多地指语言体式。
2 江晓原:《鲁迅,作为现代散文文体家》,《浙江学刊》,2003年第5期。
3 江晓原:《鲁迅,作为现代散文文体家》,《浙江学刊》,2003年第5期,第85页。
4 [美]J.希利斯·米勒:《解讀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5 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1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
2 鲁迅:《故乡》,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3页。
3 鲁迅:《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2页。
4 徐妍:《重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性视野》,《文艺报》,2018年6月13日。
1 李东华:《儿童文学:写出人类共通情感》,转自2020年7月16日光明网,原发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