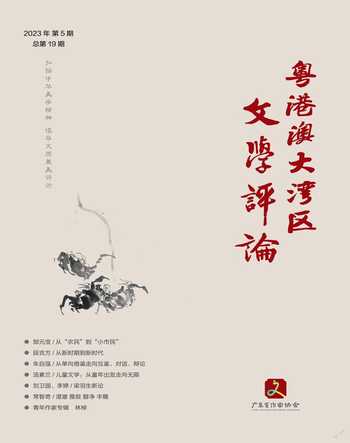《潮汐图》与十九世纪珠江口
高旭
摘要:《潮汐图》以极富张力的粤语方言和汪洋恣肆的想象,讲述了一只雌性巨蛙的游历之旅。小说兼具地方性和世界性视角,在丰富的历史资料支撑下重构了19世纪广州口岸的宏大历史。
关键词:《潮汐图》、虚构、珠江口、地方性
一、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广州口岸史
《潮汐图》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20至30年代,在疍民的渔船上,巨蛙度过了它的幼年时代,随后又沿着珠江口抵达澳门好景花园,最后航行至英国伦敦和湾镇。这是一条典型的东方海上贸易航线,也因为有了历史真实的框架,小说在前两卷里呈现了丰富而生动的清末广州口岸风景。
《潮汐图》进入历史的方式,从珠江中间的一条渔船开始。巨蛙睁开双眼打量这个世界:船只、江面、海皮。岸边有十三行夷馆,有行商、买办和事仔。只需稍加留意,我们便可以在小说中发现这些真实的历史碎片,海幢寺、琶洲塔、黄埔港、靖远街、同文街、通草水彩画,甚至是屈大均的诗句。“海皮”一章里,这些反复出现的历史词语描摹了一个熙熙攘攘的珠江口岸。
夏时行南风、打台风。行立夏南风的珠江湿湿静静。冬时翻北风。立冬北风好似回魂风。买办、通事、事仔拥着番鬼波士由澳门返归。好快番鬼大商船又入黄埔,珠江艇家又再冲锋。之后是番鬼水手放生日。番鬼水手一艇一艇登陆海皮,好似鬼门关又开;驳艇向江面乱钻,喧哗鬼叫好似发癫;珠江艇家,又要笑,又要惊。海皮不够大!靖远街同文街新豆栏不够长!番鬼水手由街头巷尾喷出去,由海皮边缘跌落去!1
广州作为明清时期最早的贸易口岸之一,自1757年颁布一口通商政策以来,逐渐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小商船密布在珠江水岸,十三行“商贾云集,殷实富庶”,每年的海关税银超过百万,是名副其实的天子南库。在此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黄埔港是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先停泊在澳门,查验货物与缴纳口岸税之后,清政府为往来船只颁发许可证,再派引水船只带领到黄埔港卸货。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颁布《防范外夷规条》管理这些来华商人,其中规定“夷商在省过冬,应请永行禁止”1,外国商人只能在每年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贸易,禁止在广州过冬,去往澳门和返回广州,都需要政府许可:
船货如已卸清,大班等应立即回国,不得逗留广州。但商船必须依季候风行驶,往来有定期,故大班亦只有在此期间内回国。如有交易未了、账项未清者,得留居澳门,不必返回欧洲,以免奔波劳顿。2
“商船必须依季候风行驶”就对应了上文中小说里“夏时行南风”“冬时翻北风”“买办、通事、事仔拥着番鬼波士由澳门返归”这样的描写。小说中有多处这样依托真实史料而生发出的想象,蛙的发现者,博物学家H“脱胎于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群像”3,作为买办的细春,作为本土画工的冯喜等等。依靠这些高度写实的历史脉络,作家复原了一个充满世俗气息的南中国贸易图景。
《潮汐图》中历史现场感的获得,不仅得益于小说中对历史地点的反复指认,也藏在一些关键性的转折时刻中。巨蛙短暫的一生与大三巴的起火、蒸汽动力船舶的使用这些宏大的历史事件叠加在一起,以想象缝合起虚构与真实。这些细节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时间线,也展现出作家从史料中获得的历史意识。历史学家以“漫长的十八世纪”和“急速的十九世纪”来区分欧洲史,对中国近代史来说,似乎也一样适用。经历了稳固结构的传统帝国,到了19世纪猛然遭受到结构性巨变。《潮汐图》的结尾,已经是鸦片战争的前夜,这也是庞大帝国转型的重要时刻,林棹在小说中以巨蛙之口,讲述了历史剧变时刻那段看似平静却暗潮涌动的历史。在珠江口岸往来商贸中,作家已经察觉到了变动前的微小讯号。
“母亲说H必死。必死的还有长辫、帆船、V.E.I.C、煤与硝、兵荒马乱的年月。”4小说里这样写道。这似乎也是近代中国史的一个缩影,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响,“长辫”“V.E.I.C”(联合东印度公司)以及附着在往来贸易之上的庞大商人群体,都成为了历史。
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以往由中国为主导的贸易模式,已经开始悄然改变。稍一检索广州口岸贸易的史料即可发现,从康熙年间到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作为贸易口岸的广州在中西知识互动与交流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术界多用“广州体制”(The Canton System)来描述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体制,鸦片战争之后则变为“条约体制”5珠江口岸的贸易,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扩张息息相关,它涉及了基督教的传播、海外贸易的扩张与掠夺。尤其是欧洲各国在华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来华商人群体,既承担了往来商业贸易的工作,也是中西文化和知识传播的中介。他们身兼多职,是商人、宗教传教士、掌握帝国知识的博物学家,正如《潮汐图》里对主人公之一H的描述:
以下即是H——持牌药剂师,博物学家,鸸鹋眼高阶会员,岭南十大功劳(Mahonia cantonense) 和七星眼斑龟(Sacalia heptaocellata)发表人,鸦片贩子——前半生故事,我未曾参与的部分。
事实上,H这个人物的塑造非常具有典型性。H作为西方商人群体的代表,他的传奇发迹史依靠的却是鸦片贸易积累的财富。小说中,H作为“神圣辛布里大公国”的领事,除了本职的工作之外,还热衷于搜集岭南植物标本。药剂师、博物学家和鸦片贩子这三种身份,也象征了全球扩张的脚步中,西方对东方的物产进行科学帝国主义式的描述。受到西方商人喜爱的外销画,不仅是一种纪念品的存在,也是一种知识传播的方式。《潮汐图》里多处用反讽的语调来描写这种西方猎奇视角下的南中国。
这是怎样的一个广州城呢?一方面,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精美的商品吸引着外来商人,另一方面,他们也带着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来审视着这个“停滞的帝国”。早在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1768年,英国人威廉·希克(William Hickey)的游记中就曾形容过十三行的繁荣:“这里有玻璃画工、制扇工匠、象牙工匠、漆器匠、宝石匠及各种各样的手艺人”1小说里写到的画师冯喜,就是职业的外销画家,他摹仿学习了西方的油画和水彩画绘画技巧,创作出适合当时的畅销画,“珠江四景、三百六十行、大船小艇、花鸟鱼虫、人物肖像,万千皆有”2对外贸易催生了广州新兴职业的诞生,画工、制扇工、象牙工,以及为外商服务的买办、事仔、引水人,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才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
美国商人威廉·亨特这样描述1825年的珠江口的繁华:“从内地来的货船、客船、水上居民和从内地来的船艇、政府的巡船及花艇等,数目是惊人的。此外,还有舢板,以及来往河南的渡船,还有些剃头艇和出售各种食物、衣服、玩具及岸上店铺出售的日用品的船;另外还有算命的和耍把戏的艇——总而言之是一座水上浮城”3围绕十三行贸易产生的商船、花艇、舢板和渡船,和岸上的制扇工、画工、宝石匠等共同组成了珠江口岸一片繁华的商贸图景。
与下层社会与外商的密切交往相反,当时的官方政府对在华商人群体有着诸多傲慢和自大的轻视。清政府不仅颁布了严格的限制令来规定外商活动的时间、范围,禁止他们私下雇佣仆人,禁止与政府指派行商之外的人贸易等等。例如1830年10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时任英国商馆特选委员会主席的盼师(William Baynes)偕妻子从澳门来广州,两广总督李鸿宾以“番妇”住进商馆违背旧例为由下令驱逐。也是同一天,李鸿宾发现外国人在广州乘轿,大怒下令严查。英国人盼师作为特选委员会的主席,都没有权利带妻子来广州,更何况那些普通的随船大班和医师。这一举动也引起外商的强烈抗议,进而不断冲击了稳固的“广州体制”直至破灭。
《潮汐图》以巨蛙之眼审视这个世界,在细节处展现了广州口岸的日常贸易生活。细春、冯喜这一类新兴群体,已经在旧世界的胚胎中破土而出。尤其是小说的第一章“海皮”和第二章“蚝境”,分别对应了19世纪贸易体系中关键的两地广州和澳门,为宏大的晚清中西贸易史做出一些感性的注脚。
但历史远比小说更驳杂。近代中西关系以鸦片战争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从所谓的“旧中国贸易时代”(old China trade time)或“广州贸易时代”,变为西方殖民者主导的条约口岸通商,晚清的来华商人群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动者角色。这也涉及了19世纪西方“中国观”的转变,哈罗德·伊萨克斯(Isaacs Harold Robert)把18世纪美国对中国的印象定义为“敬仰的时代”(the age of respect),把1840-1905这一时期定义为“蔑视的时代”the age of contempt 1在广州贸易时代的后期,来华商人群体已经通过自办报刊如《广州纪事报》《中国丛报》等向西方提供关于中国的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蒸汽动力汽船能够迅速通过虎门水道而不用受到清政府的控制,这些在外商群体中的变化,迅速改变了广州贸易体制的结构,而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却丝毫没有发现这些变化的先兆。
事实上,外商群体并非传统意义上广州贸易体制中的弱者,清政府下辖粤海关对进出口贸易的监管,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密。鸦片战争前,生活在珠江口的这一批外来商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管理着中西贸易的基本走向。19世纪初广州口岸的政治与商业实态,反映出了中西贸易权力格局的变迁。在全球史的背景中重新审视广州口岸贸易,能够清晰地看出處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的位置和处境,以及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嬗变的艰难历程。
二、想象如何重塑历史?
让我们再次回到小说,林棹在《潮汐图》里究竟如何以想象塑造了这一段广州口岸历史呢?作家的本意肯定不在照搬历史材料,而是以出色的想象力完成了一次文学重构。
《潮汐图》开篇第一句话“我是虚构之物”,已经奠定了整篇的基调。有趣的是,虚构之物不是人类,而是一只两栖动物。从蛙的视角来审视,许多不可能的沉重的现实主义,能够瞬间飘浮起来成为可能。小说中有许多抒情性浓厚的段落,从巨蛙的忧郁到珠江的漫游,都写得灵气十足。比如写“珠江游,一味向东。在逼近大海的时候珠江已是极大,它的分量压低地层、荡平山丘,稍一翻动就使横跨天穹的经线颤动不已”2这里能读出屈大均《广东新语》里摘录的怪力乱神的影子,雷神、山神与南海神,想象奇崛。
林棹还设置了一个“讲故事的人”,出生在“省城建设四马路某工人新村”的蛙之母。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林棹对“虚构”的技术性关切,“讲故事者”的主体身份的强调,与穿插进的真实资料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
《潮汐图》所打开的地理空间十分庞大,随着巨蛙的游历版图不断扩大,19世纪初的中国广州、澳门和英国生活图景,都一一展现了出来。作家对广州十三行的描写尤为细致,空间感强烈。比如对各处方位布局的描写:
“十三行街,”细春答,“沿街西行,几步即到行商公所,总商大官办公议事处;向东行,过回澜桥,直通木匠广场和谷埠。”2
根据一份1843年绘制的十三行分布图,各国商馆与领事地规则地排列在江边,中国行商的商行分布在北侧,与之相邻的还有“炒炒馆”和“水手店”,为泊船的水手提供补给。《潮汐图》里既有真实的地名,也有来自作家的虚构文学版图。想象拓展了书写的地理边界,抵达幽微的深处。
同时,作家讲述故事的声音,是不断交叉与回溯的,比如开头写巨蛙的幼年遭遇到了断尾事件,与时间线上的澳门产生了交叠:“断尾失踪在一八三二年。那时我已远在澳门了。”以全知视角透露了巨蛙之后的命运轨迹。在写到历史重大时刻时,也有多重声音:
照豆皮亚弟讲法,那日上午,他照例步行去板樟堂前地采买。刚过议事亭就听到大炮台方向传来轰鸣,好似山基慢慢崩——那是六点正,因为支粮庙小子正好走出来敲钟。……烧剩一块残壁的三巴堂立在西侧。现时人家不再叫它“堂”,改叫“牌坊”。3
据史料记载,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1月26日,大火烧毁了澳门圣保禄学院及其附属的教堂,只留下一堵门壁,也就是后世所称“大三巴牌坊”。这里林棹不仅使用了历史真实的时间(1835年)来标注H破产自杀的关键时刻,而且还以叙事者的视角对这一事件进行解构。“现时人家不再叫它‘堂”里的“现时”,是讲故事者的时间,与巨蛙的时间线索形成了交叉、重叠、分流。
小说中常常以真实的历史时间为虚构划定疆域。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终止,此后来华商人多以散商出现,在这条真实的时间線上,作为东印度公司雇员的H破产自杀,巨蛙乘船远赴大英帝国。巨蛙的生命轨迹是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流动的,历史真实为小说虚构划定了疆界。这似乎也提示我们想象的限度:小说三个部分中,“海皮”和“蚝境”讲广州和澳门,“游增”讲英国伦敦。前两部分因为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调研经验的支持,文字更能够铺展开来,也更加饱满。而“游增”一章只涉及帝国动物园和湾镇,在地理空间上较之前的两地,就少了很多灵动丰满的想象,想象力和语言的敏锐度都呈现了下降的趋势。人物塑造上也似乎可以着力更多,作为来华商人代表的H,作为“新人”的冯喜,其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也远比小说中立体。
当然,正如林棹在后记中所自陈的那样,“我们一起行过真实和虚构的珠江、它流经的真实和虚构的土地、它汇入的真实和虚构的大洋。两种光景以双重曝光的形式相印”1那些通过想象力生成的形象,是如何在复杂的历史中间站立起来的?那些历史真实是如何制约想象力的发展的?《潮汐图》的写作正是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找寻一种最合适的黏合方式,找到叙述者主观声音与历史言说方式之间的有效平衡。
三、地方性与世界性:“新南方写作”
何以可能
《潮汐图》中地方性的获得,不仅依赖对珠江口岸自然景观、物候条件等南方风物的赋形,还体现在林棹在写作时的一种观察世界的自觉。小说中呈现的珠江口岸形形色色的人物、风景、语言,天然具有了区别于北方书写的特质,这是作家的创作优势。那种蓬勃的面向海洋的描写,使小说拥有了一种流动的海洋气质。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海洋书写——关于海洋的书写和具有海洋性的书写都是缺席的。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即使有关海洋的书写也基本是‘海岸书写,即站在陆地上远眺海洋,而从未真正进入海洋的腹地”2而《潮汐图》提供了一种真正的“海洋书写”,是站在出海口向外探索,是在连接、交流和互动之中形成的地方性。对传统中国人来说,海洋或者海岸线意味着陆地的边界,它框定了人类活动的范围。从《潮汐图》里巨蛙的旅行开始,那种以北方或者陆地为中心的叙述被打破,形成了一种面向未知海洋的空间,提供了新的文学审美范式。
方言土语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增添了《潮汐图》的地方特质。粤语方言经过加工和改造,形成了一种独属于林棹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这也有一种去中心主义的尝试,大量粤语词汇带来的阅读的陌生化,挑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在“中心/边缘”框架下挖掘地方视角,恰恰契合了小说所展现的19世纪初珠江口的历史背景。作为晚清政治格局中偏安一隅的最南方,与1824年粤英词典《通商字汇》,共同冲击着古老中国稳固的权力结构。
正如巨蛙不仅会讲水上话、省城话和皮钦语,还认识一点福建话、荷兰语和葡萄牙语,19世纪珠江口岸的港口、人群和社会,都一样被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与世界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巨蛙从澳门登船航行,周游列国的故事,更像是一部文明交融的历史。东印度公司的船舶从欧洲码头出发,满载版画、烛台、镀金刀、鼻烟壶、望远镜和西班牙蜡烛这些象征了西方知识技术文明的物品,经过马六甲海峡抵达珠三角,又在季风时装载铜器、生丝、茶叶、漆器、刺绣品和珐琅器驶回欧洲大陆。在《潮汐图》里像H这样的西方商人眼中,东方是神秘的、蒙昧的西方文明参照物,而巨蛙的旅行是与之相对的他者视角。因此,小说不仅提供了一种“西方如何认识中国”的视角,也展现了“中国如何认识西方”这一历史命题。
19世纪的珠江口岸,还产生了许多具有世界精神的新人。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潮汐图》与程美宝的《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和大世界》一书之间的互文关系。《遇见黄东》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英商怡和洋行的档案中有一份中国打铁匠的手写单据,里面写了各种船舶零件的英文词汇英译。一个身份低微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底层人,却能流利处理与西方商人之间的贸易需求,并且得到外商的认可,这是独属于广州口岸社会体系的因应。有趣的是,《潮汐图》里也提到了类似的情节,为H服务的佣人“哥仔”,不仅能和主人进行流畅交流,还学会了用西方的烹饪方式来加工食物,做出主人满意的“咖喱牛”“猪脚冻”“周打汤”“梅挞”和“油煎鸡忘记”这样的西方餐食。
《潮汐图》里的文学讲述,向我们展示出早期全球在地化的多重场景。与晚清政府的高傲自大相比,身处珠江口岸的普通人在与西方商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和适应了外来文化,并且创造出了适合本土的表达方式。无论是冯喜以西方水彩的方式描摹中国景观,还是十三行商馆的事仔用广州的食材烹饪西餐,又或者巨蛙在漫长的旅行过程中学会了多国语言,都是中西文化在碰撞中产生完成了文化的在地化。
从文学的角度,《潮汐图》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的特质呢?在复杂立体的清代广州贸易史、社会史、民俗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之外,林棹以修辞建造了一艘通往19世纪历史迷雾的小船。即使是通过巨蛙之眼,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时期面临的剧烈变化和动荡,感受近代转型前夜的东方帝国摇摇欲坠的讯息。
从这个角度出发,《潮汐图》的出现无疑具有某种开创意义。在自然风貌之外,小说提供了一种现代性的审视,一种新的历史解读方式,一种在政治、经济、宗教和商业之外的,文学的感性表达。因此,《潮汐图》是一场站在珠江口的创作实践,它不仅解构了那种南/北二元对立的传统结构,重现19世纪广州口岸的日常,还写出了一种流动中的世界性。
这似乎完美契合了近年来“新南方写作”的期待。作为一个正在不断生成的概念,“新南方写作”包含的精神气质和对审美变革的需求,与我们常见的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岭南文学”或者“粤港澳大灣区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有着一种命名的焦虑,但“新南方写作”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话语阐释和建构的标尺,也不断提醒我们,地方路径与地方视角,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想象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潮汐图》更像是借由19世纪广州口岸历史的文化寻根。虽然小说中三章分别对应三个不同的地点,但真正的精神原点却只有巨蛙的发源地珠江。林棹对处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是真实地褒有着爱和同情,也能在《潮汐图》讲述的两百多年前的巨蛙的丰富的、混沌的世界背后,读到一种现实的隐忧。《潮汐图》本意不在于勾勒一个遥远时代的历史,而在于作者以一个当代的眼光来观察和审视世界。因此,在漫长历史的航道中,我们有理由对林棹的书写怀抱更大的期待。
1 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2 [美]马士 Morse. H. B:《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5卷,区宗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3 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82页。
4 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8页。
5 根据吴义雄教授的研究,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西关系是动态演变的,经历了再建构的过程,西方商人集团为了打破“广州体制”,为自身谋求最大化利益,在行动上和舆论上都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变革。参见吴义雄:《商人集团与中西关系建构——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体制的再认识》,《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1 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9页。
2 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66页。
3 [美]威廉·亨特 William C. Hunter:《广州番鬼录 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1 Isaacs Harold R. Scratches on Our Minds. West-port: Greenwood. 1973. PP.70-71.
1 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79页。
2 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9页。
1 林棹:《被“虚构”引领,沉入神秘陌生的文字国度》,《文学报》,2022年1月13日。
2 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9页。
3 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98—199页。
1 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81页。
2 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