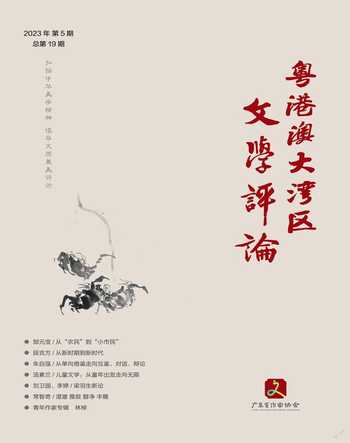探寻词与物:理解《潮汐图》的一个视角
李雨轩
摘要:林棹的《潮汐图》中存在着一个容纳不同阐释要素的深层框架,即对词(语言)与物之关联的自觉省思,具体包含词与物的状态、秩序和实践。就状态来看,小说中的词与物都呈现出“过剩”的特点。就词的秩序来看,作者依据小说的结构和进程对方言、白话和翻译腔进行调配。就物的秩序来看,作者表达了万物平等的理想,并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就实践来看,博物学表征着人对自然、帝国对殖民地的双重统治关系,物之物性被其褫夺。就此而言,小说中蕴藏着一种可能性解放,也即走向词与物的“断裂”。
关键词:林棹;《潮汐图》;词与物;博物学
林棹的长篇小说《潮汐图》初刊于《收获》杂志2021年第5期,并于2022年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这部小说以其宏大的视野、奇特的设定、异质的语言和深刻的意蕴,获得了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潮汐图》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很多研究者从虚构形象、叙事风格、方言书写、新南方写作等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均可谓切中肯綮;但小说还存在一个容纳不同阐释要素的深层框架,即对词(语言)与物之关联的自觉省思,目前还少有研究者就此进行重点论述。笔者拟以“词与物”为主题对小说进行探析,具体可分为词与物的状态、秩序和实践这三个层面。就方法来看,将语言问题设定为研究重点之一,要求我们对局部文本进行较为精细的析读。
一、词与物的状态:同构的过剩性
《潮汐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呈现物的丰富性,作者在多处直接采用了铺排、堆砌的方式。比如全书第二小节介绍海皮(泛指珠江边缘),有一段集中的物之呈现:“海皮住客有:红毛鬼、白头鬼、花旗鬼、荷兰鬼,瑞国鬼、马拉鬼,佛郎机鬼、法兰西鬼,个个在海皮开公司,被立夏南风吹来,被立冬北风打去;有差人、打手、乞儿王,烂瘫、卤莽、半日清醒醉酒鬼;……有蝉,有凤蝶、粉蝶、蛱蝶;……有糖霜,经年累月敷在白银之上。”
这些物的堆叠固然有介绍当地自然风物和社会环境的功能,但又不止于此,至少另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小说的标题“潮汐图”暗示了作者的跨媒介实践或曰“艺格敷词”(ekphrasis)的目标,作者借由小说所要完成的是一幅幅图画,所以客观上需要呈现丰富的物象,并且对物的铺排、堆砌也基本与图画中物象的排列方式同构。其二,知识的语言形态在此显形。如对蝴蝶的介绍,凤蝶、粉蝶和蛱蝶都是依据科(family)的层级对蝴蝶所作的分类,这表明物的排列具有一定的知识属性。虽然作者并非要展现纯粹的博物学知识,但这种知识形塑了作者书写的结构和形态。其三,这些物是如此之多,甚至可以说有意违背了简洁原则而达到了“冗余”的程度,形成了笔者所谓物的“过剩”(surplus)。“过剩”不是剩余、残骸、遗迹,sur-和plus这两个词根的语义都指向“更多”“超出”“过度”。
提出“过剩”概念之后就能发现,《潮汐图》中的语言也同样呈现出“过剩”状态。文中有一处描写细春行船的沿途景象:“鹭鸶惊飞!水鸭惊飞!金龟、蛤乸、秧鸡,飞飞跳跳,鸡飞狗跳。芦竹林里有民熙物阜千年鸟兽帝国哩。”在这个细部的描写中,“鸡飞狗跳”不论从语义还是用词上看都是对“飞飞跳跳”的重复,这是一处典型的语言过剩。还有一处写鸬鹚胜利用鸬鹚捕鱼:“鸬鹚胜越?越勇,焕发童颜,万寿无疆;鸬鹚泄气,束手就范,瘫作粮袋。”这一处的描写采用了对仗结构,鸬鹚的“束手就范”和“瘫坐粮袋”之间是一种语义顺承的关系,但鸬鹚胜的“焕发童颜”和“万寿无疆”之间则明显存在一定的跳跃,这是因为“万寿无疆”有强烈的夸张意味,从而中断了前后两个表述之间的语义顺承关系,将自身显示为“过剩”。同时“万寿无疆”所带有的夸张意味显得“过度”,“过度”也构成了“过剩”的内涵之一。因此,此处的语言过剩同时体现出两种内涵。
文中还有一处写巨蛙对酒精的感受:“我讨厌酒精,讨厌它的气味、口味、回味、回忆。”通常意义上的书写表现为词对物的指涉、涵括、模仿和追踪,物总是占据第一位,词则退居第二位。但这里的四个名词几乎摆脱了词与物的关联,它们的排列受制于词本身的关联机制,即从第二个词开始,每个词都保留了前一个词的其中一个字并替换了另一个字。每一次的替换都产生了新的语义,即使是在语义上非常接近的“回味”和“回忆”,后者也比前者范围更大。虽然每一次替换都產生了新的语义,但综合四个词来看,仍可以说形成了语言的过剩。赋予这种过剩以正当性的,正是这种前后呼应的语言游戏。这种语言的过剩体现了鲍德里亚所谓“拟真”(simulation)的超真实性:当拟像(simulacre)模仿拟像而悬置现实之时,它也就取代了现实。这里过剩的语言就是一种悬置了现实的拟像。
纯粹的语言过剩主要表现在非名词的书写中,以动词性、形容词性表述为典型。而一旦涉及名词,物的过剩和语言的过剩就自然合流了。从事实层面看是如此,从理论层面看也是如此:将词与物进行并置、关联是作者自觉的实践。文中有一处描写巨蛙对海底沉船的感受:“我向着大船尸骸去。它不再是大船尸骸,而是变乱的签文,永失解签人;是所有被母亲剔除的定语的漩涡,是折断的腐烂的段落的渊薮。我命运的线索发着噗噜声一串串升起,我不复存在的注脚浮游,废稿碎成粉末,错谬的标点摆荡似鱼群,词条被海沙深埋。”这一段话值得细读。首先,作者在物与词之间建立了一种隐喻的关联,作者连续使用诸如“定语”“段落”“注脚”“标点”等一连串与“文章”相关的词语,与海底的物象分别对应,营造了词与物相互交融、难以分辨之感。并且,作者在语句的行进中悄无声息地完成了隐喻的逆转:第一句是以“大船尸骸”作为主语,先呈现本体再呈现喻体;其后,主语则变成了“废稿”“标点”“词条”等喻体。这种隐喻的结构性逆转在深层上表征着词的反客为主,表征着词对物的彻底征服。
再者,这一段话由沉船的残骸开启,却最终落脚于巨蛙自身,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巨蛙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叙述。巨蛙将自己还原为一个语言的存在,或者说是一个虚构的存在。这与全书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虚构的自我揭示——息息相关。巨蛙在开篇就强调自己是“虚构之物”,其后又不断提及这一点,使小说呈现出明确的“元小说”特质。但实际上,不仅是巨蛙,小说中其余所有的人和物不都是虚构之物吗?与其说作者是在进行某种元小说的反思,不如说她在进行一种跨层的越界实验,在探索小说的叙事哲学。词对物的取代在此处与小说自身的本体存在产生了关联,作者以巨蛙直指小说创作行为本身。
文中还有一处介绍H的寓所:“新领事寓所墙壁丁香紫,三组木百叶窗蕉叶绿,壁炉仔、乔治亚风格大柜单人床、黑酸枝写字台包绒脚凳四枝吊灯并黄铜灯笼钟,山水屏風红木盥洗架并彩瓷盥洗套组等等寰球词与物,尽在此搁浅。”这一处其实只是对物的呈现,但作者却有意使用“词与物”这个表达,从而突出了这一连串描写本身的语言属性。这种对语言属性的强调,揭示了语言的自我指涉性和自我反思性。它表明《潮汐图》中词的过剩与物的过剩不是彼此无关的巧合现象,而是统一于作者对词与物的整体性、自觉性思考。
在一次访谈中,当吴俊燊询问作者“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1时,作者再次提及她在小说中援引的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我们扬帆远航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夸夸其谈,而是为了享受超越语言的,纯粹的发现之美。”2这句话可作两种理解:一是未知之物在固有语言之外存在,不断“发现”的过程就是未知之物不断显形的过程;二是纯粹之美本身超越了语言,语言对某些经验的指涉和表达存在着自己的界限。不论哪种理解,都指向语言自身的限度。作者随即又引用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话:“我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世界的界限。”3这直接表明作者对语言与世界(词与物)的关系有着自觉的思考。不论是维特根斯坦还是海德格尔,都强调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首先奠基于语言并以语言为界限,这正是“语言学转向”的重要理论遗产。
二、词的秩序:方言、白话与翻译腔
刚翻开《潮汐图》时,有如迷失在语言的丛林中。连续不断的方言好似迷宫,将读者团团包围。但随着阅读的推进,语言异质性带来的震惊感逐渐平复,我们又体验到熟悉的语言。其实,这是作者对词(语言)的秩序进行有意识的构造的结果。依据巨蛙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群体,可将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巨蛙与海皮原住民的故事,第二部分是巨蛙与H等外商、买办的故事,第三部分是巨蛙在欧洲的故事。这三部分的语言使用也不相同,李德南准确地指出:“除了粤语,《潮汐图》也使用标准国语,以及翻译语言,这三种不同的语言,出现于不同的空间和场景,也对应着巨蛙不同时期的生活历程。这样的语言试验,并非出于形式的单一需要,而是与对象、内容紧密结合。”1
在这三部分中,第一部分的语言运用是最精彩、最传神的,这里拟对其进行细致分析。方言运用是其中一个明显特点。作者不但在人物对话中采用粤方言,还用粤方言进行故事本身的叙述,并融入大量的方言歌谣、谚语等。针对海皮“水上仔女”使用方言,是符合人物的历史真实的;但将其融入故事叙述则是一个风格学问题。作者之所以使用粤方言,还需要从这种语言本身的肌理中去寻找原因。作者在访谈中说:“写作《潮汐图》的时候,更吸引我的是粤方言当中那些活力强劲的、带有风物水土烙印的因子。”2粤方言本身具有未被完全驯化、规范的民间特点,显得爽利干脆、生动熨帖、一针见血,作者对方言的使用正是为了吸纳这种活力。同时,作者在对语言的关注中寄寓了对物本身的关注,作者重视语言对物本身的激活。可以说,这也是对当时整体性的历史经验、生活状态的恢复与贴近。
精彩的方言运用的确是《潮汐图》语言的重要特征,但仅从方言角度理解还不够,至少还要看到另两个方面。其一是与民间“讲古”艺术的关联。在粤语中,“古”不单指过往之事,而是泛指故事,“讲古”就是讲故事、说书。《潮汐图》与讲古本身存在密切联系,文中既直接写到讲古及其语言,又以开篇题记“听古勿驳古”展现了小说与讲古的整体性关联。讲古作为语言艺术讲究“开相”,强调对首次出场的重要人物进行全方位描摹,力求以语言形式呈现出鲜活的形象。试看小说对契家姐的介绍:“契家姐,罗圈腿,蟒蛇腰,巨臀轰然”,“契家姐的大脚,睡觉时向外一伸,船尾棚罩不住,悬向江面大过水师船船楼”。此处的语言符合“开相”的要求,并有意进行幽默式的夸张,体现出鲜明的讲古特色。小说第三小节写阿金不幸去世,其详细情境是通过契家姐的转述来介绍的。这里的语言颇值得关注,从标点符号使用看,契家姐的转述不是间接引语,而是直接引语。她的话中既有事态描述,也有人物对话,尤其是其中一句评论,“此一句,吹埋来似大阴风,吹得满天人头脚板嗡嗡作动”,不但注意了押韵,还生动地渲染了当时的情状。契家姐在此俨然化身为老到的“讲古佬”,身处故事内又欲跳出故事外,承担起双重功能。小说第五小节还直接叙述了盲公讲古的内容,“故事”的内外根本没有鲜明的风格差异,内文本(讲古本身)、外文本(对讲古的叙述)都是讲古。尤其是中间由破折号开启的两段,甚至无法让人轻易分清其究竟是内文本还是外文本。如果说方言给予了小说丰富的词汇和口语的形态,那么讲古则影响了小说语言的韵律、节奏,提升了小说语言的质感。
其二是与典范白话的间杂和调配。比如小说第一小节写《弔秋喜》与南无咒在江上的遭逢,这里本身呈现出不同语言风格的多声部对话,作者有意让不同风格的语言在此间碰撞、较量。就具体描写来看,伴随着歌声的是江上啸叫着的大风,先是“乱拨”桅杆,最后将桅杆“吹碎”,可这时作者将其描写为“似吹散一撮鸭绒”。要关注此处语言本身的韵致,“一撮鸭绒”本身体现的轻柔之态与前文的猛烈之势形成强烈反差,使文势由生猛磅礴突转为柔婉清丽,节奏也相应变得舒缓。这样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它们使方言与白话得到了平衡,也调配了叙述的节奏。
上述主要讨论了小说第一部分的语言问题,而第二、第三部分则不但几乎放弃方言,采用白话写作,甚至使用了一些“翻译腔”和欧化汉语。有一处写巨蛙观察帝国动物园内的动物,羊驼是“一个光膀子、长脖子的怪东西”,“马来貘喜欢用浑圆的、上白下黑的光屁股对着我”。这两处都采用了多项定语的并列,使单句拉长,而典范的汉语多用短句,尤其不习惯多项定语的并列,因此这里体现了典型的欧化语法和“翻译腔”。这种语言实验一方面彰显了作者强大的语言调用能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小说精巧的结构设定,使小说的语言与小说的进程相呼应。
我们还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小说的第二十三小节?它位于小说第三部分,却突然又将笔触重新伸向海皮。从内容上看,这是对第八小节的接续,补叙标本师老鲍和那只金鸡的故事。这一节采用全知视角来叙述,应该将其理解为作者的自我现身。虽可简单将其理解为一种对小说结构、叙述节奏的组织和调配,但必须承认这也表征着一种语言的“回魂”,是作者钟爱、熟悉的粤方言的回光返照式的再度显现。
三、物的秩序:反思人类中心主义
如果说词的秩序是对语言之不同体式、风格的调配,那么物的秩序则是对人与物之关系的形塑。作者在小说中对万物平等共生的理想秩序進行了文学式的表达。从物的角度看,作者对物采用了一种普遍的拟人式描写。比如写蒸汽火车“每天进站三次,排出一肠子乘客,得意地大叫,跑走,奔向强光外的新世界”。这里不但借由动词、形容词表现其动作和情态,还特别使用了身体性词语。再如写楼,“混血小楼紧拥着,用伤疤、病变、雕花边饰诉说”,“我们钻入楼的私处”。作者实际上描述的可能是楼房中西结合的风格和残旧破败的状态,但她使用的语言完全是拟人化的。还有写风和帆,“风躺进帆里睡觉,帆就受孕。帆大大地隆起了。帆分娩,船滑进港口”,这是对帆的形状变化的形象描写。与一般的拟人修辞不同,作者更倾向于从血统、疾病、性、生育等角度切入,为物赋予人的身体性存在。这些物不仅拥有人的情态,还拥有人的肉身——万物与人均有其感性肉身。从更深的层面看,对这种现象的分析不能仅停留在修辞层面上,还应看到其背后体现的一种泛灵主义视角,也即认为一切物都有其生命、身体、感知,并将物与人等而视之。
在《潮汐图》中,人与物的关系是混沌、模糊、暧昧的,在这种浑然一体中透露出平等的意味。这种“平等”有着不同维度。首先,人与物的“平等”具有反讽性维度。作者借迭亚高之口说:“帝国人对待人,倒更像对待货,那些茶、丝、生棉花。帝国人把人捆起像捆木料,推入底舱塞满。帝国人让园丁精心服侍一花一木,免得它们在海上染病、死掉;帝国人让园丁给植物浇水、驱鼠、防风,领植物去呼吸、晒太阳。可是,在帝国人眼里,人倒是不必呼吸、不必动换、不必见光的货哩。”此间人与物地位的颠倒是以异化的占有关系为根源的,帝国列强及其代理者是这种颠倒的中介,物正因被其占有才获得了更高的地位,换言之物本身并未得到凸显。主导这种人—物之颠倒关系的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其次,人与物的“平等”还具有真正的本体性维度。《潮汐图》的主要视角是一只巨蛙,这既是一个身具东方传统的物象,又贴合海皮的水上生活。以非人视角进行叙述并不简单意味着对人类视角的冲击,除非这个非人主体真正具有异于人的特质。巨蛙恰恰符合这一要求,她并不是一个乔装了的人类,她就是一只巨蛙。巨蛙与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最初通过“生吞”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这首先是一种泛灵主义的设定,通过吞食对象以认识对象、获取其能力,它是对弗雷泽(J. G. Frazer)在《金枝》中提炼出的“接触律”的极端化和变态化,“在将一个人身体的某一部分吃进肚里的同时,食人者也就获得了被食者的特性”1;但它同时还有着精神分析的维度,这一点来源于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家对文化人类学的吸纳,弗洛伊德1915年版的《性学三论》“引进了口唇组织的观念,食人行为成为此一心性发展阶段的特征”2。在这种模式下,主体对吞食对象同时呈现出破坏和保存的悖论性关系。这样一来,巨蛙的吞食性就成为人的一种早期发展阶段或一直与人相伴随的隐秘潜意识。巨蛙不是人,但似乎也是人——原初之人或隐秘之人。巨蛙向人自述:“你看见我,我,肥大、丑陋、疣疮密布,皮肉无一处平整,呼吸恶臭无比,我就是一座咕嘟嘟冒泡有机粪池,我和我的展台冒犯了你和你的文明世界”。巨蛙的异质性使其成为对“文明世界”的反观和对照;而其受挑战的异质性又显示出与人暧昧不明、千丝万缕的隐秘联系,使其内嵌于人类世界。
巨蛙的吞食性还具有超越人的象征意味。巨蛙帮水哥去水底取货,在此过程中她吞食了一具男尸,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同时吞下一个男人、一个番鬼、一个死人”。这曾是她隐秘的渴望,现在终于被她付诸行动。这一情节具有典型的象征性,它象征着对人—物之固有等级关系的僭越,即物超越于人之上。巨蛙与人的差异、对人的僭越使其很多观点、看法都饱含着对人的困惑和质疑,人与物的平等诉求就在其中显现出来。
再次,从更深的角度看,人与物的平等还体现在语言维度。文中有一处写迭亚高父亲的降生,迭亚高的祖母腹部传来阵痛,作者写“宫缩引来索科特拉岛又将它推远”。作者实际要描写的应该是分娩过程中船的行进,但她创造性地在人的生理空间、感受空间(宫缩)与岛的位移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这是一种语言的组织形态,它从更深刻的维度体现了人与物的平等关系。这是另一维度的词与物之关联。
当然,人与物的平等本身包含物内部的平等。作者毫不避讳地描写屎、尿、屁等“秽物”,便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让我们自然地想起《庄子·知北游》中的一段话: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3
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又不断举出形而下的例子。这传达了一种万物平等观,而其本体论基础是“道”寄寓于万物之中,万物平等乃是因为它们同等地分享着“道”。更为重要的是其后的一句话,即“物物者与物无际”。陈鼓应将其理解为“支配物的和物没有界限”4,这是准确的;但后人在理解时误解了其主语,因而产生了一定的混淆。“物物”的主语不是人而是道,“物物者与物无际”强调的是道与物的相融性;其后所谓“不际之际”和“际之不际”,都是强调道与物之界限的暂时性和可消解性。从整体语境来看,这段话最终强调的还是物与物的关系,而非道与物的关系,因为万物都保持着与道的关系,所以万物之间也是平等的。由《庄子》反观《潮汐图》,作者对屎、尿、屁等的描写要放在物的秩序这一角度来理解,作者所要实现的正是对物的平等秩序的塑造。
作者在小说中明确使用了“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术语,“人类世”虽然在构词上以“人类”(Anthropo-)为中心,却从根本上体现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作者所要反思的“人类”,是肇始于启蒙运动的典型主体,自身拥有强大的主体性,对万物进行“祛魅”。尤其在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对自然的无限扩张、侵略和征服。正如小说所预示的那样,“人正在开发一种低温透明,专门用于贮藏、展览月球。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人要用钢铁手臂盗取星体,用比海洋更大、比水滴更小的人造透明贮藏劳碌的行星、飞逝的流星和无星宇宙的寂静”,人要将万物纳入自己的收藏。而从巨蛙的角度看,巨蛙一经人类发现就不断与“人造物”发生关系,甚至用人造物命名自己回忆的各个阶段,比如生命最后的“澡盆时代”,还有此前的“船底时代”“鱼盆时代”“花园时代”“动物园时代”,这些前后相续的人造物不仅展现了巨蛙生活场所的变更,还表征着她是如何一步步被不同的社会群体给调教、驯化、规范的,巨蛙的“人性”在被动中不断增加,她自己固有的“物性”却在不断丧失,或者说在等待一次“触底反弹”。
四、词与物的实践:博物学与帝国
有研究者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潮汐图》1,这很有道理;但若将其置于作品的深层框架——词与物的关联——之下,便能对帝国的“殖民”有更深的理解。作者借助了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视角,深刻地展示了词与物的实践。博物学本身是西方与世界相遭遇、碰撞的结果,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应对未知事物的尝试:“面对这些未知事物的出现,十八世纪的欧洲演进出一套认识世界的崭新方法,那就是让东西与其原本的脉络分离,仅以肉眼可见的特征为基准进行分类、排列、整理。这就是所谓的博物学。”2福柯早就向我们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紧密关联,虽然他在《词与物》中对博物学的论述中并未涉及这一点,但从其整体思想看,知识—权力的理论模型是完全适用于此的。
就人与物的关系看,正如范发迪(Fa-ti Fan)所论,“在帝国背景下,博物学的活动——制图、采集、整理、分类、命名等——不只代表探求事实的科学研究,也反映出(某种文化定义下的)认知领域的侵略性扩张”;而就国与国的关系看,19世纪的这些科学考察的最终目的是要“全面而精确地书写全球博物史”3,这种想法是与欧洲扩张相伴而生的。也即,欧洲的博物学家对万物的命名表征着欧洲人对万物的征服、占有、收藏,同时暗示着欧洲对世界的同一进程。这种复合的过程体现了一种科学帝国主义(scientific imperialism),所谓博物学完全是参照欧洲的“科学”标准建立起来的,各国参与者必须主动汇入这一范式才能得到认可。
小说中的H就是一个典型的博物学家,“他同时漫步语言和物种的丛林,把少校的博物学目录越搞越厚”。当H决定“收编”巨蛙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该把巨蛙“关进哪座笼舍”,而是怎样将其恰切地安置于博物学谱系之中,这棵“谱系树”力求不断延展,最终“吞下宇宙万物”。博物学作为一种知识实践,集中体现了词与物的关联:当巨蛙说H的博物学图鉴是“吞吃新词的怪物”时,这直接展现了物种作为词在图鉴中的存在形态,以及物种作为词在现实中的存在形态。图鉴取代了现实,词取代了物。巨蛙最终变成了Polypedates giganteus,这一由作者杜撰的拉丁语词组,其意为“巨大的树蛙”。
博物学还与图像有着深刻的关联,具体言之就是对各种未知的动植物进行图绘,制成图册、图鉴等。中西绘画的交流和碰撞产生了中国洋画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其“典型地综合了欧洲艺术与中国艺术的风格元素”,其风格“是一种中国俗民画与西方写实主义的混合”1。这是因为当时的洋画画师采用了西方写实主义的技法,如透视法及明暗对比法等,从而使传统绘画呈现出新特征。而洋画这种新形式被广泛地运用到博物学中。这涉及对小说人物冯喜的理解。冯喜一开始跟随一名耶稣会士学习洋画,后来遇到詹士,又掌握了炭笔画、油画和水彩,直到他遇到塞巴斯蒂安。H评价冯喜“处理动物像刽子手——‘一画即死‘把南美土人画成木头雕像”。冯喜所面临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范式危机”,他只学会了用西方写实主义的技法来画植物,却还无法用其画动物和人。詹士与H的“惊天宏图”其实就是绘制整个岭南的博物学图鉴,而之所以只有塞巴斯蒂安才为这项计划带来曙光,倒也不在于他的技法怎样高超,而更在于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本身置身于西方绘画的传统之中,天然与这种博物学图鉴的范式相契合。作者借由冯喜及其绘画技艺的进展、瓶颈,展现了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认知范式的中西碰撞。
作为词与物的实践,博物学对物的记录也意味着对物的剥夺。福柯在对博物学的剖析中已指出其中词与物的原初性、必然性分离:“在这种语言的语言(langage du langage)面前,物以其本身的形态(caractères)出现;但在这种现实中,物又从一开始就与名称(nom)分割开来。”2也即,在物被命名、记录的同时,其丰富性、完整性(也即物性)也受到了剥夺。呈现在博物学中的物永远是一个片面、破碎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帝国动物园完全与博物学相同构。这些奇珍异兽既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是作为其余国家的一部分而被“收监”的。帝国动物园同时体现了人对自然、帝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关系,或者说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这两者本身就统一于欧洲列强的实践。当巨蛙将H的博物学图鉴称为“无情帝国”时,这里的“帝国”便同时拥有上述两层含义。从思想倾向上看,作者对词与物的这种片面连接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小说“对帝国博物学实践的再现和批判”,既可视为“对帝国话语政治的隐喻式批判”3,也可视为对帝国现实行动的批判。
五、结语:走向词与物的“断裂”
博物学所表征的词对物的征服和褫夺,有无可能被引向解放?在对鸟类跨洲运输的讽刺性描写中,作者引用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具体引文出自第一卷的《序诗》:“维纳斯,生命的给予者,/在悄然运行的群星底下,/你使生命充满航道纵横的海洋”4。对于那些在世界范围内搜集、运送珍奇鸟类的人来说,“使生命充满航道纵横的海洋”的代价是更多生命的陨落和凋零。但卢克莱修的原著指向更深远的东西,“物性论”是对拉丁文“De Rērum Natura”的翻译,意为“论物的本性/本质”。卢克莱修意在阐明物之“物性”,而这项事业在海德格尔及当代的思辨实在论、新物质主义等理论中获得了生动回响,在中国亦产生了“物性诗学”的创构。这些都为重审《潮汐图》中词与物的关系提供了视角。
塞巴斯蒂安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恃才傲物,却有着崇高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理想。他要前往北极画北极熊,这种追求远不止于艺术本身,它代表着一种不断远航的意志。也正是这一点使冯喜对他由嫉妒转为敬佩,并催生了冯喜自己的远行意志。“塞巴斯蒂安永恒穿行于蓝颜料的水面、绿颜料的岛屿”,他本身超越了帝国的意志和知识的诉求,他追求的是纯粹的物,他要创造的也是纯粹的图像,物与图像在此间交融。
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看,词与物的关系由相互无涉發展到彼此连接,这一过程有其意义,否则人既不能认识万物,也无法发展自己的理智。正如小说开篇,巨蛙追溯了所谓“洪荒时代”的特征:“那时刻大地为我准备好了,但光秃,不着一物。字符滔天翻涌,无方向,无意义。”没有了词对物的秩序化,世界就无法向主体呈现意义。巨蛙吞噬自己的卵,只觉无限悲苦,这昭示了伦理生发的必然性;巨蛙无法吞下自己,也就无法认识自我,这揭示了其认识方法本身的局限。国内学者张进在物性诗学的创构中提出了物性的三个阶段——附魅、祛魅和返魅。1返魅即是重新认识到物中蕴藏的不可穿透性、神秘性乃至神性,即是认识到人作为能动主体、语言主体的限度。在其中,人与物的关系、词与物的关系都被重构了。词与物的“断裂”不是回到最初的“无涉”状态,而是重新认识到“物”本身的不可抵达性。人最终记起自己身处“世界”之中,在世界之中存在,与万物共同存在。这是《潮汐图》给我们的启示。
1 林棹:《潮汐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本文对小说的引用均出自此版本,以下不再注明具体页码。
1 林棹、吴俊燊:《在语言的边界出海》,《文艺报》,2022年1月28日,第5版。
2 [英]刘易斯-琼斯:《航海家的笔记本》,木同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注:帕斯卡的原文出处尚不明确,但由于上述转引版本与作者引用的中文表述相同,故推断作者也引自同一版本。
3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韩林合译,商務印书馆2013年版,第92—93页。
1 李德南:《世界的互联和南方的再造——〈潮汐图〉与全球化时代的地方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7期。
2 林棹、吴俊燊:《在语言的边界出海》,《文艺报》,2022年1月28日,第5版。
1 [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赵立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2 [法]拉普朗虚、彭大历斯:《精神分析辞汇》,沈志中、王文基译,行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3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62页。
4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63—664页。
1 林培源:《“去帝国”的虚构之旅——论林棹〈潮汐图〉的叙事特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2 彭兆荣:《“词与物”:博物学的知识谱系》,《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3 [美]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
1 [美]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
2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6. p.142.
3 李德南:《世界的互联和南方的再造——〈潮汐图〉与全球化时代的地方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7期。
4 [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方书春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页。
1 张进:《物性诗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