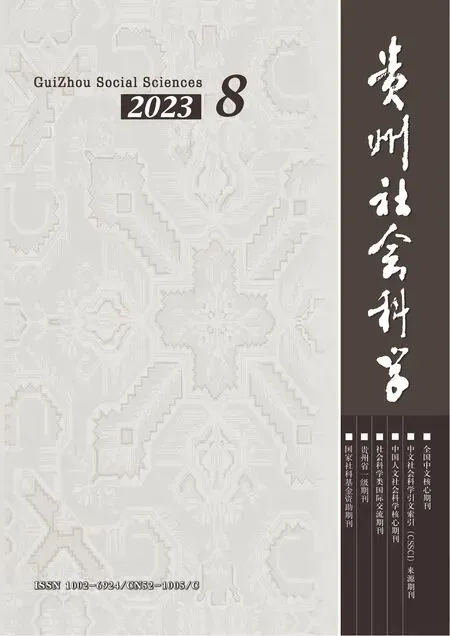试论元代大儒吴澄诗歌中的出处情结
孙文歌 吴光正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南宋被元廷征服后,出处问题就成了由宋入元的南方士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作为元代南方最著名的理学家,吴澄在其一生中先后七次被元廷征召、启用,最后官居二品,其子孙也凭借着元廷赋予官吏的荫袭特权跻身官僚阶层。但是,吴澄出仕元廷的经历却颇为奇特:在第一次被征召时选择了拒绝,其他六次任命或未到职,或在职时间非常短,所有在职时间加起来,在地方仅三月,在京师不到五年。仔细分析吴澄创作的诗歌,我们发现,这一特殊任职经历与吴澄颇为纠结的出处情结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学术界目前很少有人关注。[1]故此,拟根据吴澄的仕宦感悟和体道思维来分析其诗歌中的出处情结,进而揭示其精神风貌。吴澄出生于1249年,卒于1333年,入元后生活了将近六十年,其诗歌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出处情结足以反映元代南方士人的精神风貌,值得我们深入剖析。
一、吴澄的仕宦感悟与诗歌创作中的出处情结
吴澄年轻时“尝作草屋数间,而題其牗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2]860这种自比诸葛亮的用世志向,在由宋入元的南方士人中显得独一无二。铨改举废的现实让绝大多数南方士人失去了进入仕途的门径,作为其中的幸运儿,吴澄尽管由布衣超升至二品京官,尽管欲有所作为,但其仕途业绩却颇令人失望:“稽其立朝之日,未尝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师道尊重;劝讲内廷,诚意深远;与大议论、大事,虽可概见,而无悠久浃治之功者,非人之所能为也。”[2]865吴澄几乎每隔十年就会获得元廷君臣的荐举、征召,但几乎都以无所作为告终,这必然会在吴澄的内心产生极大的冲击,形诸于诗歌创作,便呈现出浓郁的出处情结。
吴澄的入仕机缘有二。一是根脚大臣的荐举。第一次荐举他的根脚大臣是他的同年好友程钜夫。吴澄十六岁拜临汝书院山长程若庸为师,从此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成为好友。1275年,抚州郡守降元,程钜夫以郡守侄子身份入质元廷,深得元世祖赏识,1286年以南台侍御史的身份奉诏求贤江南,强起吴澄至京师。吴澄以母老辞归后,程钜夫特向元廷推荐吴澄校订的《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元廷令行省加以誊录,进呈国子监,令诸生拜读。此举对于提升吴澄在朝野的学术声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次荐举吴澄的是根脚更为深厚的董士选。他是世侯董俊的孙子,与父亲董文炳在元廷进攻南宋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296年,吴澄游龙兴,在元明善的引荐下拜访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被董士选视为平生未见之“天下士”。1297年,董士选拜行台御史中丞,入京奏事,首以吴澄荐,但是中书省官吏“颇缓其事”;1298年,董士选佥枢密院事,亲自到中书省,向丞相完泽和平章军国重事不忽木推荐吴澄,得到首肯,但由于不忽木改任御史中丞,不久得病而亡,荐举一事也就没有下文。[3]429直到1301年,吴澄53岁时,元廷才授其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编修官,董士选特地写信勉其应召。吴澄入京履职,却发现职务已被他人代去。董士选上章抗议,认为这种行为有失朝廷崇儒重道之意。在董士选等人的努力下,元廷于1304年任命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并于1308年任命吴澄为国子监丞。
二是儒治君臣的征召。到了仁宗、英宗、泰定时期,由宋入元的南宋士人已经凋零殆尽,如当年一同被程钜夫征召至京师的赵孟頫在1322年就去世了,就连一直护持他的两位根脚大臣程钜夫、董士选也先后于1318、1321年去世。这一时期,正是元廷大力倡导儒治的时期,仁宗恢复了科举,英宗甚至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推行儒治,享年甚高的吴澄成了南方儒学的一面旗帜,多次被元廷君臣礼遇、尊崇。1317年,在仁宗的过问下,吴澄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特命集贤修撰虞集给驿聘召。1323年,右丞相拜住以“有德老儒”为由,向英宗推荐吴澄,英宗遂任吴澄为翰林学士,遣直省舍人刘孛兰奚给驿聘召。集贤直学士为从五品,翰林学士为从三品,吴澄的这两次任命,均属于超格提拔。1324年,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泰定帝命中书平章政事张珪、学士吴澄等人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1325年,吴澄与张珪同时告老。1326年,泰定帝诏加吴澄资善大夫(二品),赐中统钞五千贯、金织文币二表里,特遣翰林编修官刘光至家传旨。吴澄的这些殊荣,与奉行儒治的中书平章政事张珪密切相关。吴澄知经筵,就是出于张珪的推荐。1326年,张珪再拜翰林学士承旨,首以吴澄荐:“翰林学士吴澄……聪明经学之师,当代寡二,虽恩赐存抚,为礼甚优,然合召还,资其学问,良非小补。”不久,又举以自代,期待吴澄能够完成“两朝实录”“辽金宋史”这样的大工程:“虽曰年近八十,其实耳聪目明,心清力赡,今不使身任其事,后必追悔无及。近朝差官优赐存问,礼意诚厚,然须使当承旨之任,总裁方可成就。所合举以自代,允协舆论。”[2]864
尽管有着迥异世人的入世志向,尽管获得了元廷君臣的青睐,但是,吴澄的出仕却是被动的乃至是失败的。吴澄随程钜夫入京,是以观光中原为理由的,此举表明吴澄对于出山为元廷服务是抗拒的。程钜夫不顾他的意愿,准备将他的名字写入奏章复命时,吴澄当即以母老为由,辞归江南。他向赵孟頫辞行时给出的理由是:“吾之学无用也,迂而不可行也。”[4]此话不假,但其拒绝出仕的根本缘由还是在于内心有强烈的遗民意识。翰林应奉文字、国史编修官之召,江西儒学副提举、集贤学士之命,吴澄均不愿意赴任。董士选私信敦请,吴澄却引用邵雍的诗句婉拒:“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教巢由作外臣。”[5]17其拒仕元廷的立场依然未变。在官府的督促下,吴澄才在任命下达一年多后抵达大都,结果发现执事者以官旷别授他人了。儒学副提举之职,吴澄两年后才在儒学提举司的催促下前去上任,此前一直以养病为由推迟赴任,后来甚至动身前往衡岳观光;上任三个月,他便以疾谒告,就医富州:“五旬之内,本司遣学职催请者六,吏人催请者四,文移往复凡数十,又移省宪趣还,公固辞以疾”。在他看来,“学校教育各有其职,钱谷出入,总之有司,提举之官,本为虚设,徒糜廪粟,故勇于辞职。”[3]430他在《答姜教授书》中则表示,自己不需要像他人那样,“为饮食之费、妻妾之奉、子孙之遗”而出仕。[5]24一句话,他对这个职位没有兴趣。集贤学士之命下达时,吴澄刚好有病,久无行意。虞集告诉他:“此除实出上意,宜勉为行。”[3]431行至仪征,吴澄便以疾病辞谢征召。国子监丞之命,吴澄也是在官府具礼敦遣的情形下才赴任的。在国子监,吴澄兢兢业业教导学生,甚至想改革国子监的教学模式:他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6]4012“同列欲改课为试,行大学积分法,公谓教之以争,非良法也。论议不合,遂有去意。”[3]431吴澄弃官南下,教法四条未及实行便寿终正寝。对于吴澄的弃官南下,“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2]862。嗣后,集贤院官员到中书省,请以国子祭酒召吴澄还朝,平章李孟亦予以拒绝。“近臣以先生荐于上,而议者曰:‘吴伯清,陆氏之学也,非朱子之学也,不合于许氏之学,不得为国子师。是将率天下而为陆子静矣。’遂罢其事。”虞集、邓文原抱持同样的改革态度,结果遭到北人同僚的攻击:“于是纷然言吴先生不可,邓司业去而投劾为矫激,而仆之谤尤甚。”[7]吴澄教法改革的失败,反映了元廷南北儒士之间的竞争,揭示了南方儒士在元廷发展的艰难困境。在翰林学士任上,照理吴澄应该有所作为,最后却不得不以失望告终。吴澄本不愿意赴任,使者告诉他:“上欲用先生已久,所以来召之意,必欲见先生,宜毋自辞。”[3]432可惜的是,吴澄六月在大都上官,八月南坡之变爆发,征召他的英宗和丞相拜住被反对儒治的权臣杀害,吴澄连英宗都没有见到,英宗交给吴澄的唯一一个任务《金书佛经序》也来不及完成。十一月,泰定帝即位,吴澄便打算回归江南,因河冻无法行船,只好作罢。吴澄在泰定朝曾对太庙昭穆之次发表过自己的见解,认为宗庙叙次应该遵循金宋旧制。但是,“有司急于行事,竟如旧次云”,这让吴澄大失所望,“已有去志”,[6]4013在修完《英宗实录》后,吴澄便治舟南归。可以说,这次出山,政治上毫无成就可言。
吴澄的入仕尽管很被动、很失败,但他对元廷君臣的荐举、征召是满怀感激的,其心中的抵触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转化为对元廷的认同和拥戴。对于程钜夫的荐举和照拂,吴澄自是满怀感激。1293年12月,程钜夫抵达福州,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1294年正月,吴澄便专程前往拜访,直到11月才返回江西老家。1300年,程钜夫官拜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吴澄于1302年秋赴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一职前,特意拐道武昌,拜访程钜夫。两人之情谊,于此可见一斑。董士选之于吴澄,其间“势位之相悬”可谓天壤之别,董士选既荐之于朝,“又先之以翰墨,敦请谆谕,如前代起处士之礼”“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荐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来所希有也”。这样的恩情让吴澄感到“虽木石犹当思所以报称,而况于人乎”![5]17吴澄辞官归田后,元廷派大臣抵家褒奖,吴澄在《谢赐礼币表》中回顾了自己被朝廷礼遇的历程:“惟成宗法至元,首贲邱园之隐;历武宗逮延祐,荐升馆阁之华。先帝擢之禁林,今皇处之经幄,讲读古训,对扬耿光。”最后表示:“虽心同葵藿,常恋阙庭;奈景迫桑榆,宜归田里。”“臣栖迟畎亩,固难彊筋力以输忠;教诲子孙,誓当竭精神而报上。”[5]9由此可知,在元廷不断的眷顾下,宋廷的“草莽臣”已经彻底内化为元廷的“精忠士”了。
吴澄的这种仕宦经历、仕宦感悟在诗歌中呈现出浓烈的出处情结。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意蕴。一是出处有道。1275年,吴澄所在的抚州归附元廷,作为宋朝乡荐的吴澄本来没有作遗民的义务,但是,吴澄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遗民自处的。此一时期的诗作,吴澄以儒家的出处之道对南宋官员的出处进行了评判。乐安县丞黄酉卿拒署降状,吴澄对其气节钦佩不已,1277年避乱华盖山时还作《怀黄县丞申》,表达自己的怀念和敬仰之情。1276年12月,他在《和桃源行(效何判县钟作)》一诗中指出,在“冀州以北健蹄马”面前,南宋已经没有唐代坚守睢阳的张巡那样的英雄了,举目所见,“总是开关迎拜者”;他指责南宋官员不能像“元亮至今尚东晋”那样坚持自己的操守,为南宋守节。他伤心不已,将自己描述为“血泪交流草莽臣”,即使“拟学渔郎棹舟入”,也要像张良那样,心中始终想着为故国复仇。[7]3261278年,吴澄作《伯夷传》以明志。1280年,吴澄在《和答枝江令何朝奉》诗序中指出:“时予服道士服,读书巴山之阴。”[8]290巴山之阴即是他和乡贡进士郑松隐居四年之久的布水谷。他的这一举措应该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萧立之便有《赠崇仁吴幼淸逃儒入老三首》纪其事。对于自己逃儒入道的心迹,吴澄在《和答枝江令何朝奉》中有清晰的剖白:“生平辟老凛如秋,一旦番成老氏俦。晋士无心入莲社,楚累有兴托丹邱。”[8]290一向讨厌道教的自己不得不穿上道士的衣服,就是为了像陶渊明和屈原那样效忠故国,坚守出处气节。1287年,程钜夫强起吴澄至大都,吴澄最终还是选择了为南宋尽忠。在北上途中,他作有《徐州怀古四首》《采石渡》《泗河》等纪行诗,触目伤怀,兴亡之感溢于言表。在南归的舟中,他连撰三首诗表明自己坚守的出处之道:“周召分方伯,酂留著世家。西山二子薇,东陵故侯瓜。”“子房为韩心,孔明兴汉事。三代以后人,卓伟表万世。”“扬雄莽大夫,陶潜晋处士。男儿百岁中,盖棺事乃已。”[8]220第一首诗歌宣达了出处的两个境界:出仕尽忠者,就应该建立如周公旦、召公奭、张良、萧何那样的功业;如果自己的国家被颠覆,为臣民的就该像柏夷、叔齐那样不食前朝之菽,就该像亡秦的东陵侯召平那样在汉朝种瓜长安城东。第二首是对为韩国复仇的张良、恢复汉室的诸葛亮的赞叹,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这表明,尽管此时南宋已经灭亡十来年,吴澄心中依然还有光复南宋的幻想。第三首提到易代之际如何保持气节和操守的问题:扬雄屈身侍奉王莽,陶潜坚守晋室臣节,这两个正反典范是每个士人生前都应该牢记的。必须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元廷君臣不断的荐举、征召,吴澄这种忠于南宋的出处情结慢慢在消退,并进一步转化为对元廷的尽忠情结。
二是出处有时。如前所述,面对元廷君臣的一次次荐举、征召,吴澄总是显得不情不愿总是显得被迫无奈,其中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坚信一个原则——出处有时。吴澄不是不愿意出仕,而是觉得自己的学问无补于时。他拒绝程钜夫的荐举,向赵孟頫辞行时便表明了这一观点。对此,赵孟頫深有同感:“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莱岩穴之间,老死而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并且表示:“吴君之心,余之心也。”[4]吴澄对于学问的生命是无比自信的。他在《感兴诗》其十九中就曾指出:“批导郤窾际,出入齐泊中。解牛与蹈水,万理一道同。”[8]220他化用《庄子》典故指出,任何事功,只要掌握了“理”,一切均可迎刃而解,大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豪迈气概。但是,学问如何成就事功,关键在于“时”,即需要恰当的时局和环境。他在《感兴诗》其二十中指出:“千金屠龙技,百金不龟乐。一壶济中流,五石叹濩落。”[8]220此诗化用《庄子·列御寇》《庄子·秋水》《鹖冠子·学问》《庄子·逍遥游》典故,强调任何技巧、器物,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功效。《感兴诗》其二十一则进一步说明时局、环境乃是人才实现其志向的关键:“汉皇弃梁傅,郑公负唐帝。君臣际会难,礼乐竟沦废。”[8]220贾谊才高却被汉文帝用作梁王的太傅,魏征做的是修修补补的诤谏工作,未能引导太宗制作礼乐,实现三代之治,有负唐太宗的信任。一个才非所用,一个用而未能效其能尽其才。其《题诸葛武侯画像》诗云:“含啸沔阳春,孙曹不敢臣。若无三顾主,何地著斯人。”[8]221指出刘备三分天下、在沔阳称汉中王就是因为三顾茅庐礼请诸葛亮出山。从这两首诗可知,吴澄强调的“出处有时”,是指出仕需要明君,“出处有时”的最高境界是如刘备、诸葛亮那样的君臣遇合。吴澄的这种体认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在《题蹴鞠图(并序)》作出了如下论述:“聚戏人间混等伦,岂殊凡翼与常鳞。一朝龙凤飞天去,总是攀鳞附翼人。”[8]235对于入仕元廷,吴澄从“出处有时”的角度给予了否定:“箕畴八政目,末师首食货。井田封建后,此事如何可。”“踰济巢鸲鹆,入洛啼杜鹃。大事可知已,禽鸟得气先。”“风前白浪恶,雨后黄流浑。公无渡河去,天未丧斯文。”[8]220这三首诗是《感兴诗》中的既有对元廷重用聚敛之臣的抨击,也有对南士北上将会被北人当作灾异排挤的预判,还有用白浪和黄流比喻仕途之险恶、期望自己和友人能够全身而退、转而弘扬理学捍卫道统。应该说,吴澄对“时”的分析是敏锐的,他的历次入仕就是因为“时”的问题而宣告失败。这大概是元代所有南方士人的共同命运,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吴澄识见之敏锐!
三是出处有命。如前所述,从1286年开始,吴澄几乎每隔十年就面临着出处的选择;1287年从大都归来之后,随着声望的提升,不断有游士请他题诗写序,以资交游。吴澄慢慢发现,出处是自己无法左右的,他将之归结为天意:“夫士孰不欲遇且达也,而其遇不遇达不达,系乎天,岂人所能为哉?”[5]1831302年,吴澄北上赴任,途中写下了《徐道川〈次文生韵〉,仍韵奉呈》一诗:“北行往往值齐年,先后冥符岂偶然。却幸筋骸尚康健,又将步武接英贤。行藏非我由天意,久速何师赖圣传。况有兰金同志在,芳香弥烈守弥坚。”[8]2721303年南归时又写下了《归舟次韵徐道川》一诗:“齐来齐去好齐年,只觉吾庐愧此川。西日不淄持钓手,南风初试阜财天。一舟汎汎身无系,十亩闲闲里有田。尚欲超然游八极,可能共我话良缘。”[8]272当时,吴澄携带儿子吴文、吴京北上,途中又碰到同年受召入京的徐道川,一路唱和,心情颇为畅快,似乎还有点踌躇满志。“行藏非我由天意,久速何师赖圣传”一联颇值得注意。“久速”典出《孟子·万章章句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8]用以说明自己的出处是遵循圣人准则的。“行藏非我由天意”说的是自己的出处无法由自己努力达成,一切均出于天意。吴澄抵京后发现职位已经为人代去,回归南方时又与徐道川同舟,因而写下了后一首次韵之作。前四句交代了两人于春季南归,后四句由漂浮的舟子、广袤的田园联想到自由自在的生活,甚至期待朋友和自己一块“超然游八极”。对于此次沮丧的遭遇,吴澄大概已经将之归结为“天意”,所以能够淡然之。1312年,吴澄在国子监推行教法改革失败,南归途中写下的两首诗也传达了出处有命的哲思。其《壬子自寿(皇庆元年正月十九)》诗云:“昨日辞京国,通州岸下船。年年此初度,度度似今年。快活神仙地,欢愉父子天。小成重八数,圆满大三千。”[8]259被同僚排斥,理想无法实现,按常理说来,应该是颇为沮丧的。但是,吴澄在弃官途中却说自己身处“快活神仙地,欢愉父子天”,心情颇为愉快。其《途中代柬监学僚友》云:“畴昔何曾三宿恋,如今已是四年淹。朝廷礼意不相薄,朋友欢情殊未厌。日月无私光普照,烟霞有约分应潜。归衫鸟哢花香里,处处春风动酒帘。”[8]285此诗首联回忆自己的宦途,说自己本来就无意于在京师做官,这次在京师已经跨越了四个年头了,应该知足了;颔联没有述说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也没有怨恨同僚的排挤,反而感谢朝廷的知遇、朋友的欢情;颈联认为皇恩浩荡普照一切,自己的弃官归隐乃是天意,是所谓的“分应潜”;尾联写归途之景,用鸟语花香、春风酒帘来烘托自己平静而舒畅的心情。吴澄在大量诗作中揄扬相士,但在《赠壶中仙谈命》中却作了如下表述:“春花洞树各媸妍,堕溷飘茵亦偶然。”[8]226“堕溷飘茵”典出《梁书·儒林传·范缜》:“ 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9]吴澄用来说明人之境遇高下悬殊是偶然的是命运的安排。他甚至从出处有命的角度来理解陶渊明的诗歌:“陶子之诗,悟者尤鲜。其泊然冲澹而甘无为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发而欲有为者,表志愿也。”[5]360从这些表述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吴澄拥有极高的修养,也可以说吴澄悟透了人生,用“命”用“分”用“天意”消解了人生出处的种种悲欢离合,从而归于“平淡”之化境。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吴澄胸怀之豁达。
二、吴澄的体道思维与诗歌创作中的出处情结
吴澄年轻时以豪杰自期以接续朱熹道统自任。他撰文指出:
道之大原出于天,圣神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原(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鲁邹,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乎?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顔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也,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盖有不可得而辞者矣。又尝与人书曰: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当斯时也,旷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没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习,滛于老佛之异教,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间,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其孰能与于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2]859-860
这种接续道统的使命感强化了吴澄的心性修持,并内化为一种体道思维,不仅指导着吴澄的日常行事而且浸淫于吴澄的诗歌创作。这种体道思维让吴澄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总是以理学思想为依据,聚焦于士人的出处行藏,详加评判,揭示了元代南方士人出处的复杂面相。
1287年春,吴澄拒绝程钜夫的荐举,以母老辞归江南,舟中所作25首《感兴诗》就是用理学家的体道思维来思考自己的出处问题。该组诗前四首分咏三才、日月、山川、五行,说的是宇宙的生成;第五到第十首,说的是文明的生成。在吴澄看来,这个文明的生成谱系就是儒学——理学的生成谱系。他吟咏文字的产生、六经的产生、六经的传承后指出,“冀北盛尧禹,雍西大文武。洙泗东极天,舂陵南教祖。”“临川捷径途,新安循堂序。本堂近定慧,末失堕训诰。”这两首诗梳理出了尧舜—文王、武王—孔子—周敦颐—陆象山、朱熹这样一个文明谱系。第十一到第十三首分咏佛老和杨墨,指出佛老的产生及其功能,并对杨墨进行了批判。第十四到十五首吟咏诗经、楚辞、苏武、李陵、董仲舒、韩愈,认为文统是弘扬道统的,并用“微子吾谁与”来表示自己的认同。第十六到二十一首分咏历史上的出处典范,宣扬了自己遵从的理学原则。第二十二到二十五分析当前的出处环境,表达自己的立场:“公无渡河去,天未丧斯文。”[8]219-220即远离可怕的政治环境,以退隐的方式来弘扬理学、捍卫道统。由此可见,这组诗歌的前十三首是在梳理理学的道统,第十四、十五首强调以文弘道、并以接续理学道统自认,这和前文所述吴澄的论著、书信的行文逻辑何其相似!后十首则用理学原则分析历史人物、友朋和自己面临的出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体道思维。换句话说,这25首《感兴诗》是一组说理诗,甚至可以说是理学家用诗歌形式写就的关于士人出处的学术论文。这组诗歌在吴澄的诗歌创作史上无比重要,因为这组诗歌的体道思维支配了吴澄所有的诗歌创作。《感兴诗》的小序指出:“至元丁亥自京师回,舟中寄子昂及在朝诸公。”[8]219这表明这组诗既传达了吴澄自己关于出处的思考,同时也是对赵孟頫等服务于元廷的南方士人的劝告。当他用理学的体道思维来观察现实中南方诸多士人的出处问题时,才发现南方士人出处的复杂性,因此不得不用同样的体道思维来加以解释。
元代南方士人出处的复杂性首先表现为“忠宋”与“忠元”的双重变奏。吴澄以南宋“草莽臣”自处,曾在诗歌中批评南宋守臣的投降行为,但是,荐举他的两个根脚大臣,一个是灭宋的功勋,一个是因叔父降元而骤贵,对于他们的“忠元”,吴澄是大加赞赏的。程钜夫将京师住斋取名为远斋,作《远斋记》表达思亲之情,吴澄为其作跋文云:“今以行台侍御史得旨南还,庶几便养。而回望阙庭,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乐;日以远者,人臣之忧,此远斋所为作也。”[5]456此文作于吴澄拒绝朝廷征召的南归途中,却一反程钜夫原文之初衷,彰显程钜夫的忠元情愫,并认为自己这么理解深得程钜夫之心。1302年,吴澄为董士选五十大寿写下了如下诗句:“邦基身世同悠久,敢赋《崧高》第二篇。”[8]273《崧高》为《诗经》“大雅”中的诗篇,为歌颂申伯辅佐周室、镇抚南方侯国的功劳而作。此诗表明,吴澄是站在元廷的立场上说话,不再是南宋“草莽臣”的观察视角了。他后来甚至在《滕国李武愍公〈家传〉后序》中称赞占领江西的李恒之师为仁义之师,理由是他的军队不杀不扰以致吉州军民纳款投降。1287年春南归之前,吴澄和大都的中原大臣以及归顺元廷的南宋士人有过不少诗歌唱和活动。他见到了曾经的南宋宰相、如今的元廷高官留梦炎,给他写了三首诗,却使用了《呈留丞相》这样的诗题,并表达了自己“与世相违分陆沉,半生藏息寄书林”[8]263的志趣,使用春秋笔法表达自己对贰臣的不满。不过,他的《别赵子昂》诗却表达了另外一层意蕴。他在诗序中对赵孟頫大加颂扬:“是行也,识吴兴赵君子昂于广陵。子昂昔以诸王孙负异材,丰度类李太白,资质类张敬夫,心不挫于物,而所养者完。”他认为赵孟頫具备文学家李白、理学家张栻的涵养,必定能够弘扬儒家道统和文统。他在诗歌中追忆自己与赵孟頫的相遇,称赞赵孟頫的才华,对出仕元廷的赵宋王孙赵孟頫期待甚殷:“鹤书征为郎,瑚琏惬清庙。班资何足计,万世日杲杲。蹇驽厉十驾,天下共君操。”[8]3271302年应诏北上前,吴澄特意前往武昌拜见程钜夫,其《次韵湖北程廉使访岁寒亭,亭在黄鹤山下,有柏一株、竹数茎》诗云:“偶然剔荒秽,幽意毕呈露。生本来孤特,疆使此君附。作亭以面之,相对澹无语。虽蒙新知厚,颇若违余素。”[8]298此诗虽然是咏物诗,但也寄托了吴澄被朝廷征召的无奈心情。不过,就在北上途中,他还是写下《寄济州张脱脱和孙》一诗表达自己对元廷的感激之情:“圣朝厚德遍穹垠,驿置舟车待小臣。”[8]272到了1309年担任国子监丞时,吴澄已经在《次韵鲁司业(二首)》其一中表达效忠之情了:“小儒忝缀班行末,咫尺龙颜奉玉音。”[8]294就在一年前,江西抗元英雄后代何太虚出山北游,吴澄用另外一种理学理论为何太虚的出游寻找依据。在他看来,游有两种,一种是为利之游:“方其出而游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所,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一种是“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那样的为道之游:“书必钟、王,诗必韦、陶,文不韩、柳、班、马不止也。且方窥闯圣人之经,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讵敢以平日所见所闻自多乎?”[5]232-233何太虚之游无疑属于后者,因此他的北游大都是符合出处规范的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其次表现为仕宦与隐逸的双重变奏。自比诸葛亮的吴澄对于仕宦自然有着崇高的理想,当他晚年迎来人生中的一次次超常提拔时,他已经向往着隐逸生活了。1318年,已经70岁的吴澄和前来迎接他的虞集一道北上,路过彭泽水驿,游览孤山,想起了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接连写下了《彭泽水驿和虞修撰》《登孤山(有序)》《彭泽遇成之之京都(有序)》。诗中有云:“秫田旧治民犹昨,柳岸新亭客避烦。江面波神应冷笑,曾闻容膝可偷安。”[8]292“人海茫茫名利场,盛年快意一观光。顾予白发归来晚,羞过渊明五柳庄。”[8]242前者由陶渊明联想到自己的仕途奔波,对自己不能归隐山林深感惭愧;后者想起自己三十年前北上观光时置名利于不顾、毅然归来的情景,如今自己白发苍苍还在为功名奔波,深感无颜面对陶渊明的隐居地。这种仕宦与归隐的内心冲突,加上身体有病,促使吴澄行至仪征时便以疾辞谢诏命。实际上,吴澄的两次京师仕宦生涯均不如意,他在题赠诗中屡屡发出归隐的慨叹:“亦欲从师了耕种,县南郭外有良田。”[8]266“我亦谋归理荒径,寄诗先到岘台东。”[8]294在为自己的画像作赞时,他将自己塑造成“只合幼舆置岩壑”[8]316的隐士形象:“舒舒其居也,于于其趋也,其山林樵牧者乎?野之耕筑者乎!”[5]628对于南方士人的仕宦与隐逸,吴澄在诗歌中表达了两可的态度。在《送国子伴读李亨受儒学教授南还》《送南雄总管之子皮昭德赴京当儤使》等诗中,他对于那些与元廷合作而获得世胄身份的南方小根脚子弟的出仕满怀期待,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欢喜不已。对于大部分南方儒家子弟来说,宦游充满着艰辛、屈辱、绝望,吴澄甚至创作《楚歌五首劝潭士归乡》《宜黄友人远游不反因其投赠用韵招之》《楚语赠欧阳尚古》等诗歌,劝告他们安于命运,不要在无谓的挣扎中虚耗生命。也正因为此,他对于龚舜咨这类情怀高洁的游士和隐士满怀敬意,接连为他写下了一组诗文。其《送龚舜咨南归(有序)》云:“舜咨一出游观京国,略不动世俗利名之想,浩然而归,其志趣之超迈,可尚已,诗以饯行。”诗中有云:“快甚双眸窥宇宙,鄙哉百计入樊笼。浩歌归去浑无事,栖碧山前月上东。”[8]268吴澄回到江西后,又为龚舜咨作《山间明月楼记》《寄题栖碧山》,诗云:“栖碧山前有逸民,爱山终日与山亲。几番晴雨青如故,人不傲山山傲人。”[8]238在吴澄看来,能够挣脱名利之想,安于命分,自由自在地享受隐居生活,亦是人生的一大快乐。这种隐居的快乐,既源于老庄思想的熏陶,更源于理学理念的涵养。其《寄题桂溪陈氏山居》诗云:“斗邑西来谷可盘,天教隐者宅其间。萦纡几曲桃源水,突兀一拳蓬岛山。竹树百年清荫在,图书四壁白云閒。日长自对圣贤语,鸡犬不惊人往还。”[8]279据吴澄《故桂溪逸士陈君墓碣铭》可知,陈氏字贵道,名仕贵,宋亡后隐居读书,元祐开科后居然以一老儒而跻身科场。他的隐居,和陶渊明的隐居迥然有别。“日长自对圣贤语,鸡犬不惊人往还”云云,说的就是他的精神境界与理学涵养功夫密切相关。
再次表现为宦情与亲情的双重变奏。元代南北一统、东西贯通,疆域辽阔,地理距离成为困扰士人出处的一大难题;元代铨改举废的同时实行族群等级制,这个政治距离也成为困扰士人尤其是南方士人出处的一大难题。这两大难题,在吴澄诗歌中表现为宦情与亲情的双重变奏。他在《送李文卿序》中指出:“窃怪海宇混同以来,东西南北之相去,地理辽绝,有违其乡而仕远方者,于其亲也,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余年而不一省,不惟安否之问、甘旨之供阙,至有畜妻抱子、新美田宅于它所,而其亲自营衣食、自给繇役于家,窘穷劳苦而莫之,老矣而无欢;或不幸永诀而不相闻,甚者闻而不奔,又甚者匿而不发,饮食、衣服、言语、政事扬扬如平时。噫!是岂独无人心哉!其沦染陷溺之深而然与?其未尝讲闻礼经之训而然欤?可哀也已。迩来国典许人子以终养终丧,此孝治天下之第一事也。”[5]210有鉴于此,吴澄一方面视士人出仕为禄养、孝亲的成功举措,如其《送征东儒学提举敖止善荣还高安》诗云:“男儿弧矢四方身,直欲飞腾作贵人。膝下数千余里远,客中十又一年春。乘桴岂爱九夷俗,奉檄聊娱八帙亲。此去东风归袂软,故园花鸟亦欣欣。”[8]264敖止善志在四方,从江西远赴高丽做官,如今荣归故里,奉旨娱亲,实乃人生最大幸事。另一方面,吴澄对士人弃官归养赞叹不绝。如其《送李景仙归湖南》诗云:“外省天官属,前朝阁学孙。甘心辞显要,雅志便晨昏。卓卓廉能吏,堂堂忠孝门。此归得模楷,菊里有乡尊。”[8]254这位出自高官显宦之家的“廉能吏”能够断然放弃功名利禄、弃官养亲,可谓忠臣孝子之楷模!地理距离、政治距离造成的痛苦在吴澄诗歌中常常表现出宦情与亲情两难的处境:“家在江南山水村,黄尘陌上两眸昏。偶然此景梦中见,归路迢迢欲断魂。”[8]225身在远隔几千里的朝廷做官,看到绘有风景的手卷,想起梦中的家乡景致,不禁悲从中来!“潋滟浮杯泛九霞,还家未久便辞家。出门恻恻重闱远,前路漫漫万里赊。”[8]267重闱,一指闺门,一指父母。诗中的远行人刚刚回家探亲,为了功名不得不匆匆踏上漫漫长途,自是悲痛无比,凄凉不已。吴澄也因此常常慨叹:“只为浮荣卖了身,天涯多少未归人。”因而对友人的致仕羡慕不已:“八十衰翁作计疏,羡君六十早悬车。”[8]246对于游士宦情、亲情两无着落的处境,吴澄寄寓了深刻的同情:“万里远游双足倦,百年终养寸心忙。”[8]284这种由于空间造成的宦情与亲情的冲突,此前的诗歌中不是没有,但在元代诗歌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实与元代的疆域、制度、文化密切相关。
三、小结
宋元之际,南方士人的出处成为诗歌创作中的一大重要母题,起因于改朝换代给士人造成的巨大冲击,深受理学思想浸淫的南方士人不仅面临着异质文化的冲击而且面临着生存的困扰。程钜夫代表元世祖访贤江南,体现了元廷政策的转化,赵孟頫等二十余位南方著名士人因此得以进入元廷为官,其中的吴澄在观光中原后断然辞归,被元廷重臣阎复形容为“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3]428,成为朝野震惊的事件。吴澄向赵孟頫辞行时“赋渊明之诗一章、朱子之诗二章而归”,赵孟頫当即“书所赋诗三章以赠行”。[4]这两个人的身份、这两个人的这个动作,对于元代南方士人的出处来说,实在是意味深长!一个是赵宋王孙,元代南方最著名的艺术家,居然入仕元廷,最后官居极品!一个是江南布衣,元代南方最著名的儒学家,居然拒绝元廷的征召,最后居然在元廷的不断征召下官居极品!他们吟诵、书写的陶渊明、朱熹之诗,体现了南方士人出处的最高准则。他们虽然最后官居极品,实际上不仅无所作为,而且终生为这些出处准则所困扰,在各自的诗文中形成浓郁的出处情结。就吴澄来说,他年轻时以诸葛亮自居,在元廷君臣的不断荐举、征召下,由宋廷的“草莽臣”内化为元廷的“精忠士”,其诗歌中的出处情结因而呈现为出处有道、出处有时、出处有命三重意蕴,这表明南方士人对现实的体认、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对文化传统的坚守始终处于变化和调适之中。他还以理学传人自处,用理学的体道思维吟诗作文,思考南方士人的出处,其诗歌中的出处情结体现为忠宋与忠元、仕宦与隐逸、宦情与亲情的双重变奏,揭示了南方士人出处的复杂面相。这说明,深入历史语境对元代南方士人的诗歌进行分析,有益于深入揭示南方士人的精神风貌,改变我们基于各种先在理念而形成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