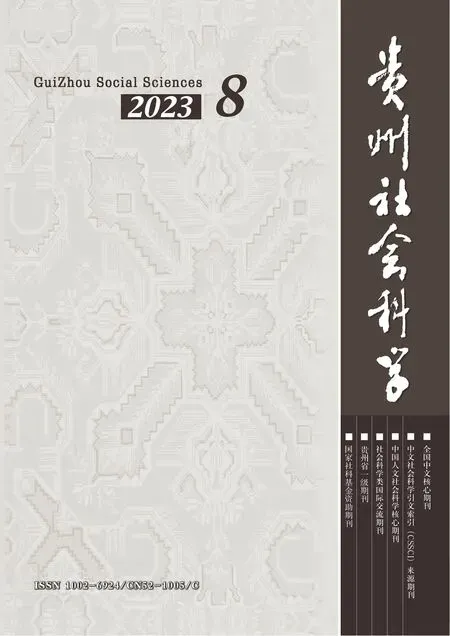布拉德雷与现代中国哲学
蒲力戈 朱进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 南京 210013)
作为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布拉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1846—1924年)(1)布拉德雷(Bradley)姓氏的译法有多种,曾以“柏烈得莱”“柏烈得来”“柏列莱”“布拉德雷”“布拉德利”“布莱德雷”等不同译法出现。本文除引文、书名、文章名外,一律以布拉德雷行文。是19世纪后期最有原创性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英王功绩勋章的哲学家,在世时被尊为“休谟之后最伟大的英国哲学家”,被西方哲学史家们誉为“近代哲学中的芝诺”[1]326,其代表作有《伦理学研究》《逻辑原理》《现象与实在》《真理与实在论文集》。
布拉德雷哲学在争议之中得到发展、传播和研究。国外布拉德雷哲学的传播和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1)19世纪后期,布拉德雷哲学体系的制定。另一位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年)在1885年出版专著《知识与实在:对布拉德雷先生〈逻辑原理〉的批评》,促使布拉德雷在1922年第二版《逻辑原理》中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哲学逻辑。(2)20世纪初期,那场著名的“舌战群儒”式哲学论战,使布拉德雷哲学被人误解。1924年布拉德雷逝世之后,他的名声迅速下滑,其思想在20世纪很长时间里被人忽视,当然,这主要是因为罗素和摩尔对其的批判。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哲学开始重新受到哲学界重视,仅关于布拉德雷哲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就有10篇之多。20世纪80年代,有西方学者将他与黑格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作比较研究,第一次系统地纠正了前人对布拉德雷哲学的种种误解,为其哲学正名;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布拉德雷的形而上学导致怀疑论,而非得出一致性是真理的标准”[2]。20世纪90年代,他被当作英美分析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其论点被与分析哲学传统中的当代问题联系起来”[3]。1995年,英国《布拉德雷研究》杂志创立。1999年,12卷本《布拉德雷全集》出版。这两个学术事件表明了西方哲学界对布拉德雷哲学的重新关注和重视。(3)进入21世纪,布拉德雷学术地位得到重新评估。布拉德雷的著作《现象与实在》在欧美印刷12次,西方学界出版研究专著6本,发表学术论文45篇,内容涉及布拉德雷形而上学地位,布拉德雷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布拉德雷与罗素的争论,布拉德雷与叔本华、柯林伍德、詹姆斯、弗雷格、怀特海等的比较研究。据我们统计,国外已出版27部布拉德雷研究专著和16篇博士论文,其中《商羯罗和布拉德雷的现象与实在》和《商羯罗与布拉德雷哲学中知识的两个层级》两篇博士论文将布拉德雷与印度中世纪哲学家商羯罗(Samkara或Sankara)作比较研究。布拉德雷与罗素的争论,被认为导致了英国唯心论的灭亡和分析哲学的诞生。
布拉德雷哲学引入中国已逾一个世纪。早在“五四”运动以前,杨昌济在《各种伦理主义述略及概评》和《哲学上各种理论之述略》两文中就对布拉德雷哲学有所研究[4]。若从1935年谢幼伟发表专门论述布拉德雷哲学的《柏列莱之太极观》[5]一文算起,中国布拉德雷哲学研究已走过八十余个春秋。讲到布拉德雷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影响力,有两个典故可以证明:(1)张世英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师从贺麟学习哲学,其毕业论文便是《论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6]254;(2)1941年,冯契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师从金岳霖研习哲学,金岳霖给他开设了研读布拉德雷原著的课程[7]。然而,国内哲学界尚未有学者对布拉德雷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作出研究和梳理。有鉴于此,我们将考察布拉德雷哲学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状况,评估中国对布拉德雷哲学研究的得失,探讨布拉德雷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并对未来中国对布拉德雷哲学的研究提出一些看法。
一、布拉德雷与现代中国哲学:一个概述
近八十年来,国内布拉德雷哲学研究可以分成五个时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创性译述和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和批判、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专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伦理学和比较研究,以及21世纪多维研究。这几个时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简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翻译。1.整本著作翻译。近八十年来,有3本布拉德雷著作被译成中文。第一本是1946年谢幼伟翻译、贺麟校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伦理学研究》,此为布拉德雷第一本中译本著作。谢幼伟作《译者序》,并在正文中作《译者按》,还附其撰写的《柏烈得莱的宗教观》一文。第二本是1959年至1962年庆泽彭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逻辑原理》(上、下册),贺麟作长篇代译序——《布拉德雷逻辑思想评述》。第三本是何兆武和张丽艳在2007年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何兆武作《本书提要》。
2.《现象与实在》的四次选译。第一次,谢幼伟1948年在《学原》第9期发表译文《柏烈得莱论实在的通性》,文中有译者注3900字;其同年在《民主评论》第4期发表另一篇译文《柏烈得莱论思想》。两篇译文选自《现象与实在》第十三至十五章。第二次,1964年王太庆摘译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收入洪谦主编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著作选辑》。第三次,20世纪90年代初期,朱亮翻译《第一版序言》《第二版序言》《导论》《第十三章实在的一般性质》《第十四章实在的一般性质(续)》《第十五章思想与实在》,收入张世英主编的《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卷》,朱正琳翻译的《附录:关系和质》也载于该卷。第四次,莫伟民在20世纪90年代末共摘译了全书的十一章,载入俞吾金、吴晓明主编的《20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序卷(20世纪西方哲学先驱者)》。
3.《真理与实在论文集》选译。20世纪60年代,陈万熙翻译《论实用主义的不明确》《论詹姆士教授的〈真理的意义〉》《论詹姆士教授的“彻底经验主义”》三章,载入《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二辑》。20世纪90年代,邓国春翻译《第十一章论真理的某些方面》,收入张世英主编的《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卷》。
(二)著作。据我们统计,有78本(或篇)著作涉及布拉德雷,其中专著2部和评传1 篇。1973年,谢幼伟出版《柏烈得来的哲学》,这是我国第一部布拉德雷研究专著,集作者数十年研究布拉德雷哲学成果之大全,由布拉德雷生平与著作、玄学观、逻辑观、伦理观、宗教观、历史观,以及附录构成,虽系旧作集结出版但仍不失原有价值。朱正琳的一篇《布拉德雷》评传,由生平、著作、哲学思想和结束语、参考文献五个部分构成,载入侯鸿勋、郑涌编的《西方哲学家评传》。张家龙的《布拉德雷》也是一本布拉德雷研究专著。万俊人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中辟专章,分成六个部分——布拉德雷及其《伦理学研究》、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自我实现原则:目的与手段、“善良意志”与“为义务而义务”、道德理想、从黑格尔归于康德——考察布拉德雷伦理学[8]261。
(三)学术论文。据我们统计,近八十年来有38篇论文涉及布拉德雷,其中有15篇专论布拉德雷。譬如,贺麟的《布拉德雷逻辑思维评述》、周辅成的《法兰西斯·赫伯特·布拉德雷》。有5篇从新黑格尔主义视角论述布拉德雷,其中有贺麟的《新黑格尔主义批判》、谢幼伟的《柏烈德莱的玄学》、俞吾金的《略论新黑格尔主义的非理性化倾向》。有6篇是学位论文,包括张世英的《论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学士论文)[6]254、朱正琳《布拉德雷的绝对经验》(硕士论文)[9]、臧勇的《罗素与布拉德雷关于关系的争论》(博士论文)[10]等。
二、布拉德雷哲学在中国:研究内容
(一)关于布拉德雷哲学体系的研究
1.布拉德雷哲学的定性。在《布拉德雷逻辑思想评述》一文中,贺麟指出,布拉德雷唯心主义哲学实质上是“反唯物主义的、反科学的、替英帝国主义、替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11]。从与黑格尔的关系观之,布拉德雷在更加神秘主义化黑格尔哲学的同时,使其“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入主观唯心主义”[11]。尤其到了晚年,他更趋向主观唯心主义,且有更浓厚的神秘主义成分。布拉德雷逻辑哲学(即玄学)继承了黑格尔传统,尽管他不承认自己是黑格尔派。因此如谢幼伟所言,“不谈玄学或排斥玄学的人,固可忽视他的逻辑,但亦不配批评他的逻辑”[12]45。在我们看来,布拉德雷站在自己的哲学立场上批逻辑心理主义,这种对逻辑中心理主义的批判与现象学家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可以说二者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
2.从“绝对”来看布拉德雷哲学体系。周辅成较早提出布拉德雷哲学是有体系的,是在破除“谬见”中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而且“关系理论”是他破除所谓“谬见”的主要武器,布拉德雷的“绝对”是凭空突然出现的[13]。布拉德雷论述“现象”是为了证明现象知识的非真实性,论述“实在”与“真理”在于证明“最终实在”是包含“现象”而又超越“现象”的“绝对”,对“绝对”的认识乃是绝对真理[13]。这就决定了布拉德雷的芝诺式消极辩证法必然囿于“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同时决定了其体系中最高实在“绝对”实即可以令人陶醉、欣赏、安息的神秘境界式的“绝对经验”。作为“绝对”的“最终实在”自然受到质疑,正如朱正琳所言,布拉德雷宣称实在是精神,而“不变不动、非主非客的精神到底指的什么”[14]281。我们认为,这确实证明,德国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种传统被布拉德雷融为一体,而摩尔和罗素的哲学的确肇始于批判布拉德雷哲学。
3.布拉德雷哲学实即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之混杂。依刘放桐的说法,《现象与实在》一书正文最后数语证明实质上布拉德雷“建构了英国绝对唯心主义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具体点说,布拉德雷哲学糅合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剑桥柏拉图主义及浪漫主义思潮等多种哲学,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哲学体系”[15]。这是迄今国内哲学界对布拉德雷哲学体系做出最明确、最具体的判断。在辩证法方面,布拉德雷对待黑格尔,宛如克拉底鲁看待赫拉克利特;在每个判断中,作为主词的实在,区别于作为谓词的形容词,“在期望超出这种区分时,思想的目的在于自杀”[16]148。所以心灵与“实在”的关系是:心灵只能在“绝对完满的”实在中得到满足,对于事物及其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没有意义的[17]。在我们看来,这里的“直接经验”大抵诸如“意识流”(詹姆斯)、“绵延”(柏格森)之类概念,而且布拉德雷对同时代古典实用主义者詹姆斯的真理观大加批判,并成了一笔重要的哲学遗产。
(二)关于布拉德雷“关系理论”的研究
1.“关系理论”(或“关系学说”)在布拉德雷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即使像“绝对”这样的概念,也必须依靠“关系学说”加以刻画,但“此关系学说乃柏氏[布拉德雷]哲学中最重要又受驳斥之部”[5]。换言之,“关系理论”也是其最被人误解的。有人说布拉德雷似乎认为“关系是不可能的”,接受所有关系都“修正它们的词项”。金岳霖则认为,“布拉德利[雷]绝没有尝试以一贯之地将性质和关系视为重言式表达(tautological expressions)”[18]。其实在布拉德雷那里,性质和关系相互蕴涵,因此“我们的认识关系(our knowledge-relation)必须被解释为外在的”[18]。我们发现,金岳霖列出学界对布拉德雷的种种误解,意在为布拉德雷正名,此举早于西人五十多年。
2.布拉德雷与罗素等在“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很难说“关系”为何者,但“关系”俯拾即是,而就“关系”而言,布拉德雷的无穷倒退毫无意义。在布拉德雷那里,不可能将“关系”看作能够被联系且能够进行联系,而是认同“关系非关系者,亦非按照自身选择进行联系”。在布拉德雷外在关系的确证与斯堡尔丁所采用的确证的基础和方式有何不同方面,金岳霖认为,“罗素的话没有太多意义”,而摩尔“大抵恰当地评价了这个问题”,并坦言受到摩尔很大影响。就布拉德雷的“没有关系就没有性质”和“没有性质的关系是不存在的”这两个观点来说,给人的感觉是“布拉德利总是充满文学味道但缺少清晰性……仿佛‘关系’既被用作关系复合句,又被用作纯粹而简单的关系”[18]。毋容置疑,我们无法通过经验证明“我们的认识关系”是何种关系,无法证明我们的认识关系不是内在的就是外在的,但是必须将“我们的认识关系”解释成是外在的,从而达到“反驳所有关系都是内在的这一命题”之目的,“同时确立有些关系是外在的这一命题”。我们认为,在布拉德雷的关系理论上,金岳霖的评估有别于罗素和摩尔的评估。
3.阐释布拉德雷的“内在关系论”。完整地阐述布拉德雷“内在关系论”,目的在于论述独立的关系和关系项是不存在的,在于论述《现象与实在》中的关系思想体现为性质与关系不可绝然区分,在于论述《遗稿》中《论关系》表明独立的关系无法构成事实整体。布拉德雷“关系理论”居于哲学产生“语言学转向”阶段[19]1-165。我们认为,在哲学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方面,布拉德雷哲学本质上区别于分析哲学,因此显然不可像罗素把黑格尔和布拉德雷做简单等同,毕竟《遗稿》中《论关系》作为应《心》杂志之约而撰写的一篇未竟之作对“关系”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在“关系”的实在性方面,陈启伟“对罗素本人的某些说法及以往学者的解释有所辨正”,认为罗素以为布拉德雷否定关系的存在的根据是布拉德雷不承认关系具有“绝对的和形而上学的确实性”[20],而布拉德雷的目的只是否定“关系”之为独立实在而非否定“关系”的实在,因此罗素以所谓“关系的不可能说”攻击布拉德雷否定关系实在性,这“不仅是对布拉德雷的一个误解乃至曲解,而且是将自身理论弱点推上审判台的自戕行为”[20]。我们认为,陈启伟纠正了罗素批评布拉德雷的偏颇之处,带有为布拉德雷辩护的浓厚色彩。
(三)有关布拉德雷伦理学的研究
1.布拉德雷伦理学的目的。欲研究他的伦理学说,须先研究他的哲学观,及他在伦理学上的消极批评(即对主张快乐论的功利主义和“为义务而义务”的批评)和其道德当以本身为目的的积极主张。但是照谢幼伟说,自快乐论有史以来,像如此细腻而有力的批评,布拉德雷或许堪称第一人,“以后批评快乐论的如摩尔氏(G.E.Moore)有许多地方不能不采用柏氏[布拉德雷]的批评”[21]。在布拉德雷眼里,要想有好国家须先有好国民,而好国民只能出现于好国家。由此观之,布拉德雷的思想不但没有违反民主主义而且实乃最好的民主主义。在译著《伦理学研究》中,谢幼伟作《译者按》,涉及布拉德雷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对康德哲学的理解、政治哲学、青年对自由的理解、“具体的普遍”、艺术与社会或艺术与道德的关系、对禁欲主义的批评,以及“善自我”与宋儒的“天理”(或“恶自我”与宋儒的“人欲”)等等,属于对布拉德雷伦理学思想较早的研究。
2.康德、黑格尔与布拉德雷伦理学。万俊人对布拉德雷伦理哲学的研究,主要涉及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自我实现原则。在“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方面,布拉德雷“理论上避免了机械决定论和非理性主义自由观的两极分化”,因而较之格林的相关见解显得更为全面,但布拉德雷“根本上并没有超出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8]261。在道德理想方面,布拉德雷和格林都“不得不调和道德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最终投入宗教怀抱。因此,两人“都没有超出他们的前师康德和黑格尔”[8]280。布拉德雷道德世界是其“仰仗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为我们提供的康德式的伦理学体系”。不难发现,布拉德雷和格林的伦理学是以黑格尔观念辩证法重新进行从黑格尔哲学到康德伦理学的逻辑演绎。
(四)布拉德雷与西方哲学家的比较研究
1.布拉德雷与西方古典哲学家比较研究。在张东荪看来,布拉德雷当属“最近英国唯心派的唯一重镇”,其“思想在精神上可说与黑格尔相似,而在方法上则迥乎不同”[22]123。因为布拉德雷认为一切都是现象。此说与斯宾塞的知识相对性有些相通。布拉德雷的贡献在于,“他能用极精细的分析功夫,把所有的思想范畴都加以检查,其结果正和希腊的芝诺(Zeno of Elea)一样”[22]125。布拉德雷在思想研究方面另辟蹊径,但与康德可谓殊途同归。在谢幼伟眼里,“柏氏[布拉德雷]之太极非康德之‘物自体’(Ding an sich)也,非全不可经验之物也”[5]。从“太极”(即“绝对”)的心理性质来看,布拉德雷的论证同贝克莱的论证毫无二致,“两人均带有主观色彩。勃氏[贝克莱]所谓‘存在即被知觉’(To be is to be perceived)与柏氏[布拉德雷]所谓‘存在即被经验’者,故如出一口也。”[5]
2.布拉德雷与维特根斯坦的比较研究。布拉德雷“内在关系”学说与维特根斯坦“基本事态”学说具有内在关联。卢雁认为,关系的外在给予必然导致恶性循环,要摆脱这种循环就得遵从布拉德雷的一切关系皆奠基于“项”的性质,就得将“基本事态”视为世界的逻辑原子,使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成功避开哲学本体的无限回溯[23]。依我们之见,“基本事态”间的联系确实符合布拉德雷的内在关系说。照黄敏的说法,布拉德雷的关系非实在性论证,被维特根斯坦直接用作出发点来建立分析理念[24]。我们觉得,这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关于意义的观点(即语言是有意义的、体现于用法的统一体)相一致。
3.历史哲学:布拉德雷与柯林伍德。关于历史的真理标准。布拉德雷揭示,历史真理标准由史学家本人确立,而且史学权威们接受批判时必须参照此标准。柯林伍德则断言,布拉德雷在批判历史学方面先着一鞭。具体说来,历史学家带到解释中的标准乃是“历史学家本人”,接受历史的证据,实为表示让我们的思想成为“史学家自身的思想”[25]。布拉德雷觉察到,历史批判绝非先验之物,而是源自史学家的实际经验。但布拉德雷眼里的历史经验却是纯粹的感觉和感觉的直接活动。
柯林伍德的“科学历史学”崇尚布拉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批判精神,却批判后者作为批判标准的“前提假设”带有的实证主义印记,而前提假设并不限于实证主义,柯林伍德倒是意在剔除史学“客观主义”,“进而调和当时英国社会在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矛盾”[26]。在我们看来,确如鲁宾诺夫所说那样,布拉德雷哲学活动“在于为人类行为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打下根基”,因此布拉德雷开辟了批判的历史哲学抑或分析的历史哲学之蹊径,进一步说,布拉德雷从认识主体着手的批判的对象是人们的心灵。
(五)布拉德雷与中国哲学家的比较研究
1.布拉德雷与“抽象的普遍”、墨子“兼爱”和基督教“博爱”。“一般的(或者普遍的)行善,可以是不行某种特殊的善,所以是绝不行善,而所行或可是善之反面。”[27]208谢幼伟认为,布拉德雷这句话可以改成:“一般的(或者普遍的)爱人,可以是不爱特殊的人,所以是绝不爱人,而所行或可是爱之反面。”[27]208布拉德雷虽然没有直说但无疑反对“抽象的普遍”。“耶教的博爱,和墨子的兼爱,其所爱为上帝,为全人类,均有抽象的普遍之嫌,这即可为柏氏[布拉德雷]所反对。”[27]208所以,王船山在论述“爱”与“仁”时指出,“墨释之邪,韩愈氏之陋”,主张爱之有择,不可“散漫以施”。这番话“实可为柏氏[布拉德雷]上面一段话的注脚”[27]209。空洞的博爱实为抽象之爱,这种一无所爱之爱终归随意决定爱抑或不爱。
2.布拉德雷与告子、王阳明持有相同之见。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颇受后儒诟病。照谢幼伟说,“实则,心之体自不能有善恶可言。善恶之分,乃道德以内的事。心之体是超乎道德的,即不能以道德名辞加之。大概批评阳明的人,都是认为道德是绝对的(康德的‘绝对命令’),而不承认有超道德的存在,但道德若是绝对,则善恶之对立,即永无超出之可能。我国儒者多未窥见此点。”[27]405-406因此,孟子的“性善论”是有问题的,而告子的“性无善不善”之说、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之心体”之说,与布拉德雷的“超乎善恶的本体”之说,显然是相通的。由此可见,谢幼伟不但点出后世一些儒家对王阳明产生误解的缘由而且显示出在打通中、西哲学方面的良苦用心。周辅成在《法兰西斯·赫伯特·布拉德雷》一文中,还把布拉德雷的“绝对”与老子、庄子的有关思想作了比较[13]。
3. 布拉德雷与董仲舒和金岳霖。金岳霖思想不可仅仅归为新实在论,因为在他的哲学中尚可看出布拉德雷思想影响的痕迹。具体说来,金岳霖在《论道》中对元学的追求同“布拉德雷绝对唯心主义一元论的目标是一致的”[28]。融贯论著名代表布拉德雷眼中的真理等级实为金岳霖所说的“程度”[29]。在布拉德雷那里,重视整体且意识到道德目标在于自我实现,跟整体或关系世界融合为一;与之相近的是董仲舒,视“我”为“义”,而“义”则为约束主体间关系的一般规范[30]。这足见两人使主体自己消失于主体间。“人为什么要有道德”之类问题,实即布拉德雷所言“德行有什么好处”的翻版[31]。
(六)布拉德雷《现象与实在》的翻译和解读
1.《现象与实在》的翻译颇具悲剧色彩。在谢幼伟看来,《现象与实在》是布拉德雷最重要的著作,可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相提并论。“我在抗战结束后,在杭州浙大任教,曾打算把全书译出,并加注释。当时只译了十五章,便大陆沦陷,其中十二章已寄给北平友人,另三章分在《学原》及《民主评论》发表。”[12]3就我们所知,这是国内学者对《现象与实在》一书的最早翻译。在所发表的这三章中,“为帮助读者的理解起见,差不多每段都有作者(指译者——引者注)的按语,加以简明握要的解释”[32]。在“柏烈得莱[布拉德雷]论实在的通性”这篇中,译者注总共约3900字,这很可能是国内学者对《现象与实在》的最早解读。谢幼伟对布拉德雷一些术语的译法如“何”(what)和“彼”(that)为后来译者如周辅成等所遵。
2.贯穿《现象与实在》全书的是“现象”和“实在”的关系问题。“形而上学”的必要性构成“布拉德雷思想的出发点”[33]。形而上学探讨“第一原理”,了解“内在关系说”即读懂大半部《现象与实在》。“观念”只能是“现象”;“实在”包容各种各样的“现象”,使“现象”成为一以贯之的“全体”。“实在”的质料几乎是逻辑上的一种直接断言。超“关系”中的“感觉”“思想”“意志”,此三者与其各自“对象”统统融为惟一的“实在”这一“绝对经验”。只有人们被称为“实在”,才有可能完全知道“实在”。“知”可为“真”但不可为“实”,可获得“真理”而无法达到“实在”。“实者”必为“彼”(that)与“何”(what)的统一,“彼”与“何”可识别但不可分割。“思想”是观念的和理想的(ideal),而它虽然奋力致使“彼”与“何”或宾词与主词一致却达不到一致。“思想”陷入无限或无穷发展。无论如何我们始终在“关系”的迷宫中兜圈子。因此“感觉、思想、意志都不能独自成为实在,实在是它们之交融为一体”[33]。作为有限者的我们无法达到充分的“实在”,但作为“现象”的我们又未被“实在”摒弃,因此一切都处在“实在”中。《现象与实在》的结局必然是“实在是精神的……在精神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在;凡精神性越强的事物,其实在程度定然也相应地高”[16]484。
三、布拉德雷哲学在中国:评估与展望
(一)梳理中国布拉德雷研究成果
中国哲学界引入布拉德雷哲学已逾一个世纪,他曾对金岳霖、张东荪、贺麟、冯契、唐君毅、张世英等当代中国哲学家都产生影响,在引导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方面也曾经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如此,目前国内哲学界对其重视有限,未呈现系统全面的学术成果。在布拉德雷著作翻译方面,谢幼伟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译著《伦理学研究》(贺麟校译),译出半部《现象与实在》,当属国内最早的布拉德雷哲学译者。庆泽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译著《逻辑原理》,使中国哲学界能够全面了解布拉德雷哲学逻辑。21世纪初,何兆武和张丽艳译出《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让国内学界得见布拉德雷哲学思想的初始面目。在布拉德雷哲学思想进大学课堂方面,洪谦、周辅成、夏基松、刘放桐、张世英堪称功德无量。在布拉德雷哲学研究方面,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用英文在《清华学报》发表《论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长文,张东荪把布拉德雷与其他西方哲人作比较研究,谢幼伟在20世纪40年代以《译者按》形式将布拉德雷与中国哲学家作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都具有开创性。贺麟对布拉德雷哲学逻辑的评述,对后来研究布拉德雷哲学起到定调作用。万俊人以两万字的篇幅描绘布拉德雷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谢幼伟以专著《柏烈得来的哲学》成为近80年来布拉德雷研究第一人。朱正琳以《布拉德雷的“绝对经验”》等五项成果奠定了在布拉德雷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二)亟待翻译出版《现象与实在》
出于以下四点考虑,急需译出布拉德雷的扛鼎之作《现象与实在》。第一,《现象与实在》在布拉德雷著作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包含了他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体现其哲学体系之作,因此一卷在手可尽揽布拉德雷哲学之全貌。第二,《现象与实在》是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一本影响巨大的哲学著作。该著自从1893年问世以来印刷20余次,21世纪以来被欧美出版社印刷12次,并被列为世界哲学名著。第三,翻译出版《现象与实在》,以实现几代中国学者的翻译梦想。70多年前谢幼伟翻译出该书前十五章(只发表其中三章),迄今仍无该书的全中译本。第四,翻译出版《现象与实在》,丰富中西哲学比较的内容。书中哲学具有宏大而古老的风格,大有先秦诸子百家中惠施哲学的味道,亦有西人把《现象与实在》视为西方的商羯罗版本。
(三)探讨布拉德雷的哲学体系
关于布拉德雷有无哲学体系,贺麟没有作出明确判断。刘放桐则断言,布拉德雷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是“一种独特的哲学体系”。依我们之见,研究布拉德雷哲学体系时首先要看他是怎样谈论自己体系的。在写《现象与实在》一书之前,他就想“写出较成体系的著作”,该书问世了却了他的这桩心愿,不拘一格地建构了“第一原理的一个理性的体系”[34]。布拉德雷承认自己有形而上学体系,梯利也认为“他的形而上学体系经过深思熟虑而被表述于《现象与实在》中”[1]326。我们认为,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深植其学术研究之始终,《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标志着他历史哲学的问世,成为“布拉德雷思想的颇为简练的导言”,后来某些富有特征的论题在这里已初露端倪,他那朦胧晦涩、蔑视以例说明的哲学风格在这里得到了突出表现。他的某些形而上学思想展现于其对道德哲学的辩护中;他那有别于传统逻辑学的哲学逻辑中某些深刻论述似乎预示着后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的运用,就连罗素本人也服膺布拉德雷的论证。所以说,贯穿于布拉德雷历史研究、伦理研究、逻辑研究之深层的是哲学思考这根主线,不能轻言其经过逻辑学才转到哲学。
(四)开阔布拉德雷哲学研究视野
近八十年来国内布拉德雷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上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普遍不重视甚至没有文献综述,给人以白手起家、“钻木取火”之感。既无法证明自己的创新也无法避免重复研究。第二,现有的布拉德雷著作中译本和部分研究布拉德雷的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例如:谢幼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真理与实在论文集》中,陈万熙的三章中译文至今未见有人引用。第三,除几篇学位论文作者外,国内学者大体上是关起门来研究,基本上是在各说各的。
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在布拉德雷研究方面打开眼界。首先,充分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例如,谢幼伟译的《伦理学研究》,金岳霖、贺麟在布拉德雷哲学逻辑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果。其次,在适当时候召开国际布拉德雷哲学思想研讨会,推动中国布拉德雷研究走向世界。再次,国内学者应该加强联合,组织翻译出版十二卷本《布拉德雷全集》。此外,还要充分借鉴国外学者在布拉德雷研究方面的成果。例如,对布拉德雷形而上学作最清晰描述的坎贝尔(C. A. Campbell)的《怀疑论与建构:作为建构哲学基础的布拉德雷怀疑论原则》(Scepticism and Construction:Bradley's Sceptical Principle as the Basis of Constructive Philosophy)、研究《逻辑原理》的曼瑟(A. Manser)的《布拉德雷逻辑学》(Bradley’s Logic)、长达630页的斯普里格(T. L. S. Sprigge)的《詹姆斯与布拉德雷:美国式真理与英国式实在》(James and Bradley: American Truth and British Reality)等学术专著,都可资借鉴。
(五)研究布拉德雷与古典实用主义者的论战
20世纪初,布拉德雷为回应詹姆斯、罗素、杜威等哲学家的批评,捍卫自己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展开了哲学上的“舌战群儒”,留下了一份极其丰厚的哲学遗产。这场世纪哲学论战,其中布拉德雷与罗素的争论,国内外学界已有研究,但布拉德雷与詹姆斯的论战,迄今尚未见详细研究。周辅成等学者对此仅仅一笔带过,只有贺麟列出布拉德雷对詹姆斯的两点批评。这场哲学论战的历史背景、概况、主要内容、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对21世纪哲学变化的启示,还有待作全面系统的探究。再者,布拉德雷哲学中的怀疑论、宗教思想与东方思想,布拉德雷神秘主义与东方思想之联系,布拉德雷怀疑论与维特根斯坦后期怀疑论,布拉德雷怀疑论与卡维尔(Stanley Cavell)怀疑论,这些都有待进行拓展性的比较研究。布拉德雷哲学与中国某些哲学家哲学也只作了零星比较研究,还有待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对比。
布拉德雷哲学的核心是关系理论,《现象与实在》第三章蕴藏着他整个哲学的秘密,他对“绝对”(或“太极”)的描述在英语世界无出其右,以致有人认为在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前,最好先读布拉德雷的《现象与实在》。他被公认为“新黑格尔主义者”,但他在哲学上更加彰显出康德式虔诚,而且他的神秘主义、哲学的出场方式等对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卡维尔产生了实在影响,尽管他们没有明确说过与布拉德雷的哲学遗产有什么关联。
最后,作为本文总结,我们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西方学界一般认为,布拉德雷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升温,西方学者重新燃起对他哲学思想的兴趣。但是我们发现,20世纪60年代西方就已出版如《布拉德雷的观念论》等3本关于布拉德雷研究的专著和写出如《布拉德雷哲学中的具体共相》等5篇博士论文,而此前30年才出版如《布拉德雷与柏格森》等6本专著和写出1篇博士论文(即《布拉德雷〈伦理学〉批判研究》),可见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哲学就开始受到青睐。是何原因使其然?我们觉得这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代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在1964年授权出版的《布拉德雷哲学中的知识与经验》这篇博士论文有关,因为文中对布拉德雷哲学充满同情但只带有些许批判。
第二,布拉德雷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毋庸置疑,布拉德雷因形而上学而获得极高的赞誉,但他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靠的是道德哲学和逻辑哲学的贡献而非他的形而上学。学者们对他哲学的重新定位,不大会去维护他的全部哲学观,但对他本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更广泛的思辨问题。换言之,布拉德雷最看重自己的形而上学。那么,形而上学能否成为布拉德雷哲学中的“活东西”呢?客观地说,在形而上学方面,他拒斥了多元论和实在论,主张把物质一元论与唯心主义融为一体,通过“现象”来揭示隐藏在人们关于世界的日常观念中的矛盾;“实在”是“一”而非“多”,没有真正独立之物,绝对唯心主义意义上实在是概念。布拉德雷的形而上学对青年时代的艾略特的诗歌确实产生了深刻影响。布拉德雷的形而上学是否能够恢复到他在世时的影响还有待历史来证明。不过,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者们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在于忽视了布拉德雷的广泛兴趣,他的哲学不仅有形而上学,还有历史哲学、政治理论、伦理学、逻辑学和知识论。
第三,布拉德雷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是与黑格尔哲学在当代的命运紧密相连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哲学界提出了“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样一个问题,问题的背后是要把分析哲学通到黑格尔,而在此之前只是把分析哲学与康德哲学打通。诚然,在“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们无法做出也不应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在当代哲学中或广而言之,在哲学中有时康德哲学问题较为显现而有时黑格尔哲学问题较为显现,二者在哲学发展过程中总是在交替不断地苦恼着人类的意识。像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存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关系一样,黑格尔与布拉德雷之间也存在这样的关系,换句话说,黑格尔哲学在分析哲学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布拉德雷哲学几乎就有什么样的地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布拉德雷仅仅继承了德国哲学传统,包括洛采的哲学,而应该说,布拉德雷很多哲学思想虽然遭到误解,但是要对他的哲学思想做出恰如其分的阐述,势必要充分考虑他对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黑格尔理性主义传统的双重继承。至于布拉德雷与分析哲学的关系,说布拉德雷是符合论者,这样的说法是不够全面的。他的形而上学真理论尝试证明弗雷格所看重的符合论的不足。不言而喻,布拉德雷尽管对哲学逻辑和语言哲学有所贡献,尽管在他那里还可以见到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相平行的东西,但是如果因此就给布拉德雷戴上一顶分析哲学家的帽子,这肯定是不合适的。西方哲学家对布拉德雷的重新评估,与对分析哲学起源兴趣的复兴密切联系,这又与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对其的批判有关。
第四,布拉德雷的知识论是与其形而上学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他没有把知识论看做独立的探究领域,而是作为形而上学讨论的一部分。寻找对知识的合理解释,可谓其对实在与知识的旨趣所在。在获取知识的手段方面,由于无矛盾是知识与实在的标准,布拉德雷倡导思想与直觉的重要性。从知识论角度看,布拉德雷早期哲学具有后期哲学的雏形,所以,他的哲学理路,不是由历史转到伦理,再由伦理转到逻辑,再由逻辑转到形而上学;而应该说,他论述的历史是历史哲学,他讲究的伦理是伦理哲学,他眼中的逻辑是哲学逻辑,他的形而上学体系见于《现象与实在》。所以,想到布拉德雷哲学那充满丰富隐喻的文学风格,想到他赋予思想和直觉的使命,想到他的哲学中的宗教神秘主义,把他的哲学与先秦惠施哲学、印度中世纪商羯罗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能有大大超越分析哲学传统甚至超越西方哲学整个传统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