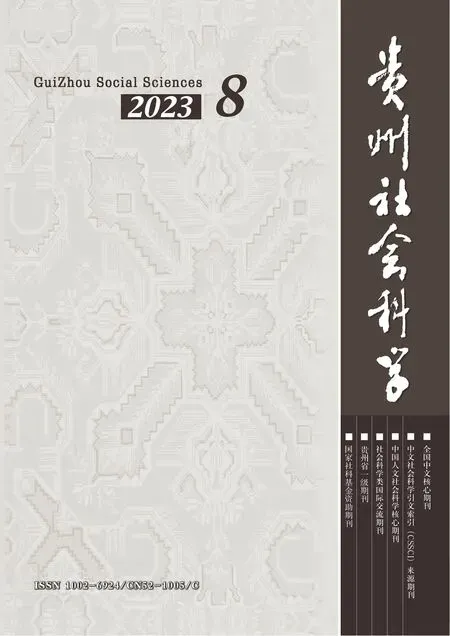从萨满到佛陀:契丹建国前后的政治变局与信仰转向
王德朋
(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有辽二百余年间,佛教大盛,以至于元世祖有“辽以释废”①之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佛教并非契丹人的初始信仰,而是经过契丹建国前后对萨满教的逐渐疏离,才实现了由信仰萨满到崇拜佛陀的巨大转折。关于辽代萨满教、佛教,学术研究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②但契丹人由信仰萨满到崇拜佛教的转向过程则鲜有探究。因此,这种转向何以可能,究竟哪些因素参与其中,需要详细剖析。本文拟以契丹人的宗教信仰为核心,深入探究契丹建国前后政局变化与信仰转向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萨满崇拜:契丹早期的宗教体验
萨满教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的原始信仰,虽然在汉语史料中“萨满”一词晚至南宋才由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以“珊蛮”定名,云“‘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③但“变通如神”的阐述却指明了萨满的主要功能:在人与神之间充当中介和桥梁,进而实现趋利避害,祛灾祈福。
终辽之世,萨满信仰对辽代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日本学者认为“辽代契丹的风俗和制度,几乎都是建立在萨满教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④有鉴于此,欲了解契丹人的宗教信仰如何转向,就必须从了解萨满信仰开始。萨满教是一种多神信仰,唯其如此,萨满信仰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就契丹的情况看,主要有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厌胜习俗等。
(一)祖先崇拜。祖先崇拜直到今天也是世界各民族民族情结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人祖先崇拜的特点是更加强调祖先的神格色彩,这在契丹民族起源传说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辽史》云:“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⑤在此,契丹人直接把他们的始祖描绘为乘白马的神人和驾牛车的天女。在契丹的祖先书写过程中,继青牛白马的始祖传说之后,又有三主传说:
后有一主,号曰廼呵,此主特一骷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骷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喎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后因其妻窃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国之能名,余无足称焉。⑥
上述三主,廼呵化身枯骨,祭祀乃现;喎呵戴猪豕服,时隐时现;昼里昏呵已食之羊,次日复有。这些事迹皆充满异能色彩,表面看来荒诞不稽,甚至为“中国之人所不道也”,⑦但细究三主的行为与萨满的通灵形象极为相似。因此,日本学者提出,“萨满都是每个集团的统率者,有时也是军事指挥官,并被设想为各该血缘集团的始祖”,而“契丹的始祖也是萨满”。⑧
如果说始祖及其后三主的神话传说还仅仅是口耳相传,《辽史·太祖纪》所塑造的太祖形象则是一位现实生活中的神。这位大辽王朝的开创者生而不凡,“初,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⑨考诸其他正史,各朝太祖因灵异受孕,出生时遍体生香、满室红光者并非稀见,如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皆有此异,惟辽太祖出生不久即“知未然事”在正史中极为罕见。这项“知未然事”的特异能力非同寻常,它无疑同知未来、晓生死的萨满形象更为接近。其后发生的史事进一步验证了辽太祖预知未来的异能:天赞三年(924年)六月,太祖召皇后、皇太子及诸臣,诏曰:“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闻诏者皆惊惧,莫识其意”。⑩直至天显元年(926年),太祖崩于途次,众臣方悟,而“天赞三年上所谓‘丙戌秋初,必有归处’至是乃验”。从生而有异到死而先知,太祖的形象塑造较之契丹始祖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飘渺传说及其后三主忽而骷髅、忽而戴猪豕服的怪诞装扮,已经摆脱了萨满信仰中普通巫者的形象而向更为高级的“神”的形象进阶。从契丹始祖传说到太祖的神格形象,契丹人塑造历代祖先神异形象的目的不过是突出本民族的特异性,以为后来统一各部乃至奄有天下提供合理依据。乾隆就看透了这一点,他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的上谕中,针对《契丹国志》记载的三主传说指出:“虽迹涉荒诞,然与《诗》《书》所载简狄吞卵、姜源履武,复何以异?盖神道设教,古今胥然,义正如此”。
(二)自然崇拜。作为一种多神信仰,萨满教本身就含有万物有灵的观念,契丹人对山川、天地的祭拜和崇信尤为突出。
契丹的山川崇拜集中表现在对黑山、木叶山的祭祀上。“黑山在境北”,冬至日,“天子望拜黑山”。相比于望拜黑山,契丹对木叶山的祭祀更为隆重:其一,祭祀的地点就设在木叶山,而非黑山那样的遥祭。其二,就出席祭祀仪的人员结构来看,皇帝、皇后、宰执、群臣、命妇悉数参予。其三,祭仪之高度繁复,既非正旦、夏至、重九等岁时杂仪可比,亦远超同为吉仪的瑟瑟仪、拜日仪之上,足见契丹人对祭祀木叶山的重视程度。
契丹人对天地甚为敬畏,国之大事,名义上都一秉天意而行,连契丹皇帝的年号、尊号都频频出现“天”字,年号如天赞、天显、天禄,尊号如大圣大明天皇帝、天授皇帝、天赞皇帝、天辅皇帝、天祐皇帝。契丹人既敬畏天地,则祭祀之礼也倍显殷勤,连宋人都知道契丹“一岁祭天不知其几”,史实也的确如此。翻检《辽史》,契丹早期祭天地的记载几乎无时无事不有:兴兵征伐、巡幸游猎、偶得吉兆、新皇即位等事皆须祭告天地。
(三)厌胜习俗。厌胜,又称厌禳、厌祷,是一种趋吉避凶之术,曾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中,契丹人也继承了厌胜传统,其具体作法,一种是直接行厌胜术,如辽太宗征伐后晋,进入后晋皇宫时就曾“磔犬于门,以竿悬羊皮于庭,为厌胜法”。另外一种是将厌胜术夹杂于各种仪式当中,如射鬼箭,“凡帝亲征,服介胄,祭诸先帝,出则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乱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
二、辽朝初年的军事征服对契丹人佛教信仰的影响
契丹早期佛教信仰与对外军事征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发展脉络看,这种联系首先从契丹对唐的侵扰开始,“武德初,数抄边境。二年,入寇平州”。武德六年(623年),契丹改变了对唐策略,“其君长咄罗遣使贡名马丰貂。贞观二年,其君摩会率其部落来降”。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契丹对唐政策再次发生变化,“窟哥等部咸请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无极县男,赐李氏”。至此,契丹人开始大规模内附,唐王朝则以羁縻之道处之,这种紧密的政治联系决定了契丹早期信仰不可能不受到唐代佛教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契丹内附以后,唐代的契丹羁縻州大部寄治于营州、幽州界内,而营幽二州堪称唐代北方地区佛教重地。营州地区早在三燕时期就流行佛教,北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更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思燕佛图。隋唐时期,营州佛教依然引人注目。相较于营州,幽州的佛教更为发达。在中晚唐河朔割据的背景下,由于地方割据势力的支持,幽州成为北方重要的佛教中心。据敦煌文书记载,幽州有“大寺一十八所,禅院五十余所,僧尼一万余人,并有常住,四事丰盈”。如此众多的佛教寺院、僧尼归入契丹势力范围,对契丹信仰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值得玩味的是,几乎在幽云十六州入辽的同时,太宗宣布,“改元会同”。这一年号颇具象征意义,它透露出辽太宗将塞外游牧之地与幽云农耕地区混而为一的强烈愿望,这种“会同”当然也包括宗教信仰上的彼此接纳,它预示着此后契丹人有可能接受佛教。
天赞四年(925年)冬,阿保机亲征渤海,天显元年(926年)正月,渤海国灭。其后,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辽太宗耶律德光又将大批渤海遗民迁徙到辽东地区居住。渤海归入契丹版图对契丹早期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而契丹奄有渤海的佛教意义却常常被忽略。渤海人信奉佛教,考古工作者曾经在渤海上京城内发现九处佛寺遗址以及石灯、舍利函等佛教遗迹,遍布渤海上京、中京、东京等地的佛教遗迹说明奉佛是渤海的普遍现象。渤海崇佛习俗不能不对契丹人的宗教信仰产生影响。有学者曾对吉林农安辽代古塔塔身暗室出土的佛教文物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这些佛教文物蕴含了渤海国的文化因素,其中,释迦牟尼铜坐像应为存在于辽代的渤海遗物。至于天显三年(928年)迁东丹国渤海遗民入辽阳故城,并以辽阳为南京之后,渤海人更是把奉佛习俗由渤海故地传至辽东。
回鹘,亦称回纥,是唐宋时期中国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契丹与回纥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过程。据《辽史》记载,阿保机称帝后,太祖七年(913年)冬十月,“和州回鹘来贡”。不过,这种朝贡关系是不稳定的,辽太祖决意向西北一带扩展自己的势力。经过一连串的军事打击,天赞三年(924年)九月,“回鹘霸里遣使来贡”,次年四月,“回鹘乌母主可汗遣使贡谢”。从此,回纥朝贡契丹几乎贯穿了辽朝始终。除军事征服之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回鹘商人赴辽贸易,以致《辽史》记载说,“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谓之“回鹘营”。有些回鹘人来契丹后滞留不归,甚至仕于辽朝,如“孩里,字胡辇,回鹘人。其先在太祖时来贡,愿留,因任用之”。太祖皇后述律氏也是回鹘后裔,《辽史·外戚表》谓“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后”。这些长期滞留契丹并最终融入契丹社会的回鹘人对契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深刻的当属宗教领域。有学者认为,八九世纪时,摩尼教取代萨满教成为回鹘国教。回鹘摩尼教对契丹早期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检讨阿保机的降生神话、契丹人的始祖神话以及一些重要的契丹习俗,它们大都能在摩尼教神话、教义中找到相应的原型或依据,据此可以看出,摩尼教的传入为契丹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阿保机藉摩尼教神话自况,进而建立国家,实行帝制,成为契丹人的民族英雄。需要注意的是,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后,佛教取代摩尼教成为回鹘最为流行的宗教。史载,回鹘“奉释氏最甚”,可见佛教已深深渗入回鹘的日常生活。此时,回鹘通过朝贡、贸易等方式将佛教带入契丹社会当在意料之中。
三、契丹由萨满信仰转向佛教信仰的必要与可能
藉由军事征服,自北魏初年至唐末五代的近600年间,契丹人与崇佛的大唐王朝及汉、渤海、回鹘发生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对契丹人的宗教信仰产生影响,其结果就是促使契丹人由信仰萨满转向崇敬佛陀,而这种信仰转向自有其内在逻辑。
(一)转向的必要性。归根结底,宗教信仰是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社会意识领域的投射,因此,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联。早期的契丹人“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契丹人这种行踪不定、饥饱无常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们与需要严密的组织机构、严格的宗教戒律的佛教无缘,同时,契丹人对客观世界极为有限的认识能力也决定了他们无法接受拥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和思辨色彩的佛教。如此,也只有相对粗陋、拙朴的萨满信仰与契丹人比较原始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公元8世纪上半叶,随着大贺氏联盟的瓦解,遥辇氏部落联盟的重建,契丹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对契丹人早期“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的游牧生活,到遥辇氏联盟时期,农耕因素已经渗透到契丹人的生产方式之中。例如,始祖涅里时期“究心农工之事”,“教耕织”,“皇祖匀德实为大迭列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太祖平诸弟之乱,弥兵轻赋,专意于农”。显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契丹人逐渐改变了单一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开始向农牧并举方向发展,尤其幽云十六州入辽后,农业在契丹人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进一步加大。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的转变促使契丹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幅提升,这样,原始的萨满教已经不能适应他们的精神需求,“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及人类自身的发展,人类已不再满足于最简单的生存需要,他们追求社会角色的确认,心理与情感的满足,这时,制度化的宗教便取代了原始宗教”。契丹生产方式由单一游牧向游牧农耕兼有的转变急切地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宗教信仰,至此,佛教进入契丹的精神世界已是水到渠成之势。
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的转变一起呼唤佛教到来的,还有契丹势力的不断扩大。早在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契丹人就不断向外扩张,“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郡”。痕德堇可汗时期,在担任夷离堇的阿保机的推动下,契丹人更频繁地展开对周边各族的征战活动,仅唐天复二年(902年),即“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阿保机立国后,除继续对周边各族用兵,还染指中原,灭渤海而置东丹,继之而起的辽太宗更将燕云十六州收归辽朝版图。契丹势力的不断壮大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大量汉人、渤海人被契丹俘获,二是阿保机于天祐四年(907年)正月庚寅,“燔柴告天,即皇帝位”。与这两个后果相对应的问题是:如何安置被俘的汉人、渤海人?如何解释阿保机即位的合法性?对于前一个问题,阿保机采取了“不改中国州县之名”,“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的策略。对于后一个问题,仅以契丹人传统的,包含于萨满信仰之中的天灵信仰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此时阿保机治下除了契丹人,还有大批的汉、渤海人。因此,他必须借助萨满之外的宗教体系来解释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实际上,阿保机“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的疑问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他急于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寻找依据的心态,在此,以佛教理论来解释阿保机即位的合法性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二)转向的可能性。随着契丹势力的壮大,特别是向汉地的扩张,大量汉人被置于契丹统治之下,寻找一种新的宗教体系已经势所必然,这正如杞奇斯钦总结蒙古人信仰转变时所指出的那样:“从一个古朴简单的游牧社会一跃而成世界之王的蒙古人,面对许多不同的文化、新奇的生活,都不能不有所爱慕和采纳,对于外来的宗教,当然也是如此。同时也因所接触的外族文化愈多、愈复杂,其原始简单的宗教,愈不会像一个有哲理和隆重法仪的宗教,更能吸引或满足这些世界征服者们的精神上的需求”。外部世界对契丹人的精神吸引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契丹崇奉的萨满教与佛教能否相互包容?分析萨满教和佛教的特点可以看到,萨满教没有系统的文本教义,没有统一的宗教组织,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多神信仰,而佛教经过由魏晋至隋唐的演变,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圆融能力的宗教,这意味着两者之间互不排斥。这样,一方是契丹游牧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特征的萨满信仰,一方是经过长期发展,已经高度成熟且具有强大圆融能力的佛教信仰,两者的彼此接纳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实际上,契丹萨满教的某些仪式、功用与佛教尤其是密教有异曲同工之处,进而为契丹人接受佛教提供了重要基础。日本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鸟居龙藏在20世纪早期就提出“萨满教原为辽人固有之宗教,真言宗加持祈祷又类似之,故密教为契丹人所喜。当时俗人对于密教,与萨满教殆同一信仰之,辽之王宫贵族等亦然。要之,萨满教与密教之加持祈祷,由民众之目观之,固同一也”。野上俊静也指出:“密教的流行发端于契丹民族固有的信仰——萨满教教义。”
四、太祖、太宗时期契丹佛教信仰的最终确立
太祖、太宗时期,辽代社会发展的主线是不断开疆拓土,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汉人、渤海人纳入契丹人的势力范围。然而,如何安抚接踵而来的汉人、渤海人则需谨慎处理,阿保机采取的策略之一就是兴建佛寺。阿保机时期见诸《辽史》记载的寺院主要有以下几座:
(一)开教寺。唐天复二年(902年)秋七月,阿保机伐河东代北,“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
龙化州,“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阿保机伐破代北后,“建城居之”,此城是阿保机担任迭烈部夷离堇之后,以俘掠建立起来的第一座城池,此后阿保机受大圣大明天皇帝尊号,建元神册即在此地,可称阿保机的龙兴之地。在具有如此重要象征意义、政治意义的城池,阿保机兴建起一座佛教寺院,其虔心向佛并借以收拢人心的意图十分明显。
此外,“开教”之名也颇具深意。就其字面含义来看,明显有“开宗创教”之意,这足以反映阿保机强烈的宗教意愿。而在佛经语境中,“开教”有教化愚顽,俾向佛法之意,故后世有以“开教”入高僧谥号者,如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诏谥竺法兰开教总持法师。可见,“开教”无论从字面意义来看还是佛教语境来看,既是一个宗教目标,又是对弘教功业的充分肯定。阿保机以“开教寺”为治下首座新城的第一座佛教寺院命名,其宗教倾向、志向都已显露无遗。
(二)大广寺。太祖三年(909年)四月,“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该条史料中的韩知古是太祖时期重臣,曾任左仆射、中书令等职,“为佐命功臣之一”,以这样一位重臣主持立碑,可见太祖对此事的重视。不过,该条史料所云“功德”究竟指何而言尚须斟酌。“功德”,或可指世俗的功业与德行,或可指佛教中诵经、布施等事。从阿保机自即位以来迭次征伐,屡立功勋的情况看,此处的“功德”应指前者。值得深思的是,阿保机在佛寺内以佐命功臣为自己立碑纪功并非契丹传统,而这种新做法说明早在辽太祖时期,佛教就与政治发生了紧密联系。
(三)天雄寺。《辽史》记载,太祖六年(912年),“以兵讨两治,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这段史料中的“西楼”位于辽上京,《旧五代史》谓天祐末阿保机自称皇帝后,“名其邑曰西楼邑”,“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这三座佛寺是否包括天雄寺,无史可稽,但“僧尼千人”则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足见上京城僧尼数量之多。
阿保机在上京建天雄寺的目的是“以示天助雄武”,这一点颇值玩味。契丹人的萨满信仰以天地崇拜著称,其具体表现形式是“祭天”,而此时阿保机却采取建立佛寺的方式暗喻上天对自己的佑护,这显然已脱离了契丹人的萨满传统,而更多地向佛教信仰方向靠拢。
(四)安国寺。天赞四年(925年)十一月,阿保机“幸安国寺,饭僧,赦京师囚,纵五坊鹰鹘”。阿保机这次巡幸佛寺主要有三项活动:饭僧、赦囚、纵鹰鹘。这三项活动背后的意义值得深究。天赞三年(924年)六月,阿保机召集皇后、皇太子及群臣,恺叹“未终两事,岂负亲诚”。从阿保机后来的举动来看,此“两事”一为征服回鹘、党项等西北部族,一为征服渤海。前一事已于天赞四年(925年)九月以前完成,“惟渤海世仇未雪”,阿保机于天赞四年(925年)十一月幸安国寺、饭僧、赦囚、纵放鹰鹘后,该年十二月“乃举兵亲征渤海大諲譔”。因此,天赞四年(925年)阿保机幸安国寺,饭僧、赦囚、纵鹰的目的应该是为此后的灭渤海祈福。
《辽史》记太祖朝佛教史事有限。除上述几例,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下面一段记载: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召皇太子春秋释奠。
辽太祖与群臣的这段对话大致发生在神册元年(916年)前后,因关涉到辽朝初期文教政策及儒释关系的走向,故常常为论者所引用。太祖作为创业之君,欲祀有大功德者,遂询之臣下。臣下的回答分为两种:侍臣“皆以佛对”,独皇太子耶律倍以孔子对。仔细品味这两个答案,“皆以佛对”充分说明佛教在契丹人中间,特别是在契丹上层人物中间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影响。虽然在耶律倍的建言下,神册三年(918年)五月,“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但这仍不能说明儒学在辽朝初年的文化策略之争中占得上风。相反,从众臣“皆以佛对”,独耶律倍主张祭祀孔子的情况看,辽初社会文化生活中,佛教已占有明显优势。
太宗是辽代的第二位皇帝,也是辽朝初期奠定契丹基业的皇帝,故明代学者谓“辽之兴也,吾不曰太祖,而曰太宗”。明代学者之所以对太宗赞誉有加,关键在于太宗施行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因俗而治”的治国方略有效地巩固了辽朝初年契丹对汉人的统治。而要成功做到这一点,必须对汉人佛教习俗有深刻了解。从相关史料的记载来看,太宗对佛教并不陌生,陶谷《清异录》载:
耶律德光入京师,春日闻杜鹃声。问李崧:“此是何物”?崧曰:“杜鹃。杜甫诗云: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许大世界,一个飞禽,任他拣选,要生处便生,不生处种也无,佛经中所谓观自在也。”
这则史料中的“观自在”是佛教用语,《心经》首句便为“观自在菩萨,行深波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则史料中,太宗以飞禽拣选栖息之地为喻,说明佛教心无所碍的境界,可见太宗已有较深佛学修养。
太宗本人有一定的汉学修养,又对佛教有所了解,这为他在宗教政策上实行“因俗而治”提供了可能。尊重汉人的佛教信仰,继续推行太祖以来的佛教政策以收拢民心便是“因俗而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显十年(935年)正月,太宗皇后萧氏崩于行在,而他追思萧后的途径是向佛教祈福,天显十年(935年)十一月,太宗“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就在弘福寺,太宗“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顾左右曰:‘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岁时未几,今我独来!’悲叹不已”。太宗的慨叹不仅是对父母兄弟的怀念,从佛教意义上说,更是对“一切不久留,暂现如电光”的佛教观念的认可。
太宗时期的重大佛教事件是建菩萨堂于木叶山。《辽史·地理志》云:
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于诸部。
天显十一年(936年),太宗出兵援立石敬瑭,进而取得燕云十六州是底定辽代疆土的重大事件。太宗之所以愿意出兵援立石晋,内在动因当然是契丹扩张疆土的强烈渴望,而在这则史料中,却记为太宗梦中受菩萨开示所致,其目的在于为辽太宗奄有燕云十六州披上神圣外衣。
辽太宗以神意藻饰援立石晋还有巩固皇位的深意。太祖时期,立耶律倍为皇太子,太祖去世后,耶律倍理应继承皇位。然而,在述律后的强力干预下,耶律倍被迫让位,太宗最终得以继皇帝位。耶律倍“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的不满与愤懑自不待言,契丹大臣对太宗得位也多有不满者,南院夷离堇迭里即是其一。史载:“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指辽太宗)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指耶律倍)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鞠,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由此事可知,太宗继位前后围绕皇位继承问题的斗争极为激烈、残酷。与此同时,太宗甫一即位,便产生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对手——皇太弟李胡。李胡为太祖第三子,深受述律后的宠爱,后来李胡与世宗争夺帝位时,述律后亦自述“昔我与太祖爱汝异于诸子”。天显五年(930年),李胡“遂立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同年三月,“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太祖崩时,太宗便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即皇帝位,循此故事,作为皇太弟、皇太子、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李胡当然也有资格继位大统。李胡的上述头衔加之述律后的支持,无疑对太宗的帝位构成了巨大威胁,何况太祖崩后,述律后最初欲改立的很可能就是少子李胡。因此,太宗继位之初,既面临契丹上层贵族的质疑甚至反对,又面临着李胡对皇位的现实威胁。欲应对如此严重的权力危机,以天意、神意打扮自己是行之有效的策略。由此,可以明显看出,谙熟佛教的辽太宗已将其应用于政治斗争之中。
萨满教是契丹人的初始信仰。虽然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萨满教是否属于宗教看法不一,但就契丹早期情况而言,契丹人的萨满信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宗教因素,例如神灵崇拜,这为契丹人提供了最初的宗教体验,从而为契丹人接受佛教提供了经验基础。但是,辽朝建国前后,随着契丹对外军事征服的不断胜利,政局日益复杂,契丹上层既要解决接连不断的内部斗争,又要着力安抚数量庞大的被俘人员,以巩固不断扩大的疆域。显然,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既无系统教义和完备典籍,也无严格教团组织的萨满教无能为力,因而,时代在迫切地呼唤着成熟宗教的到来,以为解决契丹人面临的难题助力。太祖、太宗前后,契丹人通过军事征服等渠道,经由汉、渤海、回鹘等民族受到佛教影响,并最终实现契丹人由信仰萨满到崇敬佛陀的宗教转向。这种转向虽然缓慢但有迹可循,检视《辽史》,可以看到萨满的影响在契丹宗教世界里逐渐消退。以萨满教一向看重的祭天而论,辽朝前期,太祖、太宗直至穆宗、景宗,祭天地的记载屡见于《辽史》。而圣宗在位时,1006年之后20余年的时间里没有祭天地的记录,兴宗在位25年里,只有4年祭祀过天地,道宗在位47年,只有一次祭天记录,天祚帝在位15年则从未祭祀过天地。祭天地频率的急剧衰减乃至完全废弛充分说明契丹人对包括天地崇拜在内的萨满信仰已经日益疏离和淡漠,与之互为对照的则是佛教信仰逐渐走向兴盛,至道宗时期,辽代的佛教崇拜达到顶峰。
注 释:
① (明)宋濂:《元史》卷163《张德辉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823页。
② 关于辽代萨满教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朱子方:《辽代的萨满教》,《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6期;张国庆:《辽代契丹贵族的天灵信仰与祭天习俗》,《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任爱君:《神速姑暨原始宗教对契丹建国的影响》,《北方文物》2002年第3期。关于辽代佛教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主要有:张国庆:《佛教文化与辽代社会》,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尤李:《多元文化的交融:辽代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编:《辽金佛教研究》,金城出版社,2012年;蒋金玲:《论辽代汉人与〈契丹藏〉的雕印》,《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日)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0年;(日)藤原崇人:《契丹佛教史研究》,京都:法藏馆,2015年。
③(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④(日)蒲田大作:《释契丹古传说——萨满教研究之一》,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293页。
⑤(元)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2016年,第504页。
⑥(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中华书局,2014年,第3~4页。
⑦(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3《正统辨》,中华书局,1959年,第34页。
⑧(日)蒲田大作:《释契丹古传说——萨满教研究之一》,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314、313页。
⑨(元)脱脱:《辽史》卷1《太祖纪·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1页。
⑩(元)脱脱:《辽史》卷2《太祖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