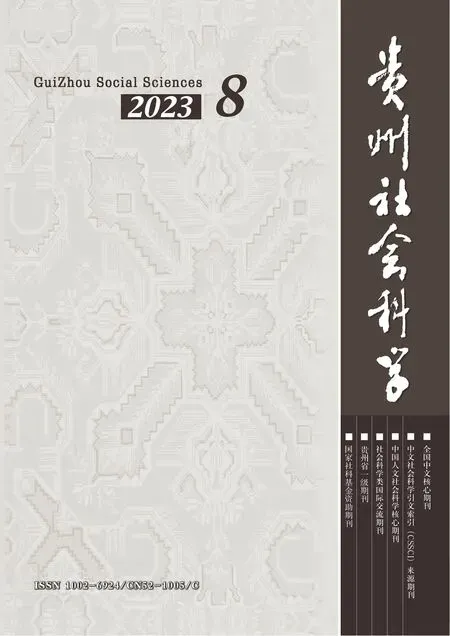先秦诗乐之教与“君子”人格
刘冬颖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立德树人,君子人格尤其受到普遍推重,凸显了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文献可以稽考的“君子”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左传》《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中亦多有出现,最初的意义是指“君王之子”,着重强调地位的崇高;后泛指贵族统治者,常常与“小人”相对而言;终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阐扬其精神价值,逐步由统治阶级的专称演变为“有才德的人”的代称,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尊奉的道德人格化身。在君子人格的培养中,以《诗经》礼乐教化为核心的“诗乐”教育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一部汇集文学、礼仪、音乐、民俗、政治、伦理、教育和舞蹈的综合文化经典,以多元艺术形式承载着我们的民族精神、道德理念和审美情趣。《诗经》的教化功用,正是通过音乐、舞蹈、歌唱、乐器演奏等,将诗歌文本视觉化、听觉化、口传化,在诗乐的美好旋律间,在舞者的翩翩身姿里,以艺术表演的巨大魅力,形成一种礼乐感召的精神力量。通过诗乐艺术对身心的培育与修养,最终形成的君子人格,是内在完满道德与外在仪容举止相互统一的美善境界。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君子”道德价值系统已经成为了中国精神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因此探究先秦时期的诗乐之教与君子人格建构的关系,对于溯源中华文化精神具有深远意义。
一、诗乐教育是君子的必修科目
“君子”一词广见于先秦典籍,《左传》中出现了185次,《周易》卦爻辞中出现20次,《论语》中出现了107次[1],可见“君子”在先秦的重要性。“君子”意涵,随历史演进不断丰富,最初专称统治阶级,《尚书》中出现的 8 处“君子”,一处指的是有德的贤能之士外,其他七处都指的是各级王臣官员,后由孔子定义为“个人道德修养高尚”的义项。在“君子”意涵的丰富与转变过程中,成就“君子”人格的重要教育内容“诗乐”,起到了推动作用。
诗乐教育最初学在官府,正是为了培养贵族阶层“君子”设立的,随着礼崩乐坏,私学兴起,原来专属于贵族阶层的诗乐教育下移,成为普通士人成就自我人格修养与进身之阶的重要途径。无论在西周时期的官学,还是由孔子开创、惠及普通士人的私学,诗乐教育都是重要的部分,教与学的设置都非常体系化,对教授的诗歌篇目、乐器种类、学习顺序,都有严格的规定。
(一)诗乐教育与君子治国修德培养
据《尚书·舜典》《尚书·益稷》的记载,在中国文化史上,至晚在虞舜时期就有专门从事歌舞表演的艺人。夏商周三代均纳乐于礼,将乐作为国家政典运行的一部分。周代对礼乐更加重视,周公“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2]卷三十一,842。国家层面对礼乐的重视,推动了歌诗的繁荣。诗歌唱诵、乐舞表演穿插在礼仪之中进行,通过艺术的审美实践,完成礼乐的教化功能,陶冶人的内在情操,培养性情高雅的君子。《仪礼》《礼记》《周礼》《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都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礼乐仪式。从今本《仪礼》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等来看,《诗经》的“二南”已成为周代礼乐的组成部分,《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与《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蘋》就常见于乡饮酒礼的诗乐表演中。在古人看来,通过“诗乐”教育培养出的人,正直、宽厚、恭谨,能够维护社会和谐。诗乐,也因此成为早期“君子”(贵族统治者)从童年就开始的必修科目。
《周礼》所记的周代音乐教育机构完备,由管理、教师和表演等三部分人员组成,职官多达1463人。《礼记·学记》记录了诗乐教学的主要内容,也明确了诗乐教育的目的:“《宵雅》肄三,官其始也。”[2]卷三十六,960唐代孔颖达疏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小也。肄,习也。当祭菜之时,便歌《小雅》,习其三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取其上下之官,劝其始学之人,使上下顺序也,故云‘官其始也’。亦谓以官劝其始也。”[3]1522特别强调学子要学习歌吟《小雅》诗篇,重点学习歌吟的是其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官其始也”直言学习唱诵这些诗歌,能使学生懂得从政的道理。
之所以在国子的教育中特别重视诗乐教育,是因为在先秦,尤其是周公“制礼作乐”之前,不入礼乐仪式的散乐和夷乐发达,其特点有二:一是旋律动听,听者沉醉、沉溺难以自拔;二是表演者多为俳优和侏儒,娱乐性强。散乐和夷乐在文艺的审美中没有融入礼仪和德育的内容,对教化无益,甚至会消解、冲击社会的礼仪秩序。[4]因之不能起到治国修德的作用,不可称作“乐”,只能称作“音”或“溺音”。所以在国子的教育中,重视诗乐教育成为培养君子所必备修德治国能力的重要一科。
(二)细化篇目与分科与依年龄循序渐进教学
礼、乐、诗一体的《诗经》是诗乐教育的主要教材,据《周礼》所载,当时的大司乐分科教授国子“乐德”“乐语”和“乐舞”。其中的“乐语”与“《诗》教”相关,包括“兴、道、讽、诵、言、语”几个部分,要求学生诵读诗歌、互相切磋交流诗歌;能创作诗歌,以诗言志;能熟练地在社交场合言谈中运用诗歌,并以诗讽谏。《周礼·春官·大师》:
大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5]
是说乐官大师在教国子《诗》时,不但要教他们《诗》中的具体诗篇,更要从礼仪和音乐上引导国子学《诗》要重视礼乐内涵。如,《大武》是祭祀庆典中歌颂武王伐纣的大型乐舞,学术界已有共识,认为《大武》的每一表演环节都有一首相应的歌诗,分别为《周颂》的《武》《酌》《赉》《般》《时迈》《桓》,旨在赞颂武王克商的丰功伟绩。
《礼记·内则》的记载更具体化,记录了当时的诗乐教育是依年龄循序渐进的:“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郑玄云:“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2]卷二十八,770这里的《韶》舞是文舞,《象》是武舞,跳这两种舞蹈时伴奏的诗乐分别是《酌》和《维清》。在乐官教育国子的过程中,根据学习的难易程度,先学文舞,再学武舞。国子十三岁开始学习音乐,诵读《诗经》,练习《韶》舞,年龄稍长再学习《象》舞和驾车、射箭。其中象舞是歌颂周文王的,舞象舞要歌吟《周颂·维清》。《维清》诗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毛诗序》谓:“《维清》,奏《象舞》也。”郑《笺》:“《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3]584表演时,舞者扮演成文王,手持戈戟,威武亮相,在乐队庄重、肃穆歌唱《维清》的伴和中载歌载舞,以彰显文王征伐的仁义之师形象。通过文献考证可以发现,周代《诗》教采取综合艺术形式进行。国子们经过几年的学习后,六艺之事就能够逐步熟悉了。年轻国子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并演练这样的歌舞,本身就是一种礼乐熏陶。
(三)诗乐承载君子“令德”,浸润家国情怀
《诗经》305篇选自两周500年间,其中62首诗中出现“君子”183次,多为称颂:《鲁颂》1首1次,《大雅》9首28 次,《小雅》32首102次,《国风》20 首 52 次。不同篇章中的“君子”涵义不一,既有统治者,也有品性高尚之人,还是被女子思慕的男子之称。《诗经》中的君子,哪些是贵族尊称,哪些是庶民化了的男子美称,有时很难判断。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有身份、有地位、有学识、有教养、有品德。因《诗经》是国子教育的重要一部分,所以《诗经》对于“君子”的称颂也成为国子培养的目标。《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2]卷三十八,1006这段经典的美学阐释,言简意赅地指出了《诗经》与礼、乐合一,学习、歌吟、观赏这样的《诗》乐,能够受到包括伦理、道德、民俗、礼仪的综合文化教育,会培养内在和谐、外在方正的君子,并为后世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垂范。
首先,君子文质彬彬,“莫不令德”,有风度有修养。如《卫风·淇奥》中“有匪君子,如切如磋”,诗所赞美的主人公不断磨砺自己,品行如玉一般高洁;《湛露》《假乐》《南山有台》等诗篇更是将君子与“德”直接联系在一起。如:“显允君子,莫不令德。”(《小雅·湛露》)“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大雅·假乐》)“乐只君子,德音是茂。”(《小雅·南山有台》)。《诗经》从君子的服饰、言行举止等方面,多次描述了君子的风采与仪态,如“淑人君子,其仪一兮。”(《曹风·鸤鸠》)又如,“岂弟君子,莫不令仪。”(《小雅·湛露》)赞美君子仪表端庄,文雅知礼,温柔敦厚。《诗经》中的“君子”外知礼仪,内修品德,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了诗乐教育君子人格培养最重要的精神内核。
其次,君子德才兼备,是“邦家之基”,富有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诗经》多处称颂君子是“邦家之基”,对邦国兴亡、人民命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如“乐只君子,邦家之光。”(《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小雅·采菽》)“君子万年,保其家邦。”(《小雅·瞻彼洛矣》)“伯兮伯兮,邦之杰兮。”(《卫风·伯兮》)等。《卫风·淇奥》赞美卫武公是如玉一般的君子:“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塑造了一个德才兼备、内外兼修的完美“君子”的形象,也可以说是提出了“君子”的标准:勤于政务、清正廉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温和友善,仪表堂堂。这样一个如玉般的“君子”形象屹立于中国文学史上,随诗乐之教走进历史上无数人心中,熠熠生辉。
以诗乐为代表的文化修养,在君子人格的养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明确了“君子”所应具备的精神气质,傅道彬先生总结为“以仁爱忠信为核心的道德追求”,“以谦敬辞让为规范的礼仪风度”,“以诗书经典为基础的知识修养”和“以勇武敏行为追求的英雄气度”。礼乐文化熏陶下,君子“令德令仪”,是“民之父母”,有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其中呈现的精神、气象和风范,以及其自我期许、要求共同奠定了后世君子人格的基本品格。
二、雅言、雅乐是君子必备的礼乐修养
诗乐教育中最重要的就是“雅言”和“雅乐”的修养。据《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3]2482雅言是当时中国通行的共同语。孔子学生众多,来自方言各异的不同诸侯国,孔子在讲授经典《诗经》《尚书》和司掌礼仪场合时,并不使用鲁国方言,而是运用当时各国的共同语“雅言”。“雅言”的载体,《论语》说的很清楚,就是《诗经》《尚书》和礼仪场合用语,这也使得“雅言”明晰地带着礼仪、诗歌和音乐的色彩!
《诗经》用语的雅正优美、韵律严整、言简意深,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正是“雅言之美”。《诗经》不仅“思无邪”,文辞素朴、典雅,意蕴纯正、厚重,使人感受到情感的真挚与中和,而且诗句回环往复,诵之声韵优美,体现了鲜明的音乐特点。孔子就曾对他的儿子孔鲤说过:“不学《诗》,无以言。”[3]2522学《诗》,可以学习各诸侯国共同使用的“雅言”,锻炼、提高自己在正式礼仪场合的语言表达能力。《左传》和《国语》里都记载了很多次“赋诗言志”的例子,当时的谋臣智者们在外交场合,往往都通过赋《诗》的方式互相交流,这充分体现了学习《诗经》的意义。修习“雅言”《诗经》的君子,“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诗经·小雅·都人士》),博文知礼、言语雅致,内在的精神气质与外在的衣饰举止和谐统一,能够出使四方,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既实现自我价值,还能为民众和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诗经》不仅是雅言的课本,还是雅乐的载体。《诗经》在当时被称为《诗》《诗三百》,不仅包括今天流传下来的《诗经》文本,也包括艺术呈现的声乐旋律、器乐合奏和协配诗乐的礼仪。正因为《诗经》作为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是以综合艺术表演的形式存在的,听《诗》、观《诗》的视觉和听觉感受,频频见诸历史文献,其中最早的记录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的“季札观乐”。
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受本国新任国君所托,出使鲁国。鲁国是当时保存周王朝礼乐最多的一个诸侯国,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在鲁国人为他表演周王室乐舞的过程中,季札非常陶醉,时时点评,彰显了他所代表的吴国对周王朝礼乐的尊崇与认同,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季札点评周乐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今本《诗经》分类排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风》提前,可能因政治或礼乐原因,未表演或未记《曹风》。从季札观乐的评论中,清晰可见《诗经》风、雅、颂的音乐风格大不相同。“颂”是季札最推崇的,他认为“颂”是艺术水准最高的表演形式:“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6]季札的评论,充分展示了《颂》作为一种综合礼乐艺术的视听之美。季札生于当时的文化偏陋之地吴国,却能有很高的诗乐修养,对中原各地的音乐一一给予评点,对雅、颂之声、前代乐舞也能各陈其是,这说明他受过良好诗乐教育。以此来推想,当时中原各国的诗乐教育是远过之的。
《诗经》作为雅乐的载体,在于彰显礼乐文明。如何能更好地推进诗乐教育,诗乐表演是重要的前提。《周礼·春官·磬师》和《笙师》就分别提到了磬师和笙师对国子传授钟、鼓、竽、笙、埙等乐器的演奏方法,并且教授这些吹奏乐器的演奏场合、使用规则,及如何相互配合等。诗乐表演的乐器配制、乐队和舞队的编制等,都有严格的礼仪规范,形式丰富而多元:
1.《诗经》保存了鼓、瑟、钟、琴、磬、笙、簧、管、埙、缶等29种(又有说为32种)乐器之名。钟、鼓、磬为主的打击乐,是《诗》乐表演中使用的主要乐器,又称为“金石之声”。作为一种音乐语言,“金石之声”是以四分之四的拍子为基本节奏的,表演时以齐奏为主。“绝大多数的西周钟都是双音钟”[7],这种双拍式的音乐节奏多反复,音乐风格平和、舒缓。学习这样的诗乐,会培养内在和谐、外在方正的君子。
2.诗乐表演形式多元,有武舞、有文舞;有大舞、有小舞;舞者有男也有女;既有象舞这样诗、礼、乐合一的盛大表演,也有只用一种乐器伴奏的清越歌唱。《周颂·清庙》就是祭祀中仅用瑟一种乐器,以最简单的弦音伴奏所唱的歌曲,《礼记·乐记》云:“《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2]卷三十七,982瑟是一种古老的弦鸣乐器,声音铿锵有力,清晰明亮,能够表达出音符的细节和变化,如轻柔、明亮和深沉等。瑟有25弦,强化抒情时还能变奏出复杂的和弦。歌吟《清庙》时,只用瑟一种乐器伴奏,音乐简单质朴。伴着瑟深沉又华丽的音色,一人唱,众人和,领唱清亮歌咏,合唱队和声浑厚,听起来庄严而隽永,有余音绕梁的感觉。诗乐表演中场面最为宏大的是万舞,《鲁颂·閟宫》载:“万舞洋洋,孝孙有庆。”裘锡圭先生曾对殷商甲骨文中的万舞进行研究后指出,由于万舞参与者众多,故有“多万”的说法。[8]要同时调配人数众多的舞者,自然要用声音响亮、铿锵的乐器,《商颂·那》“庸鼓有斁,万舞有奕”说的是万舞之时钟鼓齐鸣,舞者排列有序,气势磅礴。根据表演形式不同,诗乐表演时表演者有不同装扮,文舞舞者装饰华美,或持羽、或持旄;而武舞的舞者则修饰不多,多持兵器而舞。万舞舞蹈文武兼备,既重视舞者的仪容修饰,同时也有武舞的力量之美。《邶风·简兮》:“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诗人生动抒写了卫国宫廷的万舞表演:领舞的表演者魁伟健美,他先是武舞,舞姿矫健,后又文舞,感人至深,既赢得了国君“锡爵”畅饮的赞赏,更令在场观赏的一个女子情思涌动。此诗以一个女子对舞者的爱慕,烘托了万舞表演的魅力。
3.诗乐表演应用于祭天、祭祖、朝会、出征、农耕、宴饮等不同场合,承担着礼乐的功能:祭祖的各项典礼仪式完成后,“钟鼓既戒”(《小雅·楚茨》),演奏起钟鼓之乐祀神祈福;宴会品尝美酒佳肴时,“鼓我吹笙”“吹笙鼓簧”(《小雅·鹿鸣》),宾主尽欢;宴饮欢愉时,“式歌且舞”(《小雅·车舝》),推进宴会达到高潮;伐木劳动时,“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小雅·伐木》)音乐的节拍起到了统一劳动者步伐、振奋劳动者精神的作用;土山祝祷时,“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陈风·宛丘》)诗中的女主人公不论冬夏,都手持鸟羽,演奏鼓等乐器为人们祝祷跳舞;举行射礼时,“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齐风·猗嗟》)执弓而舞,展现了力与美。
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下,诗乐是作为雅乐的基本文化载体而存在的,庙堂祭典、宴享乡饮、使聘盟会等活动都会使用诗乐。诗乐表演的艺术效果和教化功能,孔子亦颇多嘉许。据《史记》记载,孔子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后,观赏了鲁国乐师挚的表演,曾有过一段经典评价:“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从太师挚开始演奏,到压轴表演的《诗经》首篇《关雎》乐曲,美妙动听的音乐都充盈在孔子耳边,让他特别陶醉。诗乐不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介入了周人的日常生活,痴迷于诗乐的贵族君子,甚至是走路的脚步也要合于诗乐的节奏节拍。《礼记·玉藻》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2]卷三十,820诗乐雅化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塑造了君子的风雅气度,奠定了之后中华君子人格中“文质彬彬”的基本特征。
三、践行、推广诗乐是君子的人生担当
周代形成了体系化的中央和地方教学机构,有“国学”、有“乡学”,不仅担负着培育贵族子弟成为“君子”的重大责任,还要在各个乡里按时举行盛大的乡饮酒、乡射等礼仪中开展诗乐表演,全面推广诗乐教育。贵族子弟在成长中,通过必修的系列诗乐课程,参与诵读、表演、观赏、聆听礼仪中的诗乐,在实践、体验中受到礼乐的熏陶。体系化的“乡学”和“国学”促成了每一乡里的诗乐实践,希冀通过普天下的诗乐传播使得全社会都在礼乐的影响中。
以乡饮酒礼为例,乡饮酒礼是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根据《仪礼·乡饮酒礼》和《乡饮酒义》来看,在周代的礼乐实践中,诗乐表演就是仪礼的一部分。《仪礼·乡饮酒礼》并汉代郑玄注云: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
地壳当然比我们对弹性波传播不完整表述得出的模型更加复杂多样。有时候,当与波长相关方法的分辨率低于基于射线方法的分辨率时,其属性可以描述为统计分形介质(如,Levander and Holliger,1992)。有为得到更多这种不均匀性质而提高地壳模型分辨率的可能性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需要更合适的波传播的物理性质(波动方程的数值解)和密集采样波场的记录。
郑注:笙, 吹笙者也, 以笙吹此诗以为乐也。《南陔》《白华》《华黍》, 《小雅》篇也, 今亡, 其义未闻。昔周之兴也, 周公制礼作乐, 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 所以通情, 相风切也, 其有此篇明矣。后世衰微, 幽、厉尤甚, 礼乐之书, 稍稍废弃。孔子曰:“吾自卫反鲁, 然后乐正, 《雅》、《颂》各得其所。”谓当时在者而复重杂乱者也, 恶能存其亡者乎?[3]986
乡饮酒礼有迎宾、献宾、宴宾、送宾四个环节,举行宴饮仪式的时候,不仅严格区分尊卑长幼,升降拜答,而且礼仪中伴随着《诗经》的吟唱,整个活动更像一场规模宏大的礼乐艺术的演出。“诗乐艺术集中展示的‘乐宾’环节,共囊括了十八首《诗经》作品(十二首《小雅》作品和六首《国风》作品),通过多种形式的音乐演绎,表达了对宾客的尊敬和慰劳,同时在礼乐教化的层面突出厚重典雅的君子风貌。”[9]
推广礼乐的前提,是简化礼乐的繁琐程序,孔子于春秋时代开启私人讲学之风,有教无类。验之于经典文献,孔子是十分重视诗乐教育的,“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0]卷四十七,1938(《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承袭了西周以来的礼乐精神,最重礼乐教化,希冀在潜移默化的优雅艺术熏陶中,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孔子深感音乐的六德(中和祗庸孝友)、六义(兴道讽诵言语)与《诗》之“思无邪”“兴观群怨”的重要性,将诗乐与人生修养之间的关系提炼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2487(《论语·泰伯》)
孔子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修养是从诗歌开始,以礼为依据,而由音乐来完成的。如果说“兴于诗”强调的是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抽象起点,那么“立于礼”则主要指示了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具体准则,其中既包括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包括个体内心对礼的精神实质的理解和遵从。诗乐是以钟鼓管弦乐队配合乐舞进行表演的,需要诸多条件,这样复杂庞大的演奏形式普通民众很难实践。《史记·孔子世家》中载: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0]卷四十七,1936
孔子弦歌《诗经》,使得本来属于贵族礼乐范畴的《诗》乐,可以个人用简单的弦乐器琴、瑟伴奏,吟之唱之,实现道德修养的自我完成。孔子曾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3]2458(《论语·学而》)明确了君子人格的特征,将好学与君子人格的成就联系在一起。孔子立私学,有教无类,实现了《诗》乐“移风易俗”的普及教化,也使得“君子”的培养得以超越社会阶层,真正实现其广泛的道德意义。
孔子特别强调通过日常生活建立君子的人格风范,《论语·乡党》篇文字多记孔子于乡里间的日常生活形态,把神圣的道德规范付诸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孔门弟子更是礼乐的践行者,子游、子夏、闵子骞等都在礼乐传播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子游,在地方治理中践行礼乐教化:
这段记载正是历代儒家尊奉并努力践行的,希望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礼乐教化,实现整个社会的美好风气。
孔子特别重视阐发“君子”的品性德行,在《论语》中,孔门师生多次研讨何为“君子”,譬如“君子不器”“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不忧不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语更是高度概括了孔子“君子人格”的综合表征:“文”,是指礼乐和典章制度的熏陶,重在强调君子的外在风范;“质”则是指仁义忠信,突显了君子的内在修养。他对子张、子贡、子游说:
慎听之!女三人者。吾语女 : 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已。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籥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2]卷四十九,1269
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礼乐要靠真正具有君子人格的人去践行,也只有自觉践行礼乐的人才能成为君子。这种从内外两方面对于立身行事的理想君子人格设计,逐步成为中国儒家文化与中国道德价值的核心概念,在中华文化的传统里、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具有极高的共识度和影响力。在漫长的历史中,君子人格逐渐融入到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与性格之中,对中华民族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先秦诗乐之教是一种承担了综合教育功能的文化艺术教育,诗乐用于社会生活的不同场合,承担着礼仪与教化的功能,其表演的多种形式和艺术美感,推动了《诗经》所承载的礼乐精神和君子人格传播、传承,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独特的审美特征。《礼记·乐记》云:“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3]卷三十七,1545诗乐对君子仪容举止、令德令仪的歌颂、培育,奠定了中华君子人格的基本特点,成为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认同的一部分。
——诗乐全球CEO阿诺德·施密德(Arnold Schmied)谈TMA系列面世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