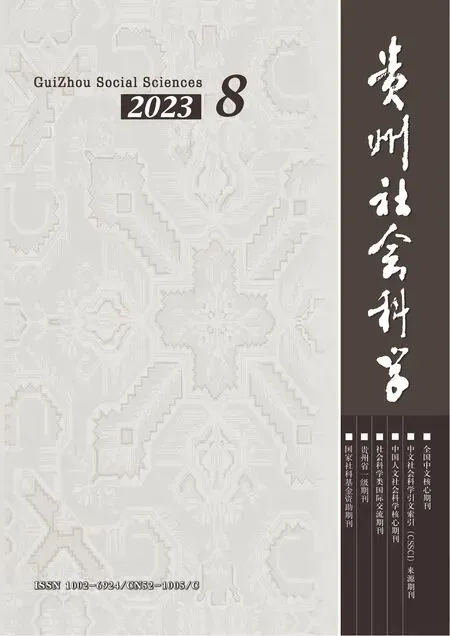“南岩之会”与辛弃疾后期创作的理学渗透
李洁芳 王兆鹏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0)
与理学士人的交往是辛弃疾生平中的重要话题。理学士人,尤其是理学宗师朱熹对辛弃疾的生活、仕宦、思想及诗词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辛弃疾与朱熹的交往历来不乏关注(1)参邓广铭《辛弃疾传·辛弃疾年谱》(三联书店2007年版)、巩本栋《辛弃疾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辛更儒《辛弃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对辛朱关系都有专门论述。另有多篇论文也予以专门探讨,如汲军、马宾《朱熹未赴陈亮、辛弃疾铅山之会原因再探究》(《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第2期);程继红、程国栋《朱熹与辛弃疾交游考述》(《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王昊《辛弃疾与朱熹交游关系考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在辛朱交往的论述中,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未赴约的鹅湖之会尤被重视。,但许多问题仍有待深入及重估,辛朱南岩之会既是辛朱关系转折的重要节点,又是理学渗透辛弃疾后期诗词创作的关键节点。南岩之会的经过,记录于韩淲《访南岩一滴泉》中:
忆昨淳熙秋,诸老所闲燕。晦庵持节归,行李自畿甸。来访吾翁庐,翁出成饮饯。因约徐衡仲,西风过游衍。辛帅倏然至,载酒具殽膳。四人语笑处,识者知叹羡。摩挲题字在,苔藓忽侵遍。[1]
聚会简单而有趣:朱熹辞官归乡,路过上饶,借机拜访故友韩元吉,韩元吉于是邀请徐衡仲作陪,在宴会行将结束之际,辛弃疾匆匆赶来。一个本来简单而又老套的聚会,却因辛弃疾的突然介入而妙趣横生。辛弃疾的参与,不仅为此次聚会增添了愉悦的色彩,也为文学史留下一段佳话。在赞叹之余,却不禁令人追问:辛弃疾为何在朱熹行将离别才匆匆赶到?辛朱二人当时的关系究竟怎样?这次聚会对辛朱的交往有何意义?简单记述之下的南岩之会,是否隐藏了许多被忽略的内容?
一、南岩之会前的辛朱关系冷淡
辛弃疾和朱熹在南岩之会前有过三次交往:一是朱熹曾告诉他人“向见辛幼安说,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某初不信,后提举浙东,亲见如此”[2]。朱熹于淳熙八年(1181)九月二十二日改除提举浙东常平茶盐,说明在此之前二人曾有会晤;二是淳熙八年(1181)春,辛弃疾用密封之船贩运牛皮,被朱熹拘没入官,后经辛弃疾投书索要,朱熹方才放还。朱熹特地将此事告知黄灏,说“因笔及之,恐传闻又有过当耳”[3];三是陈亮《与辛幼安殿撰书》载:
始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见元晦说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言必不妄。[4]
辛弃疾带湖新居落成,据陈亮所说朱熹是“潜入”观看,则朱熹事前未打招呼,辛朱二人当未曾会面。此事发生在淳熙八年(1181),朱熹被命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往临安奏事,路过上饶,辛弃疾时在江西南昌任上。之后不久,辛弃疾便被王蔺以“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为由弹劾。从上述事件来看,辛朱在南岩之会前的交往或为公务性质,或为不愉快的插曲。两人当时的关系很是冷淡。
事实上,辛朱二人南岩之会前的关系,不仅冷淡,甚至颇为紧张。根源在于当时辛朱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从辛弃疾淳熙八年(1181)落职事件及朱熹对“主战”“近幸”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因台臣论列被罢,此事有个政治大背景,即孝宗的治国方略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一年,孝宗一改以往积极筹划“北伐”的雄心,转而谋求“安静”,其政治风格从“事必躬亲”转向“无为而治”。阶段性标志就是最后一位力助孝宗谋求“恢复”的宰相赵雄被罢职,王淮继而为相。也正是在这一年,朝廷中的职业型官僚与理学型士人联手逼退了以往在朝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战派”。自此,“主战派”在朝廷中的势力一蹶不振。辛弃疾正是这一政治转折背景下的牺牲品,其落职是职业官僚集团与理学士大夫集团联手打击的结果。
具体来说,辛弃疾被罢时,宰相王淮正是职业型官僚在朝中的代言人[5]355,操刀弹劾辛弃疾的王蔺则是后来韩侂胄《伪学逆党籍》名单的四位宰执之一[6],算是当时理学士大夫的代言人。王蔺与朱熹为了理学士大夫集团的共同利益多有互动策应。淳熙十六年(1189)周必大罢相,朱熹深感不安,于是投书劝说王蔺“熹独窃意明公之优游不迫,盖将有所待而为之也。虽然,时难和而易失,古之圣贤盖有皇皇汲汲而坐以待旦者。唯明公不忘畴昔之志而果断奋发,以乘其不可失之机,则宗社之休,生灵之幸也”[7],鼓动其清除何澹、黄抡、范处义等政敌。可见,不仅王蔺是理学士大夫中的打手,朱熹在理学士大夫集团中也发挥着顾问与策动的作用。[8]加之朱熹对“主战派”虞允文胡海之气的行事作风和借恢复之名、行敛财之实的批判,[9]弹劾辛弃疾的过程,朱熹或许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王蔺外,周必大更是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对辛弃疾持续排斥打击,以致辛周二人毕生未见有私人层面的交往。周必大与王蔺一样,也是理学士人的政治护法,与朱熹关系密切。
淳熙七年(1180),辛弃疾在湖南创置“飞虎军”,其时周必大任参知政事。在向孝宗上报时,周必大对稼轩“止欲先得军额”颇有微辞[10]。三年之后,周必大在给友人的札子中对此事依然耿耿于怀,又批评稼轩“又竭一路民力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焉”[11]。朱熹也曾对“飞虎军”发表议论“潭州有八指挥,其制皆废弛,而飞虎一军独盛,人皆谓辛幼安之功。以某观之,当时何不整理亲军?自是可用。却别创一军,又增其费”[12],虽然语气较周必大稍有缓和,但同样持负面态度,认为耗用过度。辛弃疾创建“飞虎军”引发的怀疑与争论,成为一年后(1181)被弹劾的最主要理由。辛、朱南岩之会后,朱熹再次评价“飞虎军”,说:“熹窃见荆湖南路安抚司飞虎军,原系帅臣辛弃疾创置,所费财力以钜万计,选募既精,器械亦备,经营葺理,用力至多。数年以来,盗贼不起,蛮猺帖息,一路赖之以安。”[13]评价稍趋正面。但这缘于南岩之会后辛、朱关系的改善。
可以说,辛弃疾淳熙八年(1181)因王蔺论列被罢,根本原因不在其本身是否真的“奸贪凶暴”,而在其政治立场。辛弃疾志在建立功业,进取心强,因而其行为方式往往不按常理出牌。在“主战派”当政时,因属同一集团阵营,辛弃疾所采取的行为方式与手段一般都会被包容,甚至被表彰。辛弃疾在江西平定“茶商之乱”后获得升迁就是明证。但当寻求“安静”成为孝宗朝的政治导向时,当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当政时,同样的做派就会被视为异端,会被当成是对既有秩序的冲击,而遭受打压。辛弃疾的行为模式既与职业型官僚循规蹈矩、只求无过的治理模式冲突,又与理学士大夫推崇的理想士大夫人格相违背,因而受到双重打压。
朱熹与辛弃疾立场并不一致。其对“恢复”的态度前后有变化,政治立场介于“事功”与“保守”之间。隆兴北伐失败之初,朱熹上书孝宗主张抗金,反对议和,偏于“事功”。孝宗朝后,朱熹则批判主战恢复而因循保守,主张“恢复”应以修明内政为首务,趋于“主守”。
乾、淳时期,朱熹对北伐的态度由积极转为保守,力主“恢复”之士皆成为其嫌恶的对象。乾道五年(1169),力主“恢复”的虞允文与力撑理学士人的陈俊卿并相后,朱熹极力诋毁虞允文、王炎等“主战派”,称“如王公明炎、虞斌父之徒,百方劝用兵,孝宗尽被他说动。其实无能,用著辄败,只志在脱赚富贵而已。所惟孝宗尽被这样底欺,做事不成,盖以此耳。”[14]不止于此,朱熹还对同属理学阵营的“事功派”深表不满。朱熹曾批吕祖谦之弟吕祖俭:“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为后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15]朱熹与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也终以不欢而散收场。同时,朱熹的仕途曾为“主战派”所阻。淳熙五年(1178),“保守派”史浩再相,欲起朱熹为中都官,加以重用。赵雄时为参知政事,议宜“以外郡处之……乃除知南康军”[16]。在赵雄的打压下,朱熹只得外任。
除与“主战派”交恶外,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士人与孝宗之“近幸”更是水火难容。淳熙六年(1179),朱熹上疏孝宗“亲贤臣,远小人”,说:“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亵之鄙态。”又说: “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之门,名为陛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阴执其柄。”[17]12754孝宗读后“大怒”,后在宰相赵雄操作下将其贬为提举江西茶盐公事。孝宗时期,“近幸”又往往与“主战派”交织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孝宗对“恢复”的态度及治国方略有关。孝宗早年矢志北伐,为避免各种干扰,尤其是为避开来自于理学士大夫群体的阻挠,便利用“近幸”为其传话及代言。基于共同的立场目标,“主战派”与“近幸”很自然地就走到一起。“主战派”宰相,如虞允文、蒋芾、叶衡等都与“近幸”过从甚密。缘起于此,朱熹抨击“近幸”迷惑孝宗,并将“近幸”与“功利之卑说”牢牢挂钩。不幸的是,辛弃疾身上同时贴有“主战派”与“近幸”两重标签。辛弃疾“主战派”的标签毋须多论,从稼轩词中频频出现的“功名”“金印大如斗”字眼,就足见其“功利”之心。需要强调的是辛弃疾还有一重很少被人提及的“近幸”身份。张端义《贵耳集》中罗列了诸多孝宗朝的“幸臣”,说他们“读书作文,不减儒生,应制燕闲,未可轻视”,而其中所举“北人”代表即为辛弃疾。[18]以辛弃疾的一贯做派及其与虞允文、叶衡的关系来看,辛弃疾被称为“幸臣”当不是空穴来风。朱熹及理学士人与“主战派”及“近幸”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而辛弃疾却同时具备此双重标签。辛朱关系紧张在所难免。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辛朱之间的巨大分歧,南岩之会后二人关系并未立刻改善,其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相互试探时期。直到绍熙三年(1192)辛弃疾仕闽,两人的关系才进入“蜜月期”。
二、辛朱南岩之会及辛朱关系的改善
淳熙九年(1182)九月中旬,朱熹弃官南归,途经信州,是促成南岩之会的直接动因。朱熹弃官南归,缘于他与当朝宰相王淮关系的彻底破裂。这层背景对了解南岩之会时辛朱的微妙关系极为关键。略引《宋史》四百二十九《朱熹传》加以说明:
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神祠。[17]12756
再看《宋史》卷三九六《王淮传》的记载:
初,朱熹为浙东提举,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陈贾为监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衣诏痛革之。”郑丙为吏部尚书,相与协力攻道学,熹由此得祠。其后庆元伪学之禁始于此。[19]
唐仲友案牵连甚广,朱熹先后六上弹章,并最终惊动孝宗,闹得沸沸扬扬。事件很快就由个体发酵为以王淮为首的官僚型士大夫与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型士大夫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垒。朱熹弹劾唐仲友案是南宋理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后,以王淮为首的官僚型士大夫对“道学”展开全面打压,并最终酿成“庆元党禁”之祸。
朱熹与王淮的关系颇为复杂。但从党争的角度来分析,又非常明朗。事实上,他们的关系牵涉到南宋朝廷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职业型官僚与理学型士大夫集团之间的党争。政治党派之间往往因集团利益而分分合合,变幻莫测。一年前职业型官僚与理学型士大夫联手逼退“主战派”,但当“和战”问题不再是朝廷关注的焦点后,新的矛盾又产生,昔日暂且苟合的两派很快又走向对立。朱熹本来是王淮提拔起来的理学士大夫,然而两者之间终究是貌合神离。最后,朱熹以唐仲友贪污不法案为切入口,六上弹章,希冀以此扳倒唐仲友及其背后势力王淮。其时孝宗更信任王淮,朱熹不得已,惟有辞官回乡。[5]357-373
经由唐仲友案,在朝理学势力受到削弱。同时,此案也引起了王淮党的警惕,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排挤理学士人。两派势力此消彼长。在此情况下,朱熹自罢任开始广泛联络、结交理学士人及同盟,以凝聚力量。其弃官前后,先与浙东理学人士聚会,后途经信州玉山,又与理学士人徐文卿、段钧、赵成父等相聚并游南山。
朱熹此行至上饶拜访韩元吉,也是有目的的。韩元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理学士人,他既与理学家友善,又与“主战派”相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南涧甲乙稿提要》载:
元吉本文献世家,据其跋尹焞手迹,自称门人,则距程子仅再传。又与朱子最善,尝举以自代,其状今载集中。故其学问渊源,颇为醇正。其他以诗文倡和者,如叶梦得、张浚、曾几、曾丰、陈岩肖、龚颐正、章甫、陈亮、陆游、赵蕃诸人,皆当代胜流。故文章矩矱,亦具有师承。其婿吕祖谦,为世名儒。其子名淲,字仲止者,亦清苦自持,以诗名于宋季,盖有由矣。《朱子语类》云:“无咎诗做著者,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诚定评也。[20]
韩元吉既以“二程”弟子理学家尹焞门人自居,又与叶梦得、张浚、陆游等“主战派”颇多交往。退居上饶后,韩元吉与辛弃疾频繁唱和,以“恢复”为号召,相互激励。他不仅与朱熹“最善”,且与稼轩亲密。朱熹这次拜访韩元吉的原由有二:
一是访友。韩氏家族历来与理学士人甚为相得。韩元吉之四世祖韩维与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及邵雍皆有交往,尤与程氏兄弟颇相友善。至韩元吉,又与“朱子最善”。韩元吉曾力荐朱熹入朝为官。二人学问又同出“二程”,故而韩元吉是朱熹政治上最可靠的盟友之一。
二是慰问。韩元吉是理学家吕祖谦的岳父。韩元吉曾先后将两位女儿嫁与吕祖谦。而朱熹与吕祖谦为莫逆之交。朱熹曾遣送其子朱塾至吕祖谦处受学,可见二人情谊之笃。一年前(1181),吕祖谦因病去世,朱熹为作祭文,极尽悲悼。本年正月,朱熹在浙东任提举,巡历至武义县,又特地前往明招山吕祖谦墓祭奠。九月十二日朱熹去任前,又与吕祖谦之弟吕祖俭等浙东理学士人聚会于衢州常山,并应吕祖俭之请为吕祖谦《吕氏家族读诗记》作序。[21]747-750吕祖谦英年早逝,韩元吉当悲痛之极,因而朱熹借路经上饶之机,对其示以慰问。
韩元吉接待朱熹,邀请了徐衡仲来作陪。南岩之会中,徐衡仲本是次要角色,但对探究辛朱二人相会时的微妙关系至关重要。徐衡仲是上饶有名的孝子,其行为品格与理学家之主张颇相一致,理学大师张栻曾为其作《一乐堂纪》,盛赞其孝行善德。[22]841-843更重要的是,他与吕祖谦同为隆兴元年进士,两人为旧识。作为理学士人的徐仲衡,同与理学宗师朱熹相见,之间不会存在隔阂与不便。因而,韩元吉请其作陪极为妥帖应景。
在官场打磨多年,韩元吉比较清楚辛朱之间的政治立场及微妙关系,加之当时政坛浓厚的“反道学”气氛,此次朱熹到访并未直接邀请辛弃疾。但较辛朱年长的韩元吉,游走于“主战派”与理学士人之间,无疑是弥合辛朱二人嫌隙的最佳“凝和剂”。辛弃疾与韩元吉所居城南隔河相望,很快得知了南岩聚会的消息,并抓住这次机会。
在自身“主战”和“退闲”两重身份意识下,极具军事头脑的辛弃疾采取了非常有策略性的方法:在朱熹将要离开上饶之际,才“载酒具殽膳”“倏然”而至。这样做,既表明身份和立场,避免了尴尬,还释放了善意。表明身份和立场,是因为朱熹归途访友,带有讲学布道,凝聚理学士人性质。辛弃疾此时并不认同朱熹的政治立场与学术理念。他在整个带湖时期与韩元吉及各类官员的唱和仍一直以“恢复”为念。他不全程参与朱熹、韩元吉、徐衡仲的理学性会谈,就避免了两人在性理方面没有太多“共同语言”的尴尬。同时,辛弃疾在聚会收尾阶段载酒具美食而来,巧妙地向朱熹表明了冰释前嫌的友好之情。
辛弃疾的策略是成功的。虽然此次会面,礼节性的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但两人的首次私下会面,不仅仅是在融洽的氛围中圆满收场。对辛弃疾来说,南岩之会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南岩之会是辛朱二人在私人层面定交的第一站,成为他们关系改善的起点。南岩之会后辛朱二人虽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再次会面,但出现了相互靠拢的苗头。淳熙十五年(1188)秋、冬间[23],朱熹得知门人杜叔高欲造访辛弃疾,便向其交待:
辛丈相会,想极款曲。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见闻,岂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为嫌,亦必不以贤者之言为忤也。[24]
此处 “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有认可又颇多惋惜,当指辛弃疾之前于理学不甚留意,缺少纯正的理学修养,才授人以“奸贪凶暴”之口实,而横遭非议。“彼中见闻,岂不有小未安者?”难以确指何事,然可能引起两人误会之事不外乎两件: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上旬,朱熹潜入辛弃疾带湖新居,十二月辛弃疾便被弹劾之事;淳熙八年(1181)春,朱熹扣压辛弃疾牛皮一事。无论何事,朱熹都欲借杜叔高“具以告之”,以消除误会。由这段颇为客气的话语,不难推知:南岩之会后的七年时间里,辛朱二人的感情依然生分;朱熹通过门人杜叔高向辛弃疾释放善意,除推许辛弃疾外,欲借机劝说其用心理学,颇有引为同道之意。细微处仍可看出,相较于南岩之会前的生疏态度,朱熹对辛弃疾有了正面肯定和友善劝勉的意味。
绍熙二年(1191)冬,辛弃疾被起复为福建提点刑狱。淳熙三年(1192)春赴任前,先驰函问候朱熹,表达拜访之意。朱熹走札奉复并贺喜道:
光奉宸纶,起持宪节。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詟之威;今圣上选贤,更作全安之计。先声攸暨,庆誉交兴。伏惟某官,卓荦奇材,疏通远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轺车每出,必著能名;制阃一临,便收显绩。兹久真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思。当季康患盗之时,岂张敞处闲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权。歌《皇华之诗》,既谕示君臣之好;称直指之使,想潜消郡国之奸。第恐赐环,不容暖席。熹苟安祠禄,获托部封。属闻斧绣之来,尝致鼎裀之问。尚烦缛礼,过委骈缄。虽双南金,恐未酬于郑重;况一本薤,亦奚助于高明?但晤对之有期,为感欣而无已。[25]
若将这封书信与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落职时的制辞对读,可见朱熹对辛弃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詟之威;今圣上选贤,更作全安之计。”朱熹站在全局的立场,肯定了孝宗因事贬罚辛弃疾和宁宗选贤任能、不计前嫌的作法。接下来称赞辛弃疾的忠勇、智略、才能和影响力,表达朝廷所寄托的厚望。一如谢枋得所言“公有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所学皆圣贤之事。朱文公所敬爱,每以‘股肱王室,经纶天下’奇之。”[26]朱熹的回信对辛弃疾的过往做出了完全正面的评价。结尾一句“晤对之有期,为感欣而无已”,不但欣然答应了辛弃疾相约见面之事,还对辛弃疾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可以说,辛弃疾作为部使者,先致函问候请祠居家的朱熹,这份礼节和情意所展现出的大度,得到了朱熹的热情回应。可惜辛弃疾的信没流传下来。
从淳熙九年(1182)南岩之会到绍熙三年(1192)的十年间,辛弃疾闲居带湖,朱熹在仕途上亦几经浮沉,两人联系不多,为何朱熹对辛弃疾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除了南岩之会后两人对彼此有了更多关注和了解之外,还因光宗即位后,理学士人在宰相赵汝愚的支持下开始实施孝宗晚年的政治理想,朱熹内心的“外王”力量超过了“内圣”。[27]533-619相同的政治目标促使两人有了更多的认同和交流。
三、 南岩之会后辛弃疾诗词创作中的理学渗透
南岩之会后,辛朱关系的缓和为辛弃疾主动向理学群体靠拢、深入接受理学思想打开了新局面,理学也逐渐渗透进辛弃疾后期的诗词创作中。这种渗透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辛弃疾与理学士人往来唱和的诗词增多。
辛朱关系在南岩之会后得以缓和、升温,并在辛弃疾仕闽后进入“快车道”,二人开始频繁往来应和。绍熙三年(1192)二月,辛弃疾赴福建提刑任,并前往建阳拜访朱熹,两人自此开始频繁交往,关系也逐渐升温。朱熹《与刘晦伯书》中亦说“今年缘与宪车相欵”[28]。庚申春,两人一起游赏武夷山,辛弃疾以诗《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应和朱熹《武夷棹歌十首》,赞其是人间“擎天柱”和“帝王师”;[29]63-75朱熹生日时,辛弃疾还特地为之庆寿,夸赞其“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二三人”,给予朱熹极高评价;[29]78同时,辛弃疾多次就政治、理学向朱熹请教商讨。[30]3180辛弃疾仕闽后的经界、钞盐、办学等措施多受朱熹影响。朱熹则对辛弃疾多有称道,称其为“人才”“帅材”[30]3179,积极劝勉,并据辛弃疾的性格行事风格,笔赠“克己复礼”“夙兴夜寐”两斋名。[31]12165辛弃疾晚年还特意书此斋名自勉。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得知消息后,辛弃疾悲伤感慨“白发多时故人少”[32]。辛弃疾高度评价朱熹“所不朽者,垂名万世。孰谓公死,凛凛犹生”[33],称其功业如“江河流日夜”[22]841,将名垂青史,并不顾“伪学禁方严”的严酷形势,“为文往哭之”[31]12165。辛朱二人的关系,由形同陌路发展至相知不渝的情谊,其转折点即为南岩之会。
南岩之会后,辛弃疾开始与周边的理学士人频繁往来唱和。辛弃疾与理学士人的融合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带湖初期,辛弃疾与理学士人还刻意保持着距离。辛朱会面后不久,南岩之会的参与者徐衡仲曾惠琴于辛弃疾,却被他很客气地拒绝。辛弃疾为什么不接受徐衡仲惠琴?当与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有关。琴对古代士人,并不简单是一件纯粹的娱乐工具,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道德化象征良器。《风俗通义》曰 :“故琴之为言禁也,雅之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声动感正意,故善心胜,邪恶禁。是以古之圣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适,故近之闲居,则为从容以致思焉。”[34]293将琴视为君子的象征。辛弃疾在《鹧鸪天·徐衡仲惠琴不受》中谈到却琴的理由时说:“不如却付骚人手,留和《南风》解愠诗”[22]294。《南风》是什么样的诗歌?《风俗通义校注》引皮锡瑞疏证曰:“《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扬雄《琴清音》:‘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化’”。[34]294可见,《南风》透露着贤人心系万民,期待天下大治的儒家情怀。伯牙鼓琴的故事人所共知,因而士大夫之间的赠琴被赋予了觅求知音的特别含义。辛弃疾当是看出了徐衡仲欲以理学思想对其施以影响的意味。与理学士大夫在行为观念上的巨大分歧,使辛弃疾很难与理学士人在短时期内快速消弭嫌隙。徐衡仲身处理学士大夫阵营,辛弃疾以却琴的行为表明其对理学的暂不认同。
与带湖时期拒绝接受徐衡仲赠琴形成显明对比的是,瓢泉时期辛弃疾愉快地接受理学士人赵国兴的赠琴。在《和赵国兴知录赠琴》中稼轩写道:“劝君往和薰风弦,明光珮玉声璆然。此时高山与流水,应有钟期知妙旨。”[29]153对赵国兴甚相推许并引为知己。瓢泉时期,辛弃疾同赵国兴和词多首,并常将其与傅岩叟、叶仲洽并提,此三人皆为理学气息浓厚的士大夫。
朱熹作为当时的理学宗师,他的举动对理学士人具有导向作用。淳熙十三年(1186),赵蕃受学于朱熹。[21]856两年后,赵蕃归上饶,即以《以归来后与斯远唱酬诗卷寄辛卿》诗送辛弃疾。徐斯远也是朱熹门人,赵蕃将与徐斯远唱和诗寄辛弃疾,颇有引为同道的意味。由此可见,朱熹在辛弃疾与信州理学士人圈交往过程中的纽带作用。当然,辛弃疾与理学士人真正全面接触要到仕闽之后。随着与朱熹交往增多,其思想与行为开始快速向理学靠拢。辛弃疾仕闽期间,听闻朱熹门人陈骏之子陈成父颇有才名,不仅“罗致宾幕”,还把女儿嫁给了他。[35]在辛弃疾仕闽及再次落职退隐瓢泉时期,理学士大夫俨然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游对象。这一直持续到辛弃疾晚年、其与陈亮、杜斿兄弟,吴绍古等理学友人的唱和表现出极高的文学价值。
二是,理学思想开始渗透于辛弃疾诗词之中。
稼轩诗词中的理学思想并非都与朱熹有关,但南岩之会后,辛弃疾与朱熹及理学士人的关系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其诗词中理学思想的渗透。辛弃疾毕生志在“恢复”,认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22]829,因此其早年诗词多与抗金北伐及追求功名有关。理学家以穷理尽性为首务的思想特点与辛弃疾早期的追求格格不入。在辛弃疾留存不多的诗文中,写于南岩之会前的仅有一篇《祭吕东莱先生文》(1181)与理学有关,还是缘于其与吕祖谦之间的特殊关系。
南岩之会后,辛弃疾诗词开始濡染理学风习。总体说来,稼轩诗中理学思想的意味远比词明显。寓居带湖之初,辛弃疾作《有以来请者,效康节体作诗以答之》,开始模仿“康节体”写诗,之后稼轩反复强调“作诗犹爱邵尧夫”[29]94,“饭饱且寻三益友:渊明、康节、乐天诗”[29]101,“学作尧夫自在诗”[29]109,表达对邵雍诗的喜爱。辛弃疾对邵雍的青睐,一方面缘于邵雍恬淡自守的独特风格深契于稼轩退居之后的心境与现实,一方面又缘于南岩之会后,辛弃疾对理学家态度的转变。另如“西园曾到不?要学仲舒能”[29]62,“屏去佛经与道书,只将《语》《孟》味真腴”[29]116,“我识箪瓢真乐处,《诗》《书》执《礼》《易》《春秋》”[29]206,都透露着浓厚的理学意蕴。
理学思想融入稼轩词主要表现为直接表露和间接渗入两方面。
直接表露。理学思想融入稼轩词主要表现为直接表露和间接渗入两方面。直接表露。最明显的如《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
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 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粲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22]767
上片开篇用《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明确自己不被用时选择归隐的意志。第二、三句反用《论语·子路》中樊须专心学稼的典故,以“小人请学樊须稼”坚定自己甘愿做普通百姓,专心稼穑,享受简单生活的立场。下片辛弃疾以孔子自指,诉说自己命途多舛的奔波人生。结尾引《论语·微子》《论语·宪问》的典故,表达自己选择归隐的无奈和愤懑。全词使用10处“经学”语典 、5处《论语》典故抒写自己的不平之气,理趣十足。又如《水调歌头·题吴子似县尉瑱山经德堂。堂,陆象山所题名也》:
唤起子陆子,经德问何如。万钟于我何有,不负古人书。闻道千章松桂,剩有四时柯叶,霜雪岁寒馀。此是瑱山境,还似象山无。 耕也馁,学也禄,孔之徒。青衫毕竟升斗,此意正关渠。天地清宁高下,日月东西寒暑,何用著工夫。两字君勿惜,借我榜吾庐。[32]
这是一首完整的“说理”词,词的上片写经德堂,开头用《孟子》中的两个语典点出“经德”涵意,强调高于物质利益的风节操守和吴子似与陆象山的渊源;下片写“经德”对吴子似的意义,使用《论语》、《孟子》、《老子》中的典故,明确功名利禄不如修养自身、追求自我人格完善。通篇谈“经德”,其理学修养,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辛弃疾还时时以理学语入词,如“学窥圣处文章古”[22]1161“最好五十学《易》,三百篇《诗》,男儿事业看一日,须有致君时”[22]1600“君诗好处,似邹鲁儒家”[22]1648等。
间接渗入,即通过与理学士人的接触,由人及词,影响到其创作风格。辛弃疾词与理学关联最多的,是与吴子似、赵蕃、韩淲、徐安国、杜斿等理学士人在瓢泉的唱和。这个时期,理学被斥为“伪学”,惨遭禁锢,理学士人多为在野隐居状态。再加上理学士人普遍注重风节操守,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辛弃疾日夕与之交游酬唱,受其濡染,词中便不时流露出退隐自全、安贫乐道的出世倾向。这成为其后期词与前期慷慨纵横之作明显不同的底色。除了大量与理学士人酬唱之作外,瓢泉时期稼轩还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咏梅花词,梅花高洁自赏的品格与理学士人的人格追求正相契合。同时,稼轩不慕权势而重风节的儿女婚嫁选择,也用行动表明了其内心对理学士人的认可。理学思想的间接渗入,无疑丰富了辛弃疾的生命底蕴,成为辛弃疾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辛弃疾与朱熹的关系经历了由带湖之前的冷淡疏离,到带湖时期的相互试探,再到带湖之后的相互赏识三个不同阶段。其中,南岩之会时两人的关系最为微妙。辛弃疾巧妙得体的举措,使南岩之会成为辛朱关系由差向好的转折点。由此,辛弃疾与理学士人的关系也大为改观。这为辛弃疾后期创作中的理学渗透提供了养料。
绍熙五年(1194),辛弃疾再被谏官论列,理由之一是“交结时相(赵汝愚)”[36]。同年,中书舍人兼侍讲陈傅良又以“芘护辛弃疾,依托朱熹”[37]遭参劾。赵汝愚任宰执时曾全力汲引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士人以自助,陈傅良本身就是理学士人,辛弃疾俨然以理学党人的身份被再次罢免。至于“庆元党禁”中辛弃疾未被列入“伪学逆党”名单,原因在党禁本质属于政治权力斗争,“官僚集团关心的重点始终都在‘权’的得失而不在‘学’的正误”[27]671,党禁“仅限于仕途上的罢黜,并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进行什么清算”[38]。总之,辛弃疾早期因“奸贪凶暴”被理学士人贬斥,近晚年却被归入理学党人,这种明显的反差与理学宗师朱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这种变化的关键节点正是需要被重新认识的辛朱“南岩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