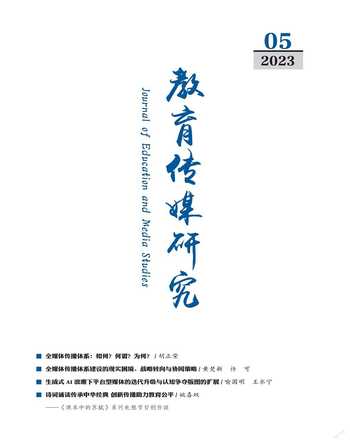算法素养研究综述:定义、研究视角与教育实践
任贝佳?何苑
【内容摘要】算法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其诱发的诸多风险挑战也引起各界担忧。“算法素养”概念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旨在促进用户捍卫自身自主选择权,抵御算法的负面影响。本文对“算法素养”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就未来的算法素养教育实践提出建议。
【关键词】算法素养;算法知识;算法意识;数字鸿沟;内容生产
当前算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人们几乎每天都会使用算法平台,接触经算法筛选、过滤后的信息,并可能不加怀疑地接受,而基于算法的内容自动生成技术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2022 年11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发布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它不仅能通过对话的方式解答诸如“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洲”等较为常规的问题,甚至能以及格分数通过大学考试。①这一技术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同时,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如虚假信息、虚假新闻等)也引发人们担忧。②毋庸置疑,如今算法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工具,而是成为改变并形塑社会文化,影响个体认知与行为的一项人类生活基础设施。③对于算法引起的诸多问题,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这些研究当中,一些学者从用户的主体能动性出发,提出“算法素养”(Algorithm literacy)概念,并认为其可能成为促使用户捍卫自身的自主选择权、抵御算法负面影响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围绕“算法素养”展开的研究日益丰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算法素养”定义。同时,由于算法应用场景等的多样性,以及語境、文化等的差异性,学者研究的问题类型不尽相同,出现了许多研究视角。因此,本文旨在归纳分析现有的与“算法素养”相关的定义及研究,并在当前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为实现这一目的,作者进行了中英文文献的检索收集:中文文献通过在中国知网的主题栏搜索“算法素养”“算法知识”及“算法意识”3个关键词筛选得到,英文文献通过在Google Scholar搜索“Algorithm(ic) literacy”“Algorithmic knowledge”“Algorithm awareness”3个关键词搜集而来,作者在此基础上按照研究目的对文献进行了筛选。本文将首先分析算法素养研究的重要性,在对算法素养进行定义后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最后针对“如何提升算法素养教育”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算法技术的积极应用及社会面临的挑战
算法是为解决特定问题及任务(如数据处理、自动推理等)而被定义的一套指令,通常由计算机程序执行。从电子邮件的发送到GPS定位技术都需要通过算法实现。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算法普遍渗透到消费、医疗、教育、传媒等领域。如推荐算法在电商平台的应用,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对结果的排名,Facebook、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的“热点趋势”等。对于互联网用户而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信息过载危机,算法机制对信息的整合、筛选,让用户能够更高效地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对于平台而言,算法能够分析数量庞大的用户数据,匹配用户与信息,提高用户黏度,从而实现其盈利目标。如新闻资讯平台今日头条能将百亿信息与上亿用户进行匹配。④
算法的发展提升了各行业的工作效率,并带来全新的机遇。然而,算法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其诱发的诸多风险挑战也引起各界担忧。首先,算法模型存在局限性。虽然算法在运算能力等方面显著超越人类,但算法模型训练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存在局限,而这将带来不良后果。如当用于机器学习环节的数据库缺乏代表性及多样性时,最终由人工智能机器人输出的结果也会存在偏差,如价值观偏向。Hartmann等人在对ChatGPT的政治言论进行研究后发现其存在一定的政治偏向。⑤其次,算法技术“向善”与否,与使用者的意图息息相关。如微软公司于2016年发布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Tay”在与社交媒体用户互动的几小时内,逐渐习得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类型的偏激言论。⑥除审核机制设计存在缺陷外,这也与部分用户有意为之有关。当前算法的所有权主要被科技公司掌控,其所追逐的商业利益常常与公共利益相冲突。在科技公司的操纵下,算法机制可能会变得更加不透明,这将导致用户逐渐失去决策自主权。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数字劳工现象便深刻反映了这一问题。⑦在这些显性问题之下,体现在用户认知及行为方面的隐性问题同样令人担忧。如有研究者认为算法会导致“过滤泡”问题,在潜移默化中用户的视野将变得更加狭窄,不同群体间的偏见及不理解将得到深化。⑧算法不仅影响着普通用户,新闻生产中算法技术的应用也引发了新闻从业者对于职业伦理的反思。⑨
随着对算法的批判性关注日益增多,学界开始反思如何应对算法带来的负面影响。除行业自律、国家监管等措施外,一些学者从用户主体能动性视角出发提出“算法素养”概念。算法对用户造成的显著影响之一,是用户独立、自主选择能力遭到威胁,而与“赋权”(empowerment)理念紧密关联的“素养”概念,⑩可能成为促使用户捍卫自身的自主选择权的关键因素。因此,下文将进一步探讨算法素养的概念演进、内涵及问题。
二、从媒介素养到算法素养:概念演进与研究视角升维
素养研究起源于印刷媒介时代,可以被定义为阅读与书写的能力。当时的精英文化群体旨在通过提升大众的素养以促进经济进步与社会平等。随着西方学界“新素养研究”(The New Literacy Studies,NLS)的发展,素养概念逐渐褪去技术决定论的色彩,而是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象征着不同群体的惯例、规范及价值观等。在该视角下,社会机构被认为应通过不同类型、层级的素养教育,实现特定的教育功能。
随着技术载体和媒介环境的不断变化,素养(Literacy)概念的内涵不断延伸。视听媒介问世后,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媒介素养研究。与素养研究相同,媒介素养研究也经历了范式变迁。20世纪初的媒介素养研究认为大众媒介文化是低俗的、使人堕落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发挥保护民众的作用,提升受众对媒介负面影响的免疫力。随着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不再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媒介素养应提升民众对媒介内容的辨别力。从该视角出发,Aufderheide对媒介素养进行了定义:媒介素养是获取、分析、评估、创造各种形式媒介信息的能力。
上述是对媒介素养的一种技能性取向定义。但媒介不仅是一项“技术”,它还具有文化和政治意涵。随着传播过程中交互性的增强,“受众”向“用户”转变,对媒介素养的研究也发展为结合个体所在的社会、文化及政治背景,进行“参与”和“批判”式的研究。如Hobbs将素养定义为“通过符号系统分享意义、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还有一些学者针对传播权力机构、媒介环境及媒介信息建构等开展批判性研究,认为媒介素养應培养人们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由上述分析可知,媒介素养主要包含媒介使用能力及批判性分析能力两大维度,其目的除培养用户更好地使用媒介信息、应对媒介负面影响外,还包括促进用户在媒介环境中对社会活动的参与。面对当前因算法参与而变得更加复杂的媒介环境,不同学者提出的算法素养概念既延续了上述内容,又包含新的维度。Dogruel结合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新媒介素养(New media literacy)及隐私素养(Privacy literacy)定义,提出算法素养应包含“算法意识与算法知识”“批判性评估”“应对行为”“创作设计”4个维度。该定义发展了Aufderheide提出的媒介素养定义,两者的区别之处在于:Dogruel的定义包含了用户对算法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用户对算法的感知能力(如算法定义、算法工作机制等)。在算法时代来临前,我们在媒介使用过程中逐渐忘记媒介物的存在,媒介仿佛成为我们“身体的延伸”,而算法在诞生之初便是“隐形”的。因此,许多学者在算法广泛渗透各类平台之际,都选择调查、测量用户对于算法的感知程度,以及这种感知如何进一步影响用户与算法间的互动。除此之外,算法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也启发了学者对算法素养的定义,如Shin等人认为算法意识,即用户对算法的感知,应包含“公平性感知”“可解释性感知”“负责任性感知”“透明性感知”。除与用户认知相关的维度外,算法素养也应包含用户行为素养。加拿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CCUNESCO)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两者共同发布的“算法素养与数据项目”(Algorithm Literacy & Data Project)中指出,“该项目旨在为儿童‘赋权(empower),使其成为积极主动并具有创造力的使用者及制作者,而非仅仅是被动的消费者”。
结合上述定义,本文将算法素养定义为:获得算法意识、获取算法知识、批判性评估算法以及创作内容的能力。接下来,本文将结合这4个维度,对目前围绕算法素养展开的研究进行分析。
三、算法素养研究的不同视角和关注重点
算法素养旨在提升用户应对算法环境的能力。面对算法技术对用户的知识建构、身份的“标签化”建构以及对创作行为的规训等问题,现有算法素养研究从算法意识、算法知识、算法批判性思维及算法环境下的创作等视角出发展开研究。接下来,本文将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
(一)算法环境下的知识建构与数字鸿沟
在媒介素养的研究当中,学者已对不同阶层用户在媒介信息获取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及其造成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行了研究。当前算法成为“把关者”和“调控阀”,拥有决定信息“流向”甚至存亡与否的权力,但由于算法的隐秘性,缺乏算法意识及知识的人可能难以意识到算法对其所处拟态环境的塑造。用户间算法素养的不平等可能会对不同用户的信息获取方式及其对现实世界的感知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使用户之间出现“算法数字鸿沟”。
已有研究发现,在算法环境中,由于社会资源的分层,处于更高阶层的用户在获取与算法相关的信息时往往仍然更具优势。在陈逸君和崔迪对我国视频类、新闻类与购物类应用用户算法使用的线上调查,以及Cotter和Reisdorf对美国搜索引擎用户进行的在线调查中,均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用户间的算法知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处于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用户掌握更多的算法知识。虽然以往研究发现人们的技术使用经验能够增进其对该技术的理解,并且在对算法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但上述研究显示,算法使用频率并不一定能抵消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影响。
随着算法对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决策的影响日益增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用户间的“算法数字鸿沟”可能会进一步加深。由于个性化推荐算法使得不同内容拥有不同级别的可见度,内容创作者需要采取策略以增强内容的可见性,在此过程中,拥有更多算法知识的人会在可见性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Klawitter和Hargittai在对25位美国独立艺术品销售者进行访谈后发现,一些销售者会利用算法机制增强其商品在社交平台及搜索引擎结果中的可见性。因此,掌握更多算法知识的人可能会拥有更多营销展示的策略,从而收获更高的经济收益。在其他学者对Instagram中“网络红人”(influencer)的调查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用户间的差异是否会在可见性的竞争中得到进一步加深还有待研究。
(二)算法环境下的身份建构与用户意识
当算法成为当代社会的一项网络基础设施,用户长期生活在由算法打造的个性化信息世界中,不但可能会失去与多元化信息的交流,还可能会依赖算法对其身份的“标签化”建构,而逐渐失去构建个人身份的自主权。当用户具备反思算法背后的权力结构及算法如何塑造我们生活的能力时,才能实现用户对算法的主动批判与监督,进而采取行动改变现状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从用户意识到算法的存在以及正确认识算法的功能是培养其批判性算法素养的前提条件。学者对Facebook的内容推送服务News Feed的用户进行调查后发现,当用户没有意识到算法存在时,可能会将由算法导致的决策结果错误地归因于自己的朋友或家人,认为是他人故意不对其展示自己的文章。而了解News Feed算法功能的被调查者则会推测是“算法偏好设置”“用户可见设置”功能在发挥作用。因此,算法知识能够帮助用户更加正确地使用与评价算法。
当用户具备基本的算法知识后,就有可能发展出批判性算法意识,并进一步反思算法与自我的关系,从而摆脱算法对自己身份的建构。Cotter在对Instagram中的网络红人及在YouTube发布内容的内容创作者群体“BreadTuber”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虽然这些创作者在追逐可见性,但同时也在对“算法想要什么”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一批判性意识使得内容创作者发展出自己的内容品牌策略,并减轻了自我异化的程度。陈阳和吕行对河南农村青少年群体进行调查后发现,算法素养能够促进青少年的“算法抵抗”行为,发挥自身能动性,使算法系统更加满足自己的偏好。
有研究者提出用户与算法的“互构”可能,即算法规则在“结构化”用户的同时,用户也在通过实践重塑算法逻辑。因此,提升用户算法素养,不但会使用户摆脱算法对自身的建构,也可能使得算法系统的运行逻辑更加符合公共利益。
(三)算法环境下的智能创作与技术规训
当前算法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工具,而是作为一种“技术文化实体”深度参与到社会建构中,网络平台所有者对平台规则进行编码并通过算法执行后,形成了新的文化生产规则。值得警惕的是,算法“并非纯然中立的客观物”,如推荐算法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量至上和商业利益优先的算法价值观”。在该价值观的引导下,用户满意度、内容影响力等被转化为数据指标,并由算法对其进行排名,内容生产者能够通过该排名预测受众的需求,进而进行内容创作。于是,数据与流量规则的控制削弱了文化多样性,算法让人们直接看到什么是热门的,但人们对规则背后的论证却无从得知,文化的语境感被消除,剩下的则是“对各种数据指标和量化方式的痴迷”。
内容创作者对于算法有着不同的使用立场。如有的创作者会选择遵从算法规则获得可见性。Cotter在对Instagram中的内容创作者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用户了解平台的算法规则,并通过学习平台规则发展自己的策略,并且他们的行为始终不曾威胁平台规则。一些创作者完全被算法支配,只关注如何制造让观众上瘾的内容,如一些平台上,自媒体为吸引用户点击,催生了“标题党”式的资讯内容,夸张表达与偏激陈述成为人们创作内容的惯用手法,信息的真实性、健康性、有效性被削弱。而一些创作者在创作高雅内容的同时却又忽视了算法规则,没能兼顾人文性与算法机制的协作。在Aufderheide提出的媒介素养定义以及本文在其基础上提出的算法素养的定义中,“创作内容的能力”均为最后一个维度,这暗示着用户在使用媒介进行创作前,需要首先掌握前3个维度的能力。创作者在了解算法如何运作或平台规则的基础上,还需要具备批判性评估算法的能力,认识到算法对自己知识及身份的双重建构以及算法技术对创作行为的规训。未来研究可探索如何通过算法素养教育,使内容生产与算法形成良性协作。
四、如何提升算法素养教育
提升算法素养教育需要用戶、平台、政策机构三方的共同努力及协调配合。在这三者组成的动态系统中,用户与平台算法间的互动最为频繁、直接。面对算法规则对自身的“结构化”,用户的实践也能够反向重塑算法逻辑。因此,算法素养不仅能帮助用户抵御算法风险,还能够以间接的方式影响平台算法的运行。由此,在分析“如何提升算法素养教育”这一问题时,需要对用户、平台、算法素养这3个相互关联的因素进行分析。
首先,从用户角度来看,用户间的差异性是算法素养教育面临的一项挑战。在用户的年龄方面,青少年、老年人相对而言是算法使用的弱势群体。例如在算法的“推波助澜”下,一些明星、网红发表的低俗言论可能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造成负面影响,因而需要侧重培养其算法意识及批判性思维能力。而许多老年人对新媒介的使用并不熟练,应侧重提升其算法意识与算法知识。未来的算法素养研究也应关注这两类人群。在用户的职业方面,上文主要提及的是普通用户和内容创作者,而其他与算法关联性强的职业(如新闻从业者、数字劳工)的算法素养教育也应得到重视。譬如,新闻生产行业中算法技术的使用已是大势所趋,其在增强新闻工作者能力的同时,也威胁了其原有的新闻价值观念。而ChatGPT的出现也使学者担忧其可能会使虚假新闻的生成和传播变得更加容易。因此,未来可考虑算法素养与职业伦理的协同教育,使其在算法技术规训的背景下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念。此外,由上文提及的数字鸿沟现象可知,应加强对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阶层的算法素养教育,弥补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算法素养差异。除了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算法素养教育,我们还应看重用户在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算法知识。此外,用户间、不同的社群间会分享算法知识,因此在教育机构、政策引导之外,也应促进用户间的自主分享与相互提升。
其次,从平台角度来看,不同平台的算法设计及其主要承载的媒介形态不同。例如新闻资讯平台与电商平台均使用推荐算法,但其所处的生态、应用的场景及针对的目标均不同,因此,算法素养教育应针对不同算法平台的风险问题作出细化。另外,对平台算法引发的风险、伦理问题的思考能补充算法素养的内涵,而通过算法素养研究,也能促进对何为负责任的、符合公共利益的平台的思考,以推动平台算法设计朝有利于用户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方向发展。
最后,算法素养中的4个维度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关系,在算法素养教育当中也应注意协同培养。
五、结语
算法技术发展下机遇与风险并存,其使学界开始思考算法素养“赋权”用户的可能性。本文延续素养研究脉络,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算法素养定义为:获得算法意识、获取算法知识、批判性评估算法以及创作内容的能力。本文从这4个维度出发,结合当前用户面临的算法风险,将现有研究归纳为3类视角,分别为“算法环境下的知识建构与数字鸿沟”“算法环境下的身份建构与用户意识”“算法环境下的智能创作与技术规训”。分析发现,以往由于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导致的数字鸿沟问题同样体现在了当下的算法环境中(如可见性竞争),不同阶层的算法素养差异可能会加深数字鸿沟;算法在信息空间建构着用户的身份,增强批判性反思能力是发挥用户主观能动性、抵御算法建构的重要方式;算法作为一种“技术文化实体”生成新的文化生产规则,用户在遵守乃至过度迎合平台规则的过程中正面临着遭遇算法技术规训的危机。本文认为,提升用户算法素养不仅有益于用户的数字化生存,并且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平台算法运行,重塑算法逻辑。具体到实践上,提升算法素养教育需要用户、平台、政策机构三方的共同努力及协调配合。用户及平台间的差异还需未来研究及教育对算法素养进一步分析细化。最后,算法素养的4个维度相互关联,在教育实践中应注重协同培养。
参考文献:
①Kelly, S. M. ChatGPT passes exams from law and business schools, CNN Business,https://edition.cnn.com/2023/01/26/tech/chatgpt-passes-exams/index.html, January 26, 2023.
②Rachini, M. ChatGPT a‘landmark eventfor AI, but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future of human labour and disinformation?,CBC Radio,https://www.cbc.ca/radio/thecurrent/chatgpt-human-labour-and-fake-news-1.6686210, December 16, 2022.
③方师师:《算法:智能传播的技术文化演进与思想范式转型》,《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9期。
④白红义、李拓:《算法的“迷思”:基于新闻分发平台“今日头条”的元新闻话语研究》,《新闻大学》2019年第1期。
⑤Hartmann J., Schwenzow J. and Witte M.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conversational AI: Converging evidence on ChatGPTs pro-environmental, left-libertarian orientation ,”arXiv preprint arXiv:2301.01768, 2023.
⑥Rainie Lee, and Janna Anderson. “Code-dependent: Pros and cons of the algorithm age,” Pew Research Center, 2017, p2.
⑦洪馨仪:《平台经济下劳工算法素养不容忽视》,《青年记者》2022年第14期。
⑧Pariser E.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M]. penguin UK, 2011, P10.
⑨D?rr, K. N. and Hollnbuchner, K., “Ethical challenges of algorithmic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vol.5, no.4, 2017, pp.404-419.
⑩Livingstone, S.,“Media literacy and the challenge of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vol.7, no.1, pp.3-14.
Rowsell, J., and Pahl, K.,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iteracy studies[M], Routledge London, 2015, pp.35-36, p.37.
黃旦、郭丽华:《媒介教育教什么?——20世纪西方媒介素养理念的变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Aufderheide, Patricia. Media Literacy. A Report of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M], Aspen Institute, Communications and Society Program, 1755 Massachusetts Avenue, NW, Suite 501, Washington, DC 20036., 1993, pp.1-2.
Hobbs R. Digital and Media Literacy: A Plan of Action. A White Paper on the Digital and Media Literacy Recommendations of the Knight Commission on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in a Democracy[M]. Aspen Institute. 1 Dupont Circle NW Suite 700, Washington, DC 20036, 2010, pp.16-17.
Potter, W. J. Media literacy[M]. Sage Publications, 2018, p.54.
Dogruel, L., “What is algorithm literacy? A conceptualization and challenges regarding its empirical measurement,” Digital Communication Series 9, pp.67-93.
Eslami, M., Vaccaro, K., Karahalios, K., and Hamilton, K., “‘Be careful; things can be worse than they appear: Understanding Biased Algorithms and Users Behavior around Them in Rating Platform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 and social media, vol.11, no.1, 2017, pp.62-71.
Rader, E., and Gray, R.,“Understanding user beliefs about algorithmic curation in the Facebook news feed”,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15, pp.173-182.
Shin, D., Rasul, A., and Fotiadis, A., “Why am I seeing this? Deconstructing algorithm literacy through the lens of users”, Internet Research, vol.32, no.4, 2022, pp.1214-1234.
CCUNESCO, and UNESCO. The Algorithm & Data literacy Project, https://algorithmliteracy.org/, 2023.
何苑、张洪忠、苏世兰:《基于算法推动的文化传播“破圈”机制研究——以B站“法国音乐剧”的传播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陈逸君、崔迪:《用户的算法知识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视频类、新闻类和购物类算法应用的实证研究》,《新闻记者》2022年第9期。
Cotter, K., and Reisdorf, B. C., “Algorithmic knowledge gaps: A new horizon of (digital)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4, 2020, pp.745-765.
Blank, G., and Dutton, W. H., “Age and trust in the Internet: The centrality of experience and attitudes toward technology in Britain,”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vol.30, no.2, 2012, pp.135-151.
Klawitter, E., and Hargittai, E.,“‘Its like learning a whole other language:The role of algorithmic skills in the curation of creative good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2, 2018, pp.3490-3510.
Cotter, K., “Playing the visibility game: How digital influencers and algorithms negotiate influence on Instagram,” New Media & Society, vol.21, no.4, 2019,pp.895-913.
Dogruel, L., Masur, P., and Joeckel, 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lgorithm literacy scale for internet users,”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vol.16, no.2, 2022, pp.115-133.
Eslami, M., Rickman, A., Vaccaro, K., Aleyasen, A., Vuong, A., Karahalios, K., Hamilton, K., and Sandvig, C., “‘I always assumed that I wasnt really that close to [her]Reasoning about Invisible Algorithms in News Feeds,”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15, pp. 153-162.
Cotter, K., “Critical algorithmic literacy: Power, epistemology, and platform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2020, pp.41-43.
陈阳、吕行:《控制的辩证法:农村青少年的短视频平台推荐算法抵抗——基于“理性—非理性”双重中介路径的考察》,《新闻记者》2022年第7期。
Schwartz, S. A., and Mahnke, M. S.,“Facebook use as a communicative relation: Explo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Facebook users and the algorithmic news feed,”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vol.24, no.7, pp.1041-1056.
溫凤鸣、解学芳:《短视频推荐算法的运行逻辑与伦理隐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毛湛文、张世超:《论算法文化研究的三种向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朱鸿军、周逵:《伪中立性:资讯聚合平台把关机制与社会责任的考察》,《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王一楠:《智能媒体时代内容创作者对算法的使用立场研究》,《中国编辑》2021年第3期。
姚雅晴:《互联网时代青少年媒介素养提升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析——以粉丝群体为例》,《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5期。
Fubini A., “New powers, new responsibilities. A global survey of journalism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Problemi dellinformazione, vol.2, 2022, pp.297-301.
王超群:《智能媒体时代的高校传媒职业伦理教育改革研究》,《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2期。
喻国明、张剑峰、朱翔:《后真相时代:真相认同与社会共识的可能——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个体认知的类型与效用机制》,《教育传媒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