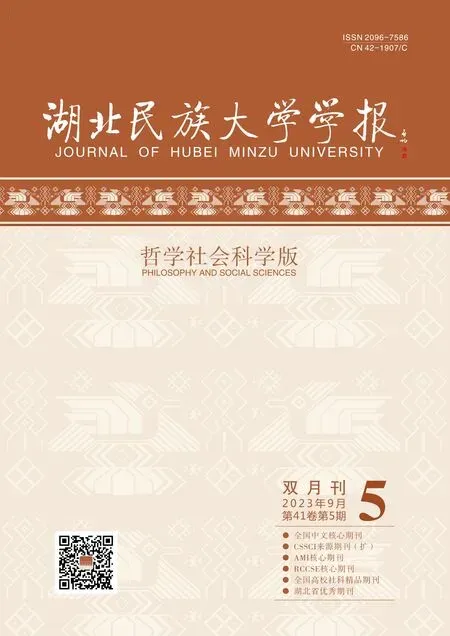“风景”的建构与“边疆”的国家认同
——从“灵溪十景”“颗砂八景”到“永顺八景”
李凌霞
一、“风景”的象征研究
明清以降,随着王朝国家统治的扩展,无论是政治地理空间上的边疆地区,还是在王朝权力尚未延伸到的内地“边疆”,其方志中涌现了大量以当地自然景观为名的“八景”(有时“十景”、有时“十二景”)及相关的诗词歌赋。从命名规则来看,“八景”一般由四个字构成景观名称,前两个字是地点,后两个字是美景,类似《诗经》的四言诗构造。“八景”并非自然而然的风景(landscape)(1)Landscape在国内可翻译为“地景”“风景”或者“景观”。,它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王朝国家对“边疆”的文化影响。
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当中,风景时常因为其“自然化”的特点而被忽略。(2)Eric Hirsch, “ Landscape: Between Place and Space,” In Eric Hirsch and Michael O.Hanlon(eds.),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30.邓肯(James S. Duncan)曾经提及风景是文化生产的结果,是意识形态的理想载体,并倡导从社会文化角度进行风景的解读。(3)James S. Duncan. The City as Text: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 in The Kandyan Kingdo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9-22.米歇尔(W.J. Thomas Mitchell)也强调风景是一种权力的文化实践,揭示风景如何消除各种权力关系的痕迹成为自然之景,显得尤为重要。他特别考察了欧洲帝国如何将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看似“自然而然”的风景之上,并重塑了一种新的风景秩序,作为民族与帝国的象征。(4)W.J. Thomas Mitchell. Landscape and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pp.1-4.
近年来学界已经涌现了较多关于“八景”的研究,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了边疆地区在国家化进程中移植、模仿内地“八景”文化的现象,指出“八景”的形塑,见证了王朝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和治理,也折射了地方精英的理想、审美和情感认同。(5)参见林开世:《风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纪宜兰的个案》,《台湾人类学刊》2003年第2期,第1-38页;周琼:《“八景”文化的起源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云南“八景”文化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06-115页;李渌:《书写“要荒”:“八景”所见明清贵州的开发与社会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68-176页。但是大多数研究讨论的是流官和外来的文人墨客对“八景”的塑造过程,并未涉及到土司的风景建构。
土司所建构的“八景”文化,模仿国家象征符号的同时,也具有某些逃离国家控制的特征。“国家化”和“逃离国家”是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Scott)在讨论赞米亚(Zomia)山地社会时所提供一种分析视角,“国家化”指建立在谷物农耕基础上的一系列标准化进程,包括政治上建立行政区划、给民众编排户籍,经济上集中人口、征收赋税,文化上进行语言等交流模式的统一;“逃离国家”作为“国家化”进程的副产品,建立在采集和游耕的基础之上,以远离国家的生存策略为主要特征,表现为政治领域上权威的分散和平等主义,人口以流动与分散来抵制国家的赋税征收,无文字重口传的文化传承方式等。(6)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17-421页。中国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中国西南山区普遍存在的土司群体,介于“国家化”区域和“逃离国家”的山民之间,处于与国家和土民同时进行博弈的状态中。(7)吴旭:《山地食物与土司化:以清代容美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91-94页。透过这些理论视角,可以更深入地揭示土司建构“八景”文化的政治意图和社会表征。
永顺位于湖南湘西北部的酉水流域,自五代十国以来便为彭氏土酋所辖。这里虽然不属于传统政治地理意义上的王朝国家边疆,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维持着王朝内部“边疆”的状态。对于想要与王朝国家保持距离的土司而言,难以进入的山区堡垒成为其“外逃国家”的重要依仗,山区中普遍流行的“刀耕火种”以及低产杂粮作物的种植使其进一步远离了国家控制,推崇巫术信仰、重视口传文化而非书写谱系使其能维系政治权威的自主性。在这样一个国家政权难以深入的空间中,土司“内控土民”基础建立在有限通达水路交通的控制、稀缺资源的垄断、祭祀仪式的诠释和尊卑有别的官僚体系之上。当地留下不少版本的方志,其中包括由永顺土司彭世麒仿照王朝体例主导编撰的《永顺宣慰司志》以及由永顺流官撰述的多个版本方志。这些志书先后记录了土司时代的“灵溪十景”“颗砂八景”和改土归流后的“永顺八景”及相关诗文。“八景”所描绘的景观不仅仅是一些风景秀丽的地点,还是空间上特殊的转换点。它们作为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出来的特殊空间,具有将各种不同活动汇聚在一起,并赋予界限和范围的效果。(8)Edward Soja,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 Verso, 1989, pp.149-151.土司“外逃国家”“内控土民”的行政意图在其早期建构的景观中多有体现。改土归流后,流官的任务在于迅速建立“清晰化”的行政治理空间和“标准化”的文化象征体系,景观的选址和命名便具有规范化的特点。
二、土司时期的“灵溪十景”和“颗砂八景”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永顺土司所处之地为武陵山区腹地,高山耸立、沟壑连绵,在军事上易守难攻,成为封建时期逃离国家控制的绝佳之地。明代万历年间四川江津知县为永顺土司所撰的《永顺宣慰使司祠堂碑》中提及:“永顺界楚西南隅,接壤黔中,进制诸夷峒。大山窈谷,翳林深箐,郁郁千里,盖雄镇云。”(9)鲁卫东:《永顺土司金石录》,长沙:岳麓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这里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方面,永顺土司地处大山深谷之中。“翳林深箐,郁郁千里”暗示了其盘踞国家腹地,不在王朝国家能够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按照斯科特的说法,水稻和谷物构成了王朝国家政权建设的基础,而运送谷物的物理距离和交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内陆国家所能到达的边界。(10)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54页。另一方面,“接壤黔中,进制诸夷峒”。这里的“黔中”指的是“黔中郡”,沿袭了秦代四十郡之一的黔中郡的提法。(11)“重修永顺县志序”中提及“永顺为楚巫中之地,群蛮所在,自秦罢侯置守,分天下为四十郡,而黔中居荆州四郡之一,汉曰武陵”。参见《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页。辰州为黔中故郡城,是明代从中原地区进入土司辖区的重要通道和中转站。与黔中接壤,显示永顺土司其实也没有离平原地区很远,四周受到羊山卫、崇山卫和酉水千户所的监控。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永顺土司统治的维持有利有弊:首先不利于王朝国家权力对自己的渗透,能够偏安一隅;其次不便于对土民的控制,难以集中人口和积累物资。永顺土司既要维持自身管辖的边界,保持与王朝国家的距离,又保留着与境外沟通交流的通道,垄断有限的资源。表现为“风景”的选址,有一部分是连结国家的重要战略节点,另一部分则是阻隔国家控制深入的险峻要塞。
(一)权力资源的控制和垄断
土司旧志所录的“灵溪十景”包括:(1)福石乔木;(2)雅意甘泉;(3)绣屏拱座;(4)玉笋垒天;(5)石桥仙渡;(6)翠窟晴岚;(7)羊峰毓秀;(8)龙洞钟灵;(9)榔溪夜月;(10)铜柱秋风。(12)《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49页。从“十景”的地理位置来看,可以初步了解到永顺土司的意图。“灵溪十景”并不只是风景秀丽的地方,它们是地貌的重要结点、行政区域的边缘或者权力资源垄断的咽喉之地。
1.陆路交通的阻隔与身份区隔的维持
“福石乔木”“绣屏拱座”“玉笋垒天”和“翠窟晴岚”分别位于彭氏土司的治所老司城周边,为拱卫老司城安全的重要山峰,也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王朝国家进入这一区域的陆路交通。
“福石乔木”,位于福石山,即永顺土司司治老司城的背后。明万历年间彭元锦曾于福石山边的将军山顶建有关帝庙,又于福石坪上修建了江湖廊庙、公署及若云书院。(13)《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9-40页。关帝庙和江湖廊庙已经无法追溯,不过关于公署和若云书院还留下一鳞半爪的痕迹。清初谈迁在游历彭元锦所修筑的公署时,曾经感慨其建筑华美。(14)谈迁:《北游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2页。而若云书院的修建有可能在汉人幕僚张天佑的辅佐下完成。(15)《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77页。因此,福石山为永顺土司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中原地区流行的庙宇和书院出现在这里,显示了土司试图借助中原文化符号,维持身份区隔与社会秩序。
“绣屏拱座”,绣屏山是位于老司城前六座并列的山峰,山顶修筑有烽火台,地势较高,成为可以俯瞰整个老司城的守护点。
“玉笋垒天”,位于老司城北面,为形似笋、高高耸立的一座山峰。明代辰阳的千户长张明曾经题诗有云:“圣朝久托为栋梁,万古擎天永赖功”(16)《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8页。,大有将土司比拟为朝廷栋梁之寓意。
“翠窟晴岚”,位于绣屏山右边的山峰,也起到防护老司城的重要作用。曾有知县李靳来到当地游览,并赋诗云:“万仞崔巍壁立山,个中风景别人间;虚涵浩气春恒在,静闭尘嚣夜不关。月薛葱笼凝翠霭,云萝纷绕带苍颜;何年得入灵溪境,吟对樽前着意看。”(17)《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9页。诗句所描绘的意境显示,该处山峰似乎成为隔绝老司城与外界的屏障,竟使得山外与山内的“个中风景”与“人间”有别,山势险峻、阻断交通,令他产生“何年得入灵溪境”的感叹。
福石山、绣屏山、玉笋山、翠窟山是位于老司城地理格局东西南北方位的山峰,是保卫城池安全的天然屏障。选景在此处,并定期巡视这些地点,体现了土司对治所边界的重视。
2.水路要道的控制与稀缺资源的垄断
“雅意甘泉”和“榔溪夜月”则位于外界通向老司城的重要水路之上;“石桥仙渡”和“羊峰毓秀”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分别连结王朝所设置的永定卫和羊山卫。道路是国家加强统治的一种方式。斯科特注意到,拒绝修路或者有意破坏道路是山地居民抵制国家权力渗透的手段。(18)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53页。老司城位于陆路通道难以到达的地方,永顺土司以通行困难的崇山峻岭达到“分隔”的效果,但是又保留了容易通达的水路通道,扩展了资源与外界交换的渠道,造就了权力的聚合点。
“雅意甘泉”,位于灵溪河的西岸,改土归流后为邮传设置点(19)《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7页。,说明该处是重要的水路交通中转枢纽。灵溪河以半环状绕老司城而过,是老司城通往外界的重要航运通道,可连接酉水,通达沅水、洞庭以及长江流域。险峻的地理屏障和崎岖的陆路交通形成了王朝国家政权深入的困境,成为永顺土司与中原保持距离的关隘。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内,通航水路意味着权力节点的存在,土司掌握了运送战略物资的咽喉要道,成为其对土民进行政治整合的基础条件。
“榔溪夜月”,即榔溪河,在老司城下游,为重要的渡口,改土归流后流官在此地设置了驻防把总一员,兵丁十六名。除此之外,榔溪和自生桥还盛产硝土。(20)《永顺府志》卷十《风俗》,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60页。硝土是炼制火药的重要原料,明代在永顺地区的采挖和炼制已经较具规模,甚至成为土民与外界进行交易的重要物产,永顺司等地“素产焰硝,土人以煎熬为业,外省小贩多以布盐杂物零星换易”(21)《四川通志》卷二《雍正七年上谕》,嘉庆二十一年刻本影印,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43页。。说明硝土的产量较为可观,甚至成为部分土民赖以维生的重要行业。
“石桥仙渡”,石桥又称自生桥,横跨在灵溪河之上,路从山梁上通过,为永定卫进入永顺腹地的必经之路。永顺地区山多田少,“稻谷多仰给永定卫、大庸所”(22)《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页。,使得这条陆路交通要道成为扼住当地生计咽喉的重要粮道。永定卫曾经设置在永顺土司境内的羊岸坪,后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迁到大庸,原大庸卫改为永定卫,并在卫城西桑溪关另设大庸千户所。(23)薛刚:《湖广图经志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645页。自生桥上有彭世麒于明弘治十年(1497年)所留下的石刻:“弘治十年重阳 石桥仙渡 宣慰使思斋立。”(24)鲁卫东:《永顺土司金石录》,长沙:岳麓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羊峰毓秀”,即羊峰山。明洪武二年(1369年),茅冈土司叛乱,朝廷派杨景平乱,其后便在羊峰山设置了羊山卫,编棚为城,屯军戍守。(2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七册卷七十七《湖广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645页。这显示明初朝廷希望对永顺土司有所牵制,但最终因为地域险峻而无法立足,羊山卫仅维系了五年,后便因为“此地险远,运饷维艰”而迁移。(26)杨显德:《永定卫志·建置》卷一,收入《张家界卫所史话》,张家界:张家界日报印刷厂,2006,第228页。
羊峰山则是明王朝曾经修建过卫所的地点,作为人工的军事据点,对于老司城的安全来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甘泉、榔溪河和自生桥是外界进出老司城的重要门户,是人与货物交通的关口,后两者还是土司区重要矿产硝土的重要产地。掌控这些节点,意味着控制了统治土民的稀缺资源。
3.神圣空间的构筑和统治基础的合法化
“龙洞钟灵”是当地土民认为祈雨灵验的地方;“铜柱秋风”则是记载了唐末溪州彭氏土酋祖先丰功伟绩的遗址。两者与耕种、农作、捕鱼、买卖等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都没有关系,隔绝于一般的世俗生活,构筑了一种超越日常的神圣空间。
“龙洞钟灵”,龙洞在老司城的东南方向,边上有土司彭宏澎所修建的水府阁,阁内供奉关帝。(27)《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78页。龙洞“相传龙居其中,土人祈雨最应”(28)鲁卫东:《永顺土司金石录》,长沙:岳麓出版社,2015年,第170页。。龙洞祈雨反映了当地土民崇尚巫术的信仰文化。土民散居山间,“尚巫信鬼,语言侏离,不识文字”(29)《永顺府志》卷十《风俗》,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51页。。碎片化的巫术信仰、重视口传文化而非书写体系,可以让土民不断调整他们的信仰和认同,远离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永顺土司在龙洞修建供奉关帝的水府阁,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明代中央王朝对于道教的大力推崇,以国家认可的合法仪式活动来巩固地位,同时又叠合在当地土民“尚巫信鬼”的祭祀空间之上,体现了土司上层对国家认同以及对内聚拢权力的特点。
此处还留存有钟灵山石刻一方,石刻内容为:明嘉靖二年(1523年)秋仲月吉旦,湖广都指挥使、仍致仕龙虎将军上护军、永顺等处军民宣尉使司前宣尉使彭世麒“率众于此地收粟一万秤,以备赈济”(30)《湘西永顺老司城发掘报告》,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学会编:《湖南考古2002(上)》,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325页。。水稻和小麦作为国家空间的首选作物,易于被掌握和征收,在永顺土司辖区较为稀少。据史料记载,“按旧土司家承,永邑山多田少,刀耕火种,食以小米、糁子为主”(31)《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31页。。“刀耕火种”意味着土民的流动性较强,是易于逃避国家征收的一种生计方式,配合以小米、糁子和粟这些相对低产的杂粮品种,起到逃避征税的效果,大量种植又能形成一定的聚集效应,成为土司政权建设的基础。
石刻的落款人除了彭世麒及其家族成员外,还出现了“收粟舍人”“舍目”“把总”“总管”“把目”“首士”“管工”和“造字匠”的名字。这表明永顺土司已经形成有尊卑有别的等级社会,位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永顺宣尉使彭世麒及其家族成员,“舍目”“把总”“总管”“把目”等为土司负责具体事务的仆从差役。从社会结构来看,逃避统治的特点表现为无首领的平权状态,如水母般的族群认同(32)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47页。,而土司社会模仿了中央王朝的权威模式,建立了一套尊卑有别的官僚体系来统摄土民,要求他们缴纳粟等实物税收。除此之外,土司的权威还依赖仪式体系、通婚联盟和祖先叙事来建构和强化。(33)李凌霞:《土王祭祀、家族建构与国家认同——以湘西田家洞村舍巴节为中心的考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13-138页。
“铜柱秋风”,指的是溪州铜柱,位于老司城南施溶司与王村之间,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希范与彭士愁设盟所立,高一丈二尺,重五千斤,其上刻有盟约誓词的铭文。铭文显示,溪州在华夏的系谱中地处“边缘”,为王朝羁縻统治之地,一方面自有君长,无租税之赋;另一方面“归顺王化”,接受朝廷印信。(34)鲁卫东:《永顺土司金石录》,长沙:岳麓出版社,2015年,第4页。由此可见,溪州铜柱在某种意义上是“王化”的象征,也是对祖先功绩的追溯,土司将其纳入“八景”的框架,以重构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龙洞”作为神圣地点,其上修筑了供奉关帝的水府阁,“铜柱”作为文化遗迹,记录了溪州土酋与王朝的盟约,两者都是“王化”的象征,凸显了与化外蛮夷的差异,体现了土司依赖朝廷来证明其作为边疆地区首领的政治合法性,彰显在身份上的优越性以及在文化上的威信。
总体而言,“灵溪十景”选址有着行政考量的色彩,基本上围绕着老司城,也即福石城。不过溪州刺史的州治溪洲城,最初位于酉水河畔的会溪坪,彭士愁的第八代孙彭福石冲继任后,才于宋绍兴五年(1135年)将州治从会溪坪迁到灵溪河谷,在福石山下的福石坪建城,为老司城。(35)周明阜、吴晓玲、向元生,等编著:《凝固的文明》,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事实上,宋代以来土酋首领与王朝之间关系时而紧张,比如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土酋彭仕义自号“如意大王”,起兵反叛,最终被朝廷官员率兵攻入溪洲城。(36)鲁卫东:《永顺土司金石录》,长沙:岳麓出版社,2015年,第11页。而彭氏土酋集团内部也出现内讧,彭仕义谋反之事就是由其子彭师宝所告发,“师宝妻为仕羲取去,师宝忿恚。至和二年(1055年),与其子知龙赐州师党举族趋辰州,告其父之恶”(37)《宋史》卷493《西南溪峒诸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78页。。彭师宝试图借助朝廷的兵威来打压彭仕义。熙宁三年(1070年),彭仕义为其子彭师彩所杀,而彭师彩又为其兄彭师晏所杀,最终彭师晏“纳誓表于朝,并上仕义平生鞍马、器服,仍归喏溪地,乃命师晏袭州事。五年(1072年),复以马皮、白峒地来献,诏进为下溪州刺史”(38)《宋史》卷493《西南溪峒诸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79页。。可见,向朝廷表达归顺之意,争取朝廷的封号,只是彭氏土酋内部权势竞争的一种策略。
防范周边土酋势力的侵扰以及规避中央王朝攻陷州治的危险,成为溪州土酋首领所面临的困扰。彭福石冲袭职后,便是感觉到来自辰州的约束,才决定迁移治所。(39)《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40页。老司城地处偏僻,群山环抱,只有灵溪河一条水路与外界相通,有着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地理的阻隔限制了王朝国家权力的深入,通达的水路构成了一定行政范围内权力聚集的基础。
“灵溪十景”的方位,表明了直到明代,土司关注点还在于行政区域界限的开放与封锁问题上。永顺土司与明王朝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和谐。元末明初,永顺彭氏曾经投靠过与朱元璋对立的明玉珍政权,在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又间接参与了土千户夏得忠发动的叛乱。(40)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癸亥,湖广千户夏得忠结九溪蛮作乱,靖宁侯叶升讨平之,得忠伏诛”。参见《明史》卷三《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6页。明廷在沅水沿岸设置卫所,试图对周边土司有所牵制和弹压,比如短暂维系的羊峰卫就曾经深入永顺腹地。而永顺土司与近邻保靖土司关系不睦,时常相互仇杀,明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永顺、保靖二宣尉世相仇杀”(41)《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987页。。除此之外,永顺土司还承担着防范苗乱的职责,正所谓“‘镇苗’不法,责在永顺”(42)段汝霖:《楚南苗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34页。。
因此,即便治所已经搬迁到远离王朝行政范围所及的福石坪,但土司对于山水地理界限的重视和交通节点的敏感,仍然可以在“灵溪十景”的选址中发现。关卡和边界对于行政治理来说尤为重要,统治者以此来建立起不同等级的分化区域,维持正常的阶层等级秩序,以及规划在边界出入的人与物。毕竟对于山地上的政权来说,收取税金、垄断贸易和矿产资源,是维系权力的关键。而且这些景不只是不断被巡视的军事要塞或者行政关卡,还是象征“文明”和“原始”的分野之处。
(二)社会声望的巩固与强化
永顺土司在老司城周边选定“灵溪十景”,除了透露出在行政上远离王朝国家又控制土民的意图外,也展现出其社会活动的目的。即营造“十景”周边的文化活动氛围,彰显文人气质,来巩固与强化其在土民心目中的社会声望。换言之,对于王朝国家文化秩序的认同和模仿,可以转换为地方社会中区隔异己的政治资源。在王朝国家中,文字的统一力量被视为有助于精英文化维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字书写是社会精英阶层自我认同的重要方式,没有熟练的文字技能,社会声望和知识声誉都无法获得。(43)罗友枝:《帝国晚期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罗友枝、黎安友、姜士彬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赵世玲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3-14页。题字或者题诗作为一种公共书写,核心目的是让他人看到和阅读,在特定的场所展示给特定人群,往往能起到宣传教育、区隔身份的作用。(44)Yueh-ping Yen, The Sky Rained with Millet and the Ghosts Wailed in the Night: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9. p.20.
“灵溪十景”出现时间已无史料确证,但是为“灵溪十景”题诗的官员文人身上透露出一些重要信息。

表1 “灵溪十景”赋诗官员文人名录(45)鲁卫东:《永顺土司金石录》,长沙:岳麓出版社,2015年,第164-172页。
从官员文人的生卒年月或者从政时间大致可以推断,“灵溪八景”的出现应该不会晚于明正统年间(1436年—1449年),大致就在永顺土司接受儒学教育的阶段。虽然溪州铜柱铭文显示,永顺彭氏土酋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在与官方的往来文书中采用汉名,但是直到明宣德年间(1426年—1435年),汉名都未被当地土司广泛采用和重视。(46)谢晓辉:《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02页。在此阶段,很难想象他们已经可以模仿中原做法或者有意识延请汉人幕僚,选定并命名“灵溪十景”。随着明廷不断鼓励土司子弟入学,甚至规定承袭的土司子弟必须入学,才慢慢出现了彰显土司汉文和儒学水平的记载,比如永顺宣慰使彭显英(1440年—1492年)“营治猛洞河别墅,优游林下,日与文人诗士唱和岁月”(47)刘文澜:《彭氏族谱》,道光六年抄本。;其子彭世麒(1477年—1532年)从四岁开始就“教之字义、小诗”,长大后就“延师责以经学”(48)鲁卫东:《永顺土司金石录》,长沙:岳麓出版社,2015年,第83页。。虽然“日与文人诗士唱和”似乎有溢美成分,但从这一时期老司城周边所留下的摩崖石刻来看,土司的确掌握了一定的汉文读写能力。因此,土司以“题字”的方式代替“题诗”来参与文人阶层的高雅活动。
“灵溪十景”,是供土司和文人阶层游览休闲的地方,通过“十景”的营造,土司可以在监督行政事务的同时,通过游览、“题字”等行为,彰显一种边疆与内地无甚差别的“文明”感和安全性。比如,彭世麒留下了“石桥仙渡”的石刻游记,“弘治十年重阳 石桥仙渡 宣慰使思斋立”。彭宏澎在“龙洞钟灵”上修建了水府阁。这相当于风景的文本化(textualize)(49)Richard E. Strassberg,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s from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pp.1-2.,即将文字痕迹、书法笔墨转化为山水景色的一部分,将平淡无奇的自然地理转化为被“文明”篆刻过的“风景”。
外地文人官员来到这些胜地,不仅仅可以享受山水风光,同时也可以巡视帝国的“边陲地带”,并且留下一些诗作。按照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说法,文人寻幽访胜,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场合吟诗作对、怀古思今,可视为一种“记忆的仪式”(rituals of remembrance),能将文学个体与象征整个中国文明传统的文人群体联系在一起。(50)Stephen Owen,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2-26.
永顺土司与外来的文人墨客在“灵溪十景”中体验自然,通过游历“灵溪十景”的空间实践,使得偏远、“蒙昧”的“边疆”得以连接到“文明”的中心。比如永顺土司彭翼南在灵溪河沿岸还留下石刻铭文:“嘉靖乙丑季夏,予款内阁大学士徐门下锦衣仝云州、吕松泉、庠士杜太行,携宗族人等偕游于此。”(51)鲁卫东:《永顺土司金石录》,长沙:岳麓出版社,2015,第51页。在“风景”中题字、巡游,永顺土司彰显了与中原士大夫阶层无差别的文字技能和审美风格。
自然风光本身不足以成为“风景”,“风景”的建立离不开文人墨客的社会活动。一处山水的知名度,会因为诗人之名声或官职大小而改变,而诗人也有可能因为山水知名度提高而声名远扬。从表1中可见,在“灵溪十景”题诗的官员文人中,除了千户、知县、知府等地方官员,也有中央朝廷各部官员。每处“风景”都有不止一位诗人留下作品,从官员生卒年月或者从政时间大致可以推断,他们游历“灵溪十景”可能从正统年间开始,到弘治时期达到一个高峰,一直零星持续到嘉靖年间。这显示了“灵溪十景”虽然位于交通不便的边疆山区,但也逐渐小有名气,吸引了一些文人官吏慕名而来。由此可见,土司以及文人在游览山水时吟诗作对、刻字留匾,将自然风光以比喻或者命名的方式转化为文字痕迹,刻画出“文明”的空间——“风景”。
(三)文化品位的彰显和提升
除了“灵溪十景”,土司旧志还记录了另一套“颗砂八景”。“颗砂八景”具体包括:(1)奇峰葺碧;(2)晴野流云;(3)北岭樵歌;(4)东江渔火;(5)竹桥吟眺;(6)松坞棋声;(7)平川霁月;(8)老圃寒梅。(52)《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49页。“颗砂八景”的出现应与颗砂行署的修建有着密切的关系。颗砂作为土司行宫,早在明中晚期彭世麒(1477年—1532年)时便已经修建完成,史载“公在任一十六载,所向克捷,茂著多功。疏请于朝,乞休林下,建修颗砂行署”。(53)刘文澜:《彭氏族谱》,道光六年抄本。
主持修建颗砂行宫的彭世麒曾经聘请汉人协助制度改革,建祠修学,对当时的名家大儒都“厚礼厚币”求教,广为结交。(54)《永顺宣慰使彭忠轩墓志铭》,“赐进士上□中宪大夫贵州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前兵部车架司员外郎辰郡大酉王世隆撰,嘉靖二十三岁十一月十一日”。此碑现藏于永顺县老司城。与此同时,彭世麒及其弟彭世麟率领土兵频繁被朝廷征调前往各地平乱,先后被敕封为“昭勇将军”“昭毅将军”。(55)彭肇植:《历代稽勋录》,“彭世麒”条,嘉庆十二年;又见《明武宗实录》卷八“弘治十八年十二月甲戌”条,“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卷影印,1962年。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又因朝廷大兴土木,彭世麒及其子彭明辅进献楠木七百余根,朝廷奖励其擢升都指挥使,红蟒衣三袭,地位日趋显赫。(56)《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一“正德十三年夏四月丙戌”条,“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卷影印,1962年。总体而言,从明成化到嘉靖年间,卫所废弛和募兵制的兴起促成了湘西苗疆官府弱而土著强的格局,永顺土司在帮助官府平乱的过程中获得了朝廷的正统身份,已无其他周边势力可危及其区位安全。(57)谢晓辉:《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69页。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使得土司更有闲情逸致去寻幽访胜。永顺境内摩崖石刻在这一阶段数量较多,也证实了这一点。
颗砂一带为丘陵河谷地带,比起老司城所在的狭隘山谷更为开阔,是不干政后的老土司休闲悠游的好去处。老司城地处群山之中,基本没有耕地,山地政权垄断权力的核心主要建立在对中心市场和重要物产的控制之上。不过作为人口有一定密度的中心聚落,老司城必须依赖周边聚落提供足够的粮食。颗砂作为土司专供大米的重要产地,承载了山地政权的重要经济功能。清雍正二年(1724年),末代土司彭肇槐正式将治所迁移到灵溪河上游的颗砂,即新司城。(58)《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43页。
“颗砂八景”与“灵溪十景”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行政区域的关隘、边界已经不再是统治者所关注的重心,文化品位的彰显和提升才是土司的迫切需求。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品位带有等级区分的性质,既是社会地位的体现,同时还有增强社会阶层成员联系的功能。(59)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2页。永顺土司努力呈现与内地文人官员具有类似的高雅品位,同时也力图拉开其与土民及周边土司的等级区分。(60)周边的容美土司、保靖土司和桑植土司尚未发现留下关于“八景”方面的记录,“容美八景”“保靖八景”和“桑植八景”为改土归流后出现。流官在编撰方志时曾抱怨道,“桑植本土司辖入版图才三十余年,土官不学,无文献可征”。参见《(同治)桑植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0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页。“颗砂八景”不但更为符合中原地区的诗文传统规范,也更贴近儒家文化的审美旨趣,体现了永顺土司对于王朝国家诗文传统认同进一步加深。
从选址来看,风景所在地不再是防御工事或者战略要地,而是参与性强、更具生活气息的地点。“颗砂八景”的选址除了“奇峰葺碧”“东江渔火”和“北岭樵歌”三处位于颗砂城外,其余五处皆在颗砂城内,甚至就在土司行署四周,为土司日常起居赏玩之处。从内容来看,“颗砂八景”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石刻题字。“奇峰葺碧”,位于颗砂城西北五十里的山涧处,旁边的岩石上刻有“斗泉”二字(61)《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54页。;“东江渔火”,在颗砂城西北三十里的松云潭,石壁上刻有“东江渔火”(62)《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54页。;“松坞棋声”,在颗砂城的古篆“碧水”前,每当微风拂过,两棵巨松便发出如棋子掉落棋盘的声音(63)《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49页。。
其二,人工造景。“晴野流云”,在颗砂南桥三里处的鱼池,有天际云朵映入池塘内而得名(64)《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49页。;“竹桥吟眺”,位于颗砂土司行署前的竹桥,长三丈、宽二丈、高二丈,由巨石所垒,为彭世麒所建(65)《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63页。;“老圃寒梅”,栽于颗砂土司行署旁边圃园中的梅花树,自成一景(66)《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50页。。
其三,自然风光。“北岭樵歌”,在颗砂城北,采樵者经过山岭时歌声与鸟声相和而得名(67)《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49页。;“平川霁月”,位于两棵巨松旁的一汪泉水,因山川和月色的倒影相映成辉而得名(68)《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50页。。
原来留存有石刻的地点更容易得到土司的青睐,这意味着与曾经游历此处的文人墨客建立起象征性的文化联系。人工精心雕琢过的景致则可以消除“蛮荒”之感。剩下两处,则突显了即使面对“纯粹”的景色,土司也具备鉴赏能力,有所感悟。
从参与度来看,“颗砂八景”更能让人产生心理上的共鸣,观看主体的活动经验较为丰富。例如,聆听北岭采樵者的歌声,在灵溪河与颗砂河交汇的东江观渔翁垂钓,在竹桥上吟诗远眺,等等。“松坞棋声”“老圃寒梅”等景,更是从声觉到嗅觉突显出统治者对于景色更为具体的体验和欣赏。相较之下,“灵溪十景”的名字和选景显得更为严肃而刻板,观赏者只能在远处欣赏风景,并不能近距离参与其中。
“颗砂八景”与“灵溪十景”的选景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也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从命名来看,首先四个字构成的景观,一般前两个字是地点,比如“灵溪十景”中的福石、绣屏、玉笋、石桥、翠窟、羊峰、龙洞、榔溪、铜柱,“颗砂八景”中奇峰、晴野、北岭、东江、竹桥、松坞、平川、老圃;后两个字是修辞加工后的景色,如由“乔”修饰“木”,由“夜”修饰“月”,由“秋”修饰“风”。其次,两组景观各自形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仗相对工整的整体,比如“福石乔木”对“雅意甘泉”,“绣屏拱座”对“玉笋垒天”等等。这在结构和对仗上面与中原地区的“八景”基本保持一致。土司及其幕僚试图按照儒家文化的美学标准、诗学技艺或者文学传统,将山川流水、月色秋风等自然现象和石桥、竹桥、老圃等人造建筑予以文学化,使其变成可供广大文人雅士品评鉴赏的对象,构筑了一种品味高雅的文化意象,按照中原地区的一套文学标准构筑“八景”文化,并不时与汉人幕僚、士大夫游览题字。
综上所述,土司时期的“八景”文化建立在行政体系和社会活动规约的空间之上,隐藏着不同权力运作交织的痕迹。“八景”的命名和结构是边疆社会重组人群和区别异己的重要框架,土司阶层模仿内地诗文传统建构了“八景”文化,是华夏边缘对于族群分层混居的回应,隐含着游离于国家权力控制之外的行政意图,但也彰显了其对王朝国家文化秩序的模仿与认同不断深入的过程。土司择出“灵溪十景”和“颗砂八景”,并到这些景点巡游题字,也是为了显示自己比起他们的子民更高一级。透过“十景”“八景”的文化营造和空间实践,土司阶层将自然山水区分成为“景”与“非景”,实际上就在意识上将超然的休闲活动与日常的生产活动区分开来,以突显自身与完全没机会读书识字的土民之间的不同,巩固他们在山地既有的政治地位。从“灵溪十景”到“颗砂八景”,其背后的时空背景有所不同,反映了截然不同的取舍标准。由此可见,永顺土司对于“八景”文化的建构,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生活实践中回应看得见的邻里、子民,以区分彼此族群阶序,彰显地方领袖的身份优越性。
三、改土归流后的“永顺八景”
改土归流后,朝廷的政治力量直接进入永顺,从官府的角度看来,无论土司子弟还是土民、客民抑或苗民,只要表现得足够“开化”,就意味着“版图”的成功拓展。也就是说,永顺纳入清政府直接统治的过程,意味着透过官僚行政治理的规划,配合“客民”的流入,将“土民”“苗民”居住的生活“空间”,转化为符合儒家价值标准,适合中原地区人群分类、了解、旅行、交易、渔猎与耕种的“地方”。与土司时代超越日常经验、区隔与土民之间等级阶序的“八景”有所不同,这时候的“永顺八景”会涉及贸易、休闲沐浴等的日常活动,而且也会遵循中原地区传统的风水堪舆之学。
清雍正七年(1729年)彭肇槐主动申请改流,永顺府正式设立。政府官员开始在这里选定“永顺八景”。永顺府下辖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府治设在永顺县猛峒坪(即今永顺县灵溪镇)。作为负责永顺府筑城的主要官员,时任首位永顺县令的李瑾,从众多名胜风景中选择了八处地点,定为“永顺八景”,分别是:(1)玉屏焕彩;(2)文峰拥秀;(3)榜岫云晴;(4)福岭霞蒸;(5)龙洞朝云;(6)双溪夜月;(7)河港温泉;(8)连桥新市。(69)《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5页。
(一)行政空间的清晰化
斯科特认为国家治理的要义在于“清晰化”,即清晰识别出地域空间、人群类别和物产储备,是行政控制的前提。(70)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页。永顺府县行政体系建立的第一步,是从战略交通、地理形式选择一个中心地带设立城池,由此连通四周道路,在空间上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的阶层结构,从行政治安和资源流通的维度设置一套清晰的定位,在边缘地带建立关隘堡垒,派驻军队、安插营哨、管理集市,建立一个可以系统治理的行政区域。
1.行政边界的维持
“玉屏焕彩”“文峰拥秀”和“榜岫云晴”所在之处皆为拱卫府城安全的险要之处,各据南北,控制陆路交通,保护和维持府城的边界和安全。“福岭霞蒸”作为旧土司统治中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玉屏焕彩”的玉屏山,在永顺城北十五里处,系列山脉会聚于此地,形成一块护卫永顺城的屏风。从湖北八面山而来的地理龙脉,经容美、桑植蜿蜒而来,与东西横亘之武当山脉交汇集结于此,隆结成为玉屏山,是整个永顺府城门户的守护点。(71)《永顺府志》,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文峰拥秀”的文峰山三峰耸立,正起到拱卫府城南面的作用。
“榜岫云晴”位于府城西南面的挂榜山。挂榜山是从西南方向进入永顺腹地的第一个要地,与沅陵相接,处于水路交通要道之上,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福岭霞蒸”中的“福岭”指的是福禄寿三座山名的合称,即“福石山”“寿德山”“禄德山”,位于原永顺土司行署老司城后。
2.水陆要塞的控制
“龙洞朝云”位于陆路关隘,而“双溪夜月”地处水路节点,道路作为国家权力延伸的触角,所及之处都是国家权力施展之地,这两处对于新设府城而言至关重要,意味着行政界限的开放和封锁。
“龙洞朝云”位于府城东面的飞霞山,山上有飞来石,形似屋宇房门。此处官府建有一个飞霞关隘,这个关口控制着两条交通路线,一是通往原永顺土司行署新司城颗砂,另一是通往永定卫大庸所的要道,客民往来经商之地。官府在此地设有外委一员,兵丁十名,常年驻扎,维持这一交通要道的畅通。(72)《永顺府志》,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双溪夜月”,位于府城南门外,指的是绕行城西的猛洞河和绕行城东的白沙河交汇处,双溪交汇后流经列夕,最终从王村汇入酉水。此地乃当地河道交通的咽喉之地,这里水路交通的便捷,沿着河道乘船而下,经王村,可上通川黔,下达辰州。这一河道是全府重要的商品转运通道,也是盐商从辰州运送盐包进入湘西的交通路线之一。(73)《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21页。
3.日常活动的管理
在传统王朝时期,语言和世界被认为是“同构”的,古代中国人通过“命名”创造世界的秩序,对空间进行分隔、“命名”并规范化,是政府宣称合法性控制的文化象征行为之一。(74)Robin D.S. Yates, “Body, Space, Time and Bureaucracy: Boundary Crea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in Early China,”In John Hay (eds.),Boundaries in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Press, 1994, pp. 56-80.空间的边界不仅包括行政区域的边界,也包括人文活动和地理气脉的交汇点。对温泉和集市的关注和命名,体现了王朝官员对于山水人文界限变动的关注。
“河港温泉”,在永顺城南大约十里处。这个景的特色在于,温泉是可供人们沐浴休闲的去处,也是文人墨客喜欢逗留的胜地,因为泡温泉不仅可以强身健体,也是与大自然全方位接触方式,作为天地山水与人的身体连接点,人文与地理之间的边缘地带,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独特的身体经验。
“连桥新市”,在永顺城东半里处,指的是猛洞坪集市,从土司时代以来就是连接老司城和猛洞河、洗车河流域的重要商贸中转站。改土归流后知县李瑾为往来的商民提供便利,在此地架了两座桥,并搭建了两个凉亭,永顺知府袁承宠分别题额匾为“迎恩”和“太平”。(75)《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49页。
从“永顺八景”的选址来看,李瑾也较为关注拱卫府城安全的战略要地。位于府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山峰“玉屏”“文峰”“挂榜”和“飞霞”,这些地方维持着永顺府城的边界,猛洞河和白沙河“双溪”的交汇处,是进出永顺府城的水路关口。位于老司城的“福岭”,虽然不在府城的边缘,但它象征新旧政权交替的界限。“温泉”是人们在地表上享受地气之所在,是自然地理与人的身体接触的边区。“连桥新市”是人和货物交通的关口,是官府收税和盘查的节点。这些景观的实际所在,有着特殊的军事部署和防御意义,显示了它们需要不断被巡视以及层层军事保护。即使永顺末代土司主动献土改流,但乾州等地的红苗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清雍正八年(1730年)九月初六,永顺府同知李珣陪同辰沅靖道王柔带兵招抚乾州上六里的红苗。(76)段汝霖:《楚南苗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49页。当地流官想要开始从事一些文学娱乐活动时,仍然不可避免要对府城安全和行政治理有所考量。
(二)风水象征的标准化
除了行政安全的考虑,传统风水知识体系也是“八景”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永顺县令李瑾在《永顺府建城记》提及曾经与书吏姚惟孝、阴阳学陈绍尧一起登山堪舆,“始知此地自湖北八面山起,祖历容美、桑植至永顺,由武当山之东复折而西,蜿蜒起伏,至永顺结玉屏开帐,顿起观音山,层峦叠嶂,落脉平阳,结兹城局,而左右随龙之水,直会于城局之南,流出辰方,且东则飞霞诸山,龙势飞舞,西有挂榜诸山,如仓库、如旗旛,南则文星罗列,水口完固,果天然一都会之地,千百年藏闭于此”。(77)《永顺府志》,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06页。
按照李瑾的看法,此地位于“龙脉”之上,左右又有“随龙之水”,就风水地理的格局而言,是理想的“都会之地”。在堪舆家关于中国的想象当中,中央王朝的疆域地理都在南、北、中“三大干龙”龙脉延伸的区域范围内。风水术数中的“龙脉”,象征着朝廷的权威统治。(78)陈进国:《风水的文化记忆与地域空间的意象化——以福建地区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92-101页。边疆地区的文人官吏通过对“龙脉”的风水地理表述,展示其对帝国文化秩序的认同,同时象征性地确认当地在“边陲(周边)—中心”格局的政治从属位置。
“玉屏”“文峰”“挂榜”和“飞霞”这四个方向的山峰以及“双溪”会成为“八景”之一,因为它们是符合传统风水格局的地点。华琛曾经借由“标准化”的概念指出,国家倡导的是象征结构,而不是信仰内容。(79)华琛:《神明的标准化:华南沿海天后的推广,960-1960年》,陈仲丹、刘永华译,刘永华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4页。在尚未完全开发的边疆地区,不管其与内地的差异多大,流官只要建立起符合王朝标准风水格局的“八景”,便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蛮荒”已入“化内”。
(三)文教活动的规范化
除了命名“永顺八景”外,李瑾还依次写了八首七言诗。(80)《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5页。“永顺八景”的七言诗,透露出作为负责筹备永顺设治的主要官员,李瑾除了要监督行政和部署军事防御,同时还需要关注民众生计,比如发展农业、控制市场,更是地方儒学教育的推动者。他认为永顺筑城,等同于“出草昧”“辟混沌”,作为“文明之会”,永顺府城的首要功能在于教化民众。(81)《永顺府志》,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06页。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他不仅协助永顺知府袁承宠兴建府学、县学,而且筹资捐建桂香书院,拟“将延师聚徒讲习于其中也”,有时还会在里面讲学,亲自教导学生。(82)《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22页。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永顺县志》便收录了不少以“永顺八景”为题的诗歌,诗人基本上都是本地的邑廪生、邑庠生、贡生,这也许与书院的教学传统有莫大的关系。(83)《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据湖南图书馆藏本影印,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51-52页。李瑾歌咏的对象,讴歌的地点,以及八景诗中流露的迫切改造蛮荒边疆的情绪,成为今后永顺文人官员的诗歌范本。经过儒学教育和文化素养的熏陶,地方的文人们得以培养起一种特殊的社会美感,通过阅读前人的诗作,游览山水,再透过特定的比喻和文体,将自然风光转化为可流传后世的诗文,营造出“文明”的氛围。
四、结论
从土司时代的“灵溪十景”“颗砂八景”,到改土归流后的“永顺八景”,它们的命名和结构基本上都遵循古典四言诗的格式。值得注意的是,土司时代的选景完全超越了日常生产活动,发挥着划分群体等级的作用,体现出“内控土民”“外逃国家”的特点。具体而言,“灵溪十景”体现了土司对于权力资源的掌控,尤其重视影响山地政权稳固的关隘、通道、矿藏乃至圣地。“颗砂八景”则出现在永顺土司取得王朝显赫身份之后,此时文化品位的提升较为重要,可以让其进一步拉开与周边其他土司、土民甚至苗民的等级差距。而改土归流后的选景则注重将日常生产生活纳入其中,流官按照“标准化”的风水格局选定“永顺八景”,力图让行政区域及民众变得“清晰化”,将他们的贸易、泡温泉等日常活动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中。不论如何,偏远边疆的奇山异水,透过选址、命名、游览“八景”的文化实践活动,都被转化为内地文人所熟悉的统一形式,帝国的秩序得以在“边疆”确立和扩张。
土司地区“八景”的建构、变化与区域历史环境的演进息息相关,反映了“边疆”社会“大一统”进程中某些较容易被忽略的侧面,为明清土司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近年来土司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土司制度的运作转移到土司制度的影响,比如土司制度如何改变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而纳入大一统中国。然而,土司作为王朝国家和边疆社会的中介者,其适应国家的独特方式值得深入探讨。永顺“八景”文化的个案研究表明,土司阶层和流官群体建构“八景”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与恪守王朝典范的流官相比,土司在认同、模仿王朝文化秩序的同时,也在以此来抵制国家力量的深入,他们借助华夏的文化标签强化乃至扩大其在地方社会的权力基础,与内地一致无二的边疆“文明”景象背后充满了矛盾和博弈。另外,来自中国西南土司的案例研究也可以让我们反思斯科特关于“逃离国家”和“国家化”二元对立模式的解释力度,进一步拓展民族史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