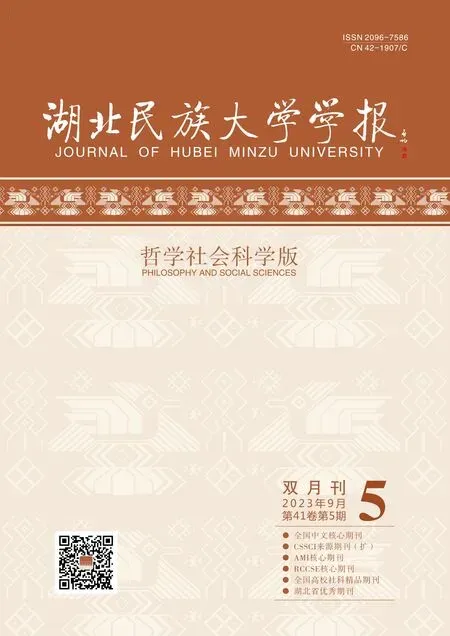历史中的神话与神话中的历史
——夏启叙事的四重证据法求证
叶舒宪
一、古史的辨伪与求真
20世纪初年,在西方学术的历史科学观念借道日本传入中国后,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了古史辨派运动风潮,要打倒国学传统坚信两千多年的上古史三代偶像以及更早的三皇五帝圣王谱系。在疑古派群体的颠覆性打击下,严谨的古史研究者不再盲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体系,对商周以上的帝王谱,特别是无文字记录的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传承叙事,持否定或存疑的态度。
一个世纪之后,立足于考古新发现带来的史前史系统资料,今日已经具备重新权衡评估古史辨派学术利弊的客观条件。笔者认为,古史辨学派的巨大学术影响力,成为现代学术史上迄今无人超越的高峰,并且仍在发挥余威。但时过境迁,以当今的知识更新水平和学术标准再评判,该派的学术努力可谓功过对半。其功劳在于以摧枯拉朽之魄力,揭破古代史书以层垒叠加方式构建出的上古史谱系的虚假、不可信;其所忽略的,或没有尝试的另外一半在于,即便是上古遗留下的神话文学叙事中也潜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有待于后世学人的努力辨析和充分认识。限于当时学界的知识条件,尚不足以在这方面形成有效的学术自觉和问题意识,所以该学派只能一味将主要目标聚焦到上古史的辨伪和打假上,未能对古史的求真方面提出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与方法论。
20世纪末期伴随改革开放而兴起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一派,希望能够在古史辨派止步之处重新出发,探寻学术突破的方向,尽可能弥补上古史和史前史之间的虚无空缺,找出商周两代之前的文化传承和历史演变线索。换言之,要在三皇五帝谱系的神话偶像群坍塌的废墟上,重建某种真实可信的上古史年代线索,侧重在物质文化进化的真实过程方面。那么,文学人类学派首先要完成一个重要的研究转向,是从求证古史早期的神圣帝王人物谱系,转向求证古史人物叙事背后的物质文化真相,这即是四重证据法的“物证优先”原则。(1)叶舒宪:《物证优先:四重证据法与“玉成中国三部曲”》,《国际比较文学》2020年第3期,第415-437页。这是一种针对研究对象的取舍策略:不再一味地纠缠于三皇五帝之类传说人物的历史真伪之争辩,而是全面转向有考古资料支持的相当于夏商周三代和史前时代的物质文化求证。唯有如此,才能够做到研究证据的有效性:从物质文化解读入手,迈向5000年文明的真实深度,并充分利用四重证据的间性互动空间,探索学术瓶颈的重要突破口。
本文以国学界所公认的上古第一史书《尚书》中的《甘誓》篇和同样公认的神话书《山海经》为例,以此二书所记夏代开国君王夏启事迹为对象,构成一组两相对照的夏文化叙事个案,揭示“假作真来真亦假”的叙事现象产生的奥秘,说明史书所记夏启甘誓事件的虚构成分和可信成分,同时说明神话书《山海经》夏启叙事可求证的史前史内容。
文学人类学尝试重建华夏历史文化文本的发生过程,其所倚重的新方法论,具有交叉学科知识互动互补的性质,称为四重证据法。这主要是在传统的二重证据即文字证据之外,开辟非文字的第三重证据(口传的活态文化)和第四重证据(考古实物和图像)。(2)杨骊、叶舒宪编著:《四重证据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页。而2020年提出的“物证优先”原则,便是将第四重证据,抬升到超越前三类证据的最重要地位,开辟出某种“以物证史”的新境界。
夏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国君王,他所在位的时间和建都地望,目前尚无法提供任何足以确证的材料和线索。与此同时,借助于百年来的大量考古新发现,相当于夏代初年的中原文明王权的起源线索却是可求证的。这些充裕的物质文化资料,可供研究者参考和对照。
二、《尚书·甘誓》夏启叙事的真伪辨析
《甘誓》为《尚书》六体之一的“誓”体。《尚书》共收录夏商周三代的五篇誓辞,发誓的五位主人公分别为夏启、商汤、周武王和鲁公、秦穆公。前三位分别是上古三代的开国之君,后二位则为春秋时代的鲁国和秦国国君。由此可知,在古史上留下重要誓词的五人全部为王者,地位最低者也是诸侯国君,没有一位凡夫俗子,也没有一位属于臣子百官。归纳起来看,《尚书》所记誓体文字肯定与王权相关。王权的背后则有神权,因为王者或为天子,或为代神立言者,其誓词的内容是首先要强烈地确证发誓人是将神意或天命传达到人间的中介者这一身份。誓词中的如下两句“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成为整个誓言内容的转折点,发誓人一旦宣告自己替天行道的神圣性使命,随后将要展开的征伐战事的神圣起因就已经明确。听取天子发誓的六师及其属下应该如何作为,就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假如有人胆敢“不用命”,其结果就是违反神意和天命,乃大逆不道冒犯和忤逆,必然遭到天罚。
据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所叙:夏启的讨伐战事和战前誓师大会,关系夏代王朝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也关系到夏启作为天子对忤逆者有扈氏的征伐权力,及其背后的神学信仰。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04页。
将《史记》与《甘誓》内容加以对照,可知司马迁对夏启的这段叙事写作,是以《尚书》为底本的润色修订,增加了作誓背景的交代。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4)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54页。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所著《书经中的神话》一书以西方的历史科学观分析《尚书》,认为早期中国史乃是按照“神话的历史化”(原文为希腊文,汉译为“爱凡麦”)方法而写成的。他指出:“(古代史官)为了要在神话里找出历史的核心,他们排除了奇异的,不像真的分子,而保存了朴素的残滓。神与英雄于此变为圣王与贤相,妖怪于此变为叛逆的侯王或奸臣。这些穿凿附会的工作所得者,依着玄学的学说(尤其是五行说)所定的年代先后排列起来,便组成中国的起源史。这种东西仅有历史之名,实际上只是传说;这些传说或来自神话,或来自祭祀的祖庙,或来自各地的宗教,或来自学者们解释某种礼仪的记载,或来自民间故事,等等。”(5)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冯沅君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6页。按照这个观点,《甘誓》发生的夏初战争背景,敌对双方夏启和有扈氏,分别为天神变成的国君和妖怪变成的叛逆侯王。
既然史书撰写采用文学虚构法,当今学人应该如何面对呢?马伯乐给出全然否定的答案,并给中国的古史辨派造成深刻影响:“这些充塞在中国史开端中的幽灵,都该消灭的。我们不必坚执着在传说的外形下查寻个从未存在的历史的底子,而应该在冒牌历史的记叙中寻求神话的底子,或通俗故事来。”(6)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冯沅君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7页。
马伯乐对中国神话与历史的见解,对顾颉刚先生影响很大。顾先生为推广马伯乐的《尚书》研究之观点,专门为冯沅君的中译本撰写一篇序言,其中推崇马伯乐的治学态度是客观的,其方法是科学的,其成绩也是值得钦佩的,并表明马氏研究“可以做我们研究的先导”(7)马昌仪主编:《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0页。。于是,在马伯乐用洪水神话解说历史人物夏禹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这是由于战国时代诸子造伪,将禹的神话传说历史化的。包括禹与夏的关系、尧舜禹三者的关系、鲧禹启三者的关系。顾颉刚希望把夏史专题研究写成一书,先拟定考证对象为启和太康。不料此计划未能完成,搁置了五年后,于1935年委托认可自己观点的童书业来协助完成。他对童书业说:“夏代史本来只是传说的堆积,是我们的力量足以驾驭的材料,不如索性做一部《夏史考》吧。”(8)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605页。并拟定该书共十章包括四个附录的总目录。1936年,顾颉刚、童书业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联合署名发表该书的第五章至第七章,题为《夏史三论》。顾颉刚在文前添加的说明有这样的判断:“禹与夏发生关系在前,鲧与夏发生关系在后。自禹和夏发生关系之后,禹才与启发生了父子的关系。再合上原有的几个夏代之王,夏代史算有头有尾了。”(9)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607页。该文附论又考证《左传》“夏启有钧台之享”叙事说《国语·鲁语下》“禹致群神”叙事在先,是原始的神话,由此派生出《左传》的“禹合诸侯于涂山”和“夏启有钧台之享”和“启本是有神性的人物,其享诸侯怕也是享群神传说的演变”的叙事。除此之外,《太平御览》八十二引《归藏》注:“昔者夏后享神于晋之墟,作为璿台于水之阳。”璿台就是钧台,这为璿台的事是可以说成启的罪状的,似源出于商纣王为瑶台的罪状。(10)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618页。
《古史辨》第七册还同时收录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一文(原为长文《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中的一小节),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史记·夏本纪》叙禹至帝癸凡十四世,似脱胎于《殷本纪》叙帝喾至示癸凡十四世。启与契古音相通,二字皆有开启的意思。(11)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691-692页。由此可见,古史辨派的意见并不把夏代和夏启的相关叙事当作真实历史,而是当作神话传说,乃至要揭示从原始神话到派生传说的因果关系和演变过程。不过,顾颉刚晚年时观点有所逆转,似乎不再否认夏史的存在。2005年,顾颉刚和弟子刘起釪合著《尚书校释译论》一书问世,在《甘誓》篇校释中,二人表示相信这篇誓词为夏代遗留下来的。(1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75页。
《甘誓》这篇夏后氏与有扈氏作战之际的誓师词,大概在夏王朝是作为重要祖训历世口耳相传,终于形成一种史料流传到殷代,其较稳定地写成文字,大概就在殷代,所以用了在殷代后期已出现的“五行”“三正”字样。(13)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73页。
笔者认为《甘誓》为夏代口传下来的史料说,是不足为凭的。古史辨派主将们在21世纪发表的此类观点,似乎是20世纪古史辨伪观点的变相否认和倒退。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尚书校释译论》,皆认为《甘誓》成文时代是在商代,后经过周人的润色。这样的立论仅凭文字词语方面的对比(如六卿、五行等),说服力不足,还需要提供确凿证据。
如果利用考古学新资料去重审这个公案,就会意识到史书中的记载可能与夏代历史并不相符,而神话书《山海经》夏启叙事中反倒可以求证某些真实的史前史信息。鉴于夏代始于距今4000年上下这个时期,物质文化史方面的求证空间已经全然打开,这就是文学人类学派所倡导的“第四重证据”。第四重证据能够对古书记载的真伪虚实发挥试金石一般的检验作用,此种检验的结果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夏代初年的马拉战车作战,战车左右皆有将士,中央有驾车者,这样的情景肯定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的中原地区既没有家马的驯养,更没有战车的生产和使用。不要说两军对垒时作为机动性攻击武器的战车,目前的考古证据就连最简陋的木质独轮车也没有发现。那个时代,甚至还没有任何使用车辆的技术条件。据考古报告,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车之实物是商代的,商代以前尚未找到有车辆的实物(哪怕是车的零部件也没有)。考古工作者推测二里头遗址三期有类似车辙的痕迹,但这也多少有些捕风捉影之嫌。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年代,距今约3700余年。三期的年代距今约3600年,距离夏代初始的4100年尚有四五百年的差距,这不是能够轻易抹平的。
且不论夏朝是否存在过,至少在4000年前的中国根本不存在马拉战车并有左右兵将加中央驾驭者的战车形式。那时的统治者怎么能说出“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样匪夷所思的话语呢?
当然,《甘誓》主要内容,除后人伪托之外,也有其符合历史真实的一面,试举几例。其一,围绕着祖先崇拜和土地崇拜的祖和社,代表上古时期的国家祭祀制度,确实长期存在。其二,军事征伐权力需要借助于誓师礼仪作为神权合法性的保障,这也体现了祭政合一的史前社会之权力运作真相。周代之人模拟此前的夏代君王口吻,按照自己所熟悉的车战现实情况,将周代统治者讨伐作战的情形投射给夏代初年的讨伐战争,让夏朝的国家领袖像周王或东周的诸侯王那样行动,说出类似周王誓师的话语。其三,上古发布军法的仪式语境。《渊鉴类函》卷十五引《三略军谶》云:“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甘誓》之誓词,显示出军令如山的绝对权威性和赏罚分明。
以上几个方面,就是在《书经中的神话》这样的辨伪研究范式以外,还需要有求真研究范式的理由。问题在于,如何去具体求证《尚书》中的真实历史信息?发挥四重证据彼此之间的证据间性,有利于找出失落的历史的可信性一面。就誓言这样的体裁而言,事关汉语文学发生的历史真相。在华夏最早的史书《尚书》的文体形式背后,确实潜藏着一种异常深厚的文化传统——口传文化传统,这也属于文学人类学派提示的文化大传统的特性所在。即前文字书写的时代,重要的仪式行为大都伴随着法术语言的运用效力,誓言只是其中的一种。其他如祈祷、祝颂、咒语、呼告等,拙著《文学人类学教程》和《论语:大传统视野的新认识》曾针对文学史中被误作散文的《尚书》六体(典、谟、诰、誓、训、命)和孔子《论语》,结合金文叙事发语词模式如“唯”“若”(诺)等,尝试口传语境的具体还原,以王权话语架构的“神圣言说”,呈现汉语文学发生考的分析案例。(14)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70-214页。
政治哲学家指出,自古以来社会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有四个方面:神明第一,国王第二,团体第三,个体第四。前三个源头常常会压抑第四个源头,正如约翰·拉尔斯顿·索尔所指出的:“这些源头有许多变体。许多国王声称直接受命于神明,因而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从拿破仑到希特勒的现代独裁者曾声称继承了国王的合法性。”(15)约翰·拉尔斯顿·索尔:《无意识的文明》,邵文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2页。在荷马、孔子及其之前的时代,神明和天命无疑是凌驾一切的终极源头。文化人类学将此种社会合法性现象归结为政教合一或祭政合一,华夏文学最早的文本《尚书》之六体(典、谟、诰、誓、训、命),其实全都出自通神降神的王权仪式语境中的“语体”,这也是《甘誓》中夏启代神立言,代行天之赏罚的信仰奥秘所在。
三、距今4000年至2500年之间的车马物证
为更加翔实地呈现《甘誓》涉及的战车与马等物质条件在历史上出现的大致年代,我们采用一张图表,内容包括12个年代相当于夏朝初年(公元前21世纪)以来,地望在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史前遗址和商周遗址,按照年代顺序呈现如下。

表1 史前与“三代”遗址出土车马情况
为了说明表1所显示的物质文化内涵,我们需要聚焦第四重证据对文献记载的求证作用。杨泓在《中国古兵器论丛》中讨论中国战车的起源时指出:“关于商周时期使用的战车的形制,在古代文献中,尤其在《考工记》里保留有较详细的记录。但是,由于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木构的车子没有能够保留下来,人们看到的仅仅是文字记录,对具体的形制,还是弄不清楚。经学家们坐在房子里考据,也想象着画出一些图来,但是,谁也无法准确地描绘出当时车子的真实面貌。这个问题只有靠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才能解决。”(16)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杨泓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先在河南辉县琉璃阁成功地剥离了战国时代的车子,根据木痕弄清楚了它们的形状和细部尺寸。以后,陆续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孝民屯发掘了殷代的车子,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了西周的车子,在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了春秋的车子。……又在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发掘中,获得了一批记录有当时的车、马和甲胄,兵器装备的竹简。都是了解古代车子的重要考古资料。”(17)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113页。由此可见,借助一大批新出土的实物证据,今人可以充分认识《甘誓》所涉及马和战车的实物及其年代问题。杨泓共列举出土的商周两代马车21辆,其基本形制是单车辕、单车厢、两轮,车辕两旁驾二马或四马(成语“驷马难追”的出处)。战车上的乘员数量,刚好有三人一组的情况。杨泓并列举山东胶县西庵西周车马坑出土的战车加以说明,指出这辆战车上放置有两组青铜兵器,右侧一柄戈,左侧一组有戈、钩戟、箭镞、铠甲。当时一辆车上有三人,主将在左,配备武器是精美钩戟和戈;武士在右,配备戈;中央是驾车人,即文献常见的“御”。可见《甘誓》反映的战车三人制与西周的实况最吻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于商代制造车辆的论述同样值得重视。在商代考古中,作为实物遗迹的车,仅出现在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中,以殷墟车马坑为代表,总数约有60座。在殷墟以外则有西安老牛坡车马坑、渭南南堡村车马坑、滕州前掌大车马坑、益都苏埠屯车马坑和灵石旌介村车马坑等。(18)《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11页。根据这些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马车实物,可知当时马车基本结构:“都是木质双轮单辕车,辕前端有一驾马衡,载人的车舆位于辕后部轴的上方,除车轮以外,其他几个部件均附有少量的青铜零件、饰件。”(19)《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14页。据分析,商后期马车的用途为战车和乘车。前者正是本文要求证的《甘誓》夏启所言之马拉战车。“在已发现的商代晚期车马坑中,有18座放置了兵器。这种车,大概是用于作战的战车。车上的兵器大多为铜质的,少数是玉石或骨质的。有镞、戈、盾牌等。此外,还常见弓形器。”(20)《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16页。如果说作为实物的战车,目前还没有见到商代早中期的,只有商代晚期的。那么,迄今所知最早的车之生产,为何在表中确定为距今3400年的郑州商城呢?
因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郑州商城遗址的紫荆山北铸铜遗址中,发现属于二里岗上层文化一期的车轴头陶范二件(外范)(21)《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80页。,其年代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如果说商代前期已经具备制作车的技术,那么其形制、大小以及由人力或马力驱动,迄今仍为谜团。目前考古发现的紫荆山北骨器作坊遗址,所用骨质原料出自四种动物(牛、猪、羊、鹿)和人骨,而没有发现马骨。按照这种情况,尚无法推测当时已有马车。而马拉战车的可能性,也就更显得微乎其微了。真正能够看到实物的马拉战车,只有等到商代后期的出土实物。
归纳距今4000年至2500年间所有的第四重证据,古代使用马车的实证材料并不早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年代上限距今3300年左右。而有车的时代,可以上溯到郑州商城的二里岗上层文化一期,距今3400年左右。不论是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化,还是郑州的商代早中期文化,都距离夏代初始的公元前21世纪相当遥远,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夏代早期便使用马和马车。这样看,如果真有一位君王夏启,其时代不可能有《甘誓》所言的驾车作战的内容。又由于商人是颠覆夏代政权的敌对者,商代后期虽然有了马车和车战,但是商人模拟夏启发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假托夏启发出甘誓言辞者,很可能是自称“有夏”的周人,《甘誓》的成书年代应以周代较为可信。
除了以上物证优先的求证,还可以考虑将第一、二重证据作为辅助性的说明,那就是文本自身的语词证据。《甘誓》誓词鲜明体现崇拜天与天命的观念。众所周知,替天立言或借用天命的口吻,并非商人的习惯,而是典型的周人习惯。作为甲骨文的第二重证据表明,商人称天神为帝、上帝,陈梦家等学者都曾论证过这方面的语言习俗情况。他认为西周人发明呼天言论,用来替代商人的上帝观念。陈氏《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结论之四说道:“商周并有天神观念,并同以天神能降丧乱施福祐。然商人之帝为有权势之大自然,诸凡生活上之供给咸依赖之,故商人之帝为生活上之主宰。周人以天威可畏,恒祈年寿福佑于祖考,而以上帝与天子为统治邦国之两重元首,视天子受命于天,故周人之‘天’若‘上帝’为政治上之主宰。”(22)《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0页。
陈氏还列举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用词习惯,认为商人仅称天神为上帝,至周于上帝之外,更以实质的“天”为天神之代称,《大盂鼎》“天翼临子,法保先王”,《大豊簋》“天亡佑王”之天即上帝天神也。盖商人神人不分,对天神先祖唯一混沌在上之观念而已,周人则确指天神先祖所居者为“天”,而以天概括天神。(23)《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9页。《大盂鼎》和《大豊簋》都是西周青铜器,作为甲骨文之后的二重证据,这样的语词习惯特征,可以作为辅助性的证据,说明《甘誓》在观念和措辞方面不符合商代的实情,而对应的是周代的语言习俗。从西周金文中“格于皇天”的宗教套语,到《甘誓》“天用”“天罚”一类代天立言习惯,再到《论语》“知天命”说和屈原“天问”说,乃至当今百姓依然挂在嘴边的“天哪”和“老天爷”,某种一以贯之的信仰底蕴,还是依稀可辨的。
四、《山海经》夏启叙事的真伪辨析
《山海经》是当今学界公认的神话书,在《四库全书》的分类中列于子部小说家一类。因为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公开表示对《山海经》内容的不信任,自古就没有学者将其当作史料引用。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从来不会考《山海经》的任何内容。如今,我们却要一反常态,专门辨识神话书中的信史内容,所依赖的还是第四重证据。按照“物证优先”的研究原则,本节只涉及《山海经·海外西经》所叙夏启乘龙操玉环佩玉璜的仪式之舞的关键细节。
启作为禹之子,是中国华夏王权“家天下”(父子相传)的始作俑者,同样以玉礼器作为夏王朝最高统治的权力标志物。不过夏禹的神圣礼器标志为玉圭,夏启的则是玉璜。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郭璞注:“半璧曰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24)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09页。
笔者参照《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叙事,指出史前时代的玉环玉璜皆为沟通天人之际的神圣媒介物,其神话信仰的功能类似龙。夏启多次上天,其升天工具便是乘龙和佩玉璜。将两个叙事文本组合分析,可归纳出华夏国家天人合一神话观的基本范式,以三个相关母题为表达,即升天者—乘龙—佩玉璜。再参照《周礼》所讲的国家礼制,玉璜是先秦六种主要玉礼器之一,其形状为半璧形。华夏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一件权力符号,就叫“夏后氏之璜”,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政权更替,一直传承到西周王室分封诸侯时作为周公之子伯禽分封鲁国时的镇国神器。这也是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制作传国玉玺最高权力符号的原型。就此而言,《山海经》有关夏代开国帝王启以龙和璜为通天通神符号的叙事,比《尚书·甘誓》的驾马车作战叙事更具有历史可信性。因为早在距今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时,玉璜已经在中原地区登场。更早的物证则是北方兴隆洼文化的玉弯条形器和南方河姆渡文化的玉璜,其历史的深度分别是8000年和7000年。相当于夏朝初年的距今4000年前后,本文上节列表呈现的14个史前遗址和商周遗址,如陶寺遗址、石峁遗址、喇家遗址、王城岗遗址、石家河遗址、二里头遗址等,均有史前玉璜出土。这就充分证明相当于夏代的高等级社会普遍使用玉礼器玉璜的情况。不论夏禹夏启作为国君是否存在,玉璜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玉礼符号标配,这就是能够佐证《山海经》夏启叙事中真实信息的大传统物证。
从神话信仰传播角度看,玉璜及相关的虬龙神话观率先进驻中原,并在史前中国大部分地区获得广泛的认同,由此开始奠定华夏统一的认同基础,这是笔者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第九章第五节得出的结论(25)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34-356页。,本文仅引作《尚书》虞夏书夏启叙事辨伪的对照物,不用再详细展开。
五、结论
将《尚书》与《山海经》的夏启叙事对照起来看,原来被公认为史书的内容可能是后人伪托,而神话书《山海经》却包含更符合历史实际的内容。夏代如果存在,那时不仅有玉璜,而且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因为不存在马车和车战的可能性,《甘誓》的誓词就不可能出自夏人手笔,显系后人假托。四重证据法的物证优先原则,在此得到了很好的学术应用经验。
本文没有涉及夏禹或夏启铸九鼎之事,这个说法在古代流传久远,但同样经不起考古出土物证的检验。古书中任何相关夏朝的金属物叙事,如今都需要持审慎态度。距今3700年的二里头遗址二期文化之后,才出现冶金器物零星出土的情况。相当于夏初的距今4000年以上,唯有中原以西和以北的遗址(齐家文化遗址、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存在零星的小件铜器,根本不可能有青铜鼎。九鼎传说虽然在历史上流传极广,家喻户晓,但显然也是商周以后的神话再创作,并不具备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条件。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相对较晚,文献中有关远古帝王玉礼器的叙事,则可以根据出土文物的情况加以一一辨析,求证真伪,辨明虚实。
玉璜的历史有七八千年,这根本不是《尚书》为首的古代经典知识体系所能企及的时间深度。《山海经》保留这方面的更丰富信息,可延伸到史前史知识的考古文物参照方面。这样的新知识条件,是古史辨派的时代所不具备的。需要当代学人与时俱进地加以拓展和不断更新。
在禹或启的夏代之初时,中原地区会有马拉战车吗?如果考古学就此给出基本否定的意见,就可通过四重证据法的物证方面,对夏启甘誓的可信性一票否决。因为殷商时期才出现马和车,《甘誓》所言内容完全不可能发生于夏代初年,而应当出自周人的伪托之作。《甘誓》的实质不是散文,而是神圣口传文化的誓言话语之标本,其真实可信的部分,是远古社会政教合一与军法颁布的誓仪语境。
在夏代历史的探索方面,以往有许多学人希望求证人物的真伪虚实,但这些努力尚未取得任何公认的结果。今后的研究如果能够贯彻“物证优先”原则,聚焦现有学术条件下相对而言能够求证的物质文化方面,暂放弃或尽量回避不切实际的认知目标,以免继续放任学术上人力物力的无休止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