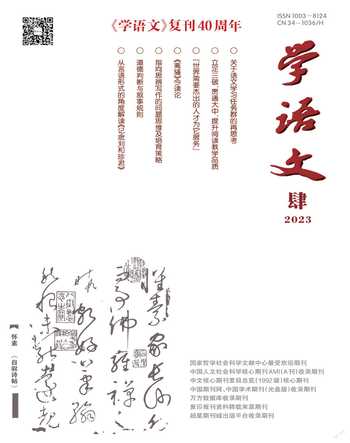从言语形式的角度解读《记念刘和珍君》
摘要:《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的一篇写人记事的纪念性散文,由于先生在文中寄寓的情感较为复杂,再加上鲁迅式独特的言语形式和表达手法,所以该名篇一直是中学生学习的难点。若能从特殊的言语形式入手,指导学生通过比较、还原等路径,梳理出鲁迅在文中曲折强烈的情感变化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读懂文本、读懂鲁迅,并掌握通过言语形式解读文本内涵的阅读方法。
关键词:《记念刘和珍君》;言语形式;教学解读;文本内涵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两周后,为纪念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却被残暴屠杀的刘和珍而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该文现被编排在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教材中册,位于“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的学习任务群。语文教材虽经多次修订,但《记念刘和珍君》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熟悉面孔,其经典的教学价值不容置疑。
经典常读常新,经典的教学也应常教常新。在最近一次教学该名篇时,笔者发现文本中有许多有意味的言语形式,主要有避简就繁的遣词、一再重复的语句、春秋笔法的运用、语气脱节的标点和自相矛盾的表达,其承载着鲁迅复杂而强烈的思想感情。教学中,笔者指导学生揣摩、探究特殊的言语形式,思考其异于常规的表达中所蕴含的情意,充分利用激趣、设疑等手段,促使学生思维爬坡,深入文本与作者、同伴对话,最终师生在一定程度上读懂了鲁迅,并学会抓住言语形式进行文本解读的阅读方法。
一、避简就繁的遣词
文章开篇,鲁迅写道:“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中华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但鲁迅为何用民国来纪年?事实上,在鲁迅的年代,已经有了公元纪年的用法,比如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就有“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这样的表达。另外,《记念刘和珍君》写于1926年的4月1日,按照一般表达,完全可以省去年份,同时代的读者也不会产生误解。亦即“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从语言表达简洁层面考虑,要么写成“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要么就直接写成“三月二十五日”。
如何解读这一反常的言语表达形式?笔者指导学生从“中华民国十五年”这一短语来分析,首先“十五年”说明中华民国的成立并非一朝一日,而是长达15年之久了;其次,现在是什么朝代?早已不是过去腐朽的晚清时期,而是“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先生曾对“民国”作过阐释:“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1916年孙中山在上海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讲中对“中华民国”作过全面阐述:“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華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国民者,民国之天子也。”结合这个阐释,学生不难发现,鲁迅用“中华民国十五年”的真实用意:现在都是中华民国了,并且是中华民国15年了,在国民做主的国家,在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家,执政府门前竟然发生屠杀徒手请愿民众的惨案,真是骇人听闻,不可思议。这样的政府早已名不副实,居心叵测。如此反常的表达中,愤激之情不言而喻,字里行间包含讽刺之意。
另外,文章第五节也有一句反常表达:“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这句话的特别之处,在于将词语有意隔断开来,形成一种断续、停顿的言语形式。将其还原成正常句式,可以表达成“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将其中三个逗号删去,与原句相比,整个句义没有任何影响。
一般而言,长句表达的情感较为舒缓、平和,短句表达的情感较为急促、紧张。之所以将词语隔断,笔者认为这与作者当时的情绪是紧密关联的。这一句反常表达后面的内容是,鲁迅还原了刘和珍等青年学生遇害的现场。可以想见,当先生在提笔再现这群中国青年惨遭屠杀的场景时,内心时多么的悲痛,以致于一字一顿,字字皆泪。这句表达是“一字一泪,是用血泪写出了心坎里的哀痛,表达了革命者至情的文字”(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的真实体现。如果将其中的逗号去掉,这一效果就会荡然无存。
二、一再重复的强调
文章在第三节对刘和珍生前事迹的回忆中,鲁迅两次提到她“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在其后第四、五、六等三节中也多次提到。笔者统计了一下,类似的表达共有五次之多。这句话固然表现了刘和珍的乐观开朗,以及心地良善等性格特点。但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多的重复表达,究竟还有没有别的用意?
笔者指导学生从文本上下文中来揣摩鲁迅反复表达的本意。在第四节,鲁迅先生不无痛心地写道,“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对此事的反应,其中:“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从“三一八”惨案发生的事实来看,是段祺瑞执政府指使卫兵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但事后段祺瑞执政府竟然污蔑这群请愿学生是“暴徒”。请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且手无寸铁去请愿的“暴徒”?如此看来,段祺瑞执政府在一手制造血腥惨案后,非但没有反思、认罪,反而为自己的暴行找借口。对执政府这一欲盖弥彰的丑恶行径,鲁迅没有针锋相对地加以揭露,而是通过五个重复句,以四两拨千斤的笔力揭穿了反动政府为己遮羞的谎言,使其罪恶昭然若揭。
三、春秋笔法的运用
散文的第五部分,鲁迅给读者还原了刘和珍、张静淑和杨德群三位中国青年遇害的现场。其中,对三人中弹的情形作了详细的说明:刘和珍“(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张静淑“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杨德群“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按照常理说,刘和珍等青年学生在执政府门前无辜被害,这已经令鲁迅悲痛欲绝,鲁迅不应该也不忍心再详细地描绘刘和珍等人中弹的情形。
那么,鲁迅为何要详细地还原烈士遇害现场,尤其是详细描述身体中弹的部位呢?笔者认为,要指导学生分析三位烈士在什么情况下中弹的,有助于理解作者这样写的目的。刘和珍是“(子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杨德群是“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这说明是从背后中枪的。背后中枪意味着什么?还原请愿现场,大概有两种情形:一是刘和珍等人被包围枪杀,一是被追赶枪杀,这就排除了请愿群众与卫兵因为正面肢体冲突,而导致擦枪走火误伤的可能。另外,张静淑中的四枪中“其一是手枪”,这一句格外醒目,发人深思。众所周知,在当时,手枪不可能是普通卫兵所能配备的枪械。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很显然,鲁迅通过烈士中弹情形的详细描写,曲折地告诉读者,这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屠杀,绝非是因卫兵自卫而导致的一场意外流血事件。在本节中,鲁迅叙述时,态度很冷静,情绪很平静,但字里行间却饱含深意:这是一场血腥的谋杀、虐杀,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
这段关于青年烈士遇害现场的还原性文字,鲁迅没有表达任何情感情绪,但义愤之情已经蕴含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之中,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重视的“实录”——寓褒贬的春秋笔法的运用。
四、语气脱节的标点
文章第四节是对“三一八”惨案的概述,其中有一处标点值得探究。“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的解释是请愿学生是“暴徒”,接着有人为其站台,说请愿学生是“受人利用的”。原文如下:
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我们发现,这两句句式结构、内容均相似,但为何前面一句用“!”,后面一句用“。”?按照常理来说,两句都用“!”,都使用感叹语气,既保持了句式的整齐对称,又能传达出鲁迅先生出离的愤怒之情,即改为:“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但是鲁迅为何反常地使用句号呢?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来分析,段祺瑞执政府一手制造“三一八”惨案,但为了遮羞和掩盖罪行,故意往请愿青年学生身上泼脏水,污蔑学生为“暴徒”,言外之意即是,开枪镇压“暴徒”是政府维持秩序的分内之事,合情合法,无可厚非。对段祺瑞执政府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行径,鲁迅愤怒达到了极点,于是用“!”表达自己这种强烈的谴责。然而,更为无耻的是,为段祺瑞执政府摇旗呐喊的反动文人又站出来,污蔑青年学生是“受人利用的”,嫁祸他人,企图混淆视听,转移民众关注的焦点。对反动政府及反动文人这一唱一和的卑鄙行为,鲁迅已经失望至极、愤怒至极。若果从生活常识出发,我们便会发现,第二句不使用“!”,使用陈述语气的“。”,恰恰是“愤怒的情感达到顶点的回落,是顶点的极致。有生活体验的人都知道,气愤至极是无语,悲痛至极是无语。”[1]正因为如此,第二句用“。”是妥帖的,与鲁迅此时因悲痛而无语的情绪匹配,如果用“!”,反而显得别扭。
另外在本节最后一段,也有一句类似的用法:“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段末之所以不用“!”,也是因为情感升至高潮后回落,表达了鲁迅在反动政府屠刀加钳口术的双重统治下,民众沉默不语、衰弱不振的无奈和痛心。
五、自相矛盾的表达
通读《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我们会发现鲁迅一方面说“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另一方面又说“我实在无话可说”,给人一种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感觉,这类自相矛盾的句子在文中共出现了7次。如此密集的自相矛盾的表达,鲁迅究竟是“说(写)”,还是“不说(不写)”呢?鲁迅先生使用这样的言语形式,究竟要表达怎样的情感呢?
笔者认为,探究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达,有助于梳理出作者情感变化的脉络,让学生真正读懂鲁迅在本文中寄寓的复杂情感。第一节第二自然段中,鲁迅写道:“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文章开端,因为程毅志的劝说,鲁迅回忆了刘和珍生前喜爱看他的文章,并且在艰难生活中依然预订《莽原》杂志等事迹后,于是说了这句话,体现出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但在第三段,鲁迅以“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开端,因为反动政府利用屠刀加钳口术来统治民众,无耻至极,让鲁迅极为愤怒,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憎恶和愤懑。这里就呈现出情感上的矛盾:鲁迅觉得为死者“写点东西”,没有必要,没有太大的意义,一是死者没有在天之灵,不能因此而获得安慰;二是对于生者也“只能如此而已”。对于这一点,孙绍振先生分析道:“这里正面表现的似乎并不是愤怒,而是无奈,于事无补,似乎很消极的样子。这显然不是感情的全部,仅仅是他感情的表层,或者说内在感情相反的一种外部效果,显示内部悲愤如此强烈,以致一般的抒写不足以显其志”[2]。笔者认为,这是非常精辟和深刻的解读。
在第二节中,鲁迅两次写道“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在“庸人”的世界里,时间的流逝会让他们淡忘一切,包括烈士们的流血牺牲,鲁迅觉得有必要写文章纪念烈士,提醒“庸人”勿忘历史,记住历史。两句同义反复,表达了鲁迅作为“战士”的责任感。第四节里,鲁迅指出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和有恶意的闲人流言,出人意表;而惨案之后,整个社会禁声、沉默的现实,让自己“无话可说”,表达了愤懑之情。为了揭露惨案真相,在第五节,鲁迅以“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发端,与上文“无话可说”构成转折,从“不说”到“要说”,是欲扬先抑的手法,表达出鲁迅揭露真相、记录历史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感。在第七部分,鲁迅用“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收束全文,哀痛达到了极点,一腔悲愤意犹未尽,反而无话可说、无可诉说,此时“无话”胜“有话”。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能感受到鲁迅在文中表达的情感是异常复杂的:“对学生有爱,对段政府有恨,对流言家有恨,对大众庸人有失望,这些感情混杂在一起,也就是哀痛的、悲愤的、激昂的、仇恨的、失望的复杂感情,但表达时处于要说又说不出话来之间。”[3]59而这种复杂的感情,正是借助“說”与“不说”表面矛盾的言语形式来体现的。本文感情抒发之曲折,诚如孙绍振先生的透彻分析:“鲁迅反反复复抒写的感情,从性质上来说,是悲痛、悲愤、悲凉和悲哀的郁积。从表现形式来说,力避尽情直遂,情思在曲折中展现。这种曲折还是多重的,写得沉郁顿挫,回肠荡气。”[2]
中学生反映说鲁迅的文章难懂,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教者若能从先生作品中有意味的言语形式入手,指导学生去悉心揣摩,发掘出文本内涵,读出特殊言语形式背后蕴含的真意,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读懂鲁迅,并掌握切实可行的阅读方法,提高阅读兴趣,提升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周旭东.《记念刘和珍君》的教学究竟“难”在哪里[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旬),2013(7).
[2]孙绍振.杂文式样抒情:在曲折的逻辑中深化——读《记念刘和珍君》[J].语文建设,2010(3).
[3]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等编著.语文必修①教师教学用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作者:童志国,安徽省铜陵市第十八中学高级教师)
[责编:张应中;校对:尹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