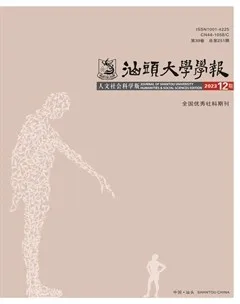“第二个结合”语境下“四个自信”的生成与发展逻辑
黄荣琴 崔发展
摘 要: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真理力量和文化底蕴,构成了“四个自信”自洽一体的内生性枢纽和必然逻辑。主要体现在经由百年的历史实践,“第二个结合”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助力了一次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形成了通古联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造福世界。新时代继续以“第二个结合”强化“四个自信”,有利于续写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新章,创造更加令人瞩目的中国奇迹。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四个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23)12-0081-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國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进一步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2]9。同时,“‘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2]8。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法宝,其逻辑地内嵌于“四个自信”的历史生成过程。从“第二个结合”的角度回溯“四个自信”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为理解和巩固“四个自信”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历史主动,以更加雄厚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凝聚复兴伟力。
一、道路逻辑:“第二个结合”
推动中国道路行稳致远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3]1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实践,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华文明根本精神的独特发展道路,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3]234。
“第二个结合”指引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先进分子准确把握住了世界历史潮流的脉搏,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连贯性融入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实践,构建起“近代中国往何处走”的全新思路。然而,受“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影响,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城市中心论”和“正规阵地战”的策略,成为导致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从“吃了先生的亏”[4]的事实中吸取经验教训,尝试辩证地从历史和诸子百家中汲取思想智慧以脱离革命困境。毛泽东认为,儒家思想“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5]。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引用了“黄巢起义”以及晁盖、宋江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等,提出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科学方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中,毛泽东两次引用孙武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阐明了朴素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辩证法意义,正确处理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创造了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的实践价值哲学;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分析经济发展关系时,毛泽东引用孟子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反对从普遍性出发、忽视特殊性的教条主义,通过“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6],围绕中国革命实际和农民运动的经验,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经济观和文化观,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因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实践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道路自信发轫的重要线索。
“第二个结合”指引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的成立充分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敏锐觉察到,照抄苏联模式容易走向“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7]的困境,指出要“开动脑筋、有创造性”地找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8]557。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要切实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中国的”“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期探索的一个主要标志。“中国具体实际”事实上包含了中国文化这一重要组成部分,隐含着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进行结合的现实要求。毛泽东指出“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8]245,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其进行批判总结。通过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结合实践,我们党实现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科学解决了独立自主与借鉴他国经验的关系问题。在继续向着纵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一直以来实事求是地看待传统文化的重要经验,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9]335,指出既要肃清封建余毒,也要把我们的文化遗产继承下去,以“我们祖先的成就”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9]90,同时要用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以“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9]212的原则对待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9]111,使其精华成分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服务。
“第二个结合”指引中国共产党坚定自我开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之“新”体现在经由“第二个结合”的百年实践,中国实现了制度层面的“社会主义”与文化层面的“中国式”的高度统一。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了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关系,承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围绕时代课题,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1]7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传统文化中“反者道之动”“内外调和,邪不能侵”等思想,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中国与世界、党内与党外、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重要关系;通过对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被赋予了“天下为公”“以和为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精髓,并集现代化因素、社会主义因素、中国文化因素三者于一身,开辟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向作了积极引导,实现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融通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创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价值理念和思想智慧,是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的精神支撑。
二、理论逻辑:“第二个结合”
推动理论创新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0]。具体来讲,党的百年理论创新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以深刻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同时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丰富和发展先进理论的精神创作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和独具中国风格的民族话语形式。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加以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1]。推进理论创新是增强理论自信的不竭动力,“第二个结合”则为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立足点。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12]408。强调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12]373,“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12]381。这些论述表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具备了正本清源的主观意识,既守住了马克思主义之“正”,也成功迈出了尝试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发展和完善的重要一步。基于革命建设的实践,毛泽东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3]534的历史命题,强调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13]533,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现方式、具体之道和发展形态的特定含义。这一历史命题是“第二个结合”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具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4]的集体自觉和思想共识。在“原则性和灵活性”[15]相统一的原则指导下,通过创造性地以“实事求是”的传统概念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以“知行合一”的传统哲学理念阐释“实践-认识”辩证关系原理,以中国古代先贤的“矛盾”哲学阐释对立统一规律等,毛泽东身体力行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著作,由此汇集而成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历史化、民族化和具体化,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推进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承接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力,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形成了一条理论创新突破的历史轨迹。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尚变求新”理念,用“解放思想”补充和完善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使二者达到了高度科学的辩证统一;将共产主义社会特征与传统文化中“小康”概念相结合,以“三个有利于”的时代话语赋予传统文化以现实性和进步性。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理政智慧,提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从党的建设的高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充分发挥了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本质,也体现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思想运用到当代,提出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通过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和洽”“万物一体”精神,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通过扬弃传统“民本”思想,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日新月异的实践发展需要,坚持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粹,以科学的理论认知和高度的理论自觉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不变与变”的辩证法,适时提出要继续推进“第一个结合”的优良传统,同时立足于传统文化本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源力。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广泛引用传统文化经典用语,以中国文化的独有气韵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德不孤,必有邻”“言必信,行必果”等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党升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们党继续发扬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等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我们党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以“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政者,正也”等论证说明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要求,我们党将党的自我革命推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16]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并未成为束之高阁的典籍,反而因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而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党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三、制度逻辑:“第二个结合”
推动中国之制日臻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和目标为导向”[17],同时“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18]的科学制度体系,“既坚持了科學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3]10,以制度化的形式推动了中华民族从独立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经由“第二个结合”而产生的历史选择,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之劫难,无数仁人志士和多重政治力量在改良和革命中探寻救国于危亡的制度体系。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是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制,亦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均以失败告终。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落地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求解近现代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3]686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科学理论和中国现实相结合,通过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有关社会治理的思想资源,创新了一系列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制度设计。在规划未来社会理想之时,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学说与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思想因子紧密联系,对缺乏真理性和现实性的“大同理想”进行解释和改造提升,以阐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的使命即是领导人民经过不懈奋斗,“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汲取中国古代“尚同”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选贤”与“上同”的辩证统一,发展和完善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20]的民主集中制,为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提供了组织保障和领导力量,保证了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为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铲除了障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改造和巩固了延续千年的民族共生关系,继承了古代“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继承传统“中”“和”“生”的价值观念、兼容并包、天下共治的治理理念和“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协商民主过程中“多”和“一”的关系,创建了刚柔并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和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的历史实践,同时继承中国传统“人本”思想,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经过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中华民族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21],建构起了历史规律与文化渊源内在统一的制度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经由“第二个结合”而形成的科学安排,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邓小平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22]的重要论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本步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和国家学说,继承发展了自古以来的“大一统”理念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赋之以社会主义的崭新内涵,使之与国家统一的制度取向高度融合,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其他制度类型的独特制度优势。如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提出“一国两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优势等。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健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付诸了一系列努力,如继承传统“天下为公”的精神和“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理念,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通过继承传统的“为政以德”“以法治国”等政治准则,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治理效能;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达到“货殖厚生利天下”之目的,创造性地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度认可和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认识,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和思想精华,在巩固制度价值的同时培育党和人民的制度自信。如,汲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思想,坚持和完善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吸收“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崇法精神,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继承“亲人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23],坚持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承上所述,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二个结合”,将“以文化人”的逻辑延伸至提升现代政治制度亲和力和创造力的时代实践,极大地强化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色彩,使“中国之制”为推动“中国之治”迈向更高境界提供更为有力的制度支撑,完成了世界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四、文化逻辑:“第二个结合”
推动中华文明造福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是文化自信。”[24]在党和人民伟大革命斗争中孕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环境、条件和任务下对党的理论和文化逻辑进行的调整和适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独特的中国文化性格,勾画出党和人民文化自信不断提升的历史轨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提出之后,中国共产党纠正了长期以来党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案头哲学”的倾向,同时也纠正了一味拒斥传统文化的态度,通过理性批判和辩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创造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毛泽东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13]663新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3]698,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3]708。民族的新文化是“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3]706的文化,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立和尊严,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科学的新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13]707的文化,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继承和补充;大众的新文化是“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3]708的文化,强调文化应贴近群众、融于群众,成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巨大革命性的力量。新民主主义文化“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了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3]663,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次现代转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重拾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台阶。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最新形态,“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25]。
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是上层建筑应对经济基础变化的必然趋向。毛泽东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6]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方向”和“两个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27]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针,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用于文化建设事业,将《诗经》《礼记》中的“小康”思想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构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民族复兴追求。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28]的新命题,表明中国共产党自觉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文化主体意识空前提升。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29],这些重要论述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忠恕廉明德、正义信忍公、博孝仁慈觉、节俭真礼和”的辩证继承和科学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和鲜明特质。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21]35社会主义文化,形成了承继于千年历史的民族精神和生发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时代精神,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度理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接续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文化建设实践,“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1]9,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高度,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担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和部署,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三个自信”扩充到“四个自信”,从“一个结合”上升到“两个结合”,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升华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变化深刻体现了其对于中国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30]“第二个结合”的深入实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一方面,“第二个结合”造就了外来文化实现本土化的成功范例,马克思主义成为助力我们党不断认识自我、反思自我、革新自我的理论工具,使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性地位更加稳固,“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实现了党和人民在精神上的高度自为和完全主动,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精神状态上走向新的自信高度。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文化走出“中体西用”的内在困境,确立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属性,激发了“公正严明”“仁者爱人”“修齐治平”“厚德载物”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能量,并由此衍生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16。这一价值是响应时代呼唤的重要产物,具有超越国度、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为将现代化從一种消极对立性逻辑转换为一种积极建设性逻辑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对于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和启示。
结 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民族坚定“四个自信”、持续向上向好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实践。深入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在“四个自信”之历史生成中的定位和意义,有利于我们以更加积极的历史主动性和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探索面向未来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创新。以“四个自信”为依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以更加自信的步伐走向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38.
[5]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33.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7]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31.
[8]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10.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8.
[12]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3.
[15]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6.
[1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
[17]肖贵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J].新视野,2013(5):9-10.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9.
[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9-1471.
[20]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2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2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2.
[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20.
[2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25]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19.
[26]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5.
[27]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4.
[28]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0.
[2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
[30]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86.
(责任编辑: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