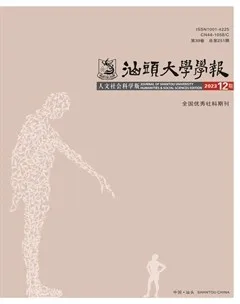《民法典》视域下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者的“合理核实义务”
周志远
摘 要:《民法典》第1025条、第1026条所构建之规则体系,给予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者抗辩保护的同时,要求行为人在言论严重失实的情况下承担合理核实义务以作平衡。解释论上,确定承担合理核实义务之主体时,应注意将无新闻资质的社会公众纳入“舆论监督”者、对“等”采狭义理解、降低“为公共利益”的证明门槛。行为人应承担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证明责任,但前提是权利人证明被诉言论有“质”的失实。第1026条实为确定合理核实义务强度的因素列举,其逻辑理据可整合为实质信源原则、“具体人”原则、利益衡平原则。具体运用各因素时宜采光谱化的思考模式,在利益衡量基础上吸纳比例原则思想。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之判断属独立问题,可类型化出征询权利人、客观报道、行业惯例、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等典型情形便利裁判。
关键词: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公共利益;合理核实义务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23)12-0067-14
一、引言
媒体为公共利益实施监督报道影响他人名誉的民事责任问题历来是侵权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并且在进入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后不断对既往法律规则提出新的考验。其不仅关涉传统名誉侵权案件中无法绕开的“名誉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而且涉及被诉侵权信息所承载之“公共利益”的考量。域外主要立法例多力求构建可平衡两造主体、三种利益的规则。例如,回溯至上个世纪,德国、西班牙、比利时等一部分欧洲国家的有关判例即已承认新闻从业人员可能“没有真相义务”,即使报道内容客观上是错误的,但只要已经进行了“足够的审查”,便未必会因此承担责任[1]。向來偏向“名誉保护”的英国法,亦曾于世纪之交的Reynolds v Times Newspapers案中,确立了关注媒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所谓“雷诺兹抗辩(Reynolds defence)”[2]或称“雷诺兹特权”(Reynolds privilege)这一抗辩事由①。雷诺兹抗辩包含两项要素:被诉言论关乎公共利益、被告在发表言论时负责任地行事(acted responsibly)[2],被告人可证明之以主张免责。
我国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新设第1025条、第1026条,规定在名誉权侵权案件中,行为人得以“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为理由抗辩,但是有三项除外情形。“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即为除外情形之一种。第1026条则规定了认定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时所应当考虑的因素。第1025条第一款与但书第二项、第1026条协同一道,构建起以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人“合理核实义务”为核心的,平衡新闻舆论与名誉保护的中国民法典方案。此规范之理论和实践意义至深且巨,然对于“合理核实义务”之承担前提、性质、举证责任、认定方法等解释论课题,实践与理论中仍然争议颇多,亟待澄明。
本文即不揣浅陋,循“承担合理核实义务主体之确定、合理核实义务强度之确定、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之判断”的思路,尝试疏方解之。
二、行为人承担合理核实义务之前提
(一)行为主体的类型与界限
1. 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的二分
明确哪些主体享有可援引第1025条之抗辩的权利、承担法定的合理核实义务至关重要。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就“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这一表述,曾有部门建议改为“新闻监督、报道”[3]。该建议或意在避免概念内容的重合,毕竟在通常观念中,监督之责主要由新闻行之,但该建议最终没有被《民法典》采纳。事实上,从客观解释论的角度,本条之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的二分可能深具意义,对其之理解可能关乎一般社会公众的为公共利益之言论能否被纳入本条适用范围。
“报道”是“新闻”的形式,而“信息”是“新闻”的实质[4]。尽管“新闻”在理论上有着众多定义,但通常可以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5]。然而,并非所有对于新近发生事实与信息的报道都属于法律规范层面的“新闻报道”。在我国,从事合规新闻出版活动需要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相关管理在规范上呈现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区分的局面。针对传统媒体,新闻报道者应遵循《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新闻出版许可证管理办法》等规范。针对网络媒体,则有《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规范公布施行。其中,《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7)第2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定所称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通过传统媒体从事新闻出版活动,以及通过网络媒体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定义下的新闻信息服务,均需要取得相应的资质。易言之,我国现行规范体系下的“新闻”概念系资质媒体进行的新闻报道。
而在我国以往的法规范用语层面,“舆论监督”通常与“社会监督”①或“群众监督”②相区分而存在。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多部法律中,都直接强调要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可见既往法规范体系下的“舆论监督”这一概念主要与资质新闻媒体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容易导致这样一种解释结论:“舆论监督”的主体应是资质媒体,“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的区别仅留下并不显著的新闻内容主题之分,而一般社会公众的言论只能通过个案判断能否被解释入“等”中。应该认为,此解释结论于《民法典》第1025条的语境下并不妥当。一方面,考虑到法学方法论上的“法概念的相对性”,表面相同的用语在不同的法律中本就可能有不同的含义[6]。另一方面,承认非资质媒体可以是此处“舆论监督”的主体没有超出“舆论监督”的日常语义,并且有着强化一般公众正当监督权行使的充分价值。此外,在多部法律法规中强调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义务也仅是对于资质媒体已有的法定义务的再强调,并未排斥其他主体进行舆论监督。同时,司法实践中已有诸多判例将资质媒体以外的为公共利益言论纳入了本条的适用范围中①,公众舆论的作用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如今逐步得到更多关注。
因此,对《民法典》第1025条“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一种相对合理解释是,这里的新闻报道者指向具有相应合规新闻资质的主体,而舆论监督者包括资质媒体和不具备资质的一般社会公众②。正确理解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二分的价值不仅在于将为公共利益进行监督的公众言论纳入第1025条之适用,还在于提示考虑到资质媒体有着相应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因此其承担的合理核实义务强度可能与一般公众有别。
2. “等”的狭义理解
对于“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中的“等”该如何理解,有观点主张其属于“等外等”且不应严格限定行为,无需与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具有等价性,甚至“属于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即为已足。因为《民法典》第1025条确立了类似英国法上的“公正评论抗辩”,而英国法已然去除了其对于公共利益的要求。如此可保护信息时代“每个公民享有的正当的言论自由”[7]。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摆脱“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这一文义限制而径行向比较法上的“公正评论抗辩”靠拢在解释论上显得较为勉强。依其观点,甚至出于私人恩怨的言论在某些情况下都可能被纳入“等”中,这种结论显然有失妥当。
“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仍然是本条的核心,在解释“等”时不能脱离这一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向人大代表所作民法典草案说明报告中曾指出,第1025、1026条旨在“为了平衡个人名誉权保护与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8]。其表述中的封闭列举为“等内等”的解释方向提供了助益。即使要将“等”解释为“等外等”,也必须强调行为与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的等价性。
在法典编纂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2018年3月15日稿)[9]将该条表述为“行为人对他人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正当批评、评论,或者实施其他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维护公序良俗行為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后“对他人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正当批评、评论”被删除。事实上,此类行为通过解释入“舆论监督”概念或者强调其具有等价性而纳入第1025条之范围并无太大障碍。而《民法典》通过后,不少判例将银行在提供贷款时对于冒用他人身份者的材料未加充分审核,致使被冒用身份信用评价受损的情形亦纳入第1025条之适用③,此做法则有所不妥。征信评价问题与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不具有等价性,应依据《民法典》第1030条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及其他相关规范。
3. “为公共利益”
在《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一次审议稿)》中,曾有“行为人为维护公序良俗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表述,后“为维护公序良俗”被删除,并最终被“为公共利益”所取代。考虑到“新闻报道、舆论监督是为保障媒体监督权、公民知情权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传统民法对公序良俗的理解并不完全重合[10]。且使用“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概念亦是域外通行做法,应当认为“为公共利益”之表述更为妥当。
由于“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属于《宪法》赋予公众了解公共信息、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途径,其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定位本身附有公共属性”[11]。故通常情况下被告仅需提供证据证明自己行为系新闻报道或舆论监督,即可初步完成“为公共利益”的举证。有观点认为有关明星的娱乐新闻信息不能属于“为公共利益”[12],对此应当指出,娱乐明星等特殊公众人物的监督尽管常以“绯闻”等受争议的形式呈现,但这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公众对于娱乐明星的道德行为期待。对其进行新闻报道或舆论监督,仍然可属于“为公共利益”。惟此处“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较低,从而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者对此类信息可能负有更高的“合理核实义务”。此外,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行为人因收受金钱、出于私怨等原因而为信息传播,则可能意味着报道者“主观意识”上“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13],进而难以被认定属“为公共利益”。
4. 新闻舆论信息生产视角下的行为主体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使得新闻生产从理念到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4]。区分传统传播媒介与网络传播媒介,循新闻舆论信息生产链条,可对行为主体进行清晰地梳理。
就传统媒体维度而言,其所涉主体主要包括报业出版者、期刊出版者、广播电视公司等①。从新闻信息生产流程链条角度观察,一篇文章或一则广播电视消息还会涉及供稿者、编辑审核人员。其中编辑审核人员属于媒体机构内部人员,其行为系职务行为。供稿者既可能是隶属媒体机构的人员,也可能是其他社会人员。若隶属新闻机构的供稿者、编辑在进行职务行为过程中未尽到本条的“合理核实义务”,则其所属新闻机构为可能的责任主体。供稿的其他社会人员若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则可能与新闻机构为共同被告。如果采编活动涉及从特定民事主体获取信息,则该民事主体作为“信息提供者”在如提供虚假信息等情况下也可能承担侵权责任[14]。对于报纸期刊印刷者与出租销售者,在域外法上存在承担侵权责任的可能,但条件往往比较严格。例如英国2013年诽谤法第10条规定有“法院无权审理和裁定对非被诉言论的作者、编辑或出版者提起的诽谤诉讼,除非法院确信对作者、编辑或出版者提起诉讼不合理可行”。即使不满足第10条的条件,被告也可能存在被称为“无辜传播”(Innocent dissemination)的抗辩事由[15]。文义上看,“印刷、出租销售”等行为与“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仍有距离,不应被纳入“等”的范围,此二者并非第1025条之适用主体。
此外,对于转载者。可以解释入“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的同时,通常认为其亦应当对转载内容尽到合理核实义务[12]。尽管曾出现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一次审议稿)》的“行为人对转载的或者他人提供的事实是否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可以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中“转载的”一语后被删除,但不宜就此径行认为转载者不必承担合理核实义务,因为“转载的”本不必被特别规定,而可以纳入“他人提供”的含义内。规范层面,原新闻出版总署制定施行的《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①《新闻出版总署关于采取切实措施制止虚假报道的通知》②等规范中均包含要求新闻机构严格落实对转载内容进行核实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亦有诸多承认转载者具有核实义务的判例③。转载者承担责任的理据一方面在于其客观上扩大了被诉言论的传播范围、加深了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于其读者可能出于对于转载者的信赖而错误地相信侵权言论。此处原始发布者与转载者之间的关系、信息来源对于媒体受众的作用程度,可能影响“合理核实义务”强度的判断,留待后文叙述。
就网络媒体维度而言,依《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5条第二款,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括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据此可参照分类出采编发布者、转载者、平台及作为舆论监督者的平台个人用户。
第一,针对采编发布服务者,《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6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许可的,应当是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其新闻信息生产流程所涉主体与前述传统媒体所差有限。第二,针对转载者。除前述转载的一般问题外,涉网络转载侵权明显呈现出易多发、传播快、影响广等特征。《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纠纷规定》对此及时出台相关裁判规则,司法实践中也普遍承认网络环境下转载者的核实义务④。第三,针对平台。单纯的传播平台不宜纳入第1025条的适用范围,因为平台的相关承担责任、提出抗辩的规则依据已有《民法典》第1194条至第119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另平台提供服务是否属于“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亦颇值怀疑。故不宜认为平台享有本条所规定的抗辩、承担本条之“合理核实义务”。第四,作为舆论监督者的平台个人用户的发布言论行为、转发行为亦可以主张第1025条之抗辩自无疑问。对于转发行为是否应当承担基本的合理核实义务,比较法上对于网络转发行为采取极端绝对保护的如美国,其著名的《通信规范法案》230条⑤规定:“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用户不得被视为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提供的任何信息的出版者(publisher)或发言者(speaker)”。但在如今名誉权极易在网络空间受到侵害的当下,此种规则的妥当性殊值怀疑。一方面,固然应当承认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互联性使得一般网络用户难以对其进行“转发”的舆论监督的信息进行非常实质的核查⑥,但“当被转发言论存在凭借转发者基本专业知识或一般理性之人的常识就能识别、就能判断的失实或侮辱、诽谤等情形”①时,其仍然可能承担侵权责任。也即,第1025条但书第二项对于网络转发行为仍然适用,只是“合理核实义务”的强度可能与其他行为有别。
(二)“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
“他人提供”一语应采宽松理解。首先对于“他人”,其包括新闻采编过程的“信息提供者”、向媒体机构提供文章的一般社会供稿者、出于职务行为而供稿的媒体机构工作人员,也包括相对于转载、转发者而言的原发布者。“提供”一词不能狭隘理解为仅仅包括他人有意识地提供给特定人(例如授权转载、在采编过程中提供信息),而应该宽松理解为,文章或信息公开后即属于已向公众“提供”,从而将运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进行新闻舆论信息创作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第35条第2款规定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进行转载的媒体,以及进行未经授权的转载行为者等也纳入第1025条但书第二项的适用范围。过于机械地理解“提供”可能得出后者反而不用承担“合理核实义务”这一明显造成法律评价矛盾的解释结论。
对于“严重失实”,直至《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第三次审议稿)》对于该要素都尚未有“严重”性要求。但事实上,严重性要求由来已久,1993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即规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同时,“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只要“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且无侮辱性内容,不构成侵权。而对于如何判断“严重失实”,有学者认为,“严重失实”是指达不到作为与“事实真实”和“法律真实”相区分的“新闻真实”的要求[13]。但此种论点仍然需要处理“新闻真实”的判断。也有观点指出,对于严重失实内容尽到合理核实义务,意味着报道的主要事实、基本事实准确[16]。但是此种情况已然可以主张内容真实作为抗辩理由。这种观点混淆了真实抗辩与合理核实义务。报道真实与否是裁判时问题,而其所言是否合理核实是行为时的问题[17]。被诉言论是否严重失实,应通过权利人举证,由法官在裁判时进行判断。其严重性一方面需要从事实的偏离程度判断,另一方面需要从此种事实对于权利人名誉毁损的重大程度,由法官个案判断。此处的“严重失实”是“质”而非“量”的概念[18],即使失实内容属于被诉言论的非主要内容,也有可能构成“严重失实”。
三、盡到合理核实义务的
性质与证明责任
(一)阻却违法的必要实质审查义务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稿》至《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第三次审议稿)》,草案均使用了“合理审查义务”这一表达。从“合理审查义务”变更为“合理核实义务”并没有非常本质性的变化,惟“核实”可以起到提示审查的要点在于“事实陈述”而非“意见表达”之作用。审查义务首先可能包含形式上的审查义务,也即在转述、转载他人提供的信息时,应做到内容、思想一致,不得添加、删减而误导受众。审查义务还可能包括必要的实质审查,也即对于事实真相的核查。具体个案中行为人所承担义务强度需要动态判断,是否尽到相应义务应结合证据认定。
对于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体系定位,如果承认违法性要件在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地位,则其为违法阻却事由[19]。如果主张以过错要件吸收违法性,则其为排除过错的免责事由[12]。两种学说在最终的法律后果上未必有实质区别,但一般认为“违法阻却事由”的说法会比“免责事由”更为精准[11]。
事实上,比上述更重要的,是对于“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一句诉讼抗辩结构的理解,这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具有关键影响。
(二)行为人应负担“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证明责任
法谚有云:“证明责任乃诉讼之脊梁”,其关乎法的可预测性。证明责任规范的使命在于“消除事实问题方面的疑问”[20]。然而吊诡的是,我国媒体名誉权侵权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却长期有着一副普洛透斯之脸孔。自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施行以来,作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理论上之通说的“规范说”便有了进一步的肯定与法条依据①。可是,即使在实证法上名誉权侵权之构成要件有着明晰规定的情况下②,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被诉诽谤事实”真伪之证明责任③的态度却仍然莫衷一是④,理论上更是有着“谁主张,谁举证”与“谁报道,谁举证”之辩[21]。《民法典》施行后,此一论争已然可以停歇,第1028条明确了权利人应当对“内容失实”承担证明责任。但是,媒体名誉权侵权案件证明责任之争并未消弭,未散的迷雾退至了第1025条之“合理核实义务”。
支持由权利人(被侵权人)承担“行为人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之证明责任的观点多来自传媒研究领域的学者及少部分法学学者⑤,其最主要的实质理由可归结至以下两点:一,在法典编纂过程中,直至《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第三次审议稿)》,仍然有着“行为人应当就其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但最终该款被删除。据此可认为《民法典》的态度是应由权利人承担证明责任;二,第1025、1026条所涉侵权类型仍属于一般过错责任范畴,应由权利人承担证明责任。而“合理核实义务”或被认为是对于过失的判断标准(其实质上是将“尽到合理核实义务”认定为否认规范,“否认规范”对应非独立抗辩的“积极否认”,不改变被否认方的证明责任[22]),或被解读为对于“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而免责”的反抗辩,并进而推导出“尽到合理核实义务”证明责任由权利人负担。
然而,立法过程中的草案文本变化本就存在不同的解释方向,删除“行为人应当就其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也完全有可能是出于该问题属于当然之理、无须法律特别规定之原因。从部分参与立法工作的相关人员态度来看,其亦坚持主张证明责任在行为人方[16]。从规范角度,对于“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一项,不宜将“严重失实”与“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混而论之。由于侵害名誉权这类“有名框架性人格权”的违法性、过错判断与侵害行为判断合一,需要进行利益衡量予以认定[23]。本条“严重失实”的意义毋宁是划定了在此种情况下,被诉行为经过利益衡量通常可被认为具备违法性,必须由行为人再行证明违法阻却事由。也即在原告证明了名誉权侵权的一般构成要件后,被告可以“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为抗辩。原告倘若能证明涉案被诉消息属于“严重失实”,被告则可通过证明自身“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作为违法阻却事由进行抗辩。这种证明责任方案更为符合利益衡平的要求,行为人是否、以何种方式进行了合理核实活动,行为人对之最为清楚。若需由权利人举证证明,可能致其诉讼负担过重[24],由行为人承担证明责任“属应有之义”[12]。
四、尽到合理核实义务判断
因素的再整合
(一)第1026条的开放构造及应用限制
有学者认为在法典编纂过程中,第1026条曾有改“可以考虑下列因素”为“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的过程,且考虑到该条为封闭式列举,故司法机关就应当且只能以本条项下的规定作为判断依据[13]。该观点殊值商榷。确立英国法上雷诺兹特权的Reynolds v Times Newspapers案中,Lord Nicholls亦曾提出了著名的十点判断因素①。然而,Lord Nicholls亦承认因素清单并非详尽无遗。赋予列举因素和其他相关因素的权重因案而异[25]。其提出的该十点因素曾经一度被部分法院错误地理解、滥用——它们将其理解为必须逾越的“十点障碍”,任一障碍都可能导致抗辩失败②,这一失误在英国2013年的诽谤法改革过程中得到反思。在2013年誹谤法替代雷诺兹案后,十点因素虽然将继续发挥作用,提醒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可能相关的主要因素,但不会是详尽无遗[25]。英国法对于因素清单错误理解导致损害公共利益、言论自由保护的上述教训值得警醒。
《民法典》第1026条虽采“应当”用语,但并未排斥其他因素考虑的介入。其以类似《欧洲侵权法原则》第4:102条规定“必需的行为标准”[26]的方式吸收了“动态系统(体系)论”的思想③。是否要求要素体系所列举的因素限定,是“动态系统论”理论上的争议性问题[27]。就动态系统论的创立者,维尔伯格的观点而言,其“能够包容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情形及其特殊的性质”[28]。德国学者Westerhoff亦指出:“要素的预先限定是不可能的”[27]。在解释第1026条时,应承认开放因素的意义,不能封闭地考虑其所列六项因素。
但是另一方面,该如何避免这种动态判断滑向恣意呢?动态系统论的一种常见阐释即在于,认为其衡量确定的要素,以此区别于对考量利益不作限定的传统“利益衡量论”[27]。而如前所述,限定要素此一路径并不可取,防止不透明的随意裁判也不必拘泥于此路径。《民法典》第1026条与被通说认为吸纳了动态系统思想的第998条一样,并未完全构建起以要素、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为支柱的经典动态体系,实则没有跳脱出利益权衡方法的范畴,属于“采取了一种比纯粹的自由法学立场和动态体系论更为稳健的论证方法”[29]。第1026条并非对“考量利益不作限定”,其示例出“应当考虑”的六项因素,要求法官必须进行考量。同时六项因素也划定了公共利益(第三、四项)、行为人言论自由利益(第一、六项)、权利人名誉保护利益(第二、五项)此三类考量利益。法官并非可以任意将关联度较低的因素填塞入第1026条之判断,而应该紧紧围绕这三种较为具体的利益进行补充。
第1026条所谓“认定行为人是否尽到前条第二项规定的合理核实义务”这一课题,事实上可分为确定合理核实义务强度与判断行为人是否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举措此二议题。但第1026条所列六项因素实则主要指向前者,除其所列第二项外的其余五项属于前者的确定因素应无疑义。对于第二项“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否进行了必要的调查”,表面上似为判断行为人是否采取了相应举措的因素,但实际上也可以解释为发表“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需承担较高的合理核实义务——需要对争议事实进行必要的调查。据此,《民法典》第1026条实为对于判断行为人承担何种强度“合理核实义务”的因素列举。而至于行为人是否尽到对应强度核实义务之判断,这一方面是特定强度核实义务的内容要求体现,同时也关乎证据材料的充分性认定。学说建构的重点在于划定典型情形,给予裁判类型化指引。
(二)确定合理核实义务强度因素的再整合
教义学乃法律人用理论阐释现行有效的法的活动[30]。《民法典》第1026条之因素列举并非没有充分理据可循,对其所确定合理核实义务强度因素的再整合,就是要对表面松散的因素列举进行理论阐释,揭示背后的价值逻辑与利益考量,提升其裁判可操作性。实证法所列六项因素可抽象规整出以下三原则:
1. 实质信源原则
信源,也即消息之来源。在新闻传播学中,有学者将新闻信源区分为作为客观事实所发出之原始信息的“一级信源”①、对“一级信源”进行收集、选择、加工,制作成可供媒介传播之新闻的传播者为“二级信源”、将新闻传播出去的新闻媒介为“三级信源”[31]。此对于传统新闻媒体的信源分类对于目下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消息传播亦是同理可用。且可将其推进一步,将进行转载信息行为的媒介称为“四级信源”。
在确定行为人所应承担合理核实义务的强度时,应当遵循实质信源原则。所谓实质信源原则,也即对于在传播活动中扮演了“实质信源”的行为人课予更重的合理核实义务,相关案件中一般以“实质信源”为责任人。实质信源②的认定,需要通过判断行为人作为传播媒介在传播活动扮演的角色,及由此所引发的信息受众对其之信赖程度等因素。
社会需要新闻媒介,首先就因为它们能满足人们获取信息的需求[4]。对于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者科以合理核实义务的理据之一也正在于其提供错误信息可能误导社会评价、进而影响他人名誉。职是之故,在此传播链条中对于受众造成决定性影响的传播媒介——也即作为实质信源的行为人,其最具可责性。在判断其是否履行了合理核实义务时,应采取较高标准的。在一条涉名誉权侵权的传播链条中,实质信源可以不唯一,存在多个实质信源的情形。例如转载相关消息的媒体较为权威③,基于其公信力对于侵权事实的背书,媒介受众的观点同样会受重要的影响。此时,转载媒体与其上级信源便同属实质信源。
相对的,在多级传播链条中处于非实质信源地位的媒介,其所负义务的要求便低于前者。《民法典》第1026条将“内容来源的可信度”规定为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即与此有关。例如,倘若被转载媒体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新闻媒体,新闻报道内容可信度较高”,则应降低“转载文章时的审核义务”①。又如,倘若行为人的信息来源于权威部门(如“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文书和公开实施的职权行为等信息来源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其一般可以此为由证明自己尽到了合理核实义务[24]。这一理由有时也被独立地称之为“权威消息来源抗辩”[32]。1998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有“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究其机理,即在于引用权威信息时,行为人在传播链条中的定位属于非实质信源。就第1026条中的该项因素,还应指出以之为理由免责并不是绝对的,不宜径行认为引用权威消息来源便“无需再考察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而应推定该事实为真实”[7]。相反,不仅在转载引用过程中的形式审查义务仍属必要,还应考虑行为人所添加的标题、导语等是否有不当之处②。一旦行为人转载过程所添加的信息足以误导受众,那么其仍属违反了合理核实义务,因为就该误导信息的传播其已经扮演了实质信源的角色。实例如在“黄仕冠、黄德信与广西法制报社、范宝忠名誉侵权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为人虽然是依據检察机关文件所做报道,但措辞不准,文章标题遗漏“涉嫌”二字,且未做后续报道、更正报道,应当追究侵权责任③。
2. “具体人”原则
民法上对人的对待向现代法的变迁中存在从抽象人格向具体的人的转变[33]。在确定合理核实义务的强度时,应遵循“具体人”原则,根据两造主体的实际情况,动态确定其应承担的义务强度。
对于行为人,第1026条明确应当考虑其“核实能力”。如本文前揭所述,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者可分为资质媒体与一般社会公众。由于资质媒体有着法定的准入门槛,享有法律上给予的便利④,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因此通常资质媒体的合理核实义务要高于一般社会公众。资质媒体据其依托的传播媒介不同,可以分为传统资质媒体与网络资质媒体。尽管在一般印象中,网络空间是更为自由的虚拟空间。但实际上,恰恰是网络空间更容易对于他人名誉产生更广泛、更严重的侵害。职是之故,网络资质媒体的合理核实义务要高于传统资质媒体。此外,由于一般社会公众进行舆论监督主要通过互联网,参考《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纠纷规定》第7条第一项,可知对一般社会公众应依据主体性质、影响范围予以区分考虑。主体性质方面,司法实践中存在将“普通网络用户的非盈利性转发行为”与职业性、盈利性行为相区分的做法[34]。应认为前者的核实义务极低,以维护公民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之行使。影响范围方面,对于所谓的“网络大V”,其“借助网络表达更为便捷、受众更多,可以说既能唤起爱心,也能煽动愤怒,乃至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舆论导向”,故应当承担更高的核实义务⑤。
对于权利人,第1026条未作“应当”考虑因素之规定。但是依据《民法典》第998条,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应当考虑”受害人的职业。对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侵权问题,理论上素有诸多探讨。在“合理核实义务”的语境下,如果被诉言论关涉的权利人公众人物属性较弱,则行为人应承担更高的核实义务。
3. 利益衡平原则
在涉“合理核实义务”的案件中,需要平衡两造主体、衡量三种利益——其一是被诉言论所指向的公共利益,其二是行为人的言论自由利益,其三是权利人的名誉保护利益。其中,公共利益的存在是行为人得以主张第1025条抗辩的根本原因,名誉保护则是要求其承担合理核实义务的理据。依第1026条规定,“内容的时限性”与“内容与公序良俗的关联性”应当被考虑。在《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一次审议稿)》中,此两项尚被合为一项,事实上,两项因素皆为从内容关注的“公共利益”角度进行的表述。如果被诉言论与公序良俗关联性比较高(公共利益的维护比较重要)、内容的时限性使得不得不立刻报道(公共利益的维护比较紧迫),则此时权利人的名誉保护利益应暂时让步,行为人无需负担过高的核实义务。例如,对于著名的范某毅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名誉权纠纷一案,一方面范某毅“赌球传闻”可能影响中国足球队、乃至中国足球的形象(公共利益的维护比较重要),另一方面“新闻报道由于其时效性的特点,不能苟求其内容完全反映客观事实”①,本案“每一场比赛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下一场比赛进程”[18],也即公共利益的维护比较紧迫,故对于行为人不能科以较高的核实义务。
然而,对公共利益和言论自由的保护不应过度牺牲他人名誉。“受害人名誉受贬损的可能性”,即提供了从权利人名誉保护利益观察的视角。《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纠纷规定》第7条第二项亦强调“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名誉受贬损的可能性”或“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与所谓“指控的严重性(The seriousness of the allegation)”相关。指控越严重,如果指控不属实,公众被误导和个人受到的伤害就越多②。此外,如果被诉言论“明显可能引发争议”,则行为人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查”,“必要”程度可能受到“争议程度”“核实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三)第1026条所列因素的具体运用
揭示第1026条因素列举背后的原则遵循属于确定合理核实义务强度的基础。它可以帮助裁判者明确诸要素同质促进或异质排斥的协同作用,但法官并非直接以上述原则裁判,而仍然要回到六项具体因素及可能的补充因素。如何具体运用第1026条所列因素,仍可能有不同处理方法。一种可能的经典主张是,确定要素各自的重要性,发现立法因素排序对于“在法律的适用中明确综合考量的权重”的引导[12]。但第1026条显然没有确定这样的权重,也很难讲既有的因素排列方式暗示了某种重要性排序——例如内容来源可信度未必就比名誉受贬损可能性重要。就更为妥适的学说而言,并非是要自负地先验确定各要素的权重,也并非仅仅粗枝大叶地强弱两分,而应该是一个光谱化的理论。其可以做到类型化确定两极的典型情况与少部分中间状态情况,也承认将中间细微变化之部分完全类型化实属力有不逮,应将其交予裁判者。
法官在确定合理核实义务强度时(尤其是针对“中间状态”情况),可以在对案件关涉利益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进一步吸纳比例原则思想。就个案事实运用比例性原则调和相冲突的权利,是利益衡量在方法论上的一种模式[35]。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已有诸多论证[36]。比例原则与利益衡量相辅相成,将比例原则作为利益衡量的指导和参考框架具有重要价值[37]。在明确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可考虑运用比例原则的分析框架与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合理核实义务”之“合理”的内涵。完整比例原则包括目的正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最小损害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四部分[38]。就目的正当性原则以及适当性原则而言,通过要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者承担合理核实义务,可以避免以“公共利益”“言论自由”的名义过度损害他人名誉。这通常具有目的正当性,考察其可以促进这一正当目的即可。就最小损害性原则而言,如果核实真相存在多种途径,在可达到目的的方式范围内择一即可,不必要求所有行为人都采取如征询直接当事人等要求较高的方式。例如,若网络资料检索与实地考察均可以达到相同的核实效果,那么通常要求其选择成本较低的网络资料检索即可。就狭义比例原则而言,应比较特定方式途径的核实成本与核实收益,要求行为人承担的核实义务强度与内容的争议程度、侵害他人名誉的可能性等相适应,不能过度苛责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人。
(四)是否尽到对应强度核实义务之判断
在动态地确定具体行为主体的合理核实义务强度后,仍然需要判断行为人是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尽义务。
有学者主张我国宜借鉴英国2013年诽谤法放弃了雷诺兹抗辩中的“负责任的媒体”客观标准,转采行为人是否“合理确信”之主观标准①的做法,在运用第1026条判断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时应该注重其对“报道内容的基本真实是否形成了合理的确信”,而非注重“查证程序是否合理”“证据材料的多寡”等[17]。但也有英国学者指出,两标准并无本质区别。如果一篇文章关于公共利益事务,并且报纸在发布文章时以及形式上的行为是负责任的,那么他们认为发布这篇文章符合公共利益是合理的。相反,如果这篇文章是关于公共利益的问题,但报纸在发布这篇文章时没有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以及负责任的形式,那么他们认为发布这篇文章符合公共利益的想法就不合理了[15]。与侵权法上“过错”的判断也存在客观化趋势类似,即使采用“合理确信”的主观标准,仍然需要从行为人是否采取了与其所承担强度的合理核实义务相适应的措施判断。
以下典型情形对于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判断具有一定意义:
第一,征询权利人。行为人是否就相关事实征询过涉案权利人,属于公认的重要标准之一②,对应较高的核实义务强度。如存在此核实步骤,一般即可认为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者尽到了合理核实义务。此标准的机理与侵权法上“受害人同意”这一免责事由相通。
第二,客观报道。如果行为人对于争议事实两方的观点都进行了初步的核实,在行文时客观地报道了双方的主张,则一般可被认为尽到了合理核实义务。在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制定实施的《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广播电视舆论监督工作的要求的通知》以及原新闻出版总署制定实施的《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中都有类似要求③。但应注意避免客观报道沦为隐藏诽谤内容的借口,行为人仍应提供履行了初步核实义务的证据。
第三,行业惯例。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其为验证信息采取的步骤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其同类别媒体对类似事实的通常核实程序、核实标准,则一般不宜进一步苛责其承担更高的合理核实义务。这某种意义上也是“给予编辑或记者的专业判断以重视”①的体现。
第四,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对于他人提供的事实,如果行为人在转述、转载过程中甚至未能尽到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导致原意遭到误解、损害他人名誉,通常应认为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规定》第7条第三项之“對所转载信息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公众的可能性”即为此意旨之体现。
结 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新媒体的兴起,为公共利益的新闻报道与舆论监督行为与其他民事主体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愈显凸出和重要。《民法典》第1025条第一款与但书第二项、第1026条协力构建起的规则体系,一方面通过给予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人“为公共利益”的抗辩保护,另一方面在内容严重失实的情况下要求行为人承担合理核实义务作为平衡。确定承担合理核实义务之主体主要通过第1025条第一款与但书第二项予以界定,第1026条则为确定合理核实义务之强度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尽到特定强度合理核实义务之判断可类型化出征询权利人、客观报道、行业惯例、基本形式审查等典型情形便利裁判认定。在可见的将来,为公共利益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者的合理核实义务之判断仍需视媒体环境的变化以因应而动,及时完善相关理论与制度建构。
参考文献
[1][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法(下)[M].焦美华译、张新宝审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18.
[2]PEEL W E, GOUDKAMP J. Winfield &Jolowicz on Tort[M]. Nineteen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14.
[3]《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420.
[4]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第八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
[5]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23.
[6][德]罗尔夫·旺克.法律解释[M].第6版.蒋毅,季红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80.
[7]李劲松.公正评论抗辩的适用要件及效力解释论研究[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3):150-151.
[8]《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14.
[9]何勤华,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89.
[10]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国民法典适用大全(人格权卷)[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370.
[11]温世扬,袁野.人格标识合理使用规则的教义展开——《民法典》第999条评析[J].法学论坛,2022(5):26-39.
[12]王利明,程啸.中国民法典释评·人格权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13]陈甦、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人格权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
[14][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M].[日]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0.
[15]NICHOLAS J, MCBRIDE & RODERICK BAGSHAW. Tort Law[M]. Sixth Edition. London: Pearson, 2018.
[16]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169.
[17]岳业鹏.论新闻舆论监督的合法界限——基于名誉侵权抗辩规则的考察[J].新闻大学,2021(3):21-29.
[18]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第7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19]王泽鉴.中国民法典的特色及解释适用[J].法律适用,2020(13):12.
[20][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第五版.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14.
[21]谢鸿飞.使用匿名信息源新闻报道侵权案中的举证责任、报道者特权和利益平衡[J].人民司法(案例),2016(29):11.
[22]吴香香.民法典请求权基础手册(进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3:25-26.
[23]吴香香.请求权基础视角下《民法典》人格权的规范体系[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4):131,134.
[24]张红.《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人格权编评析[J].法学评论,2019(1):118-119.
[25]James Price QC & Felicity McMahon. Blackstones Guide to the Defamation Act 2013[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3.
[26]欧洲侵权法小组.欧洲侵权法原则:文本与评注.[M].于敏,谢鸿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17.
[27]解亘,班天可.被误解和被高估的动态体系论[J].法学研究,2017(2):49-54.
[28][奥]瓦尔特·维尔伯格.私法领域内动态体系的发展[J].李昊译.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4):112.
[29]朱晓峰.人格权侵害民事责任认定条款适用论[J].中国法学,2021(4):49.
[30][奥]恩斯特·克莱默.法律方法论[M].周万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137.
[31]李元授.论新闻信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3(6):55.
[32]杨立新.论中国新闻侵权抗辩及体系与具体规则[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5):3.
[33][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C]//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论丛.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5.
[34]北京互联网法院涉网络暴力典型案例[EB/OL].https://
mp.weixin.qq.com/s/_QOXaIxyHTN4v0TdoPsBig,2023-8-3.
[35]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3:316.
[36]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J].政法论坛,2016(3):95.
[37]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J].中国法学,2016(2):157.
[38]刘权.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J].中国法学,2014(4):133-150.
(责任编辑: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