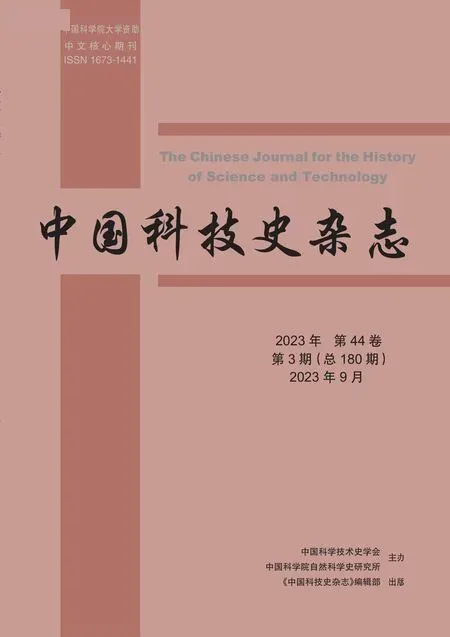导语:试析科技-外交分析框架对中国现当代科技史研究的意义
张 藜
关于科学知识、技术、物质等跨地区流动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科技史界最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每一位踏入科技史大门的从业者,或深或浅、或快或慢,都一定会读到丰硕的研究成果——既有近代及以前的中西交流史,也有近代以来特别是现当代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构成我们认识中外古今科技发展历史的基础,更是引领我们去理解不同地域的文明、文化之间如何互动的起点。
近年来,一个描述现当代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术语——科技外交,越来越常见于文字和语言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自21世纪以来,外交官、科学家、国际关系研究者、科技政策研究者等等对于科技外交在现代国际事务中的概念、实践和历史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概念界定与功能阐释(1)美国国务院科技顾问认为科技外交是国家间的科技交流,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构建建设性的基于知识的国际伙伴关系(1999)。日本将科技外交定义为“把科技和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实现共同发展”及“利用外交促进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利用科技手段实现外交目的”(2008)。法国对此的定义为“通过科技合作搭建桥梁,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及对话,其外交效用在其他官方政治对话机制失灵时将更为明显”(2013)。赵刚在《科技外交的理论与实践》(2007)一书中指出科技外交是“以主权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机构、科技部门、专门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企业等为主体,以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而开展的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等之间的谈判、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建立研究机构等多边或双边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樊春良在《科技外交的新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对策》(2010)一文中认为“科技外交是把科技发展和外交结合在一起,实现国家的外交目标和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等等。。最常被引用的定义见于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于2010年发布的联合报告“科技外交新前沿”(2)The Royal Society, AAAS. New Frontiers in Science Diplomacy: Navigating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London: The Royal Society, 2010.。该报告提出科技外交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外交中的科技(Science in Diplomacy),即依靠科技来实现外交目标;二是为了科技的外交(Diplomacy for Science),即通过外交手段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三是为了外交的科技(Science for Diplomacy),即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来促进国家间的关系。美国科学促进会早在2008年就成立Center for Science Diplomacy,2012年起又发行网络杂志Science&Diplomacy;自2017年以来,有多国陆续任命技术大使(Tech Ambassador),以处理技术发展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服务于本国发展的整体战略。这些行动标志着认可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发展人类科学技术和国家间外交关系以及在科学制订公共政策中的重要作用。
与以上科技外交实践和行动相呼应的是科学史/历史学对科技外交的历史的兴趣也正日益浓厚。仅笔者目力所见,国际科学史学会(Division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DHST)于2017年成立科技外交委员会(Commission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plomacy,STAND)(3)2017年7月,在巴西举行的第25届国际科技史大会上,会员大会审议批准成立“科技外交委员会”(Commission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iplomacy,STAND),该委员会的宗旨为:(1)促进对科学、技术和外交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历史认识;(2)设法促进对国际科学事务及其对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的影响感兴趣的科学和技术历史学家之间的合作;(3)促进科学和文化活动的组织,促进实现上述各点所述的目标。,欧洲科技史学会的会刊Centaurus、英国科学史学会会刊BJHS等学术刊物先后刊出科技外交史专辑,欧盟委员会与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多个跨国项目包括Negotiating World Research Data: A Science Diplomacy Study,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于2022年推出科技外交系列演讲“Were We Ever at Peace?”(4)详见马普所在其youtube频道推出:MPIWG Institute’s Colloquium: Were We Ever at Peace?-You Tube。,以及国内冷战史、国际关系、国史等领域的学者先后成立或组织以科技外交为主题的学术团体或机构。这些活动不仅表明了全球性的对促进科学外交反思的意识,并且呈现制度化的趋势,也表明了学术界日益关注将其历史研究与科学政策联系起来,为当代科技政策/外交政策提供学理依据甚至参与其实践活动。可以预期,科技-外交视角下的历史学/科学史研究,将是目前和未来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那么,在现当代科技史研究中,“科技外交”与传统性议题——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其区别在哪里?换言之,是否有必要将“科技外交”纳入中国现当代科技史研究之中,以及研究什么呢?笔者认为,科技外交是中国现当代科技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在继续关注科学知识、技术与物质跨地域流动的同时,将更加重视参与这一流动的主体(除了科技等专门机构之外是否有主权国家的政府、外交部门)、目的(有些交流合作的目的预设与外交无关)以及效果(是否介入了国家间关系、国际政治事务之中)。当我们以这一视角回溯近代以来、特别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跨地区科技流动时,可以看到,科技在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往往也是一种外交成就,科学外交常常起到调解技术、科学知识和物质流通的作用。科技史学者对科学外交历史的研究可进一步阐明推动/阻碍这一流动的机构、网络和实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由此产生的科技与权力的关系,为重新/深化全球现当代科技发展的特征提供新的视角。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科学史/历史学对科技外交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更多地为“西方”观点所主导,倾向于关注欧美参与者的职责、活动和影响,但将“西方”背景和规范作为衡量非西方国家的标准和坐标系,往往会暗中支持甚至强化有问题的价值判断。因此,在STAND的首届年会(5)2019年7月在丹麦玻尔档案馆举行STAND的第一届年会,主题为Diplomats in Science Diplomacy: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聚焦全球议题的基础上,第二届年会的主题为“20世纪中国科技外交史”,更多地关注以中国为中心的科技外交研究——在我们今天称之为科技外交的研究框架下,在20世纪的中国,科技如何在大国外交中发挥作用、国际关系如何影响了科技的跨国流转等问题。这次国际研讨会已于2022年3月19至20日在北京举行,由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与STAND联合主办,包含专家研讨会、圆桌会议和博士生论坛,共有27篇论文在会议上宣读,近5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在读硕博生,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进行了丰富和充分的学术探讨。
本专辑选刊会议中三位作者的论文——作者们来自不同学术机构,专业背景有所差异,其所研究的历史时段、议题也各不相同;但也正因如此,它们互为补充、支撑,共同构成一个连续的观察视角,即通过科技-外交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中国的科技史将收获什么。这些新的叙事将包含哪些角色、过程、区域和活动?这些反思是否会引发对科技外交概念和意义的重新思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静副教授长期从事中美关系史、中美科技外交史研究,本专辑刊出的《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与政治博弈》一文,为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缘起、实践与叙事(1971—1979)”的系列成果之一。论文以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发生与演变为案例,充分使用了中美两国丰富的外交档案、科技档案进行细致解读,从政治博弈和国家权力运作的视角,分析中美关系解冻前后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决策、制度、渠道、形式等多个方面,探讨国家间的政治博弈与“人民外交”(popular diplomacy)、民间科技交流的相互关系,既展现了“科技”如何成为缓和敌对关系的手段而非强化对峙的工具,又揭示出国家、政府、政党等传统政治力量如何对作为跨国交流主体的科学家加以利用并再行塑造。因作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积累深厚,论文呈现了一幅清晰的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图景和中美两国政府政治博弈的动态变化,使我们得以知晓这一时期诸多关于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项目因何进行、如何进行的情况,为中美科技外交史的各个议题提供了完整的政策背景。推荐所有从事20世纪科技史研究者一读。论文所指出的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作为缓和对峙关系的工具而非增强对抗的手段被加以利用,对于我们如何认识、评估当下中美冲突和寻求破解之道,无疑具有高度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与张静所揭示的1970年代中美两国政治博弈与民间科技交流互动的动态图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补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王慧斌助理研究员的《科学为外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对外科学交流(1949—1955)》则是重点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科学家与科学组织为中心,从西方科学国际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所形成的国际主义外交方针、中国科学家的多重角色和身份以及网络三个维度,分析了科学家与科学组织如何成为共和国初期的国际对话者,指出这一时期科学家及科学团体的对外交往常常超出科学本身,呈现“科学为外交”的特点与组织机制。特别是,该文促使我们结合当下进一步思考:作为行动者的科学家和科学组织,应如何制定持续开放的行动战略与策略?换言之,应如何通过网络、组织和活动在国际科学中发挥影响力和汲取有效资源?张静与王慧斌两篇论文,共同揭示了中国的科学外交在不断发展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这些变化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不同时期的大国关系相关。
在科技-外交这一分析框架下,事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人类和平等的非常规知识、技术、物质(如传统的军事科学与技术、核科学与技术、以及新兴的网络技术等)的流动,与常规体系相较是否有特殊性?王默的《科技外交视域下技术科学知识的流动——以中国兵器科学与技术学术谱系的形成与演化为中心》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具有启发性的探讨。该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冷战背景下所形成的中国兵器科学与技术学术谱系演化做了量化描述,建立起不同代际学者的学术合作网络及主题网络,对谱系成员学术成果文本内容所表达的内在知识要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兵器科学与技术在中国得以建立的原因,除了中西间有效的知识流动,更在于知识的本土化过程。由于多种原因,关于非常规知识、技术与物质的交流和国家外交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演化这一独特议题的研究,正在并且仍将继续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但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科技史学者给予更充分、更深入的关注。
综上,三篇论文通过对不同时段、议题的分析,初步勾勒出:在20世纪的中国,科技的跨国交流活动如何具有了外交(政治)性;中国科学家的身份及其组织、活动,如何对科技发展乃至国家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而且,这三篇论文(以及其他更多的相关论文)共同揭示出,科技外交并非始于冷战时期若干大国之间为正处于对抗状态中的两国而创造的建设性对话渠道,事实上,当中国作为国际关系中日益重要的参与者时,科技-外交的互动就已成为20世纪中国科技发展的结构性动力并正日趋加强。
这三篇论文仅为2022年3月会议重要成果的一部分。最初我们选择了七位与会学者所分享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们均极契合本专辑主题且多有洞见,将有助于构成更为连续、开阔的视野来观察20世纪中国科技外交的历史。但因作者在成文时间或发表渠道上另有安排,未得收入本专辑,殊为遗憾。
我们深知,仅三篇论文远不足以揭示科技外交分析框架下的科技史研究所应有的特征、研究径路与方法论,更无法完整呈现20世纪中国科技外交的历史。换句话说,科学外交的历史考察仍处于早期阶段,那么本次专辑的意义就在于引起科技史界的关注与讨论:当审视科学外交的历史根源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正在蓬勃发展的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科技政策研究等诸多领域学者都在思考科技外交在全球科技发展进程中的意义的时候,科学外交在历史上是什么?应该如何从方法上进行研究?目前,科学史家、历史学家和相关领域学者在研究科学外交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和议题,这些分散的文献和学者群体所形成的新的知识网络对于科学外交研究有何意义?期待着同道更深入的思考与推进。
本次专辑得以刊出,国际科学史学会(DHST)科技外交委员会(STAND)给予巨大帮助,特别是委员会成员、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中心Aya Homei和Gordon Barrett悉心阅读所有参会论文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中国科技史杂志》主编和编辑部充分肯定我们申请专辑的计划并给予耐心指导。在此一并表达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