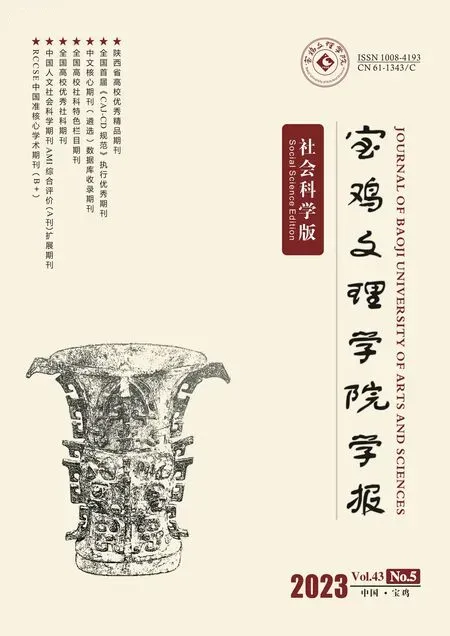《文选》诗“以类相分”本义探析
——兼论乐府作为诗歌题材的依据
王 帅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102)
一、问题之提出
《文选》诗歌部分单列“乐府”一类,收诗41首。一般认为乐府诗单独确立为一类是因为诗歌体式的原因。胡大雷就认为乐府和杂歌之所以能够单列一类,是因为乐府诗“自汉以来人们就视他们与诗不同体”[1](P397-399)。查屏球则认为“前18种以题材立目,后5种以体裁立目”[2]。这些解释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但是仍然有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检阅《文选》,萧统在军戎、郊庙、杂歌、挽歌等类目中均都收有乐府诗,可见,在萧统的心目中乐府单独列为一类绝非诗歌体式的原因。《文选》诗“有些靠题材分类,有些靠体式分类”的解释不符合萧统编选《文选》的实际情况。那么,萧统将乐府单独立类的原因是什么呢?想要彻底探究这一问题,必须对《文选》诗“以类相分”的本义进行探究。
二、中国诗歌的分类标准的演变
在探讨《文选》诗歌分类的标准之前,有必要对萧统之前的诗歌分类加以简要的探析,以了解萧统诗歌分类的诗学背景和理论渊源,进而探析萧统编撰《文选》时“以类相分”的本义。
中国最早的诗歌分类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这主要是依据诗歌的使用功能划分的:《国风》主要侧重于诗歌对于百姓的教化作用。“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大雅》《小雅》虽然偶有士大夫个人情志的抒发,但是其归为一类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讽谏作用。所以《诗大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是宗教、祭祀用诗。“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3](P1)这种诗歌的分类方式,以诗歌的功用为核心,以不同的使用场合作为编排诗歌分类的标准,是我国诗歌分类的滥觞,也是后代诗歌分类的一个基础。
中国早期诗歌的分类主要是依靠形式,特别是以每句诗的字数来区分的。如挚虞在《文章流别论》说:“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4](P190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是按照诗歌的字数分类,但是,“郊庙歌多用之”、“俳谐倡乐多用之”还是侧重于诗歌的功用。稍后任昉在《文章缘起》中也将诗歌划分为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5](P205a-206b)。与《文章流别论》一样,之所以按照字数分类,是因为在当时诗歌的字数与功能是紧密联系的。任昉以夏侯湛所作为三言的起源,以韦孟《楚夷王戊诗》作为四言的起源,以李陵《与苏武诗》作为五言的起源,以高贵乡公所作为九言的起源。[6](P3)这些诗歌今已失传,但是联系诗歌创作的实际,大约可以推测,在任昉的分类体系中,五七言类似于风,主要功用是表达私人情感;四言类似于雅,主要功用是表达政治讽谏;三言、九言类似于颂,主要功用是宗庙祭祀。值得指出的是,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诗歌的字数和诗歌的使用功能与创作传统是密切联系的,而这两个因素正是诗歌题材形成的最重要因素。
随着诗歌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以诗歌体式、题材进行分类的趋势。刘勰《文心雕龙》开始引入以诗歌的体式划分诗歌类别的思想。刘勰在书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诗歌的分类问题,但是在叙述中,还是可以看出刘勰对于诗歌分类的认识:“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7](P65)除了主要以字数分类外,也涉及离合、回文、联句、共韵等体式。但是通观《明诗》全篇,刘勰对于诗歌功用的强调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对于诗歌功用的强调,所以,诗人在同一场合创造的诗歌无论在体式还是内容上,都具有高度的类似性,这就推动某一功用的诗歌,在创作传统上形成一定的惯例,并被后世所沿用,这些因为功能类似而集合在一起的诗歌,逐渐形成了一类固定的题材。编选者们便开始依靠诗歌题材来进行诗歌的分类。
六朝时期,诗歌的分类开始出现依靠题材分类的情况。比如江淹的《杂拟诗》三十首,则开始以诗歌的题材对诗歌进行分类拟作。江淹在这组诗的小序中说:“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效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8](P136)这里的“效其文体”就是诗歌的体式,其中就包含着对于诗歌题材的标榜。事实上,江淹在具体的拟作过程中,按照题材分类的意识是特别明显的。江淹在拟作过程中,就特别强调每首诗所模拟的题材为何,如《魏文帝游宴》《陈思王赠友》等,很显然是将公宴诗、赠答诗作为一类独立的题材。这一点是当时文坛的共识,钟嵘在《诗品》序言中也强调了诗歌在不同场合的功用:“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9](P47-48)在这些场合下,创作出来的不同诗歌,因为功用相同或相似,集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独立的题材。
综上所述,在萧统之前,诗歌分类的思想源远流长。从《诗经》到《杂拟诗》三十首这一序列中,虽然具体的分类标准有细微的变化,但是紧密围绕着诗歌功用这一中心是没有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歌使用功能日趋增多,传统的“风、雅、颂”分类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和个人对于诗歌的需求。江淹《杂拟诗》三十首就开始探讨诗歌功用的分类,但是,这一分类的真正完成,还有待萧统。
三、《文选》“诗以类分”本义探析
在了解了当时的诗学观念和背景之后,我们进一步来看萧统的分类标准。《文选》共收诗443首,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二十四类,历来因为分类过于琐细和分类标准不统一受到批评。萧统在《文选》序言中曾明确指出,自己在编选诗和赋的时候,分类的标准是“以类相分”: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6](P78)
但是,以类相分的这个“类”究竟是什么?既然诗、赋均是以类相分。我们可以先考察《文选》中赋的分类,作为我们研究诗歌分类的一个基础:《文选》将赋分为十五个子目,即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那么这些分类的标准是什么呢?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就是赋的题材:“《文选》将赋体按照题材分为十五个子目……前四类内容上与国家政治典礼有关,可统称为政治讽喻赋……中间六类侧重抒写对社会人生的体认感触,可归并为观览咏物赋……最后五类是情志艺文赋,内容上与人类情感精神有关。”[10]既然赋的“以类相分”是按照题材区分的类别,那么,毫无疑问,诗歌的“类”也就是题材。也就是说,诗歌的二十四个二级类目,就是萧统心目中二十四个平行的题材。
为什么这个分类标准会给后代造成杂糅、混淆的印象呢?这是因为萧统和后代研究者对于题材这一概念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那么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萧统或者萧统所在的时代划分诗歌题材的标准是什么?仔细考察萧统所选的诗歌,可以看出萧统是以诗歌功用为中心来厘定当时诗歌的各种题材,并进行分类的,其标准和方法都是明确而科学的。
而在萧统的时代,诗歌的功用无外乎两个:第一个是公共场合的使用功能,这类诗在目的上侧重于政治和道德教化,以《诗经》为源头和代表,是一种群体诗学观,注重诗歌的使用功能。《毛诗序》中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P1)就是表达诗歌的这种政治功能,诗序之后,孔子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所谓兴,指学诗可“感发”“志意”,提高伦理道德方面的修养。所谓观,是指通过赋诗观察对方志意。所谓群,是指诗能起政治上的团结作用。所谓怨,是指可以来讽刺当时统治阶级,又可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11]孔子的观点被后世所继承,如和萧统同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就提出:“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6](P65)强调诗歌要与自然之理、政治秩序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的场合,自然需要不同的诗歌,而且,这些创作活动往往和政治生活紧密结合,具有非常大的传承性,所以当某种场合下所创作的诗歌达到一定的数量,又都是按照同一种艺术规范,自然就形成了一类独立的题材。仔细分析《文选》在这些类目下所选定的文本,可以看出萧统侧重于强调诗歌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功能。所以,这类题材,在创作过程中都有政教道德的意味:补亡诗通过增补《诗经》来阐发孝成天下的伦理道德;述德诗通过描绘父祖的事功,赞美祖先的高尚道德;劝励诗无论是讽谏他人还是勉励自我,其重心都是在道德建设;献诗一类作品,重点也是围绕着赞颂皇威;军戎诗是为了鼓舞军心,宣扬军威;郊庙诗是祭祀时演奏,歌颂祖先与神灵的乐章;公宴诗是臣下参与帝王宴席所做之诗,中心还是要赞颂主人的德业;祖饯和赠答的创作虽不以此为中心,但是在诗歌中都能体现出砥砺双方不断进德修业的意味。总而言之,这类诗歌题材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场合,但是都围绕着政教、道德这个使用功能。
第二个是私人场景的自我咏怀,这类诗在使用目的上侧重于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以《离骚》诗歌的创作不再刻意强调在公众场合的使用功能,而是向内收缩,侧重于审视为滥觞和代表,是个体诗学的代表,诗歌侧重于作者内心,表达自我的情感。这类诗歌的创作也因为内容和表达方式的传承性形成了一个固有的传统,尤其是首创之人和代表作家的创作,具有非常明显的典范意义,[12]经过后人不断的继承,开拓形成一类全新的题材。所以这类诗歌,在创作过程中都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创作传统,文人创作时自发模拟这一题材首创者的写作方法和创作模式。如咏史大都沿袭班固所开创的“传体咏史”的传统,用诗歌的形式歌咏历史,表达自己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咏怀诗则都是沿袭阮籍所做,用繁复的诗歌意境,表达作者因为政治高压而不能言明的愁绪。总而言之,这类是个题材,和创作传统密切相关,侧重于表现诗人内心的情绪。
萧统为诗歌分“类”,正式以诗歌功用为中心,以上述两种公用场合为具体参照而进行的,是具有非常科学而明确的。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去分析萧统所列的乐府、挽歌、杂歌几类诗歌,就会发现,这些诗歌单独成为一类,并非因为诗歌体式的原因,也是因为诗歌功用的不同而独立成为一种题材的。
四、作为诗歌题材的乐府诗
《文选》收录的四十一首乐府诗,前三首为古乐府,这三首乐府古题的题材,基本可以涵盖《文选》中所见乐府的全部题材范围,接下来对这三首乐府加以分析。《饮马长城窟》: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6](P1277-1278)
李善注解释这一乐府古题为“长城蒙恬所筑也,言征戍之客,至于长城而饮其马。妇思之,故为《长城窟行》”。这一乐府主题所涵盖的题材主要就是“游子-思妇”这样的中心,表现了游子出征在外,思念家乡,思妇独守空闺,牵挂远行的情感。
《伤歌行》一首:
昭昭素明月,辉光烛我床。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微风吹闺闼,罗帷自飘扬。揽衣曳长带,屣履下高堂。东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鸟翻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6](P1278-1279)
这类乐府题材主要通过夜间观看景色,有感于时序变化,书写作者“忧人不能寐”的情绪,诗歌题材的重点在于感物怀思,描写的是诗人对于时光流逝,岁月不再,情感无托,物是人非的徘徊与彷徨,进而表达出自己对于人生和前途的忧虑和迷茫。
《长歌行》一首: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6](P1279)
通过描写园葵从春到秋、由盛而衰和百川东流、一去不返两种自然现象,表达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经验与哲理。具有一定名言警句、人生箴言的兴致。
这三首乐府所描写的题材,为后世乐府继承和发扬,逐渐形成了乐府诗歌中女性、励志类题材。《文选》中所选定的乐府,大都是在这些题材的涵盖下引申、扩展而成的,具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继承《饮马长城窟》的游子—思妇的题材,但是在具体中有所发展,主要产生以下几种类型:1.单纯描写女子对于丈夫、爱人、或故乡的思念之情。如班婕妤《怨歌行》借歌咏团扇,描写自己“失宠,希复进见”的心情;曹丕《燕歌行》其一描写“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的思念之感;石崇的《王明君词》描写昭君远嫁他乡,思念祖国的情感。2.从游子、征夫的角度描写外出征战、行役的艰辛与困难,如曹操的《苦寒行》描写天寒地冻的行军征战场景,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外出游览的侠少形象,《名都篇》描写了一个纨绔子弟,逍遥的浪荡之气。陆机《从军行》《苦寒行》《饮马长城窟行》描写了远征环境的恶劣,进而表达“远征人”的辛苦。
二是继承《伤歌行》的题材,用精致客观的景物描写,抒发无可奈何的生命愁绪和人生悲哀,重点在于哀伤情绪和迷茫心理的表达。曹植的《善哉行》就通过描写上山采薇抒发“忧来无方”的愁绪;曹植的《美女篇》用精致的笔法描写一位美女,最后抒发的还是因为“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而“中夜起长叹”的情绪;陆机《豫章行》表达的是“寄世将几何”的忧伤之感,《门有车马客》仍然是借助热闹的场景描绘突出“慷慨多平生,俯仰独悲伤”的愁绪,《君子有所思》接自己登高所感,抒发“荣华随年落”的愁绪,《齐讴行》铺排洪川、崇山的景色,最后抒发的却是“长存非所营”的人生经验,《长安有狭斜行》描写富饶繁华的都市景色,最终借道路抒发自己对人生前途选择的困惑与迷茫。这类诗歌的特点,都是借助于某一形象的描写,抒发具有普遍性的情感。
三是继承《长歌行》的题材,抒发人生哲理,具有十分浓郁的格言色彩。通过诗歌列举人生普遍的经验,虽然有些描写在内容上与《长歌行》这类乐府有交叉,但是区别在于,前者的重点在于抒情,而这类的重点在于说理,比如陆机的《猛虎行》表达的是“饿不从猛虎行,饥不从猛虎食”的人生经验;《君子行》表达的是“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的道理;《长歌行》借描写时光飞逝,劝谏大家珍惜时间,建功立业;《短歌行》抒发“来日苦短,去日苦长”的人生悲慨。这一类作品侧重于对于人生经验、道理的阐释。
以上可以看出,萧统所选定的乐府诗,在使用功能上具有很大的重合,进而形成了题材上的类似,从而独立成为一种诗歌类目。总而言之,乐府的功用主要是私人场合抒发群体性情感、志向、经验。诗人大多沿袭古乐府的创作传统,敷衍原文,形成了上文所分析的三大类不同的趋向,进而形成了一类独立的题材。
更重要的是这些情感、志向、经验还有一个更加具有区分度的特点——它们不是单独某个人的情感,而是带有非常鲜明的群体性的特征。上述各首诗都能体现出这种“群体性”的特征,接下来,再以《文选》选录的鲍照乐府诗加以分析。仔细品读鲍照的乐府诗,就会发现,这些诗歌抒发的并不是鲍照本人的情感、志向和经验,而是一种群体性的抒发:《东门行》一首采录古诗“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四句成篇,表达的是游子—思妇之间的离愁别绪。《出自蓟门北行》是对曹植《艳歌行》首句的演绎,描写的是“忠良之辈”投身报明主的宏图伟业;《结客少年场行》《苦热行》继承曹植《结客篇》的主题,写游侠的志向 ;《东武行》借助一位老兵的口吻,描写了这一类人“十五从军行,八十始得归”的悲惨经历;《白头吟》《放歌行》《升天行》三首,均是采取古诗中的某一点加以发挥,进而抒发人生哲理和生活经验。这也成为乐府作为一种题材独立于文人诗之外的重要原因。
五、挽歌诗与杂歌诗作为乐府边缘题材的特点
在这样的思路下,再来分析《文选》所收录的挽歌诗与杂歌诗,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萧统对于诗歌体裁准确、明晰的分类标准。
(一)挽歌为文人拟作的乐府徒歌
挽歌类,《文选》收挽歌五首,李善注引谯周《法训》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尸乡自杀。从者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此歌,以寄哀音焉。”挽歌应属乐府,为何独立一体?傅刚在《〈昭明文选〉研究》中推测道:
挽歌属于相和歌……《文选》录缪袭、陆机、陶渊明诸人诗,名为《挽歌》,恐与乐府中的《薤露》《蒿里》也有区别。……似乎当时《挽歌》只是徒歌,不入乐府。抑此是《文选》别立“挽歌”的原因?[13]
除上文提到的徒歌这一点原因之外,挽歌的文人拟作性质也是其单独独立成为一类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些诗歌并不是真正的送葬诗歌,只是文人拟作用来表达自己的哲思。吴承学先生就认为:缪袭的《挽歌》上接《薤露》《蒿里》传统,而开创了文人挽歌文体,这就是以死亡为歌咏主题,以生死为强烈对比,“生时游国都,死没弃中野”,写生之快意和死之悲伤,又极写人生短促,叹岁月流逝之速。[14]如陶渊明的诗: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6](P1761)
描写的重点并不是送葬,而是表达出对于死亡“贤达无奈何”的道理,最后表明“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超然。如果我们结合历史背景来考察,会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在魏晋南朝之际,挽歌已经不再具有传统的送葬意义,而是逐渐转化为文人寄托怀抱、任诞抒情的一种工具。《世说新语·任诞》:“张马粦酒后挽歌,甚凄苦。”[15](P837)《南史》卷三十四写颜延之:“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16](P879)《梁书》卷五十《文学下》记谢灵运曾孙谢几卿与左丞庾仲容:“二人意相得,并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17](P709)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些诗歌都是文人借助送葬这一题材,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抗拒和对死亡的理性认识,所以在题材上也有独立的意义。
(二)杂歌为不配乐演唱的地方歌
杂歌类,萧统共收杂歌四首。杂歌何以单独列为一类?通过仔细对比乐府、挽歌、杂歌三个类目下选录的作品,可以看出原因。第一,杂歌类是清唱不配乐器演奏的乐府作品。这些诗歌多是即席而歌的作品,这是杂歌之所以独立于乐府单列一类的原因;第二杂歌多是作者自己创调、填词的作品,均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接下来结合具体诗作加以分析:《荆轲歌》是荆轲渡易水时激昂而歌之作,《史记》记载了荆轲送别之际的创作场景: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18](P3074)
从材料可以看出,这首歌是不入乐的徒歌。《汉高祖歌》也具有类似的性质,《汉书》记载此歌具体情形: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军于会缶,布走,令别将追之。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上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19](P74)
亦是不配乐演奏的创作。刘琨的《扶风歌》、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乐府诗集》将其收录在《杂歌谣辞》之中,据此推测,应当也是不配乐歌唱之作。除此以外,这四首歌还都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荆轲和刘邦之作,一为燕地之歌,一为沛县之歌,刘琨之歌直接是模仿扶风本地所创作的歌曲,陆厥之作虽无明证,但是以前三首反推之,或许可以断定亦是中山王所辖一地之歌曲。
六、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萧统编撰《文选》时按照“以类相分”的标准对诗歌进行分类。这个“类”的含义就是诗歌的题材。萧统划分题材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诗歌的使用功能,一个是诗歌的创作传统。在当时的文学观念和传统中,这一分类标准是非常清晰的。但是,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这两个标准常常有所交叉,这也给后人造成了分类“含糊不清”的印象。另外,《文选》之所以将乐府单独立为一种题材,乐府类诗歌在创作中形成了游子思妇、格言劝勉等具有特定内涵和使用场景的题材。挽歌与杂歌作为乐府边缘题材,也因为文人拟作的原因而形成创作传统,故而单列成为一种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