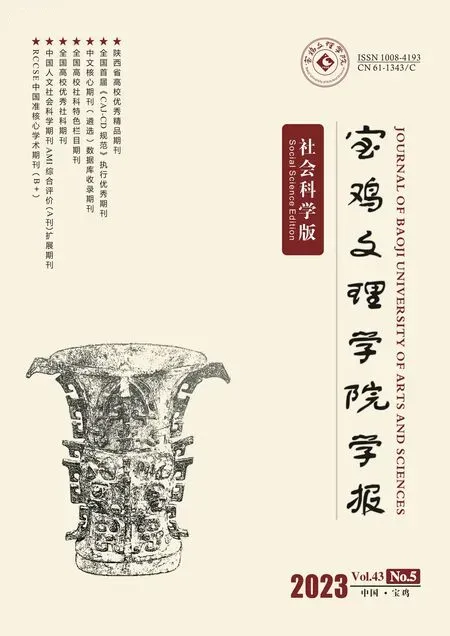远游无穷,近观生面:潘雨廷论船山思想历程
尹江铖,朱舒欣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0)
船山身处明清鼎革之际,而船山研究则在船山易箦近二百年后,方在清末兴起,于建国后渐成显学。若自1865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开始算起,船山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晚清之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谭嗣同、章太炎等士大夫与革命家,皆取船山而论时政、抒襟怀;辛亥革命后对船山的态度渐趋学术,梁启超、胡适、钱穆、嵇文甫、贺麟等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皆致力于反向格义,以西学解船山;1949年建国以后,在“日丹诺夫范式”的影响下,侯外庐、张岱年、萧萐父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唯心唯物论战背景下诠释船山,船山作为古代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备受瞩目。从晚清到建国后的这一历程,被学者称之为“船山升格运动”[1]。但正如裴士锋在论述船山学的滥觞与勃兴时所说:“了解思想史的最佳之道,乃是把思想史摆在人的时空环境里去了解,这个时空环境包含了受自己生命中特别关注之事物驱动的读者塑造文本的意义以满足自己需求的方式,以及他们接下来将之解读并化为行动的方式。”[2](P4)“船山升格”之历程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不同的面貌,然而其本质都是在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拣选船山著述中可供时用的精神与范畴,来回应外来文化的传入,而并非纯粹地关注船山思想本身。
究船山之思想,乃“立身于国破家亡之际,正学于异端泛滥之中”两方面交织共成之结果,不结合“立身”与“正学”两个方面,殊难瞥见船山之衷怀,把握其思想。八十年代至今的船山研究成果宏富而细致,但主要以范畴研究与方面研究为主,略于展现在现实与思想的双重困境中船山所历之心路。值得庆幸的是,潘雨廷作为著名的易学家和道教学家,从易学时空观、三才观、道教身体观的角度,紧密结合船山出入险阻、辨章三教的一生经历,对船山思想的发展加以审视,深入完整地呈现了船山始终追求“行己有本末”,先历地道、天道、人道之“远游无穷”,后经“反身体认”,终归六经而“近观生面”的心路历程。
一、由地道而天道:救世而究理
潘雨廷所谓“天道”“地道”“人道”,是结合时空与三才观念来讲的:“准我国传统的哲学概念论之,重空间犹地道,重时间犹天道,得时空之中,即人从天地之中以生的人道。”[3](P361)地道与天道的关系,就如特殊与普遍、相对与绝对的关系,也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变与常之间的关系。潘雨廷以24岁为界,将24岁以前判为船山矢志“地道”阶段,24至35岁判为船山上求“天道”阶段。
24岁以前,船山秉《春秋》而一心愿为世用,乃潘雨廷所判之“地道”时期。明末内忧外患,学术晦暗。作为有家学渊源的儒家士子,船山早年学在《春秋》而矢志科举,希望秉承《春秋》之道而救国家于危难。他于崇祯十五年(1642)以《春秋》第一中举,时年24岁。中举以后,船山参加熊渭公等在黄鹤楼召集的“须盟”大会,诗有“中原多故,含意莫宣,……天人有策,谁进席前”[4](P229)句,立志呈献当时之“天人三策”,入世救时舍我其谁之意不言而喻。儒家历来认为《春秋》所述乃最客观的纲常名分,是王道之大经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世事变化,《春秋》之纲常何能死执?死执即抛弃时间而困于一隅之空间之中。明理方能论事,对空间的论述必须在时空相即的基础上才能成立。故对《春秋》的理解,必须明白“《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5](P2339)的含义而与《易》合观。在潘雨廷看来,此需超越空间的桎梏,“远游无穷”而后得。三才一体,必须三者俱成立,其中一者才能成立。而船山在“地道”阶段希望理解《春秋》王道之大纲而不能的原因,就在于他尚未经过“远游无穷”,未经天道与人道,故不能“近观生面”。从时空观来讲,这一阶段的船山只有空间(地道)而无时间(天道),更无时空之相合(人道)。故其对《春秋》的理解亦未能达到后期所谓“《春秋》,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纲也。……不以人为进退”[6](P293)的认识。故武夷公虽嘱船山编《春秋家说》,但船山迟至五十岁方得以完成。
24岁至35岁,船山经历国破家亡之变局,思想上求于《周易》,乃潘雨廷所判之“天道”时期。中举当年冬天(1642),船山与长兄同赴北京参加会试。赴京参加会试前他向父亲表明心迹:“夫之此行也,将晋贽于今君子之门,受诏志之教,不知得否?”船山以“受诏志之教”为愿而不以功名为意,但其父武夷公仍然不满意。(武夷公)怫然曰:“今所谓君子者,吾固不敢知也。要行己自有本末,以人为本而己末之,必将以身殉他人之道,何似以身殉己之道哉?慎之,一入而不可止,他日虽欲殉己而无可殉矣。”[7](P219)所谓“行己有本末”,即在广学多闻之后能够出他人藩篱,继往开来而确立自己为学、立身、处世的根本。船山身处国破家亡之际,当殉不殉,“慎殉”也。“必将以身殉他人之道,何似以身殉己之道哉”!待到能“行己有本末”而开六经之生面,方能将七尺之躯从天而祈活埋。然而“行己有本末”乃变中求常,何其难也!船山一生致思核心即在此。
时李自成、张献忠横扫河南、安徽而挺进湖北。船山兄弟路途受阻而于次年返回衡阳。1644年船山26岁,是年崇祯皇帝死,船山作《悲愤诗》一百韵;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船山作《续悲愤诗》一百韵;1646年船山28岁(是年原配陶孺人殁),清军杀唐王朱聿键,船山作《再续悲愤诗》一百韵。是年,船山开始研究《周易》,作《周易稗疏》。由赴京受阻到《悲愤诗》三百韵之作,船山渐觉国事之不可为,从而在思想上由《春秋》而《周易》,开“远游无穷”之端绪。实际上,《春秋》与《周易》的关联,船山应当早就有注意。船山十几岁即从叔父牧石先生读史,岂可不知太史公“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之论?只是当时尚不明其要。国事已无可能,《春秋》之道无法付诸实践,何能不追问其原由?正如潘雨廷所说:“时代既变,《春秋》何用?反之于《易》,正可‘隐’之以‘显’”,“《易》与《春秋》隐现相通之认识,亦定型于是年。而船山之思想结构,自廿八岁起,即在具体体验此二书之实质并旁及一切学问”。[3](P356)船山由《春秋》转而上求《易》理,“远游无穷”而探古今变化之道,这就是他思想进路由“地道”到“天道”的转变。
从28岁到35岁,船山颠沛流离中经历发妻、父母、兄长、叔父等五位亲人的亡故。又经王化澄之害,唯一的抗清希望李定国亦受制于孙可望,船山一再确认国事之不可为。数年两次占卜均得暌之归妹,故有感而作《章灵赋》决意归隐。潘雨廷颇重视船山对这两次占卜的解释,认为船山于这两卦的解释已经不落经义窠臼而能自抒己见。本来暌卦上爻动而变归妹,按暌卦上爻卦辞“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此先猜疑后疑虑尽去之意。爻辞完全符合船山疑虑之情状,如按照爻辞指示,则船山应该受招前往,但船山并没有如此理解。首先,船山从易象的角度,认为暌卦上爻象征宗庙,上爻动则宗庙有变,故国事不可为;其次,船山对“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的疑虑情状进行了过度的解读,认为“豕负涂,难测其不洁之心也”“载鬼一车,其情增人之怪也”[7](P193),而对“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的断言则表示不信任。因此他又取暌卦彖辞“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认为“暌之为道,不苟同而尚别”[7](P194)。综合起来,船山做出了归隐的决定。实际上,虽然采取占筮的方法决疑,但“实为船山自作判断”[3](P358),此即船山“行己有本末”之初步体现。船山作《章灵赋》,实其跳出经义窠臼而返身体会的开始。然而在潘雨廷看来,此时船山虽有“自作判断”之事实,但仍不能认为其已能体会三才中人道的意义。准确地说,尤其不能认为其已能体会“合天地而得生物学的人道(内)”的意义。故潘雨廷说:“(天地之间的人道之理)言之甚易,体之甚难。船山既作《章灵赋》,始一心求之,四十岁后渐有所悟得。”[3](P361)
船山早年一心报效国家,奈何国事难为,数年中四处流亡,亲人相继离世。当此家国内忧外患而又无能为力之时,船山自然会上求“天道”,思考如何在此情况下“行己有本末”。船山“相比廿四岁前之学,有不同的时空结构。凡早年之学,一心愿为世用,犹化时间为空间。今则知明室已不可为,乃不求当世之用而寻究古今变化之理,犹化空间为时间”[3](P358)。在潘雨廷看来,无论化时间为空间,还是化空间为时间,都是对时空的割裂,船山最终达成之内外合一,时空合一之道,于此一阶段尚不能完成。
二、从社会学的人到生物学的人:远游无穷而造化在我
根据潘雨廷的理解,人道需“得时空之中”[3](P361)方能真正建立。但潘雨廷不仅从《周易》时空观、三才观的角度考虑时间、空间的结合以及天、地、人的结合,亦从道教身体观的角度出发,从“社会学的人”与“生物学的人”两个层面理解人自身。因此,人道的建立就不仅是外在的天道与地道的统一,更是由“社会学的人”深入到“生物学的人”,以达成外与内的统一。故潘雨廷以40岁为界,将35岁至40岁判为船山“合天地而得社会学的人道(外)”阶段;40岁至53岁为船山“合天地而得生物学的人道(内)”阶段。
35岁至40岁,船山“远游无穷”而贯通六经,以求人道之常,乃潘雨廷所判之“合天地而得社会学的人道(外)”阶段。船山35岁以前的著作大都是辞章之类,盖因志在世事。自作《章灵赋》决意归隐后一心上求,故此后著作以义理探求为主。潘雨廷谓“此数年间(船山36岁后流亡的几年),贵能不问世事,唯思贯通六经”[3](P358)。这段时间乃船山系统思考六经关系,探究变化之理的阶段,所关注的内容在于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变化,即所谓极物理人事之变,不死守一经一义之定见而贯通六经,此亦船山“远游无穷”之体现。这段时间船山有《周易外传》及《黄书》之作。
潘雨廷认为船山“《周易外传》之可贵处,已得六经互通之旨”[3](P359)。船山将《易》看作“理”的代表,将《春秋》看作“事”的代表,其余《书》《诗》《礼》《乐》则同为“事”的变化。“是故圣人之教,有常有变。礼乐,道其常也,有善而无恶,矩度中和而侀成不易,而一准之于《书》;《书》者,礼乐之宗也。《诗》《春秋》兼其变者,《诗》之正变,《春秋》之是非,善不善俱存,而一准之于《易》;《易》者,正变、是非之宗也。……天下之情,万变而无非实者,《诗》《春秋》志之。天下之理,万变而无非实者,《易》志之。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是以君子格物而通变,而后可以择善而执中。贞夫一者,所以异于执一也。”[8](P1091)以天象征理,以地象征事,理在事中,这是中国传统思想固有之看法。然而“贯通六经”却无可执取之一经一义。船山在《周易外传》广论“神无方而易无体”“贞一而不执一”之意。理不可执于《易》,事不可执于《春秋》,理与事两者都在时空的长河中时时隐现交织。在潘雨廷看来,所谓“贯通六经”在船山那里指的就是天地间“理”与“事”二者的辩证统一在六经中的集中体现。潘雨廷认为,六经之理与事亦自有其时空结构,《易》表天道,为时间,《春秋》表地道,为空间。六经所表之时空有限,“故于显明的世事不应执于《春秋》的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隐在里面的理论亦不应执于《易经》十二篇的文字”[9](P14),此即为《易》“不可为典要”(《周易·系辞下》)的道理。
但人如何能在变动不居的时空之中把握这无方无体变幻莫测之理而“行己有本末”?如何做到“贞一而不执一”?此即如何变中求常,合天地而行人道的问题。于是,船山于38岁又成《黄书》,乃船山反思历史,对如何长保华夏政统所发表的政治见解,阐述的是王道之常。《黄书》之成是船山在六经不可执的变化当中“欲观其常”的结果。然而船山从“贯通六经”到作《黄书》,都只是在外在的有限时空结构中对人道的思索,潘雨廷将其表述为“合天地而得社会学的人道(外)”。但在潘雨廷看来,社会学的人必以生物学的人为基础才能确立,不能“远游无穷”而至于生物学的人,学思始终优游于身外而不切己,如何能“近观生面”而确立社会学的人?此阶段船山尚未能反身体会,故不能真正达成人道之展开。如何合天地之道,通常变之理而“行己有本末”,就成了船山这一时期思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故在《黄书》中船山自己亦感叹:“呜呼!非察消息,通昼夜,范围天地而不过者,又恶足以观其化哉!”
40岁至53岁,船山经“反身体会”,实现了由“合天地而得社会学的人道(外)”到“合天地而得生物学的人道(内)”的转变。按照潘雨廷的说法,40岁以前的船山“时空相须而不可离,故上京道梗而及见明末之时,隐遁观时而复患我有身”[3](P358)。也就是说,船山24岁以前一心用世,为重视空间的思想,犹地道;24岁至35岁觉明室不可为,隐遁观时,“远游无穷”而探索古今至理,为重视时间的思想,犹天道。但时空何可分裂?船山亡家亡国之情,何可真正置之度外?且不论地道还是天道,都需经人道之达成才能究竟。船山想超越时空探究贯通古今之理而不能,故于40岁前渐能体会所谓“身患”。至船山43岁,其妻郑氏亡故,44岁闻桂王被害,南明灭亡。此无异于船山生命中所经受之第二次国破家亡。潘雨廷于此说:“(船山)外景如是,不悟内景之生,其何以游于伯夷求仁之景。”[3](P361)现实客观之“外景”已山穷水尽,无丝毫生意可循。但西狩获麟,元犹未终,天地生生之意,于此时此地需反身体会方可得见。
船山51岁,由败叶庐迁入新筑草堂“观生居”而作《观生居铭》:“重阴蓊浡,浮阳客迁。孰忍越视,终诎手援。物不自我,我谁与连。亦不废我,非我无权。盥而不荐,默成以天。念我此生,靡后靡先。亭亭斯日,鼎鼎百年。不言之气,不战之争。欲垂以观,维自观旃。无小匪大,无幽匪宣。非几蠕动,督之网钳。吊灵渊伏,引之钩筌。兢兢冰谷,袅袅炉烟。毋曰殊类,不我觌焉。神之攸摄,鬼之攸虔。蝝顽荒怪,恒尔考旋。无功之绩,不罚之愆。夙夜交至,电灼雷喧。”[7](P207-208)关于此铭,潘雨廷的解释十分精妙。首句“重阴蓊浡,浮阳客迁”,有学者认为是实写由背阴的败叶庐迁至向阳的观生居[10],不完全准确。因为若这样解释,则与下句“孰忍越视,终诎手援”文意不相衔接,且“蓊浡”一词形容草木茂盛,一副欣欣向荣的面貌,亦非含贬义的房屋背阴之意。潘雨廷则将其与后面的“无小匪大”至“袅袅炉烟”结合起来进行解释,认为“重阴蓊浡,浮阳客迁”乃船山自述静观天地之化的语言,即以自身状况为“重阴蓊浡”,而以时局历史变迁为“浮阳客迁”。所谓“物不自我,我谁与连”者,乃反问之肯定,其意乃物我一体,即庄子“吾丧我”(《庄子·齐物论》)之“丧我”。船山释张子《正蒙·大心篇》有云:“尽性者,极吾心虚灵不昧之良能,举而与天地万物所从出之理合,而知其大始,则天下之物与我同源……无一物之不自我成也。”[11](P144)故此句可直译为:若万物与我不同源,我又怎么能(在认识论上)认识万物,进而(从实践论上)改造万物呢?但万物与我同一,并非完全是对个体的消解,尚有“吾丧我”之“吾”在,故船山谓“亦不废我,非我无权”。综合起来讲,这两句中前一句在解决身患问题,达庄子之“丧我”,孔子之“勿我”(《论语·子罕》)境界;后一句从无我中显示真我,以达个体之真正显现。船山于此之静观万物,即是对事理之辨的体会。
船山于《张子正蒙注》曰:“物之有象,理即在焉。心有其理,取象而证之,无不通矣。若心所不喻,一系于象,而以之识心,则徇象之一曲而丧心之大全矣。……存象于心而据之为知,则其知者象而已;象化其心而心唯有象,不可谓此为吾心之知也明矣。”[11](P145)凡事无非象,象即事;心为理,存象之心非理。故船山以自己之“亭亭斯日”①观世事变迁之“鼎鼎百年”以至于亘古而今,无非是象。象有显隐,理实无穷,关键在于取象而见其理,此亦“远游无穷”之体现。“维自观旃”即同此“远游无穷”之观,到这一步船山才能“大观在上”,于是有“恒尔考旋”之语。履卦上九爻辞曰:“视履考祥,其旋元吉。”“旋”者,返也。此句意在由事、象而返理,“远游无穷”而由“合天地而得社会学的人道(外)”到“合天地而得生物学的人道(内)”。于是船山可以下观上察,透过世事变迁,从时间上的“鼎鼎百年”而见当下空间上的“亭亭斯日”;也可透过受困于国破家亡之情的事象,而见其永恒不息的生生之意。故潘雨廷说:“唯船山于居所静观世事物象的生化流迁之景,是之谓‘成象之谓乾’;观生至此,我身何足以萦我之心,是之谓‘效法之谓坤’ 。”[3](P365)
潘雨廷指出,船山之卓绝处在于他意识到体悟天地“生生之意”仍非究竟,尚余作为主体的人与“生生”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否则天、地、人三才中,就只余天地之“生生”,而人道究竟如何,反而淹没不见了。船山在阐释《老子》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一句时说:“言‘始’者有三:君子之言始,言其主持也;释氏之言始,言其涵合也;此之言‘始’,言其生动也。”[12](P49)意即儒家之阐述“始”,以乾知之生化创造为其意,万物天生地载,而此生化创造必赖人以完成其流行;佛教之阐述“始”,以万法惟心为其意,万法生灭无自体,皆自性之变现,故不可执;道教之阐述“始”,以自然之无为而无不为为其意。船山认为,仅见生生之意则见其体而不见其用,因此“体”也无所附立。佛道泯灭一切道德伦理之用,否定一切人为之造作,人道不彰,故天道、地道均不能立,而“生生之意”遂成虚妄。故船山在《观生居铭》中强调天地虽大化“生生”,却“亦不废我,非我无权”,天地造化,必经人道方可完成。这集中体现在船山《愚鼓词》和其对屈原《远游》的注释当中。
《愚鼓词》撰于船山53岁,分《前愚鼓乐》十首和《后愚鼓乐》十六首。《后愚鼓乐》之四,名为《子时》:“夜半由来非半夜,分明出现眉毛下。心肾无非淫鬼舍,谁厮惹?三更一阵光明乍。万物未生何柄把,天开只在纱窗罅,莫与钻龟还打瓦。鸡鸣也,回头又劝红尘驾。”船山自注曰:“谓有活子时者,将有死子时乎?大桡以前立活字不得。”[13]传说“大桡”为黄帝之师,创六十甲子。道教炼养学说认为,采药炼丹最重活子时。人体在半夜子时左右精炁萌动,为药生之时。“大桡以前立活字不得”意即人的修行以合于自然时间之尺度为要,精炁萌动之时未必是人类所设定的时间观念之子时,而应由人体变化出现的征候为据。人在采药炼丹时身体之自然反应为应该遵循的第一原则,为死子时,而不能以人创设的时间衡量尺度为标准。故潘雨廷评价说:“唯有不变之死在,庶有变化之活。或动辄论不变之非,则变化之是何在。能知子时之死活,获得易理之易简,斯即《周易内传》之旨。”[3](P366)潘雨廷通过对道家修炼的亲身实践,确认天理之常需返身体认,合天地于生物学的人道(内)。
船山“合天地于生物学的人道(内)”,原本只作为抽象理论的三才之道才具体地在“生物学的人”的层面得以确证。人道之成立,“行己有本末”之落实在船山对《远游》的注释中亦得以表达。《远游》本屈原想象自己飞升仙游的作品,内含丰富的早期仙术修炼思想。船山注《远游》之“历玄冥以邪径兮,乘间维以反顾。召黔嬴而见之兮,为余先乎平路。”曰:“气化于神,与天合一矣。然仙者既已生而为人,而欲还于天,故必枉道回执天气,以归之于己。乘天之动几,盗其真铅,反顾而自得,《阴符经》所谓‘天地,人之盗’,勿任天地盗己而己盗天,还丹之术尽于此矣。造化在我,乃以翱翔于四荒六合而不自丧。”[14](P364)反顾身体而自得,“勿任天地盗己而己盗天”,才能“造化在我,乃以翱翔于四荒六合而不自丧”。“造化在我”则“行己有本末”;“不自丧”者,不殉也。潘雨廷评价说:“此非有得于内,殊难道其只字,实即体得《愚鼓乐》之本。……上友古人之道,决不有执于今。”[3](P371)“上友古人之道,决不有执于今”者,“远游无穷”而不局限执着于今日之世事,而所谓古人之道者,即反身体认而得之“三才”思想。
至此,船山方完成由“合天地而得社会学的人道(外)”到“合天地而得生物学的人道(内)”的转变,经“远游无穷”而亲身体悟“三才”思想,真正落实其父“行己有本末”的嘱咐,求得人道之根基。然而,潘雨廷认为,船山由外而内的转变虽确立了人道得以成立的根基,但内外两方面仍然割裂,人道仍需进一步落实。船山思想得以合内外、落实人道的最终形态,即“诚合内外之道”。
三、诚合内外之道:回归六经,近观生面
在潘雨廷看来,船山之“远游无穷”,实际可分为三步:一见六经之贯通,二见三教之同功,三见三教之不同道。船山由“地道”而“天道”,见六经之贯通,由“合天地而得社会学的人道(外)”反身体会,“合天地而得生物学的人道(内)”,见三教之同功;船山于见三教之同功后未尝忘道,而见三教之不同道。53岁而后,其“三教功同道不同”的思想得以确立。最终船山于60岁前成“诚合内外之道”,彻底回归六经以“近观生面”。
船山之辨功与道,出现在《愚鼓词》中:“三教沟分,至于言功不言道,则一也。译之成十六阙,晓风残月,一板一槌,亦自使逍遥自在。”[12](P617)然而何谓“同功”,潘雨廷所论并不明朗。辨析之下,船山所谓之“同功”当有四重意思:第一,寄托;第二,知常达变;第三,勿我;第四,返身回溯。从“寄托”意义上来讲,三教之同功在船山看来首在同为人之寄托。《愚鼓词》在“至于言功不言道则一也”后跟着讲“晓风残月,一板一槌,亦自始逍遥自在”。体会其言下之意,三教所谓同功,就有“逍遥自在”意。道家倡逍遥,佛教求解脱,儒学崇尚孔颜之乐,同在求人生之自由。潘雨廷提到船山于吴三桂反而作《庄子通》,曰:“其思想之悲愤错杂,非庄子之荒唐,何足以慰之。”[3](P367)此即同情地理解船山之以《庄子》为寄托,由寄托而见“同功”。从“知常达变”意义上来讲,三教都有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界以见道之常的思想趋向。对于船山来讲,由地道至于天道,由《春秋》到《周易》的思想转变就在于由变而知常。潘雨廷引明代高僧蕅益大师《周易禅解》之跋语论“知常达变”之同功:“交易耶,变易耶,至于历尽千差万别世事,时地俱易而不易者依然如故,吾是以知日月稽天而不历,江河竞注而不流,肇公非欺我也。……吾亦安知文王之于羑里,周公之被流言,孔子之息机于周流而韦编三为之绝,不同感于斯旨耶!”[3](P389)三教皆有知常达变之旨趣。从“勿我”的意义上来讲,孔子本有“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论语·子罕》)之论,而按潘雨廷所论,船山于《观生居铭》已达“吾丧我”与“勿我”之境,船山“诚合内外”即含“物我一如”之意,物我两相成就,不可偏废。潘雨廷十分重视庄子之“吾丧我”,故能重视船山思想中三教同功之论。潘雨廷以“吾丧我”,《齐物论》之“三籁”,《周易》之“三才”思想合观,他说《齐物论》之“三籁”“犹三才也”[15](P280),“凡吾我相合曰人,吾我相对曰地,吾既丧我曰天,……必达‘吾丧我’之境,庶足以闻天籁。闻天籁者,庶足以齐万物云”[15](P210)。由此亦可深入理解“勿我”之“同功”。从“返身回溯”之至思路向来讲,儒学讲“克己复礼”;道家讲“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道德经》第十六章),“能婴儿乎”(《道德经》第十章);佛教讲“回光返照,撒手承当”(《五灯会元·道揩禅师》)而认取本来佛性。三教皆有反身回溯之思路。在潘雨廷看来,船山思想从社会学的人道而至于生物学的人道,外则上友古人,内则观生生之化,皆为反身回溯之过程。
然而潘雨廷认为:“或有视《愚鼓词》为船山思想之极至,则尚非知言。因功同而道不同,船山见功后未尝忘道,斯为船山思想之精华”[3](P366),“船山的思想结构,首先为明道,道之实指六经”[3](P369)。未深见三教之“同功”,不能见三教“道”之不同;未有“远游无穷”,不能“近观生面”。“远游无穷”是船山思想的时间维度,而“近观生面”是船山思想的空间维度。有“远游无穷”返身回溯之功,而至“诚合内外”之道,才能开六经之生面,此亦是“行己有本末”之训的最后确立。
船山以“实有”释“诚”:“‘诚’者实也。实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实有民彝而不敢不祇;无恶者实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见有恶,不敢不慎也。收视听,正肢体,谨言语,慎动作,整齐寅畏,而皆有天则存焉”。[16](P241)在船山看来,人之内外皆诚,皆为实有。理即实有之理,实有亦有理之实有,故能日新而诚合。“盖天理之流行,身以内、身以外,初无畛域。天下所有,即吾心之得;吾心所藏,即天下之诚。合智仁,通内外,岂有殊哉!”[16](P292)于佛道二教不同,在船山看来不论是客观世界的身体万物还是主观世界的心、情、欲,以及涵摄万物的性与理皆非虚幻,而是实际存在。船山重视“诚”之“实有”,是针对佛道异端摒弃物我之观念来讲的,旨在以儒学之“诚合”,否定佛道之“虚合”。如在对佛教的批判中,他说:“夫于其目,则喜、怒、哀、乐之情,四也。于其纲,则了、知、作、用之灵,一也。动其用,则了、知、作、用之瞥然有矣。静其体,则镜花水月、龟毛兔角之涣然无矣。铲目而存纲,据体而蔑用,奚可哉?故为释氏之言者,终其身于人心以自牿也。”[16](P263)船山认为其只是认取人心之“了知之灵”,没有辩证地认取纲与目两方面,故“终其身于人心以自牿”。
“诚合内外”实即船山“日生日成”的另一表述。“诚合内外”则突出“日生日成”的实有维度;“日生日成”突出“诚合内外”而后人道得以达成的历史维度。船山所谓“日生日成”者,即在心物内外之日日诚合而体现人参天地之变化的作用,开显出具有历史性过程的天理流行。“是故于事重用其所以来,于心重用其所以往;于事重用其心之往,于心重用其事之来。往来之界,真妄之几,生死之枢,舜、跖之分。古之君子,辨此而已矣。”[16](P289)人的作用,就在时空变化当中能自作主宰,“行己有本末”而“参天地之变化”,人何以能辨“往来之界,真妄之几,生死之枢,舜跖之分”而“参天地之变化”?这是船山“合天地而得生物学的人道(内)”已经回答了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曰“即身而道在”故能“行己有本末”,返身体悟三才之道造化在我,自然能随事而宜自做判断。
然而“诚合内外之道”首先仍属理的范畴,是普遍性的常道。对于船山自我人道的成立这一特殊的具体来讲仍然要落实于事。船山“远游无穷”而能返身体悟三才之道,已得“行己有本末”之根本。但国破家亡,历史巨变,已经不能允许他在治国平天下上有所作为。好在“西狩获麟”而元犹未终,世事变迁不妨天地大化之生生。在诸事不可为的情况下回归六经,远游近观而开六经之生面就是船山落实“诚合内外之道”的自我选择。潘雨廷认为,船山自题墓石之“希张横渠之正学”,即在张子能“广释《周易》之指,有大义,有微言,旁及训诂而皆必合于道”[3](P366)。船山于58岁成《周易大象解》,即循张子之路,明“《易》为君子谋”之旨,以在道的层面区别于佛道二教。潘雨廷又提揭船山于59岁作《礼记章句》之初衷,以明其于“远游无穷”后,能辨别三教之同功不同道,彻底抛弃一切固化之成见而开六经之生面:“《俟解》中曰:‘玄家有炼己之术,释氏为空诸所有之说,皆不知复礼而欲克己者也。’是即以礼辨功与道的不同,有其决不可通融的原则。”[3](P367)潘雨廷指出船山一方面批评断章取义之明学:“至于全书之义,详略相因,巨细毕举,一以贯之而为天德王道之全者,则茫然置之而不恤”[17](P1246);另一方面也不满将《大学》《中庸》提出另表之宋学:“知凡戴氏所集四十九篇,皆《大学》《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异视也”[17](P1246)。船山“以《大学》《中庸》二篇,还诸《礼记》,盖已得复礼之志”,足见他能在“远游无穷”后,“近观”六经之“生面”。故潘雨廷论之曰:“其上友古人之志,已由明而宋而汉。且能准诸文献而不为空论,此船山之学所以能高出侪辈而足以挽救明季心学之颓风。”[3](P367)
结 语
潘雨廷一方面从易学时空观、三才观出发,理解船山一生思想之发展;另一方面从道教身体观出发,提出船山“远游无穷”而反身体会,见三教同功不同道,最终方能回归六经并开其生面,可谓真正找到了理解船山之锁钥。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孔子晚年之编撰六经,其意义就在给后人留下能涵泳其中、权衡得道的蓝本。然而《易》不可为典要,六经亦不可执,必须“远游无穷”,才能近观生面,以至于在变动不居的时空当中“行己有本末”而得以立“人极”焉。船山生也不幸,面临国破家亡与异端泛滥的双重困境;船山生也幸,无此空间上的双重困境,则船山亦不能“远游无穷”,以贯通六经、辨章三教,明三教之同功不同道,最终返归六经而开六经之生面。然而潘雨廷作为现代著名的易学家,其对船山的理解并非止于本文所论之“诚合内外之道”,更是对船山于61岁以后“以三才之道归诸易学象数”进行了充分阐发。潘雨廷对船山的评价极高,认为“近百年来早已认识明末黄梨洲(1610-1695)、顾亭林(1613-1682)与王船山三家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船山有其独见,就在重视易学象数”[3](P389-390)。船山“所以重视易学,历四十余年而耿耿于怀者,就在利用易学的整体理论,作为其萃毕生精力而形成的思想结构的核心”[3](P352),可谓切中肯綮。但由于篇幅关系,关于潘雨廷对船山易学象数的认识,只能俟诸来日。不论是对船山思想的解读,还是对其精神的继承与践行,“石船山之是否‘仍还其顽石’,后继者莫不有责焉”[3](P390)。
注 释
① “亭亭”二字在古汉语中有直立、高耸、高洁、威严、遥远、长久等意,综合起来,可见船山所体悟的奋斗不已、生生不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