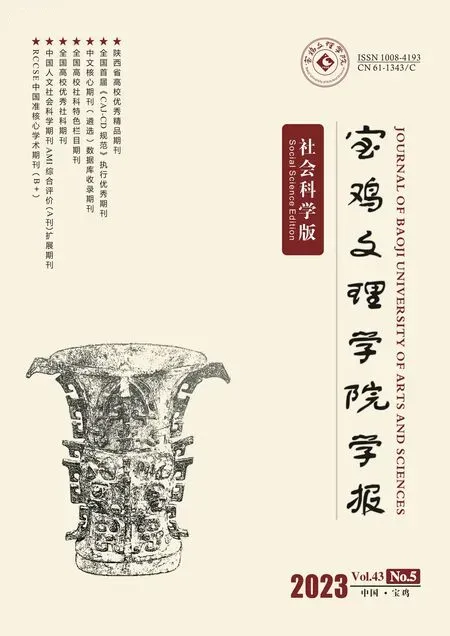影像民族志中文化的诗意书写与反思
王 兰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澳门科技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澳门 999078)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对权威、科学主义、结构等进行了全面的质疑。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人类学领域纵深发展,人类学自身理论也逐渐趋于“反思”,随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写文化”论争。后现代人类学诗学研究者正在寻找一种开放的人类学,用诗学的美学原则,来反思影像民族志在书写中的困境并改造既定范式,从而对人类文化做出更符合主体性感觉、想象、体验的文化蕴含和更富创意的阐释。
从19世纪至今,民族志影像经历了从作为一种人类学的隐形补充到与书写互文的集体人类学实践的自我转变过程,近代电影诗学和电影哲学的发展,加速了这一转向与演变的过程。人类学家和民族志电影实践者,一方面呼吁对影像民族志的研究回归到影像本身上来,即关注影像的本性以及与世界的直接关系上;另一方面,呼吁关注影像民族志作为科学的规范性问题,以及其在新语境系统下引导跨文化群体认知的创新研究上。本文意图从人类学诗学的角度,探讨20世纪下半叶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的诗学转向以及视觉方法上的创新,并反思借鉴这些范式丰富当下的影像民族志创作方式,亦即强调现代人类学电影的书写应该像“诗”,运用诗意去表达呈现田野调查成果和学术思想。
一、本体问题:民族志影像的诗学“真实”转向
诗学反思首先体现在对民族志写作的真实性与科学性的表述上。雅克·朗西埃曾在《影像的宿命》中写道:“真实性是人类学科学研究的本体论问题,它乃是一种如诗之物,但仍需理解它如何以诗意的方式,建立起它自身与它应该建构的文化之间的关系。”[1](P21)因此,从诗学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人类学影像中的真实性,不但能够洞见事实与真相,抵达深层次的真实,而且能挖掘基于视听语言创新的诗学表达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内的学术价值,且具有诗学的“分析性”和“历史性”。
(一)“虚构真实”与“诗意真实”的书写阶段
20世纪60年代的“直接电影”“观察法电影”真实再现了文化样貌,在以纪录片为文本的影像民族志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因为有些社会行为与文化内容是纪实方法的影像民族志难以呈现的,同时面对“写文化”对于人类学实践中“部分真实”话语的质疑与挑战,让·鲁什(Jean Rouch)首先坦陈在民族志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对文化的“描绘”会不可避免地滑向展演,从而进入一种“后真实状态”。基于此,他直接定义了虚拟人类学,开创了“真实电影”和“分享人类学”的理念,他从弗拉哈迪的扮演中汲取了灵感,以坦白人类学家在场和呈现自我观点为前提,遵循拍摄伦理和科学性要求,尽可能地使故事片与真实电影融合起来,使民族志融入“一种由影响力的故事设计出情节的表演”,用“虚构式影像民族志”(或称“民族志虚构电影”)的人类学方法,呈现基于人类学参与而发生的田野场景,展现某种社会文化的基本形态与核心价值[2](P45)。这种“虚构-真实”的范式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真实与虚构以诗学原则进行“编舞”,整体呈现了诗学的解读,使内在世界视觉化,并在人类学领域内展现出无限的学术潜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在当代实验民族志电影中重新获得关注,2006年索伯格在《跨越虚构》中首次创作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虚构-真实”方法,揭示在特殊语境下难以呈现的文化仪式,成为当代主流民族志方法的一种有益补充[3](P44)。进入21世纪后,视觉媒介和数字技术也为虚构式影像民族志提供了更多经验场所,不但基于文化纪实的虚构创作方式在纪录片和影视人类学领域悄然存活,VR民族志电影、文化传承装置艺术、数字影像民俗博物馆等形式更是将真实与虚构诗意般地有机结合在一起。
诗学对真实性探索的另一向度是能够在过于简单化、表面化的文化真实样态背后,呈现出对事件表象之外的文化内在现实的透视和把握。比如为了让不同生活方式的行为被人性地理解,罗伯特·加德纳在自己的人类学电影中,进一步探索了基于视听语言创新的诗学表达原则,他通过叙事和表征上的双重意义,探索了文化诗学的电影创作方式。加德纳的人类学实践更接近于大卫·波德维尔的“电影诗学”原则,他将支配整部影片的形态与动态的“潜在性的基本概念”视为研究对象,诸如叙事方法、支配惯例的范式、跨文化理解的缘由等,使民族志电影的呈现更加像神话、像寓言、像诗,冲破了我们心里萦回不去的“想象与事实”、“神话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从而寻找到内心的“诗化逻辑”。
综上所述,鲁什的“虚构式影像民族志”和加德纳的诗意民族志策略皆是一种对真实性样态的补充,主要作为传递内在世界真实内容的策略而存在。诗学表达的真实直接指向了人类学家的田野感受和观众所产生的感知和体验,虽然它在表达上并非“精确”和“准确”,但这种“神秘”和“暧昧”常常更容易接近本相。当影像民族志的真实性在诗学上被规范后,就会有意识地形成有利于表达的影像范式,这种范式也会逐渐科学化。
(二)“电影通灵”与“时间-影像”的探索阶段
另一方面,让·鲁什受到维尔托夫和超现实主义的启发,通过“电影眼睛”的手段去干扰和激发拍摄对象的表演欲望以及唤起主客体之间的对话关系,用梦境和幻想营造“电影通灵”的状态,借此突破人类学描述的表现和文化边界,抵达深层真实的文化理解。电影眼睛强调只有在拍摄状态,有些真相才会出现。“电影通灵”的状态展示的是人类学家的主观体验与拍摄对象的互动过程,“电影通灵”之后的“魅力时刻”(Grace)才是对日常经验的突破和深层真实的寻找[4](P51)。他的电影创作核心虽然强调与奇特对象相遇时产生的诗性经验,但指向仍然是人类学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对异文化的深层理解。让·鲁什的“电影通灵”是“人类学虚构”实践的理念基础,他试图利用电影抵达文化真实,拷问电影媒介本身的真实性,将电影从叙事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人类学电影更像是现场创作状态的还原,“电影通灵”是对人类学认识论的突破,是对写文化根本性问题的反思。
同时期来自电影哲学对影像本体论的挑战则更加纯粹,涉足电影研究领域的哲学家们认为即便是“诗学真实”或“电影通灵”,依然是对现实某种固化、僵化的形式结果,这种形式遮蔽了现实原初的真实。德勒兹从生命哲学的维度对电影影像重新分类,他认为影像不用借助框架再现现实,也不用把观众插入进来强行打开一个诗意的思想,影像自身亦是与现实贯穿的物质,事物的世界也是一种绝对的运动影像,即生活是一种“元电影”(metacinema)的状态,世界和影像从微观和本体上都贯通在一起,影像不是再现现实,影像就是现实,并以“运动-影像”(间接性)和“时间-影像”(直接性)的方式呈现自己的“生命”[5](P5)。“运动”和“时间”意味着影像自身“生命”两个层面的“褶皱”,相互交织,互为彼此。不同之处在于“运动-影像”是暂且以“湾曲”为中心形成的感觉回路,“时间-影像”则更直接地回归到影像本体的力量。这里的“时间”是“纯粹意义上的时间”,即伯格森意义上的“绵延”,是生命的最原始状态。因此可以说“时间-影像”敞开的就是人类学研究上一直期望企及的最纯粹的“真”。
“时间-影像”是德勒兹电影观的重要思想,他虽然不是人类学家,亦或是民族志实践者,但“时间-影像”的思想解答了人类学最基本的诉求。他将“时间-影像”看作全新电影影像的发端和起点,从“时间-影像”中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了现实。“时间-影像”是“运动-影像”断裂和脱节时呈现出的“纯粹视听情境”,它是深入到影像之下的纯粹的视觉本体,也是世界偶然的、暧昧的,不断生成(becoming)的本真,并呈现出纯粹时间本身能量流动的微观交织特征。纯视听情境不是电影诗学框架内功能性的镜头影像,它是开放性的、充满内在意义的、微观生活最本源的真实,电影所有的大小形式都是基于这种纯试听情境演绎出的固化的框架,因此,时间-影像能够通过摄影机的力量把我们带回更为接近真实的情境当中。德勒兹的电影哲学就是一部诗学,所有的事物即所有的像,它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种新的艺术分析方式,而是重新思考了“活的艺术”对生活真实的呈现。
用“时间-影像”重新反思民族志电影中的真实性,亦可发掘出东西方民族志影像中的不同面向。加德纳和鲁什的人类学电影首先都是从表面的形式中制造了断裂和脱节,把视听形式推到极限(limit)开放的空荡形态,这种空荡的形态呈现出中国美学上“虚”的意境,从而在这种形态背后认识到视听形式无法触及的现实本源。这些人类学电影用摄影机“直击”现实,从而深入到现实的微观感知层面,呈现出现实真实的、碎片的一面。它们集体表现关注现实生活本身的特征,并非导演再现主义的取向,而是要通过平常的日常生活去制造一种“纯视听的断裂”,也只有在麻木的日常影像中才能发现“纯视听情境”下生活的本真。晚近伊朗的民族志电影《樱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1997)《随风而逝》(The Wind Will Carry Us,1999)《坎大哈》(Kandahar,2000)都呈现出断裂的特征,尤其是黎巴嫩导演纳迪·拉巴基在《何以为家》中大量借用分离的空间中断各种“感觉-运动”之间的联系,观众从断裂的影像中间才看到了诗意开放影像的“真”。
相反,东方民族志电影的“时间-影像”是一种“流”(Flow)的状态,民族志电影《最后的山神》《雨果的假期》通过把影像的碎片恢复到自然的状态,使影像呈现出如呼吸、行走一般自然步调的流动特征,这种影像形式超越了角色、叙事等我们熟知的形式,在这里影像就是自然(nature)本身,影像的本体就是生活本真。日本人类学电影常被冠以诗意现实主义的美称,在经典民族志电影《梄山节考》中,今村昌平用“一切都是平凡的、规律的,一切都是日常性的”诗意影像,体现出对东方禅宗意境下“时间-影像”的理解,当影像重新恢复了自然序列中细微碎片的部分、混沌无序的状态,就意味着此时的影像不再是简单的记录和呈现,而是作为一扇窗口重新连接自然与人类的断裂。
“电影通灵”和“时间-影像”都揭示了人类学家、文化实践者、跨文化观众之间的互动状态,这种状态会激发新的电影真相产生,观众能够超越镜像模仿和自我认同,获得真实生活中所不可能获得的新的真相。同时,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承认电影能够激发我们与他者的互动,从而产生文化的深层真实。因此,“电影通灵”和“时间-影像”的诗学思想在人类学认知论上具有长期的价值。
综上所述,影像民族志的诗意绝非来自影像的浪漫化或奇观化,也绝非来自刻板的记录与影像化的复现,而是源于影像实践中虚构与现实之间非对立共存的微妙平衡。“真实性”是人类学家永恒追求的真理,“诗意”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永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对真实诗意的追问表明了文化书写者的自觉和警醒。或许,在诗学的表达下民族志电影能“无限逼近”安德烈·巴赞心中的“真实”,使人类重新“可见”“完整电影”的神话。
二、知识生产:从视觉隐喻到认识论模拟的转向
影像民族志的知识生产方式是在特定认识论的指导下发展出的一套描述和理解特定文化的方法论。西方文化知识型(episteme)的缓慢转变,改变了我们描绘与经验世界的方式,再现系统的主导地位正在被其他视觉界面取代或补充[6](P14)。事实上,一方面人类学诗学也正从强调认识各个民族文化的传统人类学,转向到“认识”本身的问题上;另一方面,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影像民族志也经历了从以视觉隐喻生产知识,逐渐转向用电影模拟人类认知的方式上来。电影被作为一种人类的思想模式“直击”文化现实,这种新的知识表述方式更类似“诗的策略”,而不是知识型的“结构”生产,因此,也可以说人类学诗学其实就是基于人类的内在感知和体验对传统民族志书写的反思,是一场重要的认识论革命,它将导致影像对民族志知识书写的方式随之发生演变。
(一)1.0阶段:可见的符号与不可见的隐喻
克里斯蒂安·麦兹在《想象的能指》中指出:电影符号是一种有理据的“短路”符号,一方面,它的“能指”和“所指”几乎相近;另一方面,电影语言没有最小单位,最简单的形象都具有外延表意的形象,每个单元都传达了一个以上丰富多义的信息,这种意义存在于“大组合段落”之间,这本质上符合了传统诗学的根基,最初跨越对文化整体客观记录的人类学家们便是利用视觉创新的方法,构建起了人类学电影的符号学与诗学。
首先,符号是“细节”,或者说是一种“能指”。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对日常生活实践的象征性诠释。以人类学电影为例,它是一种多层次的人类活动,是一种符号与意义活动,构成了语言、神话传说、艺术、宗教仪式、历史、科技等符号的再现。但米歇尔·杰克逊强调符号再现外在行为和场面只是一种肤浅的文化表象(可见的符号),民族志描述的事实不仅是作为客观存在物的事实,还应该是作为文化存在物的事实(不可见的隐喻)。最先从传统人类学模型向后符号主义人类学隐喻的转向来自于加德纳的人类学电影,在《大河之沙》中,他通过减少和改变解说方式,来探寻人类生存与人类本身的文化本质,并在拍摄现场通过对视觉符号的主动设计,为偶然捕捉到的素材确立了意义呈现上的必然性,用隐喻探究生活经验内部的关联[7](P107)。通过在观察式段落中插入其他画面的方式,寻找隐藏在“表层结构”背后无意识的“深层结构”,用“熟知”的通感而不是描述的形式,达到隐喻引起共鸣。
其次,从蒙太奇与叙事的层面分析,影像中的镜头更像一个个句子,它能呈现出与文字截然不同的非线性结构和非确定性暗示,这也是观察式纪录片很难抵达文化真实的原因。诗意人类学电影离不开对蒙太奇的依赖,比如加德纳偏爱通过生活的多义性来架构的结局和多义性的主题,经过投射在外部形象之上会引起不同文化阶层观众的共鸣,正如麦克杜格曾说过视觉媒体可以通过“暗示、形象共鸣、认同和视觉转换”的方式来营造叙事悬念和动机,进而创造隐喻,因此在诗意的电影中,不管原来的语境如何,它都有能力超越这个语境,并且能延伸到新的、普遍的语境中。人类学诗学入影,它们本就可以共享人类学的主题,呈现不同方式的隐喻,这些隐喻相互影响扩大,继而产生共鸣。蒙太奇的隐喻运用深刻影响了当代民族志电影的创作范式,在此基础上,人类学家结合影像光线色彩、拍摄技法不断创新隐喻和转喻,更深入地探索结构上的可能性。
最后,影像能凭借“视觉性”中可见和不可见的双面性,同时勾画出既“被展现”(可见的)又“被遮蔽”(不可见的)的自我民族志图景,揭示隐藏在民族文化背后的“不可见”。“被展现”与“被遮蔽”同属一个存在,有些东西被展现了,同样就有某些东西被遮蔽了;反之,某些东西被遮蔽了,肯定有些东西就被展现出来。被展现同时也被遮蔽体现了符号诗学阶段文化书写的三个基本含义:一是通过事实的表象来把握深层的意义,从想象与虚构的叙事中体察被遮蔽的真实历史,即“以观察到的现象来反映无法观察到的真实”[8](P130-131)。二是通过塑造民族文化的过程,呈现出民族志影像自我展现与自我遮蔽的文化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审查”的过程。三是以“人类学诗学”的视角反思人类学电影如何书写(展现与遮蔽)自我民族志中的“可见与不可见”,本质也是为了寻求一种满足人类自我认知的可能性路径。
(二)2.0阶段:电影哲学的模拟认识论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现实主义电影虽然可以在可见与不可见的形式之间,自由且诗意地再现真实的文化景观,但现实永远是被提前安置在一个预先设置好的电影框架(Framing)之中,这种框架可能是默会的视听语言符号系统,或是导演潜移默化流露的风格与形式,皆是期望将导演自己的诗意共鸣极力传递给观众。相比电影模拟认识论阶段,影像直接呈现主观世界的转变最先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跨文化实验电影中,受到俄国形式主义电影和格里尔逊学派纪录片的影响,先锋人类学家们尝试创新对于人类精神世界影像表达的渠道,期望跨越蒙太奇的力量和符号化的隐喻,为观察到的现实赋予新的视角,加德纳晚期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这种特征。他的《极乐森林》在形态上完全放弃了“信息完整性”的人类学电影守则,用缺少文化信息的留白,挑战人类学属性,效果上指向了非语言类的主观感受,影像打破视听媒介邀请的规则,甚至迫使观众去体验,通过对经验世界的拆解、切断和暂停,唤起观众“神秘”或“暧昧”的感知体验[7](P109)。虽然在信息层面上可能导致模糊,但却能传达出深层次的真实,这对生活碎片化的诗意呈现超越了真实记录的主观表达,能够通往超现实主义的诗性意境。
另一方面,随着电影哲学研究和《写文化》中传播认知的转向影响,人类学知识生产体现出认知科学和现象学的特征。以德勒兹为首的电影哲学启蒙者批判结构主义的民族志诗学影像并没有直接触碰到现实,他们认为纯粹的影像现实不是用电影现有的语言去破译现实,而是用摄影眼模拟人类第一次看到现实的方式去“直击”现实,真实不再是被重现或复制,而是让摄影眼和现实碰撞,用原初的眼去触及现实,用现实之力和影像之力撞击后的散漫、省略、游移或飘忽不定的形式“直击”一个有待破译、一贯暧昧的真实[5](P11)。这样对电影再现现实的哲学反思,不是仅仅是将电影的重心从形式转向内容,从实验的游戏转向对现实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对电影创作乃至对电影认识论彻底性的革命,同时也重新为影像民族志的知识生产打开了全新的思路,拯救了民族志电影奄奄一息的生命[9](P71)。
受到电影哲学和民族志诗学实践的双重影响,2006年,卢西安·泰勒(Lucien Castaing-Taylor)发起的感官民族志实验电影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感官人类学研究的转向,突破了界限分明的主体论和文本论,把思考的能力还给影像本身,侧重于用一个整体的方式去认识真相。英国肯特大学教授穆雷·史密斯(M)更是将这样的实验电影比喻成“认知假肢”(Cognitive Prostheses),上天入海的摄影和虚拟技术发展拓宽了人类的视力范围,并且逐渐转化为一种人直接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不仅改变了影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人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民族志纪录片《利维坦》(leviathan)中,泰勒把Go-Pro安置在飞翔的海鸟与颠簸的渔船之上,它所展现的视觉语言并非某个人的主观视角,而是一种代入式的“电影眼睛”,手持拍摄造成的晃动与不安,也传达出电影深层的结构与情绪,拍摄完成后的人自然的停顿和抽离,无意识地传达出了空洞和虚无的情绪。
总之,对比不同时期民族志知识生产方式上呈现出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加德纳诗意表达的意象体验带有明显的主观特征,是自己对文化群体的诗意观点。让·鲁什则期待通过“电影仪式”表达出自己对于拍摄对象世界的经验和感触。相反,以泰勒为代表的模拟认识论民族志则更为直接和野蛮,它与直接电影范式的不同,体现在人不再作为“中心”性的逻辑存在,将实践的过程从有形的可见的视听符号建构起的秩序空间,退化到无形、动荡、混沌的真实世界中去,抹去了人造成的价值间隔,没有预先设置和安排的结果模拟了人类第一次与现实相遇的诗意经验。这种范式在强调特定语境中个体感知重要性的同时,表征了一种通过感官触觉和隐喻诗学获得主体间性知识的方法。
三、方法反思:电影诗学观的民族志诗意探索
文章最初,笔者阐释了影像民族志在文化表意实践过程中的诗意探索与转向,可见西方人类学家对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方法的探索,没有仅停留在传统的“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研究,或现代诗学的“文化结构”研究层面,而是同时呈现出了对影像本体的关切和演绎等诸多特点。而中国影像民族志的创作范式仍比较保守,这需要我们学习西方民族志的创新与反思精神,尤其是从现象学的视角结合电影研究理论,创新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影像民族志方法。
(一)发挥影像自身的本体力量
近年来,随着电影媒介本身的发展和大众娱乐业的兴起,互联网成为民族志影像的主要传播渠道,视听和叙事成为影响民族志影像的结构性力量,甚至现代数字虚拟技术开始进入民族志影像的实践领域,这些现象提升了民族志影像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但也削弱了影像作为严肃人类学证据的地位。另外,大量的民族志影像充斥着“文化拾贝”的表达,也因缺乏文化脉络被批判为以娱乐为导向的“文化大餐”[10](P51)。面对纷繁复杂的现象,许多中国学者都试图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追问,什么才是我国现阶段正确的民族志实践、什么才是我国民族志电影合适的表达方式与严谨的书写范式。
笔者认为,一方面目前应先放弃将经典的范式框架置于当代影像民族志表征现象之上,相反是要基于人类学原则,对文化当代传承的电影机制提出建构性和调节性的经验性认识,以理性和经验结合的方式展开对民族志电影自身的技巧、本质、规律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充分挖掘和发挥影像自身的本体力量。正如前文中加德纳、让·鲁什给予我们的启示,希望透过影像指涉“真实”,制造一种更加彻底的、直接诉诸观众的元电影效果。实现影像民族志中文化的诗意涌现,要超越影像长久以来作为人类学研究媒介的模式,在影像本体与电影机制之间阐释所研究的社会文化,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不要纠结于文化理论的框架,而是应该回归到创作实践的具体语境,集中分析影像形式的本体和背后的人类学观念依据,真正关切当代民族志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创新影像的演绎方式,进而总结诗意探索的方法。总而言之,将当代影像民族志的创作置于理性和经验之间,从研究方法上体现出对电影艺术自身的关注,通过“诗意”搭建经验与逻辑之间的桥梁,对文化内与跨文化艺术创作原则进行的理性与经验的探究。
(二)探索观众心理认同的表达方式
民族志影像是创造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一直被寄望统一或弥合认同问题之间的对立关系,我国当代的民族文化即呈现了两个轴向上的认同问题:一是空间上体现为个体离散与群体记忆之间的动态关系,二是时间上体验为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伦理批评。[11](P247)这种复杂局面对影像民族志的文化表述提出迫切要求。认同首先来自认知,个体认知来自历史的记忆与当下的感的互动,决定这种能够感知的技能或价值判断来自历史记忆的塑造,即高层次的历史记忆系统会影响和指导低层次的知觉解释,因此认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诗的过程和诱导的过程”。但是电影诗意的产生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观众认知所建构所“赋予的”,正如大卫·波德莱尔在《后理论》中强调的“诗意是观众基于历史记忆和当下感知互动作用的结果”[12](P43)。换言之,诗意是建立在视听形式系统的引导下,来自于观众主动认知建构的动态过程,并且观众诗意化的认知过程是流动的,是与外部环境(审美变迁、电影工业等)持续具身交互的过程。
因此,从历史记忆与当下感知两个层面出发,笔者认为,首先为了借以诗的策略引导并敞开一个语境,中国影像民族志应该实现两个层面上的转变:一是实现现象学的诗意书写策略,需将宏大的认同问题重新置于日常生活实践中进行呈现和思考;二是通过主体性的激发提供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鼓励完全不同气质和特征的文化主体继承和改造既有文化(乡土文化、群众文化、历史文化),甚至以流行的形式对文化进行呈现,同时将以微观观察为手段理解社会事实的影像文本都纳入民族志影像的研究视野。其次,要基于人类学原则,对能够充分呈现中国文化的民族志电影的各种材料(如情节风格、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进行主动把握,探讨调动观众情绪,产生心理认同的电影机制。
综上所述,当代新型的影像民族志应该像“诗”一样运思,在田野中诗意表达“真实”,才能在不同气质和特征的文化主体之间唤醒本民族的共同记忆与传达生命意涵丰富的普同情感。通过从人类学诗学的理论视角探讨反思影像民族志书写的文化表意实践和创作观念,既能生成有意义的符号学范式及基于影像本体的批评话语,构建影像民族志自身的价值体系,又能在很大程度上为未来诗意影像民族志书写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