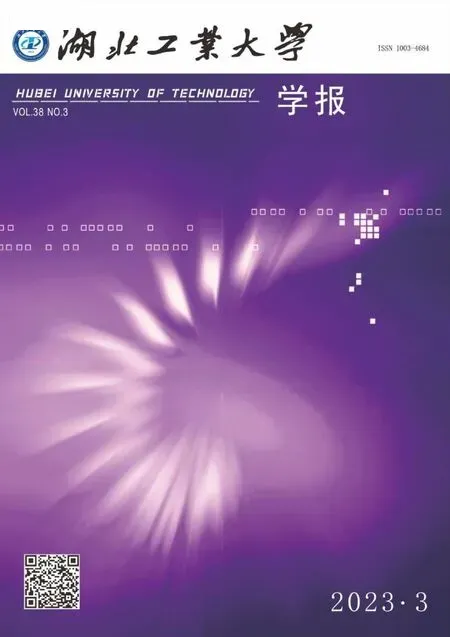霍译《九歌》的审美再现
李芸叶, 彭家海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翻译的审美再现关注的是译者尽力传达或重现原作的“原滋原味”[1]。《楚辞》具有极高的美学理论价值,“从美学史的维度看,《楚辞》于中华美学的重要意义,是开创了具有中华美学的浪漫传统。”[2]《九歌》系《楚辞》一组祭神诗歌,战国时期屈原融汇楚地的民间祭歌创作而成。学者何长文(2001)指出《九歌》于巫与圣两种文化因子的并存互渗、相摩相荡之下,体现出迷狂与理智相融并存的独特审美趋向[3]。无论是在内容、风格、或是艺术境界上都打上了巫风的鲜明烙印,巫风是促成屈原作品“深广的审美空间”“最有价值的元素”[4],是屈原文学创作灵感的来源所在。全诗审美意识深刻,主要审美特征包括:(诗歌)节奏之美,背景之美,意象之美,境界之美,抒情之美。通过不同译本的对比分析,可一窥译者的审美把握和文化取向。
1 刘宓庆翻译美学理论概述
中国的“翻译绕不开审美,翻译学绕不开翻译美学。”翻译美学理论,就是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对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原语、目的语)、审美主体(译者)和审美关系的研究,对翻译中审美再现手段及翻译美的标准等的探讨。[1]基于中国传统美学译论,刘宓庆(2005)在他的《翻译美学导论》一书中构建了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系统地论述了理论的渊源、研究范畴、价值和任务,将中国的翻译美学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也为国内外译者探究译作的审美价值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继而他又将翻译的语言审美划分为: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两个层面,前者即语言的物质形态审美构成,侧重语音、词语、文字、句段层的审美信息;后者即语言的非物质形态的审美构成,着眼于“意”与“象”、“情”与“志”及超文本意蕴。这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呈现原作的审美价值,译者要兼顾译作的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尽力传达或重现原作的“原滋原味”。
2 《九歌》英译研究
《九歌》系《楚辞》最具“神奇瑰丽色彩”[5]的一组祭神诗歌,流传至今已逾两千年。虽然相关英译研究起步较晚,却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6]。1852年,国外首位从事《九歌》传译的学者费兹曼发表了《<离骚>和<九歌>:纪元前三世纪的两篇中国诗歌》,开创了《九歌》英译的先河。其后,英国剑桥大学的汉文教授翟理斯(H. A. Giles,1845-1935)于1884年出版了《山鬼》的英译本,由于缺乏对原诗背景的深入研究,这一译作未能引起译界广泛重视。直到20世纪中叶,《九歌》译介随着韦利译本和霍克斯译本的相继问世有了历史性的突破。1955年,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九歌·中国古代巫文化研究》(TheNineSongs:AStudyofShamanisminAncientChina)一书发行,全书(《国殇》、《礼魂》两篇舍弃未译)除诗歌英译外,还补注了对各篇内容的研究考证,譬如对巫术(Shamanism)、祭祀仪式、地理背景等的阐释,深化了译入语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汉学家霍克斯汲取并发展了其师韦利的研究成果,他的代表性译作《楚辞:南方之歌》(Ch’uTz’u,TheSongsoftheSouth:AnAncientChineseAnthology)以楚巫文化为切入点,是包括《九歌》在内的《楚辞》全译本,堪称迄今楚辞研究领域“学术性与文学性”“最全面、最权威的著作”[7]。之后的一些译者如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沃特斯(G.R.Waters),大卫·辛顿(David Hinton)等也都积极参与到翻译的队列中来,为《九歌》的传译提供多视角的研究贡献。
在国内,最早致力于翻译屈原作品的是翻译家林语堂,1929年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楚辞》的英译本,他还与国内译者、海外华裔译者共同翻译了《楚辞》的若干篇目,《九歌》自然也在其中。其后,1953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Yang,1953)合译并出版译作《楚辞选》(SelectedElegiesofTheStateofChu),忠实原文,多用归化的翻译方法是杨戴译本的主要特点。基于诗歌翻译的“三美论”(音美、意美、形美),译者许渊冲(Xu,1994)出版了名为ElegiesoftheSouth的《楚辞》英译本。另外,随着《九歌》译本量的增多,译界对译本质的标准也在提升,在前辈不懈探索的基础上,卓振英(Zhuo,2006)、孙大雨(Sun,2007)、杨成虎(2008)等译者精益求精,力求最大限度再现诗歌中的审美价值,助推译本的对外传播。尽管各种译本瑕瑜互见,但是,“走在前面的巨人们弘扬了中华文化,探索了翻译的路径,为产生更好的译作准备了条件。”[6]
3 《九歌》的审美特征
诗歌是精炼的语言艺术,是最高级的文学形式。《九歌》组诗融楚人巫祭、舞、乐与唱词为一体,全诗辞藻华美,想象奇特,展现了多方面的审美特征。
3.1 诗歌的节奏美
楚辞本为楚地的歌辞,经屈原等人创作而成诗歌的一种体裁——楚辞体(也称骚体、赋体),虚词“兮”字的使用是楚辞体的重大特征。其诗行参差错落,语言隽永凝练,音韵灵动和谐,继而促成了诗歌的节奏美,使人读来铿锵悦耳,极富音乐美。学者葛晓音(2004)在<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一文中指出《九歌》十一篇的三种基本节奏类型[8]依次为“三X二(三兮二)”型,如“登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三X三(三兮三)”型,如“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二X二(二兮二)”型,如“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音段节奏鲜明。
3.2 诗中祭祀神灵的背景美
背景之美既指良辰——时间美,又指美景——空间美。以《九歌·东皇太一》为例,“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首句描绘楚人精心挑选良辰吉日,以祈东皇赐予福祉的心态;“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典雅的语言使得人的感官都感受到审美的存在,祭品如兰蕙琼芳、瑶与玉瑱(视觉),桂酒椒浆(视觉、味觉),祭舞如“抚长剑兮玉珥”(触觉),祭乐如“五音纷兮繁会”(听觉),祭服如“灵偃蹇兮姣服”(视觉),其香如“芳菲菲兮满堂”(嗅觉),浓郁的香气充满神堂。因而诗歌中精心营造的良辰美景给读者以无限的审美想象空间。
3.3 诗中的意象美
所谓“意”(image)与“象”(symbol),是指作家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物、景、境)的结合,或情之于文的“投射”(projection)[9]。屈原在《九歌》中创造了相当丰富的意象群,植物意象譬如“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中的香草石兰、白芷、荷及杜衡,动物意象譬如“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中的麋鹿、蛟龙及马,以及众多的神灵意象,如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少司命、山鬼等,这些意象的共同特点是:具外在形象美,也具内在涵义美。例如屈子笔下的山鬼美貌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一位婀娜多姿、笑意盈盈的女神就跃然纸上了。“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是内在美的表露,石兰、杜衡皆是品行高洁的象征,山鬼将自己佩戴的香草作为爱情的忠贞信物赠与思慕之人,实则是屈原借内外美兼具的神灵形象表达了自己的忠君之情。诚然,屈原对诗歌中的意象不是简单的欣赏,而是以一种强烈的审美精神与它们往来,香草美玉、日月星辰、山川河湖、巫鬼神灵......仿佛都变成了可以感知的对象,它们将美奉献于他,与他对话和交流,而他则调动着一切感官,乃至想象将他们充分地吸收和内化[9]。
3.4 诗歌的意境美
屈原将自己抽象的情感寄寓在具体的意象中生成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并借助联想、夸张、象征等手法“营造出一种特别的幻化空间”[10]或“升华为一种审美境界”[11],此为意境。在诗中,诗人的想象不受时空的局限,往古现实可以会于一瞬,上下求索可在须臾之间,通过对巫鬼神灵世界的丰富幻想,屈原“创造了《九歌》绮丽、神奇、朦胧的诗歌意境”[11],在幻想的神话世界里畅游,与神相会,折射出诗人追求自由、浪漫不羁的精神世界。
3.5 诗歌的抒情美
诗是情感的外化,《九歌》组诗的抒情主人公多为神灵,但除首篇《东皇太一》中有描绘人神相愉的热闹氛围,其余各篇都或多或少透露着诗人的愁绪。王前程(2009)在<屈原被疏与《九歌》抒情的个性化>一文中得出结论:《九歌》深婉哀怨的抒情格调与屈原遭受君王疏远时的心境十分吻合,乃是屈原的政治抒情之作[12],貌似求爱神灵,实则影射屈原求君,“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引发了无数读者深切的情感共鸣,足见其抒情的审美特征。
4 《九歌》英译审美信息的再现
4.1 形式系统
4.1.1语音层面语言审美能有效催动翻译审美过程的积极运行[1]。诗歌中的语言审美与语音层的音韵、节奏感息息相关。许译诗歌的音美、形美优势明显,尽力再现了原诗的语音美。霍译无韵律限制使得译文更显灵活,拟声词的传译准确再现了原诗的审美。
例1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山鬼》
许译:“Thunder rumbles, oh! rain blurs the eye; At night apes wail, oh! and monkeys cry. Winds sigh and sough, oh! leaves fall in showers. Longing for you, oh! how to pass lonely hours!”
霍译:The thunder rumbles; rain darkens the sky; The monkey chatter; apes scream in the night; The wind soughs sadly and the trees rustle; I think of my lady and stand alone in sadness.
例1出自《九歌·山鬼》,诗人将雷、雨、风声以及猿、狖哀鸣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衬托山鬼思念心上人的愁思,尤以五个拟声词“雷填填”、“雨冥冥”、“猿啾啾”、“风飒飒”、“木萧萧”刻画了一幅孤寂凄凉的山林夜景图。除拟声词外,用韵巧妙,前两句压ing韵,既起到强化诗歌韵律美和形式美的作用,吟唱起来又似乎有愁绪的绵延感,与诗人抒发的情感一致。且诗句起伏有致,诗歌节奏感分明,实际上这是《九歌》节奏类型的充分体现。此处为“三X三(三兮三)”型的节奏,即以两个三言词组的连缀,以虚词“兮”为句腰的诗体节奏特征。在三种节奏中,“三兮三”型是节奏感最强的一种[8]。
与汉诗不同,英诗以韵律(metre)、轻重音节的交替(一个重读音节和一个非重读音节构成一个音步(foot))而形成诗行(verse line)抑扬或扬抑的节奏(rhythm)。许译本和霍译本较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的审美信息。许译的特点是音美、形美优势明显,可读可唱,和《九歌》亦诗亦歌的性质是吻合的。全诗节奏有所变化,主要使用抑扬格(iambic),在句首的扬抑格营造出一种低沉的氛围感;韵律为aabb式,压尾韵(rhyme)“eye”和“cry”,“showers”和“hours”,压头韵(alliteration)“sigh”和“sough”,富有音律、节奏美。然而“译者一旦决定译诗的押韵词,译作的选词灵活性和自然程度必定大大折损,所调用的韵也会不尽人意(转自赵彦春,2021)。”[13]相较于许译,霍译采用英诗格律译汉诗,无韵律的限制反而使得译文更显灵活。译文为无韵诗体,主要基调节奏为抑扬格,加上拟声词的生动传译如“chatter”,“scream”,“rustle”,“rumble”以及“sough”来渲染雷、雨、风声以及猿、狖哀鸣之声的气势,大有可取之处。
4.1.2词语层面词是承载语言审美信息的最重要的基本单位[1]。译者在传译时,往往会挑选出最贴切的词语来描摹事物或者传达内涵。而文化负载词[注]带有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民族风情、饮食习惯等有一定关联(Baker,2000)。作为特定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译文选词会呈现不同的审美信息。霍译注重保留汉语诗歌文化负载词的内涵,可见译者的文化取向。
例2 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大司命》
许译:I control light, oh! and shade with ease. The people know not, oh! what I will do.
霍译:A yin and a yang, a yin and a yang;None of the common folk know what I am doing.
例2凸显了楚人对于神力的崇拜——大司命操纵人世间的阴阳顺逆,普通的民众无从知晓。其中“阴阳”概念抽象,属中国古代哲学两个表对立统一的范畴,老子《道德经》言:“道生一,一生二”,这里的道即一,二即阴阳二气,“壹阴兮壹阳”指代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之理。由于许多文化负载词是中国特有的表达,在译入语中鲜有对应词汇,一些译者不得已牺牲原文的内涵传译,于是诗歌一经翻译,就损失了其某种特定的风味。许译本通过意译的翻译方法将“阴阳”译为“light ”和“shade ”,易让西方读者理解,但却削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并不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同时,许译将屈原诗作的特色词“兮”字用“oh”译出,可见译者的细致,但《九歌》全篇“兮”都译为“oh”破坏了诗句的连贯性,也不够准确,有诗体僵化之嫌。学者周正东、张政(2019)认为翻译应该是引进新文化新思想的过程[14],实际上霍克斯在其译本正文就有大量关于《楚辞》的历史背景及相关文化负载词的解释性文字,因此他选择在译介中忠实原作,积极保留原文化内涵,两次强调“a yin and a yang”,较好地再现了原诗词汇承载的审美,传播了中华文化。
4.1.3句段层面句段的审美信息即行文的审美信息。译文中对仗、重复、对比、省略、倒装等句式大都有审美立意(音美、形美或意美)[1],有利于强化语言的形式美和感染力。许译、霍译都较好地再现了译文句段层面的审美信息,但霍译第三人称的切入视角淡化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
例3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
许译:Wordless you come, oh! wordless you go, As cloud-flags spread, oh! and whirlwinds blow. None is so sad, oh! as those who part; Nor so happy, oh! as new sweetheart.
霍译:Without a word he came into me, without a word he left me; He rode off on the whirlwind with cloud-banners flying. No sorrow is greater than the parting of the living; No happiness is greater than making new friendships.
学界一般认为少司命是掌管人间子嗣及孩童命运的女神。这段诗的大致意思是:少司命降临、离别人间之际缄默不语,乘着旋风驾着云旗飘然而去之时才不禁感叹,悲啊,最悲不过生别离!乐啊,最乐不过初相知!这两句对比句作为千古绝唱,不但贴切地传达出少司命对离别的态度,还概括了人际间的感情。后两句诗的抒情承接前两句叙事而来,逻辑上紧密连贯,形式对仗工整,语言真挚,对比自然。从整体而言,许译语言尤为简洁,如名词“cloud-flags”对“whirlwinds”,动词“spread” 对“blow”,形容词“sad”对“happy”等,利用译文整体的形式美提升审美效果。再如首句倒装句“wordless you come, oh! wordless you go”,尾句省略句“Nor so happy, oh! as new sweetheart”仅七个词传达原诗信息,并以“you”第二人称切入增强诗歌的感染力。许译保证了译文的形美和音美。基于对少司命的考证,首先,霍译将少司命视作男神,由诗中的主人公第三人称“He”可知;其次,霍译在结构和内容上也尽力忠实于原文,利用重复、对比、对仗、倒装等句式凸显原诗的审美立意,如末句对比句“No sorrow is greater than the parting of the living; No happiness is greater than making new friendships”。然而诗歌的本质特征是抒情美,“物之感人”,“感物起情”(钟嵘,《诗品》),以第三人称视角英译虽然便于客观叙述,但似乎违背了诗歌抒情美的特征,拉远了和读者的距离。
4.2 非形式系统
4.2.1“意”与“象”层面意象是诗歌的灵魂,一方面,意象既折射出诗人的审美理想,另一方面,它又隐喻深刻的文化内涵。相对于许译,在保留诗歌意象层面,霍译较为出色。
例4 荷衣兮蕙带。——《少司命》
许译:In lotus dress, oh! a belt at the waist.
霍译:Wearing a lotus coat with melilotus girdle.
诗歌意象的传译是评价译文质量的标准之一,然而《九歌》中灵动的植物意象隐喻很难为西方读者感知,在译入语也没有完全对等的表达,不过如果译者采用补偿手段译出诗歌意象,那么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传译。例4“荷衣兮蕙带”指神女少司命着荷衣,佩蕙草于腰间。荷之出淤泥而不染,蕙草芬芳怡人,诗人以“荷”与“蕙”两种意象来象征女神高洁不俗的精神品质。许译直译“荷”这一意象,“in lotus dress”似乎能让我们感受到少司命少女一般的生动活泼,但许译忽视了“蕙”的意象,使原文的意象美打了折扣。霍克思力求传达原文意象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弥补传译时产生的文化缺失现象[15]。在他笔下的少司命是男性神灵,着女性裙装显然不合适,故译为“a lotus coat”传达了荷的意象;他所译“蕙”意象为“melilotus”,豆科草木樨属类植物。有学者指出“蕙”指代兰花科植物蕙兰[14],但据史料证实,《九歌》中楚地的“蕙”即蕙草,豆科零陵香属植物,而非蕙兰。所以,蕙草与“melilotus”有些许相通之处,尽管霍译未能完美体现出这一香草意象的内涵,但在忠实于诗歌意境美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反映了译者的文化取向。
4.2.2“情”与“志”层面诗言志。不少脍炙人口的中国古典诗歌几乎都是以景抒情,以情述志,情、景、志交融一体的。从翻译美学的角度看,对情感的把握和内蕴分析是自始至终的语言审美活动的关键。[1]霍译与许译贴切地再现了《九歌》原诗的审美信息。
例5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国殇》
许译:Their spirit is deathless, oh! although their blood was shed; Captains among the ghosts, oh! heroes among the dead!
霍译:Their bodies may have died, but their souls are living; Heroes among the shades their valiant souls will be.
“屈原的作品情感充沛,然而也不只是一堆感情,它有思想”。[2]《国殇》——颂悼楚国阵亡战士的挽歌, 刻画了战争的壮烈场面,也升华了英雄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的主旨。“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意思是:英勇献身的楚国将士神灵永不泯灭,他们的魂魄永远是鬼中之雄杰。此二句作为诗的结尾可谓气势雄浑,动人心魄。许译选用倒装句,上句“Their spirit is deathless, oh! although their blood was shed”,增译了战场上将士抛洒热血的画面,把将士们的精神永存放于句首有利于突出歌颂英烈的主旨。下句借用韦利的译文,“captains”与“heroes”对仗呈现更凸显出“生当作人杰(man of men),死亦为鬼雄(soul of souls)”的英雄气节。霍译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上句“but”之后“their souls are living”是译者强调的内容,下句“the shade”英文释义为“the spirit of a dead person or a ghost”表达了“鬼”的含义,“heroes”则表达了“雄”的含义,在译者看来,战争的悲壮和英雄视死如归的气节引发人类的共情共鸣,无论以什么语言传译《国殇》,都无法阻挡人类对它的欣赏。[15]
5 结束语
综上,研究发现,在形式系统层面,许译尽力展现审美客体的音美和形美,主张使读者感受到美,文化和乐趣[16],这也是刘宓庆先生所说的“审美体验上的愉悦”[1];在非形式系统层面,霍译关注译文的意象美和情志美,更倾向于保留原诗审美信息及意象。总体而言,两位译者在译诗时虽各有取舍,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九歌》中的审美信息,尤其是霍译取得了较理想的翻译效果。通过不同译本的对比分析,可一窥译者的翻译功底和文化取向,进而启发译者更好地展现诗歌的审美特征,传播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价值。
——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